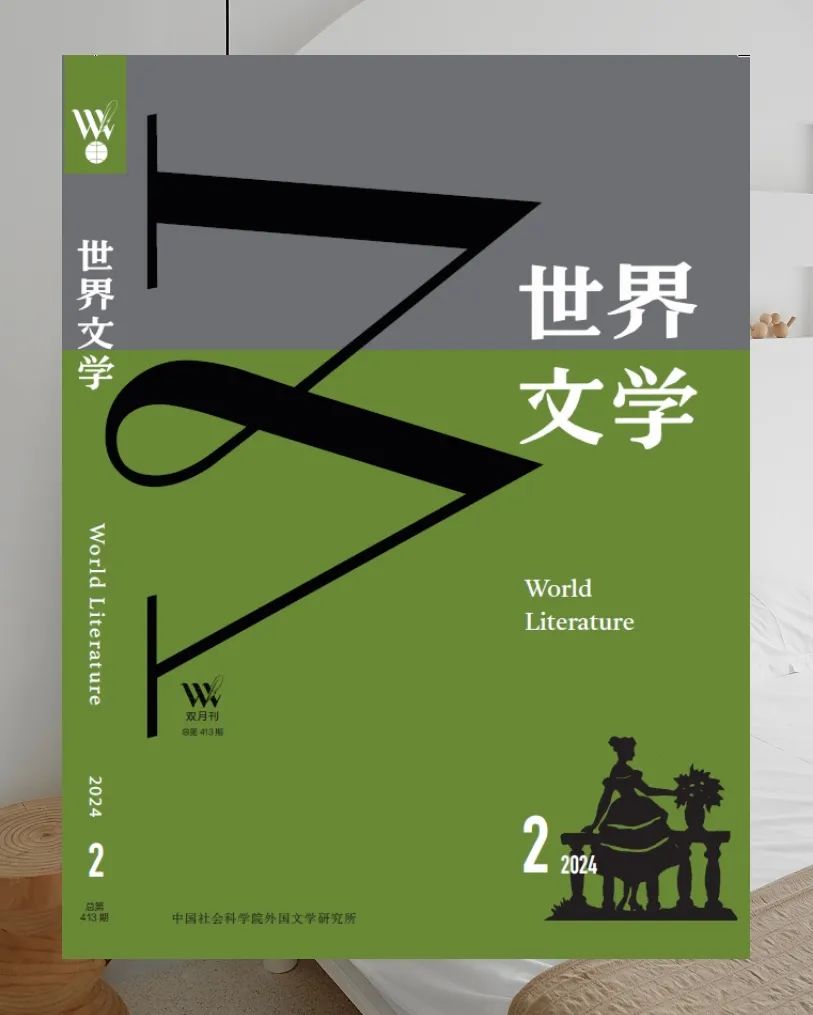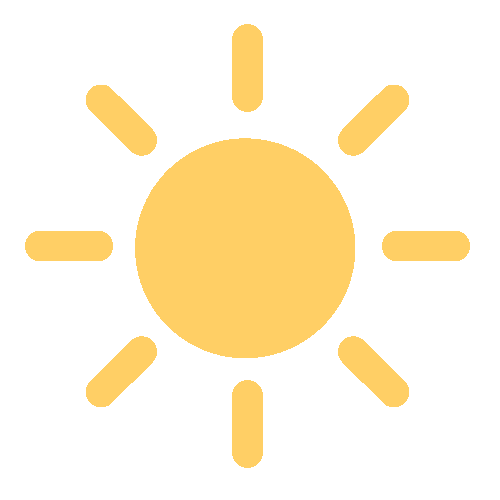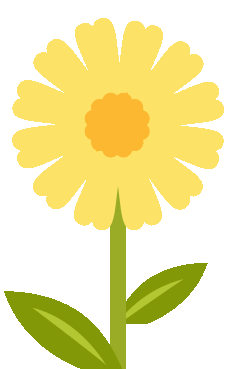第一读者 | 艾•纳瓦罗【西班牙】:记事/纪逝
![]()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这些记忆一度被埋葬在自己的海马体里,不过是童年或少年时代乏味生活的余音:母亲给她的面包抹上苦橙果酱,清洗她的红色舞鞋,送她去公交车站。从前的那些春天,一大家子人还时常聚会的时代,聊的都是老生常谈,听起来却那么生动而年轻,母亲的歌声又会盖过大家的闲谈。她每点开一个帖子都像发现一个宝箱,里面装着遗失已久的珍爱之物,一旦被人触碰,还会震颤着发出嗡鸣。
记事/纪逝
艾尔维拉·纳瓦罗作
方伊秋译
手机上跳出一条新消息提示。黑白照片的一角。秀气的鼻子,半边脸颊。眼熟的耳廓线条。她并没有看见整张脸,却还是忍不住反胃。还有那个昵称:阿佩普·奥特音。她感觉胃酸在往上冒。
她素来不喜欢假名,不过,此刻的焦灼倒不是因为这个。惴惴不安了五天,她才终于点开手机里的“脸书”图标。不安变成了惊恐:显示在她面前的,是两周前过世的母亲的面孔。她反应过来,这个用户昵称倒过来拼写就是母亲的名字。阿佩普·奥特音=佩帕·涅托【主人公母亲的名字在西班牙语中拼写为Pepa
Nieto,该账号用户名为Apep
Otein,是将组成母亲名字的两个单词分别倒序拼写】。
照片拍摄于七十年代,她敢赌上一只胳膊,这张照片从未离开过客厅的柜子。而且,唯一能接触到那些相册的人,也就是她的父亲,绝不会在“脸书”上开设一个账户,用妻子二十七岁时的照片当头像,用名字的反向拼写做昵称。除非他疯了。
她观察了父亲好几天。他看起来是正常的居丧中人,克制着沉痛的心情,形单影只,会因为没在妻子平时忙活的房间里见到她的身影而面露困惑,似乎他的认知还没有接受这一变化。她确信父亲不是在账号背后捣鬼的家伙。
阿佩普·奥特音没有好友。个人主页里只放了一张佩帕·涅托的照片,其余一片空白。她想,或许这个人只给自己发了好友申请。她没有接受,却也没有拉黑对方——她渴望查出这一灵异活动的幕后主使,而且,母亲的照片和那倒写的名字传递出微妙的气息,击败了她的理智。
自从前男友的现女友来骚扰过她之后,她就把“脸书”上的“仅好友可见”功能打开了。当时骚扰她的账号显示的性别为男,她想不出是谁,那段日子一直活在会被当街袭击的恐惧之中。等她后来发现原来是个疯婆子,简直要笑话起自己来,尤其是笑话自己的恐惧。
如今,又用上“骚扰”这个词令她害怕,仿佛用了这个词就会一语成谶。以前她太鲁莽了,以为恐惧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小事,这一次,她开始担心,是不是某个至高的力量正摩拳擦掌,要教训一下她的冒进。
她一度指望收到某条信息,以此确认阿佩普·奥特音的账号背后真的是个危险分子,擅闯她家并从相册里翻出了那张照片。
要知道,那可不是随便的一张照片,而是几百张母亲的照片中她最钟爱的一张。小时候,她曾经满怀憧憬地端详着它,一看就是几个小时,仿佛母亲的神采都浓缩在一九七五年的那一天,尽管那时自己尚未出生。整整一个下午,她就这样陶醉着,展望着自己的未来:细细端详着照片,确信自己将来也会长成母亲二十七岁时的样子,拥有和她如出一辙的五官,线条柔美,不再像当下这般更像要往父亲矮胖粗笨的方向发展。直到五年级,她都仍然幻想着自己会变成照片里母亲的模样。
母女情深的幻术在她步入青春期后宣告失效,憧憬变为怨恨,她开始极度排斥在自己身上看见母亲的影子。母亲生前的最后几个月,她还申请出国交换,躲在科研的清净地里,竭力避开器官衰竭、吸着氧、骨瘦如柴的母亲。
令她害怕的威胁信息并没有出现。阿佩普·奥特音依然没有好友,个人主页依然空空如也,仿佛这个账号只是为了存在而存在而已。
她琢磨着这件事有没有更怀好意的解释。或许是洛丽姨妈搞的鬼,姨妈就喜欢用古怪的方法纪念故人,有那张照片也不奇怪,不对,这个想法行不通,按照洛丽的个性,不可能不事先知会一声。
她开始尽量少去访问对方的主页。过了几个月,她决心放手不管了。又过了些时候,她偶尔再去看看,还是老样子,一片荒芜。空白的主页,没有一个好友。停摆的账号,一如她长眠的母亲。她点击了“接受”。
她点开那张用作账号头像的照片,注意到照片底部有上传日期和时间。二〇一一年七月七日清晨六点。那一天那一刻,她的母亲在她的外祖母和教母的陪伴下死去。当时,她正在母亲病床旁的沙发上睡觉,被叫醒的时候,护士已经接到通知要把尸体转送至太平间了。
最后的那天,清晨,母亲命垂一线(那天是周四,从周一起,母亲就喘着粗气,奄奄一息),而她体力不支瘫倒在沙发上。教母为她盖上了被单。布料覆上她肩膀的温柔与平日里母亲弯腰为她盖好被子的温柔别无二致。这将是她最后一次亲身体会到这样爱怜雏鸟般的柔软。她眯了一会儿,直到教母把她叫醒,告诉她母亲过世了。那一刻,她心下明了,方才,是母亲借教母之手,柔情万般地为她盖上被单。那是母亲的告别,亦是最后的守候。
她在“脸书”的帮助中心里查找可否更改上传内容的日期和时间。一番折腾之后,她震惊地发现,数据是不可更改的。两夜无眠,她决定告诉父亲。父亲正在电视前打发时间,他耸了耸肩,不以为意,有人在他妻子去世的确切时间点用妻子的照片和倒着拼写的名字开了个账号,在他看来像是件稀松寻常的事。
父亲的无动于衷让她感觉更糟了。她反复核查那张头像照片的上传日期和时间,不出一周已然强迫成瘾,每过五分钟就要点开一次,急于抓出漏洞,那副样子,简直像是把自己的命都押了上去。这是一场俄罗斯轮盘赌,结果是她出现严重的恐慌症,只得去诊所打镇定针。她矮墩墩的父亲绝望地看着她,像是在失去了妻子之后,又要目送女儿离开。她无法向父亲坦白是那个“脸书”账号让她崩溃。她也没告诉上门来诊疗的心理医生。面对他们,她羞愤难当。
医生给她开了一种药,能产生近似摇头丸的效果。要阻止她继续沉迷阿佩普·奥特音账号,这算不上是个好办法。她变得异常兴奋,认为自己每天去那个账号巡礼一番并非为了验证照片上传的日期和时间,而是为了证明自己能承受住眼前的一切。


又一次,她重新开始寻找答案。她想到几种离奇却并非完全不可能的情况,每一种都含有一定的偶然性。例如,某个专门盗取他人身份的小偷闯入她家翻拍了那张照片,这样他在网上能假扮的人就又多了一个。这个变态小偷总是挑选最好的照片,最美好、最幸福的时刻,还有最富情感意义的物品,用这些东西在虚拟空间里一点一滴留下他人的印迹。而且,这些印迹只有展示给受害者亲友看的时候才能发挥作用。她还设想,会不会是家族里某个深爱她母亲的人,得知母亲在医院里生命垂危的消息后,痛苦、愤怒、茫然或者单纯是对死亡的惧怕交织在一起,五味杂陈,冲动之下注册了那个账号,而这恰好是发生在他深爱之人离世的那一刻。她心想,若是如此,那个给她发了好友申请的人,等他哀悼的心情平复以后,恐怕会为当初疯狂的举动感到羞赧或是把此事完全抛在了脑后。在药物的作用下,以上假想更像是麻醉剂,她借此获得了一种万事已然真相大白的虚假秩序感。
虽然有药片,她的平静还是在七月七日母亲一周年忌日这天再度碎裂。她和父亲准备在那天上午去墓园给佩帕带些花儿。早上醒来后,她打开“脸书”,看到阿佩普·奥特音发布了第一条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条动态更新:一张泳池照片。她一眼认出了弯弯曲曲扭成数字“8”形状的泳池外形,还有深蓝色的油漆,石灰外墙,金属栏杆。
那个泳池在她七岁之前住的房子里,俯瞰科尔多瓦【西班牙南部城市】的原野,还能望见一条穿过整个村子的国道。照片上只有平静的泳池水波,别无他物。色调和她父母保存的那些拍立得照片相仿,但她记得自己没有在相册里见过这样一张只拍了空泳池的照片。
这张照片把她带回到一个傍晚,即将入夜,她和母亲泡在水里,空气微凉,身上却是暖暖的。母亲做了奶酪三明治,她们在泳池里一边吃三明治,一边悠然地摆动着双腿。泳池边的台面上还留有夏日骄阳的余温,她们从水里出来,就地躺下,听着外面公路上的车子来来往往,猜想开过去的是大车还是小车,面包车还是拖车。
她很确定阿佩普·奥特音发的照片就是那天拍的:她和母亲穿着湿漉漉的泳衣看日落,空气中弥漫着蓝莹莹的消毒水味儿。难以置信。她家一直都是父亲负责拍照,但是那天父亲出差了,她和母亲的相处状态才会如此特别,令她铭记至今:那是她和母亲的二人世界,什么也不用做,只是共度时光。
去墓园之前,她翻箱倒柜地找相册,还问了父亲是否拍过那个乡下房子的泳池。她一问出口,就觉得自己犯傻了:父亲从来不拍空镜照片。
“可能是你妈拍的。我没有印象。你问这个做什么?”父亲回道。


父亲已经差不多从丧妻之痛中走出来了。他开始和网上认识的女人约会。没有一段能坚持超过两三个星期,但他不以为意。她想,要是自己非要喋喋不休地跟他说有个家伙老拿存放在家里的照片冒充母亲,这会让父亲新近的快乐单身汉生活变得不是滋味,于是忍住了没说。
中午十二点,父女二人迈进了公墓大门。他们挑选的墓碑朴实无华,上面刻着一个不起眼的十字架,要仔细看才能看见。旁边的墓碑上尽是浮雕字母和沉重的铜制十字架,相比之下,这样质朴的风格显得格格不入。闷热的墓园里空空荡荡,正午的暑气笼罩下来,墓园和里面的一块块墓碑形成一个遗世独立的现实空间,只有石块,寂静无声。至于到底是哪个鬼魂或者疯子正在网络空间里复活已故之人,眼下再去想这个无疑是虚妄又无端的。此地只有坟墓掩埋着白骨,还有父亲的悲伤。近来,他渐渐地更多是为了自己的衰老(而非其他)悲伤。
“你今天要去找路易莎吗?”她问道。路易莎是父亲正在约会的女人。
“今天不去了。”父亲回答道。
他把一只手放在妻子的墓碑上,几枝百合摆放在碑前,那是他们从镇上最好的花店里买来的,不过等到晚上估计也就蔫了。
她控制不住又去看了阿佩普·奥特音的账号。那个页面依然保持着奇怪的沉默,自己依然是唯一的好友。她把抗抑郁药的剂量加了倍,整整四十八小时,氟西汀侵入血液,她无视时间早晚放肆大笑,懒洋洋地想着那张泳池照片。等她的状态终于稳定下来,奥特音的主页又发布了新的照片。
照片里,母亲躺在担架上,旁边是救护车。父亲正握着她的手。是从俯视的角度拍的,拍进了街道、车子、担架员,还有奄奄一息的佩帕·涅托——当时母亲已经下定决心,在那天下午入院,在医院里死去。她记得这一切,不是因为见过这张照片,而是因为她亲眼从客厅窗户里看到过这个画面。“最后一程了。”父亲告诉她这是母亲在救护车上说的。母亲往她这边看了一眼,面色既不难过也不害怕,因为无论是要做出难过还是害怕的表情都得用力,而母亲已经一点劲儿都使不上了。
她想过这张照片会不会是某个邻居拍的。只是,她家往上的两层住的只有几对老夫妻,看起来不像是会费心做这种事的人。而且,即便他们会干这样出奇的事,她也十分肯定,照片里的画面只可能存在于自己的脑海:那是从她家客厅向外看的视角。照片定格的瞬间,正是母亲望过来,看见她从窗口里探出头,并认出了她。

从那一刻起,她意识到阿佩普·奥特音的主页上出现什么内容都是可能的。确实如此。那上面后来发过两条音频:一条是母亲在唱歌;另一条是母亲在看她最爱的《窈窕淑男》【1982年上映的美国喜剧电影】,看得哈哈大笑。还有许多照片:母亲常去的餐馆,住过的酒店房间,家中的客厅,去吃下午茶的法式甜品店,摘录在笔记本上的谚语,逛过的服装店橱窗,做过的菜……每一幕都对应着母女二人共同经历过——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她跟着母亲经历过的场景。这些音频和照片是她脑海里的碎片。唯有她的记忆能如录像机一般刻录这一切:刚出锅的炖菜,永不缺席的粉白相间的桌布,店铺的展示橱窗,牙医的候诊室。这些画面大都仅仅留存于她的记忆,有两段确实拍过照片,如今躺在她的旧手机里:一张是她在VIPS餐厅【西班牙的一家连锁快餐店】和母亲大吵一架之后的情形,另一张是在太平间,母亲的尸体在装殓后被摆在柜子里:裹尸布遮掩不了骨瘦如柴的身形,脸上没有一丝一毫的表情,嘴被粘合剂粘上了,一点儿不像活着的时候,也看不出死亡追上来的那一刻是什么样的。她拍这张照片是因为姨妈嘱咐她要为死去的母亲留个影。
“你不拍的话,以后会后悔的。”姨妈说得斩钉截铁。
她原本没有这个意愿,但她还是迷信的,而且一直觉得姨妈拥有一种独特而玄妙的智慧。她把手机相机对焦到横卧着的尸体身上,按下快门。她来来回回看过这张照片,心无波澜,也想不出这张尸体纪念照将来能有什么用。后来她换了新的智能手机,这张照片就留在老机子里了。
她不止一次用心地在网上搜索过逝去的家人。最经常能搜到的是一位在二十九岁时过世的表兄。他生前的工作与软件安全相关,因此一度活跃在各大计算机论坛。她读着那些探讨专业问题的帖子,从表兄像做手术一般严谨精密的发言中感受他的存在。家人呼唤他名字的声音回荡在她耳边,她重温起大家共度的假日时光。在全家人都去避暑度夏的那个小村子里,白色的街巷纵横交错,她总会在大人还在午睡的时候就跑去表兄一家住的房子,叫上他一起骑着自行车穿梭在街头巷尾。她也搜索过自己的祖辈,在搜索框里输入曾祖父的姓名,还有那几个在战争中丧生的叔公的名字,想要找到一点遗落的信息,比如某些古早档案中的记载。当然了,她一无所获。这样的空白令她惊讶,她本以为互联网包罗万象,定能纾缓她的怀旧之心,一解求知的欲望。母亲去世后不久,她搜索了“佩帕·涅托”,想知道,除了衣柜里的衣服、鞋子,除了书籍、面霜,以及刷牙杯里那根牙刷以外,母亲还留下了什么?几乎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家医学院的网页上出现过这个名字:有母亲在哈恩市【西班牙南部安达卢西亚的小城】做学术报告的海报,获得儿科医生资格的公示,还有宣布她调任科尔多瓦的公告。


阿佩普·奥特音上传了一条新音频。那是父母之间的一次激烈争吵,她亲眼目睹过。音频再现了那场吵架的尾声,母亲大叫着“放开我,婊子养的”,接着是摔门的声音,还有更多打斗的动静和尖叫。父亲把母亲反锁在房间里。在音频里,她听到当时还是小女孩的自己在哭——她被关在另一个房间里,周围一片漆黑。
要知道,母亲尤为擅长惹人厌,父亲则恰恰相反,是个善良、正直且沉着的人。那次吵架是极为稀有的反常情况。听到自己孩童时期的尖叫令她胆战心惊。她想,阿佩普·奥特音的行事方式和母亲生前一模一样,不惜戳人伤口,去追逐某些可能永远无法如愿以偿的东西。她为此感到遗憾。不过,接下来的几天,这个账号不再折磨她,转而继续发起了轻松愉快的日常照片,甜美得叫人生疑。她不禁暗暗揣测,母亲是不是想用这个账号来颠覆女儿的记忆,让她只记得自己和母亲联袂主演的那些场面,让她的过去满满当当全是亡母的身影,同时,删去她的个人经历中所有母亲不在场的画面,仿佛如果没有母亲的亲在和指引,她的人生便不复存在。
这个猜想使她心烦意乱,她决意彻底忘却阿佩普·奥特音。她坚持了三个礼拜。而后,前功尽弃。她又把鼠标的光标移到那个名字上,急迫的手指微微颤抖。没有更新。她点开那张自己在母亲过世后拍摄的照片:陷在裹尸布里的脸,深色木棺,花圈。
在强迫自己不要去看那个幽灵账号的这段时间里,她产生了一种别扭的依恋感。那堆杂七杂八的照片和音频撩拨着她的心弦,她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渴盼着每一段有关母亲的全新回忆重现天日。这些记忆一度被埋葬在自己的海马体【位于大脑皮质下方,负责存储转化短期记忆和长期记忆】里,不过是童年或少年时代乏味生活的余音:母亲给她的面包抹上苦橙果酱,清洗她的红色舞鞋,送她去公交车站。从前的那些春天,一大家子人还时常聚会的时代,聊的都是老生常谈,听起来却那么生动而年轻,母亲的歌声又会盖过大家的闲谈。她每点开一个帖子都像发现一个宝箱,里面装着遗失已久的珍爱之物,一旦被人触碰,还会震颤着发出嗡鸣。
有段时间,她被禁止访问该账号的主页,这令她无比心焦,就像小时候,她在放学后爬上通往房间的楼梯,急切地想见母亲一面。迎接她的却是一扇上了锁的门。母亲总是把自己锁在卫生间里。她感到恐惧,大喊着“妈妈!妈妈!妈妈!”却又知道对方并不会开门。就像此时此刻,她也被阿佩普·奥特音的账号拒之门外。她又来到这个可恶的账号,点进主页,犹豫了几秒,写下一句尖叫着的留言:“妈妈!”



其后,是沉默,是她自己的情绪爆发。她为母亲的缺席而恸哭,同时又死死地盯着屏幕,焦急地等待母亲出现。直到她从错乱中冷静下来,主页上依然无事发生,这叫她讨厌又担心。
接下来的几周,一个新帖子都没有,这个账号像是已经完成了使命。一天下午,阿佩普·奥特音的主页上出现了一条新笔记,是一篇文章。那是母亲在接受第一次手术之后为抗癌协会写的征文。佩帕一直把文章的手稿和曾祖母留下的银制蜥蜴镇纸、一枚钻戒和一个胸针保存在一起。她读着母亲的记述,母亲写下这篇文字时的恍惚感与自己此刻阅读它时的眩晕感彼此交织、重叠。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在这里。只看见到处都是管子。
我听到的第一个声音是有人在说话。是男的还是女的?那个声音让我动动腿,抬起来。右腿没反应。我小心翼翼地把手探进被子,想弄明白是怎么回事。我摸到了绷带,一直裹到肚子上。左腿上没有绷带。我迷迷糊糊地想,这两条腿怎么不一样?我是不是瘫痪了?手术已经做完了,但是当时的我对此没有记忆。我不知道过去了多久。我时不时地试着动动右腿,忽然有一天,我发现绷带不见了。
我吃力地用余光打量着四周。我仍然动弹不得。我的身上接了这么多机器,我一定是快死了。死了也许更好,眼下的种种煎熬,不值得。回顾这一生,我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与其说是人生,不如说更像是大梦一场。我无比平静,一定是镇静剂的功效。虽然脑袋里一团浆糊,我还是察觉到自己不是病情最严重的。隔壁床有个家伙气若游丝,咳嗽个不停。那天晚上,也可能是第二天晚上——我在里面没有时间的概念,我猜是晚上,因为病房里光线熹微,外面也黑着,而且没听见什么人来人往的动静——又送进来一个病人,他因为尿不出来大声地哀嚎着。确实痛苦难忍。医院用尽办法,也只让他安静了几分钟。
我惊讶地发现自己并不觉得烦扰。相反,我想了解周围正在发生的一切。
一天早上,我看见两个女人陪着一位躺在床上的病人。床上的人看起来时日无多了,不过,倒不是这一点引起了我的注意,而是那两个陪床的女人一直在看我,紧盯着我不放,上上下下地打量,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也许她们看我眼熟,但是我身上连的机器太多了,她们实在是认不出我。
住院的那段日子,一天中的不同时刻会呈现出不同的色调。当时正值六月,一大早,灿烂的阳光就点亮了整个病房,天花板上那些卤素灯泡【又称钨卤灯泡或石英灯泡,比白炽灯泡寿命更长】被照得像闪闪发亮的玻璃球。日暮西山后,医院就完全依赖人工照明了。长方形的电灯闪动着,还有几盏不大不小的LED灯,发出纯白色的光。每当有紧急情况出现时,所有的灯都会亮起来,这样的场景并不少见。到了深夜,为了让大家安然入睡,房间里只留有一丝黯淡的光线。
这里的色彩令我着迷。白色和绿色是主色调,尤其是病号服和护士服的那种青苹果绿。还有罩衫的蓝色,以及口罩用久了变出的灰色。连机器的声响也是有颜色的。有几次,机器突然启动,让我无比恐惧。
我的心情阴晴不定。我还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什么时候来这儿的?有时候,我想哭,却哭不出来。我已经有一年多一滴眼泪都没掉过了。以前我是很爱哭的。
有一天,护士发给我一个小玩意儿,它有一个吹气口,连接着一个分成小格的盒子,里面装了三个小球。护士让我用力吹气,让小球飘起来。我没吹,我把这件事忘了。我也不理解护士让我这样做的用意。
有天清晨,我看见自己嘴巴里的那根管子流出了黑色的液体,吓了一跳,赶紧比划着叫人。我不记得护士是怎么解释的。
我感受到的最美妙的一瞬,是看到女儿走过来,冲我大喊:“妈妈,他们切干净了!”她周身浸透着快乐和希望,眼睛亮晶晶的。那样的神采奕奕。我还横卧在床,却顿然领悟:我要从这里出去。

艾尔维拉·纳瓦罗(Elvira Navarro,1978—),西班牙作家,编辑,已出版五部长篇小说和一部短篇小说集。2010年入选《格兰塔》杂志评出的22位35岁以下优秀西班牙语小说家。作品被翻译成英语、法语、瑞典语、意大利语、日语和阿拉伯语。《记事/纪逝》(Memorial)选自2019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兔子岛》(La isla de los conejos,兰登书屋),是一个社交网络时代缅怀亡者的故事。女儿通过一个奇怪的社交网络账号接触到亡母在互联网上留下的虚拟痕迹,由此开启了重构母女关系的旅程。或许,无论是隔着电脑屏幕,还是隔着生与死的边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需要在重新整理和解读记忆碎片的过程中消弭偏见与误会,尝试抵达理解与爱的彼岸。在西班牙语中,小说标题memorial一词意指与书面记录相关的具象载体,如记事本、请愿书等,而与其拼写相同的英语单词表示对某人或某物的纪念,某种寄托怀念的情感载体。小说家借由该词在西英双语中的不同释义,赋予小说标题更多的解读层次。一方面,文中的账号主页如同虚拟空间里的记事本,记录着母亲生命历程中的片段。另一方面,对逝去者的纪念与缅怀贯穿整篇故事——该小说的英译本(2021年美国国家图书奖最佳翻译小说奖提名作品)标题直接沿用了memorial原词,想必也是考虑到这篇作品纪念母亲的主旨。为了体现这种双重内涵,此处我们试用“记事”和“纪逝”的同音组合来翻译标题。
原载于《世界文学》2024年第2期,策划及责任编辑:汪天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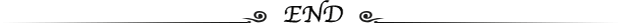
点击上图,订阅全年《世界文学》
点击上图,订阅单期《世界文学》

添加《世界文学》小助手
获邀进入《世界文学》分享会3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