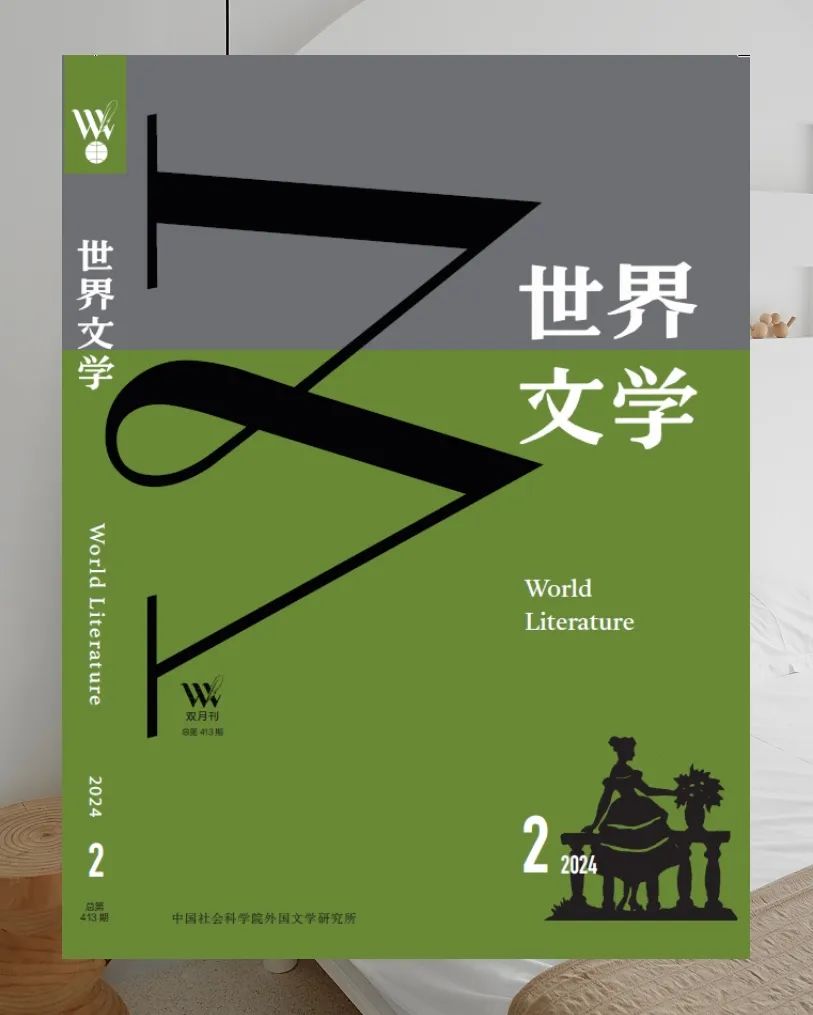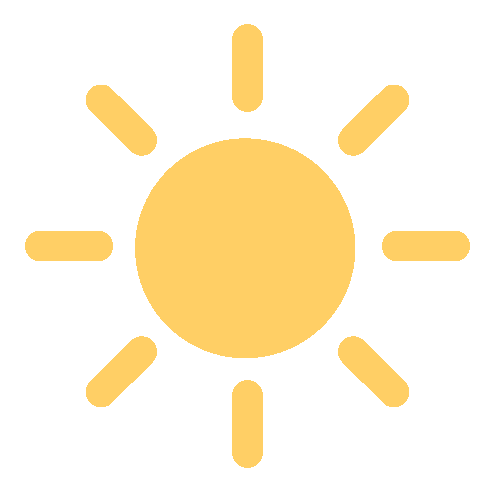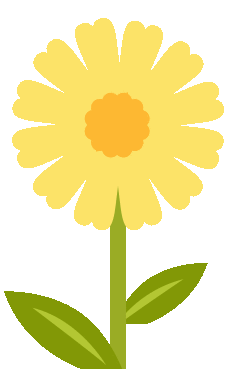世界读书日 | 沈念:阅读像一条泾渭分明的河,划分了我的白天与黑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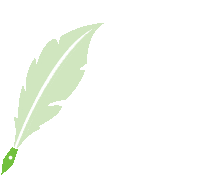
今天是世界读书日,我们为各位读者推送作家沈念的文章《暗夜生长的阅读之树》(载于《世界文学》2008年第4期)。沈念以自身阅读经历为线索,串联起博尔赫斯、卡尔维诺、萨特等文学大师的作品,展现了阅读如何引领我们穿越知识的密林,寻找生命的意义。让我们一起跟随作者的脚步,感受阅读带来的无限魅力和深远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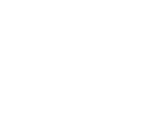
沈念
我呆在那座工厂学校的十又二分之一年的时光,渐渐离我远去。在我们互相对望却只剩下模糊的背影时,我却清晰地看到,如果像剥笋叶一样地刨掉那件毛茸茸的外套,那段时光拥有过的美好,最后残留的核心是留在从夜晚开始的——阅读。阅读像一条泾渭分明的河,划分了我的白天与黑夜;它又像一把锋利的手术刀,把体内的杂物剔除,让一个年轻的身体在阅读中成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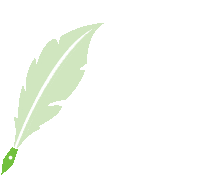
最先引起我对博尔赫斯的关注是中国当代作家马原,一次,在一所高校讲座被问及所受博尔赫斯的影响时,他的回答是:“我从未听说过这个人的名字,自然也就谈不上影响。”事后,他向朋友承认当时只是撒了个谎。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能看出马原与博尔赫斯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的人为数不多。当时我对马原这个敢在公众面前撒谎又大胆承认的作家更是惊讶不已,这种偶尔为之的狡黠一点也不影响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当时我正读完他的《虚构》、《冈底斯的诱惑》等小说,虽然实在懂得不多,但在由衷地佩服这个人的写作才能之际,我决定去认识博尔赫斯。
而我对很多外国文学的阅读就是以爱屋及乌的方式开始的。与一个作家(作品)的相遇,往往得益于对一个作家(作品)的阅读。也许我只是做了一次顺藤摸瓜的事情,根本谈不上连根拔起。
我很喜欢一句话:“世界,很不幸,是真实的。我很不幸,是博尔赫斯的。”说这话的人就是博尔赫斯,在我多次掩书沉思之际,他从头到脚都是一个糟老头子的样子,双目失明,却还在一座大图书馆的书架间窸窸窣窣地爬摸着。他对书的爱好,可能同我小时候在泥巴里滚打一模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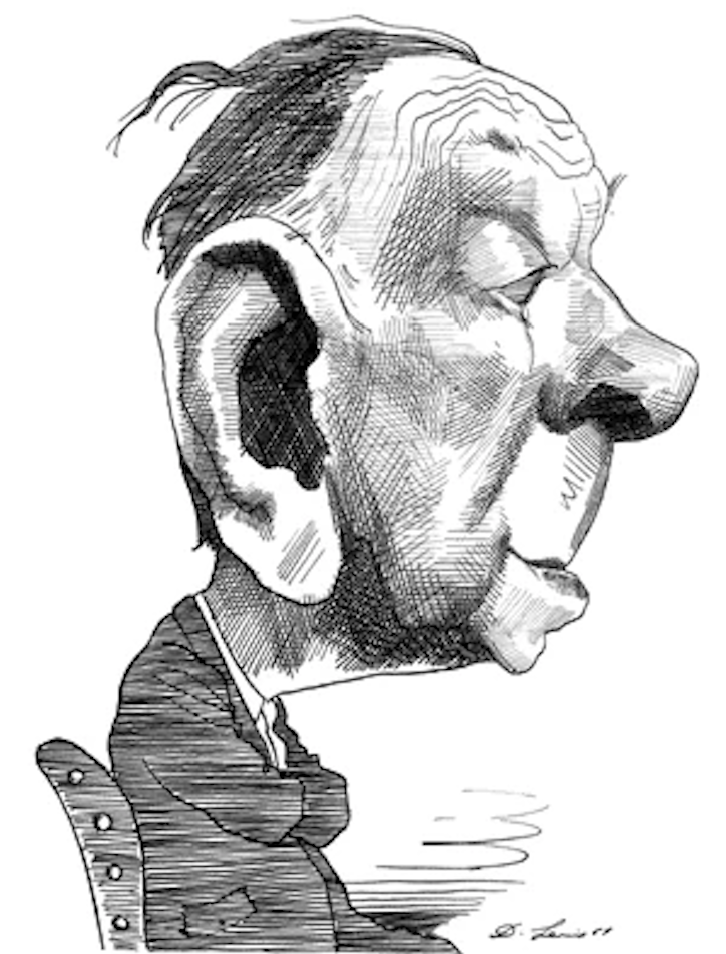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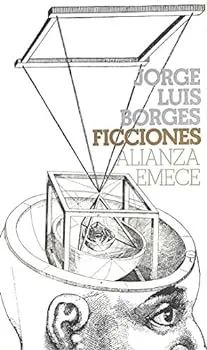
最先接触到的博尔赫斯的作品是那本由九个小短篇组成的《杜撰集》(浙江文艺出版社),语言精致流畅,结构巧妙,情节跌宕起伏,叙述引人入胜,而寓含的道理发人深思。我喜欢老头子的小说的理由是那密不透风的叙述和带给感官的刺激。我最欣赏的那篇《刀疤》真令人拍案叫绝。一个犹大似的革命叛变者带着无人知晓的耻辱的标记,远走他乡,他的身份和过去的历史是隐蔽的,直到有一天,他如实地对“我”讲述一个故事。故事里的枪声此起彼伏,房子里的光线明暗相间,场景的变动是那么缓慢,紧张惊险,扣人心弦。我感觉自己也参与其中,在渐渐真实起来的氛围里,高兴、沮丧、恐怖、逃奔……是它们向我靠拢,还是我亲近着它们?我彻底被老头征服了,我渴望快些读到故事的结尾,我快受不了了。我想大声叫喊,这才是真正的好小说。
这就是博尔赫斯,我对他必须全身心地投入。这时,我的体力是旺盛的,我的世界里不能有一丁点意外的响动,如笨重的敲门声,楼道里夸张的脚步声,远处嚣张的流行歌曲,否则心会猛然抽搐,一个精心布置好的环境被打破,一个美丽的梦夭折了,而我一定会痛哭一场。
这就是在我刚跋涉写作之路时阅读博尔赫斯的真实感受。老博(后来我和好几个喜欢博尔赫斯的朋友对他的亲切称谓),给我一种体验生活的新的方式,在乏味困惑的现实生活中注入的新鲜血液。我们要为幸福历尽艰辛。故事中的幸与不幸,情节的演变让人唏嘘之后,又重新认识自己和生活的幸福含义。
还值得一提的是,二〇〇一年夏天,我租居在一幢旧楼顶楼,是工厂的那种“扁担房”,二十平米,却被划豆腐块似的整出卧室、餐厅和厨房,楼顶板非常单薄,丝毫不能阻挡太阳的炙烤。整个暑期,我就在无比酷热中读着博尔赫斯小说全集度过,身体内的水分以从没有过的速度往外奔跑。与博尔赫斯在酷热中相伴,是我至今为止有资可谈的一次阅读经历,我感受到自己像一只忙碌的蚂蚁,整日整夜地在他的世界里奔波,搬动着一个又一个强大于身体数倍的悬念,并追逐着阅读中高潮带来的快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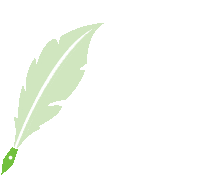
现在开始阅读了。现在已经读完这本书了。现在是凌晨两点,周围安静得只有我一个人的呼吸,我想给一些朋友打电话,告诉他们卡尔维诺撰写的这本《寒冬夜行人》,告诉他们我感受强烈的一切——这不仅仅是一部小说,也是一部关于小说的小说,一个关于阅读的故事,一份独特的文本。
我最早是在《南方周末》上读到了卡尔维诺的几则寓言,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黑羊》和《呼喊特丽莎的人》。那个生活在全是盗贼城里的诚实人,那些站在深夜的街头一齐呼喊特丽莎的人,较长一段时间让我拥有着一种阅读附加想象后的窃喜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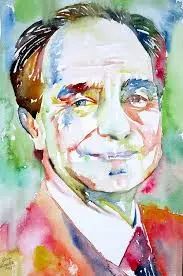
卡尔维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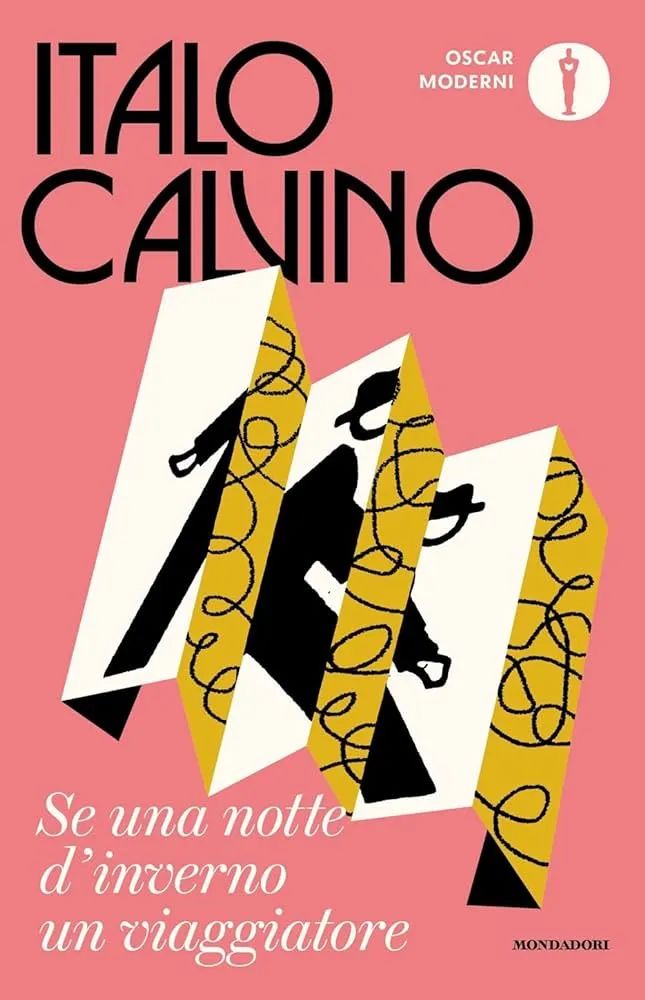
《寒冬夜行人》
还是回到我手中的《寒冬夜行人》吧。翻开那天晚上奋笔疾书的读书笔记,我是这样描绘当时的阅读感受的。
小说就从“你”的阅读开始,你既是一个显性的读者,又是一个隐性的故事参与者。你兴致勃勃地买来卡尔维诺的新小说《寒冬夜行人》,正看到入迷时,没想到却因书页装订错误而被迫中断阅读。你迫不及待地去寻找下文,不料拿回来的却是另一部小说。你读到高潮迭起之际,书又戛然而止。如此这般阴差阳错一再发生,但你却锲而不舍地一部接一部地找来读,前后读过的小说标题正好串成一个句子:寒冬夜行人,在马尔堡市郊外,从陡壁悬崖上探出身躯,不怕寒风,不顾眩晕,向着黑魆魆的下边观看,一条条相互连接的线,一条条相互交叉的线,在月光照耀的落叶上,在空墓穴的周围,最后结局如何?当然谁也不知道。这十篇嵌入的未尽小说都是紧张刺激的故事,有侦探、间谍、科幻、成长故事、日记体小说、新恐怖小说、感觉派小说等,叙述模式则包含意识流、魔幻写实、现代主义、心理分析等,描写细腻,构思奇妙,吊人味口,仿佛是跟读者玩一场你尽管沉醉的开心游戏。
在小说的行进中,一个故事的结束吸引着另一个的开始,环环相扣,而男读者“你”和女读者柳德米拉的相遇相爱,成了两条并行线索的另一条。他们遇见形形色色的读书人,有坚持己见的女性主义读者,批阅并口译已失传的文字的教授,出版社编辑,翻译家兼伪书制造者,畅销作家,负责审查禁书的政府官员等。他们被安插在不同的故事中,之间不同的阅读旨趣和见解揭发出小说阅读和写作的本质,同时也应了一句时下流行的批评语:一切阅读都是误读。
曾经在一本畅销周刊中看到,卡尔维诺的头颅长得像块圆圆的大石头,十分饱满,高敞的额头上皱纹雕刻得又深又长,像某种有光泽的海螺,眼神和唇部及微张的鼻孔都有掩不去的笑意。于是我便自然不自然地将小说的“你”和这个脑袋像石头的人联系起来。
《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这是此书拥有的另一个译名,对于这本我寻找的最渴望读的小说,还包括后来在《帕洛马尔》、《我们的祖先》等作品中,我看到文字就像卡尔维诺手中的魔方,被他轻巧地、随意地玩弄着,呈现给我们的是一幅幅奇特而悦目的图案。他以叙述的欲望为驱动力,在叙述中让你观察小说本身的成长,而且他在努力减少沉重感,天体、人、城市和语言的沉重感,结构看似繁复却不失轻盈。在阅读中我感觉像是看着一棵树,枝叶繁茂交错,走进树下就是一片天地,又像是观看舞台上一个轻逸舞者的柔软身姿。卡尔维诺让我真正欣赏到的是二十世纪世界文学园地里的一朵奇葩。
“在一片密林之中,有一座城堡向所有途中赶上过夜的人提供住所,不论是骑士还是贵妇,是王室的仪仗还是朝圣的平民。”卡尔维诺在《命运交叉的城堡》中将一所来者不拒的城堡展现在大家眼前,城堡虽处于乡郊僻野,可陈设豪华、餐具精美,过客们相貌堂堂、衣冠楚楚,但这里的安静使人无法承受,想说话已成不可能,他的幻想大胆:穿越树林让每个人付出的代价就是失去说话的能力,只留给你一副塔罗牌。
在许多次我站在书丛中的寂静时分,我仿佛看到的是另外一副神奇的塔罗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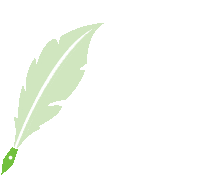
一位喜欢哲学的朋友非常强调地对我说:“读读萨特吧。你要读萨特。”他并且在送我的那本《存在与虚无》的扉页上写着:“萨特在你身旁……”
那是十年前的事了,今天回想起来却备感亲切。朋友是位有思想的人,但我却不能清晰地洞解他。我天生好像缺少对哲学著作的领悟能力,《存在与虚无》就成为一座山的标志,我翻越了,却在半山腰里遭遇到恶劣的气候,猛兽的攻击,身体的衰弱,然后寸步难行,无功而返。
一九六四年,瑞典文学院决定授予萨特诺贝尔文学奖金,被萨特谢绝,理由是他不接受一切官方给予的荣誉。他的一些有名的戏剧和小说,还有他的伴侣西蒙娜·德·波伏瓦,这都是足够的诱惑力。但我一直在等待,似乎是非得有个晴朗的日子才出发。后来真正让我对萨特产生美妙感觉的是他的童年自传《词语》(三联书店)。
他的一生都战斗在词语中,我只有通过《词语》去接近他。
一九八〇年四月十五日,萨特逝世。法国总统德斯坦惋惜地哀叹着:“这个时代陨落了一颗明亮的智慧之星。”这是一个怎样的巨人?他的五十卷左右的巨著、作品,如《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存在与虚无》、《辩证理性批判》等已成为二十世纪西方哲学思想发展史中的经典;他在文学上的成绩斐然,其小说隽永而意味深长,境况剧脍炙人口,那部被视为法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史诗的小说巨著《自由之路》仍魅力四射;他一直被当作共产党、社会主义的同路人,在后期他又成了法国极左派的的精神支柱。正如人们不会忘记曾为和平与自由奔波并作出贡献的人,萨特的词语连同思想将纠缠人类的延续。
在经历了一场信仰危机后,萨特奉词语为上帝,从而选择写作作为终身生活的快乐之源。我曾经试图去洞解这是场怎样的信仰危机,却不了了之。有人说,萨特是位富翁,他拥有一座用词语堆砌成的宏伟宫殿;有人说他太贫穷,除了词语一无所有。对这两个说法我不以为然,他就是一个以“词语”为人的自由奋斗目标的词语大师。“词语”的内涵和外延都必须是极具张力的一张巨网。然而回溯到萨特的童年,他躲在外祖父的书房里,偷偷抚摸着书本,并开始对诗人莫里斯·布肖的《故事集》的征服。他曾说:“我的生活是从书开始的,它无疑也将以书结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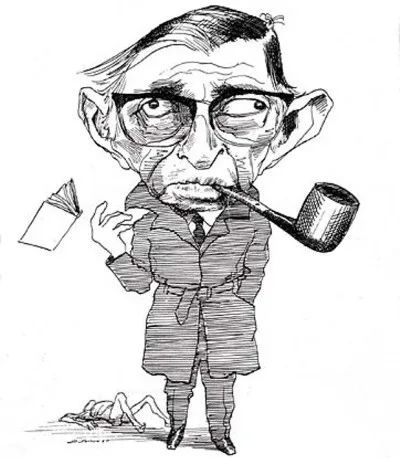
萨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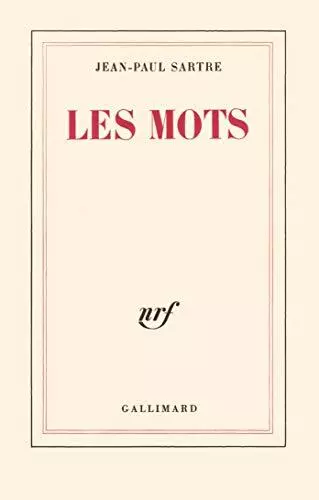
《词语》
那本由“读”和“写”上下两篇组成的不足两百页的《词语》,比他的思想论著要文学化通俗化多了,但在阅读的过程中你稍不留神,又会走进一个古希腊迷宫,路是直线的,然而会不断产生该往哪里去的混乱与矛盾的思想。所以你得在准备好清醒的头脑的同时,还得拥有足够的体力。
在《词语》中,萨特进行的关于童年的描述是带有严厉谴责的。他在谈到《词语》的创作时说:“通过我的历史,我想再现我的时代的历史。”他这个完美表达的想法却只到十岁时便戛然而止,续写青年自传的允诺成了一张空头支票,也许这份遗憾正成了奠定《词语》重要地位的一块基石。词语本身具有超时间性,把萨特的思想,以及人生一分为二。正如译者潘培庆先生在序中说:“在《词语》之前,他生活在梦幻之中,从《词语》开始,他清醒了,觉悟了……”短暂的生命在时间长河里一闪即逝,而词语是唯一的解救方式,思想是存在的关键,当人们在对词语(思想)阅读时,他便是摆脱虚无获得新生。
任何一种语言对另一种语言,任何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译读都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偏移,萨特所惯用的隐喻、双关等修辞手法一旦形成中文的表述,其精义和风格便少了趣味。尽管如此,他依然在中国许多读者心中保存着一个具体的位置。
一九八〇年四月十九日,载着萨特遗体的灵车在数万名群众自发的拥护下,缓缓走向蒙巴那斯公墓,这场葬礼无疑也是称得上法国二十世纪最隆重、最具理想色彩的。这意味着萨特与词语这个“敌人”的对抗战斗走到了生命的底线,却走上时间的无限延伸地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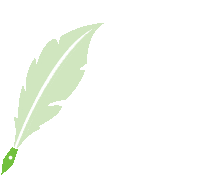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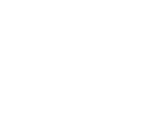
沈念,1979年出生,中国作协会员,湖南省作协副主席,当选湖南省文联第十届全委会委员、湖南省第十届青联委员、湖南省“三百工程”文艺人才。出版小说集《灯火夜驰》《夜鸭停止呼叫》、散文集《世间以深为海》、长篇儿童小说《岛上离歌》等八部,曾获十月文学奖、华语青年作家奖、三毛散文奖、万松浦文学奖、张天翼儿童文学奖、湖南青年文学奖、湖南省青年五四奖章等。
原载于《世界文学》2008年第4期,责任编辑:高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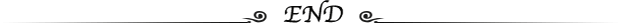
点击上图,订阅全年《世界文学》
点击上图,订阅单期《世界文学》

添加《世界文学》小助手
获邀进入《世界文学》分享会3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