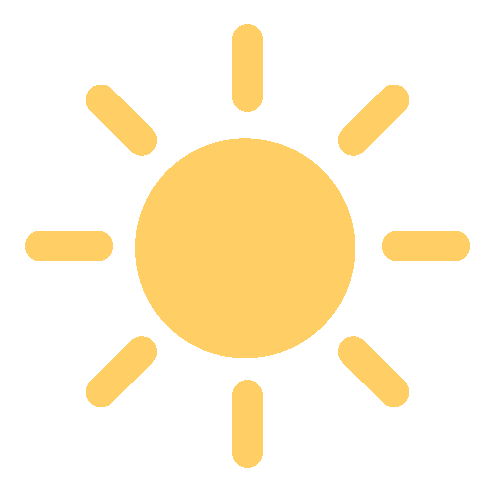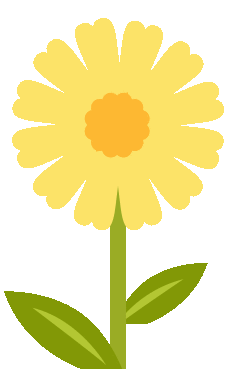读者来稿 | 榕楠:如何安顿她们的过去——《我们失去的记忆》《跑》读札
![]()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我们失去的记忆》和《跑》的贯通性在于其均采用女性第一人称视角进行反向记忆回溯,叙事光束牢牢聚焦在失败的被害者之上——前一位讲述者是罹患家族精神病两姐妹中的妹妹,而后一位讲述者则是在革命阵营内部遭遇“自己人”猥亵的女兵。

——《我们失去的记忆》《跑》读札
榕楠
《世界文学》于2023年第6期推出“南非短篇小说专辑”,所选篇目恰好错综对照地展现出“说谎”与“遗忘”作为两条独异的创伤反映路径,如何既相互倾轧,又彼此弥合。在《一次非洲布道》与《气流》中,叙事于常规中正向推进,然而聚焦视点却不时四散游离,作为施暴者、“胜利者”的男性形象在群像的统合下间或闪现,如亡命南非的卢旺达大屠杀罪犯,抑或颠簸航班上行窃得逞的黑人青年。相较而言,《我们失去的记忆》和《跑》的贯通性在于其均采用女性第一人称视角进行反向记忆回溯,叙事光束牢牢聚焦在失败的被害者之上——前一位讲述者是罹患家族精神病两姐妹中的妹妹,而后一位讲述者则是在革命阵营内部遭遇“自己人”猥亵的女兵。
根据创伤信息在传播与表达路径上的分野,可将创伤叙述细化为独白式创伤叙述、见证式创伤叙述与回顾式创伤叙述三种。独白式叙述主体在对过去的反复推演中不断自我反省与辩难,以期重塑遭受损害的自我认知;见证式叙述重在两个不同主体之间的交互联通,其固定模式基于“讲述-倾听”框架而又时常溢出;回顾式叙述则往往呈现为代际传递中后辈对前辈创伤记忆的延续或反哺。可以看到,三种创伤叙述的分辨处正依托于讲述者与受述者之间的错位分合,即讲述者并不必然与受述者,或者说创伤事件的亲历者相重叠。相反地,讲述者也可能是他人创伤的见证者或前人创伤的回顾者。需要格外注意的是,独白式创伤叙述的讲述者一般是作为受害者、幸存者出场的“我”,但在一些极端情况下,其真正的受述者也会从单纯的自涉中溢出,指向除自己之外的某一个体、群像或不确定概念。就接下来将要展开探讨的两个文本而言,马可莎拉娜·夏巴的《跑》以“我”平行剪辑式的创伤回忆为驱动,牵涉出革命阵营内部一贯徘徊于边缘的女性工作者群像,并经由奔跑之“我”与飞驰“列车”的崩坏,完成了个人隐喻到国族寓言的转换,属于有延展性的独白式叙述。而利杜杜马林加尼的《我们失去的记忆》则通过妹妹对姐姐形影相吊的外观与内察,促成了见证式与回顾式的有机糅合。


《跑》的开篇在异常浓郁的自我意识独白中层层铺排,反复言说着“我”给自己的身份锚定:一个“跑腿的”,一名边缘却光荣的“次要角色”,一位被收编于“行政支援小组”的地下武装人员。“我”目前的紧要任务,就是在非国大召开国际动员与反性别歧视大会时,奔跑在会议室和办公室之间传接消息和指令。然而,很难说此处着重渲染行动价值和生命意义的隐含态度,不是夏巴沉痛反省女性革命者自我物化与献祭倾向后的强烈批判:“我”多次自比为螺母、螺栓或机修工、润滑油,以一种模拟的阳刚口吻宣扬自己对战斗、纪律、严谨与技能的热忱。但“我”渴望以零件姿态全身心嵌入其中的“解放之列车”,却开向了暴烈、盲目与偏执的集中洗脑与口号政治,原本由女性发言者有序搭建起的反歧视构想大厦也灰飞烟灭在对虚伪男性革命偶像狂欢式崇拜的复仇毒焰之中。随着这名“烈士”身份的明确,“我”骇然发现其正为十二年前曾强暴自己的远房亲戚。彼时只有十九岁的“我”在这位牧师亲戚的诱骗下随其驱车前往郊区的野生狮子园,然而置身于毫无边际的荒原,“我”没有看见预期的狮子,眼前之人却在兽念的支配下化身为比狮子还要狰狞的厉鬼。“我”拼命挣扎后跳车奔跑,生死关头迸发出的惊人速度让“我”得以靠近另一俩车,成功逼迫尾随而来的强暴者在旁人注视之下及时止损。某种意义上,正是“跑”这一行动让处于弱势境况的“我”暂时赢了一回,其也就此成为熔铸在“我”骨髓深处的创伤应激反应,既包含兽性的生存本能,又掺杂人性的瞻前顾后,甚至带有些许神性的救赎意味。“跑”是贯穿整篇小说的最关键意象,与穿插在字里行间的列车、长矛、高速路等其他具象实体一起,交汇成既相吸又互斥的意象群落,共同织就出一套“立意在反抗,旨归在动作”的意义网络。但在小说结尾处,夏巴让奔跑停滞的处理,似乎比奔跑本身更蕴藉力量与深思。回忆和现实中的奔跑共同走向了一个动能濒临崩溃、亟需静态休整的时间结点——“我”从公共性的会场逃回私密域的“自己的房间”,油然而生一种无法抑制的“收拾房间的冲动”,想把所有东西都“码成堆、排成行”,从叠T恤开始,桩桩件件“重新整叠、重新归置”。我发现自己“得把东西收拾齐整后才能决定下一步要做什么”,一如创痛酷烈的过去只有当症结得到疏通后才能够被妥善安顿。


在这里,或许不得不酌情考量另一重职业所裹挟的思维惯性对两位作者各自行文范式和底层逻辑的潜在驱动。在成为专职作家之前,夏巴曾接受护士培训,一度在非政府组织里担任妇女健康专家,撰写有关性别与卫生的文章。因而可以看到,夏巴在《跑》终局处极富象征性的身心整顿书写,即带有看护、诊断与叩询个人乃至共同体命运的意味,展露出一个怀揣实务情结的广场型知识分子所因袭的道德律令和责任重担。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跑》在独白式创伤叙述上的终极受述者并非单纯的一个“我”,还有“我”背后所站立的所有失声的女性工作者群体,而跑、列车、长矛、高速路等不确定概念的集体越轨也表征了宏大革命话语内部血脉偾张、裂隙骤起,以致最终难以自圆的破碎困境。当然,穷夏巴一人之力,几乎无法提供摆脱这种困境的任何可能性道路,所以《跑》的疗愈方案只能悬置于一片茫然失措的空白。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在《我们失去的记忆》的结尾,利杜杜马林加尼用其笔触所剪辑出的,却是一段极富动感的影像:逃离巫术仪式现场的两姊妹睡在树下,决定“等太阳升起后,醒过来再接着走,去往某个地方”。令人遗憾的是,这里的“某个地方”仍是一个飘忽不定的所指,因而在“太阳照常升起”之后,两姊妹的身形也会逐渐地淡出画面,最终留下一个需要被某种情绪所填充的空镜。需要注意的是,在作家之外,利杜杜马林加尼还兼职摄影师与电影制片人。幼年时在乡村部落放羊的经历,又让其对农村生活十分熟稔,怀揣着割舍不断的复杂乡土情结。在《我们失去的记忆》里,利杜杜马林加尼固然表现出对落后、迷信痼疾的深恶痛绝,但其笔下的乡土风物却在儿童视角下恬然而欢脱地恣肆流转,成为点缀暗黑成长叙事的几抹微弱亮色。在两姐妹惊心动魄的亡命之路上,唯有归入山峦、大地与河流的时刻,其生命形态才获得了舒展,赢得短暂的自由和片刻的宁静——“女性同自然之间存在着某种更为天然的联系”,生态女性主义的洞察似乎在这里拖曳出悠长的回响。


利杜杜马林加尼对叙述者“我”,也即两姐妹中的妹妹在意识状态和表达口吻上的设置颇为精巧且张力十足。一方面,“我”自诩为这场家族精神病遗传链条上的幸存者,认为只有姐姐遗传了父亲所携带的疯癫基因,而自己尚是能够清醒判断形势并果断采取措施的家庭主心骨。与之构成悖论的是,在重溯过往经历时,“我”的创伤回忆却呈现出一种乱序式拼凑和选择性遗忘交织的表述障碍,通篇弥漫着不着边际的臆想、妄语,以及凌乱而扭曲的记忆碎片,让读者很难不对“我”是否也深埋病根心怀质疑。不妨想象,如果将这篇融贯了跨媒介技巧的小说进行忠实的影视化,则其一定会呈现为大批量手摇镜头、跳切剪辑、蒙太奇意象的混杂堆砌,是对拍摄者与观看者都构成极大挑战与冒犯的风险创作。然而在德勒兹意义上,“时间—影像”作为一种变革性美学结构,正是经由均质线性的现实时间向断裂异质的电影时间的嬗变,才彰显出镜头的外部特征与反讽意涵。影像经验在利杜杜马林加尼创作中的影响是如此有迹可循,不断拓宽讲述与受述主体对时间与空间的形变感知,层层深化了文本的批判力度。另一方面,“我”的讲述口吻在稚嫩的孩子气中透出一种老灵魂的苍凉,造成这种吊诡冲突的症结或许在于回溯结点的有意模糊,讲述人既可能是还在逃命路上无法安顿身心的流亡者之“我”,也可能是十年后蓦然回望的沧桑者之“我”。夹叙夹议的俯仰之间,“我”背后隐含作者的暧昧身形也明灭可见。
在《跑》的行动停滞和《我们失去的记忆》的空镜高悬之上,文学的无力感于焉显现。竹内好曾在《何谓近代》一文中,借对鲁迅文学抵抗力的辩驳,指出亚洲的主体性从一开始就是一种文学性的存在,其通过自身的无力感而通向一种弱者的连带。站在更为广阔的世界文学视域下,亚洲的连带也可延伸至南非的连带,非洲的连带,第三国家的连带。《世界文学》创刊伊始,曾为纪念鲁迅而命名为《译文》。需知南非文学首批旅行至中国,也曾停泊于周氏兄弟《域外小说集》中“被侮辱与损害民族文学”一辑。只是在创口已渐趋结痂的今天,对于当下南非文学跨界遥感的归去来兮,或许还不得不重新唤起鲁迅般“抉心自食”与挑破毒疮的勇气——“说谎”与“遗忘”背后,是否深藏了弱者道德对强者逻辑的某种隐秘服从?


有品格的控诉应一直保持正当的愤怒,无数次艰难地跨过绝境、穿越幻象。詹姆斯·伍德在评价库切时,曾指出作为南非裔作家,其创作拥有远超其他英文书写的智性与韧性强度:“没有作家像他这样严峻,具有这样痛苦而反复的诚实。他总是回到同样的痛点,就像关节在同一个地方反复碎裂。”同时,在对《耻》的剖析中,伍德也无奈地看到了南非文学向内求诸己式的寓言写作的局限。轻巧而深谙西方文坛规则的库切选择搁置了愤怒,把太多的重量,诸如对称的形式、紧凑的情节、政治的符号,一股脑程式化地加于对自身耻辱和忏悔的观念之上。这样的处理容易使解读走向清晰,最终造成对小说的简化和伤害。在此基础上,伍德呼吁对《耻》的阐释能够更为复杂,更为有益地扰乱自我,而这将是更尊重库切自身努力和小说叙事本质的真诚礼赞。同《耻》相类似,《我们失去的记忆》和《跑》无疑也是这种高度寓言化的创伤书写。意象的洗练、形式的整饬、叙事的通感、远景的溃散,固然已构成南非文学的鲜明标识,但新的书写永远将是对过去的一种反拨、背叛与重新安顿。在浮现的冰山之下,潜藏着尚待开掘的探索空间。
EN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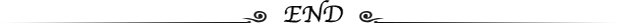
点击上图,订阅全年《世界文学》
点击上图,订阅单期《世界文学》

添加《世界文学》小助手
获邀进入《世界文学》分享会3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