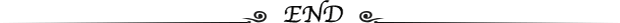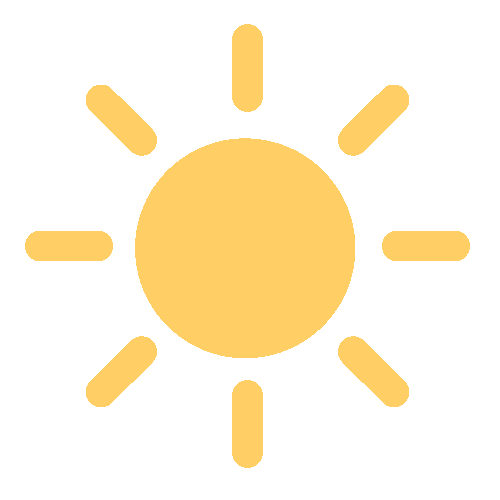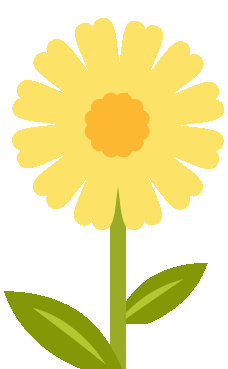小说欣赏 | 色•额尔德尼【蒙古国】:生命线就像一根很细的线,奇怪的是它就是不断……
![]()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扎木苏出去不一会儿就把马群赶回到毡房附近。大家伙儿用纳过的毡垫子把扎布老人抬到了外面,或许是生活了几十年的这个人间世界在用夏季的美好时光为他送行。太阳偏西了,空气中弥漫着冷蒿草和百里香草的香味儿,轻柔而清爽,好像在轻轻抚摸着他说:“在死亡面前要坚强和镇定一些。”


色·额尔德尼作 敖福全译
扎布老人是在太阳光照到毡房的毡壁支架顶部时醒来的。他眼睑发青、肿胀,勉强转动着变得沉重的头,用枯陷在眼腔里的失去光泽的眼睛环视毡房内。他鼻梁上的鼻翅软骨似乎已经透明,腮根骨突鼓得像要穿透皮肤似的。他的脸色已经说明,他生存在这个罪孽的世界上的日子不多了。他用骨瘦如柴的手拽着拴在床腿上的拉带侧过身子,用放在桌子上的瓷碗里的对水稀释的酸马奶浸湿了嘴唇,又看了会儿从毡壁支架上照射进来的光线。现在正是美好的夏季。扎布老人开始过这种从毡房天窗看天空、从门看草原的生活已经有一段日子了,不过,他仍然能透过从毡房支架上面照射进来的太阳的金黄色光斑看到外面的世界。一生纵横驰骋的草原和自己经历、熟悉的生活怎么能在自己瞑目之前消失呢?虽然他每天清晨醒来都在想“这种痛苦是不是该结束了?”可这日子仍然在延续着。人这东西也的确是个怪物,生命线就像一根很细的线,奇怪的是它就是不断。患病一年了,扎布老人原打算在去年草原还没有返青之前回岳丈家看看,结果愿望没能实现。“我有七条命根子。”他经常这样对人说。他过去虽然也想到过死亡,可他生来就是一个不畏惧死亡的人,所以他放心地、不因疼痛而呻吟地、坚强而平静地等待着死亡。由于他意志坚强,所以肉体上的痛苦也减轻了许多。“外面天气这么好,为啥出去还要关门呢?”他想责怪妻子,可很快又劝阻起自己。“扎布,你不要总是发无名火。”他想驱散重病的身躯散发出的令人作呕的臭味儿,点起了一块儿香烟升腾的杜松叶子末儿。他思绪万千。毡房外面百灵鸟在欢唱,远处的马群在嘶鸣,他情不自禁叹了口气。听着老伴儿挤牛奶的动静,想到她的手和手指一定疲倦了的时候,他心生怜悯。她开始用双手刷——刷——地均匀、整齐地挤奶牛的乳头,不一会儿就累得停下来掰起手指。“可怜的老伴儿,儿子从军队退役回来之前这段日子,就得由她自己过了。”扎布老人这样想着。他也曾想过坚持活到儿子回来,后来又想再坚持半年也没有什么意义。他想还是早走一些为好,这样老伴儿也少受点罪。他预感到自己似乎能够人为地接近死亡。病已入膏肓,现在明显地只有一根细线似的命脉在维持跳动。断食断水已有日子了,等待死亡的日子就等于让他躺在这里回忆往事,这也是扎布老人还没有断气的唯一原因。在他看来,自己早已经不算是这个世界上的人了,他唯一担心的是在肉体死亡之前大脑先死,可现在随着身体的衰竭,思维却愈加清晰。他想,意识应当指导躯体,他提醒着自己在适当的时候应当断气,可是,遗憾的是他现在不知道什么时间是那个适当的时机,没有一个明确的标识。


今早,浑身的疼痛奇怪地消失了。他浸湿嘴唇后闻着杜松叶子末儿烧出的香味儿,又想办法动了动僵硬麻木的身子,一直憋痛的胸口感到敞亮了,头也似乎轻了许多。他现在心脏搏动显得有些慢,但通过枕头仍然可以清晰地听到怦怦的跳动声。扎布老人看了看挂在门框右侧梃子上的马嚼子、笼头和放在一堆东西上的肚捆带子散放着的马鞍子,像是主人仍能跨马驰骋似的,马嚼子和马鞍子都放在那里备用着,老伴儿从不去动它。放在铁炉子上的奶油泛着金黄的光泽,毡房后侧箱子上摆放着老伴儿点燃的佛灯,像黑莲花的花蕊,有气无力地像快要熄灭了似的。
那年夏季垫着佛教图案刷漆的毡房椽子,在光影中显得密密麻麻。他想:“我们家毡房的木质好,儿子退役回来后更新毡房帡幪毡子就行了。”左侧老伴儿的床铺头上朱红色的床单子上摆放着画有金色法轮面儿的陈旧的矮箱子。“该给它重新刷一遍油漆了,这是老伴儿俩最早的家具。”他这样想着。除了这个旧箱子外其他用具都保持着原样,甚至勉强亮着的佛灯也一直勉强亮着似的。他忽然想:“该结束了,这样既折磨自己又折磨别人,要到什么时候算了结呢?”
老伴儿挤完奶进来了。他让老伴儿打发邻近家的孩子快马传话,请这一片儿的长者们到家里来。同辈的三个老人匆匆赶来了,想在扎布老人弥留之际陪他多坐一会儿。在过去经常进进出出的都踏出小凹地的拴马桩前下马时,他们却在心里犯难了,进去后说什么呢?进了毡房后扎布老人在用轻松但却是一个即将死去的人的欢快幽默的话语迎接着他们。他穿着棕色的绸缎袍子,佩戴着在一九四五年反法西斯解放战争中应征入伍获得的黄铜纪念章,背靠垫高的枕头坐着。进来的是扎布老人年轻时的伙伴,绰号叫“长头发”的身材粗壮的黑老头儿奈登(最近又开始留头发);在家乡这一带很受人尊重,多年来一直和扎布老人一同在乡和县里从事过各种工作的“红爆果”(老天爷才知道他这个绰号是怎么来的);本家族弟弟,嗓子尖细、嘟嘟囔囔没个完的绰号叫“蚊子”的扎木苏,他们三个人。他们没想到,已经接近死亡的人仍然这样乐观。他们知道他是个硬汉子,但是,听说他已经病入膏肓、令人不忍目睹后,无奈之下相互走动也少了。喝着一河之水一同走过人生的老人们,经历长期生活后,仨仨俩俩地相互走动逐渐减少,这也符合人生规律。他们最宝贵的青年时代是在一起喊着绰号玩耍着度过的,所以,想到要和自己亲密的伙伴就这样永远地分手时,生活就像要破碎了一样。
扎布老人好像在调解这几位的心情,当“长头发”稍后些进来,而且慌慌张张地躲避着自己的视线坐在炉子门边儿摩挲脑袋时,扎布老人逗着他:“我的‘长头发’,你越来越精神了,听说要娶小老婆,看样子是真的了。不过你我当年是同一年娶的老婆呀,为了接回你现在的老婆道勒京,你还记得当时那手忙脚乱的样子吗?为了从青格力格那里要回道勒京的破马鞍,你大腿还被他家的狗咬了一口,当时也真是贫穷啊,连牵配着鞍子的马的能力都没有啊。现在你日子过得富裕,盛气十足了,开始想小女人了。”“长头发”立即感到心里放松了许多,他把烟袋放进怀里:“死鬼!被狗咬的伤疤现在还留着呢。”毡房里变成一片笑声。朋友们以为在朋友弥留之际来陪伴是很苦闷的事,可现在却像聚会一样热闹了。
“你们这只不争气的‘蝈蝈’(自己的绰号)已经活到头了。”扎布老人说。“死之前想看看你们,再聚一聚,听一听你们唱歌拉琴。如果在过去就会说:‘来世还能见面’的。”他继续说着。“可你们是知道的,人不会永存于世。来,族弟,别光瞅着自己的鼻子嘟噜个脸儿坐在那儿,这边有酒和奶豆腐,带头吃吧,也给我递过来一块儿,抹上点黄油。你们喝吧,就算是给你们不争气的‘蝈蝈’出远门儿送个行!你们没有必须来收尸的义务,也没有喝闷酒的必要。不管怎样,还是和喘着气的、头脑还算清醒的、活着的扎布在一起,和过去一样,高兴着喝酒才对。”他这样逼着酒,吃了块儿抹了黄油的奶豆腐,喝了点烫过的酒后眼睛立刻有神,骨瘦的腮根也充血泛红了。
他就这样和知道人不会永存的几位朋友一起喝了点酒,吃着奶豆腐,唱着歌开起了玩笑。曾经是逢宴必唱的可怜的“长头发”又接受了唱歌的任务,这也验证了“枪老了打不准”那句谚语。他操起满是烟垢的音色喑哑的马头琴,用底气不足却直率的大嗓门儿唱了起来。
扎……
我们天生一对翅膀,
拥有美丽家园,
面对幸福和痛苦,
任凭命运去选落。
唱到这里时,扎布老人的老伴儿坐在碗橱旁边,面向另一侧默默地擦着眼泪。
“‘长头发’你真是朝气不减当年啊,老鸟回巢啊……”扎布老人叹了口气又很快驱散了短暂的悲痛情绪。“‘红爆果’,你就说说那年是怎么捉弄我的吧。”“红爆果”干瘦的手腕子上戴着一块儿金表,脸上架着墨镜,真是个干瘦俏皮的老头儿。他先咯咯笑了。


“那时,我是乡党委书记,扎布是宣传委员。”“红爆果”讲起了往事。“那年夏天上级下达的任务非常紧急,那是战争爆发的前一年。当时也依仗着年轻啊,为了完成征集军马和羊毛的任务,我们俩没日没夜地走家串户去摊派任务。那时,一个乡的地盘有现在的县大,怎么走也走不完。有一天我骑马走到了下呼日木图,看到有个人牵着马躺在路边,我轻轻走到跟前一看,是他,正在打呼噜,睡得真香啊。为了逗一逗他,我悄悄牵着他的马缰,打马溜走了。这玩笑开的,可把他弄得没人样了。他一醒来就傻了,只好步行,差不多走了半个驿站,脚被磨破了才见到了人家。后来他知道这事是我逗他玩儿干的后,差点没把我收拾死。”他们这样回忆着往事。
“蚊子”扎木苏酒喝多后好哭,尽管他在尽力克制着自己,但最终还是没有克制住,流着口水咿——咿——地哭了起来。
“你不要总是往人类这边靠,你哭都像蚊子声。”扎布老人这句玩笑把大家伙逗乐了。
“你从来都是铁石心肠,不知道我们这几个要留下来的都软弱无能吗?”扎木苏显得孤独和委屈,他说完就要出去。
“族弟啊!”扎布老人叫住他。“我怎能不知道你心软呢,只是开个玩笑罢了。你能出去把马群赶回来吗?我想看一看。”他求着他。
扎木苏出去不一会儿就把马群赶回到毡房附近。大家伙儿用纳过的毡垫子把扎布老人抬到了外面,或许是生活了几十年的这个人间世界在用夏季的美好时光为他送行。太阳偏西了,空气中弥漫着冷蒿草和百里香草的香味儿,轻柔而清爽,好像在轻轻抚摸着他说:“在死亡面前要坚强和镇定一些。”
家乡的蓝绿相间的小山丘在雾气中若隐若现,仿佛在说大地虽然辽阔,但人的生命有限的道理。
“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家乡的太阳、空气、风和这些小山丘了。”扎布老人这样想着。扎木苏赶回来的马群簇拥着奔跑着,马蹄声轰鸣着。有些气盛的马驹和二岁的儿马频频地向后踹着后腿,嘶鸣着。这时有个老公马似睡非睡地站在离马群稍远的地方。
“看那匹老马!”扎布老人看着那匹老马,歪着他那干裂的嘴唇笑着。“还真是有点儿骨气的牲畜啊。他已经被那些成年的骒马嫌弃了,也一定被三岁公马给咬了。现在老实了,可怜啊,不过它不会比我先走的。”这样过了一会儿,大概是突然见了太阳和风的原因,他的呼吸开始顺畅,目光也神奇地变得炯炯有神了。
“族弟啊!”他说。“请你把套马杆的皮套绳给我解下来!”他把皮套绳送给了“长头发”。“你想娶小老婆就送给你这个吧!这是用公黄羊脖子段的皮子做的好皮套绳啊,你可以显示自己有能耐的。”他把雕刻已经磨损不清的冰凉的小玛瑙鼻烟壶送给了“红爆果”,说:“漂亮的人是需要配耳环的。”


“我已经见到了你们,看了家乡的山水和牛、马、羊。”他最后说:“虽然这是令人眷恋的人间世界,但是像‘长头发’刚才在歌中唱的那样,老鸟该走了。六十几年来目睹了人世间风云变幻,没有遗憾的事了。有好老伴儿,有接续守护炉灶的儿子,有好朋友,这就足够我幸福的了。没有因为缺少什么和没办好什么而不足的,一直和大家伙在一起。扎木苏你克制一下自己(扎木苏哭着走远了),我们都会这样先后到后面的小山坡下的,这是自然规律。这不是我们蒙古人要绝后!你们回去继续养育好子孙后代吧!好,就这样。请你们把我送回毡房吧!”
扎布老人是在后半夜去世的。
色·额尔德尼(1929—2000),蒙古国著名作家,曾任蒙古人民共和国作家协会书记。1949年开始创作,出版有《春风送暖》《畜群扬起的尘土》《富饶的绿洲》等短篇小说集和长篇小说《生活的轨道》。色·额尔德尼的创作题材涉及到蒙古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作品不是停留在对事物的表面描写,而是深入人物内心世界。额尔德尼是当代蒙古国中短篇小说家的杰出代表,也是蒙古国意识流小说创作的奠基人。他的创作推动了蒙古国小说的发展,同时也提高了小说写作技巧,因此受到国内外的一致好评。
色·额尔德尼出生于蒙古国肯特省滨达尔县,1949年毕业于军校,1955年毕业于蒙古国国立大学。1965年荣获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家文学奖,1976年荣获蒙古人民共和国作家协会奖,1994年被授予人民作家称号。短篇小说《老鸟》很能体现额尔德尼的创作特点。它细腻地描写了蒙古老人扎布在疾病、痛苦和死亡面前所表现出的顽强和乐观。在死亡到来之时,扎布忍受着病痛,坦然面对死亡,与年轻时的朋友共同追忆往事、谈笑风生、饮酒欢歌,进而充分展现出蒙古人所固有的顽强意志和乐观精神。
本篇小说译自《色·额尔德尼优秀小说选》。
原载于《世界文学》2012年第6期,责任编辑:秦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