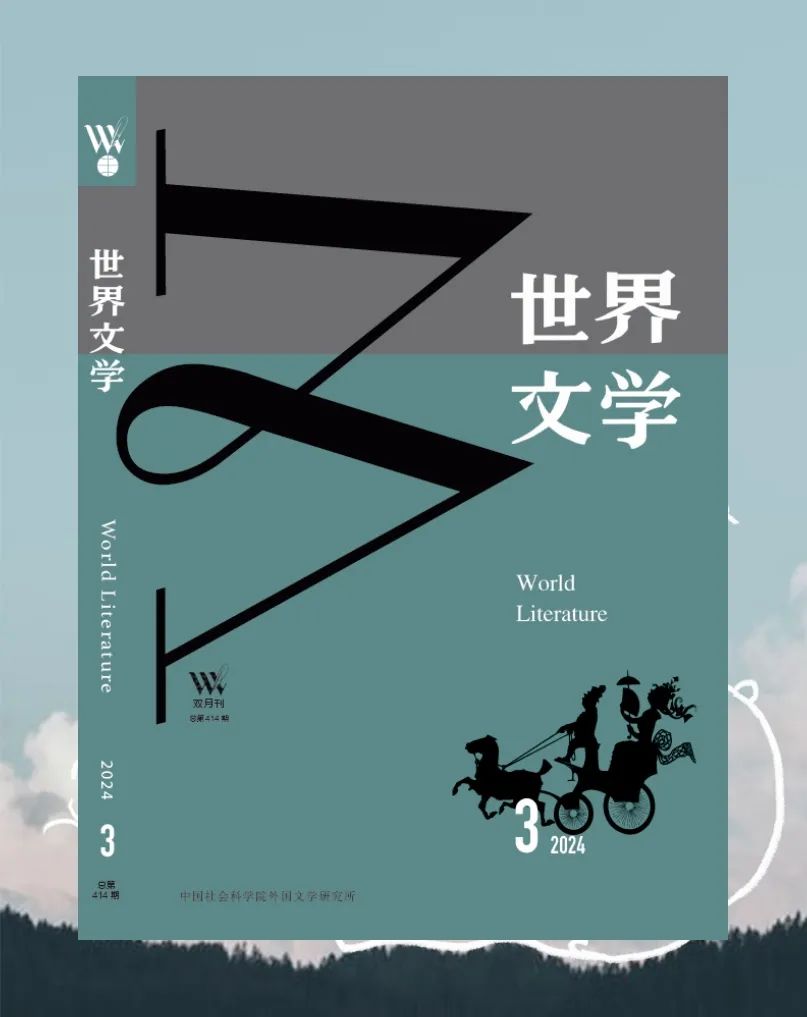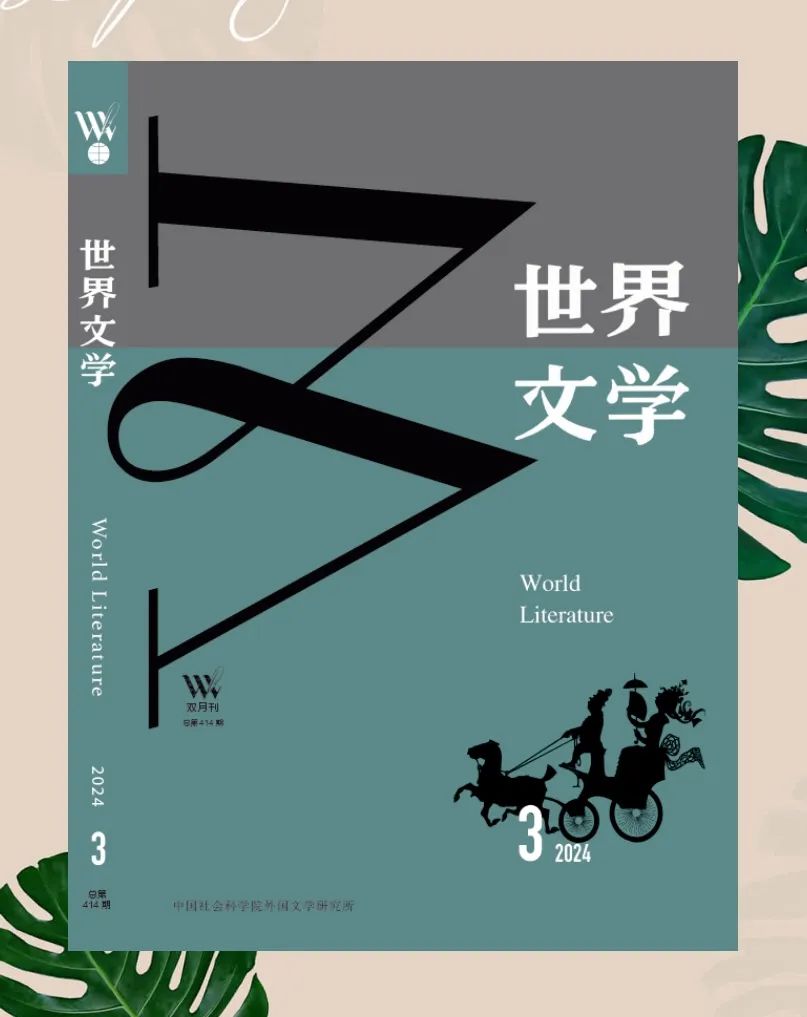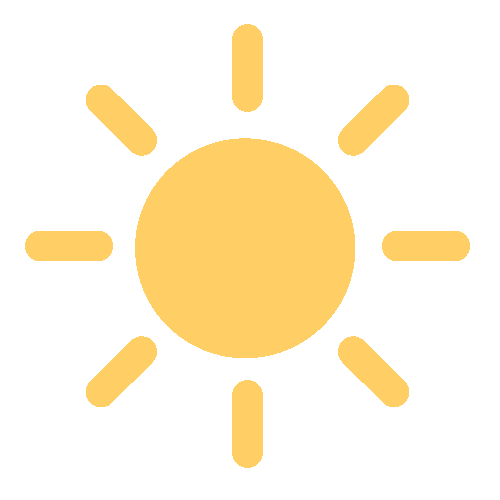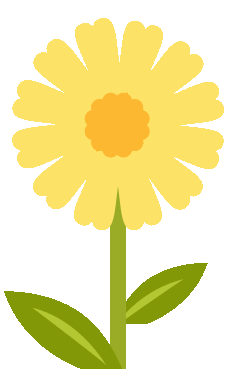散文品读 | 西•泰松【法国】:与兰波共度的一个夏天

奇迹藏匿于历险之路,形形色色的流浪者都知晓这一秘密。在路上,世界缤纷热闹,思绪流动汇聚,字词组成卫队。行走驱散焦愁。此乃毋庸置疑的炼金术:游子行于路,窃走形象,再将那形象抛在纸上。此乃游历四方的通灵者之行径。穿越世界,再用二十六个字母重组世界——直截了当、神奇非凡的行动赋予了漂泊四方、风餐露宿的生活以意义。沉醉于行走的人坚信:尚未经历之事,无法诉诸笔端。

西尔万·泰松作
陈贝译

读阿尔蒂尔·兰波,注定有一天会踏上旅途。这位创作了《彩画集》和《地狱一季》的诗人一生漂泊不定:自阿登省【兰波于1854年出生于法国毗邻比利时的阿登省的沙勒维尔市】远游逃遁,于夜巴黎潜隐奔波,赴比利时追情逐爱,在伦敦漫步游荡,最终在非洲的冒险途中与世长辞。
诗歌是万物往来之运动。兰波一直在路上,移步换景,永不停歇。他的诗作是生活的投射,在其逝世后的一百五十年,依旧触动人心。倘若万物僵凝,死亡便会来临。如今的疫情封禁便是如此,诗歌无法在消毒水里生存。
[……]
兰波的一生,似是展现了曲折绵延与全面迸发的辩证关系。他本可以循着一个普通文人的轨迹,理性、用心、高效地将其天赋诗才倾献于后世。他本可以在魏尔伦的支持下,广交志同道合之人,细细雕琢自己的诗篇,名扬四海尽揽荣光。他本可以用文字为自己建造丰碑,焚膏继晷,将生活曲折起伏地延展开来。他的一生本可以像家乡的默兹河一样:有力、缓慢、深沉,总之,是有用的。
然而,兰波选择切断道路,割裂语言。布鲁塞尔、伦敦、巴黎、爪哇、非洲:他萍踪浪迹,颠覆诗歌。结果:两部爆炸性的诗集问世,辍笔沉默引起一片哗然。兰波的一生仿若点燃的导火线,最终因腿部截肢与喉部结节而燃烧殆尽,享年三十七岁。
兰波的诗,喷射出的是火簇。在其诗篇里,我们寻索不到关于生命、死亡、爱或是艺术的教义。他画的是意象,摇摆的是幻景,这是受启者的秘密。强烈、崭新、不可逾越。言语【在兰波的诗歌里,言语(Verbe)是一种新的诗学观念】是一个隐谜。我们能做的仅仅是尝试破解其奥秘。诗句撕裂迷雾,展现新的景象。崇高的景象。不附任何解释,不附任何说明。
兰波从未达到过自己的目标,他总是将其超越。他的一生不似缓缓流淌的古老之河,不似河流那般曲折延绵地穿越大山。
兰波,全方位骤然喷涌,迸向永恒。



阿尔蒂尔·兰波的远大抱负:以文字改造世界。一八五四年,兰波仿似一枚自己开膛的炮弹,在一幢十九世纪奥斯曼建筑内降世。那是帝国时代,也是无畏的工业时代,华丽精致、自信昂扬。流亡中的维克多·雨果对人类抱有信念:
“在世界和平建立起来之前,在和谐与统一主宰世界之前,革命将成为进步的发展阶段。”(《悲惨世界》)
一八四一年,夏多布里昂在墓畔表达了相同的期许:
“然而,之后的革命并不是另外的革命,而是大革命的余震。”(《墓畔回忆录》)
大理石像俯视着小家伙,信奉着“人的完美性”这一无稽之谈。儒勒·凡尔纳将尼摩船长【尼摩船长是凡尔纳小说《海底两万里》的主人公】送入海底(1870年),一颗炮弹打进月球。科学在进步,工厂隆隆作响,蒸汽机呼啸而过,巴斯德【路易斯·巴斯德(1822—1895),法国微生物学家、化学家,近代微生物学奠基人】研制出疫苗,巴黎灯火辉煌,剧场座无虚席,四通八达的大道成了世界的轴线,海底电报连接着海峡两岸,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支持工业,资助艺术。集体无意识相信进步,相信科学!全人类都为克雷芒·阿德尔【克·阿德尔(1841—1925),法国工程师,发明了历史上第一架飞机】的飞机起飞而鼓掌!总之,那是希望的年代,街市如昼的年代!
世界正被转交给技术的鬣狗,步入尾声的十九世纪为其拉开序幕而毫不自知。很快,它将迎来凡尔登战役【凡尔登战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发生在德国和法国之间的一次战役】,更糟的是,它有一天会迎来互联网时代!但就彼时的十九世纪而言,进步带来发展。进步尚未翻脸与人作对。
在阿登地区的深处,有一学童不愿为进步拍手叫好。他想要重写人类的全部经历,重构世界,重塑语言、自然与爱情。他想要颠覆感官体验,占领一切,拆散一切,再补缀一切。从蜘蛛到上帝——雨果想要描述一切;从基督教到浪漫主义——尼采想要摧毁一切。而兰波,从风景到爱情——他想要重新表述一切。这个乡下男孩彼时十六岁,住在沙勒维尔。他自诩为宇宙大爆炸:世界可得好好站稳了。
神奇的是,日后他仅凭语言这一武器,便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其成功的首个例证是“金句”的创造,此乃波德莱尔所定义的天赋。【波德莱尔认为创造“金句”是一种独特的才能,而且是一种很罕见的才能】所谓金句是指,作者逝世后,其作品受到冷落,其语言却仍为人们所使用。在兰波逝世后的一百五十年,人们依然使用着当年那个小学童的表达方式:“我是另一个”【出自兰波诗作《我是另一个》。本文所引兰波诗句均由译者翻译,以下不再一一说明】“爱需重新发明创造”【出自兰波诗集《地狱一季》中的《谵妄I》一诗】“不可思议”【1871年,兰波在《被窃的心》一诗里创造了“Abracadabrantesque”一词,意思是“不可思议”。兰波认为,这是一种咒语或是一个方程式】“真正的生活并不存在”【出自兰波诗集《地狱一季》中的《谵妄I》一诗】“把爱情从窗上抛出去”【出自兰波诗集《彩画集》中的《片语I》一诗】这些通通都是少年之语。一个魔鬼般的奇才少年。
对于我们这些二〇二一年的网络牲畜而言,改造语言似是一个荒谬的想法。当政治家声称要管理“初创企业国度”【“初创企业国度”是法国时任总统马克龙出台的一项旨在鼓励大众创业、推进创新的举措】之时,社会便失去了它自身的逻辑。在二十一世纪,语言不再塑刻历史。表演不再需要字词。屏幕湮没言语。然而在兰波时代,语言仍主宰着世界。若想改造世界,则需攻击语言。
兰波的宏图是一个浮士德式的契约。魔鬼以换得浮士德的灵魂为筹码,给予了他获得宇宙奥秘的钥匙。兰波以其旷世才华获得了语言之钥,换取到的是自己未曾体悟到的幸福。
在寄给诗人保罗·德莫尼【保·德莫尼(1844—1918),法国诗人】的信中,兰波阐明了重铸语言的蓝图。一言以蔽之:拆除巴别塔,在一季之内重建语言堡垒。【此处意指兰波日后创作的诗集《地狱一季》】他回顾了几个世纪的文学作品,乔装成一个乳臭未干的先知,狂傲果决地将文学长廊里的“老混蛋”和“亿万具骷髅”清扫出门。他仅想做一件事:表达无可言状的事物。“细看不可见,聆听不可闻。”诗人要么成为通灵者,要么死亡!
因此,诗人的确是盗火者。
他对全人类,乃至动物负责;他须使人们感受到、触摸到、倾听到他的创造;倘若他从彼岸地狱里带回的事物有形,那便呈现其形式;倘若无形,那便以无形面世。需找到一种语言。
盗取火种,找到语言,肩负人类与动物的命运。这是普罗米修斯、浮士德、弥赛亚和俄耳甫斯的使命之集合。
他的雄心不过分,小家伙阿尔蒂尔!



诗人若不以其目光使世界丰盈,那么天地间将是一片死气沉沉。周遭万物沉睡。生活在昼夜交替的蓝蓝暮色中凝滞,田野村庄石化,大自然悬浮停摆。现实在冬眠,我们以一副可怜的、昏昏欲睡的模样在其床头守候。诗人经过,唤醒现实。世界颤抖!醒醒吧,沉睡的心!克莱芒·雅内坎【克·雅内坎(约1485—1558),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位法国著名作曲家】在十六世纪这般唱道。
兰波:
宫殿前万物静寂。流水死滞。影子驻留在林中小径尚未离去。我走过,唤醒了生动温润的气息,宝石睁眼望着,羽翼静默高飞。
林中小径铺满微白簇新的闪光,第一个邂逅是,一朵告诉了我它名字的花。
【出自兰波《黎明》一诗】
我们不妨想象诗人行走在阿登省的小径上,如保罗·魏尔伦在《被诅咒的诗人》一书里所言,兰波沉湎于“最大的逃学”之中。他逃离故乡,一路风光,一路幻象。浪荡是他的小路。兰波步行抵达比利时和巴黎。
他知道如何去看,故明白如何向前。他行步如飞。夏季的阿登省和秋季的默兹河呈现了一个光与影交织的奇妙世界。精神世界的地理坐标在大自然的国度里铺展:荆棘、灌木、沼泽,满是日本人所言的“木漏れ日”——透过叶隙洒落的阳光。在一八七○年的一首诗【指兰波《感觉》一诗】中,兰波(他当时十六岁)写道:
夏日蓝色的黄昏里,我将踏上幽径,
麦子轻刺肌肤,脚踩纤草。
他又补充道:
我将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想。
他记得维克多·雨果在前往翁弗勒尔【法国诺曼底大区昂日地区首府,是大西洋沿岸的一座古城】的路上所作的诗句。倘若法国的小学生足够幸运,遇到的老师教导有方,而非照本宣科的话,他们会将这首诗烂熟于心:
我凝望着思念踽踽向前,
什么也不看,什么也不听。
【出自雨果诗作《明日黎明》】
为何他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想?只因整个世界都在替他歌唱。他唤起了山峦“生动的呼吸”,花儿与他交谈,宝石予他注视,而“女神”,即自然本身,显身于他面前。万物的语言为他揭示。“于是我逐一揭开面纱。”【出自兰波诗作《黎明》】通灵者发现了这个世界。兰波非如海德格尔所言那般,以创作消散笼罩自然的迷雾。他是驱散瘴雾、划破秘密之境的俄耳甫斯。
自然女神的腹地对凡人隐匿,而对兰波敞怀。他已然找到了抵达秘境之法!只需真正地看着它们,待万物道出自己的名字。诗人拨开了罩在我们面前妨碍我们获得启示的蛛网。
世人的字母表构成了诗歌,诗人需做的仅是将其誊写,就好似亚马逊森林里的萨满,吮吸着植株的汁液,而后与其对话。森林里死藤水【又译为“阿亚花丝卡”“南美卡皮木”,是一种具有致幻作用的植物,或指由其制成的汤药】缠绕,吼猴出没。在那里,花有目,木有耳,兽有语,只有奥里诺科河【南美洲的主要河流之一】流域一带的受启者才能悟出其意。而兰波,这个来自默兹河的受启者,他的所见所感并非出于感觉失调(正如他所写的“打乱一切固有的感觉”【出自兰波致乔治·伊藏巴尔的信件。伊藏巴尔(1848—1931)是兰波的老师和朋友】),并非源于萨满的药汤奇效。它来自对世间万物的超常关注!
诗歌,乃成为超现实的现实。

兰波的诗作将自身的图象投射到读者的心理之中。它们不表露什么,也不解释什么。没有论题,亦没有分析。字词将景象投射于我们的颅骨之上。
在这杂乱斑斓之中,一切仿似石洞壁画所展示的那般,野兽与羔羊并肩而行,花朵在腐烂之地怒放,洪流卷席着尸体与少女、苍蝇与钻石。阿尔蒂尔在《彩画集》中指明了“白钢和绿玉”。炼金师【此处炼金师指兰波】对丹炉里的沉淀物一视同仁。
在《彩画集》的末尾,兰波将世界贱卖。他列出了清单:“那些荒诞的无休无止的追逐隐秘荣光的冲动,那些不可觉察的乐事,还有那些面对邪恶令人疯癫的秘密。”【出自兰波诗作《大拍卖》】管它是“邪恶”还是“荣光”,炼金师将一切材料通通熔进炉内。阿尔蒂尔的诗国里没有余存。
波德莱尔在其晦涩难懂的《恶之花》里说道:“你予我泥土,我炼出黄金。”于他而言,艺术需改变生活本质,需净化现实这一腐臭之物。
兰波对黄金与淤泥不加区分。在他看来,黄金并非是泥土的变形,二者相互缠绕交错。诗人碾碎原料,将其混合,幻象时而圣洁,时而肮脏,时而两者皆是。在婚礼上咏诗的孩童,纯洁或是邪恶,皆由兰波随心所欲安排。
任务次序:屠宰语言,而后再创语言。踏进淤泥,而后净化重生。第一天,阿尔蒂尔颠覆世界的根基,第二天他又将神庙修复。破坏、再生:兰波的使命宛如一种生命的乐理。诗人以反向的关怀之心将其推翻的神像捧上了高台。
在创作了数篇可爱的阿登省离家赋格曲【此处“赋格曲”的法文原文为fugue,这个词在法文里既表示音乐赋格曲,亦有(暂时)离家逃跑之意。此处有双关之意】之后,兰波开始了他的洗劫。
从传记的角度来看,在麦田里独行【意指兰波《感觉》一诗】,知晓一切,颠覆一切感官体验;在深谷里仰卧沉睡【意指兰波《深谷睡者》一诗】;在海岸另一边的太阳之下笔直而立,而后返航,于故土的岸上告别人世【意指兰波曾在非洲生活和旅行,于1891年返回法国,而后因病去世】,这便是兰波的历险人生。他的一生,是神秘赎罪的一生。在教堂前方的小广场上,古老的命运显现其轮廓,描出一种对峙之力所维持的平衡——污垢与纯洁的平衡。激荡之中,杰作涌现。赫拉克利特的第五十一篇残篇所言与兰波的人生章法不谋而合。这位爱菲斯学派【爱菲斯学派又名“赫拉克利特学派”,是古希腊哲学学派】的哲学家说道:“他们不明白相反之力如何相辅相成:和谐源于对峙,仿如弓与提琴。”
弓与琴,形式相同。前者用于战争,后者用于诗歌。兰波-赫尔墨斯执琴歌唱,兰波-阿波罗转琴为弓,中伤他所吟唱之物。古老的哲思直觉熠熠生辉:在这世上,万物先历经毁灭,方迎春至。兰波是一扇不幸的彩绘玻璃窗,他惦念着将自己打碎的玻璃重新拼凑起来。在走进《地狱一季》的门廊之前,请铭记赫拉克利特之语——“相反之力相辅相成”。
《地狱一季》的开篇:
一天夜里,我让“美”坐在我的膝上。——而后我发现她辛酸苦涩。——我便对她恨恨地谩骂。
再往后看,诗人改过自新,搁下了弓,拿起了琴。
噢,季节,噢,城堡!
哪有什么灵魂完美无瑕?
一切已成过去。今天,我知道我会向美致敬。
【出自兰波诗集《地狱一季》中的《谵妄II》一诗】
吐痰,敬礼。推倒,重建。玷污,浸洗。赫拉克利特兴许会说“黑夜、白天”。在兰波的诗歌中,温柔与残酷错杂交织在一起,仿如斯基泰人【斯基泰王朝(约公元前7世纪中叶—约公元前3世纪),西徐亚王国的奴隶制王朝,因统治者为斯基泰人而得名】的珠宝图样,豹与鹿盘旋其中,二者呈螺旋状无穷交错,无限生机勃勃,一同滚向死亡。
兰波以执琴的姿势,拉起了弓。他开弓射箭:诗歌喷射而出!赫拉克利特在另一篇章里出卖了这个秘密:“弓的名字是生,其作品是死。”【出自赫拉克利特的第48篇残篇】引弓,联结对峙之物,对立面接触,力量集聚。兰波的名字是弓,他的作品是黎明与黑夜的抗争。
阿尔蒂尔穿梭于天空和阴沟之间。费利克斯·费内翁【费·费内翁(1861—1944),法国艺术评论家、小说家,后文引文出自费内翁于1886年发表的《论阿尔蒂尔·兰波的〈彩画集〉》一书】在《地狱一季》里看到了“一种兽性的美”,它依次招来“鲜血、肉身、鲜花与灾难”。同一张弓射出了天使与魔鬼。而每一箭射中的战士,受到的要么是美誉,要么是侮辱。
纯洁的草丛,多毛的年轻手臂的叹恨!
或是在神圣之床,四月的月光存于心上!
无人照管的河畔工地的快乐,受尽
八月夜晚的腐朽萌芽之折磨!
【出自兰波《记忆》一诗】
在神的形象表现上,艺术家们因循守旧、墨守成规,而这成了阿尔蒂尔首要攻击的对象。十六岁时,他写下《维纳斯-阿芙洛狄忒》(阿芙洛狄忒在希腊语里为“从海中诞生”之意)一诗。我们这些文质彬彬的资产阶级,幼时受过良好教育,在想象的文明博物馆里饱受熏陶。因此一见到兰波的诗题,我们脑海中自是浮现出波提切利所立下的至高之美的范型:金色的头发,乳白色的肌肤,满是蓝色忧郁的双眸。然而,兰波就在那里,埋伏以待。缪斯的浴盆是一片贝壳,女神从中走出,兰波上前,吐出了诗之唾沫。
腰上刻着两个字:克拉拉·维纳斯,
——整个身体骚动着,肥臀伸展,
丑极的美丽,肛门里有个溃疡。
【出自兰波《维纳斯-阿芙洛狄忒》一诗】
自此之后,他不再阻止匈人骑兵的入侵,任其在陈列小摆设的博物馆里践踏蹂躏。兰波是糖衣杏仁里的阿提拉【阿提拉(406—453),古代亚欧大陆匈人的领袖和帝王,被欧洲人称为“上帝之鞭”】,是独角小圆桌上的装甲坦克。砰!洗劫一切。正如他在《地狱一季》中所写,“道德乃是智力的缺陷”。向荒唐,向道德,向幼稚乏味宣战。计划明确,诗人已全副武装。
在其文本里,反转倒置将成为诗学体系。“将臭名昭著当作无上荣光,将暴戾恣睢当作英姿飒爽。”【出自兰波诗集《地狱一季》中的《谵妄I》一诗】兰波处处溅污着他的彩画:用粪便、精液、鲜血和酒精。苍蝇为花儿加冕。
草原弃于一片遗忘,
于焚香与麦草里生长开花
在肮脏的万千苍蝇
野性的嗡鸣之中。
【出自兰波诗集《地狱一季》中的《谵妄II》一诗】
在他的生命中将会出现堕落行径和无赖作风,体验漂泊伶仃之感,迎来那骇世惊俗的爱情的耻辱。在一百五十年前的那个世界,同性恋被视作越轨行为,会遭来切实的刑罚。
我将在我身上划满伤口,我将给自己绣上纹身,我想变得像蒙古人一般狰狞:你看,我将到街上去放声尖叫。
——《地狱一季·谵妄I》
为何阿尔蒂尔的诗国里有腐烂之物?
我的独木舟,总是静止,抛锚固定,
淙淙水波的眼波流转
——使它陷进了怎样的淤泥之中?
【出自兰波《记忆》一诗】
可怜的诗人啊,倘若人间本是这般臭腐,倘若朵朵鲜花都自河底的淤泥中盛开,倘若每个睡在山谷芦苇丛里的俊俏小伙的胸腔上都带着伤口,这难道是他的过错吗?这是开眼者的不幸:看到世界,即看到苦难。倘若诗歌的真义便是捕捉蝇虫呢?



长久以来,他天色微明便起行。
在《被诅咒的诗人》一书里,魏尔伦描绘了阿尔蒂尔于幽径行路而永不知倦的形象:“阿尔蒂尔·兰波,彼时是沙勒维尔市立中学二年级的走读生。他沉湎于逃学之中,日夜不停地在山地、树林和平原里行走,要想等他感觉到疲倦乏力可不容易,他真是个行者!”双重节奏:诗律与步伐。兰波之行路,正如兰波之生活。在生命的末尾,他身患骨癌,病痛让他偿还了先前如苦役犯般的行旅生涯所赊下的账。学校或是他母亲——“铁石心肠”的母亲——解下他的缰绳,兰波趁势溜走。厌倦是他生命中真正的敌人,他最好的激励之物。
为何行走与诗歌如此契合?
首先,行走与童年相契合。孩子相信,生活将是一场历险。行走兑现诺言,对孩子来说是一项不费钱的锻炼。他从映入眼帘的第一条林荫道开始漫步,然而失望的时刻总会来临。
哦!存在于儿童书里的冒险生活。
【出自兰波诗集《地狱一季》中的《谵妄I》一诗】
孩提时代的梦想人生,是吉姆的人生。那是史蒂文森作品《金银岛》的主人公,一个小客店老板的儿子成为了独脚海盗西尔弗的船员。他是波德莱尔笔下的孩子,“喜爱地图与木版画”【出自波德莱尔诗集《恶之花》中的《旅行》一诗】,期望着世界能给予自己珍奇的宝物。
我总是梦见十字军东征,一个人走南闯北四处游历,梦见风平浪静的共和国,被镇压了的宗教战争,社会风俗之大变革,种族迁徙,大陆漂移:我深信所有的奇幻之事。
——《言语炼金术》
林中漫步成了幼年的入教仪式和成人的净礼。他曾绘制出自己“满是厌恶之情”【出自兰波《七岁诗人》一诗】的自画像,而行途之风吹散了这一脑中阴云。沿着曲折蜿蜒的默兹河,他一定走了很久,穿过了茂林峻岭,想必是颇有收获。
啊!我童年的这种生活,从任何时代来看都是一条康庄大道。
【出自兰波诗集《地狱一季》中的《不可能》一诗】
若要撒播幽灵般的幻想,径直走到痛苦之中乃是捷径。痛苦会使人忘记内心的灼烧。
行路人说:“我将什么也不想。”【出自兰波《感觉》一诗】行走,精神之洗涤。“而风,是那么宜人!”【出自兰波《加西河》一诗】若想透彻地思考,则需远离想象世界里的哀叹与憎厌,则需杜绝静坐不动。查拉图斯特拉的生活与兰波相似:步行!而兰波与尼采一样,对扶手椅与让人舒适的东西持有怀疑的态度——那是走向随波逐流的第一步。此外,兰波生活的时代是一个行走的时代。那时法国尚为马背上的国家,人们最常见的出行方式还是步行。尽管铁路逐渐成为法兰西大地的经脉,但现代性尚未缩小空间上的距离。仅为了一次会面,便要步行整整四天,此类之事在彼时司空见惯。一八七〇年十月的一天,兰波为了申请当地报纸编辑的一个职位,步行至沙勒鲁瓦【沙勒鲁瓦位于比利时南部埃诺省】。求职希望落空之后,他继续朝着布鲁塞尔前进。
阿尔蒂尔在田野里行走:收获的是沿途风光。行走,即贮藏材料!之后,他将在旅站,在小酒馆或是在家中雕刻记忆。若没有行走在路上的一季,便不会有《彩画集》的问世。
行走带来思考,酿出意象。身体肌肉孕育灵感,它源远流长,如同中国的羁旅诗一般历史悠久!行路是思想的热力学:从基督的方法,到浪漫主义的坚信和卢梭式的直觉,最终经由兰波的确认,如今已成了老生常谈。一公里等于一句诗!这个等式出现在了《我的波西米亚》中:
我是爱做梦的小拇指,一路
播撒诗韵。
雨果的《见闻录》【《见闻录》发表于1838年,是集日记、回忆、笔记、随感为一体的作品】是其记忆的火山喷气孔。而兰波的见闻录是他沿途的撷采。游子截获了表象。意象是被网住的蝴蝶。
《深谷睡者》的这些诗句可以用来描述蒙特枫丹的柯罗:
青青谷穴,溪流欢唱
厮缠着草地,如银光闪烁的褴褛碎布
太阳从骄傲的山上熠熠生辉
小山谷流光溢彩,若隐若现。
倘若山谷被这般描述出来,定是有人经过此地……阿尔蒂尔随后会将一位“胸腔右侧有两个红色弹孔”【出自兰波诗作《深谷睡者》】的“睡者”置于深谷之中。首先需看到风景,而后才能创造风景。在书房里——窗帘紧闭而护窗合紧——溪流不会“欢唱”。
阿尔蒂尔甚至从未叩问过自己的存在,对文化谱系亦是漠然置之。他属于这样的一脉:基督的疯子信徒【此处“基督的疯子信徒”的原文为fols-en-Christ,指的是放弃物质财富,尊崇宗教,挑战时代规范的人。该说法由圣保罗提出,方济各会的宗教人士多采取这样的生活态度】,在朋友般亲切的田野上无所事事的流浪者,云游四方的禅僧,俄国巡回画派【“巡回画派”全名为巡回艺术展览协会,是19世纪的俄国出现的重要画家组织。画派的画家们反对当时俄国保守、直接取自西方古典主义的艺术思想,主张为普通人服务的现实主义和民族主义艺术】的画家,大路上的招魂人,半伪善半圣洁的流浪汉,向尘埃寻求精神的解放。
这支行进的队伍在身体的疲惫感中寻求启示。《彩画集》的问世标志着行旅诗人把寻找奥义的探索抬升到了崇高的地位,直至给出如此定义:“寻找那应去的地方,寻找那应有的形式!”【出自兰波《流落》一诗】



在许下童年的誓言之后,兰波揭示了对抗倦怠的两剂良药:诗歌与旅行。道路和写作。后者的尘土将成为前者的养分。
奇迹藏匿于历险之路,形形色色的流浪者都知晓这一秘密。在路上,世界缤纷热闹,思绪流动汇聚,字词组成卫队。行走驱散焦愁。此乃毋庸置疑的炼金术:游子行于路,窃走形象,再将那形象抛在纸上。此乃游历四方的通灵者之行径。穿越世界,再用二十六个字母重组世界——直截了当、神奇非凡的行动赋予了漂泊四方、风餐露宿的生活以意义。沉醉于行走的人坚信:尚未经历之事,无法诉诸笔端。
魏尔伦称好友为“履风者”【出自魏尔伦《被诅咒的诗人》一诗】,穿上“风之鞋”是为了躲避良心,躲避自身的阴影与倒影,躲避自身的空虚——总之,躲避自己。
出发是为了避免坠入自身最大的“空洞”之中。
“来吧!奔波,重担,沙漠,厌倦以及愤怒”【出自兰波诗集《地狱一季》中的《坏血统》一诗】,这是《地狱一季》里的诗句,亦是兰波的座右铭。生活是我的沙漠,厌倦是我的苦楚,而行走是我的药方,愤怒是我的激励。在躲避中获得生命。烈日炎炎,穿过黄沙,影子尾随在身后,他在字里行间里向着死亡走去。
诗歌与旅行兴许会把诗人引向波德莱尔(兰波曾读过其作品)所描述的最后的终点:“到那未知的深处,去寻找新的事物。”【出自波德莱尔诗集《恶之花》中的《旅行》一诗】
在一八七一年写给德莫尼的信里,兰波曾对通灵者进行过一番描述。十七岁的诗人还写道:“他培育了自己的灵魂,已经丰盈富足,比任何人都要丰盈富足!他进入了不可知的世界。”
还有这封信寄出的几天前,他对伊藏巴尔说的那句名言:“这关乎如何颠覆一切的感觉意识,以达不可知之境。”【出自1871年5月13日兰波致乔治·伊藏巴尔的信件】
十年之后,兰波对于不可知的渴求并未消停。不过,他的瞄准线有所变化。季节啊!追求啊!轴线更替了。兰波不再想要探索语言(他曾写“需找到一种语言”【出自《兰波致保罗·德莫尼》】),而是期望行走四方。他的生活将千变万化,无尽无休。然而这正是他所渴求的。
现在,“不可知”位于文字之外。人总是向着童年的印迹和世界往回走。待无人聆听之际,大地始终在那里。除了大地,一无所有。
生命趋向终结,循环闭合。兰波的一生,自阿登省的深谷漫步拉开序幕,以阿拉伯砾石堆里的行走作为终曲。在一八八五年一月写给家人的信中,他说道:“无论如何,不要指望我的流浪性情会有所削减,恰恰相反,假若我有办法去旅行,无需为了生计而停下来工作,人们不会看见我在同一个地方待上超过两月。大千世界,满是神奇之地,人即是有千次生命,也无法将其一一探寻。”【出自兰波1885年1月15日寄给家里的信】
兰波的一生:逃跑的一生!以厌倦为起点,沿途寻找新的事物,最终走向不可知。先“找到一种语言”,后探索世界。
一八八二年九月,他写信告诉家人:“我仍在原地,但我打算离开。”
为何有些人漂零一世,扬帆出航,永无休止?为了不被自己追赶。
天涯羁旅,永不停歇,其益处是不会在镜中瞥见自己的倒影,亦不会在辗转反侧之夜撞见自己的良心!

法国人西尔万·泰松(Sylvain
Tesson,1972—)是作家,也是记者、地理学者、旅行和探险爱好者。2004年,泰松以游记《狼轴》获得广泛关注,近年来接连获得龚古尔短篇小说奖(《睡在外面的一生》,2009)、美第契杂文奖(《在西伯利亚的森林中》,2011)、雷诺多长篇小说奖(《雪豹》,2019)等。迄今,泰松已出版9本游记、7部短篇小说集、10部摄影集。
泰松是一位致力于将“诗”与“远方”结合的作家,他认为文字是“行动最终的形式”。
原载于《世界文学》2022年第4期,责任编辑:赵丹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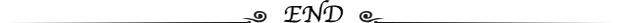
点击上图,订阅全年《世界文学》
点击上图,订阅单期《世界文学》

添加《世界文学》小助手
获邀进入《世界文学》分享会3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