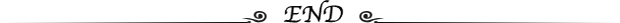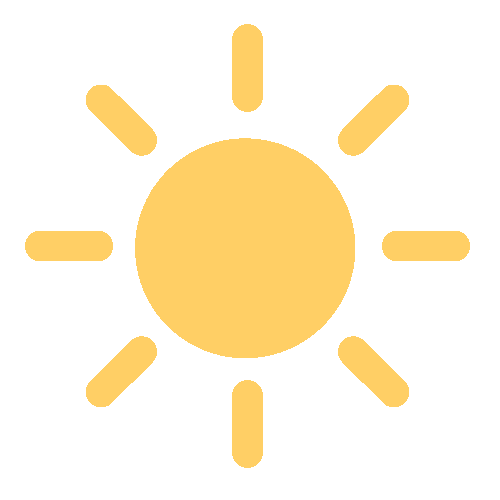小说欣赏 | 尹贾溵【韩国】:飞吧,海马
![]()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Plum的灯灭了。高高的建筑物,似毒瘤、似牛角耸立的夜里,为了看到月亮,还得走动走动。穿过人行道,经过小胡同,张望天空,再向后退几步,才能看到这长着肿瘤、长着犄角的城市的月夜。像谁的瞳孔,闪烁地,一张,一合。伊丽莎白,您,为什么,没有出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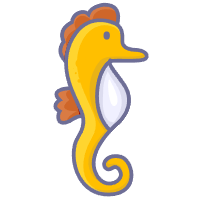
尹贾溵作 臧晓程译

市面上出现了一种有特殊功能的手机。每当手机用户血液中酒精浓度超过0.05%,手机就会自动停止呼出功能。这种“防止饮酒通话”功能是在最近的手机开发创意大赛中获大奖的方案。开发商在手机上安放了电子传感器装置,当用户讲话呼气时传感器就可以自动测量酒精浓度。当手机上的电子传感器测量到用户正处于酒后通话状态,手机信号就会自动受到限制;而当用户血液中的酒精含量降到0.05%之下后,手机呼出功能会自动恢复。考虑到酒后通话有时会引起不亚于酒后驾驶的精神和物质上的伤害,不能不说这是个划时代的创意。(后略)

上面这段文字并非新闻稿,而是社长撰写的广告文案;目的也不是宣传防止酒后通话功能,而是鼓励人们酒后通话。这篇文章随后谈到,带有防止酒后通话功能的新型手机上市后,没有此类功能的老式手机在二手市场上广泛交易,而公用电话卡也随之走俏。这段文字的重点其实是:酒后通话是人无可奈何的本能,与其打击和扼杀,倒不如将其纳入良性运转的轨道。文章的末句是“通往酒后通话良性化的路上有‘海马005’”。
调查显示,喝酒后的“那些麻烦事儿”中,比率最高的就是酒后电话、酒后邮件以及酒后传真。这当中电话又因为总是随身携带而最为危险。酒后通话又没有酒后驾驶那样的法律约束,因此更增加了危险性,因为没人能自觉下决心根除这种行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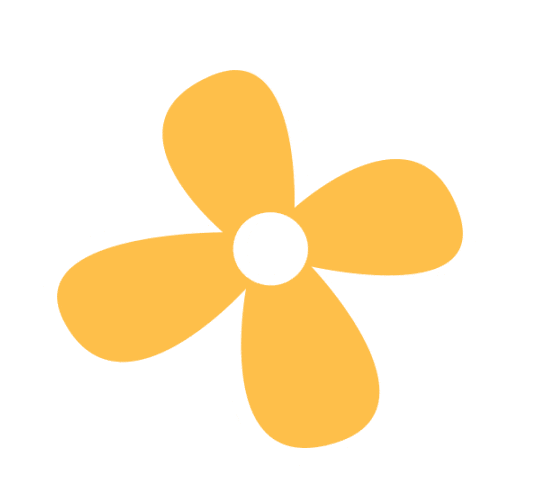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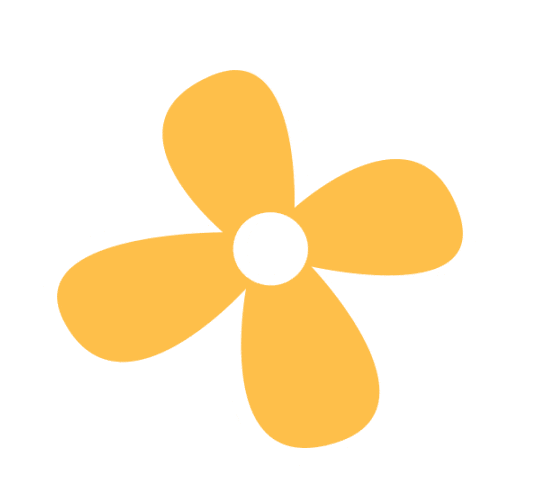
手机电池比您夜间忽然中断的记忆都长寿,第二天早上依然为您显示那些不受欢迎的通话列表。而且通话时间会被原封不动地记录,有时显示打了一个小时您却想不起说了什么,有的通话不满三分钟,那个号码您却有可能按了十来遍。这些都有可能归在“去电”列表。尴尬的是您的话语早已脱离地球,只有您留下在地球上。这个时候的郁闷肯定是起源于“被偷”的心情,而不是“流失”记忆。即使您紧握手机,望眼欲穿,即使您捡起来再扔掉,即使您按键关机,即使您到处发短信试图让手机过劳死,那也是覆水难收了。哪怕您觉得它像同谋犯,甚至是主谋,实际上呢,手机只是见证人或作案工具,应该被判有罪的是您。
喝酒之后不许打电话是因为酒精杀死了血清素。一旦血清素死了,心情要么过于低沉,要么过于兴奋,人就会变得忧郁而孤独。酒精招惹了调节感情和冲动的额叶。酒精招惹了额叶的海马。如果海马中的记忆输入装置出了故障,那么已经中断的胶片即使催眠也无法再生。这是因为时间无法输入了。
中断的胶片,与其交付给朋友、爱人、家人,或是同事保管,倒不如交至专业销毁废弃物的地方。因此海马005是很有用的。您在这里消费的时间在终止通话的同时也消逝了,因为谁都记不起来了。简而言之,海马005便是为酒后通话而开设的电话号码。讲不讲话却并不是重点。打电话的人和接电话的人相互确认,两个人的嘴与耳相对,就能实现通话了。每分钟一千五百元,几乎是越洋电话的话费标准。即便如此,通讯公司却辩称由于用户使用这一功能时都以秒为单位计算,这样的收费标准也不算过分。这种服务主要的目标客户群体有三类:为了像保持体温那样维持酒精浓度而老老实实注入酒精的人、保持适当酒精浓度的人、还有像您那样忍受漫漫长夜的人。
或者喝酒,或者睡觉,或者说话。


夜晚来临之前,海马005的电话号码就如同传单似的在喧闹的街头散落。海马005的广告随处可见,汽车的挡风玻璃,酒家的洗手间,KTV的入口,地铁的墙面,公车站,还有公用电话亭。在酒家一结完账便可以有海马005的优惠券拿。在烧酒的瓶盖里面,或是啤酒的拉环下面都可以看到海马005的广告。海马005里有时候还藏着各种不同的优惠,就像是前五分钟免费,或者十分钟后的通话费七折等等。海马005是只给那些有需要的人群看的。又或许在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海马005早已安装在您的手机里了。拨打短号0或1即可使用。为了改掉一喝酒就爱乱打电话的习惯,人们便在清醒时编造了手机里面的记忆:0号键,或是1号键。人们无意识地把海马005设置在最方便自己的位置,每当自己酒气熏天的时候,就按下0号键或1号键。关于您中断的胶片,我们既不追究,也不责怪,更不会回避。我们只是与您共同分担。
晚上九点到次日凌晨五点这段时间里,我(海马005)偷走了您的时间。最多曾偷过两个小时。就在不久前,被我偷走了两个小时时间的您,在事情过后一周,给我来电话了。“上周五这个时候给您打过电话,您还记得我当时说过什么吗?”您还辩解说这样忘了自己说过什么的情况还是第一次。
诸如此类的事件不计其数。经常会有人想确认自己在喝醉酒时说过的话,甚至还会询问是否可以告知自己昨晚说话的大致内容,有人还会确认对方是否录了音,是否获得了自己身上什么情报。然而我呢,却连您是否是我的顾客,是否与其他客户通话了都不知情。我们并不会记下客户的姓名,更不会记下客户的声音。就算当时有些印象,等今晚再接了其他电话,新的记忆又会覆盖昨夜的记忆了。这便是我的工作,也是我担当这份工作的理由:不断地接电话,在分钟与小时的累计中,赚取高额的话费。
我自己的记忆也因为过度劳累而受了损伤,您知道了以后松了一口气,不知是放心,还是失望,您长舒的那一口气中,满是酒味。您虽然早已确认了来电原由,却又迟迟不愿早早搁下电话。您常常会毫无征兆地就开始聊起今天喝酒吃菜的那些事儿。点的肉里面的那些墨鱼芥末、豆芽菜,这些都通过一条电话线,传到了我的耳朵里。您通常一聊就聊至天明。您聊这些事儿的时候,仿佛是在炫耀自己的下酒菜似的,越聊嗓门就越大。您可能也只会在快挂掉电话的时候,偶尔想起来才问一下我的名字;又或者记着了我的名字,下回喝醉酒了还是我喊我的工号让我来接听您的电话。虽然有时候您也不见得会问我的名字,可最近常找的老客户是越来越多了。我现在就是在告诉您我的名字:海马8号。


如今您已经是海马8号的常客了。做我们这一行,一旦有了常客,津贴也就更高了。
电话打来了。您的声音里夹杂着酒气,摇摆不定。好几通电话都是刚连上,就马上挂断了。您的好奇心转眼变为恐惧感的那一瞬间,就算是已经挂断了电话,在另外一头的人仍旧可以感受到您的恐惧感。其实比起恐惧感,孤独感会更强烈,因为恐惧感是可以通过不断地重复某一件事来克服的。每当我拿起听筒,接听来电,就仿佛在对宇宙发送信号似的:您、在、哪、儿?
绝对不会问说“您、是、谁?”或者“喂,您、好!”更不会问“为、什、么?”若是那样询问我便成了“回复答录机”了,而现在我要成为“您”。
从午夜的突然来电开始,热线电话便似陡削的上坡路,一直一直不断地往上爬,之后又以凌晨三点为划分点,又似下坡路,来电数量一点一点下移。随着时间流逝,来电也渐渐减少了。有的时候也就一通,有的时候会再来一通。大概到凌晨四点左右,我旁边的,或是前面的接待员就开始接二连三地去便利店买东西吃了。杯面、巧克力、三明治、冰淇凌、饼干等等,这些吃的玩意儿就像配额似的在我们的工作站里被分给大家。夜幕降临。窗外,市中心的天空像受了伤似的,通红,又映着碧色。这种阵痛,便是日暮之后迎接新的一天所要承受的吧。断断续续地会有电话打进来,这之中会有几通是噪音,又有些尽是沉默。


我还没等决定好下一个去处,就大学毕业了。父亲按着简历上的栏目,开始对我泛起琢磨来了。学历、外貌、外语能力、相关经历、谈吐、性格……父亲对照着这些“客观条件”,站在相貌平平的我面前,开始晃荡他的脑袋了。我们家,一个连大学学费都得靠我自己解决的家庭,竟然也开始谈及我整形手术的事宜了。父母们讨论着说要割个双眼皮,再动动鼻子。尽管我推脱说“就连刺猬还觉得自己孩子长得好看呢,你们怎么嫌我丑”,却被父亲一句“这样的孩子恐怕得绝种”给塞了回来。“要承认,有发展的才可以存活下来!”父亲这回是认真的了。
“(我们)也是看你总是在面试中被淘汰才让你去做整形手术的。不然的话,你就试试去找找只需要声音的工作吧。你不也就声音不错嘛!”
“我也并不是长得不好看啊,只不过不符合您的审美标准罢了。”
“金科长也这么认为。李部长也是。”
“先把整形手术的报价单拿来吧。”说着这话的父亲,就像很有责任感的A/S记者似的。
我没有去整形科做估价,而是去了我的第六十三次面试。第二天是第六十四次,第六十五次。就这样,到了第六十八次的时候,我的简历被留了下来。这家企业曾经是我觉得羞于启齿的地方,可是大学毕业都一年多了,钱都花完了,况且也过了要面子的时候,更何况这还是我唯一通过了面试的企业。实在也是别无选择。


我就这样成了海马8号。虽说起初也不过是抱着暂时先做做的想法,不知不觉却已经做了好几个月了。其实并非父亲所言我因外貌不出众而在求职中屡遭挫败,看看我们接收站里面那些外貌姣好的同事们就知道了,就业难的问题分明就是远远超出了外貌、学历这些显而易见的条件的前提。可以说这是全国的问题,或许也可以说是全世界的难题吧。
就业难是全球性的问题?这话行得通吗?言之有理的人自然就有他的道理。您便是这样说的。我看了您的个人信息。自从您成了我的熟客,我便努力地对您的事情有所记忆。当然仅仅是对那些必要的话、对对话有用的话才记。您通常都在星期五打电话过来。正准备着公务员考试。三十七岁。啊不对,上一周那位还是三十四岁来着,之前那一周另一位客人也差不多是这个年纪吧。总之这不是什么要紧的事儿。反正这喝酒呢,年纪大的喝,年纪小的也喝。今天不过是强调了即便三十七岁的您。反正成才的人总归是成了才。成才的人都成了才,可为什么我周围成才的人连一个影子都没有呢?只有在父母周围才可以看到那些成了才的人。父亲朋友的儿子,母亲朋友的女儿。他们那一帮人都是一伙儿的,要不就是那些成才的人恰好都在我父母身边。
海马24号被解雇了。凌晨两点钟的时候,社长来给海马们分工间餐的时候告诉了我们这个消息。每人分到了一个夹了两片芝士的汉堡。上班已经有四个月了,体重按着工作时间增长成正比地上升,每个月都长一斤肉。社长说海马24号被解雇的原因是喝了一瓶以上的烧酒后仍然在做酒后通话工作。社长还说在酒后通话服务界,员工酒后进行通话工作是何等严重的问题,让我们自己去思考。“我们为了酒后通话的客户,做事应当有专业精神,这里的职员们应当时刻注意提高专业素养。(对于海马24号那样的失误)是无法容忍的”云云。
听罢,海马们静了下来,默默地吃着汉堡包。面包热得刚刚好,酱料里面夹着莴苣、肉片,下面还有两片芝士。海马24号的酒后通话细目是客户揭发的。只能说是海马24号运气不好吧,客户的酒精浓度就和谎话一样单薄。酒后通话并非是只有喝酒之后才可以打的,不喝酒的客人也可以拨打酒后热线。喝了酒的海马24号与几乎没有怎么喝酒的客人掐架了。事情就是这个样子。海马24号的声音那样粗糙,他的情绪那样冲动的原因,都在于酒精麻痹了额叶。哎,反正这件事情和我也没有什么关系。海马们奋力地啃着自己手中的汉堡包。社长说有与我息息相关的事情要宣布。
公司为了保住市场份额必须得发展外国语服务的功能。首先得从掌握英语开始。
说到英语,我也是勉强把“口语不错”放进了自己的简历里。面试的时候公司只是要求我们要有正面的思想,现在又要求英语能力,哎,公司总是在随便地变。



最近,外国劳工的数量在英语补习班、零件厂、照料婴儿者、产后调理员、食堂等所有的职业里以几何级数上升,还要再加上嫁到韩国来的人,还有来韩国旅游的外国人。也就是说,最近消费酒水和电信的客户已经不仅仅是韩国本土人了,所以,海马们的工作也不能仅仅用韩国语了。最紧缺的最热门的语言要数日本语了。日本人爱喝酒。但凡爱喝酒的人,便都是我们的客人。
虽然英语是基础,但是相信未来一定也会要求学习越南语、汉语、日语等等语言的。社长最终的目标或许是在海外开设分支机构了。由此一来,将来说不准那些不会外语的海马们就会被淘汰了,于是海马们纷纷买外语书学习起来了,有些海马还在语言学校报了名。我也应该做些什么了吧,如果不想像父亲所说的那样渐渐绝种的话。
在三十分钟的通话时间里,您的语音背景从街道换成了的士,从的士换成了小巷,从小巷换成了公寓走廊,又从公寓走廊换成了玄关门。凌晨三点钟的归家之路虽然可怕,但比这更可怕的是电话通信——这就是我们如今生活的世界。有两个朋友下个月都得出差,除了我之外,您再也没有其他可以打电话的人了。您说自己偶尔也会被自己高跟鞋踩地发出的清脆声吓到。
所有的客户都被确定下来了,全部。因为到处打工的孩子越来越少,大家都成了合同工。要么干满两年转为正式工,要么被开除。两者必居其一,对吧?从现行法规来看,的确是这样吧?
我一真心赞同这一看法您就会询问我的年龄。虽然您是长辈,但称呼却也不变。您问我:“姐姐有客户吗?客户呀,客户,我是在问你有没有交往的对象啊。”我两个月前和“客户”玩完了,虽说交往有两年了,但仍没有正式确定关系,也没有分手的意思,就这样拖着,最后还是我自己递了辞呈。
“您这不是在说工作吧?是在说恋爱吧?”
“工作和恋爱都差不多呀,两者是连在一块儿的。别看我自己是这副样子,其他朋友们都一个个地抓住了自己的那个‘客户’,经过两年时间赶快就正式确定关系了。”
“是说要结婚了吗?”
哎呀,您这姐姐也真是的,像黏糕似的问起话来穷追不舍的。再怎么说这也不是我该操心的事情,都是朋友自己说的。虽然结婚了,却为新婚旅行去哪儿烦恼不已。姐姐,您说这像话吗?我虽然不清楚最近大家新婚旅游都是去一回还是去两回,但光是选择旅行地点这件事情已经够让他们头疼了。总在为去长滩岛,还是去巴厘岛而烦恼。所以我就说了嘛,这次先去长滩岛,下回新婚旅行时再去巴厘岛。可没想到我那位一听这话就大吵大闹连哭带喊地抗议,我也只好先起床出来透透风了。哎,真是烦死了。在听吗?我说得有道理吧?姐姐你也是这样想的吧?有了老公又怎么样呢?姐姐你觉得丈夫是人生中的必要条件呢还是充分条件?又或者是必要充分条件?虽然能记起来是从左边射出去的箭,可是哪边充分哪边必要已经完全混淆了。啊呀,真是烦死我了!



我听到了您走下出租车的声音。我好奇您是不是公司职员,便问了。
“公司事情多吗?”
“超级多啊。”您这样回答着。您说自己在广告公司工作。您却不知道自己可以很好地搭乘下趟来临的列车这一事实。当开往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的列车们向您隆隆驶来又逝去的时候,也许您从未有过怀疑。就像是在火车上,为了走到下一节车厢而突然打开门去穿过这个车厢一样,跟着昏暗的尾巴,生活的这副模样,您怕是从未见过吧?您经没经历过那样的茫然并不重要。可以确定的是,您现在最多不过是把就业难用作一个比喻的工具罢了,您这样说也有自己的理由,而我呢,却觉得您谈论这个话题便已经是一种奢侈了。然而这也是事实。我表示赞同您的意见,还在适当的时候随声附和了几句。海马,其实是在扮演着聆听者的角色。您或许并不明白我的心意,但您的舌头却在通话中更松弛更自然地弯曲了。
现在“招聘”都设置在几个不同的地方。这个月的周末一直在面试,上个周末也去了一次。哎,只能说那公司太臭了,就算对方觉得可以我自己也不愿意去。下周末又有两个面试,通过的话,那就,那就……因为面试和相亲会是一样的。通过“面试”的话,再经过“实习”,就可以“签约”了。也许我也可以定下一个“客户”了呢。哎。
哔哔哔哔,我听到快速按密码的声音。您进门了。姐姐慢走,您说。
如果“想走”,现在还剩三个钟头。如果说那个地方是家的话。我还不能直接回家,我必须经过许多人的谈话。这个时间段的话,大概一通电话结束之后,约七分钟之内就会有新的“您”再打电话进来。你们大多是边在路上走边打电话的。从喝酒的地方到家,从第二轮聚会到第三轮,或者从第一轮到第二轮,从洗手间到酒家旁边的小巷子,又或许是从朋友1到朋友2,从朋友2到朋友3,再从朋友3到朋友4,偶尔越过那些不接电话的人,像踩着踏脚石,或者像蝗虫似的随处逗留。然而要找到像我这样可以愉快地接起电话的朋友可真不容易。我既不会怪您深夜了还打电话,更不会给您脸色看。
谈话的大部分内容是关于开始与结束——公司生活的开始与结束,恋爱的开始与结束,婚姻生活的开始与结束,除此之外,便是些跑远的话题。关于很细微的开始与结束,恰好可以由此区分夜晚和白天。您这样海阔天空地聊着,到了日出之前又会自觉地绕回到原来的正题上,就好像身体已经从酒醉中醒来似的。开始也罢,结束也罢,但有些东西是无法收尾的。
谈话就像酒杯一样,酒杯从第一个人手中传递到下一个人手中,渐渐地便分不清楚酒杯原来的主人了。谈话也是这样——从第一个主人的舌头开始传到下一个人,至于谁才是谈话的主人,那条界限也渐渐模糊了。
我的故事成了您的故事,您的故事成了我的故事,原本的话是“我的朋友”,“是我朋友的爱人呀”,可渐渐地大家传来传去,就成了“是我呀”,“是我的爱人”,更有甚者,还会把客户的故事与自己的人生给混淆了。


星期五的客户问道:“喝过五十度以上的酒吗?”我虽然不曾喝过,可是通过想象也足以编造出与您的相似点。
“几个月前喝过一次。感觉好像嗓子里进了刀子似的。”
您说那感觉就像嗓子里面开了花似的。您嗓子里面开花的这一意象让我联想到了我父亲。去年春天的时候,父亲没有提起兰花的花茎,把烧酒稀释在水中就这样浇到花盆里面了。父亲在今年春末被卷入了结构调整的风波。这一次花就算不喝酒也一定能开,借酒浇愁的反而是父亲。确实是这样,酒如果过了几个小时,就会有肥料的作用。父亲每日的必修课不是喝酒,便是睡觉。在过去的几十年间,父亲单只养成了这点儿趣味。“爱喝酒的花就开得好啊,你也多少喝点酒吧。多喝点酒今后是用得到的。想变漂亮的话就应该用大碗喝!无论如何你现在偶尔也得喝点。”
父亲说,一个家里最多只能有一个无业游民,可现在我们家里有两个了,这可得出大事了,所以我只好晚上去做电话相谈员的工作。把找到工作的事儿和父亲一说,他的脸色才不那么难看了。这些都是四个月以前的事情了。虽然我总希望父亲不再说我要灭种的话了,但他却总以一种看“珍稀动物”的眼光审视着我,就像此刻的您一样。
春天逝去,花儿若不再开花便也没了所谓。然而父亲却即便过了春天却还是有罪恶感。他的症状就是经常喝酒,说话也少了很多。父亲经常像花朵似的躺着。父亲仿佛在安安静静地接受这个世界的输血,除了蜜蜂和蝴蝶,谁都不许打扰。我真希望父亲能说不开花也没关系,职场毕竟不是花朵,可是这台词对他来说实在是太难了。尽管职场确实不是花,然而如果不是有意为之,没有职场的生活还是很孤寂。再者就算说了花朵不开花也没有关系这样的话,也没法说服我们家的账本呀。就像我早已忘了找可以说出这些话的机会,我和父亲其实几乎都见不着面。我和父亲的时间表正好是相反的,妈妈又在忙新的保险计划,我们一家虽然住在一个房子里,彼此之间的关系却相当疏远。


有些人装作很了解海马的样子,说我们只不过是储藏记忆的装置罢了。然而准确地说,海马不是储藏记忆的地方,而是输入记忆的地方。海马虽然蜷缩在每个人的脑海里,可酒喝多了它的性能便会下降。问我名字的人通常也会问为什么我叫海马8号。其实就是因为我是进公司的第八个职员罢了。现在我都已经数不清那之后公司又招聘了多少海马了。社长为了扩张海马005正在孤军奋战着:在同一时间内打进来的电话中熟客优先的服务,与代客驾车公司的合作,广播广告,特地为白天喝酒的客户而提供的白天酒后通话组……熬夜的海马们开始关心起白天组的工作了。光是想象着自己不用再乘坐最早一辆地铁下班,海马们的屁股就更沉重了。要说该如何设置海马005的话,那就是更执着地工作呗。我呢,也得更努力地接听您的电话。
我和您就我们所在的这地球是否是圆的展开了话题。正在准备公务员考试的您成日里坐在四角方桌前,也因此对于没有棱角的物体,地球也好,宇宙也好,太阳也好,月亮也好,光是这些单词的发音就足以让您欢喜的了。酒精的作用让您说得更溜了。“棱角”已经在您嘴里坍塌,您说出来的全是些没有“棱角”的单词。宇宙,太阳,月亮,与地球,还有您的脸庞,每个人的脸庞,大家活在这地球上的理由总不是为了落榜吧?根据地球的构造,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人:失败的人和坚强的、运气好的、敢于坚持到底的人。您属于哪一种呢?您说自己现在属于前者,但正朝着后者的方向努力奋斗着。
您相信神的存在吗?您相信神是理性的吗?这微不足道的存在,倘若有神的话也会将您驱逐出地球吧。一旦选举出了问题,选出来的总统便可长期集权统治还赖着不肯走,这样的情况也不是没有发生过,可难道还有别的方法吗?如果神灵泉下有知,我们这些小人物也不至于如此吧?难道不是吗?
我并不相信神的存在。
可是,每个周末,您都会去教会。虽然不相信神的存在,但每周的教会活动却从不落下。就好似抽烟,又或者和每周五晚给我打电话一样,周日的教会活动不过是众多您无法戒掉的习惯之一吧。因为一旦戒掉的话,就会有后遗症。
海马们各自拿着整只鸡的一部分,听着社长的故事。有的人拿着鸡腿,有的人拿着鸡身,有的人拿着鸡翅膀,有的人也不知道自己拿的是什么部位,全凭空猜想。把大家手上的鸡肉都合起来的话,应该得有足足的三只鸡了吧。海马们不要别的东西的原因在于他们经常相互交换。对于性骚扰的客人,每个人的反应都不一样,有两个人承受不了就自动消失了,另外两个人就相安无事地继续在公司上班。这其中的标准取决于客户的投诉。倘若客户一直投诉的话,就算是海马005也没有办法。社长经常强调说我们的工作怎么说都属于服务业,必须以顾客为上;就算喝醉酒的客户也是上帝,即便心中有抱怨也只能往自己肚子里吞,我也是这样调节自己心情的。在饭店也好,在网上购物也好,就算平时的心足够包容,孤独的时候也别无他法,只能这样排解心情。
依照社长的话,父亲的状态还真是危险。一向在家都不怎么说话的父亲,一个月的电话费用却出奇地高,妈妈为此开始在家里嚷嚷。父亲却连一声辩解都没有。他能打给谁呢?家庭购物的售货员?呼叫服务中心?114的接待员?还是119或者112?能是哪里呢?答案竟然是广播节目里面接受听众来电的DJ们。
父亲看了蒸汽电熨斗的家庭购物广告后就急忙打电话询问电台DJ自己是否需要这样东西。与蒸汽电熨斗的销售相谈甚欢的父亲,那个模样,一定是孤单极了吧。我竟然连父亲没有可以告解的地方这件事都不知情。父亲就算问尽了蒸汽电熨斗的一切有关事宜,到头来也不能买成。十二种男性化妆品、万能洗衣剂也是如此。“嗯,知道了。让我考虑考虑再和您联系。”父亲总是以这样的句子结束通话。从海马005的客户类型来看,父亲就是“蝗虫”型。无论辗转几个咨询员,一次通话都维持不了两分钟,即便如此父亲也不肯放下电话。真是“蝗虫”。
趁着父亲睡觉的时候,我在他的钱包里面放了海马005的优惠券。像咒符。
不久前和一个外国人有了聊天的机会,他问我家乡是哪儿的。我回答说是浦项【浦项,位于韩国庆尚北道,工业城市】。“您一定不知道吧?”“啊,您知道?我这都和您说过了?”反正外国人会问我在那里生活过多久,我说生活过二十年的时候,他们都会吓一跳。我以为是问我在那儿住了多久,其实并不是这样的,他是问我从这里到浦项得多久,路远不远。从这里到浦项,走路的话得二十年吧,呵呵。那个客人还以为我是从月球上来的呢。怎么会呢?就算走到地球,也用不着二十年吧。哎,真是的。
虽然您笑得就像快要把电话机给崩裂似的,我可怎么都笑不出来。您已经有两年没能回家乡了。虽然并不是二十年,对您来说,这两年,四次大节日【指每年的中秋和春节】都是残忍的。回家残忍,不回去也是残忍。虽然您这次中秋不能回家,可却不能保证说这是最后一次。
你那儿也看得见月亮吗?您问道。我虽然看不到,却回答说看得到。看到看不到,反正都是圆月之日。您说月亮不过就是个洞罢了。瘪瘪的,小小的,圆圆的洞,只不过口子还裂得不大,但也不就是个洞吗。
如果联想到实体,那就困难了。别人会透过那个洞窥视我们。月亮就是通道。知道这个事实的就只有两个人。
我假装很严肃地问是谁,您回答说:“我,还有伊丽莎白女王。”
“伊丽莎白女王?英国的吗?”
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
“为什么是伊丽莎白女王呢?”
您回答说,其中的原因只有伊丽莎白女王自己知道。
“伊丽莎斯人?”
是伊丽莎白!
当我正为是否要把您的话当作玩笑陪着笑一笑还是该当作真事保持沉默才好而烦恼时,您突然张口了。
“啊,现在又多了个人了。你。”
虽说是三个人,不算伊丽莎白女王的话其实也就是两个人,那我们两就成了共犯啦。下班路上看见清晨天空的月亮,那是熟透了的圆。仿佛隐藏着世界上所有的棱角,像定时炸弹似的升起。一闪一闪,眨着眼睛。
海马们不仅仅做输入记忆的活,还把记忆分类。在短期记忆与长期记忆的分类之中,当然也有一些消逝的记忆。不重要的,也就不记了。社长依次呼叫我们。虽然不知道会从海马1号到几号,不过在特定时间里上班的几个人都会被叫走。我也被社长叫去过。他说,您消失了,留下的只有您的手机,还有记录在手机里的海马005的号码,还有电话账单。您的丈夫问,不会说韩语的女人在这儿能跟谁打电话?我的海马受着煎熬。其他人都在追查您的纪录。您说了什么话,打了多长时间电话,为什么哭,又为什么笑。很抱歉,我的海马之中没有您的位置。说的是哪个您呢?我把这话塞回舌头里面,收窄了视野。无数您里的外国人,外国人里面的女人,视野被我压缩到几个“您”。然而在您消失之后,我却连您的一句话都想不起来了。
也许是因为您难以理解我们的语言。因为您所想象的“我们的语言”并不是韩语。您以您自己的语言说话,尽管我无法理解您的言语,不过我或许能理解您的心情。我读懂了您的呼吸。难道您以无法解读的语言吟诵遗书,也许您是在啜泣。您一会儿念念叨叨,一会儿哭,一会儿又吵吵闹闹地,又会立马安静下来。对于这样的您,我能说的,也只不过是对不起了。对于无法理解您的语言这件事,我感到很抱歉。最近时而会打进来这样的电话。所以,您并不是一个人。所以,我无法分清您,和别人。
我因为无法回忆起您的样子而难受的那天,又有别的“您”安慰我。您不清楚我的状况,您虽然只管说着自己的话,那对我也是一种慰藉。您重复说着相同的话。从抢劫钱财的人手中逃出来的经历,从看热闹的行人中逃出来的经历,从让人害臊的事情中逃出来的经历,虽然偶尔也曾从神那里出逃,最困难的要数从过去的记忆中逃出来的事情了。不久之前听说了英国开始在市场上贩卖一种忘却药丸。已经可以了呢。这种药丸发明之后,伊丽莎白还颁发了专利。虽说女王想让忘却流行起来的阴谋听起来有些可怕,不过肯定是有意义的。在这之前,我们还是得喝酒呀。
您重复着说过的话。说不定您的胶片都已经用完了都还不知道呢。然而,对于我来说,重复说着话的您,也是一种慰藉。听着您的话,我便有了轻微的醉意。我这样说着。
“如果,我是说如果真的有这样的功能的话,如果说真有促成忘却的成分的话,那也唯有时间吧。那药丸里面紧紧地压缩的,必定是时间。”不是呀,是酒。酒能给人恬静,能加快人的忘却。您的话越来越多了。诡异的迫切感让您变得勤快,变得匆忙,变的焦躁,最后变得让您只能从酒中清醒过来。您急急忙忙地说着:“那个,一起,不喝一杯吗?”
说的不是“喝一杯吗?”而是“不喝一杯吗?”这一问,就明白问者的心意了。那种藏在否定词中的难为情与犹豫的心情,我也明白。您虽然装作没有听到我的答复挂了电话,却再也没有打来。
就如社长所言,中秋也有客人。父亲知道我节日也要上班后,偶尔也会安慰一下。就像你们客人一样。广播里面开始播放探亲的新闻了。你们想要说的话呀,就像拥堵的道路,都蜷曲在食道下面。爬到食道上面的话呢,也可能是,也可能不是。我可没有那足以区分两者的自信。有人让我帮忙打119,有人问我代理驾驶的电话,还有人问我没有打烊的咖啡厅的电话。有的人说着外语,有的人说着外星话,有的人说着想念的话,有的人说自己肚子疼,还有几通沉默的电话。这之后打来的人说的故事又让我紧张起来了。那些跟父亲同辈的叔叔,那些处境和父亲一样的叔叔。和您打电话的时候我会担心自己的父亲什么时候会变成那个“您”,一想到这一点就让我害怕。因为和父亲通话,似乎已经是很遥远的事了。
大家都忙碌的夜晚,回家的路还很远。大家都慢腾腾地回家的晚上,连休的最后一个晚上,来了一通电话。您这位“星期五客人”在非星期五的日子打来了,这还是头一回。您说道,那个,真的不一起喝酒吗?
地铁就像扫瞄仪一样移动着。挤在一群人中间,我迈着步子缓缓朝前走去。地铁在地下飞驰着,好像赶着去找人告密一样。从市厅到江南,从江南到教大,从教大到论岘,再从论岘到弘大入口,从弘大入口到新村,地铁像找人告密一般飞奔着。我在去见您的路上。
我想在顾客较多的周五休假。社长说,公司创建以来,在周末前休假的职员,你是第六个。“我真是荣幸啊,”这话在嘴边,忍了又忍,终于没有说出来。父亲知道了肯定会反对的,可是我也需要一些乐子啊。您也是需要我的,不是我的声音,而是我这个人。
您问我说是不是在咖啡plum等。咖啡plum是您经常提起的,三百六十五天二十四小时无休的一间酒家。Plum就在那里。我所不知道的街道,唯有您告诉我才能知晓的街道,在那条街上,plum就像里程碑似的一眼可见。我走进了plum。您还没有来。我在plum里面找了一个角落的位置坐下了。先来了一瓶五百毫升的,一个小时之后又点了一瓶,三十分钟后又点了一盘小烤鱼,酒菜都齐了,您却还没来。连姓名都不知道的您,连年龄都不知道的您,连职业都不知道的您,甚至于,连电话号码都不知道的您。即便如此,又如何呢?说不定我们两个一眼就可以认定对方呢?我就如您说的那样,穿了红色的衣服。我像红色交通灯似的坐了下来。可是却没有人在我面前停下来。全部都经过我而去了。我听着其他桌上的人交谈。虽然挺奇怪的,但都是我听过的内容。为什么我都会知道别人讲话的内容呢?
“客人,不好意思。我们的营业要结束了呢。”这句话像一阵风似的飘进了我的耳朵。
“不是二十四小时营业吗?”
“只到十一点呢。”
Plum的灯灭了。高高的建筑物,似毒瘤、似牛角耸立的夜里,为了看到月亮,还得走动走动。穿过人行道,经过小胡同,张望天空,再向后退几步,才能看到这长着肿瘤、长着犄角的城市的月夜。像谁的瞳孔,闪烁地,一张,一合。伊丽莎白,您,为什么,没有出现?
我离开自己的轨道,像红色信号灯似的停在plum里面的时候,您还是和往常一样向海马005发送了醉意的信号。说了几句话,您问道,难道我不是你的常客吗?和您通话的海马答说,这大概是最近的流行语吧。月亮是伊丽莎白的眼眸?这都是些什么话呀?
“说了地球为什么是圆的吗?是在准备公务员考试?”
听了我的问题,不知是海马6还是海马7,还是114,连忙检查自己的海马。说什么地球是为了变得平滑才成为圆球,却连公务员考试都不知道,还在S电子上班。
对了,你知道吗?你休假的时候,那女人的老公又来过了。说柬埔寨女人,自杀了。海马6号还是7号,或是114,亲切地转告说。
不出所料,一上班,社长就叫我过去。说我被解雇了。问题出在我是公司创设以来周五请假的第六个人,还是因为我记不住和柬埔寨女人的通话内容,还是因为我没能阻止她自杀,还是因为我不会外语,我是无从得知了。一出公司,家里就来电话了。是父亲。父亲说找到了新工作,面试过的地方今天来电话了。我告诉爸爸的海马005的号码派上用场了。听父亲的声音,心情很不错。说不定父亲正以每个月一斤的速度变胖呢。说不定以后就改成白天上班了。大白天喝酒的人越来越多,需要找人说话的人自然就越来越多了。父亲不会请假。那样的人也不会绝种。


我停了下来,可地铁还在继续飞驰。地铁驶进竹林,向着看不到的竹林。“皇帝是驴耳朵,皇帝是驴耳朵……”告密,或是告白,或是告解。就这样,真想把这个沉醉的都市夜晚,一股脑儿都吹走。我的手指摁下了已经转换为长期记忆的电话号码。与海马005连接的同时,我的海马消失了。我醉了。我睡了。我在说话。声音陌生的你接起了电话。在哪儿?
或许,我现在正在抓住已经丢失的,现在正从我身体中渐渐消失的海马的尾巴。我常常抓住几欲脱离大脑的,被伤害的海马的尾巴:“我,也,不,知,道。”
你问我,说呀,在哪儿。
渐渐转暗。我想象着自己会成为谁。是成为准备公务员考试的男生呢,还是马不停蹄地面试,只求找一份安稳的工作,做一名正式员工?或者做一个孤独、思乡的外国人?选择在我自己。你问我,说啊,喝了很多酒吗?我一点都没喝醉,可是却被醉意击垮了。我朋友结婚了。就当是做个买卖吧,一生的买卖。谁又知道呢,会不会没过几年交易的对象又换人了。我吗?我现在往几个地方投了简历,这个月的周末时间被面试占得满满的,上周还去了一个呢。但是公司怎么看都有点可疑,即使“面试”通过了我也不会去的。下周还有两个面试。如果通过的话,就这样吧,就这样吧。就说么,面试就像相亲一样。如果通过的话,经过一段时间的实习,就能签合同了。也许我的客户已经确定好了呢。啊,啊。
某个人说出的话,传到我的耳朵里,借着酒劲,说不定会再流传到别人的耳朵里。虽然这话的有效期如春花一般短暂,可是传染性一点都不弱。这话没有重量感,可是放到哪里都很适用。
你那里也能看到月亮吗?我问道。看得见。你回答说。是圆月。你说谎了。像我一样。我知道海马们身在大楼里根本看不见月亮这一事实,那份记忆挂在海马上了。
那只是个洞罢了。瘪瘪的,小小的,圆圆的洞,只不过口子还裂得不大,但也不就是个洞吗。如果联想到实体,那就困难了。别人会透过那个洞窥视我们。月亮就是通道。知道这个事实的就只有两个人。
我知道下一句台词是什么。我的台词,还有你的台词。我可是在这剧本还没成型的时候就已经把台词给背熟了的人呢。然而此刻,我并不讨厌我们彼此之间这随着剧本而流逝的对话。在你询问是谁之间,我故作严肃地回答说:我,还有伊丽莎白女王。酒精把我包裹起来,像面具。舌头卷起我身体里的醉意,像花茎似的伸出来。我们一起踩着双人自行车的脚踏板。虽然两个人的脚一起踩着,但直到脚放下来那一刹那为止没有人分得清这骑车的动力是来自于我的脚底,还是你的脚底,又或许是两个人的合力。无从证实。我害怕发现那个事实,原来一直都只有我一个人在踩脚踏车的事实。我只好更用力地踩着踏板。
所以,你的名字是?
我一问你就回答了。海马8号。以后就找海马8号吧。
海马8号现在是你的名字了。寂静。我听不到你的声音了。手机的电池一直闪闪烁烁的,现在暗下来了。手机灯熄灭的同时,我整个人也像放完电似的。街角便利店看上去就像安全出口似的。放完了电的海马飞了起来,向便利店的方向奔去。应该充电了。无意中仰望天空,月亮已经倾斜了。伊丽莎白困了吧,瞳孔只睁开了一半呢。我一边向着便利店奔跑,一边想着要和您说的话。然而却想不出什么单词来。因为酒精让我的布罗卡区出了问题。我变得感性了。因为边缘系统出了问题。我的身体摇摇欲坠。因为小脑出了问题。然后变暗,胶片断了。因为海马,海马疼了。可是,关于我中断的胶片,您既不追究,也不责怪,更不回避。您只是与我共同分担。


尹贾溵(1980— ),生于首尔。毕业于东国大学文艺创作系。2004年获大山大学文学奖,登上文坛。长篇小说《无重力症候》获同民族文学奖,此篇《飞吧,海马》获李孝石文学奖,另外还著有小说集《一个人的餐桌》。尹贾溵大学时期积极参加学生社团活动,毕业后一直没有找到正式工作,打了多种零工,做过报社记者、课外家庭教师、儿童书籍编辑,等等。她靠打零工赚来的钱养活自己、四处旅行。疏离感是尹贾溵小说最常表现的主题。

原载于《世界文学》2012年第6期,责任编辑:秦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