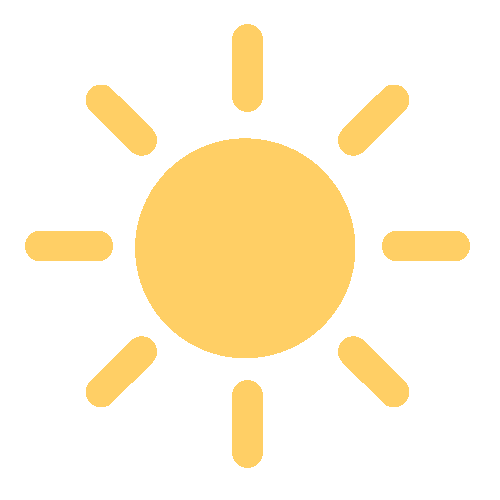小说欣赏|马•莫泽巴赫【德国】:丛林,丛林
![]()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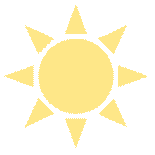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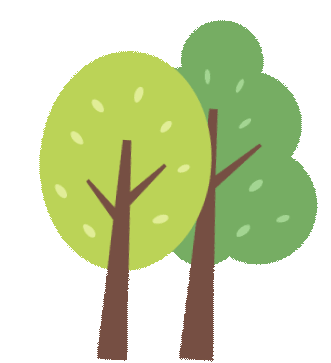
马丁·莫泽巴赫作
贺骥译
“在棕榈树下漫步必然会受罚,在象与虎的
国度人们的思想观念肯定会改变”
——摘自奥蒂林的日记
我坐在小壁炉旁,壁炉里的柴火噼啪作响。我昏昏沉沉地开始做梦,梦把我带回到了马库亚【马库亚(Macuya):印度地名】的孤寂暗夜,那个我心碎的地方。就在雨季的倾盆大雨落到我的棕榈叶屋顶上之前,我们去马库亚森林猎捕老虎。一颗心在我过去生活过的世界里碎裂了,但是我碎裂的心并不是一位爱者的心,而是恐惧者的心,当神秘而恐怖的快乐与死亡向我迎面走来时,我惊慌失措——我的心在面对惊人的毁灭时骤然崩裂。
当我动身前往那个地方时,我的心脏非常健康,它发育良好,功能正常,它在我宽阔的胸膛里有力地跳动。除了健康的心脏外,我还有一只海员用的大木箱,木箱里装满了奇异的家用器具。我总是把这些家用器具摆放在我的卧室里,并在卧室里支起蚊帐以防止狡诈的毒蚊蝇的叮咬。
我的风格总是有声有色。在雾岛上阴暗的海外事务所里,我打开了发射机,按照我如实撰写的新闻稿开始播发新闻。我的新闻报导客观而冷静,可事务所里却散发着一股独特的、令人迷醉的清香,那是笃蓐香和没药发出的香气。幸福的东方!在香气的麻醉作用下,痛苦会变得甜蜜或浑然不觉。如果我们很早就沉浸在醉人的香气里,那么我们的痛感就会消失,自然也就不需要有益于健康的蒸汽疗法了。我很晚才了解它的力量,但它已无法阻止寒疝的恶化,更不能彻底治愈它。
在一个东方的清晨,湿热的晨雾和上千只蜂鸟融为一体,蜂鸟的尖声颤鸣和急速飞行令人眩晕,使一个昏昏沉沉的起床者无法断定他是否已醒来或者仍处于低纬地带的昏睡之中。清晨的天空呈现出土著人的眼珠般的黄色,我的实用的折叠桌上的手提式打字机在昏黄的天光中呈现出清晰的剪影,这台打字机曾伴随我周游过许多国家。此时我坐在床上,看不清打字纸上的文字。昨夜我借着折叠式煤油灯的灯光,把打字纸斜插在打字机上,给霍博肯兄弟公司写了一封信。沉闷的暗夜令人困倦,我已筋疲力尽,再也不能把打字纸从打字机上拔出来并在最后一页打字纸上用富于表现力的手写体签上我的姓名了。我用颤抖的双手脱去外衣,躺倒在床上,床单立即贴上了我的身体。尽管此时我无法读那封信,但信里的最后几句话还是像疯狂的圆舞一样在我的睡意矇眬的头脑里旋转。我的信笺的结尾部分如下:
霍博肯兄弟股份有限公司的先生们,你们也许觉得我的信中附言无关紧要。你们已习惯于只从商业的角度来看我寄给你们的文件,你们认为这些文件有助于开采此地的自然资源并从中牟利,而我是在厄运和不良爱好的驱使下来到此地的。但是在商业思维中也存在着一些与商人的日常工作几乎无关的边缘领域,进入这些领域会使人突发奇想,而这些奇想也能确保我们取得最大的经济成就或阻止灾难的发生。不言而喻,一些美好的学科就属于这些边缘领域,例如动物学、地理学和人类学。我知道你们在十二点左右会坐在餐桌旁边吃肉边喝麦芽啤酒,等着来自被雨幕遮住的麦胚交易所的消息,并在饭后研究这些消息。而我是最勤奋的驻外勘测员之一,我的岗位离总公司最远。如果你们在午饭前花一点时间听听我的发言,你们就会发现我的情况和你们的想象截然不同。我的处境(我省略了动词,因为你们和我一样把时间安排得很紧):今天你们会发现我竟然是这样一种人……
请你们设身处地地替我想想。


没有女人,没有电话,没有机会欣赏现代电影艺术。贝弗利·库尔茨或拉欧尔·陶壬德之类的名字对我毫无意义,我的不可名状的梦想无法因其体形或容貌而成形(梦的实现在此地已成为一个特殊问题!),他们的虚名根本不能给我以生活上的帮助!
哈哈!
但我在马库亚却经历过一些令人难忘的另类奇事,这些奇事属于最古老的、不为我们西方人所知的(或再度遗忘的)神话领域,确言之,它们属于前神话的自然过程!是的,我甚至有幸旁观了一个神话的诞生——这个神话对所有的见证人而言都相当危险——而在场的白人都戴了皮护颈!
我们还是别谈神话学了。生活中的那个素材激发我的叙述欲,它在总体上属于我必须向你们讲述的奇事的核心。
那件奇事最重要的内容如下:
凌晨四点我们就出发了。山区雾蒙蒙的,山巅逃离了我们的视野。我们这个猎捕队由不同年龄的二十五人组成(包括搬运工!)。猎捕队中只有一位妇女,即潘尼库克女士,据说她后来非常懊悔没有抑制住自己的好奇心。我们此行的目的是猎捕老虎,猎捕老虎有其自身的规则,有其不可怀疑的神秘规则,尤其是在这个善待动物的国家,一方面官方采取了措施严禁本国军人使用火器猎杀老虎(它颁布了一条非常严厉的法令),另一方面本国的军人出于迷信打心眼里就蔑视火器并拒绝使用火器,与火器相比,他们更信赖镶有毒刺的棍棒。
潘尼库克女士撑着黄褐色的遮阳伞蹒跚而行,遮阳伞为她挡住了苍白而灼人的阳光。热带朝阳极具杀伤力,被晒死的绯红金刚鹦鹉纷纷从树枝上掉落。当我们到达丛林时,我们终于松了口气,因为丛林能使我们躲避光的利刃。当我们停留在颇有裨益的丛林里并对它产生好感时,我们就对这个国家有了一个正确的概念,因为它的丛林……
请诸君听我娓娓道来!
我们排成长长的一列向前行走。我们的脚步引起了一阵刺耳的尖声,但我们不知道这尖声是由深及脚踝的烂泥还是由被我们于无意间踩死的蠕虫发出的。我们四周的藤本植物在快速地疯长,它们伸出有力的嫩枝来抓我们和我们的装备,想缠住我们并把我们拖进灌木丛。我们不停地向四周挥舞着锐利无比的军刀,勇猛而灵巧地左砍右劈,以抵御嫩枝的纠缠。在我的想象中有两片浅绿色的树叶抓住了我的酒精炉并使它越升越高,就在我的夏尔巴人【夏尔巴人(Sherpa),尼泊尔的菩提亚人(藏族后裔)的别称,主要聚居在尼泊尔的昆布和帕拉索卢,部分散居于印度。住在喜马拉雅山南坡的夏尔巴人以从事登山向导和搬运工闻名】感到疲乏时,这两片树叶完全有可能从他手里偷走酒精炉。
我不知道艰难地登山耗费了我们多少时间。我只知道潘尼库克女士红铜色的头发粘在了她白皙的太阳穴上,长途跋涉已使她累得要死。就在这时我们的向导发出了一种声音,这是我们在出发时约定的暗号,在这片丛林里只有知情人才懂得这个暗号,而浑浑噩噩的动物世界会觉得这个暗号很普通且无恶意。
听到暗号,我激动得浑身颤栗。潘尼库克女士好不容易才抑制住了叫喊。我们明白我们已抵达了老虎的栖息地。这类猛兽的栖息地地势平坦:它位于高处,在山峰附近的林中空地上,林中空地的土质贫瘠或多石,原始森林的野生植物无法在上面顺利生长。在肥沃的原始森林里什么地段属于不毛之地?你们肯定猜出来了。那些倒塌的、被废弃的寺庙就是不毛之地,信徒们曾在这些寺庙里礼拜那些西方学术界所不了解的众神。正是众神自己造成了寺庙的颓败,因为他们在某天命令他们的祭司(普通民众对祭司的生活一无所知)终止那些可怕的敬神祭祀并关闭寺院,把钥匙扔进原始森林里的沼泽地,离开寺院永不回头,穿过森林,迁居到最近的居民点。众神也离开了寺庙,只剩下一些低等级的恶魔。群魔在残留的角落里避雨,时不时地敲打破庙并窃窃私语。
如果这类废墟终于成了老虎的栖息地,那么这就表明最后一个恶魔也离开了这种曾经供奉神明的圣地,因为老虎总是避开恶魔,它只在毫无魔力的地带逗留。有时也会发生两凶相逢的怪事:一个迷路的恶魔回到了它原先的家,它因发现猛虎霸占了它的家园而怒气冲天,而恶魔的家过去是寺院,祭司们端着松鼠头骨做成的小碗,把清香的麦粒撒到地上喂鸟。两凶相逢时,位于山谷之中的村庄里的居民们就会听见令人毛骨悚然的频繁的怒吼声,他们睁着恐惧的大眼睛相互点头示意:他们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但是古老的传说会使他们产生不祥的预感。
各位先生,我们看见的是空荡荡的虎巢。废墟的石头缝里长着小草,石头上留有人工雕琢的痕迹:奇异的浮雕、绽开笑容的鬼脸和多义的符号……你们可以展开想象的翅膀。
犹豫了片刻之后我们离开了幽暗潮湿的森林,然后分散开来,坐在隆起的地面上。潘尼库克女士松了一口气,她坐在一个倾倒的阳具石像上,掏出手绢去擦脸上的热汗。我们一言不发。我们的向导仰着头站在一棵无花果树旁,他鼓起鼻翼去嗅空气中的气味。我发觉他有些疑惑不定,然后变得越来越焦虑。他闭上双眼,聚精会神地嗅着。当他再次低下头并睁开双眼的时候,他一声不吭,但我发现他目光呆滞。
我沿着他的视线望去:那里静静地站着一只威武的成年老虎,它正瞅着我们。在它身旁的几米开外站着第二只同样大小的老虎,而在相同的间隔处则站着第三只老虎。我惊恐地环顾四周,发现大约有一百只孟加拉虎组成了一个精确的圆圈把我们包围在中间,群虎纹丝不动,眼睛紧盯着我们。


先生们!
浮想在我的脑海里如潮涌。但我想的不是获救。涌现在我眼前的是另一些画面。勃兰登堡州的小镇吕措夫的剪影在阳光中闪现,我的父母在吕措夫有一个洗衣店。幸福的少年时代浮现在我眼前:我看见了路德教堂、毕士大【毕士大(Bethesda),耶路撒冷城东北角的羊门附近的一个水池子,传说池水有治病的疗效。许多医院用"毕士大"来命名,以弘扬基督教的博爱,德国共有八十多所毕士大医院】医院、纺纱厂的红烟囱、漂白场和煤气厂。我等待着死亡的来临,恐惧使我产生了心理变态,于是我用对往日的回忆来麻醉自己,我的不幸的少年时代在回忆中显得美好而甜蜜。
其他的人究竟在想什么?他们的末日也即将来临。他们都吓得呆若木鸡,我还记得潘尼库克女士的神态,她原本想用手绢去擦嘴唇上的汗珠,但此时她拿手绢的手却停在空中一动不动。
先生们,也许你们手中的信笺会惊得飘落在地,你们肯定会产生疑问,世上怎么会有这等奇事。我不能指责你们对我的实录的怀疑,尽管实录的署名者是一位久经考验的可靠的老实人,你们的怀疑会刺痛他的心。然而是健全的直觉使你们产生怀疑的,直觉是不会欺骗你们的,因为此时在我眼前发生的是一件闻所未闻的奇事,史学家们从未记录过这类奇事。我该如何记录这件令人毛骨悚然的奇事?我记录的难道不是我所耳闻目睹的真事吗?如果我说了假话,那么你们完全有理由蔑视我。但我请你们镇定下来。我会让你们了解全部的细节。
原始森林蓬乱而纠结的树梢开始发出一阵簌簌的响声,群虎于是抬起头来侧耳谛听。我们这些人则纹丝不动,但我惊讶地发现潘尼库克女士从她坐着的石像上慢慢地站了起来,仿佛有一股神秘的力量把她拉了起来一样。群虎此时有何举动?群虎开始转动起来,它们背过身去,然后又把身体转了过来。众虎越转越快,而在此期间潘尼库克女士已处于昂首挺胸的直立状态,身体的过度伸展使她看起来似乎比原先更高了,她突然发出了一声尖利的大叫,叫声使众虎立刻停止了旋转,它们张开血盆大口,以雷霆万钧般的、震耳欲聋的吼叫来回应这位女士的大叫——先生们,我该如何表达才好呢?你们还记得,我提到了一阵簌簌声,一阵狂热而迷人的簌簌声——这种簌簌声既轻于虎啸,又比虎啸更强烈——诸位感到惊讶?——我的语言是如此贫乏!


簌簌声变得更轻了,我听得入了迷,我的感觉也有些麻木了。但是当我看见发出震耳欲聋的吼声的众虎开始向前冲时,我变得六神无主。我们都吓得呆若木鸡,根本没有能力举起手来保护自己或作无谓的反抗,但是啸鸣的众虎从我们中间跳了过去,只是把它们的臭气散发到我们身边而已。就在场地的正中,即潘尼库克女士站立的位置,长着黑黄斑纹的众虎麇集在一起,混合成一个狂野的造型,而潘尼库克女士仍在张嘴叫喊,但她发出的已不是恐惧的叫声,而是和谐的叫声,似乎她已与虎群达成了神秘的默契。在震破鼓膜的吼声中,我亲眼看见群虎叠成了一个金字塔,一个白种人从未见过的虎上架虎的金字塔,我还看见潘尼库克女士摇摇晃晃地站在群虎金字塔的塔尖,她得意洋洋,继续欢叫,但我无法保证这个场景的绝对真实性,因为就在那一刻我的双眼已经充血,濒死的恐惧已使我失魂落魄。但是时至今日这个画面仍然清晰地在我眼前浮现!
先生们,我晕了过去,又醒了过来,却再次瘫倒在地。因为我看见我的周围有无数只老虎,它们放肆地在草地上打滚,我还看见潘尼库克女士面带科律班忒斯【科律班忒斯(Korybanten),弗里吉亚丰饶女神基伯勒的祭司,他们在女神的祭仪上欢歌狂舞】的表情骑在最强壮的老虎身上,我听见她在放声歌唱!她唱的是一首艳歌,歌词暗示她母亲来自波罗的海东岸三国。歌词的前两行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里:
从前有一位里加少妇
她面带微笑骑大虎……
然后我两眼发黑,眩晕,跌倒在地。
我失去了知觉,根本不知道后来来了一架救援直升机。我躺在原始森林医院的一间经过严格消毒的隔离病房里,慢慢地重新适应了以一周为单位的作息制度,我在读书识字方面进步很快,还和我们的领事通了一次电话。领事告诉我,尽管很多天以来大家都很担心猎捕队员们的精神状态,但猎捕队中无一人死亡。很远都能听得见的虎啸促使救援队作出了决定,他们带上重武器,开着直升机朝山寺方向飞来;当直升机停在山峰附近的高地上时,救援队终于找到了似乎被雷电击倒在地的所有捕虎者,但是连一只老虎也没有看见。


关于奇事的报导到此为止。我的语言的贫乏是不言而喻的。先生们,你们可以从经济的角度为你们的公司权衡利弊,你们或许能从我的报导中得出某些结论。我只想补充一句话,如果我能在此转达潘尼库克女士对你们的问候,我就会倍感欣悦。潘尼库克女士总是客观地、甚至善意地看待她和贵公司的业务联系,她若向你们问好,你们是不会感到意外的。
但我不能转达她对你们的问候,因为她已不在此地。就在我出院后的第二天,我第一次勇敢但也义不容辞地外出散步,我一直走到港口,看见她在一艘美国救护船的甲板上,这艘船正在离港,它要开往香港。她坐在轮椅上,红铜色的头发已变得雪白。
先生们,我随信给你们寄去了我在一月、二月、三月、四月和十二月的开支账单。我企盼你们回信。谨向诸君致以最诚挚的问候。

Mosebach)是当代德国著名的小说家、散文家、剧作家和诗人。1951年7月31日,莫泽巴赫出生于美茵河畔的法兰克福,父亲是心理医生。1970年中学毕业后在法兰克福大学和波恩大学攻读法学,1980年起成为自由作家。1982年发表歌词集《歌德的一生》,1983年推出首部长篇小说《床》。由于受到前辈作家戈洛·曼和霍斯特·克吕格尔的推荐,莫泽巴赫在文坛声名日盛,并通过勤奋笔耕成为一位多产作家,其创作几乎涵盖了所有的文类: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散文、诗歌、戏剧剧本、电影剧本、歌剧脚本和广播剧,并获得汉堡文学学会奖(1984)、多德勒尔文学奖(1999)、克莱斯特奖(2002)、毕希纳奖(2007)等多项文学奖。毕希纳奖评委会为他写下了充分的获奖理由:“该奖颁给杰出的作家莫泽巴赫,他把风格主义的华美与自然的叙述欲结合在一起,并表现出一种幽默的、远远超出欧洲文化界限的历史意识;在文学的所有领域他不仅是一位天才的形式游戏者,而且是一位独立自主的时代批判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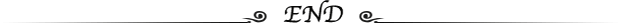
点击上图,订阅全年《世界文学》
点击上图,订阅单期《世界文学》

添加《世界文学》小助手
获邀进入《世界文学》分享会3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