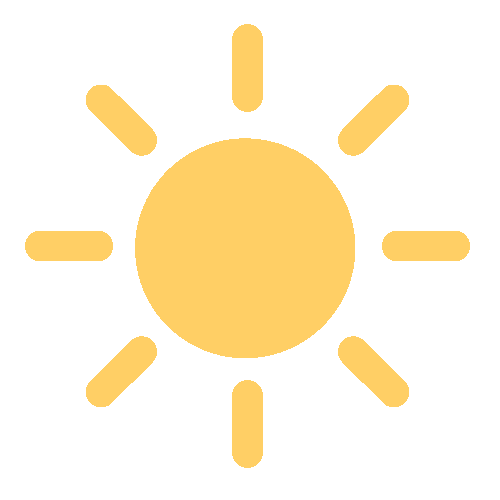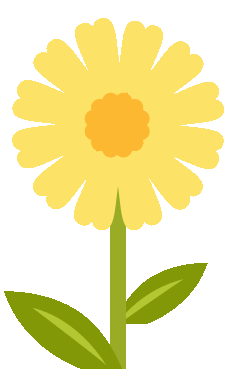小说欣赏 | 尼•戈尔兰诺娃 【俄罗斯】:一个活得很累的当代人与其心灵的交谈
![]()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尼娜·戈尔兰诺娃作 陈方译
我想割断血管。天花板已经漏了三天的水,就像塔尔科夫斯基【安·塔尔科夫斯基(1932-1986),俄罗斯著名导演,代表作品有《伊万的童年》(1962),《安德烈·鲁勃廖夫》(1969)等,他的电影以擅长运用象征意象而闻名】的电影里演的那样。而且水是滴到一口锅里去的,那口锅放在床上,在我的两腿之间。在我们家的黑暗之中没法随机应变,所以我就在夜晚聆听流水的音乐。我再也不想这样了。
心灵:“我最尊敬的同事!你是相信上帝的,而那种想法是一种罪孽。你有四个孩子啊!”
“是的,但是我瘦了三十公斤,现在我的体重是五十公斤。我无法工作,孩子们还小……丈夫养活不了我们。”
心灵:“那就更应该把孩子带大了!”
“我的女友们会立刻把他们带走的。在充满危机的日子里,她们所有人的状况似乎都不错,有的人有积蓄,有的人有别墅,还有的人变成了商人。”
心灵:“你读过古人写的这方面的论文吗?那里写得很清楚,说如果你在这里,在人间就没有建设愉快生活的话,那么在天上也是一样的。”
“可是我受不了了!我的短篇小说没人出版,等到出版的时候它们就过时了,现在谁还对克格勃或者州委会的工作人员感兴趣呢?”
心灵:“现在确实没人感兴趣了,但是再过十年还会有人读的,而且会饶有兴味地读,就像现在读马柳特·斯库拉托夫的书或者写沙皇的书那样。”
门铃响了,这是电视台的来了——可以拍摄和您的访谈吗?好,我说,我们非常需要钱(我当然没说是为了举办葬礼)。但是,只是不能在这里拍,我到你们电视台里去。但是,他们反驳道,你们这里有小孩,有他们画的画,有小猫,天花板还在滴水——这太适合拍电视了!但问题是,在这个城市里住着一个我年轻时代曾经爱过的人,万一他在电视里看见这一切并幸灾乐祸怎么办?“我把一个孩子和我丈夫带到电视台去,猫我不敢保证……”我们去了电视台。那里不可思议地豪华,所有设备都是索尼的。有数不清的放映灯。我们坐着……流汗……差不多有四十分钟,女主持人一直低声准备着一段非常奇怪的话:经纪人,彼尔姆商业银行,红利……他们难道想把我们做成广告的一部分吗?我丈夫如坐针毡——他上课的时间到了。我们继续流汗。“生意人和商人,这两个词是一回事吗?”女主持人问。我们在等待。最终我们搞清楚了,原来他们没来得及做完一个节目,现在把它录在我们的磁带上,之后再剪下来。
“和你们进行的就是谈话!”她对我们说。
非常棒!谈话是我们喜欢并擅长的惟一事情,而此刻在这里还能挣到钱。我们永远欢迎谈话!第一个问题是问丈夫的:您是否认为,名字会对一个人产生影响?是的,丈夫开始说了,他的名字是为了纪念莫洛托夫而起的,现在这个名字起到了不好的影响……丈夫本想详细地讲一讲怎么回事,但是女主持人抢下了他的麦克风,举着它冲到了阿格尼娅的面前:你最喜欢的节日是哪个?复活节,阿格尼娅说,她还想详细地讲讲自己对上帝的态度,但是女主持人打断了她的话头,拿着麦克风跑到儿子跟前: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丈夫带着一种受陷害的表情看了我一眼。“钱!为了钱,忍耐一会吧!”我小声说……现在不得不再忍耐一天,电视台的人到我们家里拍摄猫,之后在外面拍我们。而前一天半夜,房间里传来了一声巨响——斯大林掉下来了。一副巨大的斯大林像,只是眼珠变成了希特勒的头。那是索尼娅在“改革”末尾的时候画的,头发画成了一些蛇,四周鲜血飞溅,但是所有这些都罩在一个绿色的地球里,大自然的生命即将胜利,它用它自己的一大片绿色吞噬掉了凶恶的东西……墙壁被水泡胀了起来,所以画像掉下来了(也就是说钉子因为潮湿而脱落了)。该把它放在哪里呢?我现在把它送给电视台的人,也许他们会多付一些钱。他们会考虑到这一点的。他们会因为礼物而激动的。他们会很快把酬劳拿来——一百五十卢布啊!算了,应该割断血管。反正拖延是毫无意义的。一百五十卢布啊!可以用这些钱买一公斤黄油……不,连一公斤黄油都不够……
心灵:“这样什么都改变不了!如果你在这里没有为自己设定更高层次的愿望的话,你在那里也会因为同样的问题而天旋地转的。”
“可是我再也受不了了!难道去乞讨吗?作家协会连补助都不发,他们自己的钱还不够出国旅游呢!”
心灵:“这是暂时的困难。你还会看见,俄罗斯会繁荣昌盛,就像世界上的所有国家一样。”
“我相信,但是孩子们今天吃什么呢?明天呢?没什么可卖的了……”
门铃响了。阿格尼娅被人从学校送回来了,脑震荡。她现在七岁,一个大块头的七年级学生在她跑步的时候把她撞倒了。开了二百卢布的药。必须给女儿治病……上帝啊,以前就连告密者都能到家里来送吃的,有的人送鸡,有的人送糖果,而我还气愤地说过,只要一认出告密者,我就把他赶走。现在我可能会非常高兴,可是已经没人来了……但是阿格尼娅最终出院并回到了学校。可以割血管了。


门铃响了。索尼娅的小儿子跑来了:“尼娜·维克多洛夫娜,我在阁楼上看了看:房梁全烂了!得把索尼娅的沙发从这里挪开……”这就是说,天花板随时都有可能坍塌……又有什么办法呢,我们要重新挪动一下。为了挪走沙发,必须把书柜放在它的位置上……如果这些书不是读得这样破就好了!可以把它们租出去,但是这些书没人要,它们已经破得掉渣了,已经不是书了,除此之外它们身上还镶上了大理石(不是我们镶的,是蟑螂镶的)。我重新摆放家具。这花去了我两天时间。终于,所有事都过去了。可以拿起刀来,那还是索尼娅的儿子磨的(我因为不习惯,用它在手上划了一道很深的口子,因此产生了割断血管的想法——根本不疼!那是一把锋利得让人感到惊讶的刀子!)。
心灵说:“在你的葬礼上发言的将是那些没出版你的书或者没给你分房子的人。他们将感叹道:‘尼娜真是一个十足的理想主义者,她生了四个孩子,从女酒鬼邻居那儿领养了一个女儿,她写了一部又一部长篇小说,相信公平必将占据上风,可是生活终归是生活,它要求人们去现实地看待它……’”
“谁想说什么就说吧,我全都无所谓了!”
门铃响了。丈夫从“首都”出版社带回来一封信,编辑部请求我把孩子们的叙述补充到材料中,因为这很有意思。噢,写多少都可以!应该补充一句,他们会付更多的钱的,家里人正好可以在追悼会或者第四十天的追荐日上得到这笔钱。我坐到打字机旁边,可是孩子们的叙述无论怎样都塞不进去,可以无休止地写下去!剩下的手稿散落在桌子上。把它们放到哪儿去呢?“妈妈,给我一个三升的桶,我要攒钱给你买一条连衣裙!我的桶太小了,现在的裙子多贵啊!”“而我知道为什么现在不找零钱了,因为俄罗斯是叛乱中的胜利者,所有人都变得善良了,所有的零钱都给了穷人!”“妈妈,我们以前玩过跳房子,我们说:‘跳到横格,杀死沙皇,’而现在说的是:‘跳到横格,杀死叶利钦!’”我所有的手稿袋子该放到哪里去呢?唉……现在一切都已经无所谓了……
心灵:“顺便说说平定叛乱的事,你要是总能想起这个就好了!无论你现在在哪里,这场胜利都会发生的!”
“那现在我在哪里?在脖子上的绳索跟前……”
门铃声。丈夫兴高采烈地说:我找到洗澡的地方了!他给熟人打电话,他们有的不在家,有的人家里没有水。他又给一些人打了电话,他们都在家,还有水。我们出发了。我在浴缸里想:如果我有一个浴缸,可能我就不会走到不想活下去的地步了,因为就连理想都不知为什么闪出了亮光,但是我一下想起明天只剩下五十卢布了,该怎么养活六张嘴呢?不,我不能……在回家的路上我们遇到了一个爱国者。“你为俄罗斯做了些什么?”他严厉地问丈夫。“洗了澡,”丈夫立刻回答道,“在肮脏的俄罗斯至少多了一个干净的人。”他的幽默感没有枯竭,他还会活下去的,我想,可是我已经枯竭了。是时候了,是时候了……



我们走到家门口——达莎在哭。一只狗把她咬了,是邻居的贵妇狗,黑色的,它总是让我想起歌德的《浮士德》。这不是毫无根据的。
“妈妈,不是它的错!他们把它赶出来了,他们不喂它,可是它什么都不明白,发脾气了!妈妈,也不是他们的错,物价这么高,他们怎么养活小狗啊……”
是啊,所有人都没错,可是达莎因为肾脏的缘故不能注射破伤风针。怎么办?胳膊差点儿被咬穿了。苏打洗剂,就用这个吧。我用苏打泡了洗澡水,晚上的时候把她的胳膊抹上药膏包扎了起来。早上我又准备了一些苏打水。但是胳膊肿起来了。再涂一次药膏。如此这般持续了十天。终于消肿了。这个时候,电视里说社会保障处给葬礼的拨款是两千卢布。我对丈夫说:“你知道我们这里的社会保障处在哪里吗,在工会大楼旁边,它的左边,不对,右边……”
门铃声。女友来这儿流了一通眼泪,她丈夫有外遇了。
“听着,阿赫马托娃遭到过抛弃,茨维塔耶娃也被抛弃过,我们怎么了,比她们更优秀吗?”
丈夫马上说:“尼娜,你可以去倾诉热线工作,你却想着自杀。醒醒吧!你在报纸上登个广告吧:‘女作家戈尔兰诺娃愿意安慰任何一位携带一定价值的食品来找她的人……’”
顺便说说,因为我,他们把刀子藏起来了。但是我还有足够数量的安眠药……
心灵:“这个,顺便说说,什么都保证不了,因为你喝下去以后,人们会把你送到抢救室,会把你救活,但是不会救到底,就像我们这里通常所做的那样。你将半死不活地躺在那里。”
“还会变成孩子们的负担……”
“上帝不会原谅这些的!不!”
门铃声。儿子在学校的一些朋友来了。他原来已经辍学,找到了一份工作。那该怎么办呢,既然母亲已经走到了尽头,而吃饭的欲望还是有的。
心灵:“你想要的是这些吗,母亲?”
“不,我想要的不是这些……但是没有办法,这说明,是上帝想要这些。我不会偷盗,又不能工作。我没有什么可选择的……”
门铃声。安东的班主任来了,她找到了一笔赞助,为了让他毕业,那些人给了四千卢布!谢谢,万达·维亚切斯拉夫娜,我想,就是说现在,我应该先给他们买一些食物。社会保障处会给我们一些钱举办葬礼的,而他们会把四千卢布全都花在香肠上。我要给他们买些米、面条、白糖、奶酪……呜呼,四千卢布,听起来当然是一笔巨款,可是只能买一点儿东西。但是,他们总归还能过上几周饱日子……算了,我的安眠药在哪里?
我服下了一小把药片,我的四肢开始变得僵硬。原谅我这个有罪的人吧,上帝!突然儿子大声喊了起来:
“妈妈,妈妈!来热水了!”
已经三个月都没有热水了。我们这里即使凉水也来得很少,更不用说热水了!……我拖着僵硬的四肢跑到厨房,满心欢喜地洗起碗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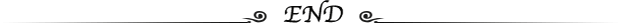
点击上图,订阅全年《世界文学》
点击上图,订阅单期《世界文学》

添加《世界文学》小助手
获邀进入《世界文学》分享会3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