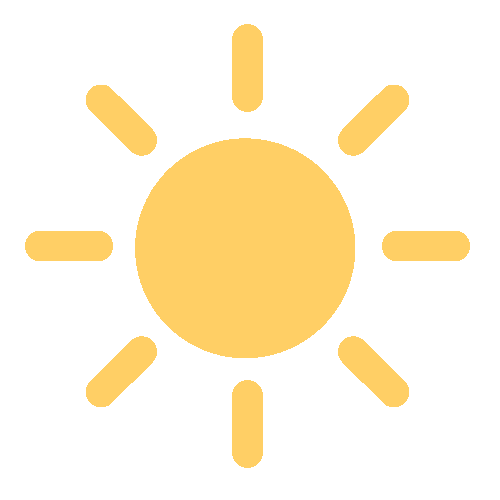小说欣赏 | 特•莫拉【德国】:在城里,沥青一直延伸到树的皮肤……
![]()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特蕾西亚·莫拉作 李永平译
不要告诉任何人,事情是如何发生的。也不要说这里的任何事情。
我哥哥很担心。我们想给园子里施肥。可太晚了,新的一年已经开始,沉重的肥料到春季都不会腐烂。尽管如此,昨晚我们仍决定施肥。今天一大早,天色还漆黑时,我们就开始干活了。我哥哥把肥料铲到手推车上,然后由我推到园子里,我翻掘垄沟,而我的哥哥则把肥料铲到垄沟里,我再在上面盖上土。我不搭理他,我们都闷头不语地干活。我的头发有些地方仍差不多有五公分长,它们在风中晃动,仿佛春天已经来临,白杨树的绒毛粘在我的头皮上。
星期天我剪了头发。那一天,我们把母亲抬进救护车,院子里挤满了女邻居,当我和吉卜赛人弗洛里安返回来时,父亲悄悄点燃了我的头发。男人们抓住他并把他按倒在鸡棚污泥里,而他就在他们的胳膊里大喊大叫。对于疼痛,我自己没有一点感觉。埃拉姑妈离我很近,她用头巾扑灭了我头发上的火苗。只烧焦了一半,从烧着处,头发像玉米穗一样掉落到地上。奇怪的是,有几缕头发没有完全烧光,还继续留在上面。
埃拉姑妈给我们留下了二十个鸡蛋。这些蛋管不了什么用,她说。冬天太暖和了,这不好,埃拉姑妈说。对动物不好,对植物不好,对人也不好。人是最虚弱的,他们中的一些人变得疯狂,一些人正在死去——就像我们的父亲和我们的母亲。而我却活着,身体健康,与我的哥哥一起为田里施肥。我昂首在温暖的风中,风把肥料的气味吹向邻居那边,一如往常把他们燃烧的木柴和阿蒂拉·霍尔娜克在阳台上饲养的鸡貂的刺鼻气味吹向我们这边。我们也应该养鸡貂,我哥哥说,可以赚很多钱。
施完肥后,我替哥哥洗头发,接着我也在带花押字的盥洗盆里洗自己的头发。我哥哥头上顶着一块毛巾,坐在一旁看着我。我们洗头时总是穿着内衣。然后我哥哥把祖父赠送的帽子戴到潮湿的头上,穿上他破旧的冬大衣。我们去长途公路旁的公共汽车站,大衣的两翼在风中摆动,像在电影中一样。我哥哥是乳白色的皮肤,身材柔和。有人说他弱智,但这不对。
我们绕开拖拉机路,穿过田野。元素。在我们行走时,我突然想起了它们。元素。
这是我哥哥上小学时背过的门捷列夫元素周期表上的元素。元素周期表挂在我的床上方,因为我要学习它。但我哥哥并没有学过完整的名称,如氢元素、氦元素等,而仅仅是表上所写的符号:H,He,Li,Be,B,C……有时他独自把它们唱出来,虽没有旋律,但节奏分明。Ha—He—Li—Be—Be—Ce—NeO【在本篇中出现的“元素周期表”中,有些字符并非元素符号,而只是一些字母组合】—Fe—Ne。他告诉从头巾下露出怀疑目光打量着他的姑妈们,这是科学的语言,宇航员就是这样谈论我们的,他一边说一边指向天空。戴着头巾的姑妈们看着我,于是我以一种严肃的语调对我哥哥说:Na—MgAl—SiP!姑妈们走后,我哥哥大笑起来,说:Au—Hage—Tele—Pe,Bi—Po?我对他说,不要再说了。人家会把他看作弱智的。
后来我在学校里得了一个五分【德国学校的评分制度,1分为最高分,6分为最低分】,因为当我被提问时,我只会唱出元素周期表:Ha—He—Li—Be。整个班级狂笑不止,像疯了一般。你们大家都该去看一下医生,到了那里才会清醒,老师说。
可以让人编一顶假发,玛格达拉姑妈说。我们大家望着院子里那一堆黄色的头发。我忽然想起,可以用它来填塞漏水的自来水管。我耸了耸肩膀。我们把头发埋在了花园里。
没有人会相信你。算了吧,我哥哥说。我们跋涉的田野一片泥泞。从我母亲那里我学会总是多带一双鞋子。如果我进城的话,就可以穿干净的鞋子在城里走。现在我也在旅行背包里为我哥哥和我自己带上灰色和蓝色的低帮鞋。我哥哥说,我最好是说,我来自城堡。
小时候,我经常在古老的庄园城堡里,尽管我害怕蝙蝠会缠住头发,我还是爬到阁楼上,在雕像的背后来回跑动。
埃拉姑妈认为,我们的金黄色头发是伯爵的遗传,我只需看一看玛利亚伯爵夫人的油画像。有许多金发女仆,与她们的女主人像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她们也有类似克莱斯岑茨、莱奥尼或阿玛利丽丝的名字。在俄国人到来,把他们的拖拉机放在城堡大厅的白色大理石上之前,她们就从城堡里拿走了他们应得的遗产。甚至连我们也有一个带花押字的盥洗盆:F.N.E。还有别的什么人得到了水罐,我们就不知道是谁了。
现在为了旅游者,他们要再次打开城堡,而且还从各处搜罗家具、地毯和瓷器。埃拉姑妈说,也有人来我们这里寻找失踪的东西。在她的卧室里有一个总是盖着块黑头巾的威尼斯镜子。如果他们来的话,我哥哥说,我就把盆埋藏在院子里。
即使今天我也还常常梦见城堡。我穿过阴暗的、空无一人的房间和五光十色的实验室,一直到我突然走不下去为止。楼梯消失了,门只开一条缝,虽然我可以透过门缝看过去,却无法穿行而过。有一次,在梦中,我周围的整个城堡在慢慢缩小,如果我不是刮得伤痕累累地从一扇小窗子逃出来的话,城堡早已把我压扁了。你真笨,我哥哥说,人家都是事先就醒过来啦。我哥哥说得常常不错。但这次却不是。在我所认识的人中,还没有一个人做过我这样的梦。
有一次一位老师对我说,我应该学会咬着舌头发咝音,并马上教我如何发S音:把舌头放在牙齿后面。但他接着又说,这个A在人的一生中永远都不会消失。我对我的哥哥说,说我从什么地方来,毫无意义。他们总会听得出来,我是从哪里来的。
我们老远就看到长途公路干线,看到那些在我们之前一个小时已经开走的公共汽车,但有时看不见自己该坐的那一班。我们从来不知道,该何时动身。有时候不知什么原因公共汽车就是不来。没有人给我们带来消息,而我们也不知道在哪里可以打听失踪的公共汽车的消息。也可能,我哥哥说,它们在长长道路上的某个地方消失了,没有人注意到这事,因为没有人去打听它们。有时候公共汽车也从我们身旁开过去,尽管我们站在路边。也可能,我哥哥说,我们有时是隐形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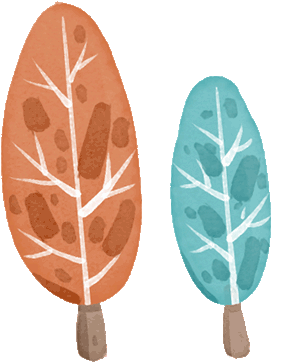


当我们终于坐上公共汽车后,他在每一次开门时都会大声数着,现在有多少隐形人一起上车。他问道:那些人会在那里站多久?
在城里,人们总是将沥青一直铺到树下。树根突兀在人行道上,人们走路时不得不看着脚下,否则就会像在森林里一样被绊倒。我们穿着褐色和蓝色的低帮鞋走着。我哥哥戴着一顶帽子,我戴着一只便帽。雨水淋湿了我们全身。绵绵细雨,润物无声,就像我在家做的梦里。我常常梦见我在雨中这样行进,我不知道此时我们是否确实存在,我们是否在这里行走,或者这是否我以后会做的一个梦。
我们在广场上绕了一个大圈,在这里有一个摄影师,他曾把马尔塔堂姐的一张照片陈列在橱窗里。已经有两个月了。她在正中位置。我的哥哥说:她一点儿都不漂亮。马尔塔堂姐看上去像一个木偶。我们的金黄色头发被卷成了天使卷,我们的蓝眼睛在她那里就像是弹子一样圆。我在家里是惟一一个高颧骨的人,我像蒙古人一样有一双细长的眼睛。我哥哥和我,我们看上去很像。尽管如此,他却长得漂亮,而我却不是。你们看上去像小天使,玛格达拉姑妈说。我们俩长得像父亲。没有人会把我们的父亲比作天使。
我们的父亲有许多孩子。我哥哥和我,我们还有一些我们不认识的兄弟姐妹。如果我们遇见他们,我们能认出他们。而他们也能认出我们。我们生下来时都是光头。然后长出了金黄色的头发,姑妈和母亲用发卷将它们卷成鬈子。有时候,他们的卷发棒会将我们的脖子烫出小红疱来。总有陌生人在我们面前驻足,赞赏我们的木偶衣服和圆圆的大眼睛,而我们不说我们叫什么。我们在拳头里把长条巧克力攥成了棕色的巧克力棒,上面贴着锡纸和有时隐藏在下面的童话图画。
在医院里,我们没有脱帽子。母亲没有察觉我已没有头发。她夸奖我哥哥穿着祖父的大衣看上去如何魁梧。在她的床下有许多四角形的小绷带,好像上面涂着黑黑的机油。我不知道我们的母亲缺少什么。我甚至不知道她是否是我们的母亲。她瘦削、黑头发。她怎么可能将我们认作是她的孩子?我们没有给母亲带来什么吃的,既没有蜜饯,也没有糕点。我们走到外面时,我哥哥说,我们至少应该买束花。在医院门口,一个农妇在卖菊花。好像这是一个墓地。
你不要离去,我哥哥对我说。如果你离去的话,我就会像骑自行车的克莱门一样。戴着护耳皮帽、只露了半只眼睛的克莱门并不会骑自行车,但人们总是看见他跟那副锈架子在一起。他推着它穿过垄沟,越过公路,从死去的猫、狗、牛和鸡的旁边走过。就像那些带着拐杖的老太太,而她们不愿意承认,她们需要一根拐杖。克莱门是一个守田人,他总是喝得醉醺醺的。他告诉夏天在这里路过的骑自行车旅游者,八月初哪里有成熟的果实,因为骑自行车旅游者自己是找不到的。守田人克莱门对骑自行车的人心怀感激之情,他轻拍他们,并向那些只会说外国话的旅游者使眼色。但我的哥哥不会成为像克莱门那样的人。我哥哥漂亮。姑娘们会供养他。他将生八个孩子。都是金黄色的头发。

如果他们问我,我会说,我不从任何地方来,也不认识任何人。就这样有了我。我会唱歌。我会唱《魔笛》里的萨拉斯特罗的咏叹调。而且我学习过扮演一些男人的角色。十一岁时,我就知道,罗慕路斯的雄鸡叫什么。多米提阿努斯是一个坏皇帝。
如果你去的话,你会成为一个妓女,我哥哥对我说。他不喜欢妓女。有时我哥哥也会举出他喜欢和不喜欢的东西。“我喜欢的”有老虎、猫、一号广场,然后就是我。而“我所不喜欢的”是班主任V和校长S。出于迷信他从来不说这些可怕的名字,也不允许我说,然后是牧羊人、妓女和汽车司机。警察也在“我喜欢的”之列。
在火车站上,一个无家可归的人拄着拐杖,手里拎着一只破鞋子。在他前面有一个警察,向他大声吼叫,要他出示证件。
埃拉姑妈给了我们二十个鸡蛋。我们回家时,我为哥哥和我自己炒了两个鸡蛋。一星期后,我哥哥不再喜欢吃炒鸡蛋。我们不敢吃挂在贮藏室里的香肠。我们害怕,如果父母向我们问起来,我们无法解释,它们到哪里去了。
我哥哥嘴里含着一粒像豆子一样的白石头。他很灵巧,他不会将石头咽下去。他向姑娘们说,我们的美国叔叔赠送给他一棵胡椒薄荷,她们相信他的话,惊奇地看着他。我也想找到这样一粒石头,和我哥哥口里的那块石头一样美丽,在牙齿之间,白色的,像白垩。但我却没有找到。
我们吃乳脂。我的皮肤到处开裂,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不再吃鸡蛋以来,由于乳脂或我涂抹在脸上的蛋清的原因。我把蛋黄涂抹在我的手背和嘴唇上。在屋子和院子里,到处是晒干的蛋黄斑。我煮可可丸子、玉米粥和加干蔬菜的肉汤。我们趁热吃下去,我的舌头烫起了泡,我哥哥后来说。至少白天他什么都不喜欢吃。
你知道吗,你很丑,我哥哥说。你根本不需要去那儿。他们只需要美人。
玛格达拉姑妈送给我一件灰色的细方格花纹衣服,一直长到膝盖,凸显出我粗壮的小腿肚子。衣服的领口和袖口有黑色的镶边。
小时候,玛格达拉姑妈总是把我放在她的旧钢琴上,我必须给她背诵“你像一朵花”。每一次她都会哭泣。我没有告诉她,“你像一朵花”并不在我的朗诵表上。她是惟一对我想当演员不感到奇怪的人。她甚至坚信,这是可能的。我母亲在医院里对我说,她恨不能恳求人们把我送回去。
玛格达拉姑妈告诉我,她在村子里看见了我们的父亲。打昨天起他就坐在小酒店里玩牌。我对着窗户玻璃,用修剪器剪直我的头发。修剪器是祖父那时从西德旅游带回来的惟一礼物。我穿着父亲土褐色的婚礼服去考试,尽管它穿在我身上有点短。
在城里,沥青一直延伸到树的皮肤。我穿着蓝鞋子围着树根走来走去。

在我们等待的房间里,没有开灯。墙上装着深色的护墙板,有一个壁炉。壁炉是浅玫瑰色的大理石,和城堡里的一样。我把手放在他的肩上。恰好合适。我们站立着。在我们周围是其他人,他们不停地走动。地板在他们的身体下发出低沉的嘎吱声。
其他姑娘盯着我的头。一层几乎看不见的金色的绒毛覆盖在头上。我的耳朵。房间里的惟一光点落在它们上面。小伙子们没有看我。他们转过身去。为我感到惭愧。
在考试时我注意到A这个音,我尽量张开口把它读出来。其中一个男人最后说:您有口音。是的,我说。为什么我想成为演员。我说,我来自一个农庄。男人们脸上毫无表情。然后另一个男人看了一眼我的表格,问我:元素周期表?我点了点头。我深深吸了一口气,唱道:Ha—He—Li—BeBe—Ce—NeO—Fe—Ne—Na—MgAl—Si—Pe—Se—CLAr……
说简单点。一字一句。不要加任何激情。不要啜泣。不要含混。说简单点。一字一句。
如果人们来到城外,从公共汽车上望出去,我的家乡就好像是一个经过发酵的物质。是由纤维组成的,像我衣服的羊毛一样是褐色的,不可拆开。当我穿着父亲的衣服伫立在田野的边缘,回头望着一分钟前公共汽车把我丢在其间的朦胧夜色中的街道时,无论是汽车还是街道都消失了。我突然知道,我哥哥说得对:确实,这里有使我们成为隐身人的时间。
我的光头像一轮低低的月亮越过风景的中心。我穿越隐形的田野。我想,我会成为演员。我想,如果我成为演员,我必须注意怎么读A,并且留心不要让自己变成隐身人。我想到一个舞台,如同想到一面波浪型的玻璃窗,想到一架旧钢琴。我想到可可丸子和乳脂。想到我哥哥和我。想到我的头发变成田里的肥料。
守田人克莱门在小酒店里拉手风琴。我父亲已经输掉了三份退休金。除我之外,这里只有男人,当我穿着细方格条纹衣服走进来时,所有人都已喝得醉醺醺的。弗洛里安来了,他虽然害怕我父亲,但还是要求克莱门再演奏一曲波尔卡,我们在入口处的一块四方形的空地上跳舞。我父亲的目光一直都没有离开牌。
我哥哥坐在克莱门身边的板凳上。他的眯缝眼由于喝果子酒完全发红了,他的脸像白垩和蜘蛛丝一样苍白,他的头发是黄色的。我与弗洛里安跳波尔卡舞。小心,我哥哥说,这是一个吉卜赛人。那又怎样,我说。地板尘土飞扬,在我们的脚下跳动。你只能成为一个妓女,我哥哥声音低沉地说。那又怎样,我一边说一边与弗洛里安腿插着腿旋转。波尔卡正是我最喜欢的舞蹈。
Ha—He—Li—Be!



Mora),1971年生于匈牙利的索普隆,1990年获得奖学金,到德国洪堡大学学习匈牙利语言文学和戏剧,自此留居柏林。1998年成为自由职业作家。1999年,她出版了处女作,短篇小说集《奇特的物质》,同年,以这部小说集中的《奥菲丽娅事件》获得巴赫曼文学奖,2004年出版长篇小说《所有的日子》,还作有几部电影剧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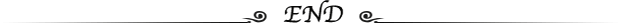
点击上图,订阅全年《世界文学》
点击上图,订阅单期《世界文学》

添加《世界文学》小助手
获邀进入《世界文学》分享会3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