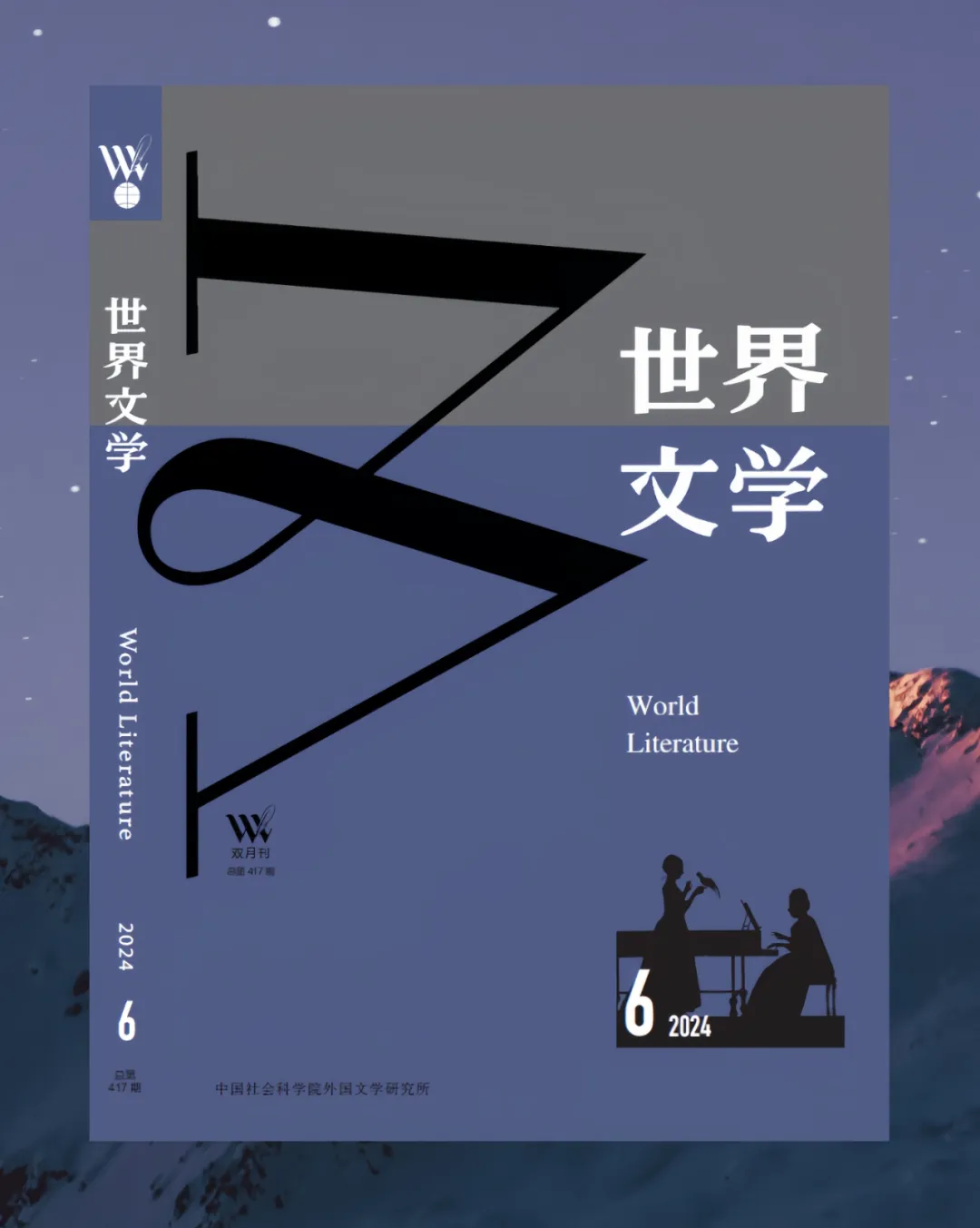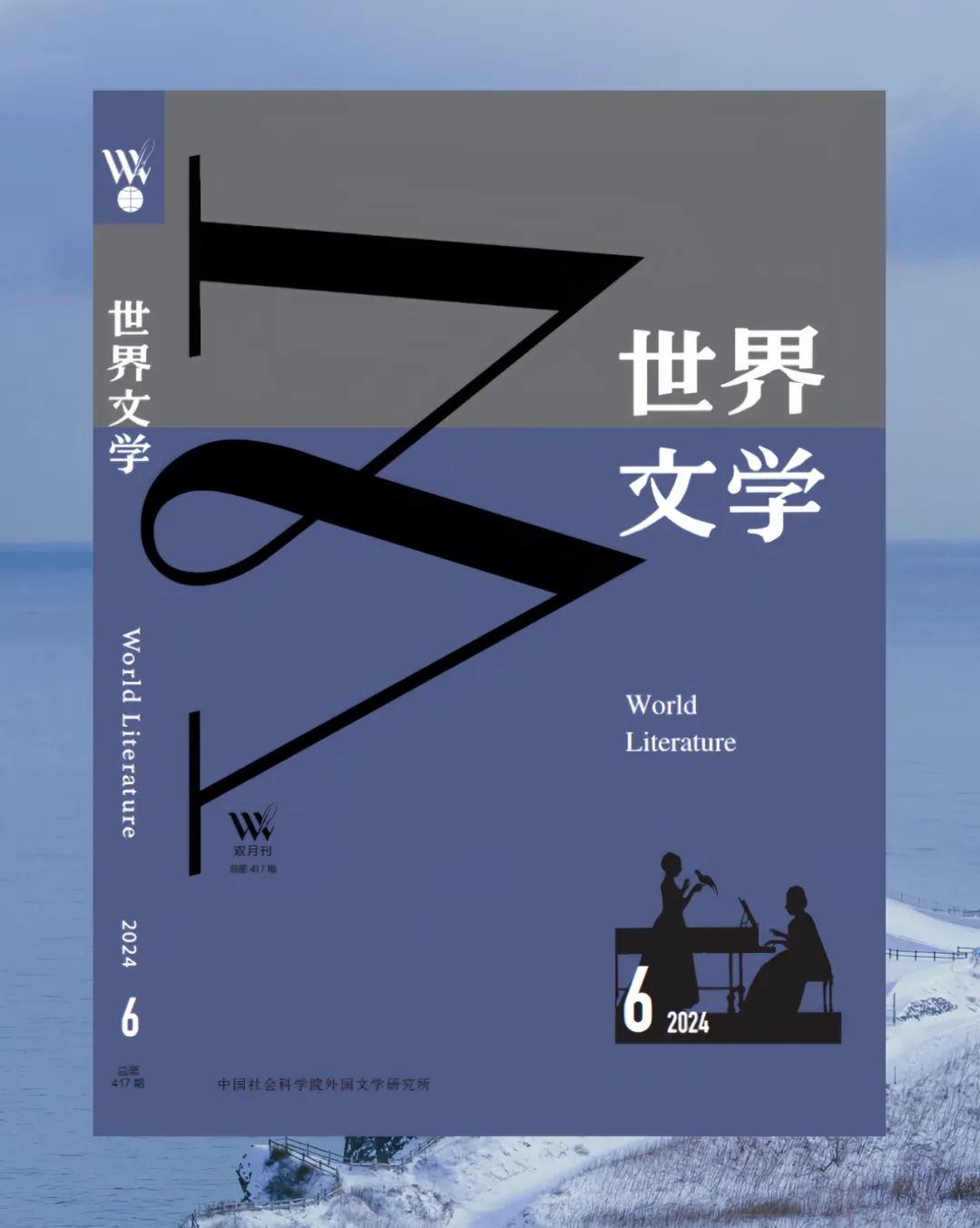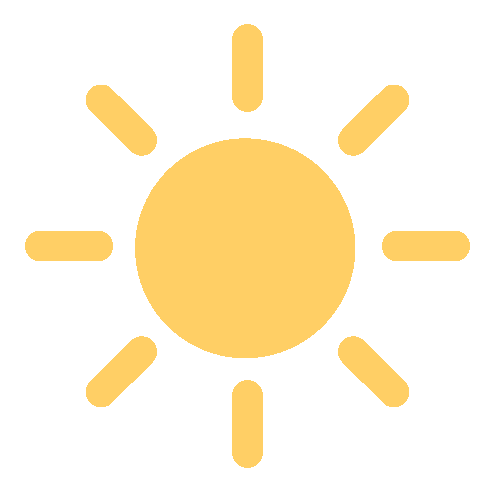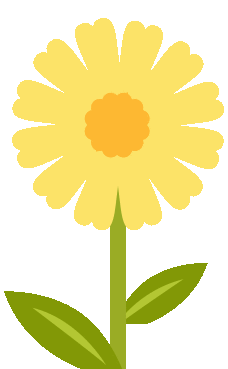小说欣赏 | 皮•莱克塞尔【意大利】:追本溯源,落实好开端,然后设法发现破绽……
![]()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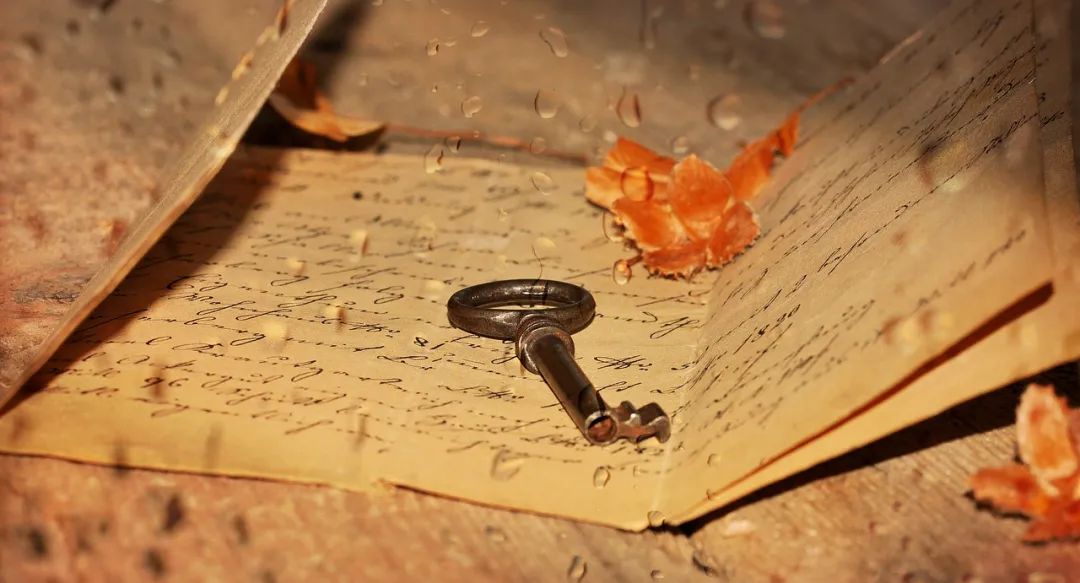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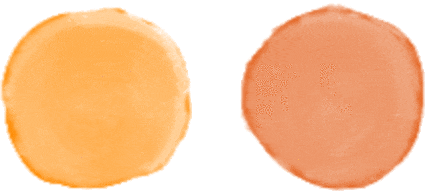
破绽
皮埃尔·莱克塞尔作
徐家顺译
今年春夏两季,阳光明媚,但是天气异乎寻常地凉爽。后山腰上的葡萄迟迟不肯成熟,以至于到收获季节时,我们不得不把相当一部分葡萄堆积在葡萄植株旁边。即使用收获的葡萄酿造,也生产不出可喝的酒来。
一些树木枯死了;漂亮而又忠诚的流浪猫穆纳不知去向,当初有一天晚上,它曾被诱狐狸的捕兽器夹碎了脚爪,多亏我们的救治,它侥幸活了下来。
我说到的那个寒冷的太阳射出虚假的光线。我被灿烂的阳光误导,多次想捕捉住清澈的光线;奇怪得很,怎么说我也算是个蹩脚的摄影师,我的谦虚、执着都无济于事,拍出来的照片在铜版纸上,光线黯淡,花朵褪了色,仿佛在田野景色上覆盖了一层忧郁的薄膜。梦中出现一个和我长得酷似的男人;当时我没有明白,他仗恃着我的自我,起初我只觉得这张脸很熟悉,我突然发现这张面孔就是我。然而,我终于发现这张脸颇有魅力——并向它伸出手去。
直到深秋季节,我才说服我的伴侣,暂时离开家中的炉火,去费拉拉待上几天工夫,那里举办的奥斯瓦尔多·利契尼的出色展览与钻石宫的名字相得益彰。
*
出发的那天早上,我们像往常一样,将房屋的钥匙交给表兄加近邻阿里斯蒂德,托付他帮忙照管房屋。一切都像是正常的,就像夏日照耀的阳光一样……
我去过意大利北方诸省及托斯卡纳,但没有去过艾米利亚。因此,我没有事先计划好在何处歇脚,加上生性喜欢冒险,我们就不紧不慢地向前行驶,太阳落山之前,我们打了几次尖。
一个小城市迎面而来——从那以后,我不愿再提起它的名字——显得静谧、殷勤、好客,我们开始感觉疲劳,因此抵挡不住它的诱惑。看来,找一家旅店不是什么难事,当时是旅游淡季。街道拐角处有一家旅店,旅店的大门朝着向后缩进去的小广场;这旅店唤起我某种模糊的回忆,我就选定这家旅店。小广场对面,是一家杂货店,那里可以买到报纸、杂志。天空飘过橘黄色的云……洛拉握住我的手说:“晚霞红,明天晴。”【原文为意大利文】
旅店入口处,有一条三或四米长的走廊,走廊尽头的短楼梯通向底层和二楼之间的夹层,那里有一个五边形的服务台;其中三面倚墙,宽度各不相同,但都有一扇门。右边的门敞开着,隐约看出是一间厨房,有两个妇人在里面忙碌着。老式炉灶上的一只铁锅及两只平底锅发出咕嘟咕嘟的声响。
我们受到质朴、亲切的接待,并且立即被领到同一层楼的一个房间里,它与楼梯成直角。房间布置得很舒适,光线从后窗射进来,后窗下面是一个果园。一个宽大的铸铁散热器散发出暖洋洋的热气。这时,从旅店传来低沉而令人放心的嘈杂声音,我们感到,晚饭前在宽大、柔软的床上躺一会儿真是再惬意不过了。一切都向我们预示着,会有一个舒心的夜晚,懒洋洋地读几页书,愉悦地做爱,甜蜜地入睡,然后平静地醒来。这一夜确实是这样度过的。


窗玻璃上凝结的水蒸汽预示着清晨的凉爽,同时伴有一层薄雾,曙光透过这层薄雾漫射在波河平原上。
下床前,我即兴作小诗一首,一首不大吉利的小诗,——就像心情比较轻松时常有的情形,一种虚假的悲怆一吐为快:
在高挂天空
趾高气扬
半透明的太阳光下面
在波河的水蒸汽亵渎的空气中
安娜,我的姐姐,安娜
你可看见什么在闲逛
你可看见什么在翱翔
我看见一个茨冈人
在他的大篷车队里
一个农妇
牵着她的驴
一只飞翔的雉
一只雄孔雀及一只雌孔雀
那只受到爱情惩罚的孔雀
钟声敲响
它悲伤的孔雀舞
栗色马马失前蹄
我的药茶凉了
安娜,我的姐姐,安娜
你可看见什么在闲逛
你可看见什么在翱翔
只有土地在翱翔
波河的水蒸汽
束缚住一个身体
一颗心在枯萎
一只乌鸦在拾谷物
死神在嘲笑
一个教士走过
我终于下决心起床,从拥抱的两臂中,从使人昏昏欲睡的温暖中脱身出来,让懒洋洋、睡意正浓的洛拉多躺一会儿,——我趁这工夫梳洗,剃胡子。我穿好衣服后,趁她伸懒腰之际,就利用我时间上的提前——让她考虑订早点——将我们的行李放在汽车后备箱里,再去昨晚发现的小店里买一份报纸。
从小店出来,我在为去费拉拉还有相当一段路程,还有一段旅程而庆幸,只有心血来潮才能改变它,为即将在一个陌生的城镇欣赏到绘画及素描而高兴,而那些绘画,我是在威尼斯第一次体验到它们的魅力,后来又在都灵欣赏了它们。
于是,我迎着凛冽的寒风,轻松、愉快地向洛拉跑去,我有些恶作剧地一路小跑着,为了暖和一下身子,很想无端地发发火,准备吃下一筐吐司……
*
……真是咄咄怪事,坐落在对面人行道旁的这家旅店——这会儿,在早上令人兴奋的空气中,我正朝它走去——跟昨天黄昏时我们看见它时,似乎有说不出的不同之处。我绕过旅店正面,惊奇万分,我怎么没有注意到一楼窗子上的锻铁栅栏,也找不着我记忆中的大门;往回走几步,竟然辨识不出周围的环境,也没见到大门及招牌上的图案,尽管茫然不知所措,我还是推开那门……
这不再是我记忆中的走廊,只是一个过道,两扇门扉的出口,紧接着一个很陡的楼梯,通向一扇玻璃门。玻璃门后面,五边形的夹层不见了,只有一个狭窄的门道,向下通往一个办事处的门厅。里面有三个妇人边干活儿、边闲聊,一个男人坐在椅子上用探索的目光看着她们,这人穿着很随便,从他顺从、狡猾的神情判断,是个侍者,正歇着。一阵焦虑在我心里油然而生。他们之中似乎没有人认识我,而且我也不认识他们。洛拉去哪儿了?发生什么事了?我应该相信我的眼睛吗?相信这一双双注视着我的探究的、还带有一丝敌意的眼睛?


“请问,”我说,“我是在旅店里,是吗?是另外有一个大门吧?我怎么找不着我和我妻子住宿的房间了……你们能告诉我……”我的话还没有说完,三个妇人都怀疑、惊奇地注视我。我像许多奥斯塔河谷的居民一样只能讲一点儿蹩脚的意大利语,因此,容易听懂。可是不知怎么的,看这些人的神情,仿佛我说的是外国话似的!
三个女人中年纪最大的一个终于回答我,她说的方言,我能猜出一点儿意思,她说,女主人出去了,她们什么也不知道。坐着的男人只是傻笑。
迟疑、尴尬之际,我含糊地道歉,就回到街上。一切都像是真的,摸得着的,一目了然的;就像四周没有任何别的旅店那样一目了然;就像我的汽车停在两株树中间的土地上那样一目了然。我畏缩地围着汽车转了一圈,担心受到幻觉的愚弄,想抓住希望,发现一点儿蛛丝马迹——也许是谜底。在我自己的东西中,发现洛拉的衣物,发现我们的旅行袋——换了另一个人,这能证明什么呢?除了我试图“制造假象”,掩尸埋迹、掩盖谋杀之外,这些平凡的宪兵还能得出什么合理的结论呢?
我的心剧烈地跳动。我的脑袋摇得像掷骰子的皮杯,仿佛要从里面蹦出三个六点……一切从头开始,我自言自语说,追本溯源,落实好开端,然后设法发现破绽,我最后一次核实前一天晚上我们不是从另一扇门进来的,然后我坐到方向盘前,焦躁而不知所措地踩下油门。
我能期盼什么样的情景呢?首先,我一上来就提问题合适吗?是不是最好像俗话说的那样,听任事态的发展呢?以至于对我从起点重新进行搜索的论据产生不了任何影响,如果有理由……
阿里斯蒂德被我从午睡中叫醒,看见我独自一人回来,眼睛瞪得圆圆的,立即证实了我的担心。
“洛拉呢,你在半路上把她弄丢了吧?”他半开玩笑、半好奇地问。
咳,我该怎么向他解释,我将她丢在了一间想象的房间里,离开了她?于是,我带着尽可能的自然神态回答,活像是一个为自个儿的冒失行为而恼怒的人:
“怎么不是呢!要是她能换衣服的话,不如说是她把我弄丢了;出发前,我忘记将她的衣服放进汽车里;我只好赶紧回来取她的衣服。”
(阿里斯蒂德不可能知道这些衣服已经都在我们唯一的一个帆布包里了。)因此我向他要钥匙,上楼去房间里,匆忙地往一个大包里塞了几件叠好的衣服,是从洗衣店取回来,出发前洛拉堆放在床上的;我心里咚咚跳,等着不知会突然出现什么奇迹,穿过冰冷、没有人的房间,装出行色匆匆的样子下楼来,这匆忙不管表演得多么像,绝不是假的;我将提包放进汽车后背箱里,重新上路朝一个莫名其妙地消失的伴侣驶去。
一丝怀疑掠过我的脑子,我的理智在侦察战场,我就要毫无恐惧地从这噩梦中醒来,一种暂时的遗忘症使我迷糊了,——我沿着前一天走过的路线,专心致志地回想我认为我曾经见过的东西。
我想不起有什么特别的东西,我应该高兴还是悲伤呢?我不敢提这样的问题,倾向于让自己躲避在一种脆弱的离题话中,那里还有一丝希望,一丝依稀摇曳的希望还能留在悬念中。
我津津有味地沉浸在这种第二状态中,接近于催眠状态,莫非这就是这次事件的原因么?……
*
有人告诉我说,当人们从人行道上将我扶起来时,我手里一直握着一张晨报;说我在奔跑中,一头撞着一家酒吧咖啡座的铁护栏,倒在地上。
有热心人送我回旅店。我还头晕目眩,在房间里看见洛拉,她一边等我,一边在烤面包片上抹黄油。我以为是在梦中……
“嘿!”洛拉叫嚷道,“我打开后备箱取油桶时,发现你忘记拿走包和从洗衣店取回的衣服。”
与此同时,我的手指头在衣兜里握住两把钥匙,就是我们出发前交给阿里斯蒂德的钥匙。
迎接我们归来的是同一个阿里斯蒂德,他顺便对我们说,他曾梦见:
就在我们动身的第二天,我独自一人返回了家,而把洛拉抛下在他不知道的什么地方,他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至于我们的钥匙么……我们的钥匙?天哪,它们跑到哪儿去了?他困惑地连连搔脑袋。
我半喜半嗔地从我口袋里掏出一串钥匙。
“嗨!”他惊叫说,“你瞧,是你忘记把钥匙交给我了吧……然而,我发誓把钥匙放在墙上纳塔丽娜的照片后面了……”

Lexert,1923—2015)出生于巴黎,但故乡在意大利的瓦尔多特,他后来也一直在那里生活。莱克塞尔小学起就开始写诗歌。其创作十分多样化,写诗歌、小说、评论、专栏文章。发表的作品有诗歌《长途跋涉的心》(1979),《如此俄耳甫斯》(1983),《情感启蒙》(1984)等。1992年获得法语诗歌银茉莉花奖,1996年获得由法兰西学士院颁发的“光大法兰西语言文学”大奖。他被评论界认为是一个比较怪的作家,他的作品用法语写作,却体现了浓厚的意大利故乡气息。
原载于《世界文学》2006年第4期,责任编辑:余中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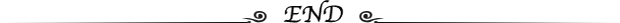
点击上图,订阅全年《世界文学》
点击上图,订阅单期《世界文学》

添加《世界文学》小助手
获邀进入《世界文学》分享会3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