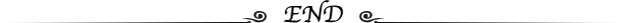小说欣赏 | 塔•托尔斯泰娅【俄罗斯】:猎猛犸
![]()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有幅画是一片遍布了悬崖峭壁的地方,一堆木贼,从木贼里钻出一只穿着拖鞋的猛犸。一个小人用弓箭瞄准它。而从侧面能看见一个小山洞,那里有一只用绳子拴着的电灯泡,电视发出亮光,煤气炉的火光闪烁着。甚至还仔细地画上了一只炒锅,在小桌子上摆放着一束木贼。画的名字叫《猎猛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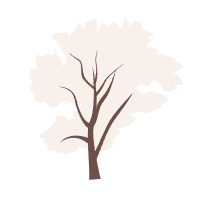

塔吉雅娜·托尔斯泰娅作 陈方译
卓娅,这是一个美丽的名字,对吗?叫起来就好像是一群蜜蜂在嗡嗡叫。她本人也很美丽:个头不高不矮等等。说细节?好吧,那就说说细节吧:漂亮的双腿,漂亮的体型,皮肤不错,鼻子,眼睛,所有部位都很漂亮。栗色头发。为什么不是金发?因为不是所有人在生活中都有这样的福分。

卓娅和弗拉基米尔认识的时候,后者简直大为震惊。嗯,或者说,他至少愉快地感到了惊讶。
“啊!”弗拉基米尔说。
他就是这样说的。他还想和卓娅多见见面。但不是经常见面。而这一点让卓娅很伤心。
在卓娅一居室的住房里,弗拉基米尔的私人物品只有一把牙刷,这个东西,毫无疑问是非常私密的,但是它还不足以把一个男人牢牢地捆绑在家庭的安乐窝里。卓娅希望弗拉基米尔的衬衫、衬裤、袜子,这么说吧,都服服帖帖地放在她家里,和她的内衣柜成为一个整体,希望它们被扔得到处都是,甚至扔到椅子上也可以;她想随便抓起一件什么毛衣,然后把它泡在水里!放到荷花牌洗衣机里!之后把它摊平晾干。
然而不是这样,他什么痕迹都不留下;他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在自己的筒子间里。就连刮胡刀也放在那儿!可是他这个大胡子男人在那里有什么可刮的呢?他有两片胡子,一片是浓密的,颜色深一些,在这片胡子中间似乎还长着一片不一样的胡子,在下巴上,稀少一些,是棕红色的,只有一小撮。这简直是个奇观!他吃饭或者大笑的时候,这第二片胡子也随着上下跳动。弗拉基米尔的个头不高,比卓娅矮半头,他长得有些野蛮,头发很密。他的动作非常快。
弗拉基米尔是一个工程师。
“您是工程师?”第一次见面时,卓娅温柔而又漫不经心地问道,他们坐在一个餐厅里,卓娅把嘴巴张开一毫米,品尝着巧克力甜点,她做出一副样子,似乎她是由于某些文化原因才觉得那东西不好吃的。
“是——的。”他盯着卓娅的下巴回答道。
“您在科研所?”
“是——的。”
“……或者在生产线?”
“是——的。”
试着去理解他吧,他实在是看她看得着了迷。他还有点喝多了。

工程师也不错。事实上,他最好是一个外科大夫。卓娅在医院工作,在问讯处,她穿上了白大褂,因此轻松地融入了这个神奇的医学世界,这个白色的、浆洗过的世界,这里有注射器、手术刀、担架和灭菌器,还有一摞摞盖着黑色戳记的干净的粗布被单,还有玫瑰花,眼泪,巧克力糖果,还有沿着没有尽头的走廊被奋力抬走的青色尸体,一个伤心的小天使急匆匆地在尸体后面飞翔,把死者那颗饱经风霜的、获得了自由的、包裹得像个洋娃娃似的心灵紧紧地搂在自己小鸟般的胸膛中。
而这个世界的国王是一个外科医生,看着他的时候,不可能不感到颤抖。他由宫廷侍卫帮着穿上宽敞的外衣,戴上卷起帽檐的绿色王冠,他站在那儿,庄严地抬起自己无价的双手,他准备完成一个神圣的国王的任务:完成最高的审判,进攻与切除、惩罚与挽救,然后用闪亮的宝剑赐予生命……哎呀,怎么可能不是国王呢?卓娅极其盼望落入外科大夫那鲜血淋漓的怀抱。不过,工程师也不错。
他们俩相识后,在饭店里愉快地度过了一段时间,弗拉基米尔那时还不知道他在卓娅身上能指望些什么,所以非常慷慨。他变得勤俭节约是以后的事情了,他后来只给自己点一道肉菜,不太贵的,而且他从来不在饭店里耽搁太长时间。卓娅表情阴沉、百无聊赖地坐在那里,她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有一点儿嘲讽,又有一点儿若有所思,也许她复杂的内心生活的影子会转瞬即逝地划过她的面孔,那似乎是一种文雅的忧郁,或许是某种细腻的回忆;她坐在那儿,仿佛望着远方,她把胳膊肘优雅地撑在桌子上,鼓起下嘴唇,把漂亮的烟圈透过涂了口红的小拱门般的嘴唇吐出来。正在进行的是一个扮演仙女的游戏。但是弗拉基米尔演得很糟糕,他兴致勃勃地吃着,没表现出一点忧郁,他畅饮着,他并不是慵懒地抽烟,而是刚刚迅速而又贪婪地吐出一口烟,就已经用他那黄色的手指在烟灰缸里掐灭烟头了。他把账单凑到眼前,大惊失色,然后马上就开始找毛病。他从来都没点过鱼子酱,他说,只有公主和小偷才吃鱼子酱。卓娅不高兴了,难道她不是公主吗?虽然是个尚未被发现的公主。后来他们根本不去饭店了,在家里待着。或者她一个人待着。很无聊。
她想夏天的时候去高加索。那里很热闹,有葡萄酒,有伴随着尖叫声的夜泳,还有一群有趣的男士,他们看见卓娅可能会说声“噢!”之后露齿微笑。
但是弗拉基米尔把一个皮划艇拖回了家,还带回来两个同志,他们和他一样,穿着味道浓烈的方格翻领衬衫,他们趴在地上,把皮划艇折叠起来又打开,在上面打了一些补丁,然后把招人讨厌的皮划艇一点点放到水盆里试,他们惊呼着:“漏气!不漏气!”而卓娅醋意十足地坐在床垫上,她不喜欢屋子里的拥挤,还有,她不得不总是抬起脚,好让弗拉基米尔能够从一个地方爬到另一个地方。
之后她不得不跟着他和他的朋友们开始那场可怕的远足,他们去北方,沿着一些湖泊去寻找一些仿佛非常神奇的岛屿,她冻僵了,浑身湿透了,而弗拉基米尔身上散发出一股狗毛的气味。他们划船快速前进,他们在波浪上颠簸着,沿着北方黄昏时分的、铅黑色的湖泊颠簸着。卓娅直接坐在那艘讨厌的皮划艇的底部,她伸直了双腿,她的两条腿因为没穿高跟鞋而一下变得很短,在运动裤里是如此可怜而又消瘦。卓娅觉得她的鼻子是红的,头发乱七八糟,而令人厌恶的水珠把睫毛膏弄得到处都是,可是接下来还要忍受两个星期的折磨,在潮湿的帐篷里,在长着松树和浆果的荒无人烟的岩石上,在陌生人中,在健壮得令人感到害羞的人们中,在他们高兴地吃着豌豆罐头做成的午饭时发出的喊叫声中。
轮到卓娅在冰冷而又深邃的湖水中清洗那些油腻腻的锡皮碗了,无论怎么洗它们都还是脏的。而她的头也是脏的,在头巾下面发痒。
所有的工程师都带着自己的女人,谁都没用特别的眼神看过卓娅,也没对她说“噢!”于是她觉得自己是一个丧失了性别的穿裤子的人,她讨厌篝火前的笑声和拨弄吉他的声音,讨厌他们在捉到狗鱼时发出的欢叫。她躺在帐篷里,感到非常不幸,她憎恨这个长了两片胡子的弗拉基米尔,她想快点儿嫁给他。那样的话,就可以享受合法妻子的全部权利,而不是在这种所谓的大自然里蓬头垢面地待着,她想待在家里,穿着柔软、优雅的睡袍(四周镶着绉边,德国出产的),坐在沙发上,跷着二郎腿,她希望眼前是大壁橱,彩色电视(就让弗拉基米尔买吧),粉红色的南斯拉夫落地灯,有一些可以喝一喝的软饮料,还有一些可以抽一抽的好烟(就让病人的亲属们去买吧),她希望等待弗拉基米尔从皮划艇远足中回来,然后带着些微的不满和怀疑去迎接他:我好奇的是,没有我的时候,你在那里都做了些什么?你们和谁一起去的?你带鱼回来了吗?之后,就像她应该做的那样,原谅他两个星期的缺席。而在他缺席期间,可能,那个熟悉的外科医生会打电话来调情,而卓娅会懒洋洋地抱住电话,故意做出些表情,她会拖长声音说:“哦,我不知道……看看吧……你真是这么想的吗?”也许她会给女朋友打电话:“哦,那你怎么样?那他又怎么样?哦,那你呢?”啊!城市!闪耀的灯光,夜晚,潮湿的柏油马路,还有高跟鞋踩出的小水洼映出的红色霓虹灯……
可是在这里,一层层波浪重重地击打在岩石上,大风在树梢呼啸着,篝火跳着自己永恒的舞蹈,而夜晚近在咫尺,那些工程师的脏乎乎的丑老婆们正在帐篷周围唧唧喳喳地说话。郁闷啊!
弗拉基米尔兴高采烈的,他起得很早,湖水在那时既安静又明亮,他顺着陡峭的斜坡走下去,扶着松树,手掌被松脂弄得脏乎乎的,他两脚叉开站在大理石般的平地上,那块平地通向阳光明媚的透明水面,他在那里洗澡,擤鼻子,大喊大叫,用幸福的眼神看着睡眼惺忪、未加修饰的卓娅,她手握一个水罐,脸色阴沉地站在那里。弗拉基米尔问:“怎么样?你从前听到过这种寂静吗?你听听,多安静啊!而空气呢?简直是天赐啊!”哎呀,他是多么讨厌啊!嫁给他,赶紧嫁给他!
秋天的时候,卓娅给弗拉基米尔买了一双拖鞋。格子面的,很舒服,鞋子在走廊里咧着嘴巴等待着他:把脚丫儿伸进来吧,沃瓦【弗拉基米尔的爱称】!这里就是你的家,这里就是你寂静的港湾!和我们待在一起吧!你总是往哪里逃呢,小傻瓜?
卓娅把自己的照片——栗色的鬈发,又平又直的眉毛,严厉的目光——塞到了弗拉基米尔的钱包里,如果他翻月票或者付钱的时候,他就会看见她,看见她这么漂亮,他会感叹道:“唉,我怎么会不结婚呢?如果她被别人追去了怎么办?”每到晚上的时候,卓娅一边等他,一边在窗台上放一盏粉红色的圆脚台灯,这是黑暗中的家庭灯塔。为了稳固家庭的锁链,为了心里头感到温暖。房子是黑暗的,夜晚是黑暗的,但是有亮光,一盏台灯亮着,那么这就是他心灵的星星没有睡觉,可能,卓娅在摆弄那些罐子,可能,她想洗洗衣服。
枕头是柔软的,在绞肉机里绞了两遍的肉丸子也是柔软的,一切都充满了诱惑,而卓娅像个小蜜蜂似的嗡嗡叫:“赶紧啊,好朋友!赶紧啊,你这个坏蛋!”


她想嫁出去,趁自己还没到二十五岁的时候,否则再往后就一切都完了,青年时代业已结束,你被赶出礼堂,别人,那些机灵的、鬈发的女孩会占领你的地盘!
早上,他们在喝咖啡。弗拉基米尔读《快艇》杂志,他嚼着东西,许多碎屑沾在他的两片胡子上;卓娅充满敌意地一言不发,她看着弗拉基米尔的脑门,给他发送心灵感应的电波:结婚吧,结婚吧,结婚吧,结婚吧,结婚吧!晚上,他又在读着什么,而卓娅看着窗外,她在等着究竟什么时候才能睡觉。弗拉基米尔读书读得并不安静,他情绪激动,抓耳挠腮,抖着脚,哈哈大笑,还大声说:“哎呀,你听听!”他笑得说不出话来,一边用手指头戳着卓娅,一边给她读那些让他感到非常喜欢的东西。卓娅或者酸溜溜地微笑,或者冰冷地、眼都不眨一下地看着他,一点儿反应都没有,而他窘迫地摇晃着脑袋,变得沮丧起来,他嘟囔着说:“这个男的可真逗……”出于骄傲,他有意在脸上保持着那种不自信的微笑。
她是善于破坏弗拉基米尔的快乐的。
不过事实上是这样的:他在这里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一切都打扫过,整理过,冰箱是按时除霜的。这里有他的牙刷,拖鞋。这里有人给他吃的,给他喝的。需要清洗什么东西,来吧!看在上帝的分上!那你还要怎样呢,你就这个样子,你不结婚,你难道只想破坏大家的心情吗?!要是千真万确地知道你不打算结婚,那就再见吧!咕咕!给阿姨带好!可是怎么才能知道他的想法呢?卓娅还是有些不敢直接问。几百年来的经验发出了警告。一次不成功的发射之后,一切就全完了,全落空了;猎物会撒开腿跑得远远的;只有灰尘留下了,还有脚后跟在发光。不,应该引诱。
而他这个混蛋住习惯了。他觉得自己就像在家里一样。他变得非常驯服。他从筒子楼里拿来了自己的衬衫和夹克。他的袜子现在扔得到处都是。他一来就换上拖鞋。他边洗手边问:“那我们今天晚饭吃什么呀?”我们——您听到了吗?他就是这么说话的。
“肉。”卓娅透过牙缝回答道。
“肉?太—好—了!太—好—了!我们这么不满意是怎么回事?”
或者,他会异想天开地说:
“你想吗?我们买辆汽车吧?我们开车,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简直就是嘲讽!就像他根本没打算离开卓娅去任何地方!可要是真的没这样打算呢?那就——结婚吧!卓娅可不想爱得没有保障。
卓娅放了一个兽夹:她要刨开一个坑,盖上树枝,之后悄悄地把弗拉基米尔推到跟前,悄悄地推……她已经穿好了衣服,化好了妆,她突然拒绝出去做客,她躺到沙发上,充满悲哀地看着天花板。这是怎么回事?她不能去……为什么?因为……不,怎么回事?生病了?发生什么事了?而她不能做的,就是不能去做客,她不好意思让自己暴露在所有人的耻笑之中,所有人都会戳戳点点,说:“有意思,她是以什么身份钻到这儿来的?所有人都带着妻子……”蠢话,弗拉基米尔说,那里最多只有三分之一是妻子,而且她们还是别人的妻子。要知道卓娅一直都是去的,不是什么事都没有吗?一直都去,可是现在不能去了,她的心灵组织非常细腻,她就像一朵玫瑰花,如果被照看得不好,就会枯萎。
“真有趣,我什么时候不好好照看你了?!”
诸如此类,诸如此类,他们离那个铺好了伪装的大坑越来越远了。
弗拉基米尔带卓娅去一个画家那里,人们说他非常有趣。卓娅想象那是一个上流社会,有一小群艺术理论家:女人们是一群好唠叨的老太婆,全都戴着绿松石首饰,而脖子就像火鸡那样;男人们是优雅的,穿着胸前缝了很多口袋的衣服,他们拿着彩色手帕,身上散发着好闻的味道。一个戴着单片眼睛的高贵老头挤过来。他是画家,身着天鹅绒衬衫,面色苍白,手里拿着调色板。这时卓娅走了进来。所有人都“噢!”的一声。那个画家变得更加苍白了。“您应该为我摆造型。”高贵的老头用贵族般的忧郁目光看着卓娅:他的岁月已经流逝,卓娅的芬芳已经不是为他而散发的了。卓娅的肖像——人体画像——将运往莫斯科。在钱币博物馆里展出。警察在制止人群的拥挤。展览在警戒线之外。防弹玻璃保护着画像。两个人两个人地进来。警笛在鸣叫。所有人都紧紧贴在右边。总统进来了。他被震惊了。原型在哪里?这个女孩是谁……


“别在这里把脚扭了。”弗拉基米尔说。他们下楼来到一个地下室。在热水管道上悬挂着一些麻布条。画室里面非常暖和。那个画家是个衣衫褴褛的小个子,他正在拖动一些分量很重的画。那上面画的是一些奇怪的东西,比如,一个大鸡蛋,从里面伸出很多小人,而在一些云朵中间,一个脚蹬胶皮靴、身着花睡衣、手握茶壶的人正缥缈升腾。所有这些合在一起叫做《罗马教皇》。有幅画画的是一个苹果,从里面爬出一条戴眼镜、拎皮包的蛆虫。有幅画是一片遍布了悬崖峭壁的地方,一堆木贼,从木贼里钻出一只穿着拖鞋的猛犸。一个小人用弓箭瞄准它。而从侧面能看见一个小山洞,那里有一只用绳子拴着的电灯泡,电视发出亮光,煤气炉的火光闪烁着。甚至还仔细地画上了一只炒锅,在小桌子上摆放着一束木贼。画的名字叫《猎猛犸》。有意思。“怎么样,大胆吧,”弗拉基米尔说,“大胆,大胆……可是思想呢?”“思想?”画家快活而又惊讶地说道,“您这是在得罪我!我难道是巡回画派的吗?思想!兄弟,应该撒开腿逃离思想,连头都别回!”“不,可是不管怎么说,不管怎么说……”他们争论了起来,挥动双手,画家把一些放不平稳的陶瓷杯子摆在小矮桌上,用胳膊肘擦了擦不太干净的空地儿。他们喝的是难喝的东西,吃的是一堆像硬石头一样的前天剩下的东西。主人用明亮的、似乎是职业人士的漫不经心的目光扫了扫卓娅的外表。他的目光并没有抓住卓娅的心,就好像卓娅根本不存在一样。弗拉基米尔的脸红了,他的胡子变得凌乱了,他们俩都在大喊大叫,说着“荒诞”和其他一些类似的词汇;一个人援引乔托【乔托(1266/67—1337),意大利画家,前文艺复兴时期代表人物】,另一个人援引莫依谢延科【莫依谢延科(1916— ),俄罗斯画家,绘有反映国内战争的《战争岁月》等作品】,卓娅被他们遗忘了。卓娅的头开始疼了起来,耳朵嗡嗡响——嗡,嗡,嗡。窗外的黑夜里下起了雨,天花板上灰蒙蒙的灯泡透过一层层幽蓝的雾气发出了亮光,在粗糙的白架子上,堆放着一些插着克里木蒺藜的罐子,它们早被打破了,蒙上了一层蜘蛛网。卓娅既不在这里,也不在任何地方,她根本就不存在。余下的世界也根本不存在了。只有烟雾和喧哗:嗡嗡嗡嗡。
在回家的路上,弗拉基米尔搂住了卓娅的肩膀。
“这个人太有意思了,虽然他是一个精神病!你听见他的争辩了吧?!真可爱,啊?!”
卓娅恶狠狠地沉默着。雨还在下着。
“你是我的好样的!”弗拉基米尔大声说着。“我们现在就回家去,然后喝点浓茶,好吗?”
无耻的弗拉基米尔。那些不诚实的、无耻的方法。打猎的规则是存在的:猛犸走得稍远一些,我瞄准,射击——嗖—嗖—嗖!于是它就准备好了。我把它的躯体拖到家里,这就是给漫长的冬天准备的肉。而这个人是自己来的,他走得很近,在草地上游荡,啃青草吃,在墙上挠背,在太阳底下打瞌睡,装出一副驯顺的样子!他让别人给他挤奶!可是牲畜棚是敞开的,大敞四开!我的上帝啊,要知道连牲畜棚都没有!他是要离开的,要离开的啊,上帝!需要一片栅栏,一面围墙,需要绳索和粗缆绳!
嗡嗡嗡。太阳落山了。太阳升起来了。一只戴着脚环的鸽子落在窗台上,它严厉地看了看卓娅的眼睛。看吧,看吧,请!一只鸽子,一只光秃秃的,脏乎乎的小鸟,就连这样的鸟都套上了脚环。穿着白大褂的学者们,他们长着诚实的、受过教育的面孔,他们是科学博士,他们抓起这只小鸽子,抓住它的背部——老爷,请原谅我的打扰——而鸽子明白,鸽子没有意见,它一声不响地为他们伸出自己红皮肤的爪子——请吧,同志们!你们的事业是正确的!咔喳!它已经不能随随便便地就飞了,它不会像一个无赖那样在脚底下打转,它不会耷拉着下巴颏躲开那些卡车,不会的,它会科学地绕过房檐和阳台,文明地啄食放在那里的谷物,它还会牢牢记住它的同胞们的灰色斑点,从现在开始,就连那些鸽子也被科学的无价之光照耀着,因为科学院知道,他们了解,而且,如果需要的话,他们是会过问的。
她不再和弗拉基米尔说话了,她坐在那里看着窗外,整小时整小时地思考着那些学术研究用的鸽子。当她在自己身上捕捉到那个工程师忧郁的目光时,她紧张地问:“喏?那些神圣的词语在哪儿?说啊!你要投降吗?”
“小卓娅,你这是怎么了?我满怀爱情来找你,可是你对我就像……”两片胡子的人嘟囔着说。
她的轮廓变得僵硬了,锐利了。人们看见她的时候,很久都没人说过“噢!”了,反正她现在也不需要这个了,因为在她心里燃烧着一束无法抹杀的痛苦的蓝色火苗,它压倒了世界上的所有火光。什么都不想做。弗拉基米尔自己用吸尘器,自己打扫地毯,自己为冬天准备番茄酱。
嗡嗡嗡,卓娅的脑袋里嗡嗡作响,而拴着亮闪闪的订婚戒指的鸽子从黑暗中站起来,目光中充满责备,非常阴沉。卓娅又平又直地躺在床垫上,用毛毯盖住了自己的脑袋,然后,她把手伸得直直的。无边无际的灾难——中世纪的大师们恐怕会如此称呼这尊木头般的雕像,这本画册会放在书架的侧面。无边无际的灾难——就是这样的。唉,只有他们能正确地刻画出她的心灵、她的痛苦和她的毛毯的所有褶皱,只有他们能刻画出来,并把她放在令人头晕目眩的花边教堂的最顶端,放在最上面,他们可能会给照片一个特写:卓娅。细节。早期哥特风格。蓝色的火焰温暖了毛毯做成的洞,没有可以呼吸的空气。工程师踮着脚尖走出了房间。“去哪儿一呀?”卓娅像仙鹤那样叫了起来,于是结了婚的鸽子冷笑一声说:“我,是这样……我去洗手……你休息吧。”那个恶魔惊恐地小声说道。
“开始他假装要洗手,之后假装要去厨房,而在那旁边就是大门,”鸽子在耳边提醒说。“一下儿就跑了……”
要知道这是真的。她往两片胡子的脖子上套上了绳索,她躺在床垫上,拽着绳子仔细听着。在那一端传来窸窸窣窣声,还有叹气声,跺脚声。她从来都没特别喜欢过这个人。没有,有什么呢,她一直都厌恶他。那是一个矮小的,有力的,沉甸甸的,灵巧的,毛发茂盛的,没有感觉的动物。
它又翻腾了一段时间,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它一直都不安分,直到最终变得平静了下来,直到一片伟大而又圣洁的、浓重而又冰冷的宁静慢慢地降临了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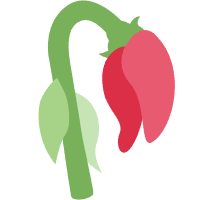
塔吉雅娜·托尔斯泰娅(Татьяна Толстая,1951— )出身于一个具有深厚文学传统的家族,其祖父是著名作家阿·托尔斯泰,外祖父是翻译家洛津斯基。作家从1983年开始发表作品,先后出版短篇小说集《在金色的台阶上……》(1987)、《黑夜》(2001)等,长篇小说《吉斯》(2000)获得2001年凯旋奖。托尔斯泰娅的作品一直受到俄罗斯评论界的关注,有关她创作的评论文章甚至超过了其作品的数量,同时,她也是最受西方欢迎的当代俄罗斯女性作家之一。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海伦娜·戈西罗在美国和俄罗斯分别出版了关于托尔斯泰娅创作的研究专著。
托尔斯泰娅的创作关注永恒的主题,她探讨的不是具体的现实生活背景下的人,而是更为广泛、抽象意义上的人,主人公的幻想和现实生活的差距则是作家诉诸最多的一个主题。托尔斯泰娅创作的诗学特征也一直为研究者所关注,她在作品中使用大量的现代派技巧,其创作具有比较醒目的实验色彩。近年来,托尔斯泰娅生活在美国,在多所大学教授文学写作等课程,她也写作政论文和随笔,2001年和2002年,俄罗斯波德科瓦出版社分别出版了她的随笔集《白日》和《葡萄干》。短篇小说《猎猛犸》(Охоmа на мамонmа)选自托尔斯泰娅短篇小说集《黑夜》(瓦格里乌斯出版社,2001年)。
原载于《世界文学》2005年第5期,责任编辑:李政文,孔霞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