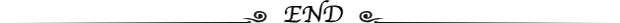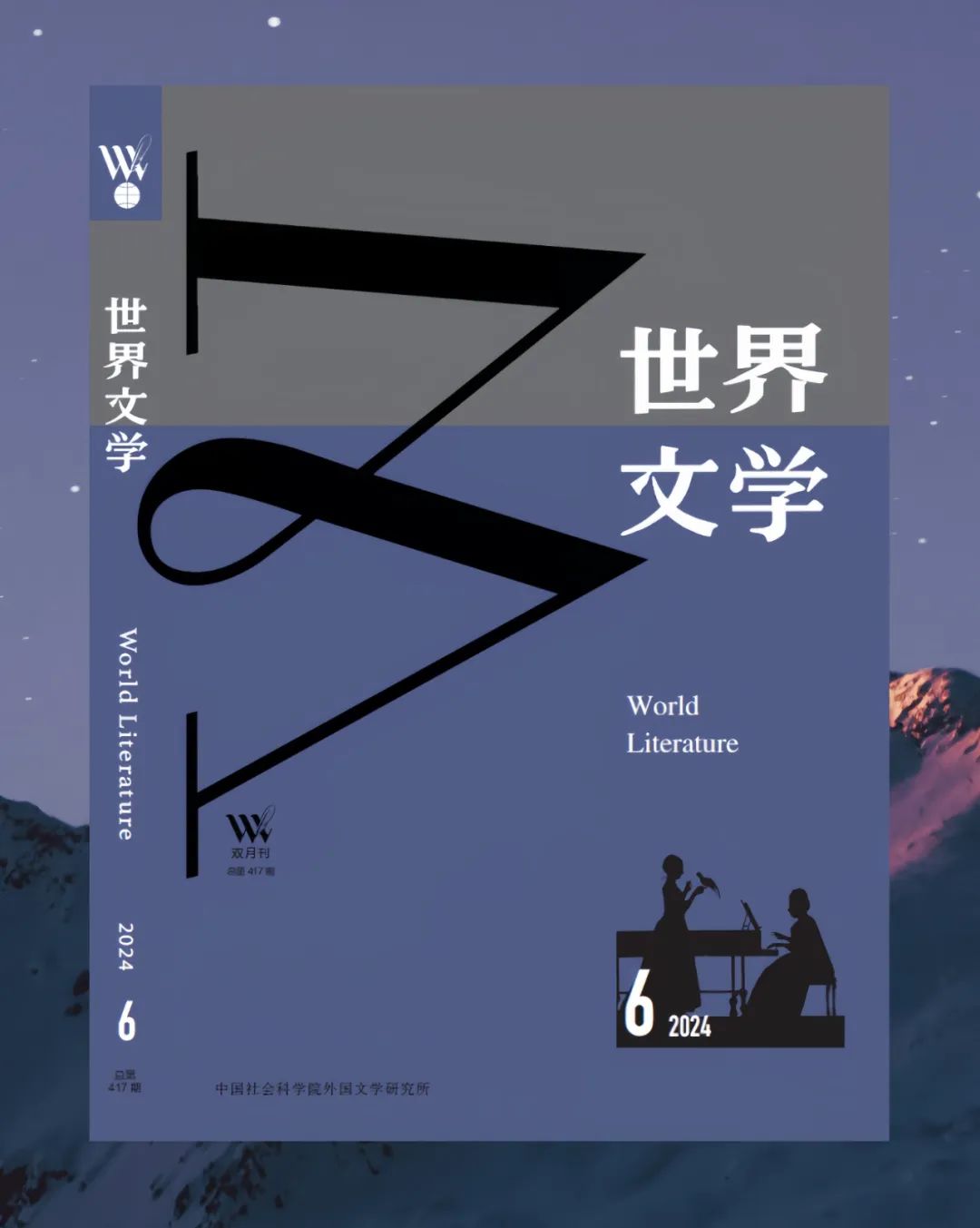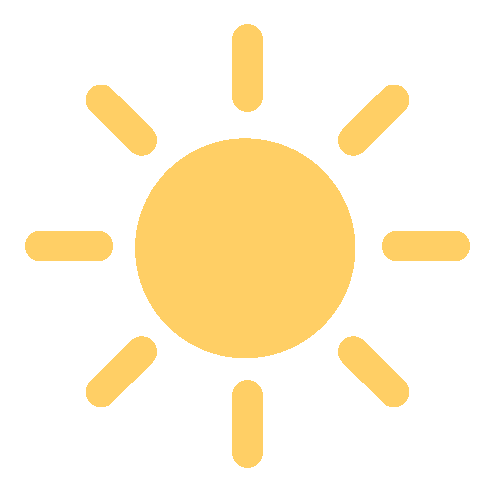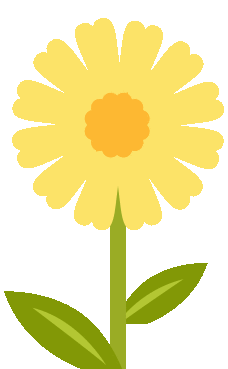小说欣赏 | 皮•莱克塞尔【意大利】:人们长时间不明白他是怎样逃走的……
![]()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人们长时间不明白他是怎样逃走的。提出过种种难以置信的假设。但是,没有人想到,这位山区建筑师在参加修复要塞工程时,曾想象并设计出只有他自己能使用的固定装置。他只不过巧妙地利用某些凸出的石头,沿要塞整个墙垣高度将它们建成一条通向湖边、攀登岩壁的栈道,实际上,这条栈道,除了他以外没有人能觉察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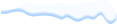
皮埃尔·莱克塞尔作 徐家顺译

这地方位于王国的边陲,四周雪山环抱,地势荒凉、险峻。一座古老、庄严的要塞耸立于巨大的峭壁之上,要塞的一部分悬垂于青中泛绿的湖面之上。要塞是用本地采集的巨石建成,气势雄伟;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暴君登基后,要塞曾于近期得到一次修复,外观作了一些与整体相匹配的调整。
早期,这阴森的庞然大物是用来监视边境省份及征收通行税的,改作囚禁政治犯的监狱已有将近百年的历史了。由未归化的众多移民挑起的内战结束后,刚刚建立起来的君主专制政体,希望让它最顽固的反对派就在这里悄悄地灭亡。在这些顽固派中间,有一些人遭到流放,另一些人顽强地转入地下。但是,也有一些务实派的人,他们竭力宣传温和的观点,企图改变事件的进程,他们的理性,跟失败的激进分子的狂热及当政政客的狭隘思想是水火不相容的。当然,这些温和派,较之被流放的人或转入地下活动的人,更易招致当局的恼怒。
因此,在十一月一个雾天的拂晓,霜雪给草地和稀有的针叶树撒上了一层白粉,将树梢覆盖住,王国警署的一架直升飞机停在要塞前面的空地上,从直升机中走出欧帕里诺·比奇,他是宣过誓的建筑师,他在风华正茂时,曾经主持过要塞的修复工程。
这人四十开外的年纪,身材瘦长、匀称,待人接物开朗、果断,面容光滑,没有皱纹,浅褐色的眼睛极富魅力。他等候办理入狱登记手续时,三名神情阴郁的小狱卒围在他身边打转,一阵阵刺骨的寒风吹乱了他浅褐色的短发。
他并不怵这地方的景色,也不觉得惊奇。他生于斯长于斯,对本地绵延的地势十分熟悉,这环境使他感到亲切,——可惜,失去了自由,他的人生价值得不到充分的发挥。他毕竟知道等待他的是何种命运。人们对福韦要塞的监禁条件颇有微词,但是有一点是公认的,监狱长手下的狱卒人数不多,——在这一点上,监狱长和他的上司是一致的,不肯为一些扫兴的人增加预算开支。这也是引导国家决策人加固要塞的最重要的理由,总之,这要塞要加固到固若金汤,难以逾越。尤其是——这是新近一项不怎么使人高兴的革新——牢房的地面及墙壁都覆盖上了铁皮,简直可以说是铺了一块铁皮毯子,光线是通过一种镜子游戏,从气窗间接地照射进来的,气窗上不仅有铁栅栏,而且每个狱室都是岔开着排列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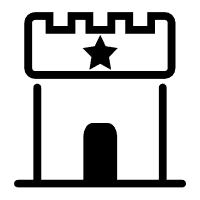


当欧帕里诺·比奇进入要塞里面,当他听见厚重的滑动钢门像爬行动物似地嘘嘘响,在身后紧闭上时,他不得不强迫自己不流露出此生此世与世隔绝的感受。
要塞司令塞雷纳跷着二郎腿,坐在厚实的栗木办公桌后面接待了来者;办公桌上的黑皮垫吸墨纸下面压着一份薄薄的公文,塞雷纳没有起身,只是心不在焉地——仿佛看破红尘似的——向来人提及监狱主要的规章制度,但愿用不着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因为他不是来消遣的,更不是为了让人打扰他的。
很快就又下起雪来了,很大的雪花,一阵紧似一阵。闪烁的白光笼罩住要塞,要塞的气氛像殡葬前夕地下墓室的气氛一样欢快。有时候,一间牢房或另一间牢房中发出的金属碰撞声暂时中断了沉闷的时间。衣服、寝具抵挡不住深夜的严寒。
欧帕里诺·比奇是一个善于随机应变的人,没有过多哀叹无常的命运。不然的话,卫生条件的缺乏,囚徒的混杂和拥挤,以及刑讯拷打,本来会是特别难以忍受的。相反,他却决定尽量地利用现有的条件,来读书、画画及写字,其间还不忘锻炼自己的身体,以备不时之需。
他获准查阅图书馆藏书的作者目录,他惊奇地发现目录中有不少怪异或不因循守旧的作家。在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追问下,一个狱卒喃喃低语说,那是要塞司令的千金小姐阿莱娅在负责挑选书目,管理卡片。比奇吃惊地问道:
“那么说,她是住在要塞里吗?”
“不,她只是利用假期来探望她父亲。”
比奇若有所思地在博尔赫斯和布扎蒂【迪·布扎蒂(1906-1972),意大利新闻记者及作家,其小说《鞑靼人的荒漠》发表于1940年】之间迟疑不决,随后,考虑到目前的处境,他自言自语地说,还是重读《鞑靼人的荒漠》吧。给他送书的同时也送来下一顿饭,里面附着一份清单,他得按相应的顺序在后续借阅人栏中填写自己的名字。他真想按从前的习惯一次借好几个作者的书。但这是不许可的。稍后,他发现虽说日光还算充足,但毕竟比较弱,不适于长时间阅读。他终止阅读,觉得诗兴大发,乃吟诗一首:


比奇重读了一遍,噘噘嘴;将诗抄录在记事本的一张纸上,塞进借阅单里。
严冬迅速占据大地的景色,万籁俱寂,对试图逃离福韦要塞的囚犯构成一道额外的天然屏障。白天日复一日单调地重复着。长夜——因为晚餐后就熄灯——使囚徒继续蜷缩成一团,向寒冷索要片刻惊醒的睡眠。圣诞节不知不觉地临近了。
十二月二十日,欧帕里诺·比奇在建筑物和城墙之间放风时,听见开门的声音,模糊地看见一个裹着衣服的妇女身影穿过内院。他猜想一定是阿莱娅,便琢磨起她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来了。
他等的时间不长就弄明白了。第二日,他受到召见,被带进图书馆。阿莱娅坐在里面打字。她向他点头,让他坐下,命令狱卒在外面等着。
“比奇先生,”她开门见山说,“我不仅了解您的档案,而且知道您寄给《荒原》杂志的诗,或者更准确地说,阅读了这诗使我查看您的档案。我从您的花招中能推断出什么?”
“可以推断出是投进海里的一只瓶子【“投进海水里的瓶子”是传递信息的意思】。”
“不错,可是在这里您希望得到什么?”
“只有希望奇迹,没有更好的,”比奇狡黠地撇嘴说。
她微微一笑,并不快乐,表情严肃而忧郁。她身材矮小,穿着朴素但颇为考究,看起来将近四十岁。她的褐发衬托出美丽的脸庞,她的面容使比奇回忆起女影星路易丝·布鲁克斯【路·布鲁克斯(1906-1985),美国女影星。】来。这位影星的头像曾经使他沉浸在幻想之中而不能自拔。
她接着说:
“我发现您挑选的书籍缺少趣味性。”
“要不是您恰如其分的选择,”比奇说,“那就越发没有趣味了。”
“您知道,我是文学教授……”
“我承认,这是知识的保证,不过,趣味和判断力并不总是相伴随行的。”
“也许吧……但是,咱们还是谈您的档案,虽然这不是我的专长。您的材料很少,解释不了您为何被投入大牢的,不是吗?”
“我想象不出我是怎样变成人民公敌的。”
“嗯,我们稍后再谈这件事。再见,建筑师先生。”
“我同意您的预言……对了,您在哪儿任教?”
“在图兰学院。”
“离这儿很远!可惜……您应该想办法来近一些的地方工作,为令尊大人着想,而且我会常去看您的。”


显然,阿莱娅对要塞司令有一定的影响力,第二天早晨,十二名相关的囚犯接到通知,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穿衣服,这命令于当晚前一直有效。
欧帕里诺·比奇穿上他来要塞时穿的那身衣服。那身衣服保暖、舒适、合身,凸现出他的长处。只有他那双山地高帮靴使他看起来像个乡巴佬。
他等着阿莱娅传唤他,他显得比平时激动,相反,是她在作例外的大巡视时,走进他的牢房。
“我只能给您和别人一样多的时间,”她承认说,“但是您要知道,由于您,我才做这样超越我图书管理员权限的事情。”
“我清楚地感觉到了,”比奇感动地回答说,“请听我说,夫人,这很重要:我越想我越觉得,图兰真的太遥远了。请仔细考虑。谢谢您所做的一切。啊,还有一件事:我刚刚重读《堡垒》,现在我需要另一本书,但是想请您挑选。”
午餐和这些规定协调一致,比较丰盛、可口。几乎与此同时,一个卫兵交给比奇他要的书;是皮埃尔·伯努瓦【皮埃尔·伯努瓦(1886-1962),法国小说家】的《阿克塞尔》。他记得书中的内容,中学毕业时曾痴迷于这本书。他备受感动,像以前一样,即席创作下面这首小诗,塞进清单中:


暮霭降临前,轮到他放风。像平常一样,他从站岗放哨卫兵门上的小窗口前经过,卫兵在隐蔽处漫不经心地监视着——由于城墙紧临万仞深渊而放松警惕。比奇像往常一样,在住处四周走了几步,伸伸胳膊,活动活动腿。接着他依循同一条路线,做柔软体操,直到消失在卫兵的视线中。
他向一个工具棚飞奔而去,他曾注意到那里寄存着几副滑雪板;他挑选了一副,放在几米远的地方,向一个小广场跑去,那里有一根旗杆,是准备举行升旗仪式用的;他用一块燧石片砍断滑动缆绳,急忙回来将所有东西放在墙角落里,再将滑雪板系在缆绳的一端。尽管寒气袭人,他却汗流浃背。他缓缓地从卫兵前面经过,故意作深呼吸,立刻再次消失在建筑物的拐角处。
他消失得无影无踪,以至于卫兵觉得规定时间过去得太长了,有一阵竟以为囚犯已经回牢房,他没有注意。然而,卫兵有点儿不安,应该为这难以置信的事情感到惋惜。只有衔接湖滨和边境方向的山峦雪地上两条平行的痕迹,悄悄证实着欧帕里诺·比奇的业绩。


人们长时间不明白他是怎样逃走的。提出过种种难以置信的假设。但是,没有人想到,这位山区建筑师在参加修复要塞工程时,曾想象并设计出只有他自己能使用的固定装置。他只不过巧妙地利用某些凸出的石头,沿要塞整个墙垣高度将它们建成一条通向湖边、攀登岩壁的栈道,实际上,这条栈道,除了他以外没有人能觉察出来。
他借助于系在他腰上的、升旗用的绳子,向上攀援,然后向下滑行到城墙的另一边,而他的毛衣、滑雪衣没有打湿,滑雪板没有结冰,他能在到达湖面后迅速逃离现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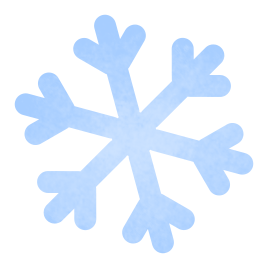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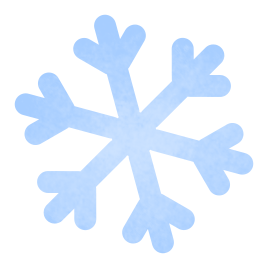
皮埃尔·莱克塞尔(Pierre Lexert,1923-2015)出生于巴黎,但故乡在意大利的瓦尔多特,他后来也一直在那里生活。莱克塞尔小学起就开始写诗歌,其创作十分多样化,写诗歌、小说、评论、专栏文章。发表的作品有诗歌《长途跋涉的心》(1979),《如此俄耳甫斯》(1983),《情感启蒙》(1984)等。1992年获得法语诗歌银茉莉花奖,1996年获得由法兰西学士院颁发的“光大法兰西语言文学”大奖。他被评论界认为是一个比较怪的作家,他的作品用法语写作,却体现了浓厚的意大利故乡气息。
原载于《世界文学》2006年第4期,责任编辑:余中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