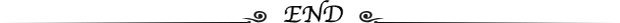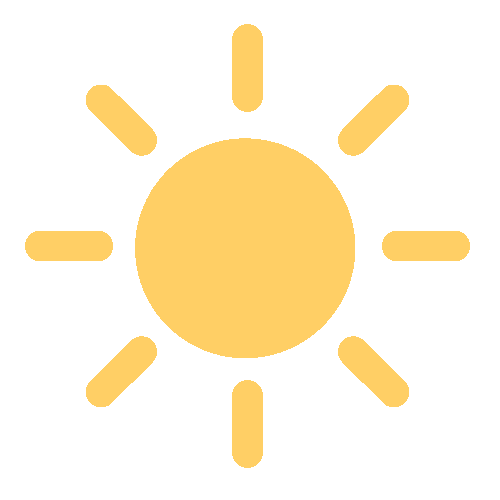小说欣赏 | 乔•哈拉【美国】:遗 赠
![]()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一位论派信众马上招标修缮钟楼,这钟楼是该加固了。在技术要求文件里,他们添了一句话:高度增加两英尺。三位一体派信众目睹大街的另一边竖起脚手架,他们把钱搁在银行里等着,看你的钟楼升到多高。

乔治·哈拉作 邓大任译
佛蒙特州维特尼角镇的《知事报》刊登了一则短短的律师启事:“兹定于星期六下午二时整在艺术大堂由理查德·伯杰律师宣读格斯·希尔和萨拉·希尔的遗嘱,敬请公众光临。”维镇大多数居民都感到诧异:希尔夫妇的遗产怎么会跟咱们相干?
好奇乃人之天性,况且十一月大冷天也没多少别的事儿可做,倒也来了一百人。拖椅子,唠家常,安静下来之后,伯杰律师没有像以往那样先抛一通法律词语,而是一下子步入正题,宣读遗嘱:“我俩特留赠维特尼角镇诸街坊友好二十万美元,其用途由多数人意见决定。”
这短短一句话的含义,正如殡葬工威利·琼斯所言,实在让人摸不着头脑。这么多钱,该怎么花:用来支持希尔夫妇钟爱的事业?创建一个基金会?投资以防不时之需?经过两小时辩论,维镇唯一的眼镜商戴夫·里甘说:“花掉二十万美元本来不成问题,现在倒好像成问题了。”



格斯·希尔眼看就要过一百岁生日了,却辞世而去。镇上好些人揣测,他离开人间与其说是身体的必然,不如说是自己的意志。理发师迪克对他的顾客就是这样说的:老头儿兴许听到了要给他开一百岁生日派对的风声,怎样逃过那个派对,他想得出来最保险的一招就是这么干。
一星期之后,萨拉·希尔那辆一九八八年的本田思域,在峭壁旅馆附近“雨天路滑”的牌子旁边飞下了山崖。这次事故,谁都不觉得意外,因为萨拉开车的冲劲儿是出了名的,尽管已经九十四岁了。
萨拉不幸死于非命,格斯看来寿终正寝,两桩事儿在时间上几乎重合,这叫维镇人真是服了上帝。平时大伙儿老这么说:要是上帝不设法在同一时间把老两口儿带走,那就不好了。如今,镇上多数人都认为,上帝做得够可以了。
格斯的葬礼在白色木结构的教堂举行,那是一所一位论普救会【一位论派和普救派是基督教中的两个派别,都认为上帝只有一位,否认基督神性和三位一体教义,与下文“三位一体派公理会”的教义相悖】教堂,在昂尼亚特街上。凌晨五点,那四十英尺高的钟楼就敲响了丧钟;在这个非常规钟点敲钟,为的是尊重格斯生前早起的习惯。一星期之后,在昂尼亚特街的另一侧,白色木结构的三位一体派公理会教堂那四十一英尺高的钟楼也响起了钟声,宣告萨拉的葬礼开始,敲钟的时间比较照顾大家,是上午十一点。
维镇共有居民四百七十二人,两个葬礼都约有一半人出席,虽然此一半并非彼一半。镇上人人都认识他俩,因为他们打结婚起就一直住在那儿,都六十六年了。可是,对于他俩,人们总是明显地有所偏向,有的偏向他,有的偏向她;有的偏向他这一点,有的偏向她那一点——比方说:格斯从不与人干仗,工作习惯与众不同;萨拉坚决奉行素食主义,热心公众事务。
可是,似乎没有谁对其中哪一位是毫无保留,倾心景仰的,更别说有谁对两个人都处处心悦诚服了。用九形人格【一种性格分析方法。把一至九围成一个圆圈,每一个号码,代表着一种性格】的术语说(萨拉本人就经常这样说),她是彻头彻尾的完美主义者和积极分子,对己严对人更严。而在圆圈的另一面,格斯总在观察事态,做事缓慢沉稳,简直没见过这么倔强的人。按理,两人本该头一回见面就吹掉;可是,年复一年,个性强烈倒把他俩扭合在了一起。镇上不止一对出了问题的夫妻说:“连他们都能坚持到底,咱们也行。”
大多数人都没注意这个事实:格斯和萨拉是分别住在那栋长长的农场房子两头的,每天只有正儿八经吃饭的时候才走到一块儿。偶尔有些晚上,他们会一起坐在客厅里听短波,但总是回各自的房间睡觉,这样就听不到对方打鼾了。
两个葬礼都出席的人没有几个,伯杰律师是其中的一位,他是以职业身份出席的。萨拉说过,他俩都“没兴趣和金钱打交道”,所以老两口儿委托伯杰管理财务。在维镇陵园,伯杰看着格斯给放进最后栖息之地;一星期后,伯杰又看着萨拉挤到丈夫那里,跟他头对头——因为格斯的亲戚们早在她之前就把旁边的宝地占据了。
也许是伯杰在维镇才住了十八年的缘故吧,他是怀着一种期待的心情前来宣读遗嘱的。律师能带来好消息,这可不是常有的事儿。他原以为,镇上的便民项目欠账太多,大家会一五一十说出一长串儿——马上想到的就有:美化公众绿地,或者扩大图书馆。
可是,发言者提出的头一个问题就不对劲儿。“我想问——我就是想问问,” 威尔·马奥尼大声说出他的想法:“只要多数人投票赞成,就可以按人头把钱平分,——是不是这样?”
“这由你们决定,”伯杰说。钱用得是否恰当,不该由他裁判。
“那每个人到底能分到多少钱?”
律师拿出计算器敲了几个数字。“四舍五入,男人、女人和小孩每人大约四百三十美元。”
大堂里响起了几声口哨。“这钱够我买一台新冰箱了,”安妮·克莱因说。“可是这不大公平,”萨姆·加什反驳,“谁家人多,分的钱就多。”
维镇数亨尼曼家里人最多——爷爷、奶奶、老婆、妹妹、五个娃儿,加上他自己——十口人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很容易就算出他有资格得到四千三百美元。亨尼曼站了起来。“要说分钱,我得的最多。可是我认为,这样做与格斯和萨拉留钱给咱们的原意不符。”
他坐下了,没有展开细说。这叫罗杰·多恩斯不得不问:“这钱咋花,他们干吗不给咱们说个清楚?”
“赠与又附带条件,那不是他们的做法,”伯杰说。他以大家现在坐着的大堂为例——修建这大堂,格斯夫妇出了一半钱,可他们就是不让大堂以他们的名字命名,也不对大堂的设计发表意见。
这例子太能说明他们的善心了,大家纷纷点头。可是,罗杰想起来,萨拉在卡弗那边的地区中学教了三十年书,她早就给那中学捐过一万美元,那会儿她倒是说得一清二楚,钱必须用在哪些地方(艺术用品,戏剧编演,来访作家),绝不允许用在哪些地方(运动会,电脑,行政开支)。消防员沃尔特·佩恩说,那一次,规定条件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学校能否作出正确抉择,实在说不准。“格斯和萨拉信任咱们,”他说,“所以我认为,只要咱们以他们的生活方式为指南,就不会辜负他们的好意。”


正好在夜幕降临之前休会了。显然,这份意外的大礼,怎样处理才得当,大伙儿还需要再想想。
过了一个星期,艺术大堂坐进了二百多人。经过反思,伯杰认识到让大家先在旁厅“交流一小时”可能不怎么好。镇上原先见面只是客客气气点点头的人,竟然打得火热,一起品尝着罗恩·博伊德做的鲜榨苹果汁。不止一次,声音大起来,原来是某个人对格斯和萨拉的生活方式作出某种解释,别的人又不同意。所以,当伯杰提早结束“交流一小时”时,大伙儿都舒了一口气。
大堂里自然泾渭分明:萨拉的朋友坐在左侧,格斯的朋友坐在右侧。伯杰把麦克风架在中间过道上,马上就有十二个人排队。维镇数丹尼尔·兰福德年纪最大,何况他一次也站不了几分钟,所以让他头一个说。他的发言是这样开始的:“我认识萨拉和格斯差不多五十年了。”他在语法方面给大家树了样板,此后,谁都不愿意带头用过去时态提到他俩。
发言者对老两口的哪一位忠贞不二,从他先提到谁就立见分明。挺奇怪的,说格斯好话的似乎女人居多。林恩·培根回想起格斯由于着着实实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利文沃斯惨受牢狱之苦,她提议以他的名义建立一个和平正义中心。
几位退役老兵对这个竟然拒绝为国家服务的男人大摇其头。莱尔提醒大家注意,萨拉在那场战争中是志愿当护士的,她还是民主的勇猛卫士。萨拉在当地建立了妇女选民大联盟支部,到了选举日就在大街上巡视,询问人们投票没有,如果还没有,打算什么时候投票。
珍妮特·汉弗莱是这个大联盟的前主席,她建议把一部分钱用于选民教育。可是查理·阿普特想起格斯说过,一九一六年伍德罗·威尔逊那个竞选口号“威尔逊使我们无须打仗”,一直让他有被出卖的感觉,从此他再也不参加投票。
安娜·塞潘尼安问:山岩农场现在境况怎样?人们上哪儿去了解格斯和萨拉的想法?到过那栋农场房子做客的人,大都只呆几个钟头,不过也有人整个作物生长季节都留在那儿的。去过的人一定注意那两本书——一本是格斯的自传,题为《痛楚之忆》;另一本是萨拉对现代教育的无情抨击,取名《烂透了的学校》。
安娜还说,得想想那些动物。方圆二十英里,凡发现流浪动物,总是送到希尔夫妇那里。他们收容过脾气坏透的美洲驼,垂垂老矣的猎兔狗,还收容过一头爪子给捕笼夹得血肉模糊的郊狼,一只三条腿的狐狸,另有数不清的猫狗。有时候,流浪者是离家出走的十几岁小孩,那是希尔夫妇最难安抚、最难让他们重返家园的“动物”。人称希尔夫妇为“救星”,他们自己却不这么认为;萨拉说过,大部分动物都能自救,只要你能帮助它们脱离险境。
三位一体派教堂的朔恩弗斯牧师在艺术大堂左侧接着发言,他不用麦克风,以深沉的男中音说道,希尔夫妇留下的山岩农场是绝对尊重一切生灵的。这时,木匠戴夫·弗里德一边嚷着对不起一边打断他的话,因为牧师大人说的不完全是事实。他记得刚过去的那个夏天,有一只家麻雀入侵萨拉的蓝色鸣鸟的笼子,他亲眼看到萨拉用手指头戳那家麻雀,要不是他自己仗义阻拦,小鸟儿恐怕要一命呜呼了。
有人大声问道:在那种情况下,格斯会怎样做?普遍的看法是:他会让家麻雀就住在那里,而给蓝色鸣鸟另造一个家。
理发师迪克提议创建一个基金会,就叫“为了更好的明天基金会”。这事儿多数人都感到有点不着边际。乔·沃伦指出,格斯并不相信明天,他认同希腊人的观点:事情要么现在发生,要么现在不发生——不必理会过去和将来。他从不安排会客日程,客人要来,让他们来就是,只要他不是忙着,就跟他们见面。不过,多半时候他都挺忙,因为凡事他都照老规矩办,比如牧场要用手清理;锯倒了一棵树,要把枝条分理得清清楚楚——树干用作柴火,大枝用作支杆或篱笆桩儿,小枝用作豆苗架,反正啥玩意儿都不会扔掉。
格斯和萨拉是无法到会了,整个下午,朋友们一直在回忆他俩的言论,试着构建他俩的完整的信仰体系。有人建议把二十万美元捐给镇里,别的人就顶回去,因为格斯说过:“不是自己亲手挣的钱,千万别沾边儿。”“可是,他俩晚年是靠投资过活的呀,”又有人这样反驳。甚至萨拉终生食素也受到马奥尼乳品店老板娘吉尔(她是威尔·马奥尼的老婆)质疑。她说:萨拉每月一次订购几加仑尼奥牌冰淇淋,要求送货到家。对这种说法,大堂里拥戴萨拉一侧的反应是:不相信。不过,朔恩弗斯牧师承认,萨拉曾经私下对他说过:如果生活能够重头再来,她会爬更多山,吃更多冰淇淋。
大约四点钟,成年人该说的都说了,艾琳·鲁滨逊的小姑娘莱拉站起来,说起那一天希尔太太瞅见她在红磨坊路摘野花。“她指着我摘花的地方说,这样就没有漂亮东西给别人看了。她说,自私的女孩才摘花儿。”
萨拉的朋友们都欢呼起来,这事儿说明她真是诲人不倦,说明她的主张是:养育孩子要靠整个村落。掌声平静下来之后,技工唐·史密斯(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萨拉那辆思域老爷车保养得能奔能跑)说得声音有点偏大:“那没好脸色看的老太婆干吗不让小姑娘摘花?”
这话儿就像一缕臭烟味儿荡漾在空气里。这样的侮辱,让萨拉的牙医詹妮·舒曼无法不还击。“没好脸色看?”她边站起来边问。“你要是想没好脸色看,甭看别的,就看格斯·希尔好了。那家伙一辈子笑过吗?”
唐用袖管儿擦了擦嘴巴,这是他老婆教他说话不至于太冲的方法。他把手挪开之后说道:“我要是讨了那娘们儿做老婆,也笑不出来。”
詹妮一下子冲到中间过道,把手中的冰水当头朝唐泼去。他一跳逃出座位,把麦克风撞翻在地,“嘣”的一声,吓得叫小姑娘莱拉把一杯果汁掉到地上,棕色的斑痕渗入艺术大堂白色的新地毯,大伙儿都挤到中央看个究竟。
“这成何体统?”朔恩弗斯牧师从椅子上站起来说,“说粗话?动手?钱把咱们弄成啥样啦?”
牧师大人经常以这样的问句说话,这叫一位论派信众大为光火,他们觉得牧师就要坦率地说出看法,别在正题旁边跳来跳去。“牧师,你给咱坐下,”这喊声来自大堂里格斯的一侧,“星期六咱们不需要讲道。”一个纸飞机从后排座位飞出,“啪”地一声击中牧师大人的胸膛。
一张张脸儿气得通红,几只拳头挥向空中,理查德·伯杰急忙宣布休会。


接下来的几星期,维镇仅有的那位律师在街上给人拦住好几次,问他什么时候再开会,那笔钱的事儿给搞得乱糟糟的,得理理顺。他说,不再开会了。他是遗嘱执行人,他会拿出解决办法,再告诉大伙儿一声。他在维镇《知事报》上公布了他的决定:十万美元给格斯的一位论派信众,十万美元给萨拉的三位一体派信众,信众认为该怎样用就怎样用。
一位论派信众马上招标修缮钟楼,这钟楼是该加固了。在技术要求文件里,他们添了一句话:高度增加两英尺。三位一体派信众目睹大街的另一边竖起脚手架,他们把钱搁在银行里等着,看你的钟楼升到多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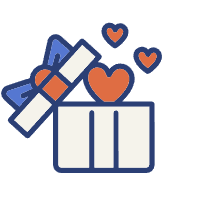

乔治·哈拉(George Harrar,1949— ),美国当代小说家。他的小说侧重生活感悟,朴实含蓄,从不哗众取宠。近几年,他创作了多部长篇和若干短篇小说。其中,《五点二十二分》(The 5:22)被选入《1999年美国最佳短篇小说集》,《世界文学》2001年第3期曾刊载过该小说的译文。本期的《遗赠》(In Memoriam)发表在1998年1月的《美国行》(American Way)上,故事虽然平凡,却耐人寻味。

原载于《世界文学》2006年第5期,责任编辑:乔修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