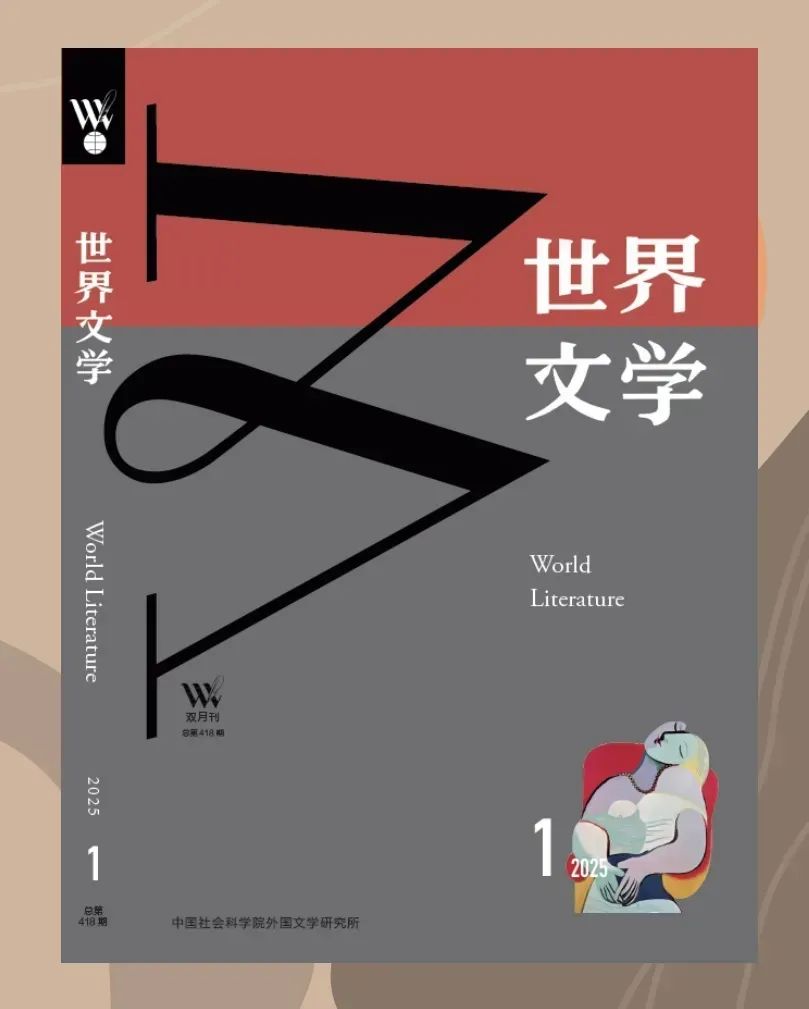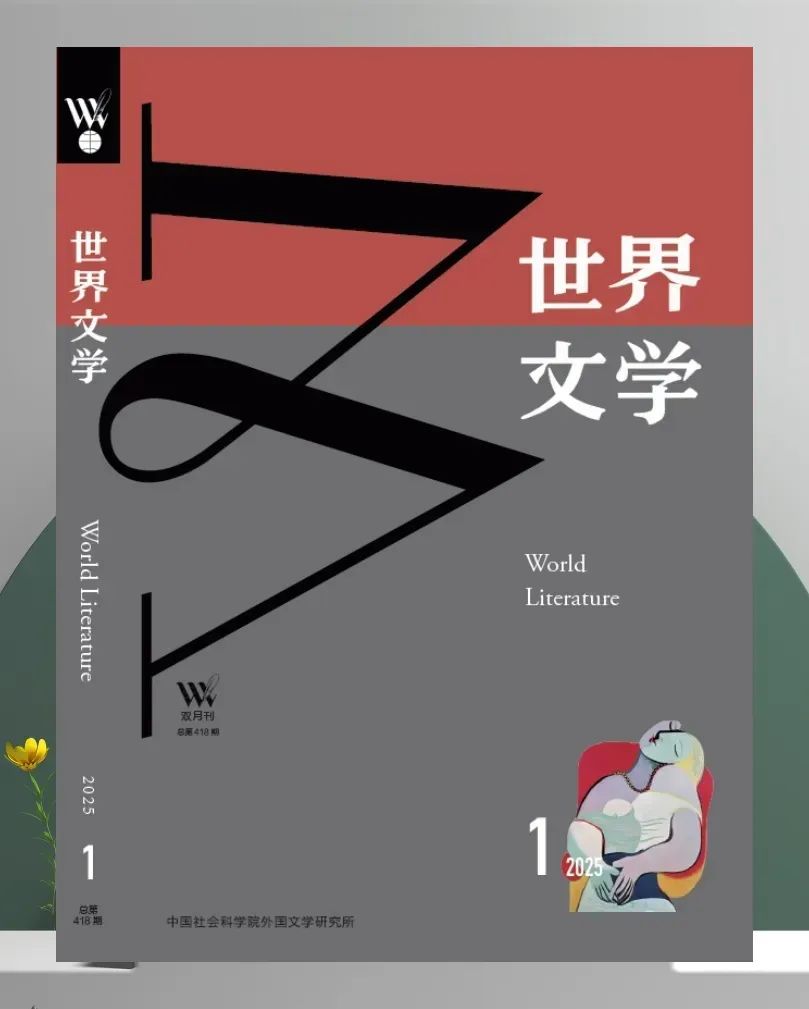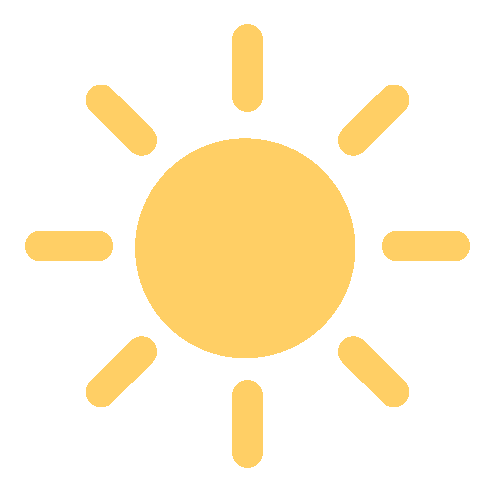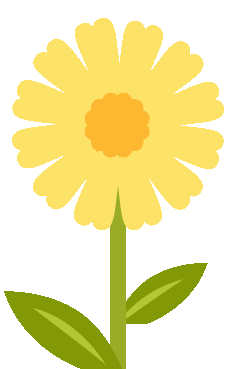第一读者 | 恩•内班【瓜德罗普】:大河之女
![]()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大河之女

恩内斯特·贝班作 何润哲译
在这个大河边的村庄里,大家都认识克安——一个似乎集齐了世间所有厄运的男人。克安是个孤儿,年幼时,有一天河神心情不爽,用一条独木舟夺走了他父母的性命。祖母把克安带大,却不喜欢他,因为孩子长得太像妈妈。祖母从未接受过儿媳,认定她就是儿子意外身亡的肇因。难道不是她吵着嚷着一定要冒险去划船吗?那时,暴风雨明明正在蓄力,危险一望便知。就这样,克安度过了“讨债鬼”的童年,众人也把他看作可以欺凌的受气包。学校的长凳,他从未坐上去过。尽管生在法属圭亚那,他的舌头却几乎讲不来法语。虱子在他脑袋上建起乐园。皮肤上长满丘疹,疤痕累累,因为瘙痒受尽折磨。鼻子里总是堵着各种陈年的感冒伤风。更不要说种种头昏脑涨,想必都是林中鬼神对他的戏耍。雷石【当地人相信雷击会催生特异的石头,从天而降。这种石头被称为雷石】将一株马里帕棕榈【一种高大的棕榈树,叶长可达10米。——原注】齐根斩断,刚好挡在他人生的必经之路上。或许,这一切不过是早逝的双亲在叫这个不该出生的孩子付出代价罢了。他的母亲曾试过打胎——森林里的草木本有这个用途。几片树皮、几段树根、几个花蕾,再加上虔心的祈祷,解决了多少麻烦事!可是,哎呀呀,克安的命实在太硬!当初投胎的时候一定有好心的守护神看顾。然而,一朝来到世间,他却是给老弱病残增添运势的。克安是个瘸子!他的一条腿有点跛,走起路来一瘸一拐,但他还是长大成人了,如今已是一个三十岁的男子。三十年经受的挫败、嘲讽和恶意让他成了一个孤僻的人。唯有当他凿木做舟时,才有些许不同。没人比得上他的手艺,那两下子堵上了不少好嚼舌根的嘴巴。克安做出来的独木舟,真叫人叹为观止。他懂得如何选择木材,也知晓月相的吉凶。他凿刻木头的灵巧堪比艺术家,使用火焰的纯熟又如同非洲先祖。独木舟大功告成之时,没有人不对他产生敬意,就连河流都对他表示感谢。有些人为此嫉妒他。还有些人声称这一切都不合常理,定有林中鬼神在暗中助力。风言风语不止,人们喋喋不休。而克安只把闲话当落叶,任其腐烂。他已经习惯于忍耐,学会了用闭目塞听来保护自己。让他们说去好了!就凭这点恶意,还不足以把他怎么样。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女人们日日洗濯旧衣。男人们则和全天下的男人一样,假装扮演着男人的角色。森林耸耸肩,摇摇头,将夜曲寄予清风,滋养着木猪【木猪是西猯的一个亚种,体型较大,毛发均匀呈深色。木猪常常成群结队出现,是加勒比海地区原住民神话的重要组成部分】、长蛇、刺鼠、树懒、西、牝鹿、蚂蚁、蠕虫、蝴蝶和其他种种争奇斗怪的造物。在克安眼中——别人并不了解——森林是世间最大的工厂。生与死在不可见之物的注视下肆意嬉戏,克安的父母也在观者之列。对他而言,森林无异于一本大书,每一页他都已学会解读。地狱或天堂,全取决于心灵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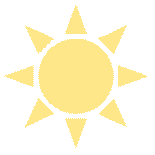
说到心灵,克安从未尝过爱的滋味。他的身边有不少适龄的美人,但她们都对他不屑一顾。谁会想要一个装着厄运的口袋呢?更别提还有林中鬼神在操纵他的双手?谁会乐意?有段时间,克安考虑过莫阿芒芒。看她经过时,他的心敲得像节日的大鼓。她搅动他的血液,直到他头晕目眩。浮想联翩时,他简直想去死,但不知如何诉之于口。这样一位上过学,去过城里夜总会的年轻姑娘,如何向她开口?她看上去早已不属于这个村庄了。说不定,已经有白人在她的耳边说过甜言蜜语了!说不准呢!
她站立时宛如一柄战士的长矛——质地是高贵的黑木——身体的线条一气呵成,如同一道倏然划过的蓝光。而她走起来的样子,则像一只飞轮,一辆上过油的滑车,轻盈得如同微风拂过手中翩然起舞的树叶。克安对她的感觉就是这样。他幻想着把她刻成一只爱的独木舟。但他最爱的,还是那一对在明眸的光芒中垂下的眼睑,仿佛一对因激动而忽闪的蝶翅。然而,她极少透过表情展露内心世界。她的脸简直是一张运到圭亚那大地上(并在这里有了生命!)的面具——可以追溯到奴隶贸易时期。在这面具之下,是鲜活的血液,她的皮肤因而透出缎子般的光泽,现出星苹果【指金星果,又名牛奶果】的颜色。而她的双唇平静地饮下空气,又在一阵率真的笑声中呼出,让话语听来仿若潺潺清溪。
二人得以亲近,是因为莫阿芒芒要给学校做一个关于制造独木舟的报告。她第一次意识到,原来自己从没有试着理解过周遭的世界。浸淫其中太久,总觉得一切都天经地义。她观察和学习,如呼吸般自然,却从未深究过,也从未寻找过意义。
克安成了完美的启蒙者。如果没有河,独木舟算什么?如果没有独木舟,河算什么?如果没有鬼神相助,人又算什么?克安,作为男人,就是这样说话的。和他在一起,树不仅仅是树,还是种子的记忆,是玛隆们【奴隶制废除前反抗或逃离种植园的黑奴或获得自由的奴隶的后代。——原注】的历史。树木就好比我们的图腾兄弟,由阳光、雨露和月光孕育,吸收那隐形的、浸润在祖先心中和土地里的爱。一棵大树又好比一所学校,传授着树干的耐心、树根的不屈和上上下下的团结一心。大树也传授着阳光的博爱,阴翳的安宁,生命的慷慨,枝叶的夜间秘语。克安,作为男人,就是这样娓娓道来的。莫阿芒芒则像盲人一般,跌跌撞撞走进这片新知。她明白此科学不同于彼科学,也知道人可以用学校之外的眼睛去看,更了解了人不可貌相的道理。对于那些愿意深入的人,他是语词的泉源,知识的宝库,或许也是梦想的箭矢。克安像对待圣物一般对待那些树干,伸出手指,带着敬意摩挲它们粗糙的外皮,爱抚它们光滑的表面,探知苞芽的孕育,阅读蚂蚁和猿猴留下的痕迹,推测木材的年纪,估算吃水线的位置。莫阿芒芒听得入神,大开眼界。就在她要为克安升起一颗桃心时,一个意外事件发生了。
“怀上了?”
“是啊,怀了!”
“是谁的?”
“母鸡猛刨地,收成准没跑!还用问?你忘了那个和她咬耳朵的白人了?”
“你是说……”
“就是他!”
“真他妈离谱!”
“那个年轻教师!”
“他喜欢黑女人?”
“他就喜欢莫阿芒芒!”
“就这样了?”
“就这样了!”
莫阿芒芒想过“流”掉孩子。她问询了克安的意见。尽管内心痛苦异常,克安还是建议她留下自己的果实。毕竟,他本人也曾因类似的缘故深受其害。后来,两个人一直没有什么进展,就分开了,莫阿芒芒走了。
生活没有时间为哪个人停步。生活继续前行,一路撒播火种和灰烬、泪水和欢笑。村庄里的日子一如既往。妇女们负责日常起居、浣洗、烹煮木薯、在夜里叫喊、照料伤者、看顾幼儿、失血、斗争,只为了让自己活下去,也让别人活下去。而男人们伐木,燃木,刻木,再把木桩推入河中,或将凿好的木头拉到港口(是的,木可成舟),敲击木头(是的,木可成骨),劈开暗夜中的木头(是的,女人也是木头)。当然会有死亡!当然会有节庆!而克安在那条跛了的腿之外,还拖着一段没有解药的单相思。莫阿芒芒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男人却一天天消瘦下去。脑袋里烦恼太多,夜不能寐!他回看自己过去的三十年,从未尝过温柔体贴或抚慰的滋味。他偷偷哭泣,在人前假装活着。
也是从这时开始,他开始整日整日望着河水。人们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吧,这条大河就是让人叹为观止。它仿佛一条正在打盹的巨蟒,不知醒来后会吞下什么。有时,河流绷紧浑身的肌肉,仿佛一头蓄势待发的愤怒水牛。河水翻搅,涌出泡沫般的文字,搅动记忆,撼动怒火。但克安看到的不止这些。他看到圭亚那和当地的水患,看到人们口中汹涌的话语。他看到亚马孙流域层层落叶下与时光一起被埋葬的命运,重重叠叠仿佛金字塔一般。他看见整个美洲的语言在尚未完工的巴别塔里推推搡搡。他听见苦难,听见清贫的孤独,听见冒险家的呐喊和淘金者的合唱。他一直追溯到非洲,在心底为那庇佑逃亡黑奴的神灵永留一席之地。他向风讲述自己人的抵抗:永远在打游击战,永远与所有生命站在一起,永远生机勃勃——尽管挫折不断,战火纷飞,身份不断改变,新的宗教接二连三出现。在这段漫长的、几乎是催眠般的梦游结束后,他回到河边,又看到了莫阿芒芒的脸,完美得如同神亲手雕刻的头像。
莫阿芒芒划着小舟,驶向她的白人。听过这许多流言蜚语,飞短流长,岁月终究改变了她。终究还是变了!



人们说:“如今她说起克里奥尔语好像嘴里有石子儿,她用母语唱歌也不如从前动听了。”
人们说:“她现在觉得鼓声很吵!”
人们说:“她舞跳得和她的白人男友一样僵硬!”
人们说:“她想用漂白剂洗掉自己皮肤的颜色哩!”
人们说:“她的梦想在巴黎……”
人们说这,人们说那,但克安无法对这些传言照单全收。他的心在守望,他对大河说:“大河啊,父亲!告诉我这不是真的!就算月亮变成黑色,一个博尼人【博尼人是法属圭亚那的布希纳格人(字面意思是“森林中的黑人”)的别称,是17世纪和18世纪逃离荷兰种植园的非洲奴隶的后裔。博尼之称来自其第一任首领博尼·奥克里弗的名字】也还是博尼人。我们延续了这么多世纪。我们承载了这么多信仰。我们遭受过这么多拒绝。我们创造过时光,也摧毁过时光。而今天(看上去!),人类的孩子已经变样了!大河啊,父亲,你想过要变成一根棍子吗?凯门鳄想变成猴子吗?”
河水在阳光下流淌,继续着没有行囊的游牧。大河嗅闻两岸的气息,想起自己在非洲的表亲,以回忆磨砺语言,像一柄弯刀般斩断光线,继续按自身之道行事,追随那滋养文明的理想。晚风从大河的背脊上吹过,像孩子一样欢笑着。只有独木舟知道大河的秘密。若天空要做出友好的表示,就会下起稠密的白雨。而克安也知道,在另一头,大河会呕出泥水,将海染成褐色。
大河没有回答。对于莫阿芒芒,大河没有什么义务。大河洗净她的镜子,是为了看清楚自己的脸。它没有时间回答男人的问题,也没有时间听树木哀泣。大河不愿意。莫阿芒芒远在天边!说这个做什么?每个生命都要照管自己的尘埃……可是,看到克安这样死心眼,人这么憔悴,大河还是带着通情达理的倾听之心,去圣洛朗【法属圭亚那第二大城市,位于马罗尼河畔】看了一眼。毕竟,助人是大河的天职!
如果说圣洛朗在世界的尽头,也不算错。然而,它却成了一个十字路口般的城市,不同的族群和各异的时代在这里碰撞。或许它是一座边境之城,但河流是不懂得何谓边境的。街上是深浅不一的皮肤、五颜六色的房屋和不同色调的季节穿搭,一片斑驳。道路不过是静止的河流,尽管有些自负,它还是温驯地为人类提供了便利——或原地打转,或直角相交。车水马龙在它身上留下道道深痕,它恨不能让河流分担些重负。


在圣洛朗,博尼人能将自己的影子照亮。大嗓门的巴西人是黄金和红辣椒的颜色。圭亚那人则个个沾亲带故,眼睛总像战士一样警惕。淘金者。贩子。正直的人。漫游的欧洲客。美洲最早的原住民,受到威胁的迹象。商人。阔佬。流浪汉。他们被同样的热量撼动,用激情填满白昼,用狂热占据黑夜。在这永远有待征服的生活中,女人们发出五颜六色的光芒。克里奥尔女人,大多是家中的顶梁柱。博尼女人是蓝色的火焰,久远传说般神秘。她们敏锐的目光仿佛来自世界的另一端,却也懂得爱抚沉默。欧洲女人则有着淡茶色的身体,来到这里既欣喜若狂又牢骚满腹。她们在阳光的恩典下感到自由,满心想着尝试更多的可能。巴西女人,男人眼中的玫瑰色宠儿,总在寻找生命的黄金。她们的爱如此强烈,让每个夜晚都惊心动魄。还有其他来自世界各地的女人,像一片片生机勃勃的叶子,足够健壮,足够坚韧。
这一切,大河早就见过、听过。大河听见种种语言之间的摩擦:陌生的,熟悉的,默契的,疏远的,每一种都急着诉说自己的底细,好以心换心。还有那些从中国来的,总被无礼地叫做“中国佬”的家伙,他们的商店里总能找到救急的玩意儿。还有一些据说有暴力倾向的人,被戴上手铐驱逐出境。不论是在母国还是在这里,大家都是无名小卒。别忘了海地的男男女女,他们一波波涌来,像是在为未来积蓄能量。
大河知道,城市中看不到命运的图像。大河也有诺言尚待履行,故乡也在等待属于自己的时刻。大河知道,自己不是大自然的地狱,没有遭到诅咒,更没有失去箭矢。大河不是野兽的园游会,也不会永远绿意盎然。
调查结束,大河再次出发。莫阿芒芒并不是人们所说的那样。她什么都没有忘记,什么都没有否认,什么都没有丢弃。她只是敞开心扉接受圭亚那奉上的一切。她成了一个大河之女。一个有着千才万艺的圭亚那女人。大树挺立在她的文化里,树叶在他者的风中沙沙作响。
克安听完了这段报告,没说什么。那是一段悲伤的日子。一天,他突然懂了。脑袋下面升起一缕轻烟。几不可见。
莫阿芒芒迁移了她的身体,而不是她的文化。在飞机的翅翼间,她还在迁移。她发现了星罗棋布的岛屿,得知逃亡黑奴曾在那里筑巢,如今已无人记得。她游历了巴黎,得出结论说没有什么能比得上森林的大教堂和太阳的祭坛。游历世界的她如今归来,手中握着一本厚如圣经的书,送给克安。他并不识字,只能读懂天空的征兆、树叶的传说和大河潮湿的书写。于是克安把书带给了长者。长者为他揭开了这些晦涩图画的秘密。他说,书中写的是“大河子民的历史”。这便是她的博士学位论文了。我们已是不朽之身。
没有人明白,一位知名大学的教授——在白发苍苍却依旧风姿绰约的年纪——为何会出人意料地来到克安的小屋。“绕了点路,但我还是来了。”她对他说,用的是他们共同的语言。仿佛一切如初。

END
恩内斯特·贝班(Ernest
Pépin,1950— ),法属瓜德罗普诗人、小说家、文学评论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专员。贝班1984年凭借诗集《静的另一面》初入法语文坛,迄今已出版诗集12部,长篇小说14部,短篇小说4篇,曾3次获得加勒比海地区文学大奖,现任卡拉贝奖——加勒比海地区最重要文学奖——评委会成员,是克里奥尔文学的领军人物之一。
贝班在小说中致力于表现在历史、传统、信仰等各种力量影响下的瓜德罗普社会风貌。他的处女作小说《拿棍子的男人》(1992)讲述的是1950年代发生在瓜德罗普岛上一桩虐待妇女案,《斑鸠的圣歌》(2004)探讨岛上女性之间的情感,《巴别鼓》(1996)则通过表现音乐传统来刻画克里奥尔文化之魂。
诗人出身的贝班在小说创作中十分重视语言的节奏感和画面感,有评论者说能够在其小说中感受到“大海的喧闹和飓风的肆虐”。贝班一直尝试将克里奥尔口语的节奏融入法语书写中,形成了极具特色的个人风格。此处选译的《大河之女》(La
femmefleuve)是一篇从主题到文字风格都十分“贝班”的小说,选自Magellan
& Cie出版社2015年出版的《瓜德罗普短篇小说集》(Nouvelles
de Guadeloup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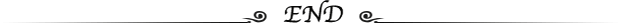
点击上图,订阅全年《世界文学》
点击上图,订阅单期《世界文学》

添加《世界文学》小助手
获邀进入《世界文学》分享会3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