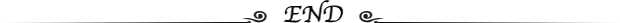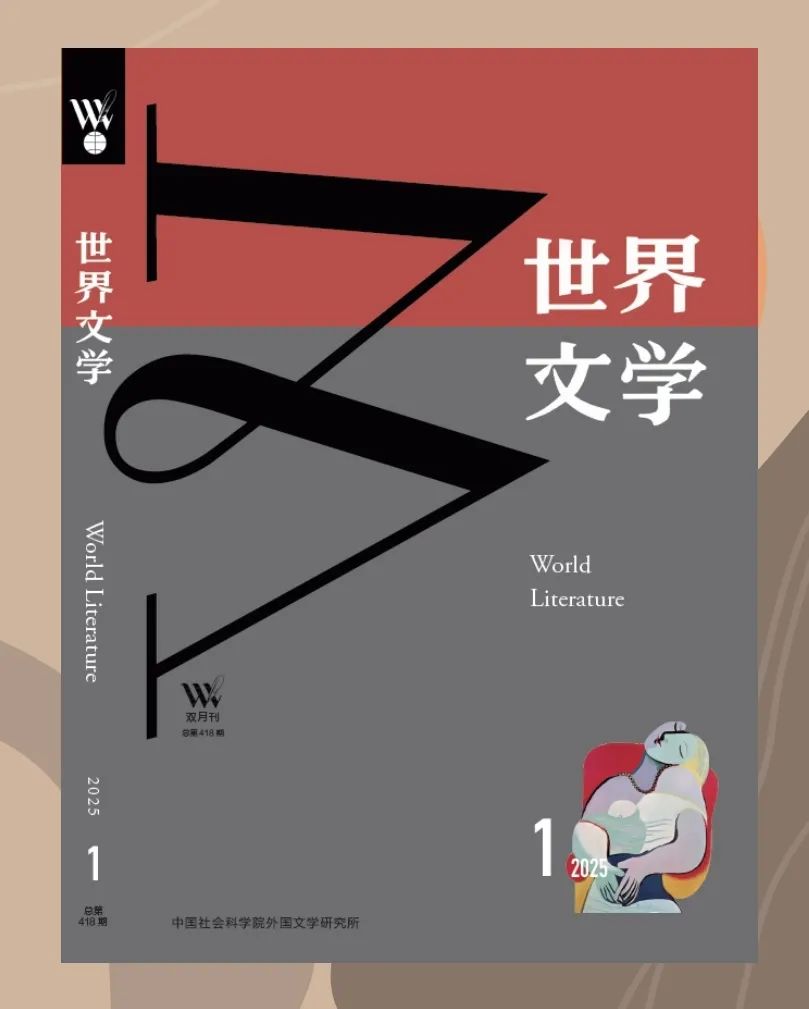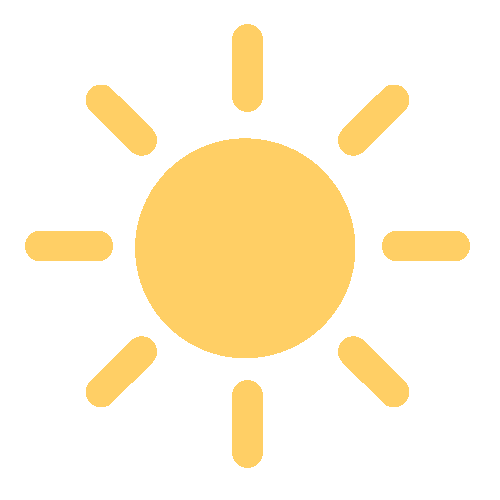第一读者 | 戴•盖茨【美国】:他垂手为我指引方向
![]()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我初次见到保罗本人的时候,他正在台上表演,腿上绑着一整条石膏——让我回想一下当时的画面——对,是左腿,两侧腋下各拄着一根拐棍,弹曼陀林的时候只有前臂在动。有好事者拿变色笔在石膏模的底部画了一只粗粗大大的牛仔靴,再加上雕花的压印,看着挺像那么回事。这是在康涅狄格州罗克斯伯里举行的一场户外比赛,时间是一九七七年,那年夏天我刚满十八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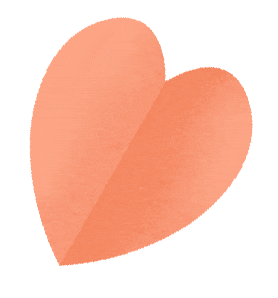
戴维·盖茨作 刘志刚译
对你们来说,保罗·汤普森这个名字想必和我的名字一样陌生,但如果你们熟悉大约三十年前纽约的“蓝草音乐”圈,估计听说过一些关于他的故事。据说,吉米·马丁【吉·马丁(1927—2005),美国著名乡村音乐家,被誉为“蓝草音乐之王”】本来想让保罗加入自己的“阳光山仔”乐队,可他硬是不肯把长发剪掉。在比恩布洛索姆音乐节【比恩布洛索姆音乐节,由“蓝草音乐之父”比尔·门罗创立于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印第安纳州比恩布洛索姆镇,是历史最悠久、最负盛名的“蓝草音乐”节】上,他让肯尼·贝克【肯·贝克(1926—2011),比尔·门罗的“蓝草男孩”乐队成员】对大麻产生了兴趣,还在迷幻药的影响下和托尼·特里什卡【托·特里什卡(1949—),美国著名五弦班卓琴演奏家】同台献艺过。其实,这种事在当时一点都不稀罕。我初次见到保罗本人的时候,他正在台上表演,腿上绑着一整条石膏——让我回想一下当时的画面——对,是左腿,两侧腋下各拄着一根拐棍,弹曼陀林的时候只有前臂在动。有好事者拿变色笔在石膏模的底部画了一只粗粗大大的牛仔靴,再加上雕花的压印,看着挺像那么回事。这是在康涅狄格州罗克斯伯里举行的一场户外比赛,时间是一九七七年,那年夏天我刚满十八岁。当时我随行的乐队刚唱完两首歌,我们几个正在后台收拾乐器,这时,保罗在前台唱起了《皮鞭》【《皮鞭》是上世纪60年代美国一部同名电视连续剧的主题曲】。我听见我们乐队里弹曼陀林的那位说:“这下可好,咱们没戏了。”


保罗乐队的队员年龄都偏大,清一色留着长发,除了那名小提琴手:一个剃了水兵式寸头、凶巴巴的家伙。和去年一样,保罗的乐队再次获得大奖,而我们则是第二名。保罗拄着拐棍,踉踉跄跄地走过来对我说,他很喜欢我唱的《在那荣耀大地上》【歌曲名,原唱者为“斯坦利兄弟”组合】。没想到这话竟然出自保罗·汤普森之口。我自认为高中刚毕业的孩子能唱到这种程度,属实不错——我不过是把基督教歌曲视为当时的类型音乐,却把腔调模仿得惟妙惟肖。我回答保罗说“多谢大哥”,但为了避免尴尬,并没有同样恭维他几句。最后,我们在外面停车的地方合唱了几首歌——记得他当时斜靠在一辆车的挡泥板上——我想他肯定很惊讶,我居然会那么多“路文兄弟”【“路文兄弟”,又名“深情兄弟”,即艾拉·劳德米尔克(1924—1965)和查理·劳德米尔克(1927—2011),是美国著名的乡村音乐组合】的歌:《来不及》《明日天涯》《你怕死吗?》。我让他唱艾拉的高音部,他说自己已经把烟戒了,现在不用假音就能唱上去。保罗的个子比我高,两侧的颧骨让他看着一脸苦相,就如同常在“沙尘暴时期”【上世纪30年代,美国中西部平原地区屡遭沙尘暴袭击,大批农民流离失所,史称“沙尘暴时期”。当时的记者拍摄了大量记录生态灾难与经济萧条的照片】的照片里见到的难民;他的鬓发已经花白,尽管年纪肯定还没到四十。他告诉我他是在打壁球时摔断的腿;当然,这想必是一句玩笑话。
我们俩都是那天下午从纽约来的,我坐的面包车,同行的有乐队的班卓琴手和他的老婆、孩子,保罗则是他女友开车送来的。就在我们收拾行李的时候,他问我要怎么回城,会不会开手动挡。他说女友生他的气,坐上别人摩托车的后座走了,现在他一个人滞留在康涅狄格州东北角这鬼地方,不知该怎么回家。保罗开的是一辆老旧的凯旋TR6敞篷跑车,座位后面堆满了杂物,我只好用弹力绳把自己的吉他绑在行李架上。回纽约的路上,他一直在播放磁带里“斯坦利兄弟”的歌曲——那些磁带每盘时长九十分钟,是从他收藏的密纹唱片上拷贝过来的。一路上我们没怎么说话——等开到西城高速的时候,我才不得不把他叫醒,让他给我指路——但我注意到,他总是习惯说“曼陀铃”而不是“曼陀林”,所以,打那以后,我也开始刻意说“曼陀铃”。
保罗住在西区大道的一栋老楼里,楼房挺大,离八十六街不远;因为是周六晚上,我轻易就在附近找到了停车位。保罗说,周一他会想办法把车挪走。我想上楼去他家再听几首歌,抽几口大麻吗?他还没把那玩意儿给戒了。可时间已经不早,我还得背上吉他去坐地铁,再说,关于保罗·汤普森的故事,我已经攒下了一个,足够说给别人听了。


我们中的多数人只在周末出来玩音乐,对别人的真实生活都是一点点逐渐了解的。我们的班卓琴手在布鲁克林学院教微积分;保罗乐队里的小提琴手(我在纽约遇到的唯一地道的南方人)在海湾岭【海湾岭位于美国纽约市布鲁克林区西部,与斯塔顿岛隔海相望】经营一家燃油公司;还有个你经常见到的家伙,冬不拉弹得非常好,但其实,他的正职是一名公共辩护律师。那年夏天我在书店打工,当时纽约大学还没开学,我打算将来读英语专业。后来我才发现,原来保罗·汤普森是《新闻周刊》的一名科普作家。有一天,我在洛克菲勒中心的地铁站见到他,但一下子没想起在哪里见过这个人:他身穿蓝色的牛津衬衫,外套一件平纹布夹克,下身是牛仔裤和牛仔靴。有人告诉我,他二十几岁的时候出版过一部小说,那本书至今还能在斯特兰德书店【斯特兰德书店创立于1927年,是纽约历史最悠久的一家大型书店】找到。
几年后,乐队主唱搬到加州,保罗便拉我入了伙,有时我俩会去一些咖啡馆表演二重唱,自称“半价兄弟”。我在康涅狄格大学读研究生,但每个月总要开车进城好几次,至于保罗,他会不定期召集乐队成员开派对,在屋里摆上一捆捆干草包【干草包很硬实,铺上布料,可以充当派对座椅,富有乡村风情】。等表演结束后,我们一帮人就到他家去,嗑药,听音乐,或者喝酒,一起聊聊书。他告诉我他很喜欢吉米·汉克【疑为保罗·汤普森给美国作家亨利·詹姆斯所取的绰号】,还从自己保存完好的老版平装“名著经典书丛”【“名著经典书丛”是企鹅兰登书屋从1948年起推出的平价版名著系列】里抽出一本《使节》【《使节》是亨利·詹姆斯创作的长篇小说,出版于1903年】送给我;这书的标价是五十美分。当时,我已决定专攻十九世纪文学,我很讨厌吉米·汉克对《我们共同的朋友》【《我们共同的朋友》(1863)是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的一部长篇小说】的评价——“此书之粗劣不在于时而出现的尴尬描写,而在于让人产生挥之不去的疲惫感”【这句话引自亨利·詹姆斯评论《我们共同的朋友》的文章(载于1865年12月21日出版的《国家》杂志)】。但即便如此,我至今还保留着这本书:封面上是一位绅士的背影,他坐在咖啡馆的椅子上,头戴高顶礼帽,手握酒杯和拐杖。想必这本书将永远躺在我的书架上,我到死也不会去翻开它吧。
就在快要完成博士论文期间,我和生平第一个交往超过一个月的女人结婚了。黛安,我最好还是承认,是我当助教时的学生。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又何必遮遮掩掩,声称我们直到学期结束才睡到一起?或者声称:谈论两人的恋爱史时,我们从来说不清是谁先迈出了第一步?当时,她常穿着牛仔短裤跟我去参加音乐节和派对,充当我的酷女友,我们都答应对方,搬出已婚学生宿舍后,要到乡下去住,要有一栋堆满书的房子,不要电视,自己种粮食吃。我从小在公园坡【公园坡,纽约布鲁克林区的高级住宅区,以褐砂石房屋著称】长大,但父亲却是个民谣爱好者——五十年代那会儿,他常在华盛顿广场附近闲逛——我十二三岁就开始听他的密纹唱片,目不转睛地看着那些站在快倒塌的门廊里、老态龙钟的爷爷们的照片;“蓝草”歌手们——身穿商务套装,头戴牛仔帽,个个不苟言笑,神情哀戚——尽管怀里抱着价值上万美金的马丁牌和吉布森牌吉他,但依然选择在山间废弃的小屋旁摆姿势拍写真。在我们这个小圈子里,人人都当自己是神秘的农村孩子。我那位老班卓琴手,也就是那个跟我一起开车去罗克斯伯里的家伙,辞去教职,搬到了“东北王国”【美国佛蒙特州东北三县的合称,与加拿大边境接壤】,听说他目前在自己的车间里生产B弦变音器【一种金属装置,能让吉他B弦升高半音或全音】,还在一支乡村乐队里弹踏板钢棒吉他。我们的贝斯手则是离开“东村”【位于纽约东区,区内酒吧林立,非主流艺术家聚集地】,去了北卡罗来纳州的托斯特,拜在汤米·贾雷尔【汤·贾雷尔(1901—1985),美国著名乡村音乐家,尤其擅长演奏小提琴】门下。就连我父亲也摇身一变,成了一名中产民谣爱好者。他在爱迪生联合电气公司干了三十年的工程师;退休后,他和我母亲在伍德斯托克附近盖了一座太阳能房。
我在新罕布什尔州一所规模较小的大学找到一份教职,黛安则是被佛蒙特烹饪学院录用了。我们买下一座需要修缮的农舍,外加一个柴火灶、一间谷仓、二十英亩土地;房子建在一条泥土路上,去我俩的学校都不怎么方便。我在老旧的鸡舍上加盖了一层金属顶棚——黛安一直想要养鸡来着——每年春天我都会把菜园的地平整一遍,此外,我还以防止土地返荒为由买了一把链锯、一台分割器,以及一辆生锈的福特8N【福特8N是福特汽车公司生产的一款拖拉机,最早于1947年面世】。我们的邻居,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儿,一直鼓励我这么做;他喜欢我们,因为我这人很没用,而黛安又长得那么好看。每年春天,他都要和我一起预备过冬的木柴,我的分割器由两人共用,他的圆锯也在拖拉机的取力器【取力器是拖拉机中的机械装置,其主要功能是将动力从拖拉机发动机传输到辅助设备或机具(如圆锯)上,使它们能够独立运行】旁开动起来。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做到这一切的,毕竟,我承担着“三加三”的教学量【即每学期每周三课时,上两学期】,还有一部书稿要完成;当老头儿最终被送入护理中心的时候,我竟然买起了成捆出售的木柴。我父母每年开车来看我们几次,父亲总是不忘带上他的小型马丁吉他,就是当年他教我和弦时用过的那把。他和我总是围坐在一起,来回弹那六首指弹类曲子——比如《路易斯·科林斯》《钉锤的呻吟》——他从来就没想要弹点别的。我父母经常最多待一两天。柴火灶不够热,秋冬天客房总是暖和不起来,而到了夏天,母亲又常常被蚊子咬得够呛。
每年七月,黛安和我都会办一次户外音乐派对,跟大家一起烤乳猪——她会提前一整周准备饭菜。她那些波士顿来的朋友和我那些纽约来的朋友会带帐篷和睡袋来;在屋后田野角落里成立的特殊乐队开始演奏时,他们就随着音乐起舞。保罗·汤普森总是带着他的曼陀林和上好的大麻出现,身边跟着一个年纪比他小的女人,而且每次都不重样。
那些年里,保罗总是开车把那个来陪自己度夏的女人送到白河岔口【白河岔口是位于美国佛蒙特州哈特福德镇的历史街区】的公交站,而自己则要一直待到周二或周三。黛安很喜欢保罗——一开始,又有哪个女人不喜欢呢?——况且他也没有添什么麻烦。他自己一个人在树林里散步;他在门廊的吊床上看几个小时的书;我们上楼睡觉,留他一个人在楼下吸大麻,戴着耳机听音乐,他也并不在意。“一个人要能死在这儿,倒也挺幸福。”他过去总爱这么说。他告诉我,他喜欢天刚亮的时候听公鸡打鸣,因为那能让他安心地接着睡。好不容易起床后,他就到门外的鸡舍去收鸡蛋,给自己做早餐——然后再搞卫生。黛安通常大清早就去捡鸡蛋,但她总是故意留几个给保罗。有一次,保罗貌似出去了很久,我就去找他,结果,透过鸡舍的窗口发现他居然蹲坐在地上,但屁股没有着地,只有一双牛仔靴和地面有接触。他自言自语,不断点头,像是对着自己,又像是对着鸡群——那些母鸡直接向他围了上去,这样的事从没发生在我身上。我悄悄回到屋里,估计他应该没有听见我的动静。
但多半时间,保罗并不是我常想到的人,尽管现在我知道他那时总在想着我。


不管什么原因吧,我从没想过要孩子。这不是什么反人类罪——事实很可能正好相反——可是,黛安过了三十岁,这很自然地变成了一个问题。除此以外,她还怀疑我和学生的关系——这也是我早该料到的——特别是怀疑其中的某个学生。(但其实,她搞错了对象。)黛安和我共同生活了十年,她离开后,我每晚都得把自己灌醉才能入睡,整整持续了一个月。这是不是证明我并非铁石心肠呢?现在她已经再婚,自己做餐饮生意,她的大女儿正在报考大学——每所大学都好过我目前任教的学校。现在,我俩关系处得不错,有时她还会寄照片给我。尽管这样,当初离婚那会儿,她说这房子自己也有份儿,坚持让我给她金钱补偿,而我一时又找不到薪水更高的工作。我的专著《凯茜的卡利班:〈呼啸山庄〉里的性、种族与崇高性》——是拿我的博士论文重写的——只收到了一篇书评;文章刊登在《维多利亚研究》上,作者(来自密苏里州同样一所不知名的大学)认为该书“有些地方蛮不讲理,有些地方味同嚼蜡”。然而,正是这本书让我获得了终身教职,因为在过去十年里,系里别的人都没发表过著作,而我也仅仅因此涨了两千块钱的工资。所以,我又回去植树造林了,直到——天哪,非得这样吗?——直到我可以出售父亲的房子。
父亲最后那次来是在秋天,当时母亲已经过世,黛安也走了。和往常一样,他带来了自己的马丁吉他,但并不怎么想弹。他会把吉他留给我吗?感觉琴弦很紧;也许可以把它拿去给我修吉他的师傅看看?这对我来说并不要紧,但我还是告诉他,我会去问问布拉德,看能不能把弦调得松一点。我心想,见鬼,他今年七十八岁,手指恐怕不如以前那么有劲了。但结果证明,这完全是哈罗德·布鲁姆所谓的弱误读【美国文学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1930—2019)认为每首诗都是后人对前人的蓄意误读,其中“强诗人”在误读中能有所创新,而“弱诗人”则拾人牙慧】。
黛安和我以前常将工厂里的木质线轴当作咖啡桌来用,我把棋盘摆放在上面——多半都是父亲把我打得惨败——将他每次都会带来的詹姆森威士忌倒满一杯又一杯。我在考虑要不要走车时,他随手从沙发旁的桌子上捡起一张照片——照片中,黛安和我坐在巴塞罗那的一家咖啡馆里——我们只去过欧洲一回,这张照片是那时拍的。
“你这是要干嘛,开博物馆吗?”他说,“我跟你说,我挺喜欢黛安。你妈有自己的看法,没问题。但我呢,觉得你真傻,竟然让她走了。不过,这是你自己做的决定,对吗?”
“可以这么说吧。”
“而且你还留着她那些洗头的玩意儿。”他朝浴室的方向晃晃拇指,黛安的确扔下护发素、润肤霜和乳液的瓶子(大多是空瓶子)没带走。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干嘛。”
“怎么,这就没招了?你刚才下那两步棋,等于自取灭亡。”我把棋局又看了一遍,然后站起身,往炉膛里添了几根木柴。
“要是我会怎么做?”他说,“找个自愿上钩的大冤种——我想想,该是什么人呢?梭罗。然后买一小块好地皮,这样,一年里有九个月你就不用干这个了。等到了我这把年纪,你还想像这样生活吗?”
“我记得你当初可是迫不及待要逃离城市吧。”
“不是为了活成佃农的样子。怎么,你这儿还有有线电视?”
“我们没有电视机。”我重新坐下,又看了一眼棋盘。
“有意思。”他说,“你说的‘我们’是谁啊?”
“嗯,好吧。我懂了。”
“总之,现在你妈走了,我整天就盯着树发呆。你可以好好过日子的。现在有没有在谈对象啊?”
我把手中的王放倒在棋盘上。“爸,谈了一个月了。”
“这就对了嘛。”他望向窗外,“这些树会害了你。”
到詹娜搬来同居的那天,我住在新罕布什尔的时间已经超过我在城里生活的时间,尽管在本地人眼里,我还是异乡客。那时,我又盖了一座房子:A字型屋架,坐落在马路斜对角的山坡上。本来,黛安和我可以把那块地连同马路这一侧的土地全都买下来,可我们终究没能再凑出一万块钱来。我很讨厌往那边看。
詹娜在“二十一世纪不动产”上班,地点离我在旧城中心的大学很近。没错,我是在酒吧认识她的——当时我上完课开始往酒吧跑。詹娜有一回走进公司,表明来意,就讨到了那份工作;老板很喜欢她在某网站学会的一些小技巧:在厨房的台面上摆几个盛满柠檬和青苹果的碗盆,在咖啡桌上放几本《乡村杂志》并摆成扇形。我感觉她在那里混太屈才了:她可是塔夫茨大学毕业的政治学硕士。可她却说自己已经找到安身立命之所。我想我也是。
詹娜一开始就告诉我,她不想当所谓的续弦,还在自己的斯巴鲁车上贴了这样的标语:“要做爱,不要小孩。”
她的公寓里有轨道灯、高级的东方地毯和煤气壁炉,但她在我家里似乎感觉挺自在。我们把客厅重刷了一遍——刷成了黄色,她说黄色比黛安和我之前选的白色感觉更温暖——此外,她也只是把沙发移到原来放扶手椅的位置,为我们找到一个松木制的毛毯箱来充当咖啡桌。詹娜不反对拨号上网,也同意不要电视——她说商业媒体以前占用了她太多时间——她甚至说公鸡打鸣不会吵醒她,尽管她不愿意亲自进鸡舍。同居五年以后,我们有性生活的日子仍然比没有的日子多:我已经习惯她肉嘟嘟的膝盖;或许她也接受了我的大肚腩和一双小手。
詹娜弹吉他——这是她的另一个加分项——我们偶尔还一起唱歌。歌是她自己选的,我负责和声——安妮·迪弗兰科【安·迪弗兰科(1970—),加拿大歌手,作曲人】、米歇尔·肖克特【米·肖克特(1962—),美国歌手,作曲人】、“靛蓝女孩”【美国一支民谣摇滚乐队组合,组员为艾米·雷和艾米丽·萨利厄斯】,有些歌并没你想的那么糟——她还了解《银线金针》【《银线金针》是乡村歌曲经典,创作于1956年】。和爱美萝·哈里斯【爱·哈里斯(1947—),美国歌手,作曲人,乐队领队,社会活动家】的那些流行歌。我试着教她几首波特【波·瓦格纳(1927—2007),美国乡村音乐大师】和多莉·帕顿【多·帕顿(1946—),美国著名乡村音乐家,曾多次荣获“格莱美”音乐奖】的歌,只不过她的音域不宽,我俩一直没找到适合她的音调。实际上,劝我重开音乐派对的人正是詹娜。她讨厌做饭,所以我们常囤啤酒、杰克·丹尼威士忌和薯片,还点披萨外卖,让参加者自己带吃的。多半时间她都躲在后面,让玩“蓝草”的乐手们互相交换内幕消息——是啊,《完全陌生人》【《完全陌生人》的原唱为“斯坦利兄弟”组合,1960年首次发行】。谁来唱拉尔夫的部分?——可是,等夜深了以后,有时她也能在我劝说下进入音乐玩家们的圈子,唱一首《罪恶都市》。
“咱们这个关系说不定能成,”我们在一起一个月的时候,她这么对我说,“前提是你我都不要变成混球。”
“这有多大的可能?”我问。
“有可能,”她说,“如果你不愿意改变自己的话。我的意思是,当形势比人强的时候。”
“可你现在很幸福啊。”
“这是谁跟你说的?”她回道。


最后那年夏天,在我发出音乐派对的通知以后——我们把日程提前了,因为想着七月能去一趟约克郡,去看看“勃朗特乡村”——保罗回了一封电邮,说他从《新闻周刊》主动离职,获得了一点补偿,现在“正生活在不安之街上”【保罗这个短语的意思是他的生活朝不保夕】,但会尽可能赶来参加。他说,他正在做与削山采矿有关的图书策划,届时会去肯塔基州东部住一段时间——在那里,他也许还能玩玩音乐,前提是别把挂着纽约牌照的车开去。
举行派对的那个周五晚上,天刚擦黑,保罗坐着一辆“吉普牧马人”进了我家的前院。开车的是个女人,年纪看着跟詹娜差不多,长相并不太符合保罗的标准——也许是鼻子偏大,下巴又偏短了一点——但她身材苗条,一头染黑的直发垂到肩上。保罗从车上下来,伸伸腰腿,望了一眼远处的山峰。“哇——靠!”他对那女的说,“你闻闻这空气。我有没有跟你说过?这是全世界我最喜欢的地方。”
“你说过几次。”她回道。
“给大伙儿介绍一下,她叫西蒙妮。”他说。只要身边有音乐环绕,他的南方口音就会加重。“我最后的女人,也是最好的女人。”
“等其他娘们儿排着队从路口过来的时候,那就说不准了。”说着,西蒙妮伸出一根手指,沿着保罗的胳膊摸了下去。
“净胡扯。”保罗说。他看着比往常更瘦削了,等他转过身,我发现他的眼袋发黑,把眼睑拽得往下垂,眼球下面露出了红血丝。“嘿,听着,我们得唱一首《爱的排行榜》【《爱的排行榜》,乡村歌曲经典,原唱为吉米·马丁】。但首先——你们说呢?”说着,他打开曼陀林琴盒,取出一支风笛和一塑料袋的大麻。
吸了一次,我就知道量多了,也许喝瓶啤酒能缓一缓,也许不管用;就连保罗也只吸了三次。他接着开嗓唱起了《爱的排行榜》,不知怎么的,我竟不知不觉跟着唱起了第一段。直到开口那一刻,我才记起歌词——“我已经听说,亲爱的,你真的大红大紫”——可是,到了合唱段落的高音部,他的嗓子却在“顶峰”的“顶”字上哑了。他问我能不能把音阶降到A。好吧,怎么说呢,毕竟都快七十岁了吧?假如我今年五十一岁,又会怎么样?
午夜前他终于选择放弃——他说一路开车,累惨了——我们安排他和西蒙妮住在走廊尽头的那间大客房。凌晨两点半左右,音乐声逐渐减弱,大家回到各自的帐篷和房车,詹娜和我上楼,发现他们屋里的灯还亮着;詹娜说她好像听见保罗在咳嗽。当灰色的曙光透进窗户时,公鸡开始打鸣,把我吵醒了一小会儿;我希望保罗也听见了鸡叫,可以安心地重新入睡。


早晨,我系上黛安留下的一条及膝的白围裙,快速炒好鸡蛋,将份量足足的炒鸡蛋,连同摘自菜园的羽衣甘蓝,满满地堆在火鸡烤盘上,然后摆好了纸盘和塑料餐叉,敲响了一副三角铁——黛安以前常用它请派对的客人进屋。保罗和西蒙妮下楼的时候,别人都快吃完了。“睡得还好吗?”我问。
“从来没这么好过。”他说。在阳光照射下,他的眼袋似乎颜色更深了。“只要搞定夜间任务就可以了。”说着,他伸手拧了一下西蒙妮的屁股:“这玩意儿会要了我的老命。”
“别吓着你的朋友。”她说,“瞧,人家脸都红了。”
保罗弯腰掀开我的围裙边,往里瞄了一眼。“早饭吃什么,妈咪?”
两人取了盘子,走到外面的门廊,我初步清理完毕后,出来一看,发现詹娜坐在保罗身边,西蒙妮则待在草坪上,试着做出一个头手倒立的动作,一头黑发正好散开,落在草地上。保罗没有碰盘里的炒鸡蛋。“嘿,厨王,”他说,“听着,我有没有跟你说过我在一支摇滚乐队里弹贝斯?像那些老头乐队一样?我太他妈喜欢了——咱们这些乡下人错过了太多东西。”他叉起一块鸡蛋,又放了下去。“不过,我可能还是得退出。”
“你的书写得怎么样了?”
“哦,是啊,还有书。这个以后再谈。”西蒙妮把两只脚举在半空,肌肉发达的两条腿伸得笔直,脚趾尖尖的,趾甲涂成了黑色。保罗拍拍手,大喊:“太棒了!”他转身向我。“真不敢相信我终于找对人了,”他说,“九局下半【九局下半,棒球术语,即比赛的最后一个回合】。你好好看看她怎么样。”
“她看着挺不错。”我说。西蒙妮穿着运动短裤,裤腿此时早已落下来,黑色的蕾丝内裤大部分尽收眼底。
“听着,我可能很快会打电话来,请你帮个忙。”他说,“有可能。会是个大忙哦。”他看了詹娜一眼。“需要你俩协助。”
“你这也搞得太神秘了。”她说。
“没问题,”我回道,“帮什么忙都行,随便什么时候。”
“那太感谢了。”他站起身向西蒙妮喊道,“宝贝,你打算这样倒立一整天吗?快来,我想给你介绍些女孩子。”
他握住西蒙妮的手,一路把她领到鸡舍。他的腿瘸得比以往更厉害了——那条断过的腿始终没有痊愈——我注意到他脚上穿的居然是耐克鞋,而不是靴子。
詹娜碰碰我的胳膊。“我看他这样子不太对劲啊。”
“人家不是在谈恋爱嘛。”我说。
“看得出来,那点恩爱秀还是对你有点触动。”我正想着要怎么否认这一点,不料她却竖起一根手指堵住了我的嘴。“我的意思是,你比我更了解保罗,”她说,“但我更懂西蒙妮,她得应对怎样的局面啊。”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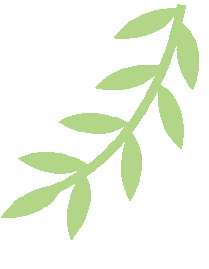

戴维·盖茨(David Gates,1947—),新闻媒体从业者,小说家。自幼学习弹奏吉他和班卓琴,喜欢乡村音乐、爵士乐、“嘻哈”等音乐类型。1972年毕业于康涅狄格大学,获得学士学位。长期担任《新闻周刊》艺术版块编辑,负责图书和音乐评论,后来在蒙大拿大学和佛蒙特州本宁顿学院教授创意写作。已出版两部长篇小说,两部短篇小说集。短篇小说常发表于《纽约客》《巴黎评论》《纽约书评》等杂志。作品曾入围普利策奖和美国国家书评人协会奖。盖茨笔下的主人公多为反英雄,粗鲁,叛逆,玩世不恭,有各种性格缺陷,却不让人生厌。这些人物以赤裸的诚实态度和怪诞的幽默感向我们展现了人类处境不堪的一面。
《他垂手为我指引方向》(A Hand Reached Down to Guide Me)最早发表于2013年的《格兰塔》杂志(第126期),后来收录于盖茨的同名短篇小说集(克诺夫出版社,2015年)。这篇小说的标题出自美国“蓝草音乐”组合“斯坦利兄弟”的歌曲《我罪恶的过往》:“他垂手为我指引方向,/面带甜美的微笑。/我听见罪人在低语:/哦,主啊,祈求您宽恕我吧。”在盖茨这篇作品里,“垂手为我指引方向”的,不是基督教徒所信奉的上帝,而是那个无意中用自己的生命结局将“我”带出人生迷局的音乐人。

上文节选小说一半内容,感兴趣的读者朋友可以进入微店,购买纸刊阅读全文。原载于《世界文学》2025年第1期,责任编辑:叶丽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