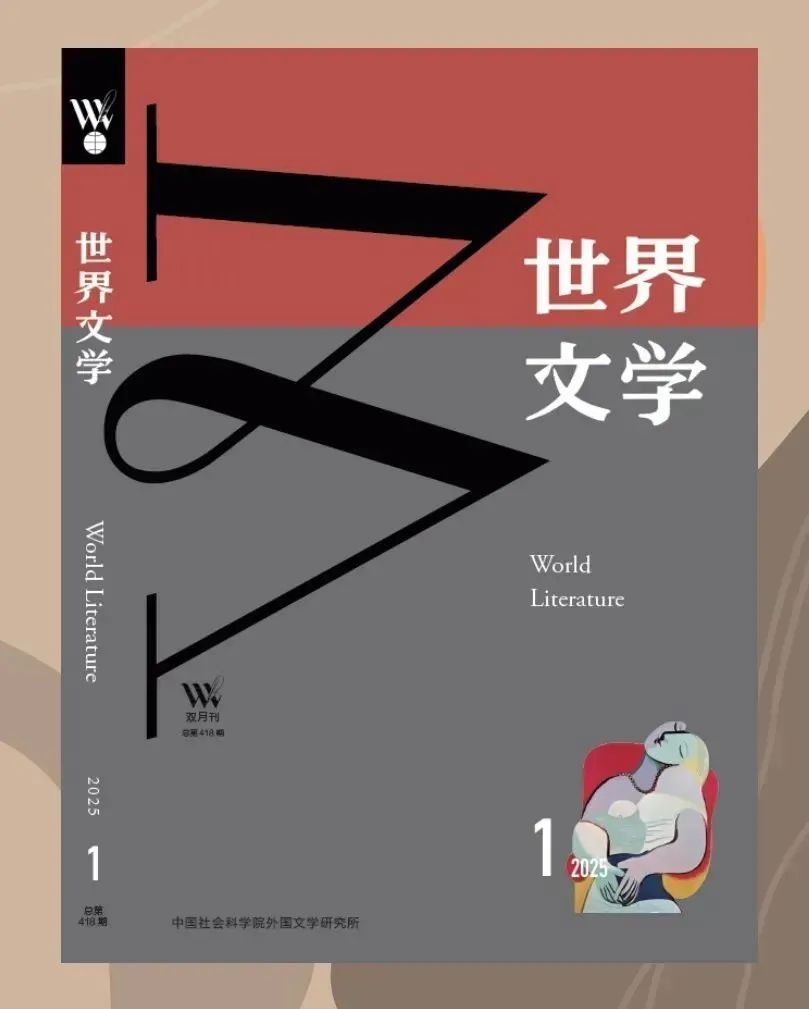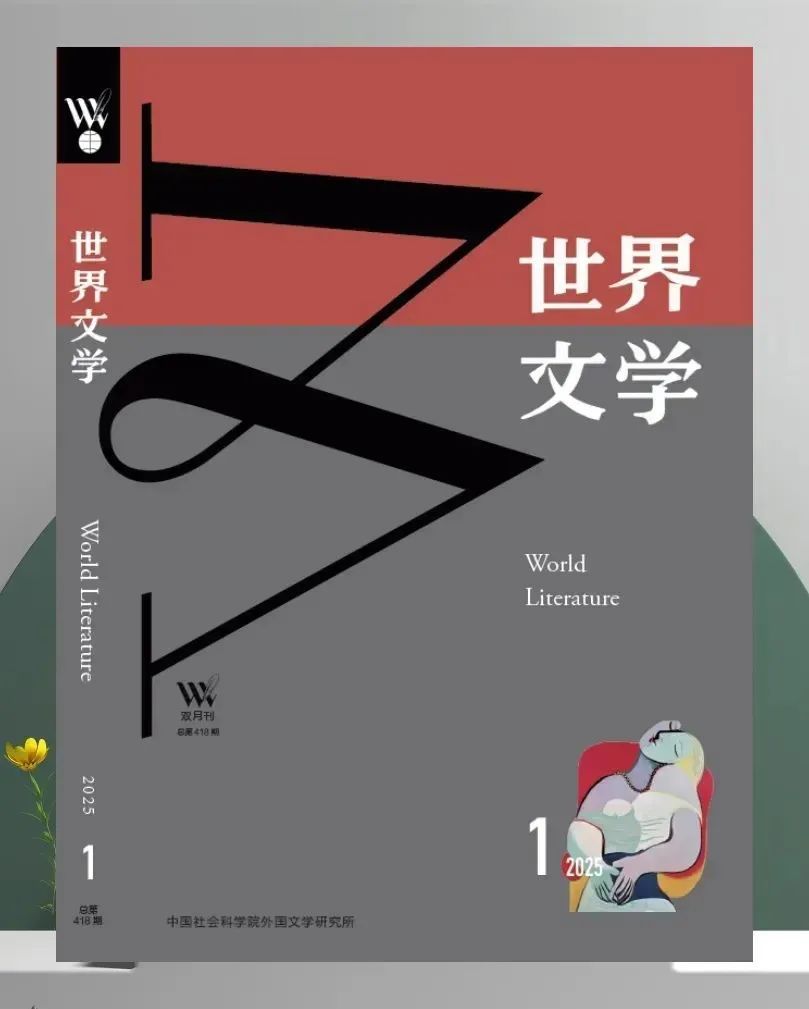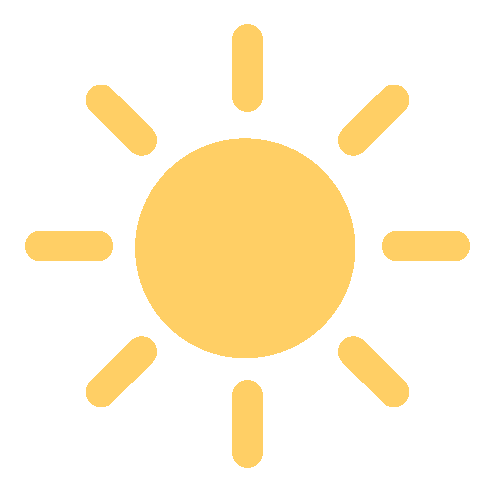散文品读 | 博•赫拉巴尔【捷克】:我的猫们

博胡米尔·赫拉巴尔作 徐伟珠译
安芭拉太太问我,哪只是您的猫来着,喜欢整天坐在河边,一动不动地看着河水?我说,那是施瓦茨瓦尔德,最笨的公猫。什么都不会做,除了每天下午蹲在凳子上往水里看,为了看到整条溪流的水,完整无保留地从自己的面前淌过。它还会做的另一件事是,当我们俩一起往小溪走时,它先于我走出家门,每走三米就停下步子来,像箱子盖似的往后仰起小脑袋,抬起身子,我只得把它抱入怀中,它闭上双眼,我把它贴近我的脸,在那一瞬间里我们俩融为一体。惟独我们俩在一起时,我才能感受到,它怎样沁入我的心田,然后复活,苏醒,在我跟前步出三米后,它重又回头思念着我,亲昵一番,如此反复。我们缠缠绵绵,心心相印,直到靠近溪边。我常说,这是我养的三只猫里最笨的猫,虽然最壮实,独自却什么也干不了,总要找其他两只猫商量,它自己表达不了时,只能由伦达或者马尼奇卡来代劳。因为力气大,施瓦茨瓦尔德还有一个名字叫卡西乌【卡西乌(公元前85-前42年),古罗马将领,刺杀凯撒的主谋之一】。
大雪纷飞的日子里,我的猫们总以为,我一迈出家门便不再回来了,于是它们先后看护着我,踏着厚厚的积雪一路伴着我前去酒馆,三个小黑点在我身后跳跃。它们在酒馆门口无怨地候着,直到我走出酒馆,一同回家。返家途中,我只得把它们轮流抱着,焐暖他们冻僵了的小爪。到家后,虽然一路抱怨,它们还是原谅了我,和我一起蜷缩到床上,共同进入梦乡。很让我头痛的是,第一只猫在半夜十二点起床撒尿,第二只在一点半,第三只在三点。我就像钟点旅馆的守门人,在夜里不停地起身。
……
妻子周末来看我们时,每次都要叹息:我们拿这么多的猫怎么办?我安慰她说:你不是不清楚,现在我们一下子有了五只猫,到春天时它们都会丢失的。有一只不回来了,夜里我们出去寻找,呼唤着它的名字,然而徒然。接着是第二只、第三只,最后只剩下了一只,我们多么担心它出去后再不见踪影……然而妻子看到这么多小动物,还是唠叨个不停……我们拿这么多的猫怎么办?尽管如此,她还是满心欢喜期盼着早晨,等我醒来后,起床去开门,五只略大了一点的猫奔入厨房,先舔净两盆牛奶,然后一起扑到床上,钻进被窝来取暖。我每次分三只猫到妻子的床上。就这样,小猫挤在我们的身边,心满意足地进入了梦乡。伦达、赛格米勒和施瓦茨瓦尔德常常和妻子睡一床,我床上的两只猫,我给那只白腿、白胸的黑猫取名施瓦尔察娃,另一只小花猫叫长筒袜。我最钟爱施瓦尔察娃,百看不厌。她也出奇地依恋我,每当我用双手掬起她来,贴向前额,对着她的耳朵倾吐亲昵的话语,她都会作出晕厥状。我,一个上了年岁的老人,头发稀疏,满脸皱褶,不期望也不可能去爱上某个美丽的女人。只有我的猫们深深爱着我,一如我年轻时对女友的迷恋。在猫的眼里,我是他们的一切,是他们的父亲和情人。最爱我的是那个白腿、白胸的施瓦尔察娃,我只要看她一眼,她就变得感性而温顺,于是我就忍不住把她抱起来,她会因我情感的投入而晕眩,而她感情的回流也会让我凝噎。那些早晨,与五只猫同眠一床,这是我们的全家福,这些猫,是我们的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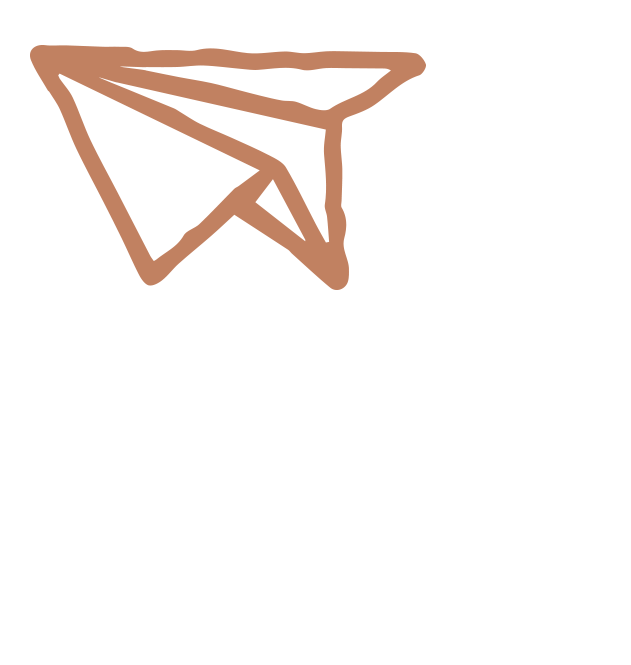

然而每天早晨,当猫们暖过身子,从夜的寒冷中缓过神来,突然间会群体比着撒欢嬉闹。它们打架,在窗帘上荡着玩,四处乱跑,上蹿下跳,小脑袋撞着柜子、磕着椅子的声响不断传来。它们在厨房折腾半个小时;把我们的衣服从椅子上扯下来,把抹布从厨房叼出来撕扯着玩;把皮鞋和拖鞋抢来抢去;钻进被子在黑暗里斗殴,纠缠不休;把桌上的东西往地上扔……这种闹剧一般持续半个小时,直到它们喘作一团,舌头都伸了出来,精疲力尽,瘫倒在绿地毯上。它们趴在椅子上,相互舔着,长时间用舌头梳理着,舔净脖子和脑袋上的毛,接着又睡去了,甜美地打着呼噜……这样的闹剧每天上演。只有当外边下起雨来,天气转冷,当雪花飘落下来,当小猫长成了公猫和母猫,当我清晨打开门,这些猫先来取暖,然后喝牛奶。天寒地冻时,它们在炉前挤成一团,伸长脖子烤着小脑袋,直到脑袋上升腾出水汽。一冬的时间让每只猫变得持重起来,有个问题让它们害怕,万一有一天我不来了呢?
它们一般睡在阳台上,凉亭下的干草堆里。从二层阳台能看到林中那条直通公路的小道。每次我坐着公共汽车,踏着积雪前来,我会从路上的某个拐角处看我的阳台,那个露天的四方平台,我看见凉亭的地板上,那里竖起了猫的耳朵,然后猫就跑出来了。我看见它们的小爪从木楼梯上飞奔而下,迎着我狂奔而来,围住我舔个不停……我总是把它们一个个抱入怀里,吻着它们的颈窝,它们紧紧贴着我。我没有把它们忘了,这让猫们欣喜若狂。
我打开走廊的门,桶里的水结了冰。我打开房门,小动物们挤到炉子跟前。我很快用木柴点上火,烧上暖气,然后热牛奶。好几次厨房盆里的水居然都冻上了……半小时后炉子和管道开始热起来。猫们享用完牛奶,全都把脑袋靠近炉子,长时间烤着,个把小时后才离开,分别躺到各自的椅子上睡觉。我给它们切好鱼,准备好肉,把奶酪撕成小块。然后我坐下来写作。打字机嚓嚓响着,我写得很急,没时间去考虑文字的风格,我必须快捷地写,为了腾出时间照料我的猫。每只猫,虽然闭着眼睛躺着,却眯缝着眼注视着我,伴着打字机声音睡觉,这让他们觉得特别安心。写了一个小时后,我穿上毛皮大衣,走到外面凛冽的寒冷里去散步。我总把门掩着,为了方便小猫去树丛里撒尿。夜间我会在盆里装上沙子,以防它们不想出门去,或者我睡得太沉。在我睡觉时,猫先从椅子上跳下来,走到门边喵喵叫,一般听到它们的叫声我会醒来。夜里我常起来,把小猫放出去,听到叫声再开门把猫放进来。逢上雨天,我用毛巾替它们擦干爪子,因为凌晨时炉火熄灭了,五只猫会跳到床上来和我睡。就像事先约好似的,每只猫都有各自固定的位置。但我的头边只能躺着施瓦尔察娃,只有她有权挨着我的头入睡,其他的猫或在我的脚边,或靠着我的背。所有的猫在入睡前都会甜蜜地呢喃几声,轻轻地打呼噜,盘成一团。太热的话,它们仰天而躺,姿势非常优美,有时热得连肚皮上的毛都湿透了。也许那是吓出来的冷汗,假如有一天我来不了了,它们该怎么办呢?

我也常常自己驾车去看望它们,但只在风和日丽的日子里。开车途中,速度稍快一些,我马上就会减速,万一出了车祸,我的猫谁来管啊?所以在冰冻、下雨、下雪的时候,为了保证安全到达,为了让我的猫们高兴,我宁愿选择坐公交车。即使在公交车里,坐在第一排时,我的心会一紧,万一撞车怎么办?于是我换到中排,出事的话,受伤的概率最小,不然有谁给我的猫去喂奶呢?
当我穿上外套,必须回布拉格时,猫们一下子变得乖巧、忧戚起来。施瓦尔察娃性格里天然有卓别林的成分,她想博得我一笑,跳来跳去翻筋斗,然后定定地看着我,希望我回心转意,留下来不走。平时两只猫打架,只要我一拿起衣服,它们马上就住手,躺到各自的椅子上,彬彬有礼地趴着,似乎只要我不走,它们就会一直这样听话,或者,即使我离开了,把它们留在家里,它们也会这么乖。每只猫都做出无比乖巧的样子,只要我不把它们弄出门去。然而我必须这么做。我把它们一只只抱起来,放到门槛外,它们像鱼儿一样从我的手中滑走。我锁上门,心情和这些猫一样地忧伤。我踏着云杉林间的小路而去,穿过林荫绵延的拱门,我最后一次转过身来,我总是看到同样的情景,每每让我心悸:栅栏的缝隙里探出猫的小脑袋,五张小脸巴巴望着我,怀着一丝希望,我会返身回去,重新回到小屋,和它们一齐聚在暖暖的火炉旁……
这样的情形常发生在布拉格的日子里。当我忧郁得无法自拔的时候,当我因紧张和害怕脑子一片空白的时候,当我孤独无助的时候,我会跳上公交车。汽车在皑皑雪原行驶的一个小时里,我坐立不安,我不知道我的猫们是否还活着。下车时,我双膝发软,我又踏上林荫道。当所有的猫向我迎来,我双手抱起它们,把额头贴上去,它们茸茸的皮毛会让我酒后的头疼和抑郁减缓许多。我一次又一次贴紧它们,它们感应到了,也紧紧地贴着我。我点燃火炉,给它们分肉块,倒牛奶。而施瓦尔察娃,她明察自己在我心中独有的份量,她感激我对她的珍视,她的眼神里分明透着这种理解,这让我吃惊。能拥有她是我的幸福,共同的秘密把我们的心系在一起。她坐在椅子上望着我,我蹲下身来,她长久靠着我,把小脑袋放入我的掌心。
我的心颤抖起来,我又必须回布拉格了,晚上有个读者座谈会在等着我。我又得把这些猫一只只驱赶到门外的寒风里,赶到潮湿的林丛和孤独里。我看到它们眼里流露出的害怕,恐怖的分别就在眼前。它们又将耽入担忧,我何时回到它们身边?我是否从此对它们的命运撒手不管。而让我揪心的是它们会被人射杀,它们会消沉而不再向我奔来,或者在车站被汽车轧死。为了摆脱痛苦的折磨,我把它们一一找来,用额头贴着它们,对我而言,它们是治疗头疼的湿毛巾。最终我迈上了林间小道,转过身去,栅栏的缝隙里还是五个小脑袋在望着我,它们一直目送着我拐向汽车站。在车上,我把头缩进竖起的衣领里,我沉入心底,自责不已。我怎忍心扔下这些善解人意的小家伙,潮冷的夜晚和刺骨的寒风在等着它们,它们只得盘缩成一团,用呼出的热气温暖自己的小爪和皮毛,互相用身子暖着对方进入梦乡,编织我回来的梦想。倘若这是真的,那该多好。盖尔斯克的夜晚极其漫长,对人来说也漫长难挨。有时这些猫让我心力交瘁,我甚至希望,我不是我,这些猫不是它们。


惟有在周末时,我、猫和妻子才欢聚一堂。我一周两次在盖尔斯克的乡间别墅过夜,我们都幸福无比。然而小家伙们知道,今天是星期天,下午我们就要启程。中午时忧伤的气氛就开始弥漫。每个下午,只要我在盖尔斯克,猫们会专门等着我躺到沙发上,盖上毯子,它们知道,这也是它们的午休时间,一只只紧挨着我躺下,盖好毯子,一直盖到下巴颏……而在星期天,小家伙们清楚,躺下也是枉然,片刻后我们就要动身,快乐就要结束了。
那一阵我听说,猎人们在林中捕猎猫,割下尾巴,每条猫尾巴能得三十克朗。远处传来的枪响都会让我一怔,我会马上冲出门去,唤来我的猫数一数,是否有一只倒在了地上,被割走了尾巴。那一阵我还听说,四周出现了收猫人,除了假装收购大大小小的猫,还偷捕无主人的猫,送到布拉格的研究所,换取每只猫五十克朗的报酬。在研究所猫的脑袋里被植入一种嘀哒作响的计数仪,测它们脑血管的脉动。我还是不要知道这些为好,枪声已经够我受的了,一想到我的某只猫被运到了布拉格,一周后因承受不住科学试验和研究,带着脑中的计数仪死去,这种想象令我发疯。多少次我在凌晨醒来,无法入睡。我恍惚听到越来越清晰的“嘀哒”声,这是善意的幻觉。我爬起来。我历来把手表裹在围巾里,我受不了秒针的嘀答声。我把表连同围巾拿进厨房,把它塞到柜子里锅的后面。然后我摸索到床边躺下,手背扶额,望着朦胧路灯光影里的天花板,我重又听到了嘀答声,它不是来自外界,而是来自我的脑海。我感到我的头颅里也被植入了计数仪,它嘀答记录着我的脑动脉和心脏的搏跳。小猫脑中的仪器会一直嘀答作响,轻者让我疯狂,重者让我死去。我胡思乱想,心神不定,不仅为自己的猫,也为所有被抓去用作科学试验的猫。当我夜不能寐的时候,这些可怜的小动物们遭遇的悲惨镜头在我眼前真切地浮现,历历在目。
冬日的一个星期天,一辆小车在我们的别墅前停了下来。下来几个人,走进来告诉我说,他们的花猫不幸死了,听说人们养了五只猫,很想从我们这里挑一只花猫带走。那个女的,一见公猫伦达,马上忍不住嚷道,如果不是亲眼看着她的猫被压在车轮下,我们的伦达和她的那只简直一模一样。这一切让我发愣,我居然没有阻止她把伦达抱到怀里,然后带走,我甚至没顾得上问她家里是否有花园,是否常出门旅游,他们是否会像我们一样爱伦达……
伦达走了。他紧贴着那位太太,俨然她就是我。那天我们所有人都怅然若失,无所适从,甚至忘了回布拉格。伦达给我们留下如此大的缺憾,因为他从来不自顾自玩。他长得英俊,比别的猫高大。伦达是监护,他看护着同伴们,是它们的首领。他做什么,别的猫都效仿。现在伦达离开了。我开始发烧。我在门前的空地上踱来踱去,骂自己如此轻易就交出了伦达,一只从不吵闹,从不打架的公猫。他总是伸出一只爪子,如同元帅的指挥棒,命令其他猫中止争吵。我竟把这样的一只猫拱手给了别人,尽管那个太太一再强调他们家开肉铺,不缺肝和肉,他们会把伦达当作自己那只被车轧死的猫一样倍加呵护。
……


在那样一个令人伤心的早晨,院子的大门吱扭一声被推开了,我看见从云杉树间走来送葬的队伍,我的弟弟和弟媳。我马上意识到,他们报丧来了,妈妈去世了,她的脑血管崩裂了。没等他们把话说完,我们就相拥而泣,头抵着头,就像中午时分啤酒厂里的马匹那样。我听见黑猫施瓦茨瓦尔德在我铺着罩单的床上拉稀,弄脏了印花毯子,渗到了被子里和绿纤维地毯上。我想揍猫一顿,然而我笑了起来,我看见猫把我的长衫撕成了丧服的样子。为了忘却心中的悲伤,为了不必去回想母亲弥留时的最后一天,最后一小时,最后一分钟,我动手粗粗地刷洗了罩单,扯下被套,把床清理了一遍。一个小时过去了,当我在风中晾起被单时,郁在心间的思念与悲苦不觉随风而散了。那苦楚,那第一个创伤啊。
妈妈辞世后,我的心慢慢平静了下来,我一如往常在去小溪的路上轻抚施瓦茨瓦尔德,去的路上二十次,回来时二十次。我一次又一次俯身把它拥入怀中,它就像保险丝断了一般,脖子紧倚着我,我也一样。如此这般,我们爱的电路在往返路途二十次的接触里连接又断开。这有多么甜蜜,这种神秘一次次周而复始与更新;这有多么美丽,这种人与动物、我与猫之间,与施瓦茨瓦尔德达成的默契。这只最笨的猫,却总是拥有最最美丽的情感,没有他我无法活。在我母亲去世时他为我把长衫扯成了丧服,为这个举动我要伺候它终老。施瓦茨瓦尔德衰弱不堪了,他已经跳不起来,只得由我把他举起,抱到怀里。他像一块黑色的抹布,像一条服丧用的手帕,像村妇的头巾。然而它的头总靠向我,那么长久,直到最后一天的到来。施瓦茨瓦尔德绝食了,他在饥饿中慢慢消耗着生命。我把他安置在绿椅子上,紧挨我的床。我入睡时,把自己的一只手伸给他,他的小爪就捧着我的手。我疲惫不堪睡着时,他用紧握成一团的小爪将我捅醒,于是我伸出第二只手,轻轻摩挲他的脑袋,他竟无力把头靠人我的手掌心了。于是我从他的小爪里小心抽出自己的手来,拉开了灯,施瓦茨瓦尔德已经死了。他一只眼闭着,另一只眼绿幽幽的,睁开着,呈惊恐状,展露出临死前目睹的恐怖情景。他死得不平和,犹如我的妈妈。我妈妈去世时对自己的年老色衰由恐怖转为愤怒,她不戴假牙,不染头发,饱经风霜,愤世嫉俗地挺立在那里,傲视这个世界,傲视我,傲视一切,因为她不曾像施瓦茨瓦尔德那样拥有我。没有大自然,没有上帝,她死得寂寞和孤单,尽管死在家人的身边,但在这个家她只在乎自己,也许她的作法自有她的合理性。我的黑猫施瓦茨瓦尔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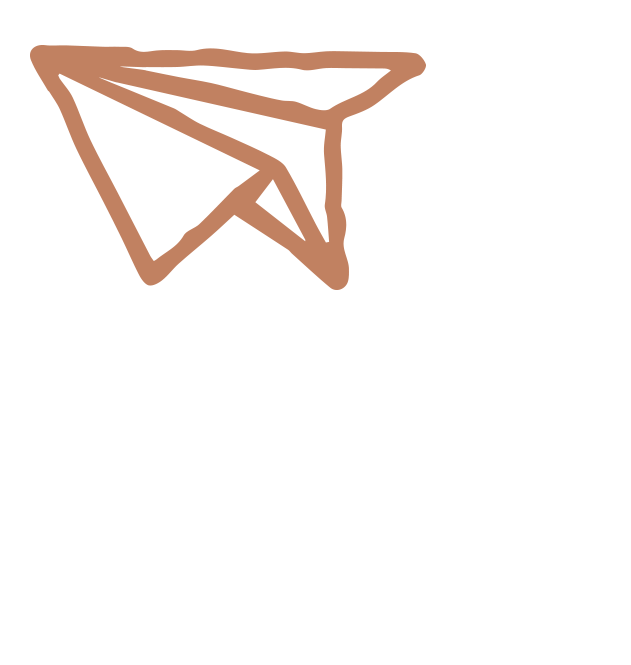
Hrabal,1914—1997),捷克著名作家,以其独特的叙述风格和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力闻名。这篇散文选自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赫拉巴尔散文集《我的世界》。原文并无标题。现标题由编者所加。这些生动自然的文字让我们感受到了赫拉巴尔对动物的细腻的情感。
原载于《世界文学》2006年第1期,责任编辑:高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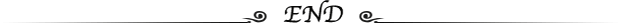
点击上图,订阅全年《世界文学》
点击上图,订阅单期《世界文学》

添加《世界文学》小助手
获邀进入《世界文学》分享会3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