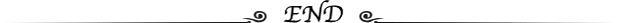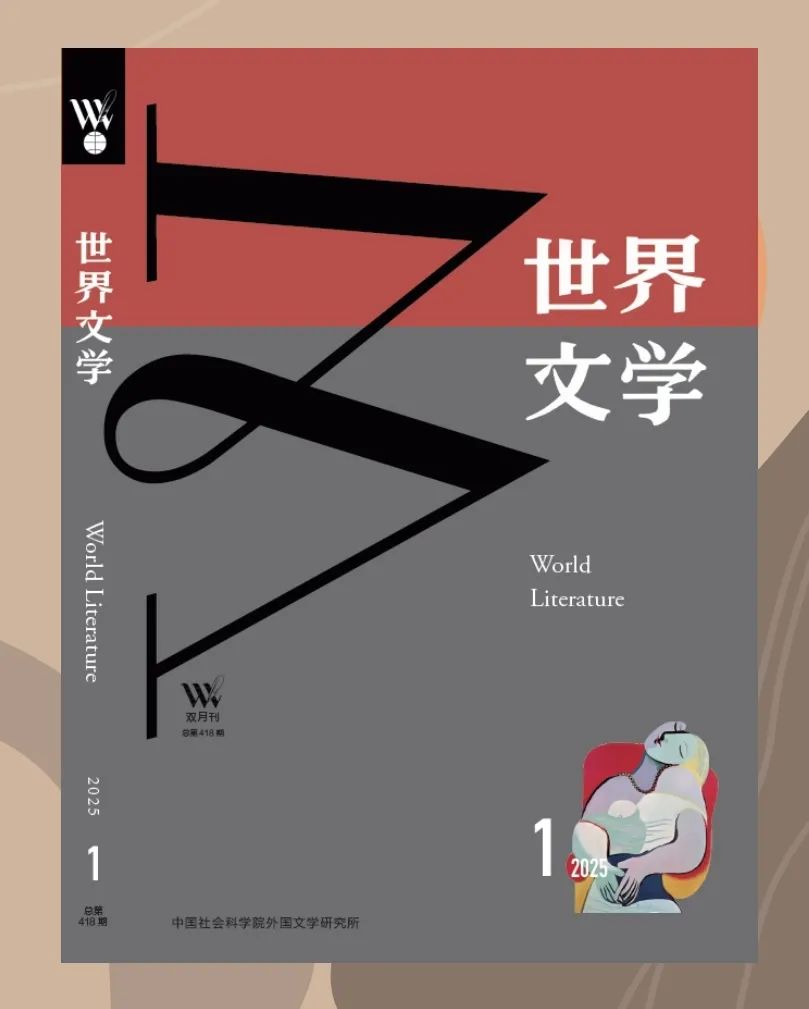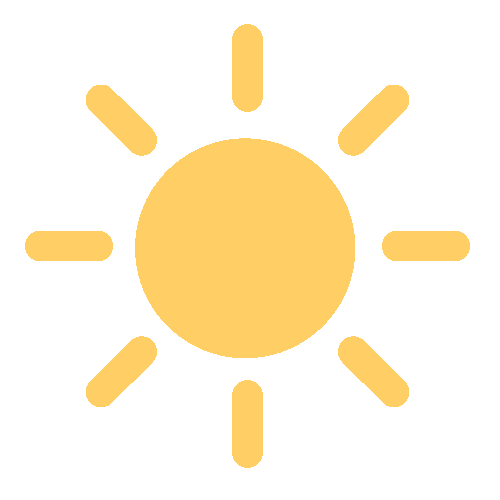读者来稿 | 倚水:“扭曲现实是尤为轻易的事情”——读皮托尔《梅菲斯托圆舞曲》
![]()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妻子迷失于现实与虚构之间,感受到丈夫在写作中传递的对激情和想象的永不妥协,进而对自己的婚姻危机产生了更加清晰的理解。她既是丈夫的“现实”的读者,又是丈夫的“虚构”的解读者……而对于皮托尔的读者而言,我们在阅读中也不自觉地具备了双重身份,即读者和解读者。如此,小说就具备了十足的张力,为我们留下了广阔的想象空间。
“扭曲现实是尤为轻易的事情”
——读皮托尔《梅菲斯托圆舞曲》
倚水
翻开2024年第5期《世界文学》,塞尔西奥·皮托尔这个陌生的名字首先出现在我的眼前。他是一名墨西哥作家,在2005年获得了西班牙语文学的权威奖项“塞万提斯奖”,翌年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所的邀请来中国做过一次演讲,《世界文学》也曾在2006年第2期中介绍过他。彼时的我仍在牙牙学语,如今再看到他的小说,不禁感受到时间的跨度。



《梅菲斯托圆舞曲》这篇小说并不长,阅读起来却相当困难。皮托尔讲述了一位妻子在丈夫发表的一篇名为《梅菲斯托圆舞曲》(这与这篇作品的题目一致,显然是皮托尔的有意为之)的小说中思考自己婚姻危机的过程;在阅读的过程中,她一眼就看出这篇小说写的是她之前和丈夫亲身经历过的一场音乐会,并由此时不时穿插自己对当下陷入的婚姻危机的反思。一口气通读下来,妻子和丈夫间的情感张力和内在矛盾一览无余:妻子对激情逐渐祛魅,对现实也持有务实态度,丈夫却对激情永不妥协,两人的情感危机已经不是表面上的分居能够解决的事情了。然而为了叙述这一看似简单的婚姻危机,皮托尔却以一种“元小说”的方式刻意地为其赋魅,让故事的层次感更加丰富,主旨更加复杂。
在小说中,一方面,妻子在刚开始阅读的时候就带着一种预设的立场:在此之前,丈夫从未发表过任何一篇未经她阅读的文字,而她确信,丈夫从来没把这篇小说给她看过或和她谈论过。她抱着复杂的心情进入这篇小说,试图寻找两人婚姻危机的原因;另一方面,在小说提到的音乐会——即演奏李斯特《梅菲斯托圆舞曲》的音乐会——中,身为作者的丈夫又“杜撰”了一个故事的叙述者(又是刻意的巧合,叙述者是一名墨西哥作家),让这位叙述者承担描写音乐会的任务。这在增加了妻子与这篇小说的距离的同时,也增加了读者与皮托尔写作的小说本身的距离。换言之,这里存在一个嵌套的双层结构:皮托尔“杜撰”了丈夫,而丈夫又“杜撰”了叙述者,到最后,小说中呈现出的《梅菲斯托圆舞曲》音乐会就与读者隔了两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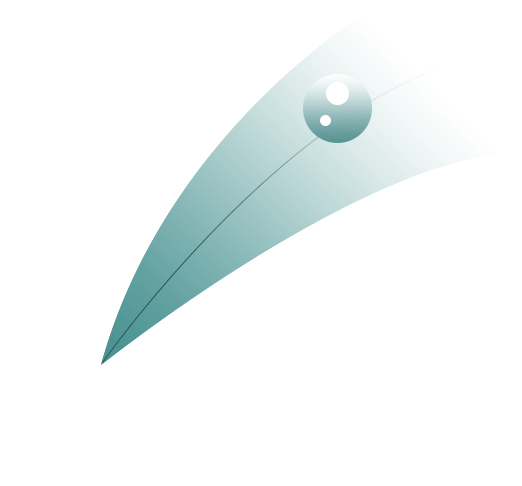

皮托尔大费周章地构建小说结构,显然不是单纯为了炫技。这种嵌套的双层结构让读者在现实与虚构之间迷失,甚至进一步让作品中的角色在现实与虚构之间迷失。对于妻子而言,音乐会是她经历过的现实,而“杜撰”的叙述者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构成了虚构。在叙述者的眼中,音乐会已经不再是丈夫和妻子的现实经历,不是那场能让妻子清清楚楚回忆起细节的演奏,而是弥漫着叙述者的想象的音乐会:比如,叙述者会在音乐会中揣摩某位观众席上的老人和台上的演奏者之间的关系,虚构出两人之间可能存在的羁绊,并进一步想象演奏者在演绎《梅菲斯托圆舞曲》时蕴含的情感——“嘲笑、讽刺和挑衅”。在叙述者对音乐会的描述中,到处充斥着他本人的想象;而在读完丈夫写的这篇小说之后,妻子并没有对叙述者的存在提出质疑,皮托尔的小说也就随着作品中妻子读完小说戛然而止。这或许说明,叙述者的声音不仅表达出丈夫对这段婚姻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叙述者的想象正意味着丈夫永不妥协的激情),而且越出了丈夫的“杜撰”,具备了自我创作的痕迹。这一点或许正是皮托尔在小说中交替呈现现实生活和虚构作品的尝试。妻子迷失于现实与虚构之间,感受到丈夫在写作中传递出对激情和想象的永不妥协,进而对自己的婚姻危机产生了更加清晰的理解。她既是丈夫的“现实”的读者,又是丈夫的“虚构”的解读者——作为前者,她对丈夫以及婚姻危机感受到的是不解;作为后者,她却逐渐认识到,在丈夫对婚姻的幻想和她的务实之间早已不知不觉地形成了一条巨大的鸿沟。而对于皮托尔的读者而言,我们在阅读中也不自觉地具备了双重身份,即读者和解读者。如此,小说就具备了十足的张力,为我们留下了广阔的想象空间。


作为小说标题以及小说中音乐会主题的《梅菲斯托圆舞曲》作于1861年,取材于李斯特最喜欢的一部文学作品——歌德的《浮士德》,而这首音乐是基于奥地利诗人尼古拉·莱瑙的《浮士德》中富有诗意的一个场景而作的。这个故事详细地记录在李斯特的乐谱上:浮士德和梅菲斯托进入了一家乡村酒馆,当时那里正在进行着婚礼。浮士德被拥有一双黑眼睛的美人迷住,梅菲斯托抓过一把小提琴演奏。舞者沉醉在魔鬼般的音乐中,婚礼集会变成了狂饮闹宴,疯狂的舞者跌倒在草地上,作曲家以双音的颤音表现了梅菲斯托回荡在空中那不断的笑声。最后夜莺的歌声唱起,强烈的欲望将他们击垮,他们淹没在像大海一样汹涌翻腾的感情之中。李斯特的这首乐曲充满了浮士德式的挣扎和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狂欢,而在小说中,这首曲子也代表了丈夫对激情的理解和追求。在丈夫创作的小说中,叙述者提到的“嘲笑、讽刺和挑衅”或许正是丈夫、也是皮托尔对现实婚姻中两人关系疏离且无解的隐喻。


2024年第5期《世界文学》选取了四篇皮托尔的小说,另外附上了西班牙作家恩里克·比拉-马塔斯为皮托尔小说集写下的序言《你让疯狂转了起来》的节选。这一题目来自西班牙当代诗人安东尼奥·加莫内达:“清醒的我原本盲目,但你让疯狂转了起来/一切都是幻想,一切都不受意义束缚”。马塔斯认为,在皮托尔的小说中,“扭曲现实是尤为轻易的事情”。确实如此,皮托尔的元小说试图将现实与虚构杂糅起来,在第一次进入的时候,我们在小说中见到的现实几乎是扭曲的,充斥着叙述者的想象。然而在认识到读者与解读者的双重身份,一遍又一遍地品味皮托尔的小说之后,这种扭曲的现实却更能透露出别样的醍醐味,我想这也正是文学的魅力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