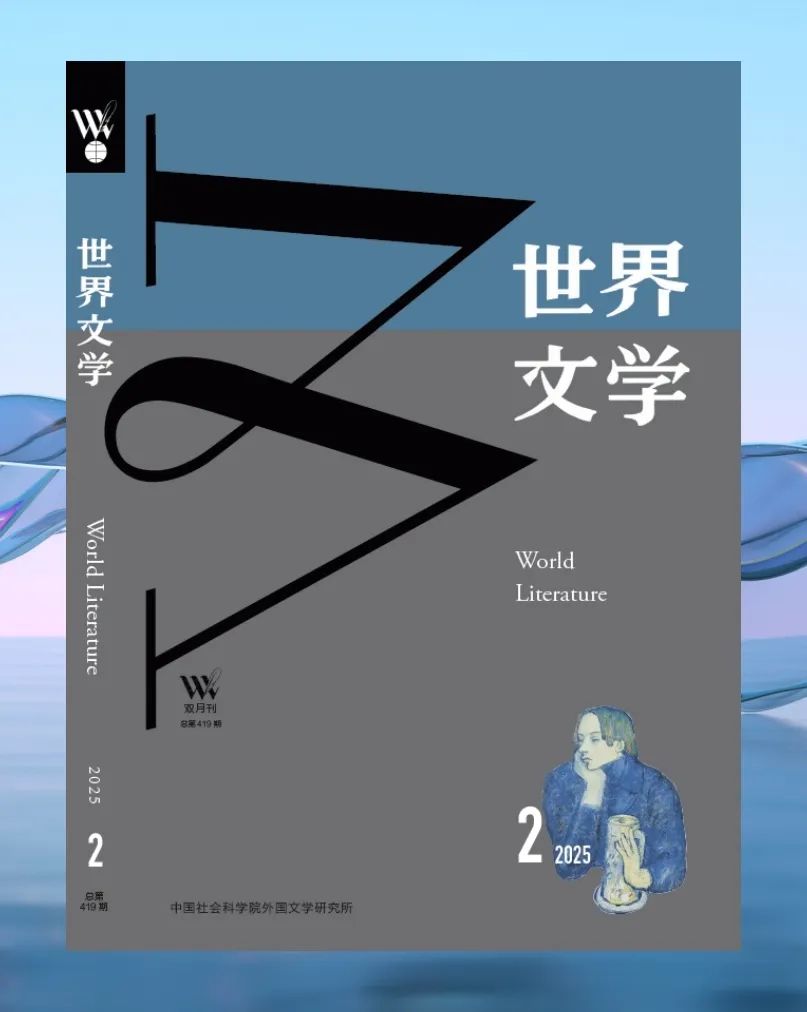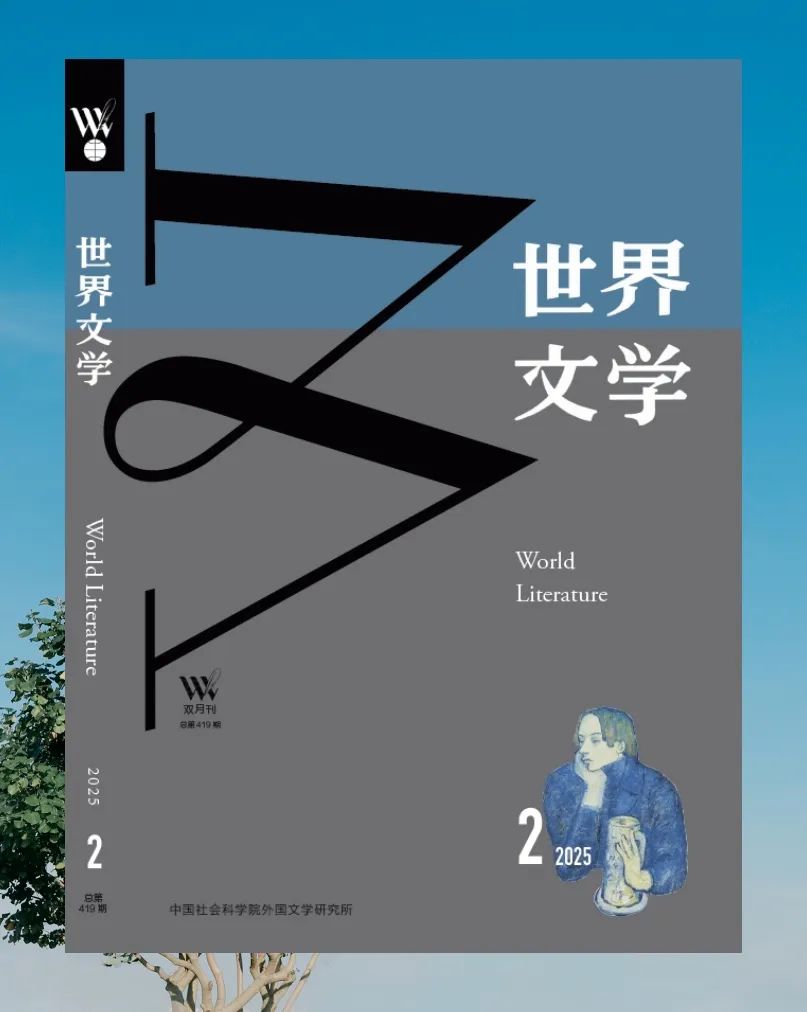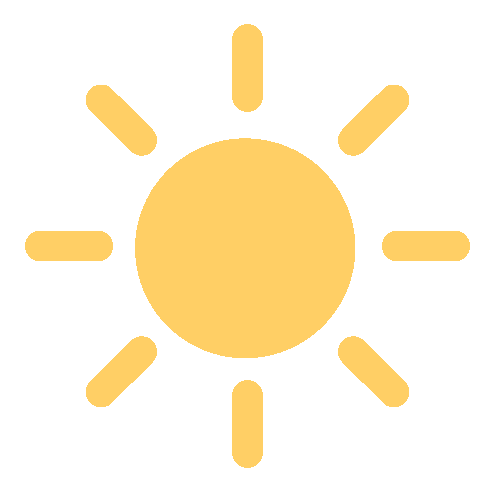第一读者 | 索•罗•帕佩【厄瓜多尔】:初次见鬼
![]()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索兰芝·罗德里格斯·帕佩作 刘浅若译
我们到达普利姆【美国内华达州小镇,距离拉斯维加斯64公里,博彩业发达】,用现金付了房费,尽量不和酒店前台的人有任何视线接触。为了办理入住,维柯决定戴一顶宽檐鸭舌帽,我则戴的是黑圆帽。在远西地区,这是常见打扮,毫不惹眼。希望前台别盘问我们,事实证明我们运气不错:当时已经是深夜了,接待的人筋疲力尽,查验工作也是应付了事。他们对现金付款没有异议,接过钱,清点,结束。完全没有核对身份的环节。
我避免在凌晨照镜子,那时我的样子总是糟透了,像我自己的百岁版本。不过这次,我抬起了眼,分外宽敞的大堂,我在其中一面玻璃窗里撞见了自己的镜像,奇丑无比。大概没人相信会有人爱我。


尽管一切进展顺利,我还是从一开始就感觉事情有些不对劲。酒店走廊像一只光怪陆离的丑陋铁桶,陈列着私人藏品——叫什么“北美死亡小博物馆”——展出武器和一些同系列的其他物什。我远远地能分辨出一架机关枪,一个满是破洞的车牌,一件血迹斑斑、撕得稀烂的男士衬衫。
“太吓人了!”我感叹道。
“这里的每家酒店都有自己的噱头,越抓眼球越好。”
维柯说得好像自己是拉斯维加斯的常客,其实他和我一样,都是第一次来。
我们重新拿起背包,就在这时,一位穿睡袍的女士飞快地跑过走廊,冲到了正在登记入住的顾客前面。跟在她后面追来一个也穿着睡衣、面色同样惊恐不定的男人。两人看上去像韩国人或者中国人——东方人的面孔总是很难辨别——说着一口奇怪的英语,时而里嗦,时而歇斯底里。大堂经理没听明白他们的意思,但眼见这场面很快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为了让大家保持冷静,他声明道:“女士,不可能!我们酒店没有鬼!”
房间在三楼,电梯坏了,我们走的楼梯。进门的时候,暖气还在给卧室升温,不过,那时我总觉得,很快就会暖和起来,没什么大不了的。整个套间一片昏暗,只有床头柜那里透出一点亮光。把行李放下以后,就是我最爱的环节:维柯允许我在他淋浴的时候坐在地上窥视他,如同一个秘密崇拜仪式——出于某种原因,我们更喜欢分开洗澡。对我来说,看见他赤身裸体依然很新鲜。透过磨砂玻璃,我看着水从他赤裸的身体上流下来,精瘦的小腿,修长的身形,突出的脊椎骨向上延伸,这一切都让我感到惊奇。我出神地看着,自问他身上究竟什么东西令我迷恋?答案随即浮现——或许来得太迟了一点——是他的美,他的美。
他洗得很慢,肥皂打过骨盆、屁股和前胸,带着刻意的性感,还时不时地向我投来漫不经心的慵懒目光。当时我就该明白过来的。我本该幡然醒悟,却过分沉溺于周遭的新鲜事物:公路尘土飞扬,把地平线切成两半;他的肚脐微微凸起;半梦半醒间,他把我的手掌放在自己的胸膛上,说这就是我在世界上的位置。
我在凌晨三点惊醒,像是刚从水底下冒出头,喘不上气。我确信有人在浴室里翻东西。一开始我觉得可能是亚当,也许他一路跟踪我们,或者雇了人来抓我们——不可能……亚当是个十足的胆小鬼。恐惧令我浑身发麻,而你,浑身赤裸,置身事外,舒展而坦然地睡着,年轻的皮肤上布满细细的绒毛,仿佛刀枪不入。就算此刻死亡降临,我最后看见的形象也会是你,维柯,恬静温和,双臂展开,如基督圣体。
“维柯,”我在他耳边轻声说,“浴室里有人。”
他起身去察看,浴室并无异样,我们扔在地上的湿毛巾也还在原处。
“睡吧。”他嘟哝了一句。
我心绪难平,想枕着他的胸膛求得安慰,他却翻了个身,背朝着我。
我感到孤单。
一路上,有个句子在我脑海里反复盘绕:我不想待在这里。万一什么地方出错,我怎么办呢?我揉了揉额头,想把这句话赶走,可是这个念头像一粒种子,不受控制地长大。我反复咀嚼着它那苦涩的果实,最后咽了下去。我伸出手臂环住维柯,把他的阴茎放在手中,感受着它像一个娇弱的生灵,此刻也只想睡觉。
“都会顺利的。”维柯喃喃道,“明天我就打电话。”
“别打电话,我们可以另找办法到利伯缇【作家本人表示,本篇中的“利伯缇”并不指具体城市,而是一种象征】去。别打了,别打了……”
“已经过去一天多了,现在大家应该在找你。”
“他大概觉得我还在气头上,所以搞离家出走这一套吧。你别打电话。”
“我明天就打,这事情很简单,我们不是都排练过了吗?台词,说话的语气……”
“别打了。”
“你后悔了。你不想和我在一起了。你觉得我会崩溃,觉得我会表现得像个毛头小子。”
“他们会报警的。”
“他们没这个胆。那人就是个懦夫。所以你才离开他的。”
“你再告诉我一次,利伯缇真的存在。”
“我祖父住在那里。一个安宁的地方,牧场,迷雾。我们会一起做面包,开始自己的生活……”
“还有你对我说的那件事……维柯,你杀过人,是吗?”
“是的。”
“你不怕吗?”
“不怕。我尝了他的血,就感觉不到害怕了。”
“真的吗?你从来都没害怕过?”
“亲爱的,害怕什么?”
“怕鬼。”
“这个世界上没有鬼。”
沉默。
“维柯?你睡着了吗?”
我在清晨六点醒来,双腿麻了,因为不习惯紧挨着另一个人侧身睡。此刻,我的一切都脱离了惯常。透过惺忪的睡眼,我瞥见床头柜的抽屉是开着的,便把手伸过去。木头粗糙冰冷的质感让我清醒了几分:我记得自己昨晚把抽屉关好了。衣服掉在地上,手提包也被动过了——我记得昨晚都放好了。维柯翻了个身朝向我,和缓地呼着气。


我轻手轻脚地起了床,在房间里转了几圈,终于彻底醒过来了。天亮了,恐惧就散去了,所有常与黑暗携行的疑虑不复存在。也许,真的都会顺利的。为什么一切不会像我们计划的那样发展呢?我们看了那么多侦探节目,学会了如何小心行事。就算拿不到赎金,手头也还有一点钱。我不管账,这些都是维柯在操心。
晨光钻进房间,透亮澄澈的天气,好兆头。我想,似乎不该一整天都躲在暗处。我去浴室草草洗漱了一下。如果说凌晨归来的女人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那么到了拂晓时分,她们总是显得疲惫不堪。至于维柯,二十三岁的他最近才开始意识到时间是魔鬼。我离开房间时,他还在睡觉——小狗总是需要充足的睡眠。
“北美死亡小博物馆”里反复播放着一段视频,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我从中得知邦尼·帕克【邦尼·帕克(1910—1934)和克莱德·巴罗(1909—1934)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雌雄大盗】——这个家喻户晓的女犯,在疯狂的二十年代曾让整个美国为之倾倒——还写诗。在留给母亲的几行诗里,她写道,灾难降临之前,五十几发子弹击穿亡命天涯的生活之前,克莱德是个好人。她初见他是在一个女友家中。两人一见如故,整个下午都在谈论戴·赫·劳伦斯。据邦尼后来回忆,她觉得克莱德是那种可以一同描绘未来蓝图的男人。两人计划去海边旅行,随即抢劫了一家加油站。邦尼的个头比克莱德高,但一直很瘦,所以克莱德喜欢把她高高举起,留下过许多广为流传的照片——后来联邦调查局正是靠这些照片展开了抓捕行动。
邦尼和克莱德太出名了,尽管有钱,却无处可用。每杀掉一个警察,就多一群崇拜者,真正的朋友却越来越少。一个熟人向警方暴露了他们的行踪,从那一刻起,包围圈迅速收拢。临死前,邦尼正在吃三明治,警方布下的埋伏让她甚至没时间掏枪。一枚子弹正中眉心,另一枚穿透咽喉。而克莱德的尸体则浮夸地躺在人行道上,头发被鲜血浸红。围观人群一认出他们是谁,就开始大肆搜刮遗体。他们抢走了鞋子、腰带、帽子,扯下一撮撮头发。警察不得不出手推开一个穷鬼,因为他试图把两人的耳朵割下来。
最后,邦尼几乎完全赤裸。他们给她拍了很多很多照片,全都归档在案宗里。照片上她骨瘦如柴、满是窟窿的身体,像一具人体标本,足以当珍奇展品卖给畸怪博物馆。邦尼只是一个拥有过传奇爱情的寻常女人,只是这段罗曼史把她的人生变成了灾难。
据说,她从未谋杀过任何人。
还有人说,她常在那些入住汽车旅馆的情侣面前显灵。真是一派胡言。
我怀着悲伤的心情想着这一切,再次确认了酒店里的氛围真的很奇怪,虽然说不出究竟怪在哪里。这里住着人,却显得十分荒凉。要知道,那些坐在几百台机器面前、几乎一动不动的赌徒,只专注于眼前这一件事情,要么是彻夜坐在这里,转动着老虎机的操纵杆,灌下一口又一口掺了水的鸡尾酒,膨胀的欲望滋养着贪婪的赌神,要么是天没亮就爬起来接着赌——对赌博的狂热搅得他们无法安睡。
这个酒店徒有其表,中年女侍应拉跨着脸,头戴炫目假发,在昏暗的灯光下来来去去。没错,普利姆就是用旧了的拉斯维加斯。这里的陈设铺张又失调,叫我反感,而且,我确信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我在大堂里晃荡,从一个废弃的吧台顺走一瓶矿泉水——竟然标价八美元,不要脸——接着,围观了一轮“21点”牌局。场上仅剩的两个玩家出牌很慢,深思熟虑。我本想借此转移注意力,却还是忍不住去想今早维柯就要给我家打电话了。我并不打算上楼查看他,却又渴望此刻自己身在房间,和他一起钻进被子。
人们总说女人到了一定年龄,就再也做不出什么重要决定或是改变自己的生活了。那他们可得看好了,我要给他们上一课:每当想起那个甜言蜜语又爱吹牛的男孩,我心底的灰烬还可以重燃爱火。他最终说服了我跟他走。那个孩子如此莽撞,第一次做爱的时候甚至连脚上的脏球鞋都没脱掉;笨手笨脚,对我来说却无可替代,因为他有一颗小象般温柔的心。
我盯着台上蹦蹦跳跳的舞女看了一会儿。她们和那些给客人端烈酒的女侍应一样上了年纪,根本无人在意。紧身上衣和五颜六色的超短裤都没能让老虎机前的赌徒们抬头看一眼。无论放什么音乐,舞女们都自顾自地弯腰、张腿、摇摆,动作机械。这首歌快放完的时候,我和其中一个舞女的目光撞到了一起。我礼貌地笑了一下,她没有回应。
这里一切都很诡异,我说了很多次了,我也想换一个形容词,但也许是先入为主吧,蹲守在毗邻拉斯维加斯的荒凉小镇,准备向丈夫勒索赎金,这种处境本身就不正常。就在这时,最诡异的事情发生了。我感觉此前的一切都是为了把我带到那里。我看到拥挤的大厅右边角落里有台装置——玻璃罩子里摆放着一个面带笑容的独眼老牛仔人偶,他的头顶上用油漆写着:“去问爸爸。”
旁边的装置像一台发光的乒乓球桌,刻着深紫色的“塔罗占卜”字样。桌子中央有个小轮盘,塑料指示灯的蓝光依次把上面贴的彩色画片照亮:倒立的男人,水中的月亮,骑马的小男孩……图案不断变幻。我像中了魔似的,迅速按下了面前唯一一个按钮。


装置沉默了几秒钟,随即旋转起来,弹簧嘎吱作响,仿佛自创世之初就不曾运转过。一连串“咔咔”的撞击声后,指针猛地停在一个轮盘图案上,上上下下的神奇动物也随之停驻在画面上的天空里【命运之轮是塔罗占卜的牌面之一,牌上画有天空中的轮盘,周围有一些神奇动物】。
“这东西早就坏了。”我背后的一个声音说道。
是那个戴着假发的侍应,一个穆拉脱【黑人和白人的混血儿】女人。凑近了看,她的眼角和额头已经有了皱纹,不过,这些混血女人一过中年,实际年龄就变得神秘莫测:可能是三十岁,也可能是六十岁。她可能来自哥伦比亚或者古巴,对我说的是西班牙语——拉美人就是这样,无论在美国待了多少年,一有机会总会讲回母语。
“它指着画着轮盘的牌。我看不懂。”我说。
“牌面是给你的预言。”
“可是它什么预言也没给啊。你知道这张牌是什么意思吗?”
“塔罗很复杂的,一张牌说明不了什么,你得再来一张。”
我又按了几次装置上的按钮,可它就是不肯再转了。
“这张牌可以单独解释吗?”
她把手里的托盘放到一边——上面放着没喝完的酒杯和烟头——严肃地看着我。
“你是真的信这些东西吧?”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那张牌是命运之轮,象征着一切皆可发生,所有道路都向你敞开。祸福相依,皆由天命。但要记住,死亡也是其中的一种可能性。”
“一切皆可发生。”我重复道。
“没错。你逃来这里,来这里的所有人都是逃亡者。但有时候,人们看似在前进,实则只是无处可去。你看——”她指向台上一个正在表演的舞女,“我们都想出名,可是大多数人连拉斯维加斯都到不了。”
我对此表达了真诚的遗憾。
“没关系,至少我还有份工作,有地方住。”
我本想说我的情况没那么凄惨,至少有人爱我,但我没说出口。
“最重要的是你得明白,你的命运并不取决于别人。你的人生完全是你的。如果让别人决定你要怎么活,你就会被怨恨缠身,鬼就会缠上你。”
我想起了那两个在前台争论的韩国人,还有我的手提包以及凌乱的衣服。
“这家酒店真的有鬼吗?”
“当然,所有的酒店都有鬼。”
她重新端起托盘去工作了。我拿起她忘在桌上的一杯蓝色鸡尾酒慢慢喝着,味道甜美。
我上了楼,发现维柯已经不在房间里,也没给我留下任何纸条。我猜他是打电话去了,不出半小时就会回来。我本想再和他排练一遍,由我来假扮亚当。我们策划了各种各样的回答,但其中并不包括威胁和粗话。如果不得不来硬的,维柯有几个朋友会去收钱,再把钱转给我们。我们会远走高飞,到利伯缇去……新生活近在咫尺。此刻,我在这家床单破烂、地毯脏污的酒店等待着,但已经可以看到未来的模样。
我在镜子前用手梳了梳头,手指间留下几缕发丝,不少发根已经白了。我老得很快,但我宁愿相信人到中年依旧能够像正午的太阳那样炽热。我冲了澡,用几块湿得不算太厉害的毛巾擦了擦身体,然后从小冰箱里拿出一小瓶威士忌,放了两部威尔·法瑞尔【威·法瑞尔(1967—),美国演员、编剧】的电影,等着维柯回来。尽管很饿,我却不肯离开房间:万一维柯回来的时候我不在呢?我取出冰箱里最贵的食物,又开了一瓶龙舌兰酒。三个小时过去了,胃里那令人不安的感觉有增无减。自从我们来到这个破地方,我就产生了一种预感,它从我身体内部蔓延开来,此刻我终于接受了它。
看完两部糟糕透顶的电影,已经是下午六点了,我终于打开了衣柜门。维柯的包不在了。我的胸口如遭重击,颤抖着拿过自己的背包,发现那个装着美元的信封也不见了。他打电话了吗?维柯,绕了这么一大圈,不过是为了这点东西。那个女人说得对,有的人连拉斯维加斯都到不了。
我坐在地板上,一片茫然。或许这是个误会,房门随时可能打开,维柯会带着好消息走进来。
又或许,什么也不会发生了。
我把冰箱里剩下的酒水喝了个精光,然后大概是睡着了。
再次醒来的时候,我确信房间里有人。电视机底下的电子钟显示晚上八点。刹那间,我清楚地看见一个发白的身影停在我面前,看起来像是要穿衣服或者脱衣服。他高高的,瘦瘦的,难以捉摸。维柯,我声音发颤地喊道,心底一下亮起来。但是,我马上发现他不是一个实体,紧接着,几秒钟内,他就化作几缕空气,房间里只剩下我的心脏狂跳的声音。
我拧开床头灯。维柯没有来,他不会来了。他躺过的地方只有孤独感继续停驻。我拖延了很久,大概一个小时,才敢重新把灯关上。也许遇到这种事本该感到恐惧,但我并不害怕,只是伤心至极。我无法入睡,夜还很深。
平日里,我迷迷糊糊打着瞌睡的时候会想着维柯,耽溺于他美好的肉体。此刻,我不再想着要到达任何地方了,我问自己,睡前该想点什么呢?我找了一个最舒服的姿势,头冲着门,躺下了。
一片黑暗中,就在门前,一动不动却分外清晰,我无比确信,我看到了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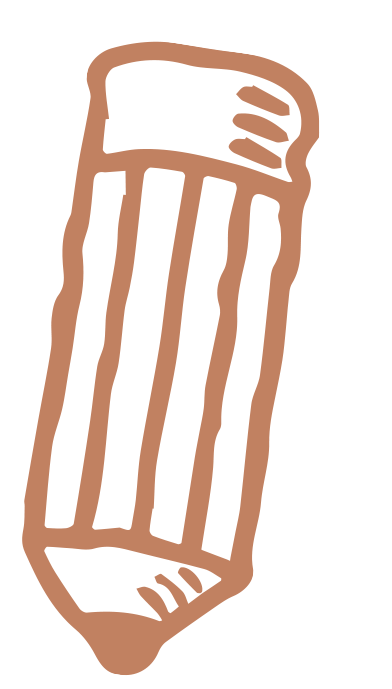

索兰芝·罗德里格斯·帕佩(Solange Rodriguez Pappe,1976—)是厄瓜多尔小说家,有瓜亚基尔土著血统,至今已出版十余部作品,曾获厄瓜多尔国家短篇小说奖和2010年华金·加列戈斯·拉腊文学奖(即年度最佳图书奖),多篇作品被译成法语和英语。《初次见鬼》(La primera vez que vi un fantasma)选自Candaya出版社于2018年推出的同名短篇小说集,已获作家授权。小说构建了一个大卫·林奇式的梦境空间,亦幻亦真,充满隐喻,主人公在逃往“自由”的途中,与内心的鬼魂打了初次照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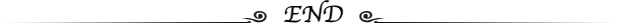
点击上图,订阅全年《世界文学》
点击上图,订阅单期《世界文学》

添加《世界文学》小助手
获邀进入《世界文学》分享会3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