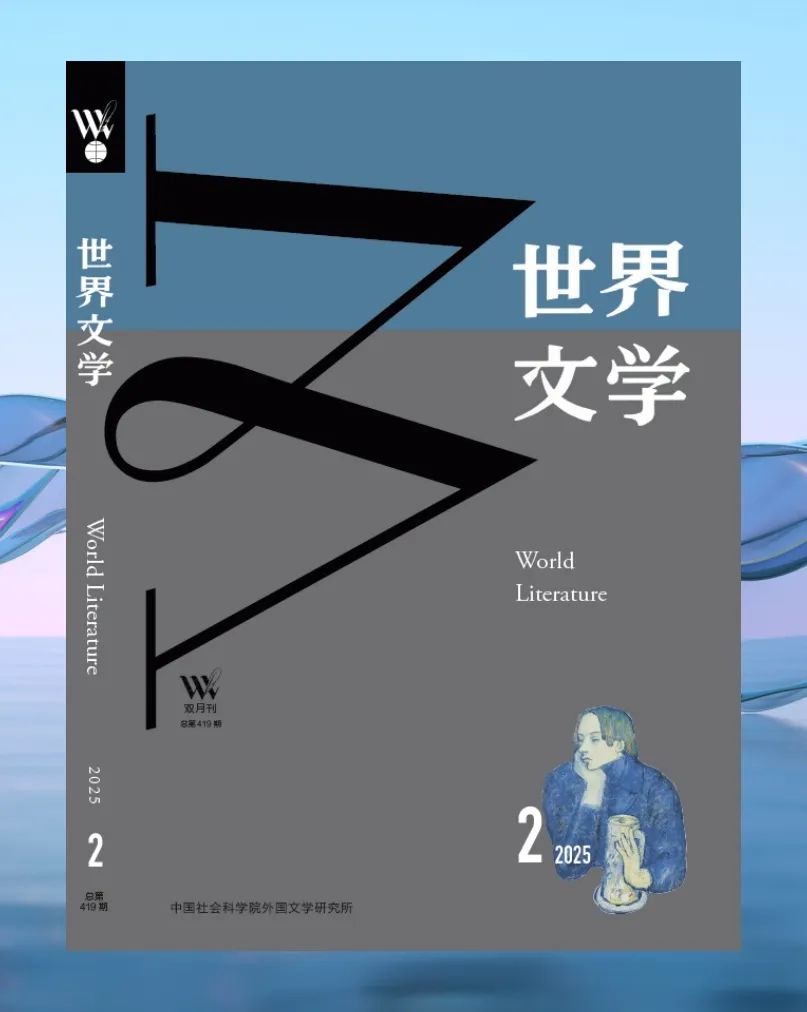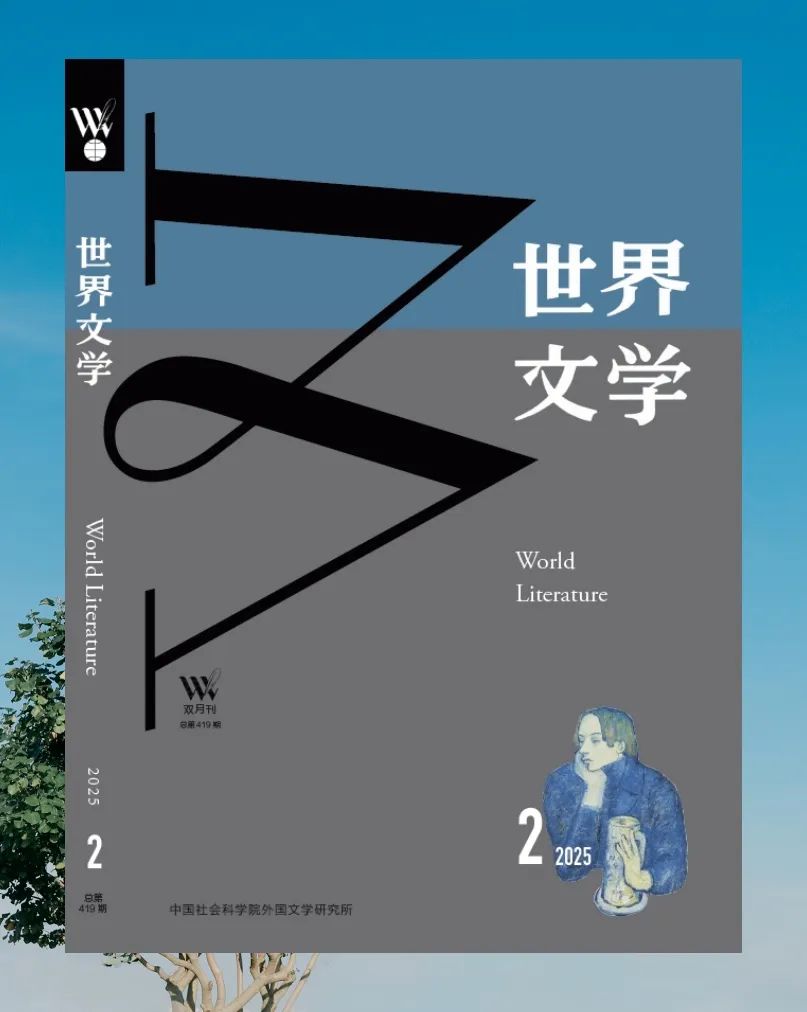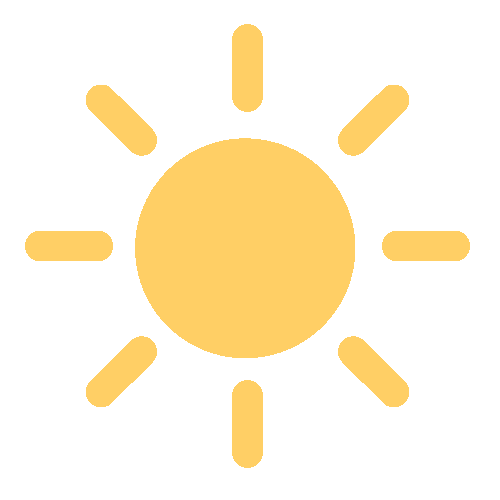纪念林洪亮(1935—2025)| 林洪亮【中国】:诗译者的名字及其他
![]()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林洪亮(1935—2025),资深翻译家、学者。长期从事波兰文学翻译与研究工作,著述和翻译共计七百余万字。专著有《密茨凯维奇》、《显克维奇》、《肖邦传》和《波兰戏剧筒史》。翻译的作品有《你往何处去》、《十字军骑士》(上、下)、《火与剑》(上、下)等。曾荣获波兰总统颁发的“共和国十字骑士勋章”,2019年获“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2000年,社科院外文所举办“外国诗歌翻译研讨会”,下文由林洪亮先生的会议发言整理而成。原载于《世界文学》2001年第2期,今天在公众号推出,以此纪念这位优秀的翻译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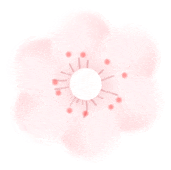
林洪亮
我是从事波兰文学研究和翻译工作的,诗歌翻译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波兰是个诗歌之邦。从中世纪第一首用波兰语写成的《圣母颂》问世以来,波兰诗歌的发展迄今已有五百多年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诗歌不仅在波兰文学中占有重要位置,就是在波兰社会生活和民族意识中也具有特殊的意义。波兰流传着这样一句谚语:“国家不幸诗歌兴”,也就是说,每当波兰国家和民族遭受危机或灾难时,这时的波兰诗歌创作便显得特别的活跃和繁荣,而且波兰人也总是在历史危急时刻到诗歌中去寻求慰藉和激励的,因此,波兰诗歌便显得丰富多采而富于爱国主义和民族特性。诗歌在波兰文化中的突出地位,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波兰的特点。波兰还流传着这样一种不乏真实性的趣谈,说波兰文学与法国文学的最显著的差别就在于:法国每年出版三百部小说和三十部诗集,而波兰却恰恰相反。最近二十年来,世界诗坛都在哀叹“诗歌不景气”,波兰却有两位诗人——米沃什(一九八〇)和希姆博尔斯卡(一九九六)——先后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波兰诗歌创作的蓬勃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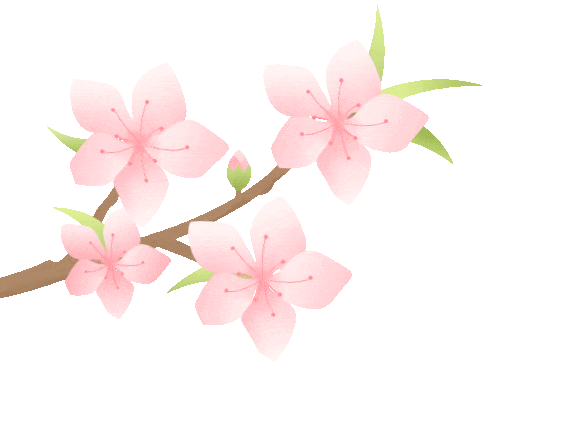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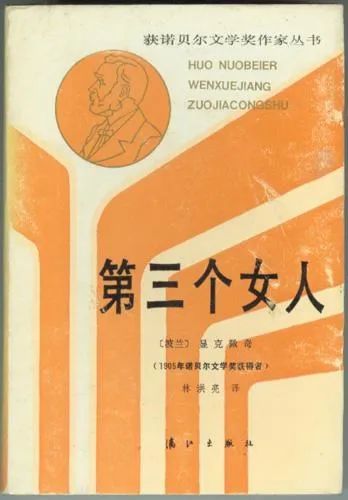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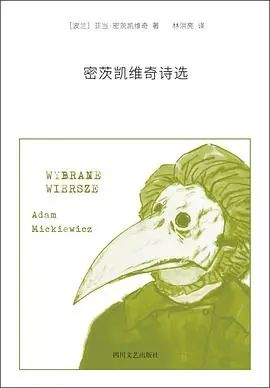
诗歌翻译是一种再创作,也是一种相当困难的工作,它与译者的水平、修养甚至性格都有一定的关联。由于两种语言文字的不同,诗歌翻译就必须兼顾这两种语言文字的特点,因此我认为,诗歌翻译很难做到完全真实,也就是说,不能照搬原诗的音节、韵律和外在形式,不能拘泥于一字一句的直译,必须经过译者参照中国诗歌的特点加以处理,读者读起来才会觉得有诗味。但也不能随意增删或改变其内涵,不能像实验派戏剧导演对待经典戏剧作品那样大刀阔斧地增减,而应像演员扮演戏剧角色或演奏家演奏大师的乐曲那样,有自己的诠释和个性,但又不脱离原作的内容、形式和风格。诚然,译诗要达到“形神兼备”的程度是相当困难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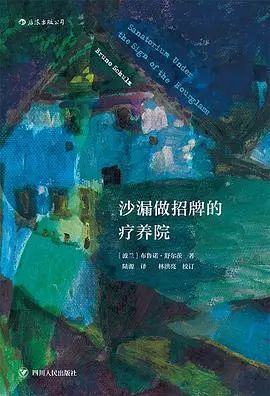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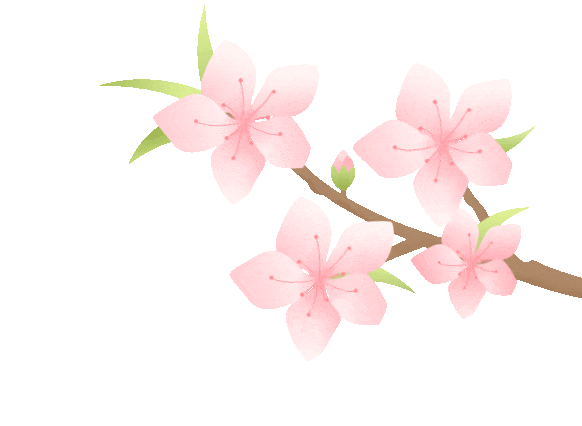

许多同志谈到现在对诗歌翻译的不重视、对译者的不尊重,这种现象是存在的。最近我到音乐堂去听了一场外国诗歌散文朗诵会,会上朗诵了外国诗人和作家的十多篇作品。在节目单上和主持人的介绍中,有作者和朗诵者的姓名,惟独没有译者的名字。我想这些作品不会是朗诵者或主持者所翻译的,即使是他们的翻译也应该提及他们的名字,何况在我听来,它们大都是出自名家的名译,不提这些译者的名字是不应该的。至于我国诗歌翻译作品的出版,最近这十年的确没有前十年那样红火,许多出版社怕亏本都不愿出外国翻译诗集。不过我还是比较幸运的,近三年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易丽君和我合译的密茨凯维奇长诗《塔杜施先生》,漓江出版社出版了我译的希姆博尔斯卡诗文集《呼唤雪人》,这说明一些重要出版社对于介绍外国诗歌还是重视的。但是现在我想要谈的是另一方面的问题:我认为,中国文学要走向世界,要得到世界应有的重视和评价,必须重视中译外的工作。我们国家的外文局、外文出版社也组织了一些中国作家作品的翻译、出版,但数量有限、推广也受到限制。我觉得我们国家应更加重视外国的中国文学翻译家的培养和扶持工作。国外的确有一批汉学家,但大多从事学术研究或教学工作,真正从事文学翻译的人却不多。在这方面,我们的文化部门,我们的大学都是有许多工作可以做的,东欧一些国家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比如波兰,过去每年暑假都要举办波兰语文进修班,邀请外国的波兰语文工作者参加,以提高他们的波文水平。波兰还设有专门机构,负责与外国的波兰文学翻译家建立经常联系,每人每年还获得赠送的三种文学期刊,外国的翻译家一旦做出了成绩,翻译了波兰的文学作品,波兰政府的文化部便会授予其“文化功勋奖章”,尽管没有物质奖励,但这种颁发奖章也是一种嘉奖和鼓励。表明他们对外国翻译家的重视,对其文学作品在外国传播的重视。
二〇〇一年一月五日改写
原载于《世界文学》2001年第2期,责任编辑:李政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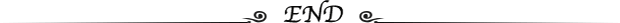
点击上图,订阅全年《世界文学》
点击上图,订阅单期《世界文学》

添加《世界文学》小助手
获邀进入《世界文学》分享会3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