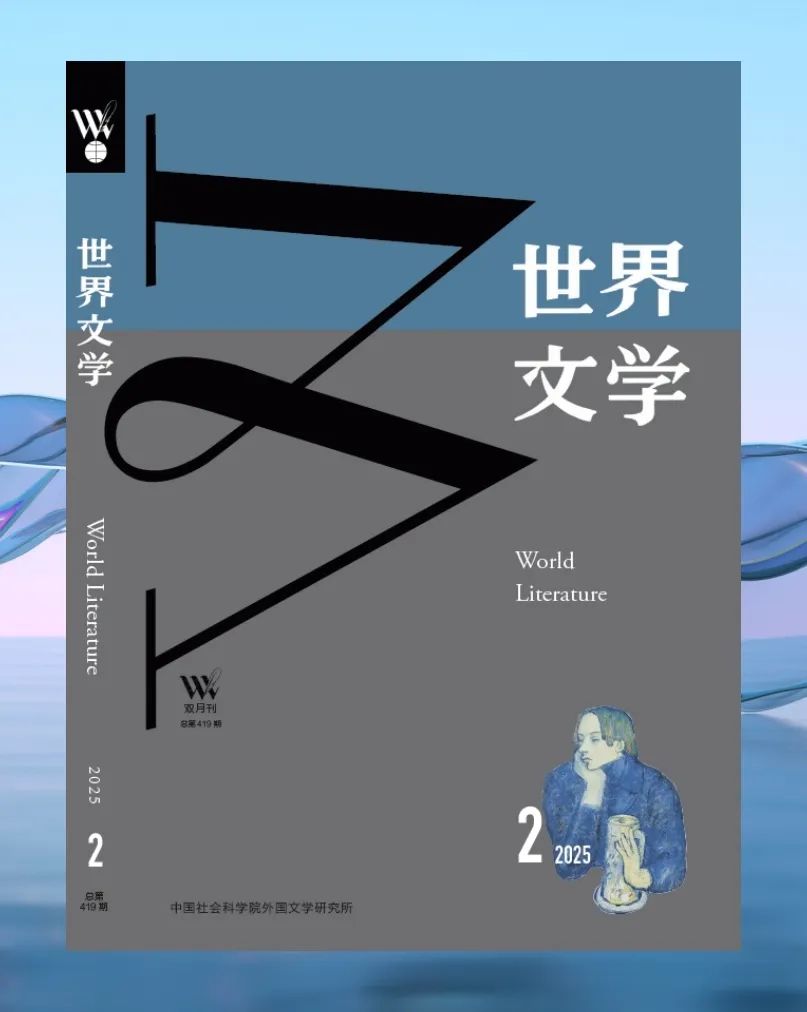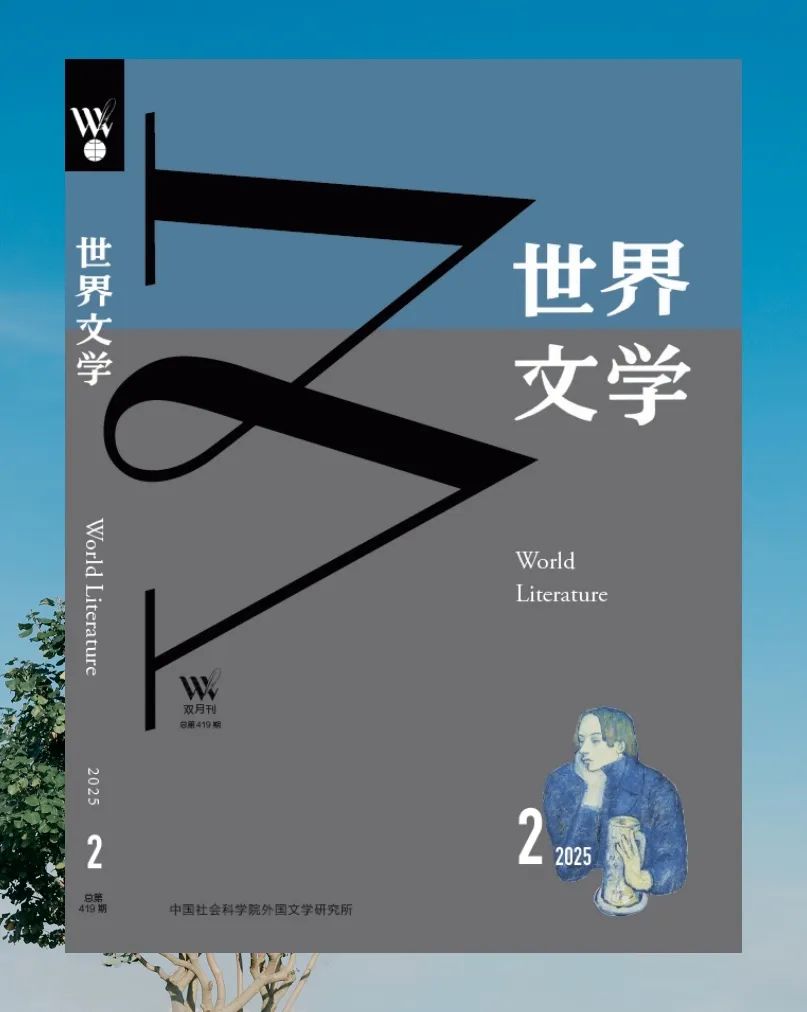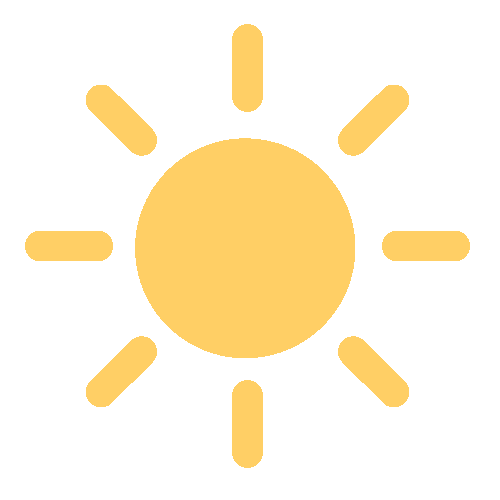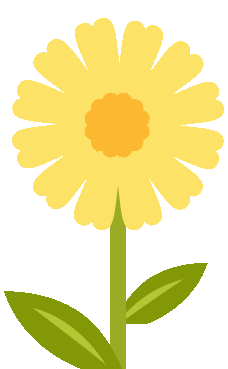第一读者 | 韩江【韩国】:光与线——韩江获奖演说
![]()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韩江作 薛舟译
去年一月,搬家整理仓库的时候,突然冒出一个旧鞋盒。打开一看,里面有十几本童年时代写下的日记。在摞起的日记中,我发现了一个薄薄的骑马钉本,封面用铅笔写着“诗集”两字,五张A5大小的粗纸对半折叠,用订书机给装订成了小册子。题目的下面,并排画着两条歪歪扭扭的线,一条是六段线,从左往上,一条是七段线,从右往下。那是某种封面插画吗?抑或只是信手涂鸦?小册子的封底,写有一九七九年的字样和我的名字,内文有八首诗,和封面的题目一样,都是端端正正的铅笔字迹。每个内页下端,则按照时间顺序填写了不同的日期。在八岁孩子天真而笨拙的句子中间,一首标记着四月某日的诗歌映入我的眼帘。开头两句是两个对仗句:
爱在哪里?
爱在我怦怦直跳的心里。
爱是什么?
爱是连接我们心灵的金线。
隔着四十多年的岁月,我突然想起制作小册子的那个下午,想起圆珠笔套里的铅笔头和橡皮擦的粉末,以及从父亲房间里偷拿来的铁制大订书机。听说我们即将搬到首尔之后,我就惦记着把过去写在纸片上的、写在笔记本和习题集空白处的、随手写在日记本里的诗歌收集起来。我依然记得当时的心情,《诗集》做完之后,绝不向任何人展示。
我把日记本和小册子原封不动地摞回鞋盒里。合上盖子之前,我用手机拍下了写有那首诗的一页。因为我觉得,那个八岁孩子使用的词语和现在的我之间有一种连续性。在我们的心与心之间,有一道连接着的金线。那是一道散发着光芒的金线。


*
十四年后,我发表了诗歌处女作,第二年,我又发表了短篇小说处女作,成为“写作的人”。又过去五年,我出版了耗时三年多时间完成的长篇处女作。虽然我喜欢写诗,也喜欢写短篇——现在依然喜欢——但对于我而言,创作长篇小说还是有着别样的诱惑。写长篇,短则一年,长则七年,我拿出了相当多的个人生活予以交换,说明工作有它吸引人的地方。借助写作,我得以进入到重要而切实的问题中,我决定接受这样的交换。
每次创作长篇,我都会忍受各种问题,并寄居其间。快要抵达这些问题之时(并非找到答案之时),也正是我写完小说之时。此时的我,不再是刚刚开始创作时的我。在写小说的过程中,我变了形,从这个变了形的状态中再重新出发。问题接踵而来,像链子,像多米诺骨牌,重重叠叠,连续不断,我又开始创作新的小说。
第三部长篇《素食者》写于二〇〇三年到二〇〇五年间。那段时间,我停留在几个痛苦的问题里。一个人可能成为全然纯洁的存在吗?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拒绝暴力?我们拒绝从属于人类这个物种会发生什么?
女主人公英惠为了反对暴力而拒绝肉食,最终竟相信自己变成了植物,除了喝水什么都不吃。她为了拯救自己而处在速死的反讽之中。事实上,这可以看作是两位主人公英惠和仁惠姐妹无声的悲鸣,她们终于通过噩梦和破碎的瞬间融二为一。在小说的世界里,英惠渴望活到最后,最后的场景也是在救护车里。救护车在绿色火焰般的树木间奔跑,清醒的姐姐目不转睛地盯着窗外,好像在等待答案,又好像在抗议什么。整部小说保持着这种提问的状态。凝视和抵抗。等待答案。
后来的小说《起风了,出发吧》沿着这些问题继续前行。人不能为了反对暴力,拒绝生活和世界,我们终究不可能变成植物。那我们又该如何前行呢?在这部推理形式的小说中,正体和斜体句子相互较劲,摇摆不定,女主人公长期与死亡的阴影作战,为了证明朋友的猝死不是自杀而用尽了力气。最后写到她竭尽全力爬出死亡和暴力的样子,我也质问道:难道我们不应该活到最后吗?难道我们不应该用生命证明真相吗?
第五部长篇《失语者》又在这个问题上继续前行。如果说我们真的要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什么地方才有这样的可能呢?失语的女人和逐渐失明的男人,在各自的沉默和黑暗中孤独前行,然后发现了彼此。创作这部小说的时候,我想专注于触觉的瞬间。在沉默和黑暗中,小说缓慢前行至这个场景——女人剪短指甲的手在男人的手心里写下了几个单词,两人在永恒般膨胀的瞬间光芒中向彼此展示了自己的脆弱。写的时候我就想问:通过注视人类最脆弱的部分——抚摸那不可否认的温暖——我们就可以在这个虚无而暴力的世界上活下去了吗?
我在这个问题的尽头想象接下来的小说。那是出版《失语者》后的二〇一二年的春天。我想写一部朝着光和温暖更进一步的小说。我要用明亮耀眼的感觉为这本拥抱生活和世界的小说充电。拟好题目后,我写了二十多页,然后停了下来。我意识到,内心深处有什么东西正在阻碍我的写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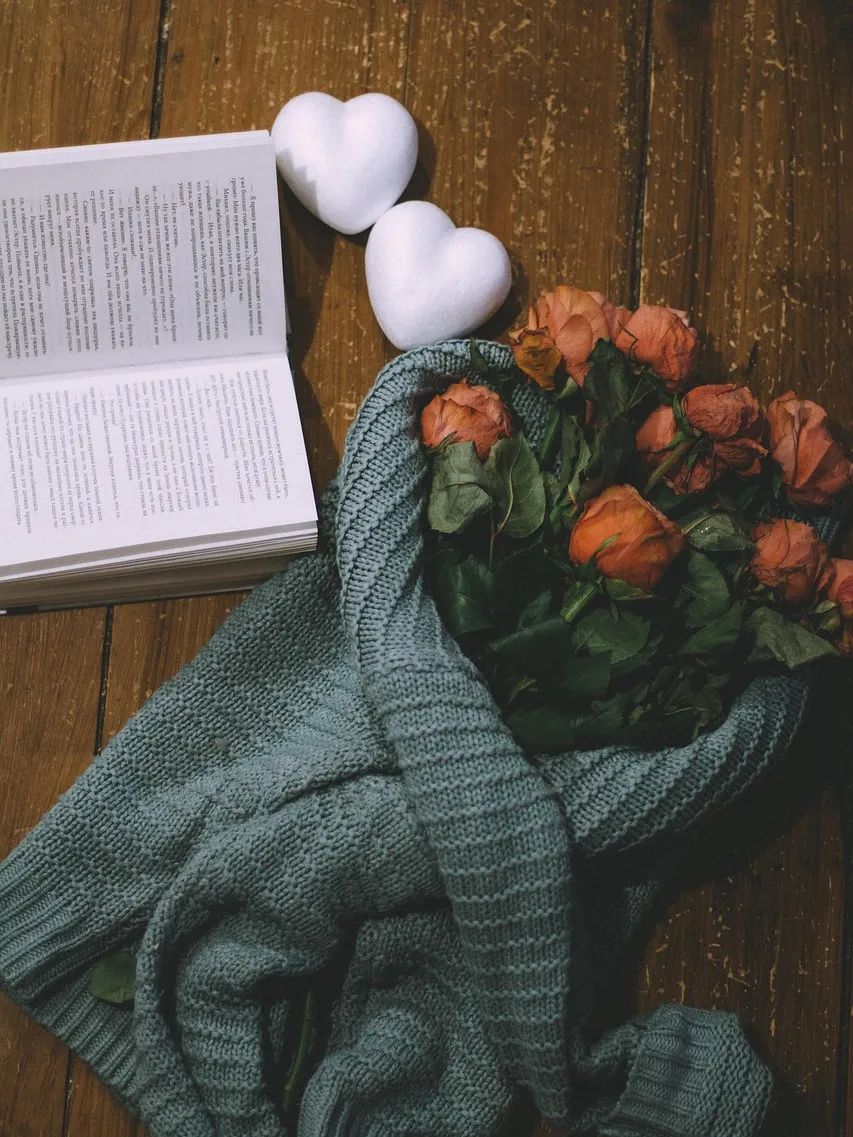

*
在此之前,我从未有过去书写光州的想法。
一九八〇年一月,我和家人离开光州还不到四个月。屠杀事件发生的时候,我只有九岁。又过了几年,我偶然发现了倒插在书架上的《光州相册》,于是背着大人偷偷读了,那年我十二岁。照片上的市民和学生因反抗政变的新军部而死于棍棒、刺刀和子弹之下,幸存者和死难者家属秘密印制了这本相册并散发出去,旨在揭露因当局严苛的言论管制遭到歪曲的真相。年幼的我还不能正确理解那些照片的政治意义,惨遭毁坏的那些面孔只是作为对人类的根本疑问镌刻在我的心底。人会对人做出这样的行为吗?我想。同时,我的心里也有另外的疑问。这本书里还有人们在大学医院前排起长队为中枪者献血的照片。人会对人做出这样的行为吗?两个看似不能并存的问题相互冲突,成为一个解不开的谜。
二〇一二年春天的某日,我正在努力创作“拥抱生活的明亮耀眼的小说”,心里再次浮现出那些从未解开过的疑惑。很久以前,我就对人类失去了根本性的信任。可是,我怎么能拥抱世界呢?刹那间我突然醒悟,如果不去面对那个不可能的谜,我就无法前行,我只能通过写作穿过那些疑问继续向前。
后来,在将近一年时间里,我都在为这部新小说画素描,在我心里,一九八〇年五月的光州将作为小说的某个层次出现。那年十二月,我去了望月洞墓地,那是鹅毛大雪过后的第二天下午。我用手按着心脏,在日暮时分走出冰封的墓园。我想,我要写正面处理光州事件的小说,而不是让光州仅仅作为小说的某个层面。我买了一本收录了九百多份证言的书,每天阅读九个小时,花了大约一个月时间才看完。后来则不再局限于光州,我又涉猎了很多有关国家暴力的其他书籍,目光投向更广更远的地方,我阅读了人类历史和世界范围内有关大屠杀的内容。
准备资料期间,我常常想到两个问题。想到二十多岁时,每次换日记本都会在扉页上写下的句子:
现在能帮助过去吗?
生者能拯救死者吗?
越是读资料,越是觉得问题无解。持续不断地接触人性中的至暗部分,对于人性的信任早已龟裂,愈发变得支离破碎。正苦于没有头绪几乎要放弃这部小说的时候,我读到了一位年轻夜校教师的日记。一九八〇年五月,光州军人们暂时离开后,朴龙俊参加了为期十天的市民自治绝对共同体,直到预告军人要返回的那个凌晨,他都留在道政府边上的基督教女青年会里,后惨遭杀害。性情羞涩安静的他在最后的夜晚写道:“上帝啊,为什么我要有良心,为什么良心如此这般刺痛我?我想活着。”
读到这个句子,我瞬间像被雷电击中了,似乎明白这个小说要去往何方了。我知道,我必须把这两个问题颠倒过来。
过去能帮助现在吗?
死者能拯救生者吗?
后来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我也的确感受到了过去帮助现在、死者拯救生者的诸多瞬间。有时我重返墓园,很奇怪,每次去都是晴天。只要闭上眼睛,橘红色的阳光便充满整个眼球。我觉得那是生命之光。我说不出话,任凭温暖的阳光和空气包裹着我的身体。
十二岁看到那本相册之后,我的心里不免生出这样的疑问:人类为什么如此暴力?人类怎么能够站在那么压倒性的暴力的对面?我们属于人类这个物种的事实究竟意味着什么?在人类的残酷和尊严之间,若想跨越连接两座悬崖的不可能的空虚之路,我们需要死者的帮助。正如这部小说的主人公,年幼的东浩用力拉着母亲的手走向阳光。
当然,对于发生在亡者、遗属和幸存者身上的事,我也无能为力。我能做的只是借用我身体的感觉、感情和生命而已。我想在小说的开头和结尾点燃蜡烛,于是,在当时殓袭遗体殓袭是朝鲜民族丧俗中的两个重要环节。“殓”是将死者遗体入棺的过程。“袭”是在“殓”之前进行的准备工作,包括给死者净身和换寿装。并举行葬礼的尚武馆里开始了第一个场景。在那里,十五岁的少年东浩为尸体盖上白布,点亮蜡烛,凝视着犹如心脏般的微蓝色的火焰中心。
这部小说的韩语题目是《少年来了》。我使用了动词“来”的现在时。在我使用第二人称呼唤“你”的瞬间,少年从灰蒙蒙的黑暗中苏醒,迈着灵魂的脚步向现在走来,越来越近,直至成为现在。正如我在写这部小说时所知道的那样,当人类的残酷和尊严以极限形态同时存在的时空被称作光州的时候,“光州”就不再是某个城市的专有名词,而是变成了普通名词。我也知道那是穿越时间和空间、不断返回到我们身旁的现在时。哪怕就在此时此刻。
*
二〇一四年春天,《少年来了》终于完成出版,读者们反馈回来的痛苦令我惊讶。我不得不思考这个事实,我在写作过程中感受到的痛苦和读者们所说的痛苦密切相关。痛苦之因是什么呢?我们原本相信人性,只是当这份信任动摇时,我们会感到自我也被摧毁了吗?我们原本热爱人类,只是当这份热爱破碎时,我们会感到痛苦吗?痛苦源于爱,什么样的痛苦又能作为爱的证据?
那年六月,我做了个梦。我在梦里走过雪花飞舞的原野。原野上栽满了成千上万个黑色的树桩,每个树桩的后面都是坟墓。某个瞬间,我的运动鞋踩到了水,回头看去,原以为是地平线的原野尽头涌来了海水。我问自己:为什么这地方会有坟墓?下面的坟墓里,骨头都被冲走了吧。上面坟墓的骨头是不是应该转移,趁着现在还不晚?可是,怎么可能啊?我连铁锹都没有。水已经漫过了脚踝。我从梦中醒来,看着依然黑暗的窗户,感觉这个梦似乎在说着什么重要的东西。记下这个梦,我想这也许是下部小说的开端吧。
那会是什么样的小说,我不得而知,我只是沿着梦的方向写下了几个故事,然后删掉,如此反复。从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开始,大约两年时间,我在济州岛上租了房子,往返于济州岛和首尔之间。济州岛上每时每刻都无比强烈的风、光线和雨雪,冲击着我的感官;漫步在树林、大海和乡村的小路之间,我感觉小说的轮廓越来越清晰。我以写作《少年来了》时的方式,阅读大屠杀幸存者的证言,研究资料,凝视着几乎不可能用语言表达的残酷细节,保持最大的克制去写《不做告别》。我梦见黑树桩和海水汹涌的那个早晨之后,大约过了七年,这部小说出版了。
创作期间我用过的几个笔记本上,写有这样的摘录:
生命是渴望活着。生命是温暖的。
死亡就是变冷。脸上的积雪不会融化。
杀人就是让生命变冷。
历史上的人和宇宙中的人。
风和洋流。连接全世界的风和水的循环。我们彼此相连。但愿,我们彼此相连。
这部小说共有三部分。在第一部的旅程中,叙述人庆荷从首尔到了济州中山间,在仁善的家里拯救了一只小鸟。如果说他为此穿越暴风雪是一种横向之路,那么,在第二部里,她和仁善一起走向人类最黑暗的一个夜晚(一九四八年冬天发生在济州岛的屠杀平民事件)、走进海洋深处则是一种纵向之路。最后在第三部,两个人在海底点亮了蜡烛。
作为朋友的庆荷和仁善像传递蜡烛似的引领小说前行,但与她们紧密相连的真正主人公却是仁善的母亲正心。她在大屠杀中幸存下来,从此孤身战斗,只为找到亲人的一块骨头来举行葬礼。她是不想终止哀悼的人。她是怀抱痛苦对抗遗忘的人。她是不做告别的人。她的爱与痛苦终生都以同样的密度和温度在沸腾。看着这样的生活,我不由得问自己,我们可以爱到什么程度?我们的极限又在哪里?应该爱到什么程度,我们才能最终成为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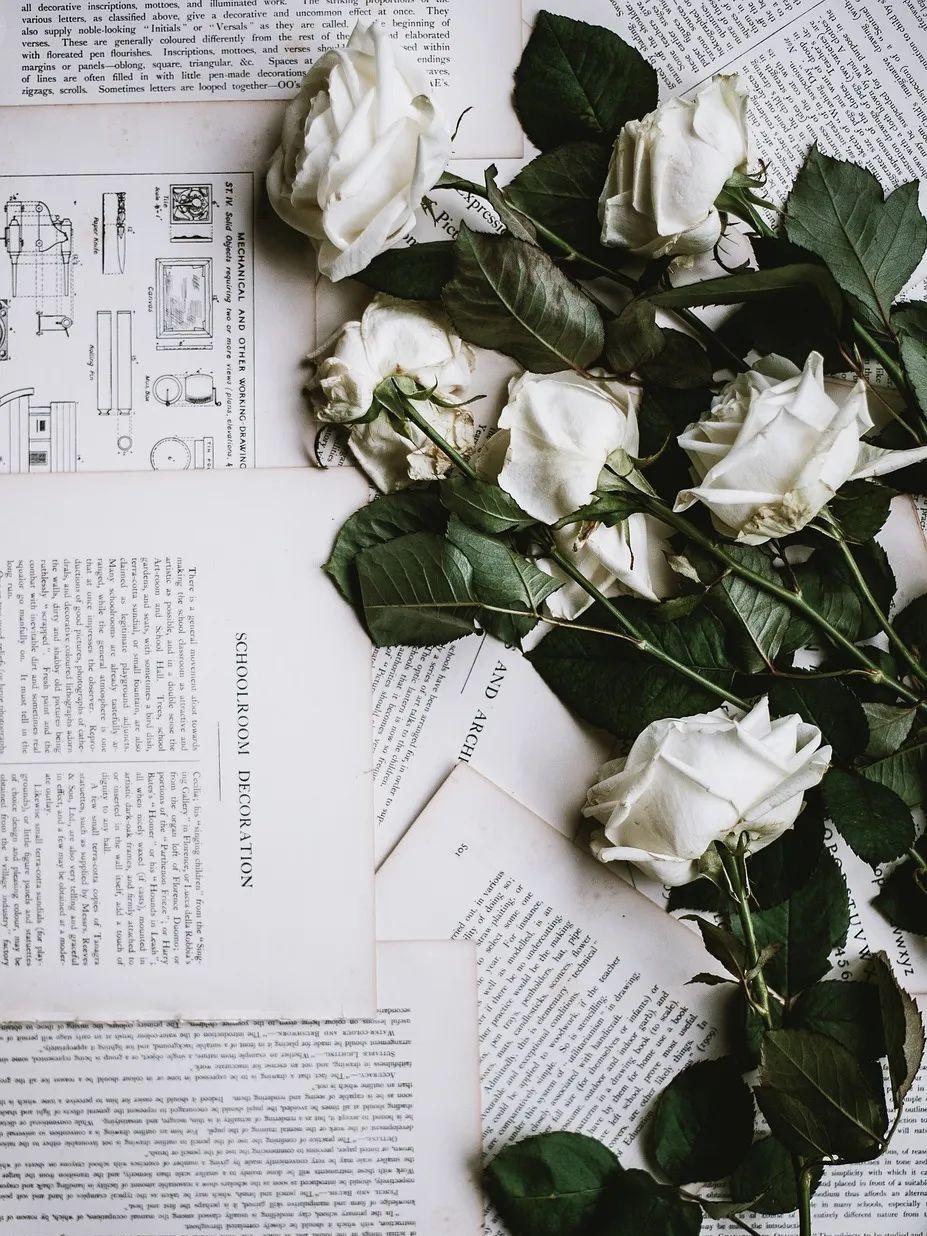
*
《不做告别》出版已经三年了,我还没有写出新的小说。完成那本书后,要写的小说早就在等着我了。这部小说在形式上与《白》有关联,我想把自己的生命暂借给出生两个小时就去世的姐姐,我想探视我们内心深处无法让任何东西破坏掉的部分。像往常那样,我还是无法预测小说的完成时间,但无论如何,我都会以缓慢的速度写下去。我会越过已经写完的书,继续向前。我会在某个地方转弯,走到生命允许的最远处,直到再也看不见从前的书。
这样不断远行的时候,我写下的书已经有了独立的生命,也会按照自己的命运去旅行。它们就像救护车里的两姐妹看着窗外燃烧的绿色火焰——她们将永远在一起。它们就像黑暗和沉默中在男人手心里写字的女人的手指——她将找回丢失的语言。它们就像我那出生两个小时就死去的姐姐,以及冲着孩子哭喊“不要死,求求你不要死”的年轻母亲。那些以深橙色凝结在我紧闭的眼睛里的灵魂,那些以无可言说的温暖光芒包裹着我的灵魂,他们又能走多远?那些发誓不做告别的人们的蜡烛,点燃在发生大屠杀的场所,点燃在压倒性的暴力席卷而过的时间和空间里,它们又将旅行到何方?是否会沿着金线,连起灯芯和灯芯,连起心脏和心脏?
去年一月,从旧鞋盒里找出的装订本上,一九七九年四月的我还在问自己那两个问题。
爱在哪里?
爱是什么?
另外,直到《不做告别》出版的二二一年秋天,我始终感觉这两个问题才是我的核心。
为什么世界如此暴力和痛苦?
为什么世界又是如此的美丽?
长期以来,我一直坚信,这些问题之间的张力和内在的斗争是推动我写作的动力。从第一部长篇小说到最近的长篇小说,我的疑问面貌不断变化向前,只有这两个问题不曾有过改变。然而,两三年前,我开始怀疑这个想法了。真的是二〇一四年春天出版《少年来了》之后,我才第一次质疑连接我们的痛苦的爱吗?从第一部小说到最近的小说,难道我全部问题的底层不都在指向爱吗?那不是我生命中最久远最根本的基调吗?
一九七九年四月的孩子写道,爱位于那个叫作“我的心脏”的私密场所(爱在我怦怦直跳的心里)。关于爱的真相,她这样回答:爱是连接我们心灵的金线。
写小说的时候,我会动用身体。我会动用全部的感官细节,去看、去听、去闻、去尝,去感受柔软、温暖、冰冷和疼痛,去感受心跳、口渴和饥饿,去感受行走和奔跑,去感受牵手走向风霜雨雪。作为终将灭亡的存在,我拥有流淌着热血的身体,我想把新鲜的感受像电流般注入句子。当我感受到电流传递给读者的时候,我会惊讶会感动。在这些瞬间里,我再次感受到了连接起我们的语言之线,感受到了我的问题如何经由电流、鲜活之事与读者们发生了关联。通过那条线与我相连的人们,以及未来通过那条线与我相连的人们,我要向你们致以衷心的谢忱。
韩江(1970—),韩国知名女作家。出生于韩国光州文学世家,毕业于延世大学韩语文学系,现任韩国艺术大学文艺创作系教授。1993年以诗歌作品步入文坛,1994年发表短篇小说《红锚》,自此开始小说写作。1999年凭借中篇小说《童佛》获得第25届韩国小说奖,在韩国文坛崭露头角。在之后二十多年的创作生涯里,韩江拿遍韩国各大顶尖文学奖项。2016年她凭借《素食者》(2007)的劣质英译本获得布克国际文学奖,在西方世界真正打响个人知名度。2024年她主要凭靠《不做告别》《少年来了》等作品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瑞典学院给出的颁奖理由是:“用强烈的诗意散文直面历史创伤,揭露人类生命的脆弱。”韩江成为韩国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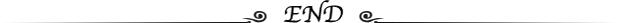
点击上图,订阅全年《世界文学》
点击上图,订阅单期《世界文学》

添加《世界文学》小助手
获邀进入《世界文学》分享会3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