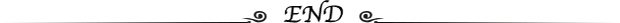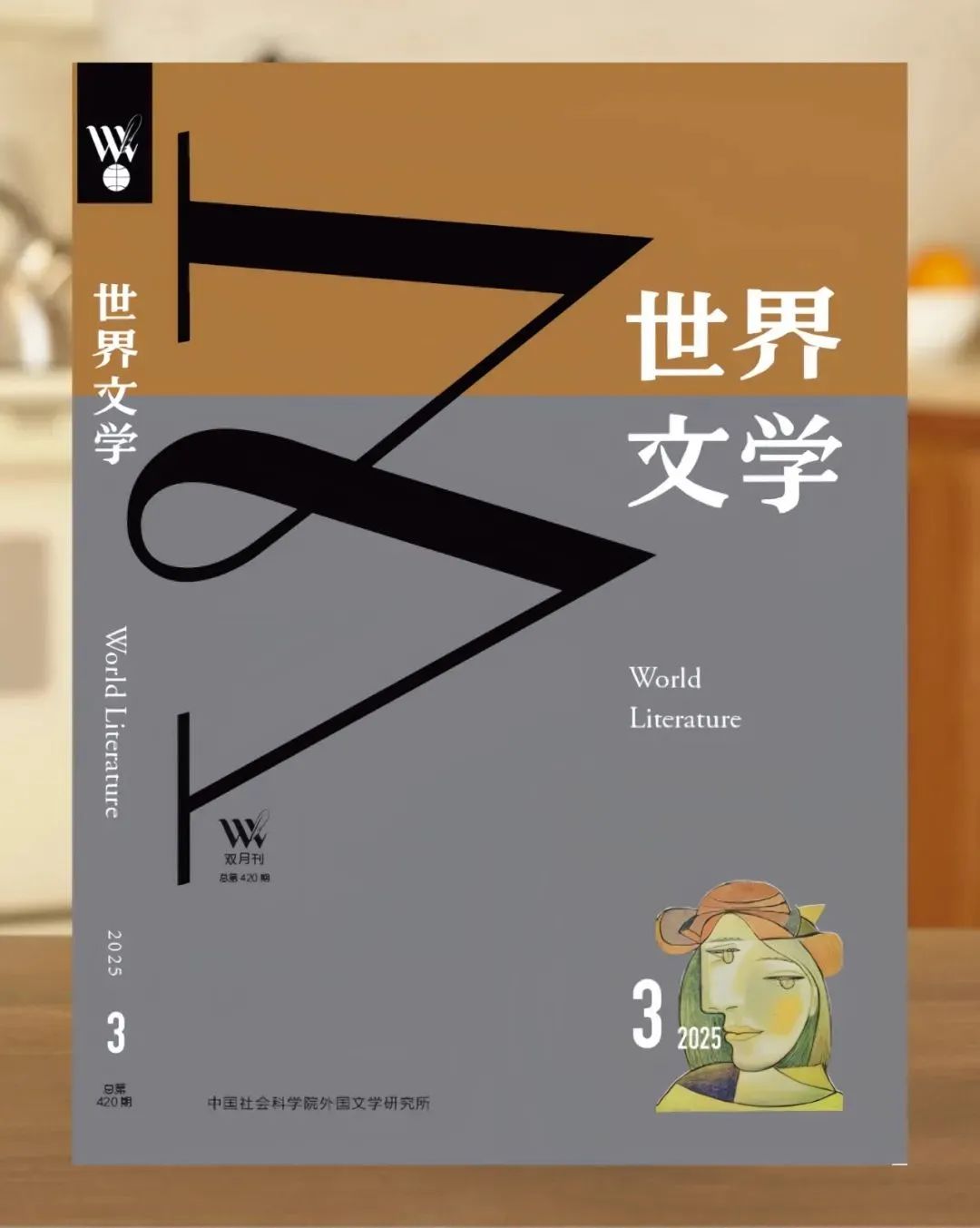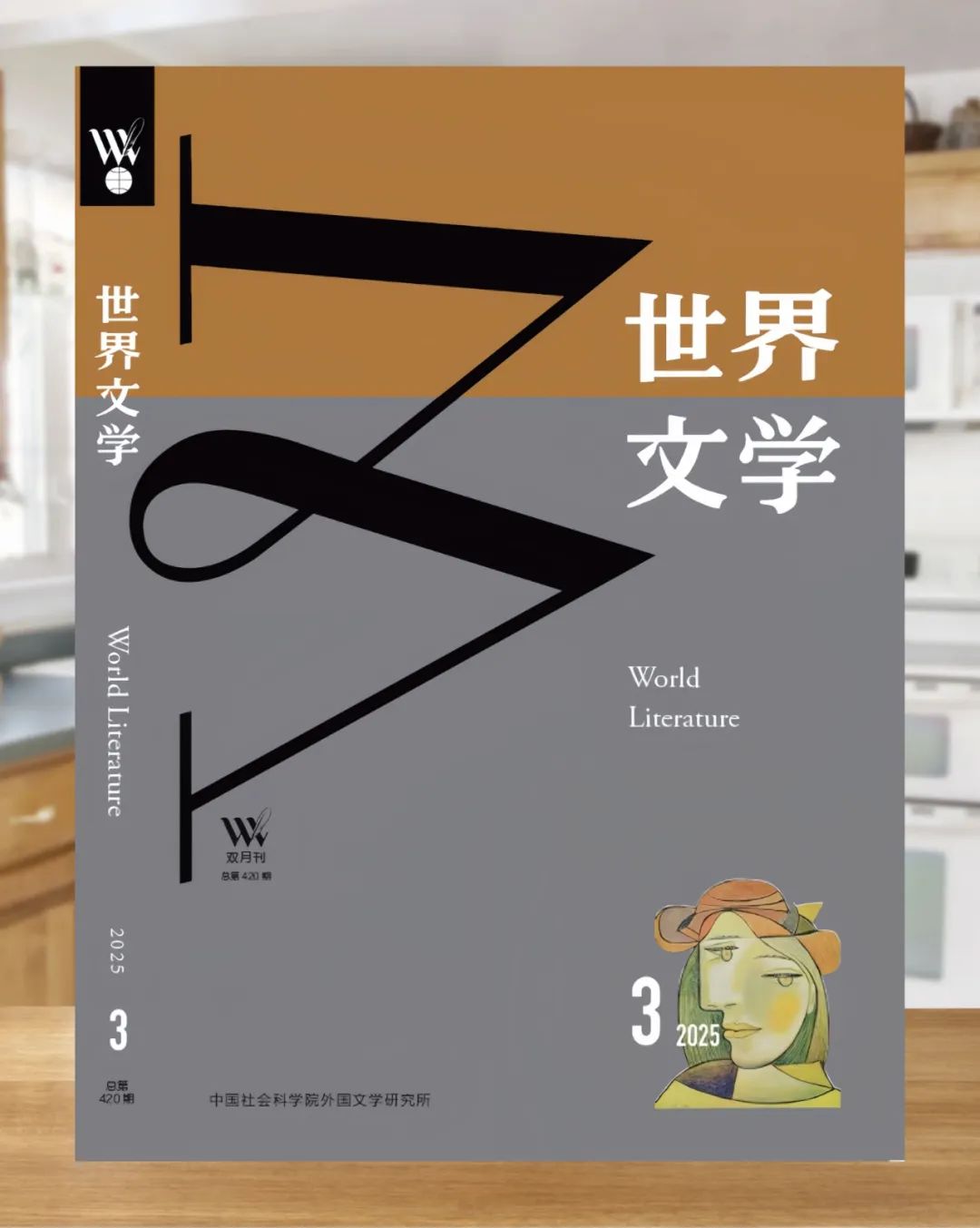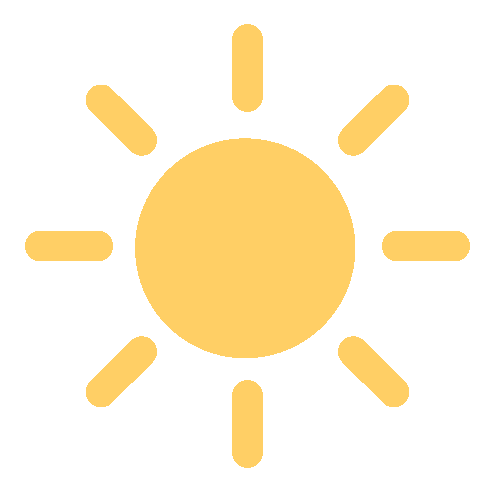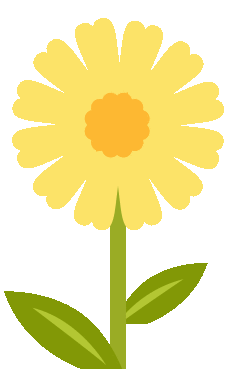读者来稿 | 可怜:读《大河之女》——被殖民文化反复冲刷的礁石
![]()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在“独木舟”和“面具”这两个隐喻的相互交织下,克安与莫阿芒芒的关系变得复杂起来。独木舟象征着留在村里的克安寻找自我认同的历程,他传承本土文化以抵抗殖民文化;而面具则象征着莫阿芒芒走出村外的探索,在更广阔的世界里她既有妥协也有抵抗,既拒绝被殖民文化定义,又不拘泥于仅用本土文化来书写这片土地。克安的独木舟与莫阿芒芒的面具象征着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策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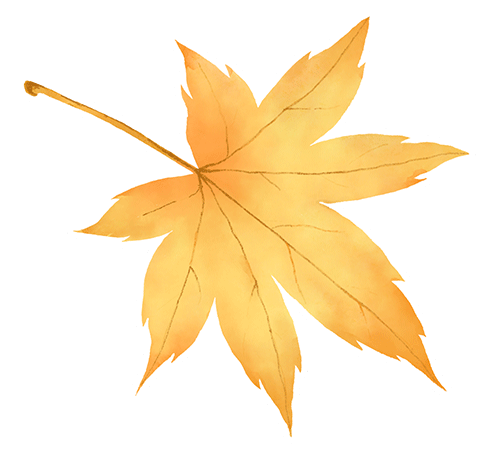
可怜
加勒比海的风裹挟着盐粒与潮声,将恩内斯特·贝班笔下的瓜德罗普岛涂抹出一番别样的风貌。贝班在《大河之女》中讲述克安和莫阿芒芒这两名主人公的人生经历,巧妙地刻画了这片土地上人与自然、历史、传统、信仰等方方面面的纠缠关系。克安和莫阿芒芒正是这片土地上的典型形象——他们在殖民记忆和本土信仰的夹缝之间生存,生命宛如被殖民文化反复冲刷的礁石,表面坑洼不平,内部却始终坚韧。作为两人的重要象征物,“独木舟”和“面具”贯穿了整部作品,承担着深刻的隐喻意义。


“独木舟”是贯穿克安生命历程的核心意象。它不仅是克安的生存工具,也是他展现自我价值的唯一媒介。克安幼年的时候,父母因独木舟翻覆去世,而他自己身体残疾、相貌不端,被旁人认为是“集齐了世间所有厄运的男人”,因此备受欺凌。然而阴差阳错的是,他以制作独木舟的高超手艺赢得了他人的尊敬,独木舟反倒成了他唯一的亮点,成为他与世界和解、找到自我价值的象征。同时,克安制作独木舟的精湛工艺还象征着他对自然的深刻理解。他“懂得如何选择木材,也知晓月相的吉凶。他凿刻木头的灵巧堪比艺术家,使用火焰的纯熟又如同非洲先祖”。月相代表着神秘,克安使用火焰的熟练程度仿佛在向自己的祖先致敬,换言之,他制作独木舟的过程也是延续本土文化的过程。克安传承了独木舟这一文化,也藉此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自我身份的认同:在他那生来不公的命运之中,他仍可以通过传承,在这片土地上找到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独木舟不仅作为当地人的出行工具存在,更作为克安的精神载体、本土文化的载体而存在,是克安将自己与这片土地的历史连接起来的桥梁。在这两者之间,几乎不存在殖民者所能介入的空间。
与“独木舟”这一隐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面具”。在贝班的笔下,莫阿芒芒的脸“简直是一张运到圭亚那大地上(并在这里有了生命!)的面具”。在莫阿芒芒的身上,“面具”拥有了极丰富的象征意味:不仅代表着自身的身份认同问题,也揭示了殖民历史对个人文化认同的深刻影响。一方面,这面具“可以追溯到奴隶贸易时期”,是殖民历史的鲜明体现;另一方面,这面具之下又显露出莫阿芒芒“星苹果的颜色”,展现出她肤色的活力。在这里,面具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矛盾体。莫阿芒芒戴上这副面具,或许正是因为她生活在法属圭亚那,不得已采取了这一自我保存之策——在殖民地的背景下,黑人女性必须在本土文化与殖民文化之间找到自己的位置,往往不得不屈从于殖民文化对她的塑造。正如小说中反复提到的莫阿芒芒与白人之间的关系:村人传着闲言碎语,说她想把皮肤漂成白色,她又怀上了白人的孩子,“她的梦想在巴黎……”,等等。她在这种情况下戴上了面具,将自己同时从殖民文化和本土文化中隔绝出来。就像小说中写的那样:“她第一次意识到,原来自己从没有试着理解过周遭的世界。浸淫其中太久,总觉得一切都天经地义。她观察和学习,如呼吸般自然,却从未深究过,也从未寻找过意义。”在这一意义上,莫阿芒芒的面具成了一种生存技巧。


然而在与克安相遇后,面具的意义开始发生变化。莫阿芒芒意识到,她的文化认同不能止步于外在的这副用于自我保存的面具,更需要从自己内心深处出发,去认识这个世界,把握自己周遭的一草一木。“克安成了完美的启蒙者”,在启蒙者克安的影响下,莫阿芒芒大开眼界。但是怀上了白人的孩子这一事实逼迫她再次拾起最初的面具。她戴着这副面具踏入了白人的世界,以流动的身份在纷繁的世界里穿梭,用并不属于自己的学术语言书写乡音:她的博士论文书写了家乡的历史,书写了“大河子民的历史”。此时,莫阿芒芒已经不再需要面具,因为她已经把面具内化成了自己的一部分。她了解了这片土地之外的世界,但仍然“握着一本厚如圣经的书”回到这片土地,对克安说:“绕了点路,但我还是来了。”
在“独木舟”和“面具”这两个隐喻的相互交织下,克安与莫阿芒芒的关系变得复杂起来。独木舟象征着留在村里的克安寻找自我认同的历程,他传承本土文化以抵抗殖民文化;而面具则象征着莫阿芒芒走出村外的探索,在更广阔的世界里她既有妥协也有抵抗,既拒绝被殖民文化定义,又不拘泥于仅用本土文化来书写这片土地。克安的独木舟与莫阿芒芒的面具象征着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策略。尽管如此,两人始终坚韧,始终信任自己生长的这片土地,他们的关系也发展成为一种深刻的相互理解。


在面对自己所处的文化与社会背景时,不论是“独木舟”还是“面具”,都是殖民地的子民面对世界、面对自我的一种方式,是“大河子民”在历史洪流中的某种自我表达。当莫阿芒芒带着“厚如圣经的书”回归这片土地的时候,她完成的不仅仅是学术研究,更是“大河之女”将西方知识体系用作工具,阐释本土文化的过程。文化的韧性于此悄然绽放:它宛如礁石,被反复冲刷,但始终屹立于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