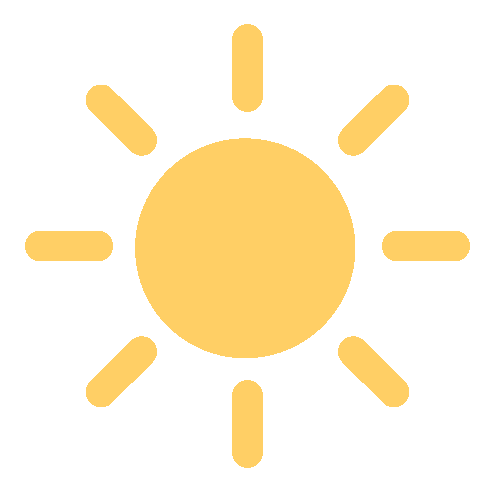小说欣赏 | 奥•德莱思【美国】:家里的小屋
![]()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你忘了那些马匹和马棚;你忘了已故的老吉戈尔和离去的厨娘;你忘了那个嬷嬷。她嫁到南美洲去了。这些曾经虐待过你的人。你忘了你曾跟她说过一两次话的那个穿蓝衣裳的姑娘,你忘了儿童时代的小路和儿童时代的方式。你忘了楼梯顶头那间关闭的小屋。
奥古斯特·德莱思作 郝一匡译
说一说家里的一间屋子吧。说哪一间屋子都行,你真的了解它吗?啊,了解,它干净或不干净,它空间大或不大;它空气通畅或有霉味儿。你知道晾在窗台上印花布衣裳的颜色,知道其中的床单或椅子或挂在墙上的画儿。但是,你决不了解在家里一间不透阳光和空气、看不透的、没有人气的小屋里潜伏着或游荡着什么。除了实实在在的黑暗外,隐形的、看不见的恐惧或害怕既无名也无形,却给了小屋以生命。
就像我外公惠普耳家楼梯顶头上的那间小屋。
一间黑屋子,走廊屋顶有两扇窗户,关着护窗板,把阳光挡在外面。是我小时候关禁闭的小屋。我表弟阿布纳也关在这间小屋里。一间一个黑暗的角落里摆着个架子的小屋,还有一个黑壁橱,为从来没来过的客人准备的一张极少用过的床铺,一张旧写字桌,以及一把桶形靠椅和脚踏凳。一间除了不住人外的多用小屋,藏着人们不想再用的家具,存放旧衣服和老唱片,送进去的小男孩一会儿就蔫了。
“谢尔登,你这个顽皮的孩子!我跟你说过不要弄脏衣服。你顺楼梯一直走上去,到储藏室去,我不叫你就别出来。”
因为把几只小鸡的腿绑在了一起,因为把核桃壳粘在猫爪子上,因为同外婆顶嘴,因为不按时回家,因为在不许你外出时远远地跑到了镇上。啊,为了一切,为了每一样小小的过失,反正都一样:在储藏室里蹲禁闭。
你坐在里面生气,怀恨。
小屋里的黑暗向你进攻,黑壁橱微微张着嘴巴,好像有说不出口的恐怖事,那张写字台,没人睡过的床,胡乱放置的架子在半明半暗中窥视。同时,你坐在那里梦想着复仇,幻想从阿拉丁的神灯里跳出一个阿拉伯妖怪。这盏灯是你自己的,藏在小屋里某个地方。这个怪模怪样没有脸的妖怪遵照你的吩咐,把你仇恨的人一扫而光。
一个仇恨与自怜、痛苦与泪水做成的妖怪。



你叫他“魔仆”。
你坐在小屋的昏暗中生气,怀恨,对住在黑壁橱中的他说话。“魔仆,”你说,“去打妈妈的屁股。”“魔仆,”你说,“去把外公扔进鱼塘。”“魔仆,”你说,“把生面包团弄到厨娘的脖子上。”“魔仆,”你说,“去拔嬷嬷的头发。”因为是妈妈或外公把你关到这里,是厨娘或嬷嬷告发的你。
你给他穿上外公丢弃在壁橱里许久的旧礼服大衣。再给他戴上外公的宽边礼帽。你交给他已故的杰里叔叔的灰裤子。那是让他在婚礼上穿的,可是因为杰里夜里过桥时落水身亡,那场婚礼根本就没有举行。你让他穿上利兹伯思大婶送给外公、外公压根儿没穿过(连为了让她高兴一下都没有)的那件花格子衫。“女人不能挑挑捡捡男人的衣服。”他说过。可是,你挑捡了魔仆的衣装。你把他装扮得又黑又大,你把他装扮成你从来没有见过的样子,脸上只剩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你把他整个儿装进丢弃在黑壁橱里的衣服里,然后派他去做你吩咐的事,去报复那神秘难解的成人世界——它管制你,强迫你服从它那些奇怪的规定。
你和阿布纳共同使唤他,因为阿布纳也被关到这间楼梯顶头的小屋。这间屋子成了“魔仆的小屋”,魔仆住的小屋,一个黑而形状不定的大块头藏在阳光从来达不到、月光也难以掠过其地面的壁橱里。
魔仆是你的秘密,是你和阿布纳的秘密。因为阿布纳也坐在这间小屋里生气怀恨。阿布纳也叫魔仆去为他报复那些骂他、惩罚他、把他关到楼梯顶头的这间屋里的成年人。
你对比两种命令。
“我今天派他去追吉戈尔。”阿布纳说。吉戈尔是外公雇来养马的男人。“他看见我今天去游泳了;他告发了我。我派魔仆去把他撕成两半。”
你会同意阿布纳让魔仆撕掉吉戈尔四肢的想法。
“我让他拔光汤米的头发,”你说,“我让他一个一个地拔掉汤米的手指甲盖儿。”
你从没喜欢过汤米。汤米表弟有女人气;他是那种当你在干草堆上玩耍或在鱼塘边垂钓时,他却坐着读书学习的人。汤米表弟是你妈妈对你说的“要有所成就”的那种人。他是外公、外婆和妈妈要求你应当“仿效”的那种人;连吉戈尔都说:“你表弟汤米,他可不是那种坏男孩。”
连在睡梦里你都听见他们全在说,“谢尔登,你这个坏孩子!”
也许你是坏。也许你和阿布纳是和别的男孩子不一样。你们肯定不像汤米。是汤米把魔仆拆卸成一件件彼比无关的衣服,把魔仆变没有了,变成在镇郊惠普耳外公家楼梯顶头关闭的小屋里的一声虚假的笑,一个空洞的梦,一粒灰尘。
但魔仆是你和阿布纳的,不能让汤米染指。不能和任何别的人共有。惩罚来得突然可怕,只在明白过来的最后一刻才让你知道人们已经知道的事,因为总是把谢尔登和阿布纳送往那间储藏室。
家里的一间屋子。一间弃置不用的屋子,有时一连一个月不打扫一次,没有客人来,就想不到它。很少有客人来。你坐在桶形靠椅里对自己、对魔仆说话。你对自己说他们全都待你十分不公正。你安慰自己,知道他们已经忘记了小时候是怎么回事;在他们的世界及其苛刻盲目的规定与你的真诚、私秘的世界之间有巨大的鸿沟,你对这道深不可测的鸿沟发火。
你坐在桶形靠椅里向魔仆诉说你的烦恼,对着黑壁橱的嘴说话。魔仆耐心地坐在那里听你说禁止你出去游泳,钓鱼,长途旅行,你不敢进城;你不跟穿蓝衣裳的姑娘说话,因为人们说她爹“古怪”和“不正常”,很难说她是什么人。
后来,有一天,你像常常做的那样告诉魔仆,把外公扔进鱼塘。你想象他穿着外公自己的那身旧礼服大衣、那件可怕的花格子衫和杰里叔叔的灰裤子,像一块穿着衣裳的雨云突然袭击外公,抓起他就丢进鱼塘。
你真切地听见他发出的溅水声。
当妈妈派人上来叫你回去后,你发现外公真的跌进了鱼塘。外公还在气得大叫。
“我没摔倒,我告诉你们!我是被推进去的,我自个儿知道。”
“好啦,好啦,老爷子,”你外婆说,“你要知道,你已经不是年轻时的样子啦。你就是滑倒的。我一直在说你不要一个人去鱼塘那里。”
“他妈的!我还能照看好自己。”外公叫着反驳她。
可外婆和妈妈用女人惯用的姿势摇着头,好像她们更知道怎么回事;外公说不过她们。
你事后直纳闷。


到了下次,就是因为汤米的告发,你又被送进储藏室的那次。汤米看见你偷偷沿着篱笆去看那个穿蓝衣裳的姑娘——他当时正坐在与篱笆墙相邻的苹果树上。你对魔仆发火,你怒骂汤米,你命令魔仆把汤米推下那棵树。
汤米跌到了苹果树下,受了伤,摔破了眼镜。
“我觉得好像被人推了一下,”汤米在那天的晚饭桌上这么解释,“可是那儿没有人,不会有人推我。我想是这么回事:一个苹果从我头顶上掉下来,力量大得把我打翻了,所以我就掉下来了。”
然后又是一天,阿布纳命令魔仆去报复厨娘;厨娘拿着满满一篮子洗好的东西跌倒了——不做饭的时候,她也管洗涤,除蹭掉膝上的皮肤外,她只好整个重洗一遍。
此事之后,你犹豫是不是再给魔仆下别的命令。
“你在上面瞧见什么东西了吗?”你被放出来后,阿布纳会问。
“你瞧见啦?”
“没,但我想过……壁橱那么黑,会是它。”
“有东西在动。”
“你瞧!是魔仆。”
“可是我实际上啥也没瞧见。”
从此以后,你知道了不要过分。因为不知怎的,你开始为魔仆担忧了。你想象,他在他的壁橱里沉思默想,等你来,等你跟他说话,接受你的命令;而你开始担心,不知何时,不知怎的,你会控制不住他,他会暴怒,会袭击人,将其撕碎;而这个人是你爱过的,即使你
一时在生他的气,恨过他。
当妈妈对你失去耐心,说:“谢尔登,我该对你怎么办呢?到储藏室去!”你说:“不,妈,不去那里。”
“现在就跑着去。”
“妈,我去别的地方吧,不去储藏室。”
但是你不得不去。你不得不去那间关闭的小屋,坐在它若明若暗的光线里。即使你把桶形靠椅转离开壁橱,你也总是强烈地感觉到身后有个壁橱,一点儿声响都会变成魔仆存在的证据。你慢慢相信了你听见他在动,在虚假的黑暗中喘息,等待着你的指挥。
阿布纳亦然。
你们跑到果园相见,你们嘘着声交谈。
“我听见他了,”你说。
“我想我看见他了,”他说。
“他在等候,”你说。
“饿了,饿了,”他说。
“我哪儿也不派他去,”你说。
“我也不派,”他说。
“万一他等烦了——会不会跑了?”你问。
“不会的!”他回答。
“谁知道呢?”你说。
你们坐下,睁大眼睛互相看着,有一点儿担忧,一点儿激动,不时从肩头望望房子那儿,好像半是害怕,半是期待地看见魔仆从护窗板下飘然而来,庞大而黑,像一团烟,像一块雷云,像一团黑穗病花粉;一个扑打着胳膊的黑东西,长着炯炯的眼睛和当作嘴巴的一道浅沟,后面拖着没有腿的大团块,仿佛噩梦中见到的虚幻之物。
这就是魔仆,童年时代家中小屋里的居住者。小屋是惠普耳外公家楼梯顶头的一间屋子,里面有一个架子,一张旧写字桌和一把桶形靠背椅;那是一间阳光和月光永远射不进去、它的壁橱是黑暗与黑暗之物住处的小屋。
仇恨和畏惧生出来的魔仆像从魔瓶里钻出来的妖怪,一个瓶中小妖,一个阿拉丁的仆人。恰恰是小孩这样的小东西才会幻想,按照他记得的图书和想象力,按照他吃的苦头和怨恨,按照他对成人世界的反叛,编造幻想。那个神秘不解的成人世界用它的规定不可理喻地管制一个儿童。
慢慢地,慢慢地,你长大了。你不再是个孩子,而是一个青年了。你走了,阿布纳也走了。你离开了惠普耳外公的家,你逐渐用一种新眼光看它了,你好像在迈上一条长巷离它而去,你回首看它——看见一个闲散、快乐的老地方。一个孩子成长的好地方。它立在地平线上,好像是儿童时代一个平静的庇护所;不过,这时看不见了,被隐隐出现在前面的岁月甩在后面。
你忘了。
你忘了那些马匹和马棚;你忘了已故的老吉戈尔和离去的厨娘;你忘了那个嬷嬷。她嫁到南美洲去了。这些曾经虐待过你的人。你忘了你曾跟她说过一两次话的那个穿蓝衣裳的姑娘,你忘了儿童时代的小路和儿童时代的方式。你忘了楼梯顶头那间关闭的小屋。
你忘了魔仆。
你从来没有自问过他怎么啦。你也许认为他逃进了他出生的那间黑壁橱的某个缝隙里了。
岁月流逝。你发现了另一个穿蓝衣裳的姑娘。你和她结了婚,在纽约安了家,有了孩子。你受人尊敬,你是谢尔登·格伦菲尔德,你根本不是“谢尔登,你这个坏孩子”了。但是,偶尔,当你听见妻子这样说你们的孩子时,就会生出一种模糊不清的烦恼的记忆,想起已经和刚刚忘却的事情,是你知道的事,可是已经看不清楚,不能再抓住的事。


时间对你是一维的。你极少回首往事。你忙着前瞻,度量着留给你的越来越少的时间还有多少;忙得顾不上去算逝去的时光,你忙着承担丈夫和父亲的义务,忙着交所得税、财产税,应付人口调查员,捐款,做俱乐部会员;从来不想时间不会为梦中的幻象而停留。时间比空气更难捉摸,比家中小屋里的灰尘更为渺茫。小屋属于远去了的、似有还无的已逝的童年。
一天,孩子们拂逆于你,提出他们的要求。“爹爹,我今年暑假不想去野营,今年不去,行吗?我们为什么不去乡下看看?”你的妻子说,“你不能责怪他们。”你便想这事怎么做。你想起惠普耳外公的农场,表妹塞莱斯特一个人一直住在那里。外公很久前就去世了。
于是,你打电话给塞莱斯特,她说来吧。“我还要请阿布纳,”她说。
你回到惠普耳外公的家,你回到了童年,一个遥远、不清楚了的童年,像透过深色玻璃看到的梦。一个没有了吉戈尔和老本,没有了外公和外婆,没有了厨娘和嬷嬷的梦。你回到一个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家,因为你和阿布纳要带着家里人回印第安纳来,那儿好像离纽约很远,其实只须一夜就到。
一种团聚。见到了阿布纳表弟,他乍看像悉德尼·格林斯特里特。他的妻子相形于他的热情便黯然了。见到了塞莱斯特表妹,她高挑苗条,像一棵柳树,严肃得像个教会执事。还有孩子们。他们是真正的陌生人——阿布纳的杰夫,你的迪克;阿布纳的塞茜莉,你的希尔德里德。男孩儿野得像没有驯服过的野兽,女孩儿拘谨得像家养小猫。
“我把两个男孩儿安排在楼梯顶头那间屋里。”塞莱斯特表妹说。
没有引起记忆的刺痛,没有一刻犹豫,你马上说:“那是他们住的好地方。”
“他们会熟悉起来,”阿布纳说,“他们会有两个星期时间,体验一个真正的老式美国男孩在农场有多么好玩”。
慢慢地,慢慢地,你明白了除了少了已逝者,添了新来者外,一切都没有变。尚在的人还是老样子,只是老了而已。爱梦想的阿布纳,矜持的塞莱斯特。
女孩儿们知道怎样听话,而男孩儿……
“我们从前也是这样吗?”阿布纳不时地问你。
你耸耸肩膀,知道你们当年也许就是这样的。“有其父必有其子。”你说。
日子过去了,最后你不得不跟迪克来硬的了。
当你抓住他又一次不听话,在没有大人陪同的情况下去鱼塘之后,“我要让你知道你会受到什么惩罚,”你说,“你到那间小屋里去,我不叫你,你不得出来。我小时犯错误,就得坐在那里。”
他去了。
阿布纳说,“好办法。我也要这样惩罚杰夫。还记得咱们那会儿多么恨这间小屋嘛!”
你笑了。
你笑当然是因为你现在年岁大了,你已长大了,永远不会被逼去储藏室,让另一个人高兴了,至少,在这一个小小的方面,情况有所变化。
你认为男孩儿们的举止好一些了。也许他们是变好了,也许这只是你的感觉。因为他们听话出去了,或因为你暂时知道他们在哪里,不用你为他们操心。
后来,有一天,迪克在他的屋子里受罚生气之时,你刚穿过草坪朝塞莱斯特走去。这时,有个东西打了你一下,把你撞倒了,你觉得那东西好像是一阵劲风或一个大树枝子。你爬起来,掸掸衣裳,朝四下看看,旁边没有树,也没有在风中摇摆的树叶。表妹塞莱斯特急忙跑过来。
“你絆着什么东西了吗,谢尔登?”
“没有呀,”你说,“有个东西撞倒了我。”
她笑了,“太荒唐了,谢尔登,你从前总幻想。你肯定绊着了。”
你叫道:“我自个儿知道……”
这时,往事涌上你的心头,引你心痛。你想起惠普耳外公大声反驳那天他是自己滑倒掉进鱼塘里的说法。
阿布纳说:“怪事。昨天,我在谷仓那儿闲逛,经历了与这一样的事情。——她们说我从干草堆上跌下来,但我发誓说我是被人推下来的。我在坐的地方被狠狠地推了一下。”
“正在惩罚杰夫吗?他那时关在储藏室里吗?”
你甚至现在还这样称呼那间小屋。
“我想是吧。他跟塞莱斯特顶嘴来着……”
说到这儿,他不说了,看着你,你也看着他。
塞莱斯特说:“你们男孩子忘了你们岁数大了。”
但阿布纳心里想的也是你心里想的,什么话都不必说了。
魔仆。
孩子们已经发现了魔仆。创造出魔仆是为了保护儿童不受目中无人、麻木不仁的成人世界的残酷暴虐。


你知道。你造出的他。你和阿布纳。
但是现在——现在你是成人了。你不是儿童了。你现在和储藏室壁橱里的魔仆格格不入了。
你站在对立的立场上了!
魔仆躺在里面等待了那么多年。魔仆,是一个小男孩用仇恨和痛苦、被逼无奈要报仇而创造出来的。
你知道你和阿布纳将买下这所房子。如果有时间的话,将对那间小屋进行改造。拆了它,剔除壁橱,盖一间阳光室、游廊什么的。除掉魔仆形成的那个地方……
但是你们怎么除掉乌有之物呢?怎么毁掉一个梦中的幻象?
说一说家里的一间屋子吧。你想到家宅中的所有屋子,想到在屋里潜伏的和游荡的看不见的、看不透的无意义的东西。你压根就不了解它。
你自问:还有时间吗?
因为这时你从对自己过去的回忆中知道,从对童年和逝去岁月的回忆中知道,儿童会是多么残忍、好报复,多么可怕……
奥古斯特·德莱思(August Derleth,1909—1971)系小说家、诗人。他是以描写美国威斯康星州地方题材闻名的多产作家,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萨克草原上的人们》(1948),长篇小说《依然是夏天的夜晚》(1937)、《奔流不息的大河》(1939)、《春天的傍晚》(1941)、《夜之影》(1943)、《土丘上的房子》(1958)、《山在放哨》(1960),以及诗集《迎风飞翔的鹰》(1938)、《地球的表面》(1942)等。《家里的小屋》通过一个隐藏在老屋里的“魔仆”的故事反映儿童与成人之间存在的代沟。
原载于《世界文学》2001年第2期,策划与责任编辑:邹海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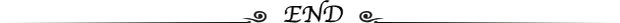
点击上图,订阅全年《世界文学》
点击上图,订阅单期《世界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