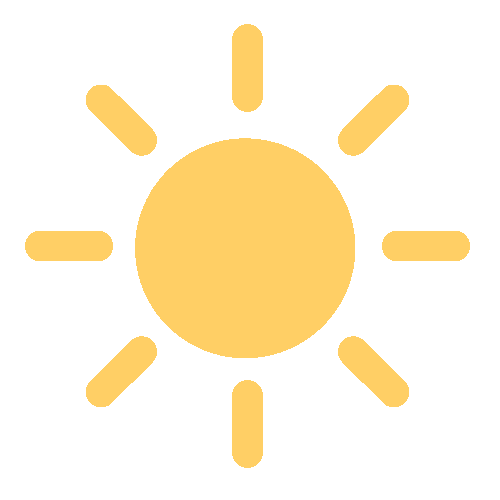散文品读 | 尼•斯特内斯库【罗马尼亚】:生存是一种痛苦,是一种闪光的参与……
![]()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惟有睡眠者,困倦者,攀梦者才睡眠,才困倦,才攀梦。
对鸟的蔑视是一种蔑视,但也是一种不是鸟的运气。
生存是一种痛苦,是一种闪光的参与。
理解意味着不存在,亦即存在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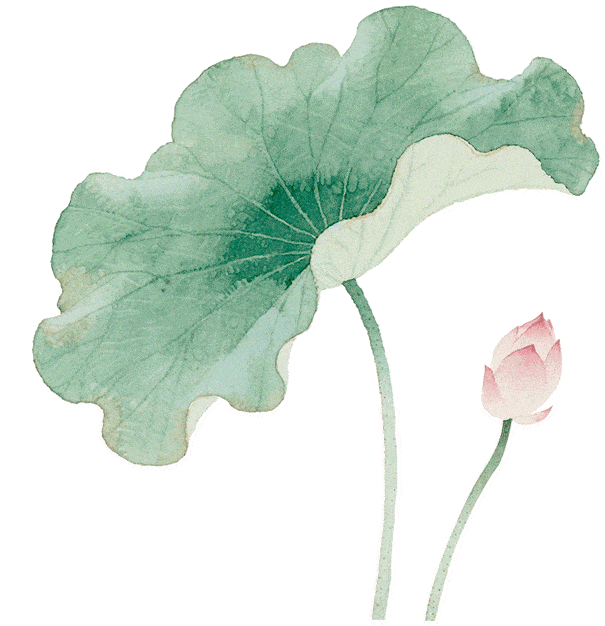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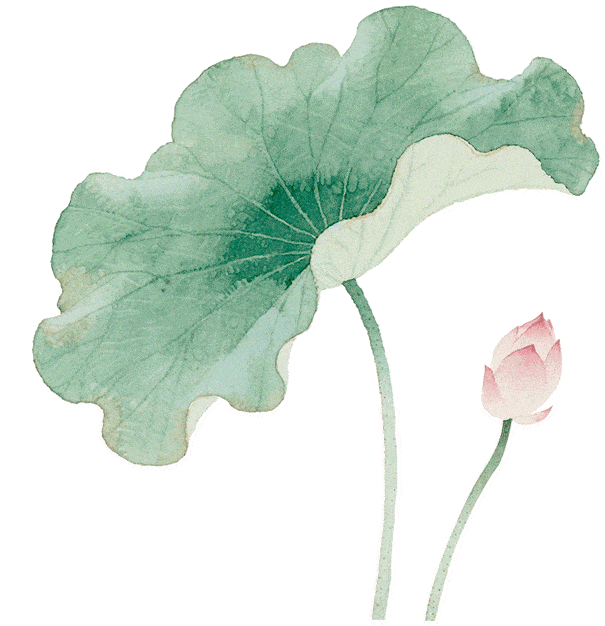
尼基塔·斯特内斯库作 高兴译
抵御死亡的最简单的行为便是夜梦。
呼吸,抗衡窒息;摸索,确定其余范围;倾听,沉默的孤独形式——所有这些都是反抗死亡的神奇形式。
夜梦是俘虏。在一场打输的奔跑战役中,它出现在我面前,酷似一匹星光驾驭的骏马。
通过诞生时的啼哭我们抗拒着死亡。
群星在天空升起,那是我们目光的见证。
我们用双脚贴紧土地,一如飞鸟用翅膀拥抱天空。
只要投去锐利的一瞥,我们会发现翅膀的根在空中,一如绿色的根在草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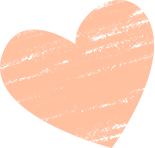
令人沮丧的并非我们生命的所在——躯体,而是我们生活的所在——时间。
时间概念——时间的情感——叙事。
惟有睡眠者,困倦者,攀梦者才睡眠,才困倦,才攀梦。
对鸟的蔑视是一种蔑视,但也是一种不是鸟的运气。
生存是一种痛苦,是一种闪光的参与。
理解意味着不存在,亦即存在状态。
倘若我们存在,我们就无法觉得我们会不存在。
我们用休息中断活动,那休息比禁闭我们的庙宇更高。
石头,处于自己的状态并且倦于自己的悲剧状态,睡眠时,必须梦见人类的血液。


连续不断实际上意味着乌有。
反抗变化是物体的偶然事件。
你的存在是一只表盘,存在在上面转动着。
梦与做梦,两者都是物体的家园。
不满引发梦,疆界引发做梦;某只丧失翅膀的鸟,在石头的呼吸中飞翔。
某种不再流淌的时间。
奇迹的中止。
原地。
生存的形式和方法恰恰在于自身的柔弱之中:休息。
凭着自然的睡眠方式,我们才会获得力量。
凭着存在战胜死亡的方式,我们存在着。
拥有意味着进入空与白。
置于乌有的砖块,穿越静止的瞬间。
我们以一个梦想的内在空间为基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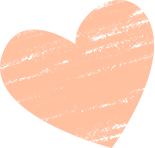
并非我们的状态,而是我们的非状态创造出时间。时间是我们的呼吸,是我们的边缘,是我们的食粮,也是我们的丧失。
惟有在睡眠中我们才能挡住时间并在我们生命的旷野中将它释放。
它凌驾于我们之上。
它凌驾于我们的毁灭之上。
离开它我们便不存在。它是我们的状态,也是我们的残余,然而我们并不是它。
从诞生起,我们便注定要走向死亡。
非存在才是永恒的状态。
我们在运动中挣扎,准备死亡。
我们存在,不为任何人,也不为任何事。
我们存在,没有任何见证。
并不存在时间之父:时间没有孩子。
我们处于人群之中,自由自在,一边搂着死亡,一边互相亲吻,仿佛并不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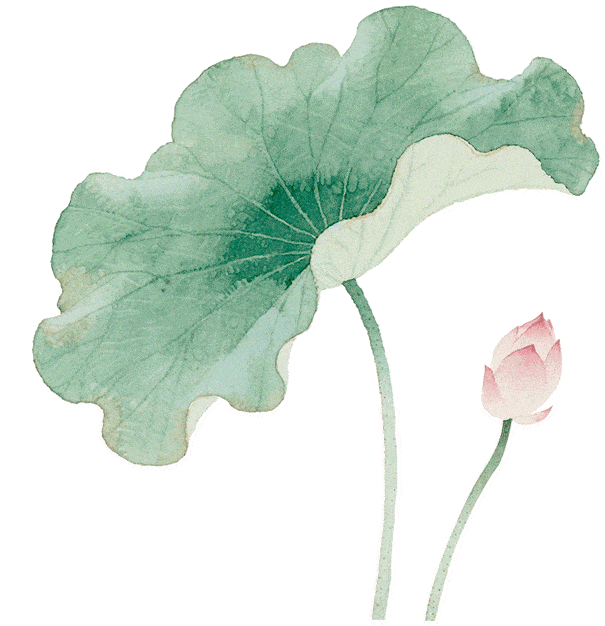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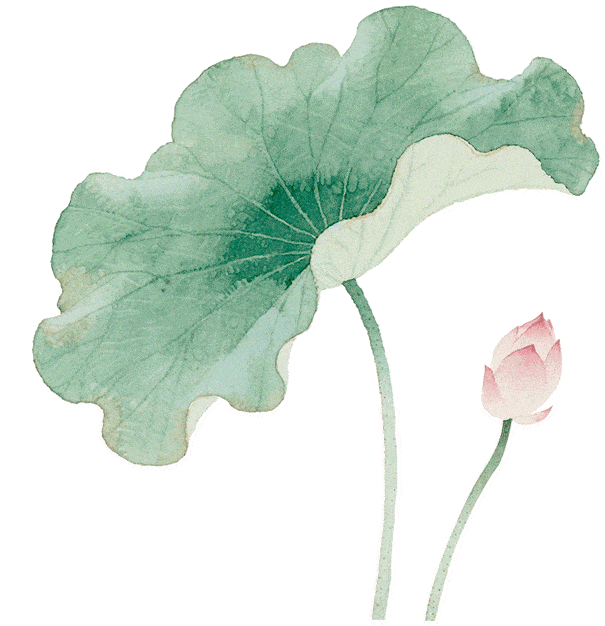
一只停止的表,一只坏了的表,一只指针死亡的表——每天有两次显示出正确时间。
一个被埋葬的死者,一个被鸟啄食的死者,一个火化了的死者——自然每天有两次显示出生命。
永远停在六点的表的指针,当六点来临时,正好指示六点。这恰好意味着当时间朝你走来时,去证明时间。
死亡,作为表达是一个悖论。作为本质也是。不知道生命是否也不时地走来证明死亡。谈论死亡更像一种思想,而非一种谈论。死亡是一种未实现的思想。



一种地形测量——亦即我们同存在物间的距离测量在我们看来合情合理。我同样可以相信某种我们同非存在物间的距离测量。离一棵树五米或十五米近或远——离死亡五米或十五米,而非十五秒或五小时近或远。死亡并非一种时间现象,而是一种距离现象。只是穿越距离是在时间中进行的,但这是依据悉心保存在伦敦的那种白金计量单位而确定的公尺【这里原作者犯了知识性错误。正确说法应为“在巴黎的那根确定为标准计量单位的铂铱合金的米尺”】。
少年时代,我有着一颗白雪般的心灵和一副总是以炽热令我惊奇的身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晚上常常难以很快入眠。我梦见自己成了滑雪者。梦中,在一片白雪覆盖的斜坡上曲折下滑时,我犹如一缕被尖厉的疾风梳理的卷发,由于失重而无法急转弯停下,以令人沮丧的快速,忽右忽左地向插满标杆的山谷下滑。
倘若我只想一个人倒下的话,除了向上没有其他可能。中断下滑,背叛常规,以一个更为抽象的动作——死亡从动作中逃脱。
走出常规意味着消灭常规,或者也许消灭你自己。



在我踏着滑雪板倾斜着身子滑行的弯道上无疑还写着碾碎的雪花,但也写着我同标杆间的距离。我离死亡更近或更远。差五厘米,越过一个标杆,二十五厘米,越过另一个,一米越过又一个,三米又一个,或者肩膀擦着标杆。离死亡更近或更远。
在我通过一个山口后,掉下一块石头,在我游过一条河流后,它干涸了。我险些在一条没有水的河里奇怪地淹死。我安然地游过了河,但河流因了我身体的热量而蒸发,忽然干涸了,使得鱼儿窒息而死。
我坐在松木桌旁。透过窗户,我听见刚被一辆汽车压死的一条狗留下的灵魂。它就在下面的街上,在狗的血泊中,在车水马龙的柏油路上哀号。十五米将我的生命同它的死亡隔开,一公里半将我同谷尔恰医院里那位死于难产的年轻女人隔开。八公里将我同在一次意外失火中被活活烧死的绵羊隔开。那只吃了我放的毒药而死去的耗子离我仅仅七米。三千公里以外的北极,爱斯基摩人用手从冰窟窿里将鱼掏出并活活地吞下。
我更近或更远地经过死亡。我更近或更远地任由死亡从我身边走过。


我捧着花发疯似的奔跑。我不知道从哪条走廊里奔跑。我只知道跑向何方。
离我一米处,离我五公里处,月亮上,下来后又在离我一厘米处,她悄悄地站着,而我笔直地往前走,就像滑雪那么笔直。
她并非一个思想。每当我希望她成为一个思想时,我挫败了她。她存在着。她给予我一次邂逅。

一小时后我们并不相见,她并没有对我说下午五点钟。她只对我说:我在离你十四米处。
我需要穿越的就这么远。十四米,朝左,向北,上方闪烁着北极星。当一切即将相遇时,当然,我不会跑三公里,也不会跑七米,也不会跑上月球,而就是这么远,不多不少。我们将会相见,时间是献给距离的典礼之名。
尼基塔·斯特内斯库(Nichita Stanescu,1933—1983),罗马尼亚当代诗歌的代表性诗人。在几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出版了《爱的含义》(1960)等十六部诗集以及《呼吸》等散文集。以下这组散文译自他的散文集《呼吸》。诗人以极为简洁的笔法,谈论着自己对艺术、对人生、对时间、对宇宙的独特感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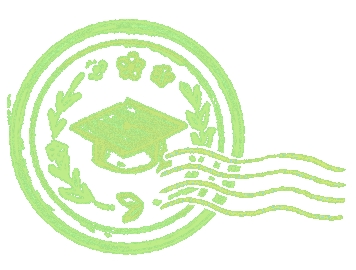
原载于《世界文学》2000年第2期,策划与责任编辑:钟志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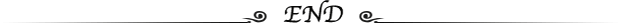
点击上图,订阅全年《世界文学》
点击上图,订阅单期《世界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