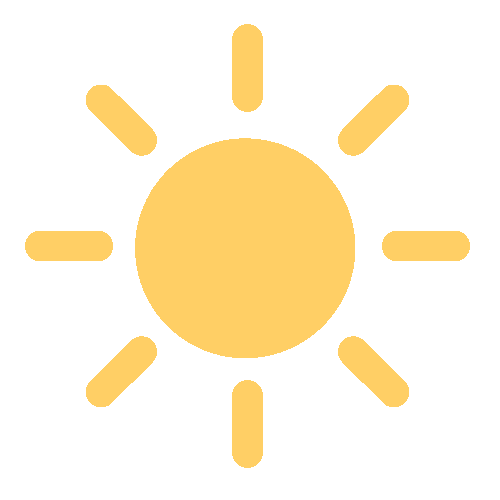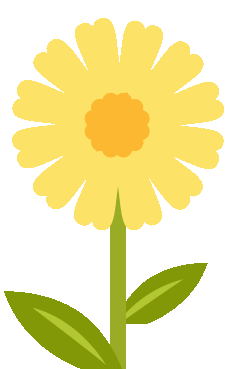第一读者 | 托•厄利【美国】:他确实激动,但那是因为他后车厢里的背包……
![]()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比赛结束后,他们坐在体育馆地板上聊天,一直聊到校内赛主管把他们轰出去。他们开始一起学习。他们跳熟了慢舞。他们毕业,结婚,工作,再次毕业,生了宝宝,宝宝长大去上大学了。约翰逐渐出现了缓慢漏气的状况。他无法保持充满气的正常状态。他修不好了。他在深夜里晃来晃去,盯着手机。他买了个背包。

托尼·厄利作 叶萌译
铁链是拴前廊的秋千用的,水泥块是给后院工具房当台阶用的,约翰这样告诉达勒姆【达勒姆,北卡罗来纳州的城市,位于约翰所住教堂山东北方向】家得宝家【得宝,美国一家大型连锁家居用品店】的销售员。他在罗利【罗利,北卡罗来纳州的城市,位于教堂山东南方向】的安伊艾户外商店【安伊艾,美国乃至全世界最大的户外用品连锁店】买了睡袋和背包,没给人家作任何解释;在沃尔玛买了充气式塑料筏、脚踩式充气泵和一把两件套的船桨。他编造了吉米·雷·加洛普这么个名字,在梅宾【梅宾,北卡罗来纳州的城市,位于教堂山西北方向】一家慈善商店挑选了帽衫、藏蓝色T恤、工装裤和靴子——全都是吉米·雷·加洛普该穿的行头。他从皮茨伯勒【皮茨伯勒,北卡罗来纳州的城市,位于教堂山西南方向】的哈德瓦五金店买了工具箱和三把挂锁。一切都用现金结算,购物小票扔进了店外的垃圾桶。他在教堂山【教堂山,北卡罗来纳州的城市,约翰居住地】什么都没买。
那把枪——38口径的H&R【全称为Harrington & Richardson,美国知名枪械制造商,成立于1871年,总部位于马萨诸塞州伍斯特市,其历史与美国军用枪械生产及越战紧密相关】——是他祖父留下的。夏洛特厌恶枪支,恋爱的时候约翰就没提过自己有枪;婚后再告诉她又会显得自己当初不诚实;卡莉出生后再坦白?那会要了他的狗命。于是他始终没说。他们结婚已有二十九年了。卡莉即将在坐落于安阿伯的密歇根大学取得粒子物理博士学位。过去二十年间,那把枪始终包在一件霍尔与奥茨【戴瑞·霍尔(1946—)与约翰·奥茨(1948—)均为美国歌手,是摇滚音乐史上最为成功的二重唱组合之一,活跃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T恤里,搁在车库椽木顶上,六个弹匣则藏在几双几乎从来不穿的袜子里。
他把水泥块锁进工具箱,把铁链、剩余的两把挂锁、筏、桨和气泵放进背包里;把装好子弹的枪裹进睡袋,又把睡袋捆到背包的支架上。那件霍尔与奥茨T恤也被他塞进背包,所有东西都堆进了车后厢。他不清楚自己在那些商店的监控录像里留下的影像要过多久才能被尽数覆盖,就等了几个星期。终于,他感到自己已经从监控里消失了,从货架间的通道上蒸发了。一个周一早晨,他早早起床,想在夏洛特去上班前见她一面。没课的时候他一般都会睡懒觉,有时会一直睡到午饭时分。他在夜间不怎么睡,而是一边在屋子里游荡,一边盯着手机,在油管上看那些象棋名局。他发现夏洛特已经穿上深色的修身套装,端坐在书房窗边的椅子上,啜着咖啡,读着一本讲断舍离的书。她见到约翰很惊讶,(让他觉得)似乎并不怎么高兴。她最喜欢清晨的家——这时候它只属于她自己。
“你怎么起来了?”她问。
“祝你早安呦。”他说。
“对啊,应该说早安。”
“你还在断舍离呢?”
“也不算,”她说,“但是读着这本书就觉得自己在断舍离。”
“我再给你倒点咖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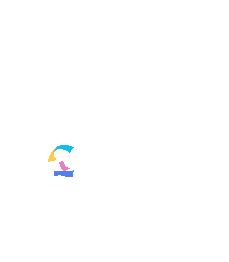

她的目光越过老花镜的镜框上沿盯着他看,鼻子一皱,就像在嗅一瓶已过了保质期限的“伴伴”【“伴伴”指牛奶和淡奶油1∶1配比的奶制品,多用作咖啡伴侣】:“你在搞怪吗?”
“没有,没搞怪。我只是问你还要不要咖啡。”
“你为什么要搞怪呢?”
“得了,夏洛特。”
她耸耸肩,又低头看书:“行吧,你没搞怪。”
他坐到她对面的椅子上。“哎,”他说,“咱们重来一遍吧。”
“好吧,”她说着合上了书,“咱们重来一遍。早上好,约翰。”
“早上好,夏洛特。”
“好啦,你今天要干点什么?”
“这不算重来,”他说,“这是唠叨。”
“约翰,这样问很合理。可以启动交谈嘛。你上周告诉过我你打算干点什么,当时你看着挺激动的。”
他确实激动,但那是因为他后车厢里的背包。“芙乐多【芙乐多,美国一个备受欢迎的零食品牌,生产多种口味的玉米脆片。“牛仔芙乐多”是该公司早期广告片中的卡通形象。后文夏洛特的回答“哎呀呀呀”即为该卡通人物所唱广告歌曲的开头】,”他说,“我在写一篇有关芙乐多的文章。”
“芙乐多。”
“玉米片。这是美国首次大规模营销本属于墨西哥的东西。‘牛仔芙乐多’。大型文化侵占是同化的先兆。”约翰常常梦想着摆脱美国史,转而从事美国文化研究,但他在奥兰治学院教十年级和十一年级,这个学院不开设美国文化课程。他并非真的在写有关芙乐多的文章,但觉得这个想法有价值。
“哎呀呀呀……”她答道。
“从没有人写过这个。”他说。
“得了。听着不错,加油写吧。”她把脚蹬进高跟鞋里,站起身来,“我看我得走了。”
夏洛特是北卡罗来纳大学法律咨询部门的一位律师。她说自己的工作就是赶在《新闻观察报》嗅到烟味之前扑灭山火。
“有什么严重的事吗?”他问。
“就平常那些事。兄弟会的男孩们卖海洛因。足球队宿舍里发现了妓女。”
她走过他的椅子时,他伸手抓住她的手,使劲捏了一下:“再见了,夏洛特。”他说。
她一把攥住他的头发,摇了摇他的头,几乎有点粗暴。“写那篇文章去。”她说。
估算着夏洛特已到办公室,约翰开始用电推剪给自己剪发、刮胡子——他们以前用这把推剪给老贵宾犬乔狼剪毛,但总也剪不好。乔狼已经死了……多少年了?十年?约翰打起泡沫,把头和脸剃光了,只留下两撇他认为与吉米·雷·加洛普相称的山羊胡。自打大学毕业,他就没见过自己刮净胡子的脸,记忆中他也从没见过自己刮光的头皮。苍白的光头上有很多鼓块,那种白像浴帽的白,不过山羊胡么,不得不说看着还挺酷。镜子里的吉米·雷·加洛普回瞪着他:“你他妈看啥呢?”
约翰和吉米·雷·加洛普的年纪相同,来自同一个山区小城——可能还沾亲带故,谁说得准呢——但吉米·雷·加洛普的人生从不像约翰这般幸运。他不是全班最聪明的孩子,不是那个一向受老师宠爱的全优生;他不曾被西卡罗来纳大学全奖录取,也不曾完成历史专业博士论文;他没娶到后来当上律师的漂亮运动健将,没住进漂亮的房子,没开上一辆漂亮的车,也没养出一个马上要完成博士论文的漂亮女儿——全世界能读懂这论文的人数不超过二百。都没有,吉米·雷·加洛普一事无成。他从未得到自己想要的爱。他所有的账单都要拖欠。他走在沙滩上都几乎留不下足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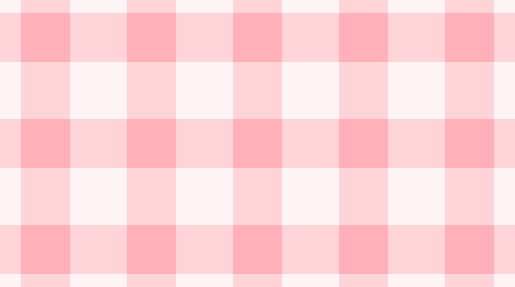
约翰在车库里穿上吉米·雷·加洛普那些慈善二手店行头,像海盗似的在头上扎了块印花头巾。他钻进车里,解开手机密码,搜了一下菲多利公司【美国一家著名的休闲食品公司,芙乐多玉米片就是该公司的一个品牌】的首页和在莫海德【莫海德,北卡罗来纳州的海滨城市,位于教堂山东南方向】天文馆举办的力高激光秀的起始时间。他点开力高网站,迅速浏览了几页。他给卡莉发了条短信:“我要去莫海德看力高秀啦,真希望你能在那里帮我讲解。爱你,爸爸。”又给夏洛特发了消息:“你坐在窗边的样子真美。今晚吃墨西哥菜?”之后,他俯身向前,额头久久抵在方向盘上,车内逐渐憋闷,他开始打起瞌睡来。醒来后,他把驾照和信用卡从钱包里取出来,把剩下的现金一起放进一个胶带钱包——那是卡莉十岁时为他做的生日礼物,他一直收藏在自己存放内衣的抽屉里。他把手机和空钱包扔到副驾地板上,迅速戴上吉米·雷·加洛普爱戴的俗气墨镜——镜腿像织成辫状金链的那种——最后一次看了看镜子里的自己。他的牙齿太白了,也太整齐了,他真希望自己有个扎眼的文身——阴森森的骷髅死神、燃烧的头骨——或是在眼睛下面文上一滴眼泪。但不管怎么说,现在要是有谁注意到有个人从约翰的奥迪车里出来,那他向警察描述此人时会说是吉米·雷·加洛普。
约翰倒车出库,开往斯塔特维尔【斯塔特维尔,北卡罗来纳州的城市,位于教堂山西方】,途中先在阿什伯勒的一个壳牌加油站停了一下,把信用卡用纸巾包好,塞进男厕垃圾桶的最底下。到了斯塔特维尔,他把车停在几个街区之外,钥匙留在点火器上,步行前往汽车站。背包不算太重,但工具箱活活有三十六磅。他每走四十码左右就得停一停,把箱子放下来,甩甩手臂。
车站柜台后的那个家伙牙齿叫咖啡染得发黄,令人羡慕,几乎可以完虐吉米·雷·加洛普。他的名牌上写着“威尔逊”。约翰不太情愿地交出驾照——他唯一的印迹——要买一张去芝加哥的车票。他准备先赶往苏必利尔湖那一带,到了密歇根湖再做打算。
威尔逊瞥了一眼约翰的驾照,又瞟了瞟吉米·雷·加洛普。“这不像你啊。”他说。
约翰取下了头巾。吉米·雷·加洛普答道:“我刚做了化疗。”
“让我看看你的眼睛。”
约翰把吉米·雷的墨镜推到自己的额头上。威尔逊盯视着约翰的脸,又低头看了看驾照,然后还给了他。约翰把墨镜压下来,又把头巾套回头上。
吉米·雷·加洛普说:“他们不得以切掉了我的一个蛋蛋。”
威尔逊指了指地上的工具箱。“那里面是什么?”他问道。
“工具。”
“什么工具?”
“石匠的工具。”
威尔逊开始敲键盘。“一共一百六十二。”他说。
吉米·雷·加洛普把背包扔在巴士行李舱里靠边的地方,硬是搬着工具箱走上了车。车上每个人都小心地避免跟他对视,他路过的空座位都被人用没戴在头上的头戴式耳机、四仰八叉摊开的杂志和内容物已清空的快餐袋筑起的战壕守卫着。眼看要走到过道尽头了,有个二十来岁的姑娘——比卡莉小几岁——把身边座位上的小孩抱到自己腿上,说道:“你可以坐这儿。”她五官小巧,一张直率的脸,正日渐圆润。漂亮姑娘常夸不漂亮的姑娘好看,她可以说就是这一类的好看。坐在她膝上的小孩端详着吉米·雷,仿佛在做着什么艰难的决定。小孩鲜红的嘴唇周围沾了一圈新鲜的多力多滋薯片碎屑。过了一会儿,她靠在妈妈身上,把拇指塞进嘴里,茫然地望着前方。吉米·雷·加洛普朝这位母亲点了点头,她回以微笑,那笑容在约翰看来实在有点期冀过多,就像几何课上坐前排的那个寡言女生在同学会上期待有人能记起她的名字。头上的行李架已经放满。她把腿整个儿从座位上抬起来,用手指了指工具箱。“把它推过来,”她说,“我个子矮,可以把脚搁在上面。”
巴士在希科里停了一站,之后是摩根顿,之后是马里昂,之后……老天爷啊,连旧堡【旧堡,北卡罗来纳州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小镇】都要停。那姑娘名叫卡门,她为女儿取名阿黛尔。她们刚去了费耶特维尔,本是想给布兰登——阿黛尔的爸爸,在布拉格堡服役——一个惊喜的。可是布兰登——卡门到那儿以后发现——有了另一个女朋友贝瑟尼,而且她已经怀孕六个月了。贝瑟尼对卡门和阿黛尔一无所知。总之,最后有个邻居打电话给军警了。卡门说她现在累得哭都哭不出来,等回到印第安纳,她要冲个澡,在浴室里放声大哭,直到热水用完为止。
他告诉她自己名叫吉米·雷·加洛普,是个船舶机械师,正前往苏必利尔湖,打算在那儿的大铁矿船上找份工作。他一直想去苏必利尔湖看看。其实五大湖都想看,还有什么麦基诺岛啦,苏圣玛丽河啦。自打九七年从海军退役,他一直在劳德代尔堡待着,在邮轮上工作。但他早已厌倦了往返牙买加的航行,也受够了每次出去喝啤酒都撞见前妻和跟她同居的那个无赖。她又不和那家伙结婚,于是他就得接着付赡养费,交公寓贷款。他想换换环境,就这么回事。
他们在黄昏时分开上了黑山【又译作“布莱克山”】的山坡,一路望着南面巍峨的群山在天幕下越来越暗。夜幕降临时,车已行至阿什维尔【阿什维尔,北卡罗来纳州的小镇】郊外,他们映在暗色车窗上的面孔渐渐清晰,而东行道上车灯的光束像一支支长矛劈面刺来。约翰开始感觉到身后的世界正在瓦解,紧密编扎的缕缕人生在尖厉的巨响中分崩离析。他开始浮想联翩:他的手机在车子的地板上响了又响,一辆斯塔特维尔的警车停在了他的奥迪后面,蓝色的警灯冷冷地闪着。夏洛特应该已经给卡莉打过电话了。你说什么?失踪了?他们在哪儿找到了他的车?可他是在天文馆给我发的短信啊。
卡门用指甲叩了叩他映在车窗上的影像。“嗨,你呀,”她对着窗子说,“你在想什么呢?”
他们得在阿什维尔车站打发两个小时。约翰帮卡门把行李搬进候车室。她挑了四个连在一起的座位,问道:“这样行吗?”约翰把尿布包丢在一个空座上,把工具箱放到地上。他们轮流上厕所,互相照看行李。他们的晚饭是在自动售货机上买的,他们抱怨椅子坐着不舒服。塑料椅为什么总是橙色的呢?吉米·雷和阿黛尔分吃了一袋芙乐多玉米片,他留意到其他的候车乘客在偷偷摸摸地观察他们仨,一个奇怪的小家庭:戴墨镜的老海盗,比他年轻太多的胖姑娘和脸上脏兮兮的孩子——显然不是他的。谁撞了大运?谁发了昏?谁是猎物,被擒获的又是谁?吉米·雷·加洛普在墨镜后面冷冷凝视着每个窥探的人。看什么看?你也要坐这破车,混蛋,管好你自己吧。他的胳膊环住了卡门座位的靠背。
巴士到了,看起来几乎是崭新的。它仿佛来自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光亮的车身在装卸区的安全灯下闪闪发光;车里的地板不是粘乎乎的;座位也没有炸鸡味。他们的待遇提升了。尽管车上空位很多,他们还是坐了跟先前他们相遇的那辆车相同的位子。车开回40号州际公路上,司机调暗了车厢的灯光,阅读灯一盏接一盏地熄灭了。有一男一女在巴士前部的某处轻声交谈,言语亲密又模糊不清,像慈爱的父母在墙壁的另一头夜谈。约翰调整了头顶的通风口,让它对着自己的脸吹。什么也比不上山间的空气。
他强撑着不睡,一直坚持到巴士开过出口,开上74号美国公路。这条路通往卡洛维【卡洛维,西卡罗来纳大学所在地】,他和夏洛特读大学的地方,过了卡洛维是阿盖尔,那是他长大的地方……全校最聪明的小子、象棋俱乐部主席、青年团体领袖、篮球队队长。他和夏洛特相识于大二那年的一场校内排球赛。她是个非法外援,为兄弟会球队打二传手。她凭着体育奖学金进了西卡罗来纳,但入学后决定专注于学业。约翰为历史系打球,他的球队打得很差。夏洛特个子矮。据他有限的经验,和矮个女孩跳慢舞很别扭,为着这个缘故最好离她们远点,以免大家突然说要跳舞了。不过,天啊,她排球打得真好,给兄弟会的小子们面上大大增光,他们不配,哪个兄弟会的人都不配。他们俩第一次轮换位置到网前时,她抬头看着他说:“你们队打得真烂。”他说:“是啊,是啊,确实烂,可我们对《邦联条例》了如指掌。”他以前从不会打情骂俏,但是那一刻,他会了,有如奇迹。下一次轮换时,她说:“你是不是为阿盖尔队打过球?我去过瑞韦斯。”他说:“我知道,我总是在看台上找你。”她说:“这话真恶心。”但是,当他成功拦网阻止一个兄弟会男孩得分时,她从网下伸过手来,拍了一下他的手。
比赛结束后,他们坐在体育馆地板上聊天,一直聊到校内赛主管把他们轰出去。他们开始一起学习。他们跳熟了慢舞。他们毕业,结婚,工作,再次毕业,生了宝宝,宝宝长大去上大学了。约翰逐渐出现了缓慢漏气的状况。他无法保持充满气的正常状态。他修不好了。他在深夜里晃来晃去,盯着手机。他买了个背包。


在韦恩斯韦尔和纽波特【纽波特,北卡罗来纳州边界附近的城镇】之间那条蜿蜒峡谷的某处,夏洛特把卡莉放在约翰膝上,他把卡莉举起来,让她的小鼻子埋进自己的颈窝。夏洛特依偎着他的肩膀,伸过手来握他的手。约翰知道自己身在巴士上,轰隆隆的每一里路都让他离夏洛特和卡莉越来越远,最终会远到自己再也见不到她们,但他也知道,不知怎的,她们同自己一起在车上,只要他不睁开眼,她们就会一直陪着自己。
纽波特。加特林堡【加特林堡,田纳西州城镇。小说中,此时巴士已从北卡罗来纳州向西穿过州边界进入了田纳西州】。诺克斯维尔。卡门打了个哈欠,开口道:“你知道吗,我觉得我从来也没有真正地爱过布兰登。”
“我遇见的每个布兰登都是小混球。”吉米·雷·加洛普说。
“我的意思是,怀孕以后,我大概这么想的,嗯,他好像还行。我不想阿黛尔从小就没爸爸,而且军队里福利很好,他还说会带我们一起去韩国。我就想,嗨,有啥不好呢?我哪年哪月能去得了韩国啊?”
克罗斯维尔。库克维尔。日出时到了纳什维尔【纳什维尔,田纳西州首府】,在奥兹国【小说《绿野仙踪》里的一个虚构的国度】一样闪闪发光的天际线上,一座摩天大楼的剪影有如蝙蝠侠的脑袋。汽车站外的人行道有小便味儿,站内的鸡蛋味儿倒是很好闻。卡门伸过手来,摘下了吉米·雷的墨镜。约翰看着她的目光在自己两眼之间来回打量。她微微摇头,皱起了眉头。
“怎么了?”他问。
“你看起来不像你,”她说,“你的眼睛不像你的眼睛。”
“那还能是谁的眼睛?”
她的中间名是艾什丽。她姐姐叫C. J. 。她们是在印第安纳州科西市的一个奶牛农场上长大的。一千英亩地,一百头奶牛。在她十岁,C. J. 十六岁那年,她们父亲的帽子掉进了玉米输送机,他想都没想就伸手进去拿。他们用直升机把他送到了印第安纳波利斯【印第安纳波利斯,印第安纳州首府】,但在把手缝回去的时候,他突发心梗去世了。他们家失去了农场。母亲开始滥用药物,两年前她在韦恩堡因吸食芬太尼过量去世了——和她在网上认识的一个摩托车手一起。不,吉米·雷没什么家人可聊。北卡罗来纳有几个远亲,都没联系了;他的前妻,那也不算,对吧?现在只有他一个人。
鲍林格林。凯夫城【鲍林格林和凯夫城均为肯塔基州的城镇。小说中,巴士在纳什维尔转向北边,现已进入肯塔基州】。阿黛尔拉了泡大的,整辆巴士臭气熏天。许多人转过身来瞪着他们。“老天爷啊。让我出去一下。”说着,卡门从吉米·雷身前爬了出去,阿黛尔紧紧搂着她的脖子。她用力扯着头顶行李架上的尿布包。
“要帮忙不?”约翰问。
“不用了,亲爱的,谢谢。我能搞定。”卡门说。
伊丽莎白镇,路易斯维尔【路易斯维尔,肯塔基州的城镇,位于肯塔基州与印第安纳州边界】,高高的桥,宽宽的河流,推着六只空驳船的拖船。欢迎来到印第安纳。阿黛尔和吉米·雷的太阳镜玩起了躲猫猫。“咱们到家了。”卡门说——其实,他们还要向北开两小时才到印第安纳波利斯,之后再往北开一小时才是科西。约翰已经走得太远,回不了头了。他买了水泥块,剃了光头,把钥匙留在了车里。他曾想象巴士在州边境会被印第安纳州的警察拦下,而实际上吉米·雷·加洛普已经甩掉了所有追踪。

“我不能回家。”约翰说。这个想法本身就像是一条布满地雷的边境线。
“你为什么不能回家?”
“限制令。”吉米·雷说。
“嗯,好吧。限制令。没什么大不了的。有一次,我就因为一个人领过限制令,现在我们还是朋友呢。只要别总开车从她家旁边过就行。”
阿黛尔把墨镜还给了他。
他戴上墨镜,深吸了一口气。“而且我也不想去苏必利尔湖,”他说,“可是现在说不去已经太晚了。我不知道还能做什么。”
“那就跟我回家吧。”
卡门的姐姐和姐夫提前把他们的PT漫步者【克莱斯勒公司生产的一款汽车】留在了印第安纳波利斯汽车站。卡门的庞蒂亚克最近挂了。交通高峰,然后是61号州道和双车道的印第安纳州——绿的原野、蓝的天空、白的云朵、白的房子、白的谷仓,诸多小小的城镇被白色的教堂尖顶散乱地钉在种着大豆的原野上。约翰逊镇,希尔特伯格,罗伊纳,欢迎光临,谢谢,欢迎再次光临,很多辆慢悠悠把家回的巨型绿色拖拉机,一架阿米什马车,一顶草帽和一把胡子,两匹灰马。
一个球场,一所小学,一个小公园和一个四向停车的路口:这就是科西。爱默生杂货店,一家废弃的“纯粹”加油站,一个砖砌的小邮局,肯特小酒馆。酒馆门上悬着的牛铃当啷啷地响起来。吧台边坐着四个穿冲锋衣的人,其中两人在高凳上半转身子,扭头看向身后。红色人造革卡座,一张褪色的鲍比·奈特【鲍·奈特(1940—2023),美国著名篮球教练,曾率领印第安纳大学队三次夺得美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冠军】海报,一打镶框相片——里面的小联盟球队穿着肯特酒馆的球衣。阿黛尔横穿过来,跑到吧台后面,卡门的姐姐一把抱起了她。“哎呦,宝贝小甜心,”她说,“C. J. 大姨想你啦。”C. J. 棱角分明,筋骨强健,身上找不到一丁点软乎劲儿,她的眼睛是一道訇然关闭的屏蔽门。她抱着阿黛尔走过酒吧间,来到吉米·雷面前,目光冷冷地盯进他的墨镜里。“这海盗是谁呀?”她问道,问的是卡门。
约翰亏气了。吉米·雷什么也没说。
“这是吉米·雷,”卡门说,“我在北卡罗来纳遇见他的。”
“他为什么在屋里戴着墨镜?”
“你怎么不自己问他?”
“喂。你为什么在屋里戴着墨镜?”
“光敏,”吉米·雷嘟囔道,“焊接害的。”
“你从没跟我说过呀。”卡门说。她溜到一个卡座上,伸手去拿菜单。“我要饿死了。”
“卡儿,你知道我没法一直供你和你拽来的阿猫阿狗吃喝,”C. J. 说,“我可以给阿黛尔弄点吃的。”
“我来,”约翰说,“这顿我请。”
卡门和阿黛尔住在一辆停在土路上的单宽式拖车房里,和科西市中心隔着一片大豆田。卡门把阿黛尔抱进去的时候,约翰将她的大包小包从车里搬了出来。马车轮做的吊灯,麦片盒,脏盘子,绿色长毛绒地毯,用透明胶补住的橙色胶皮沙发,两个角斗士装扮的男孩在墙上的画里盯着他们,神情哀伤。约翰把他的背包丢在沙发上,又拖着卡门的行李磕磕碰碰地穿过一条比他的身子宽不了多少的走廊。阿黛尔已经睡熟了,在一张与房间差不多宽的水床中央四仰八叉地起伏着。隔着一堵薄墙,他听到卡门在小便。“随便丢在那儿就行。”她喊道。
约翰睡在卡门所说的“客房”里。大号双人床,祖传的胡桃木梳妆台和斗柜,破旧的婴儿床,堆满外套的健身自行车,没地方插脚,更别说走动了。床上堆满了衣物——是干净的,她向他保证,只是没来得及叠,不好意思。她爬上床,把衣服抛进婴儿床里,又爬到窗边打开了空调。它在凛冽的轰鸣声中活了过来,像一架在北极起飞的轰炸机。“这么吵,真抱歉,”她说,“它适合用于比这大得多的房间。”


“我喜欢睡在冷的地方,”约翰说,“我喜欢这噪音。没关系的。”
“恐怕这床垫也不大好。你愿意的话,可以来跟我和阿黛尔一起睡。这地方足够了。”
“还是别了。水床让我有晕船感。”
“行吧。那,睡个好觉。”
“你也是。”
到了半夜什么时候,约翰把婴儿车里的衣服都扔回到床上,又溜回被窝里,把衣服堆在上面。他在衣服堆里钻来钻去时,门开了,卡门溜了进来,穿着件薄薄的白色睡裙。她把门半开着,走廊里的灯也亮着。她轻轻爬上床沿,跪坐下来,双手交叠放在腿上。约翰透过盖在他头上的运动裤看着卡门。她在腿上抚平睡裙,然后伸手戳了戳他的腿。“嘿,”她说,“你醒着吗?”
“嘿,”他说,“没大醒。”
“我睡不着。你想干点什么吗?”
“比如?”
“不知道呀。也许咱们可以看点黄片?或者之类的?”
“噢,”约翰说,“噢,不了。不了,谢谢你。我觉得我太累了,看不了电影。”
“也许你说得对。我觉得我也不能撑着看完整部片子。”她从衣服堆里拎出一件小小的连身裤,拿起来闻了闻,又丢进了婴儿床。“要不要看一段?”
“卡门。我真的真的很累了。请回去睡觉吧。”
“好吧。我想我现在也有点困了。我就是想,嗯,如果你想的话,咱们可以干点什么。”
“我明白。真是感激。晚安,卡门。”
她倒着爬下了床,站在走廊里朝他挥了挥手,说了声:“晚安,吉米·雷。”而后她关上了门。
午间,卡门和阿黛尔把他从床上拽起来出去野餐。他们开车绕过大豆田,在肯特酒馆右转,沿公路开了五十码,停在了科西市政公园的路边。秋千、跷跷板和攀爬架挤在一片杂草丛生的矩形木屑地上。一座松木凉亭,三张野餐桌,一棵瘦弱的枫树在喷泉池里投下稀薄而变幻不定的阴影。卡门摆出切成三角状的红椒奶酪三明治、一袋多力多滋和一盒无糖柠檬汁。C. J. 走过来,丢了个裹着白纸的超长潜艇三明治在桌上。“爱默生美食店的三明治总是放太多的肉,”她说,“希望你喜欢熏牛肉。”
卡门带阿黛尔去荡秋千的时候,C. J. 绕过桌子,大模大样地坐到吉米·雷对面,背对着妹妹。她摆出闲聊的姿态,双手交握,安然放在桌上。“好啦,”她说,“故事进行到这儿,我应该开始了解你了,看看你是个什么大人物。”
“祝你好运。”吉米·雷说。
“昨晚跟她睡了?”
“没。”
“打算今晚跟她睡?”
“没有。”
“你知道的,她把你当成男朋友了。”
“我不知道她哪儿来的这个想法。”
“你跟着她回家了,混蛋。你多看了她两眼。跟她说你觉得她的孩子可爱。你知道这是啥情况。”
“我一根手指头都没碰过她。”
“她连你姓甚名谁都不知道,你就住进她那该死的拖车房了。”
“是客房。”他说。
“行吧。你为什么骗我妹妹?”
“我没骗任何人。”
“放屁。你从没当过机修工。从没做过焊接。看你这双细皮嫩肉的手,就知道你这辈子没干过一天正经活。你还说了什么谎?你是个什么人?恐怖分子?连环杀手?恋童癖?”
约翰什么也没说。在手的问题上她说得有理。吉米·雷需要换个职业。
“我不管你是谁,”她说,“也不管你有什么企图。反正你别想大摇大摆跑到这儿来跟我妹妹玩过家家。你别想招惹卡门,更别想招惹我。”
“我没想招惹谁。”

“管你呢。我给你二十四小时。阿黛尔今晚跟我去住,等我送她回来时,你要是还在印第安纳,我对天发誓会扯下你一条胳膊,在院子中央用这断臂把你活活打死。听懂了吗?”
“听懂了。”约翰说。
“C. J. !”卡门的喊声从秋千那边传来,“快看这丫头多勇敢!”
C. J. 在长凳上猛地扭过身去,鼓起掌来。“天呐,阿黛尔!瞧你!”她叫道,“瞧你飞得多高!”
回到拖车房之后,约翰躺回床上,一直在那儿待着,全靠空调的轰鸣声和下压的冷气把灵魂留在身体里。偶尔起身去洗手间的时候,他觉得客房门外的寂静会把他锤进地底。闷热的空气堵住他的路,沉重得无法推开。卡门给他端来一碗番茄汤当晚餐,但他没多少食欲。
夜里的某个时候,她拽着肩带把他的背包一路拉进门来。她爬到床上,任由房门开着,走廊里的灯亮着,开始动手把背包里的东西取出来。她把装着充气筏的盒子摆在床垫上,把船桨和脚泵摞在盒子上面。她把铁链扔在床上,端详了会儿两把挂锁之后,小心地把它们放在铁链旁边。
约翰从衣服堆里钻出来,坐起了身。“嗨,”他说,“干什么呢?”
“你得告诉我,你打算拿这堆东西干什么?”
“为什么?你为什么翻查我的东西?”
“C. J. 让我查的。她说你可能是伊斯兰国恐怖分子也说不准。”
“你把睡袋拆开了?”
“你不该把上膛的枪带进我家,”她说,“家里有小宝宝。”
“你说得对。”约翰说。吉米·雷·加洛普是头蠢驴,但约翰本该明智些的。他不敢去想夏洛特或者C. J. 知道了会怎样。“你说得完全正确。我真的真的很抱歉。枪呢?”
“放回睡袋了,但我把子弹扔到田里了。”
“好吧,”他说,“好吧,这是个好办法。没事儿。”
她用食指戳了戳链条,像在试探它的死活似的。“这是干吗用的?”
约翰摇了摇头。
“你住在我的房子里。C. J. 认为你是个危险人物。你必须告诉我你打算拿这玩意儿干吗。”
见鬼,吉米·雷心想,告诉她得了,让她找到枪就已经他妈的搞砸了。
“我本打算乘巴士到苏必利尔湖,再搭个便车,深更半夜开到哪个荒郊野岭。然后,我就给筏子充上气,把水泥块拴在腰上,划到湖里去。再然后,会开枪给筏子打个洞,再给我自己头上来一枪。”
卡门一动不动地坐着,过了很久,她将那两把锁拿起来放在铁链上面,用手背抹了一下鼻子。“不好说,”她终于开了口,“那水太清了,你就算沉到一百英尺深的地方,说不定还能被人瞧见。”
“我不知道那里的水是什么情况,”约翰说,“我从没去过苏必利尔湖。”
“你怎么不等到了那儿再找水泥块,非要用工具箱拖着它全国跑?要是我的话,就直接弄件狩猎背心,往口袋里装满石头。”
“只是计划而已,”约翰说,“没完成。我没做到。现在我连个计划都没了。”
到了早上,他对自己说,她会开车把他送到印第安纳波利斯火车站。他会用自己仅剩的那点钱给吉米·雷·加洛普买一张随便去哪儿的票。他会在巴士停下的时候下车。卡门会开回科西,第二天回到罗伊纳的温迪汉堡继续打工。迟早会有另一个混球躲过C. J. 的雷达飞身而来,多看了卡门两眼,而卡门会微微笑着对他说,可以坐在她身旁,如果他想的话。
“哎呀,差点忘了,”她说,“你的霍尔与奥茨T恤我洗过了。”她从背包里取出T恤,递给了他。T恤闻着有阳光的味道,他将它捧到面前。


约翰和夏洛特初交往时曾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克莱姆森看过霍尔与奥茨组合的演唱会。那是他们第一次一同出外旅行过夜。第一次住汽车旅馆。约翰没看懂利特尔约翰体育馆的座位图,买的倒是一层的座位,可惜在舞台后面。约翰和夏洛特偶尔能清清楚楚地看到高个儿霍尔,但几乎看不见个子小得能装进底鼓的奥茨。他们唯一能看清的乐手是萨克斯手——被霍尔介绍为“随意先生”的那位——他有时在靠近他们这侧的舞台上表演独奏。
“我觉得你不戴头巾和墨镜更好。”卡门说。她伸过手来揉了一下他的头发。“那样更像约翰。”
他看着她,眼睛眨了一下:“约翰。”
“加尔。我翻到你的驾照了。”
“啊,卡门。”
“别生气哦。”
“我没生气,不过,天啊,我本想消失的。现在你知道我在哪儿了。”
她低头看着自己的双手。“而且我告诉夏洛特你在哪儿了。”
你彻彻底底完蛋了,吉米·雷想。州警随时会来砸门。用不了几个小时,他就会被强制送进印第安纳波利斯的一所医院。他们会把他关在那里,直到夏洛特办好手续,把他转回北卡罗来纳。她会把他送到什么抑郁症集训营,等他出来后,她可能会允许他搬回家,但永远也不会原谅他。每当她看到他,都会想起他曾带着一个水泥块和一把始终瞒着她的枪登上北行的巴士。
“找到驾照以后,我就在手机上搜你。整个北卡罗来纳都在找你。你在推特上很火。我给夏洛特发了条私信,本以为她明早才能看见,可是约莫半分钟后她就把电话打过来了。”
“她怎么说的?”
“她叫我保证自己和家人的安全,如果你想走不要阻拦,但如果你走了就报警。她让我告诉你她在来这儿的路上了。”
晨起穿衣的时候,约翰穿上了那件T恤。有弹性的领口因衣服在车库存放多年后早已松垮不堪,但这是他身边唯一不属于吉米·雷·加洛普的衣物。他仍然戴着吉米·雷的头巾和墨镜——是吉米·雷带他溜出北卡的,在印第安纳波利斯跟着卡门和阿黛尔下车的也是吉米·雷。反正吉米·雷这一身份似乎必须要保留到夏洛特来的时候。
在克莱姆森那晚,夏洛特一句也没抱怨过座位有多不好,但这其实是不言自明的。他们还不如坐在M区呢——懵逼区。那时他们已经一起睡过了——彼此都是第一次——但从未整夜睡在一起。约翰抓心挠肝地想跟她一起洗澡。他从未跟女孩一起洗过澡,可是谁会乐意跟他这么笨的人一起洗啊?但夏洛特能苦中作乐。她领他来到舞台底部的栏杆前,舞动着,又牵着他的手拉他共舞。每当“随意先生”晃到他们这边——她就骑上约翰的肩头,挥舞着手臂尖叫——仿佛是上帝降临在舞台后侧,吹奏着《噬男魔》【《噬男魔》,霍尔和奥茨组合的著名单曲,发行于1982年】的华彩乐段。
约翰和卡门坐在拖车房的前阶上等待夏洛特,阿黛尔在院里玩耍。他盯着豆田对面那个四向都竖有停车缓行标牌的路口,卡门倚着他,在手机上翻看约翰的脸书页面。夏洛特的发色是真的?卡莉有多高?这是你的房子?这是你的车?她给约翰看他的一张相片——他在奥兰治学院的课室里,双脚交叉着搁在教桌上,双手抱着后脑勺,脸上笑容灿烂。历史组组长。气充得满满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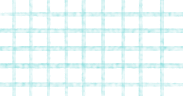


“我中学时从来没喜欢过历史,”卡门说,“我从来看不出学历史有什么意义。”
“可能确实没有太大的意义,”约翰说,“不过是些我们彼此传来传去的故事。唯一的重要问题是谁有优先权。【联系上下文来看,这句话可能有不同的理解。“谁有优先权”既可以指“在四向路口该由哪辆车先行”,也可以指“讲述历史的优先权在谁手里”。】”
曾几何时,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姑娘一同坐在印第安纳州科西市一个拖车房的前阶上。有个幼儿在院里嬉戏。男人本已踏上求死之路,却被这个姑娘无意中拦下了。在豆田的另一边,一辆白色豪车在四向路口左转,驶到豆田尽头再度左转,开上了停着拖车房的那条土路。车里的女人要来带这个男人回家。
“她来了。”约翰说。
“过来,阿黛尔,”卡门说,“妈妈给你擦把脸。”
车放慢了速度,犹犹豫豫地拐上了卡门家的车道,停了下来,车身一半在路上,一半在路外边。卡门朝车子轻轻挥了下手,车子开进院子,停在报废的庞蒂亚克旁边。约翰揪起T恤的肩膀部位朝后扯了扯,免得领子往前耷拉着。
在克莱姆森那晚,最后一次返场的时候,“随意先生”在最后一场独奏前手指着夏洛特,用口型说“送给你的”,而后双膝跪地,蜷身抱着他的萨克斯管,吹出的音那么高,还保持了那么久,连向来循规蹈矩的卫理公会信徒约翰都震惊得尖叫起来。夏洛特在他的肩膀上疯狂地又蹦又跳,他几乎都抓不住她了。周围的观众都把啤酒洒向空中。终于,“随意先生”总算结束了这个高音。他踉跄着站起身来,脸色铁青、筋疲力尽地吹奏完这段独奏的最后几个小节。他给了夏洛特一个飞吻,捶了两下心口,又指了指约翰,就消失了。乐队向场馆另一边的观众鞠躬后退场。灯光亮起。约翰把夏洛特从肩头放下来时,她跳回他的怀中,亲吻了他。你的吻。你的吻。上了我的美好清单。【霍尔和奥茨组合的著名单曲《最美好的吻》中的歌词。】离场的时候,约翰买了件T恤。
车门打开,夏洛特现身了。她皱着眉头,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找对了地方。“请问……”她说。约翰站起身来,摘掉了头巾和墨镜。夏洛特从车门后面跨步下了车。她张开了双臂。“约翰,”她说,“噢,约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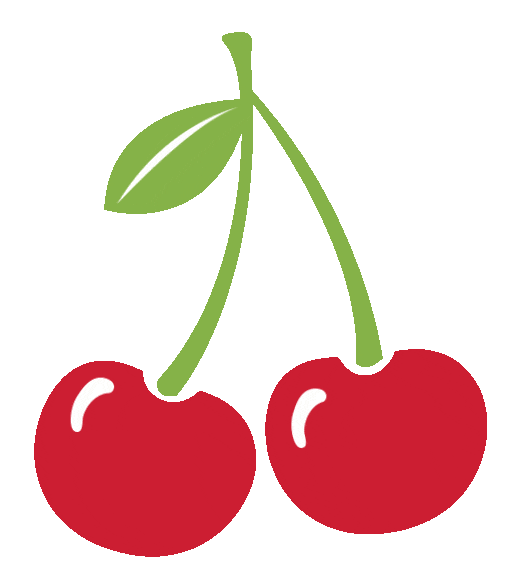
托尼·厄利 (Tony Earley, 1961— ),美国作家。出生在得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成长于北卡罗来纳州,其小说一般都以北卡罗来纳州为背景。著有长篇小说《男孩吉姆》(2000)和《蓝星》(2008),短篇小说集《我们这是天堂》(1994)和《托尔先生》(2014),获得过欧·亨利奖、南方图书奖和阿拉巴马作家奖等奖项。1983年,厄利毕业于华伦·威尔逊学院英语专业,后来在阿拉巴马大学塔斯卡卢萨分校获艺术硕士。厄利从事过记者、编辑和教师等工作,现为范德堡大学的弗莱明英语教授。此处译介的《背包》(Backpack)是厄利2018年11月5日发表在《纽约客》上的一个短篇小说。厄利的小说有青年海明威作品中的那种疏冷感,《背包》就是这样的作品,情节简单,文风朴素,但文字后面多有隐藏。
原载于《世界文学》2025年第4期,策划及责任编辑:杨卫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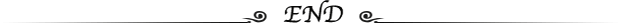
点击上图,订阅全年《世界文学》
点击上图,订阅单期《世界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