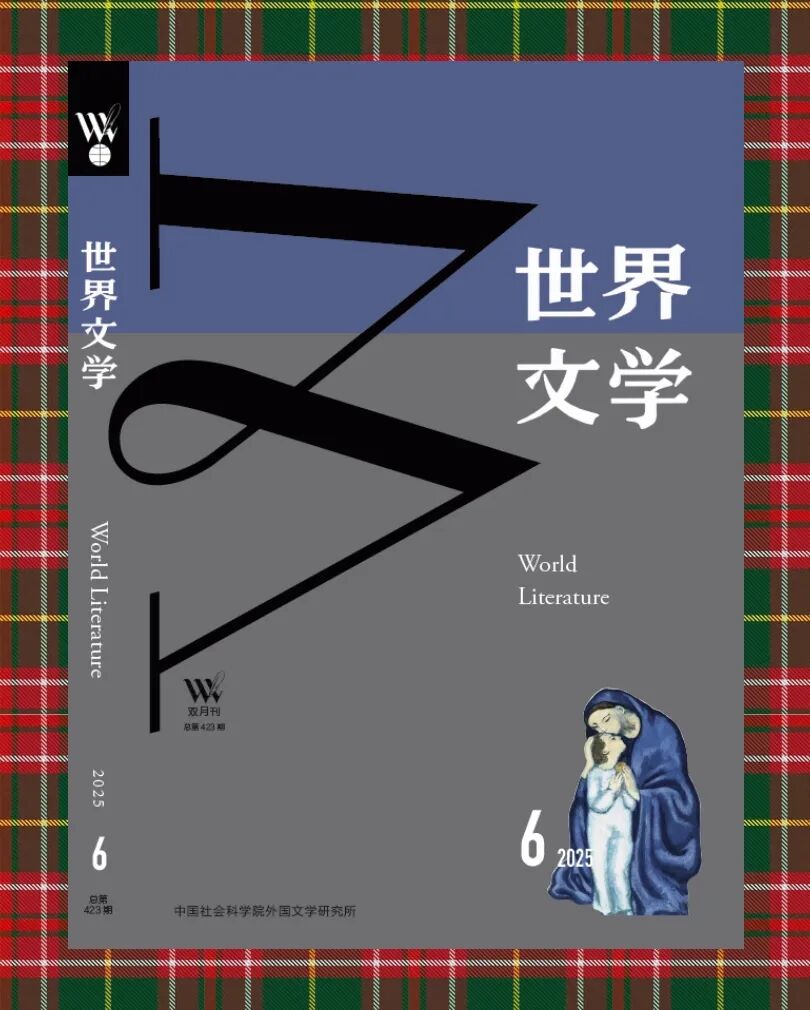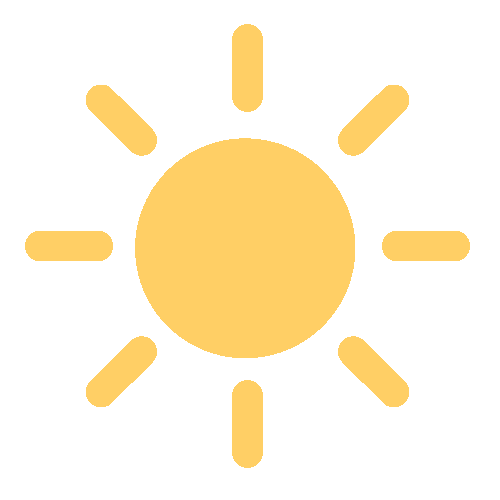小说欣赏 | 玛•玛约拉尔【西班牙】:埃娃,我的心
![]()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现在一切都过去了,回来吧,回到我的身边,或者告诉我你在哪里,我去找你。我只要一张桌子和几张纸,随你去哪里都可以。我们有那么多话要说,有那么多书要看,有那么多事要做!回来吧,或者打电话给我!
永远等你、爱你的莉莉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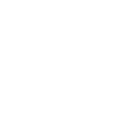
玛里娜·玛约拉尔作 杨玲译
埃娃,我的心!是我啊……
不要关掉这个页面!求你了,埃娃!我之所以学上网就是为了能够和你说说话!五万比塞塔上五个半天的课,再加上为了把这封信放到各个搜索网站所花的钱!因此,我请求你,看看我要对你说的话,哪怕之后你仍固执地以沉默作为回应,你该干吗干吗。而我却什么都做不下去,甚至不能为自己辩解,又不能去找你。在采用这个以前,我已经试遍了所有的方法,你是知道的,我并不想把我们的事儿公诸于众,但我实在找不到别的什么办法来跟你说话了。你是那么迷恋网络,而且随身带着笔记本电脑,于是我想,求助“你在何方”网站是最好的办法了。

好了,现在我想到你要读这封信,却反而不知道怎么开始了。我想请求你的原谅,我也想责备你,我想告诉你,你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你是唯一三十年来我一直都爱着的人,而且这爱至死不渝。我想对你说,我想你想得绝望,你不能就这么离开我,消失得无影无踪……如果你爸爸病了,想在临死前见你一面,那么他应该到哪儿去找你呢?我去过你家,你可怜的老爸甚至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当然,我什么也没告诉他。他看到我时多少有些吃惊,你也知道,老人都是这样的。他给我吃巧克力糖,却没有提到你。后来,他说他和你联系过,说你过得很好,但不记得你是什么时候打电话给他的。管家也不知道。对他们来说,唯一重要的是账单都按时付清了,而这些你通过银行就可以解决的。
你老爸的身体还好,我并不是想让你担心,我告诉你他的情况是因为像他这个年纪的人活一天算一天,而你确是应该留个地址给他的。已经六个月了,埃娃,太久了,几乎是永恒……再这么下去简直就是疯狂!万一厌倦了小镇的生活,你又该如何?我确信那是个偏僻的小镇,尽管这不是我想出来的,而是巴布罗告诉我的。他说:“她去了南方的一个小镇,她一直都想离开这里。”他还说我应该让你静一静。但这是个愚蠢的想法,从一开始就是。他甚至从未考虑过前因后果。他说你很能干,可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闯出一条路来,说当你想回来时就会回来的。他对所发生的一切没有感到内疚;而我却很绝望,也很自责。你怎么能为了他,先是毁掉你的事业,现在又要毁掉你的生活呢?我不想再提这件事了,因为我知道你的烦恼已经够多了,但是,你身上潜藏着巨大而高尚的美德,它们才是巴布罗应该珍惜的,他拥有你这样一个如此……如此什么呢?如此深爱着他吗?你并不是这样的,埃娃。你和他很快乐,很平静,是的。但你们除了上床,除了足球,几乎无法沟通。我不能理解,像你这样一个女人怎么会为了一个几乎无法和你交流的男人而牺牲了自己的事业、自己的前途。你先是放弃了使馆的工作,这本身就是个疯狂的举动,然后又放弃了马德里的生活。那么当你厌倦了目前的生活之后呢?你又该怎么办呢?继续逃避吗?那是无济于事的啊。巴布罗说得有道理,他说一旦回来,你马上就能找到工作,因为你是那么杰出而富有才华。但我担心的就是你的不辞而别,而且音信全无。我担心这一切都是我造成的,是我的错,因此我很绝望。我最不愿做的事就是伤害你啊,埃娃,看在上帝的份上,你应该相信我,你应该试着理解我,就像我一直在试着理解你一样……
我只想证明我所做的都是有道理的。你站在我的角度上想一想:假如你突然产生了一个灵感,然后你便开始了写作,但当你已经展开了这个故事时,却会发现它并不可信。一个人很难当好自己的法官,很难评判自己的作品,有时你会觉得一切都完美无缺,而有时你却又觉得一切糟透了,这完全取决于你的精神状态而非别的什么东西。怀疑一旦产生,你就不可能安安静静地工作了。你会想,是否有欠逼真?甚至太过滑稽?或者自己正在建造的只是一座空中楼阁……

今天的构思是这样的:一个女人给她多年来一直仰慕并深爱着的男人写了几封信,向他表白了自己的感情。之后,她却为自己的荒唐行为感到了羞愧和害怕,从而永远地弃他而去。然而,他却一直被蒙在鼓里,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从此,他们两个人,一个逃避,另一个却拼力寻找对方,两个人的生活轨道平行延伸,却始终未能交叉。要知道,这样一个原本可以有美好结局的故事使我着迷。一切都很顺利,直到我突然发现那些信根本不足以引起一个男人的兴趣,或者说,我注意的只不过是修辞,而非故事的可信程度。没有可信性,那么作品就没有生命力,你能明白吗?我必须找到解决的办法。你是知道的,很多时候我曾把我写的东西寄给你看,征求你的意见。我一向很重视你的观点。但这次不同了,我需要一个男人的建议,需要让这个故事在现实中得以验证。于是我产生了这样一个该死的主意:把这些信寄给某个男人,看看他的反应。
我当然知道,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都是一个愚蠢透顶的主意:故事的可信和文学价值是不能画等号的。生活和文学是在两个不同层面上进行的。真人真事可以充满虚幻色彩;反之,故事纯属虚构却可能叙述得十分逼真,仿佛人物就在眼前,事情正在发生。你是明白这些道理的,而且你也知道我也明白这些道理,因此请你不要以为我把那些信寄给巴布罗就是为了验证点什么。但是,既然不是为了验证点什么,那我为什么还要把它们寄给他呢?嗨!
我并不想和他有什么越轨的行为,埃娃,我以我的生命担保。巴布罗他并不吸引我,这一点我在一开始就告诉过你,那时你甚至还不确定他是否喜欢你。
我的确需要一个男人,甚至需要一个可以上床的男人,那又如何?到头了吧?至于巴布罗,还有你,我们三个人在一起的时候的确很开心。每次我和他胡说八道,比如我说最好有个穿着整齐却没有文化的男人,我真的很开心。巴布罗是个性格开朗而且慷慨大方的人,他总是邀请我,总是帮我拿东西,但仅此而已。只要单独在一起,我就气不打一处出。烦!只消说上五分钟,我准透不过气来,我从未对他表示任何兴趣,而他也从未对我有所表示。在这方面你和我是不同的,对此你该心知肚明才是。
至于你说我想把他从你身边夺走……埃娃,你总爱钻牛角尖,猫明明有四条腿,而你却偏要寻找三条腿的猫。这样是不对的,尽管你很聪明。巴布罗不像你想象的那样善变,当然也不是那么单纯,瞧,轮到他说话的时候他却一声不吭;而我更不像你想象的那样居心叵测。我已经认可和巴布罗一起分享你,我从来都在和别人一同分享你,但比起别的男人来,例如那个叫什么来着?他和巴布罗分享你的时候,我见你的机会反而比较多。那个男人虽然霸占了你的意志,却使你变得小鸟依人。和你的丈夫分享,哈,他那荒唐的嫉妒心,谁受得了?我们的关系于是就不可能太好。可以说,这四年的生活很平静,我还从来没有想过要和巴布罗开战。男人并不是必不可少的,但有一个男人爱你、关心你也是不错的,而且是令人高兴和大有益处的。巴布罗正是那种很少挑起战争的男人,这一点我承认。或许你不相信,我也很想念他,我已经习惯了晚上外出时有他做伴,就像带着一个保镖似的。自从我被带刀人袭击后,我甚至抛弃了对防身术和随身携带手枪的偏见。有他在,我感到安全可靠。因此,我向你保证,和你一样,我也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当然,应该说和你不太一样,却几乎相差不多。
我把那些信寄给他,是因为他是唯一熟识、可靠的男人。要知道,想要找到这样一个读者是很不容易的。我需要的是一个在女人堆里工作的男人,如教师、医生或者……人事主管。巴布罗是理想人选:他周围有数不清的女职员和女顾客,她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有可能写信给他。不仅如此,他还是唯一让我有机会获得反馈的人。我本应该找一个感情更为丰富、心理更为单纯的人,因为感情的微妙之处巴布罗未必都能察觉得到。然而,我周围却找不到比他更合适的人选了,因此我才会决定把信寄给他。
我以为他会告诉你。按说,一个男人收到陌生女人的情书,会告诉自己的异性伴侣,不管他相信不相信其中的内容。你觉得呢?或者他会告诉他的一位女性朋友。我是这样认为的,因此那段时间我常常制造机会和他偶遇。在我寄出第三封信时,我甚至冒着被戳穿的危险,整天都在他的商店里转悠,因为我已经等得不耐烦了。但是他什么都没说。对,只字未提。我给他寄去了最后一封信,然后焦急等待。但一切都是徒劳的。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我唯一清楚的就是他居然同样没有对你提起过,因为如果他说了,你一定会告诉我。这让我想到他一定是当真了,从而不想让你担心或引起你的嫉妒。如果他只是把这些信当成一个玩笑或者一个疯狂的举动,他就一定会告诉你。而且,我发现他比以前更加沉默寡言,不再像过去那样愿意陪我们看演出或是逛商店了。但既然你没有注意到什么,我也只好缄口了。我满意地得出结论:至少已经有一个男人信以为真了,他在自己的女人面前隐瞒了那些信,而且很可能还在密切关注周围的动静,以便找到那个神秘的写信女人。所以,这些信是可信的。这样,我就排除了之前的忧虑,继续写我的小说,把这件事抛在了脑后。

几个月后,当你告诉我说巴布罗有了情人,并说你要离开他时,我都不曾发生联想,埃娃,我真的忘了。对你来说唯一重要的是巴布罗爱上了别人,而你却不想知道任何关于那个女人的情况,你甚至不想和她竞争,但这不是正常反应。首先巴布罗并不是我的真命天子,其次你怎么能不问青红皂白就拂袖而去呢。你想一想,你和他共同生活了四年啊,而且你还放弃了使馆的工作,就算这个使馆环境不佳,远离闹市,还有黑人充斥,好吧,但你应该承认,一个女大使和一个商场人事经理在一起,唯一的解释就是这份爱情。你不应该就这样放弃这份感情。这么轻率,仿佛它只不过是一个错误。埃娃,我知道你需要时刻感觉到被爱,才能和对方一起生活。我不知道这是因为缺乏信心还是过于高傲。当他说爱上了别的女人时,你就二话不说,与他断绝了关系。你的这种做法除了骄傲,不像是因为别的。巴布罗是有些傻气,但他并不坏,他喜欢保护别人,以便体现自己的价值。如果当初你对他说你需要他,让他看到自己是多么重要,就像那个女人所做的那样,我敢保证,他一定会继续和你在一起的。可是现在巴布罗并不认为你是因为他做错了才离开他的,而是因为我。他说我像利用实验室里的小白兔一样利用了你。瞧,他是多么愚蠢啊。退一万步说,我利用的是他,而不是你啊……
归根结底,我要请你原谅,如果我不经意伤害了你,也得给我一个解释、弥补的机会。我为什么要那样做?当巴布罗告诉我说他爱上了一个给他写信、向他表白爱意的女人时,坦白说我快意极了。请原谅,说到这个我很惭愧,但事实确实如此。我有一种难以言表的快慰,恰似成功地创造了一个活人:来自头脑的思想居然获得了肌体,这种感觉如同弗兰肯斯坦博士【英国小说家玛丽·雪莱的同名小说中的人物,故事中科学家弗兰肯斯坦博士利 用人的某些组织造出了一个类似于人的怪物。】面对他的创造物一样。而我创造出来的并非怪物。但我随即想到了你,我以为我能控制局面。事实上,有人冒充了我,但我可以揭穿她的假面目,把真相告诉巴布罗。他会后悔不已,立即和那个骗子分手,回到你的身边。
我这样做了,但是生活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每个人都有一些他人无法认同的想法。你还记得那个给我写信的女人吗?她说她现在嫁给了一个警察局士官,尽管事实上一直深爱另一个男人。那是多么美丽的一个故事,我喜欢那种类型,一个曲折而又持久的爱情故事。你也喜欢这类故事,因为那个女人摆脱了农村庸俗的环境及她丈夫粗鲁的性格,最终成了一位女业主……你还记得吗?可后来她的丈夫居然也给我写了一封信,就是那个警察局士官。据他所说,他并不像故事中那个坏丈夫,而是受害者。一切正好相反。哎,埃娃,我当初觉得那故事黑白分明,结果却并非如此。唯一的坏人倒是那个横亘在他们中间的第三者,而一开始他却让人觉得是最最无辜的好人。幸好后来他死了,否则我敢保证他也会写信给我,讲述这个故事的第三个版本,把一切弄得更为复杂。
现在同样的问题在巴布罗身上发生了。那个女人说那些信是她写的,她说,因为她曾经把这些信寄给了我,而我又把她的故事美化了,用更为优美的语言写成了小说。她还说这改变不了她写信的事实。我起先很气愤,说她是个骗子。我说我写小说不需要抄袭任何人的东西。然而,她找到了我,我方知事情并非那么简单。她并不是个坏女人,埃娃。她是一个不幸的女人,一个纯朴的女人,一个需要爱情的好人。她靠阅读小说来弥补生活中的失意,她还时常写信给那些作者。她很崇拜我,读过我的所有作品,但你千万不要误认为这会影响我对她的看法。也许,怎么说呢,我也不知道……
我想说的是,当巴布罗对她发生兴趣时,她觉得奇迹来临了。因此她把我看成了专门制造奇迹的圣女,因为我使不可能的事成了可能。她已经暗恋他十年了,十年啊!你想象一下,比我们认识他的时间还要长。她现在大概已经四十五岁了,却风韵犹存。她像个修女,你知道吗,很苍白,又很规矩。她是那么崇拜巴布罗,以至于当他开始查询信主的时候就不得不注意到她了。埃娃,我相信她真的给我写过信,而且我也很可能读过她的信。我不记得了,那毕竟是很多年前的事了,也许那些信残留在我的脑子里,而后来又自己冒了出来。但她的故事确实与我的作品神奇地吻合,比如援引的《圣经》。她会背《雅歌》片段,也曾给巴布罗背诵过“站在那些少年中的我的爱人啊,就像野生树木中的一株苹果树。我渴望坐在它的树荫下,它的果实吃起来是那么甘甜”。而这段话我确实写在了我的一封信里。因此,巴布罗也就确信无疑了,因为他相信我只是个记录者,而真正的情感却来自于她。这样一来,我只是执行上天旨意的工具。她相信是上天把我安排在她的人生道路上的,使他俩最终可以走到一起。而巴布罗呢,从一只实验室的小兔,变成了好事多磨的见证:上帝用曲折的笔书写自己的旨意。

事情就是这样,埃娃,我感到非常遗憾。我从未看见过巴布罗这么开心。他和你在一起总有些紧张,好像总在努力唱高八度“do”,而现在他终于放松了,满足了,平静了,幸福了。她呢,陶醉在幸福之中。那种幸福几乎达到了你和某个男人曾经达到的境界。她一心对他好,而不是想着要获得什么。你是知道的,和巴布罗打交道并不轻松。她却什么也不需要,她只要默默地看着他,崇拜他,爱他。这就是她的幸福。
最不幸的人是我,或者你。无论如何,你一定遇到了另一个巴布罗,我是说一个陪伴你并适合你的男人。而我呢,我又怎么样呢?你觉得你这样做很好是吗?就这样丢下我,就这样放弃了我们的友谊?我们从小就是朋友,埃娃,想一想我们儿时第一次打架的情景吧……
巴布罗让我不要打扰你的平静,他说你这样离开是因为需要静一静。他还说我对你的生活干预得太多了。我不知道这是他自己的想法,还是你曾经的思想。或许他并不那么傻。求你了,埃娃,给我回信吧。我不想伤害你,也从来没有把他从你身边夺走,我向你发誓。你别把我看成故事里的坏人,尽管这已经不能更改。
现在一切都过去了,回来吧,回到我的身边,或者告诉我你在哪里,我去找你。我只要一张桌子和几张纸,随你去哪里都可以。我们有那么多话要说,有那么多书要看,有那么多事要做!回来吧,或者打电话给我!
永远等你、爱你的莉莉兹
玛里娜·玛约拉尔(Marina Mayoral,1942— )是西班牙当代著名的学者型作家。自上世纪七十年代起,她一直活跃在西班牙文坛。由于她既是名学者,又是名作家,而且关注情节,主张回归现实主义,对西班牙当代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1979年,她的长篇小说《再度纯真》获西班牙文学界年度佳作奖;翌年,她的另一部长篇小说《在另一侧》获最佳情节奖,从而奠定了她在西班牙文坛的地位。次后,她又接连发表了长篇小说《唯一的自由》(1982)、《战胜死亡与爱情》(1985)、《塔钟》(1988)、《在你怀中死去》(1989)、《遥远的和谐》(1994)、《痛苦的武器》(1994)、《身心俱献》(1996)、《记住,身体》(1998)和《天使的影子》(2000),短篇小说集《一树,一再见》(1988)、《亲爱的朋友》(1995)等,以及有关西班牙近现代作家的研究文集多种。
原载于《世界文学》2007年第2期,责任编辑:高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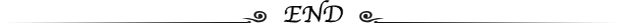
点击上图,订阅全年《世界文学》
点击上图,订阅单期《世界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