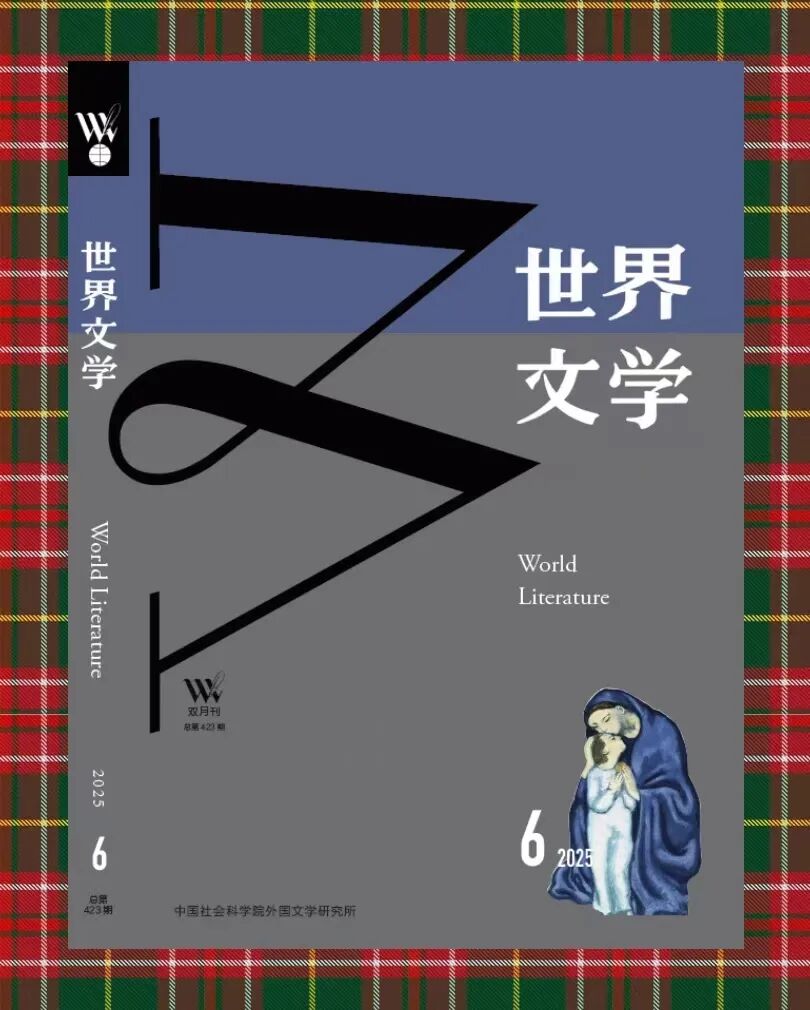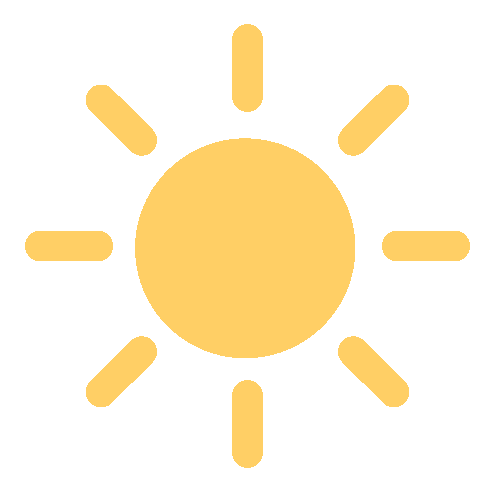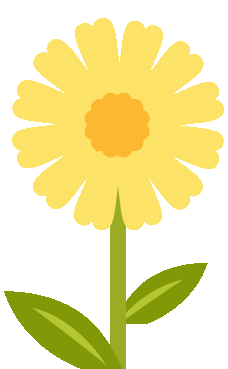第一读者 | 桑翠林:诗人的新音乐仍未耗尽,仍在奏响新的音符……
![]()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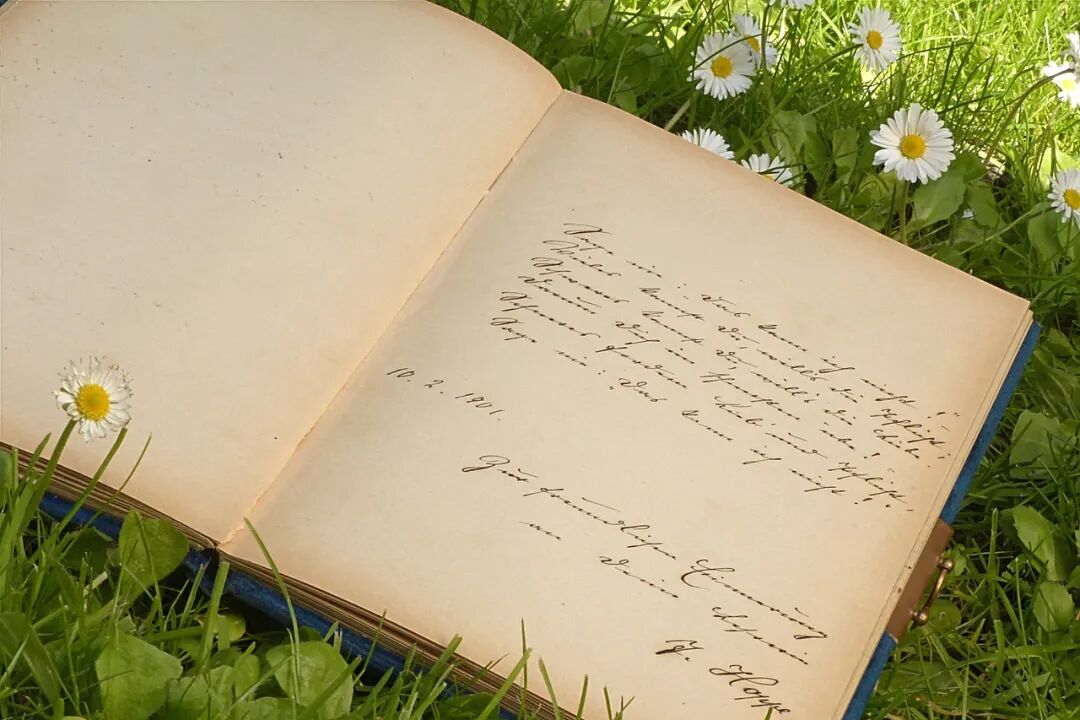
它们是颠倒(后—)世界的诗歌,也是这个世界的具身化显现。它们是外祖母写给外孙女的诗,因此语调柔软;它们也是迷途的人类写给伤痕累累的大地母亲的诗,因此充满切肤之痛。它们的情感是愤怒和恐慌之后的沉淀,也更加具有韧性、穿透力与修复能力。正是在这样的情感驱动之下,诗人的新音乐仍未耗尽,仍在奏响新的音符。
格雷厄姆《出逃者》的颠倒
(后—)世界
桑翠林
《出逃者》(Runaway)是美国普利策奖获奖诗人乔瑞·格雷厄姆二〇二〇年出版的诗集,被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评为年度最佳图书之一。这本诗集与之前出版的《海之易》《处所》《瞬/困》在创作诉求上一脉相承。格雷厄姆希望读者将这些诗集与《出逃者》一起作为四重奏来阅读。如诗人所愿,这四部诗集于二〇二一年结集出版,总标题来自《出逃者》中的同名诗歌《[生]最后的[存]人类》([To] The Last [Be] Human)。在这本“四重奏”合集的前言里,英国自然作家罗伯特·麦克法伦称格雷厄姆的诗作“直面我们星球的深时未来【“深时”(deep-time)有别于人类日常生活的时间尺度。它源于地质学,可理解为地质时间或宇宙时间,也就是以纪元乃至万世(aeons)等宏大尺度来度量的地球历史跨度。“深时未来”即指在这种深度时间关照下的未来。下文提到的“深度未来”(deep future)以及“深远未来”都为“深时未来”的同义词。”】,四个集子各司其职,依照某种“(生态)顺序共同讲述了一个故事”:“《海之易》:丰富性与陌生感;一种相移式的发生;加速与死亡……《处所》:既是动词又是名词;对所失所亡加以定位并抵达确切的落脚点……《瞬/困》:动作敏捷却又陷入困局;风驰云走却又动弹不得……而《出逃者》:一名在逃者,一种骇人的力量;无处可寻,不可阻挡;比瞬时更快;同时也是命令——快跑!消失!”
麦克法伦的评论似乎提示读者,前三部诗集都表达了处于环境危机与人文灾难之中的人类意识主体如何在极端矛盾和困境里挣扎和协商,而《出逃者》则在延续这种矛盾性存在的基础之上给出了一个貌似实际其实别无选择的选择:逃离。这似乎给了读者一种错觉,即格雷厄姆的危机故事在《出逃者》里有了某种结局:生态灾难已经开始蔓延,人类所剩的选择只有陌路狂奔。但事实上,这个根植于深时未来的故事并未止于《出逃者》。在格雷厄姆二〇二三年出版的《致2040》里,这个故事仍然在以类似或变通的方式和同样的紧迫感展开。四重奏似乎已经演变成五重奏,又或者新的多重奏正在以《出逃者》为序曲奏响。这提示我们,《出逃者》并不是这个故事的结局,而是对它的另一种深时讲述。正如麦克法伦的评论所显示,格雷厄姆在选择诗集主题方面比较钟意于能够在不同意义层面之间形成矛盾性张力的多义词。就runaway而言,虽然这个多义词不具有明显相互矛盾的义项,但词性却比较灵活。它作为形容词可以表示“逃逸”和“失控”等状态:用在“失控技术”这样的词组里,它描述的是一种超出可控范围的加速与混乱状态。作为名词,runaway并不一定专指人类或动物,还可以引申为某种现象或情状。英国版的《出逃者》封底评论说,在“气候变化、社会动荡和新的大规模迁徙等令人绝望的失控”之中,诗人竭力周旋,并试图“重新想象出一种可居住的当下,一种此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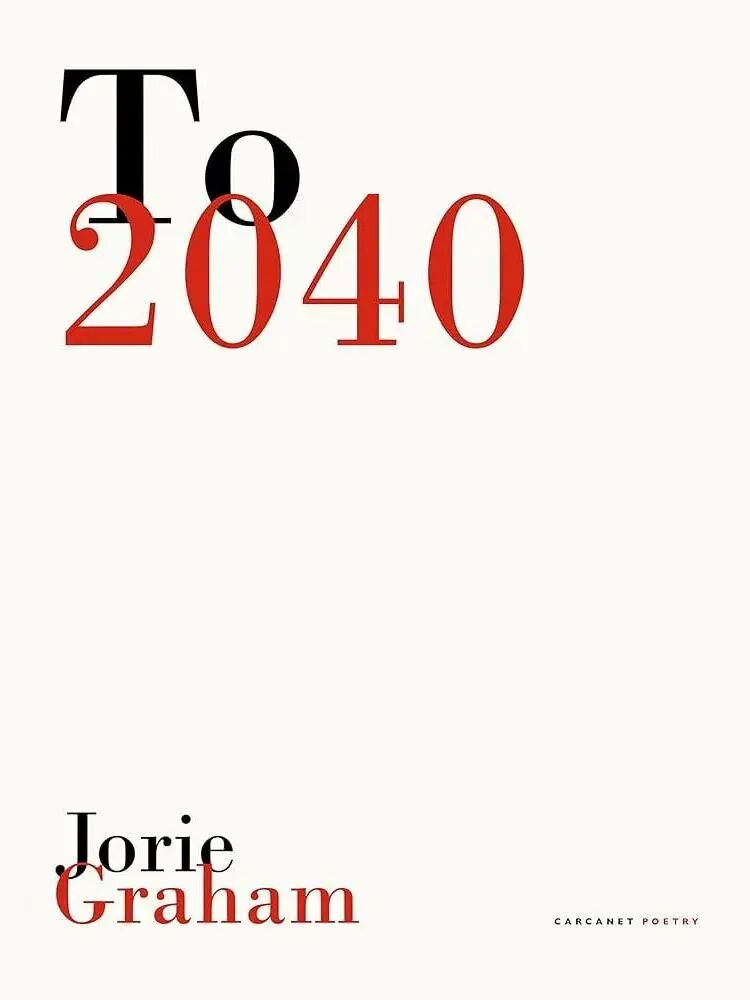
左为乔瑞·格雷厄姆照片,右为《致2040》书影
从《出逃者》这首标题诗和格雷厄姆参与设计的美国版诗集封面来看,她一直致力于讲述的故事在这本书里具象化为一场熊熊燃烧的大火:这场失控的火可理解为当下紧迫的环境与人文危机;由于点火者正是人类自己,这场失控的火也可以理解为人类意识和心灵的某种自我焚毁。由于“不远的过去”有“过多的历史”,“心点燃再多的火柴/也无法[将之]燃尽”,同时,也由于“火/不愿死去”,我们仍然效力于它,“喂养它”。在这样的情况下,心火持续燃烧,而作为点火者和喂火者的人类则只能与火为邻,在绝望里守候希望。人类与自己点燃的心火共存,暗示人类尚未丧失主动性,因而化危为机仍存在可能。也许可以说,这种共存既是在浴火与熔炼中埋葬旧我的过程,也是在此过程中等待和孕育新我的尝试。诗人多次暗示,“此时”与“此处”以及“此时此处”是新生永续之时空所在,也是跳脱出正在加速失控的线性时空或规训化时空的希望所在。
“此时此处”并非格雷厄姆在《出逃者》里的首创,而是自早期作品起就反复出现的关键母题。数十年来,“此时此处”在她的诗作里一直保持着强大活力。从作为与现代主义诗歌对话的入口开始,“此时此处”在格雷厄姆近期与环境危机相关的诗作里逐渐变得面目清晰:在一切似乎为时已晚之际,人类仍然可以寄望于这个特别的时空,因为这是一个用想象力创造的时空,而想象力以及与之相关的情感联结力正是以人类为中心的世界和世界观最为缺失的能力。此外,《出逃者》是诗人献给自己外孙女萨曼莎的诗集。这也从侧面表明这些诗的基调不是绝望,而是绝处逢生的希望。这些诗里不仅穿插、记录和描写了萨曼莎出生后的时刻,也包括她仍在母亲腹中时诗人对她的寄语与想象。也可能出于这个原因,这个集子的很多诗作字里行间浸润着细腻的温柔。虽然遣词造句会由于使用缩略语(比如,用yr代替your)而显得急迫,但这种急迫感常会被某些以极慢镜头感呈现的细节或动作消解。有些评论者往往更加关注其中的紧迫感,而忽略了更富内涵的柔软与缓慢。比如,《洛杉矶书评》称格雷厄姆的“四重奏”“承受终局的重赘”,其中《出逃者》已经没有前几本诗集与危机的距离感,而是传递了一种实时的紧迫,语义上不再有任何“延迟”。
不可否认的是,《出逃者》和前三部作品一样,都是从深时的远望与回望视角来呈现正处于剧变临界点和极度矛盾之中的当下。但这种深时视角也说明了人类在深远未来与过去的持续在场(无论是以何种形式或意识在场)。与其说这些诗集描写的是世界的终结,不如说是推倒并重塑了“世界”这个理念本身。格雷厄姆把这四本书的共同策略归结为刻意突出“方向迷失”与“祛魅”。这里“祛魅”是指通过诗歌的介入来凸显人类自我灌输的魅惑,比如人类的自我放大,以某个物种为中心的发展方向,与非人类世界的割裂等。深时既具前瞻意识,又有后顾视角,给了诗人在没有箭头指向约束的时间里解析当下空间和“超客体”(hyperobjects)的自由。生态理论家蒂莫西·莫顿所谓的“超客体”是指在时空上极度庞大、复杂且超越人类传统认知框架的实体或现象。也就是说,“超客体”,如油田、森林或黑洞等事物,具有与人类时空尺度迥异的深度时空属性,不受线性时间或常规因果链的制约。另外,“超客体”也可能具有紧迫的当下性,即莫顿所说的“粘性”(viscosity),比如全球变暖这种现象。“超客体”挑战了传统认知中的事物边界和秩序,需要我们运用反常规的认知与感知手段去理解它的在场。在专著《超客体:世界终结之后的哲学与生态》里,莫顿曾用美国诗人谢丽尔·杰曼应二〇一〇年墨西哥湾漏油事故所作之诗《午夜石油》来说明何为“调音”,即主动与“超客体”同频的艺术实践。莫顿主要关注杰曼在《午夜石油》里使用的诗行右对齐手法,认为这种对正常诗行的颠倒策略使得这首诗成为一种真正的“回应”和“深刻意义上的调音”。简言之,若要直观而深切地感受“超客体”的在场,需要装备与之协调或共鸣的认知工具;而作为仅具备人类尺度的我们,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可能就是颠倒既有的认知规训与习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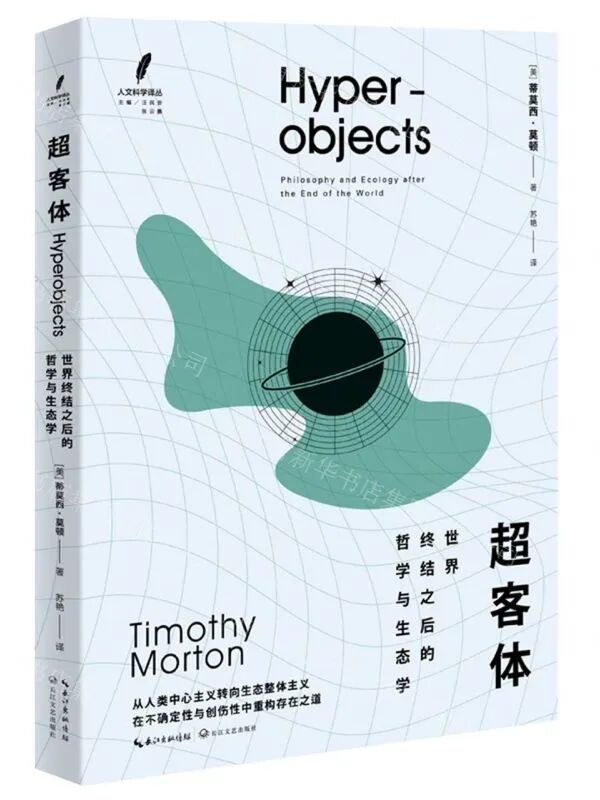
左为《出逃》书影
右为《超客体:世界终结之后的哲学与生态》书影
无独有偶的是,格雷厄姆在《出逃者》里也开始使用右对齐诗行,而且在美国文学媒体“锡房子”播客的采访里,她也提到了莫顿的“超客体”。格雷厄姆“四重奏”描述的诸多事件或现象都可以解读为从深时视角创作的某种“超客体”,不过,《出逃者》的“方向迷失”在诗歌形式和技巧层面上似乎采取了与莫顿所说的“调音”既接近也更加多样化的颠倒策略:除了从深远未来回视现在的时间线之外,更有氛围与其环绕之物、部分与整体、内与外的倒置,其中最突出的是“你”与“我”对调以及诗行向右对齐。这种环环相扣的形式颠倒层层渗透至内容层面,直至与之密不可分。这些诗作的末世、危机和灭绝主题被各种形式层面上的颠倒策略打乱与瓦解,诗人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个新的颠倒(后—)世界(类似于莫顿意义上的世界终结之后的“世界”)。这样的颠倒世界从表面上的末日警示演变为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逃逸世界”,因为其主导意识形态“逃离”了传统灾难叙事或末日思维框架,转向以想象与感觉作为公约数的另类推演。
《出逃者》收集了由这些颠倒策略所策划的诗歌事件,以想象与感觉作为认知工具,在回溯与展望中用它们组成了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经验。这种经验有时表现为处于深度未来的“我”对现在的想象,有时亦是现在的“我”对深度未来的想象,同时植根于诗人和读者正在共同经历的真实现在和共同拥有的感官经验。可以说,《出逃者》是在现有事实以及读者与诗人的默契基础上进行深时想象与感知的产物,可以表现为从一种遥远未来的、非人类世的视角来体验人类世的身体感觉,也可以表现为从人类世的视角出发来展望和探索如何解决当下的矛盾与困境。格雷厄姆将“想象”视为“同情心”和“同理心”的同义词,而在这些深时诗歌里,进行此种想象的主体是一种陌生化的、本身也是想象之对象的人类之“我”:这个“我”并非普通的意识主体,而是绵延于深时之中,并具有自我对话、自我毁灭和自我赓续的可能性。这种深时之“我”也是一种莫顿意义上的“超客体”,即不囿于人类尺度的身体、意识、灵魂和时空的意识主体。它在第一、第二乃至第三人称代词之间游移,由跨越广阔时空距离的“你”“我”“他、她/它”等复合而成。归根结底,这是一种依靠自救才能重新恢复机能或更新存在方式的主体。
在《出逃者》里,“我”与“你”所共筑的深时主体往往体现为一种对话,也正是这种对话形式使这些诗作在实验性风格表象之下具备了深层抒情特质。乔纳森·库勒在《抒情理论》里提出,抒情诗最基本的呈现形式就是“三方讲话”,即叙说者“通过对某物或某人讲话来实现对读者讲话”。从这一点来看,格雷厄姆的诗是典型的抒情诗。当然,在她前期诗歌里也曾出现过与读者直接对话的情形,但在《出逃者》里,这种与读者的沟通更多地通过“三方讲话”的方式来实现。这些诗的抒情本质提醒读者,格雷厄姆所致力于讲述的故事并不能以叙事性思维去理解,而是需要用想象、同情心、同理心等与“情”相关的官能去阅读乃至推想——打通“情”的官能是深时主体的主要自救渠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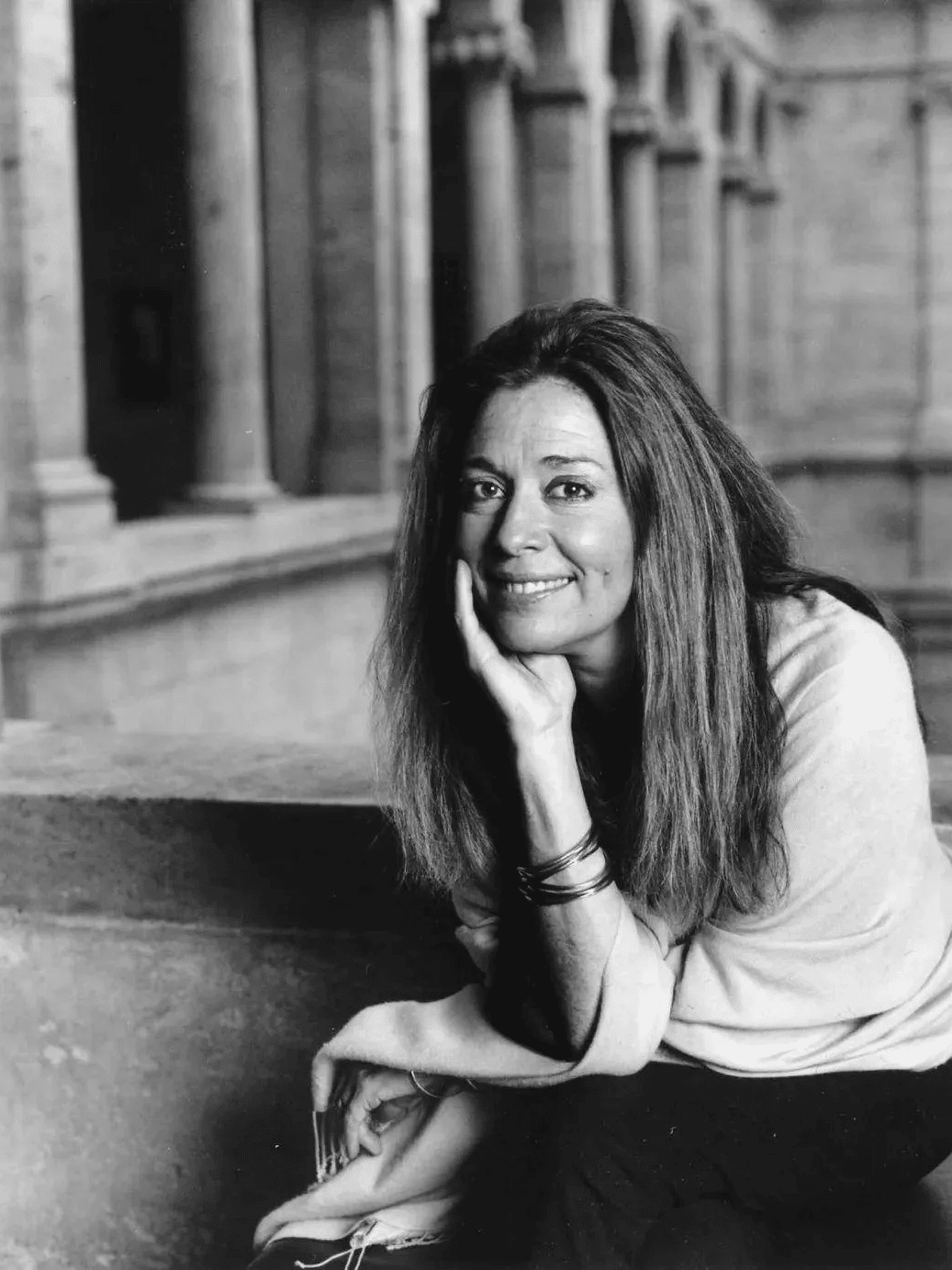
乔瑞·格雷厄姆照片
在《我没有足够的时间活着》这首诗里,作为自救路径的主要情感关联建立在遭受环境灾害之苦的“我”与仅能与“我”共享一段时间的“你”之间。在无法共享的时间里,“你”的经历将超出“我”的感知范围。“你”是否安全,能否生活在万物再次繁荣的纪元,是否会继续见证地球的枯竭,这些都是“我”无法感受但可以通过对话与想象勾勒出来的可能情境。“我”和“你”在文本表层表现为具有血缘关系的外祖母(即诗人自己)和外孙女。这是一种很多人能够与之共情的纽带:在危机笼罩之中面临未卜的将来时,长辈竭尽所能地把生存智慧教给下一代,无论是否真的会起到预想的作用。在这首诗里,长辈想要传递的信息主要有两条:一是要学会并保留与非人类生命现象形成真实联动的语言,其代表就是与鸟叫对应的“谜”——“谜”需要人们用全部的存在才能听到;二是记住“地球是你的家”。这个地球在结尾具象化为与“亲爱”(dear)同音的“鹿”(deer),也就是说,要记住与地球及其养育之万物的亲缘关系。这两条信息的共性就是去人类中心主义:人类需要立足于能够倾听非人类生命之神秘的前辈语言,并且不能忘记与其他物种共享的“此时”,才有可能转危为机。
同时,“我”与“你”依然是存在于不同身体和不同时空里的两个经验主体,而无论具有血缘关系与否,这两个人格之间的时空隔断和分离是形成某种更广义的“暗恐”关系的必要条件。在题为《交换》的诗歌开篇部分,遭受数字资本荼毒而残缺的“你”与隔离在真相之外的“我”显然并非血亲,但彼此似乎有着共同的过去,甚至拥有一种比血缘更紧密的关系:“你”在“我”的门前,而“我”在“生命里面”。“你”是某种欲望生物的再次化身,却又似乎尚未完成化身,所以“我”问道:“你此时是新生……还是旧生的残余?”“你”不仅来自不一样的时空,更是游离于生死之间的不明生物。“你”还可能是生命之外、即将在像素化现实里成形的“我”,因此是“我”所熟悉的陌生人,这也是“你”“我”之间共情和同理的根基。在诗的尾声,二者的关系已经接近甚至等同于祖孙之间的亲缘关系,同样建立在无条件的信任之上:
你必须相信我。我想同时在此处也在
你收到这个消息的彼处但我做不到。这就是完整的故事。我永远也不会知道
彼处的消息。你不会被兑换。你必须相信。


除了用类亲缘情感关联激发读者的共同想象力之外,格雷厄姆也注重在形式和技术层面上提高关联性。《出逃者》出版后不久,她接受了播客的采访,坦言自己年轻时经历了当时并不自知的巨大精神危机,并在这个时候通读了爱尔兰诗人叶芝的诗集。年轻的她在阅读这些诗歌时,除了汲取精神补给之外,所获得的最大启发其实关乎诗歌的创作层面。她发现叶芝的作品具有不可分割的完整性:每首诗里的“我”都与其他诗里的“我”相互关联;不仅如此,叶芝的每本诗集也都与其他诗集相互关联。在叶芝的启发下,她选择以一个“秘密故事”作为所有诗歌的交汇之处。但这与其说是格雷厄姆的选择,不如说是诗人与这个故事之间的一种合作。这是一个没有预设的故事,只有在一定数量的诗歌完成之后,故事的面貌才会逐渐清晰;而诗人自己也往往在完成诗歌之后才会恍然大悟,看清楚这些诗歌之间的关联。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完整的故事”(a whole story)就作为格雷厄姆诗歌的一大关键词频繁出现;也就是说,讲述“完整的故事”的意愿一直是她诗歌创作的驱动力。在不同的时期,“完整的故事”需要抵御不一样的认知分割工具,以恢复时间和格雷厄姆所谓的“历史”完整性。对她来说,“‘我’的成形是认知暴力的结果,而‘历史’则是这种‘我’的体验”。在这个意义上,“完整的故事”也许可以理解为格雷厄姆自己版本的“深时超客体”乃至完整的意识主体本身。或者说,深时里的人类主体可以在诗歌里成为去除主客体认知划分的“故事”本身。
“完整的故事”或完整的意识主体是一种不可能由“我”感受到的“我”与“你”的同时性存在。但这并不影响故事的完整性。甚至可以说,“我”的存在局限性是其完整性的必要条件之一。如《交换》结尾所示,这个故事由“此处之我”与“彼处之你”共同撰写,而“此我”与“彼你”不可实现的共处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历史认知暴力造成的残缺,使故事的原貌得以显现。或者就像《我没有足够的时间活着》里的祖孙一样,“我”和“你”必然会有时空与意识分离的存在状态。“我”在《交换》结尾那几行里的诚恳语气昭示我们,开篇两个保持一定距离的人格之间的对话已经转移到彼此更加关心的两个人格(比如祖孙)之间,也就是说,“我”和“你”这两个人称代词的所指发生了悄然转变。换个角度来说,《交换》开篇貌似彼此陌生但又有某种“暗恐”镜像关系的两个人格之间,归根结底也有类似血亲的关系。“我”与“你”、“此处”与“彼处”的距离创造了故事(或完整的意识主体)的生存时空,而“我”的自身局限性也使“你”的加入成为必然,无论这两个人格是否具有切实的血缘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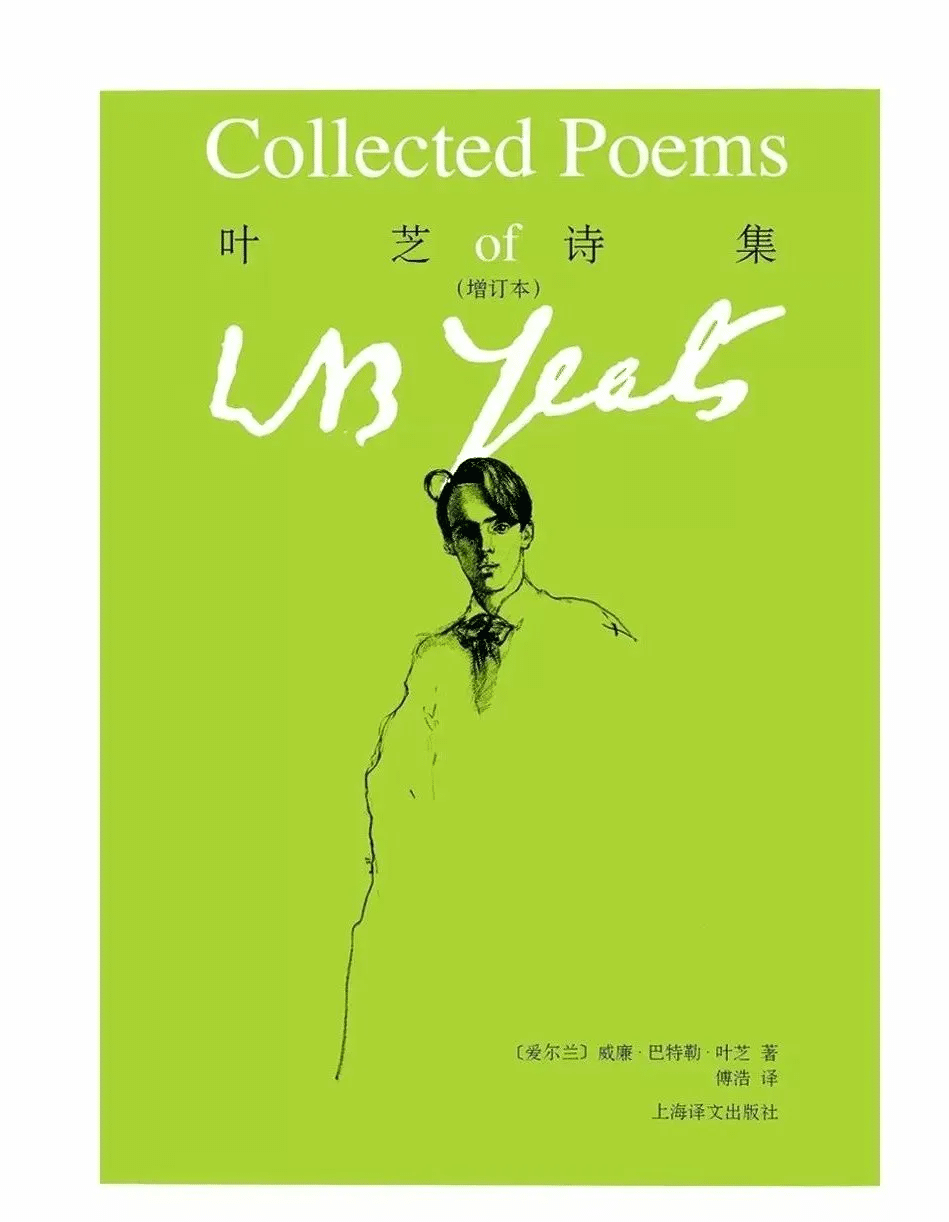
威·叶芝与《叶芝诗集》书影
从写诗和读诗的角度来说,读者也无法与诗中之人格“同时在此处也在……彼处”,但二者可以共同亲历完成一首诗的整个过程。当诗中之“我”恳求“你”对“我”无条件信任的时候,其实也是对第三方读者发出诉求。“你”和读者以及“你”作为读者都必须“相信”,也必须拥有“相信”的能力。这种未知对已知、潜能对局限的信任不仅是一种因果倒置,更是一种不依托理性却依托情感和感受来获得信息的能力,也是《出逃者》颠倒世界里的一大认知手段。这种无条件的信任可以说是一种联结意愿和行为,也属于格雷厄姆所定义的“想象”。它是发生在更广义的深时之“我”内部的联结,为深时之“我”的未知与已知状态之间的沟通提供了可能。这种自我是人类作为地球物种的某种共性自我,是失控的数字资本主义、技术和环境灾难所无法摇撼的深层联结性所在。
除了运用人称代词游移、因果倒置和以想象为认知基准等手法来勾勒全新的人类之“我”外,《出逃者》还频繁采用右对齐诗行这一鲜明的形式颠覆策略。对格雷厄姆来说,写诗主要是一个在写作中发现诗歌“音乐”的过程,也是创作意识不断延伸、探索,直至表达某种特定经验的“音乐”得以全部呈现或“耗尽”的过程。她引用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的话说,“每一种新的音乐都是一种新的意识”。格雷厄姆的每一本诗集同样也是一种新的音乐,因为正如《出逃者》所暗示,我们的意识和大脑/心既是自己的桎梏,也是一种开启未知的机关,要化桎梏为机关就要不断调整和更新(也即“调音”)我们的意识,不断寻找新的音乐。同时,格雷厄姆所寻找的新音乐种子早已在旧音乐里播下,而这种持续播种和耕作、新旧更替和新新相续的创作意识可以说体现了她从叶芝那里所借鉴的意识主体的关联性。
从先于《出逃者》的三部作品来看,诗人在遣词上积极地延伸词语的内涵与外延,利用词语本身的意指潜能同时拥抱绝望与希望,在诗行设计上也持续使用了可引发眩晕感的长短相间诗行来表达这种摇摆状态。不能适应格雷厄姆多变诗歌风格的威廉·罗根不无讽刺地称她为“伟大的诗行柔体表演者”:“几乎没有什么手段是她不愿意尝试的,也几乎没有什么让诗行扭结缠绕、拖拉延长的方法是她羞于屈尊使用的。”罗根的不满似乎源于无法定位格雷厄姆风格的挫败感以及对后者诗歌整体意义建构过程和体系的排斥。格雷厄姆并不认为自己的诗歌属于炫技派、实验派或玄奥派,而把评论者与诗歌之“隔”归因于不了解诗人专属“词汇表”。各种形态的诗行就属于格雷厄姆的专属“词汇”,而右对齐诗行就是从《出逃者》开始生根繁衍的“单词”,也是她在这本诗集里种下的新音乐。在二〇二三年出版的诗集《致2040》里,这种诗行形式仍然具有蓬勃的生命力,具有取之不竭的音乐。页面的右边往往由沉默与空白所填充,而右对齐诗行则打破了这种常规的沉默,是一种有力的镌刻与开拓。如《出逃者》的《融雪》一诗所示,右对齐诗行可以在陌生的时间乃至“时间群”里开辟新的栖居之地,即新的“破土”:
我一定不能
混淆
时间。时间群。它自带一种本来应该是新春的
清冷。我不知它是不是
气息,属于本该刚开始绽放的
花朵,或属于壤土。穿透了这种
绿色感受的
是一种正在连络和破土的
东西。是什么催它破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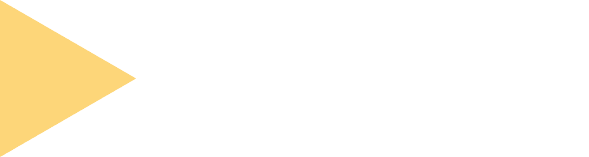
与谢丽尔·杰曼用于回应灾难的右对齐诗行有所不同,格雷厄姆右对齐诗行的“音调”更加深沉,也更具主动性。杰曼选择这样的颠倒诗行更多出于无从言表的愤怒和无以安置的诗歌韵脚:
如何讲述它
这个东西不押韵
不在抑扬格里跳动也不以可预见的方式移动
像诗行
或句子那样
在《出逃者》的语境里,格雷厄姆的右对齐诗行,相对于传统的左对齐诗行来说,也是一种出逃或失控的形式。但这种失控是对环境灾难失控的反向制衡手段。她的右对齐诗行并不像杰曼那样由一场特定灾难激发,而是她所创造的颠倒诗歌世界里的一种常驻形式。如《融雪》暗示的那样,这种形式预示了一种“破土”和可能的新生。在页面通常沉默的右边距时空里,这些右对齐诗行正在成为新的“不明之物”萌生的土壤。这些诗作不会像杰曼的作品那样去质问海龟如何在污油浸染的海里生存,不会以描绘噩梦的方式表达恐惧。或者说,它们不是一种应激式的反应,而是对新音乐的培育和新疆土的开辟。它们是颠倒(后—)世界的诗歌,也是这个世界的具身化显现。它们是外祖母写给外孙女的诗,因此语调柔软;它们也是迷途的人类写给伤痕累累的大地母亲的诗,因此充满切肤之痛。它们的情感是愤怒和恐慌之后的沉淀,也更加具有韧性、穿透力与修复能力。正是在这样的情感驱动之下,诗人的新音乐仍未耗尽,仍在奏响新的音符。
桑翠林,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文学院教授,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英语文学博士。目前主要致力于现当代英语诗歌研究与译介、比较诗学和互媒诗歌研究。在国内外文学研究期刊发表多篇论文,并曾为英国利兹大学华语文学中心和英国诗歌刊物《伯明翰诗刊》撰写书评与诗评。本文为教育部规划基金项目“乔瑞·格雷厄姆诗歌的互媒元现代性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2YJA752016。
原载于《世界文学》2025年第6期,责任编辑:叶丽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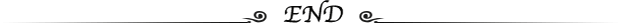
点击上图,订阅全年《世界文学》
点击上图,订阅单期《世界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