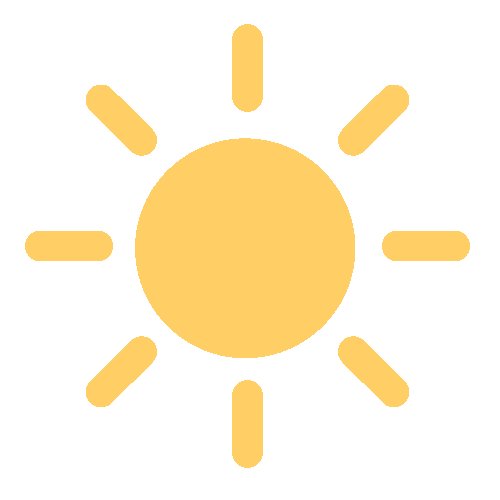小说欣赏 | 亚•茨普金【俄罗斯】:双引号
![]()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这些信时长时短,时冷时暖,时频时疏。有多少人的一生就分隔在这些纸页的两边,它们从一个终身监禁的犯人手中辗转到了另一个犯人的手上。
双引号
亚历山大·茨普金作 黄小轩译
记得那是九十年代末的一天,我又喝大了。二十杯长岛冰茶,可真是好酒。喝的时候,什么都迷迷糊糊,几天以后清醒过来,还是迷迷糊糊。不过当时的我觉得舒坦极了,还和旁边的人聊了起来。
那人告诉我,他小时候就移居去了以色列,现在时常会回来看看。我突然想起一个关于移民的故事,便前言不搭后语地给他讲了起来。故事大概是这样的……
八十年代末。人人皆知苏联就要垮了,可未来会是什么样,却无人知晓。真正的闪米特人【指阿拉伯人、 犹太人和马耳他人】和冒牌的闪米特人都在忙着移民。政府大概觉得,犹太人除了脑子什么都不需要带,于是限制携带任何能到那边售卖的物品出境。外币换来的是蹲监狱,所以要移民的人都想法子带些东西走,以便刚到的时候能换点必需品。这在今天听来可笑得很,但在当时可一点都不好笑。许多人离开时被迫舍弃了积累大半生的财产与声名。不过在与“上帝的选民”的斗争中,政府的狡猾总是输给他们的冒险精神和天赋异禀。他们总能想出各种办法,把所有想要的都偷偷带出去。其中最末流的,是把黑鱼子酱藏在行李箱中偷带出关。当时海关规定,每人只准带两罐鱼子酱(大概的数目。不过这也不重要),现今用来销毁食品的那种焚化炉那时还没问世,因此一旦超额就直接没收。
那些没收的“犹太人的鱼子酱”大概最后都被海关人员给卖了。我父亲的一个熟人,被抓到的时候坚决不肯上交。他看着带肩章的强盗们,心里快速计算了一下他们的利润,果断打开那些蓝色罐头,当场吃了个干净。在飞机上他难受得很,不过还是把鱼子酱带回了祖国——以不宜出售的形态。他的事在圈子里传开了,大家带鱼子酱的时候都谨慎了很多。不过还是有一个小伙子把多出来的鱼子酱卷在衣服里试图带走,被发现了。英勇的同志们找到了五盒偷带的鱼子酱,正准备按顺序销毁这些违禁食品。痛苦的走私者并不打算用自己的健康冒险,他开始请求他们允许自己多带一些鱼子酱,因为他到了那边根本不知道靠什么养活自己。他很诚恳地请求着。海关人员则回答他说,犹太人即便变成乞丐也是活该。他恳求得越发卑微,而海关人员沉浸在掌权者的幸福感中,丝毫没有心软。
最终,弱者屈服了。他忧伤地看着这些祖国的象征,作最后的告别:“拿走吧,小心别噎着。”
“快滚蛋,”鱼子酱狂热分子说道,“我还要去检查你所有的罐头,行李箱和信箱也都要查。得看看你的信都是写给谁的,这也不是件小事!”

两天之后,海关人员被打断了鼻梁,还掉了两颗牙。那个不幸的移民在彼得堡的混混堆儿里可是相当有名,他跟鱼厂商量好,特制了一批限量版的黑鱼子酱。铁皮罐一切正常,里面装的却是“进口”茄子酱。海关人员并没有打开罐头,而是和往常一样直接卖给了那些小贩。这个玩笑他们一直都没想明白。
当时那小伙子还偷带了一些宝石,在鱼子酱风波之后反倒没有被细查。
旁边那人听了我的故事后哈哈大笑,随后脸色又黯淡了下来。他问我想不想听听他的故事,一个关于移民和信件的故事,没那么有趣,却是真实发生过的。我记得,他是这么开头的……
你们大概不知道,在七十年代,人们若是离开,便是永远地走了。
这个说法,如今听来有点吓人,又有点怪异。永远地走了。想象一下,你决定了要去美国念书,和往常一样跑到奶奶家,和她聊起大洋彼岸科学研究的种种优势和前沿经验,而她的脸却没了血色。她就那么看着你,好像是要一次把你看个够,而她也一下子就老了。她知道,以后再也见不到你了。永远。而你也突然感受到了空虚和寒冷。难以忍受的空虚。难以忍受的寒冷。
你抬头看看身边的家人、朋友,就能明白了。哪怕是监狱都允许探视,而且大部分人还能熬到出狱回家的那一天。可那些从苏联移民走的人,既没有权利回家,也毫无指望。因此当时人们都竭力争取一家人一同离开。
而在这种冷酷的体制下,悲剧自然是无法避免的。
索菲娅·亚科夫列夫娜决定留下来。她的儿子米沙和儿媳塔尼娅则决定离开。没人想要去征求从小在奶奶身边长大的十五岁的廖涅奇卡的意见——既然是有更好的去处,怎么能让孩子来做这种选择呢。
他会受不了的。
奶奶留下来,是为了爷爷科里亚。她很爱他,而他并不想离开。他把米沙当成自己的亲儿子抚养长大,就算他没被同化成犹太人,也多次因为旁人称他的新家人为“犹太佬”而大动肝火。


科里亚爷爷并不是个死心塌地的布尔什维克,对于米沙和塔尼娅的离开,他也并不气愤,只是十分难过。他自己还有两个孩子,不过通常来说,如果一个男人用自己全部的精神世界爱着一个女人,那么也会全副身心、毫无保留地去爱这个女人的孩子,甚至比对不爱的女人所生的亲生子女还要爱得多一些。至于廖涅奇卡,就更是与他的亲孙子无异。
当周围人开始陆续离开的时候,科里亚爷爷想起当年在战场上遭遇的一次炮击。全排只剩下他一个人,每一颗炮弹飞过,他都祈祷这是最后一颗。每次米沙和塔尼娅去看他的时候,他都特别害怕,怕他们突然说“我们也要走了”。因为害怕,他甚至几次称病不让他们来。不过炮弹躲得过,命运却是躲不过的。那天晚上,所有的人都哭了,除了索菲娅·亚科夫列夫娜。她的眼泪流在心里,谁也看不见。
其他人还在拼命地安慰自己,绝望地欺骗自己,说天无绝人之路,总有法子再相见。只有真正勇敢的人才能直视真相的瞳孔。他们就这么一直看到最后一刻,不会轻易移开自己的目光。
米沙,塔尼娅和廖涅奇卡走了。科里亚爷爷久久地望着飞机的轨迹,好像期待他们还会掉头回来。廖涅奇卡也一直看着舷窗,他跟父母说,以后要叫他廖尼亚【“廖尼亚”和“廖涅奇卡”都是“阿列克谢”的爱称,“廖涅奇卡”多用于称呼孩子,“廖尼亚” 是成人用的小名】了。
他们开始用书信联系。当时政府为了切断人们之间的联系,采取了各种措施,甚至打跨国电话都成了一个大麻烦。家里的电话是打不到特拉维夫的。
特定的地点,特定的时间——对于年轻人来说打电话都是个难题,更何况是两位老人呢。因此只能写信了。这些信时长时短,时冷时暖,时频时疏。有多少人的一生就分隔在这些纸页的两边,它们从一个终身监禁的犯人手中辗转到了另一个犯人的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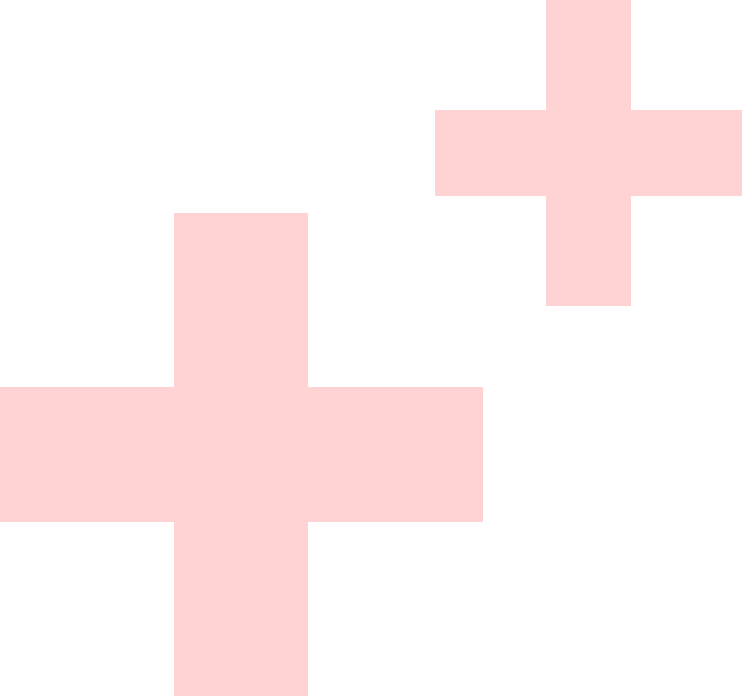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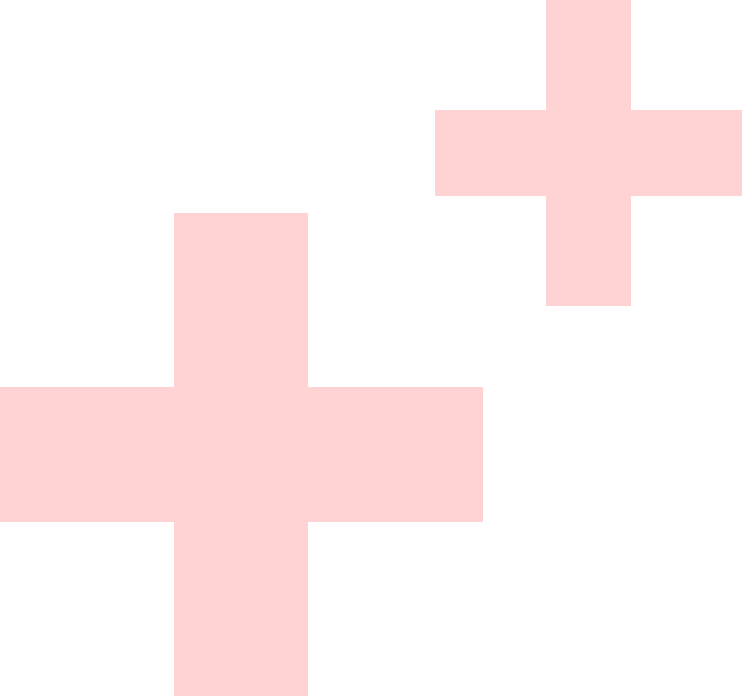
心里的眼泪是世上最烈的毒药。三年之后,索菲娅·亚科夫列夫娜病倒了。黄昏的夕阳总是落得格外快。恰好这时候米沙摔断了胳膊,只能用打字机打出信件。
他每次都在信里道歉:因为在郊外工作,只有周末才能偶尔回家,所以总是没法打电话过去。这个时候的索菲娅·亚科夫列夫娜已经没有力气自己读信了,更多时候是以色列情报官科里亚爷爷读给她听。索菲娅奶奶把信都收在床头柜里,有时候抱着这些信睡去。她去世的时候,枯瘦的手里还攥着这些信。
科里亚爷爷那个时候还能去电话站打电话。廖涅奇卡还是什么也没有说。他说不出口。
他的爸爸并非摔断了胳膊,而是在六个月之前,不小心掉进一月冰冷的海里淹死了。正巧那时奶奶突然病了,谁也不忍心把真相告诉她。廖涅奇卡得知奶奶恐怕时日无多,便和妈妈商量着,一起编了骨折和郊外工作的故事。当然,他们也没有把真相告诉科里亚爷爷。于是从那时开始,廖涅奇卡一边以自己的名义写信,一边以父亲的口吻打印出信来寄给奶奶。索菲娅·亚科夫列夫娜去世几周之后,她的最后一封信才辗转寄到。
邮局有时也是这般无情。
信是写给廖涅奇卡的。寄到的时候他已经进了部队。信中只有四句话,字迹歪歪扭扭,虚飘无力。
“我亲爱的廖涅奇卡,谢谢你替父亲写的信。我以前总是跟米沙说,叫他好好教你语文,不要总是出错。不要忘了爷爷。他是那么爱你们。奶奶。”
廖涅奇卡哭了。在心里。这之后,无休无止的阿以战争开始了,他们却再也没有哭过。
科里亚爷爷终于还是等到了他的廖涅奇卡。整整十五年。他俩终于服满了刑期。
廖涅奇卡为这个沉重的故事向我道了歉,而后不知怎么就不见了。大概是我喝的长岛冰茶太烈了些。
我当时就想着,不要回到苏联时代。永远不要。
// END
亚历山大·茨普金(1975— ),俄罗斯作家,出生于列宁格勒,毕业于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国际关系专业。2015年,茨普金将其早年间在网络上发表的小说集结成册,出版了短篇小说集《不惑之年的女人》,该书一问世便在读者中引起巨大反响,成为当年颇为畅销的讽刺小说集。茨普金的语言风格轻松明快,简洁有力,多有对当代俄罗斯人生活的调侃与讽刺,金句频出,被评论者戏称为“流氓抒情小说”,作家本人也被誉为“当代左琴科”。而比起惹人大笑不止,茨普金似乎更擅长让读者流泪,时代悲剧与无常命运交织出的动人故事让读者在心灵的震撼与净化中重拾生命与爱的美好。茨普金被认为是近年来颇具特点的俄罗斯作家之一,是新媒体时代借助网络获得极大成功的文学活动家,更是拓展文学传统边界、开启阅读新形式的重要人物。
原载于《世界文学》2020年第6期,责任编辑:孔霞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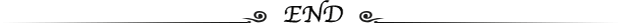

点击上图,订阅全年《世界文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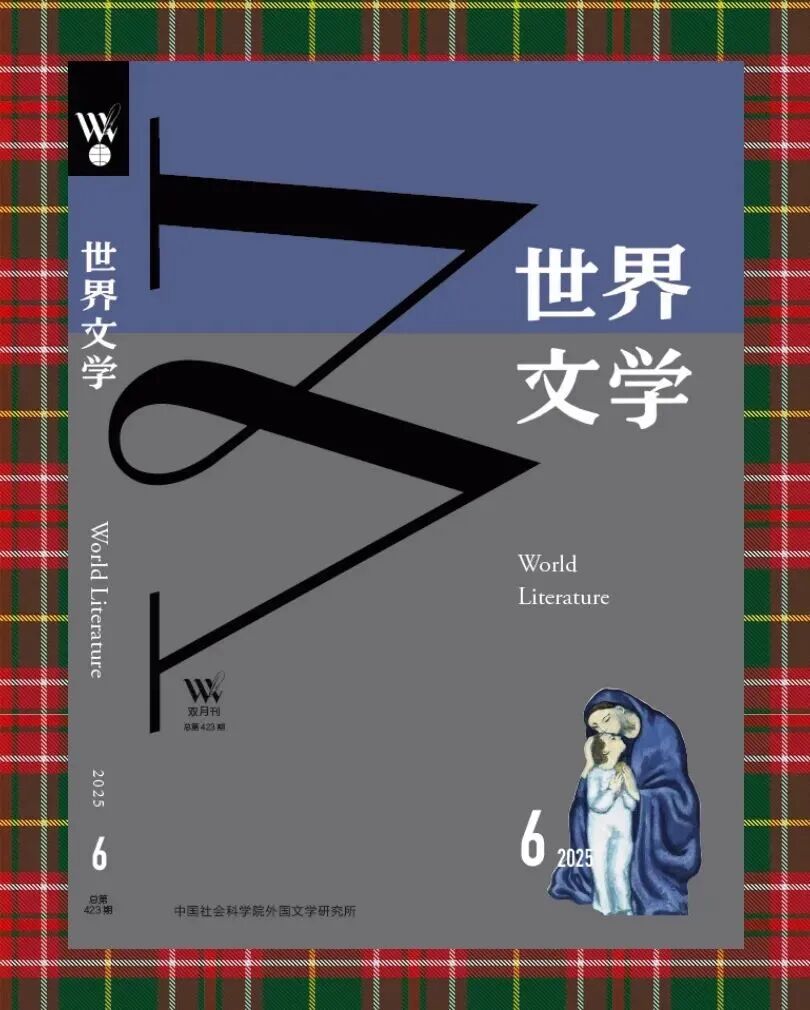
点击上图,订阅单期《世界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