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 | 古典学新视野:中西早期经典研究论坛
编者按:本次会讯材料由上海大学文学院提供,感谢授权“古典学研究”公号推送。

会议集体合影
2019年6月21日—23日,由上海大学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中心、上海大学古典文明研究中心联合承办的 “古典学新视野:中西早期经典研究论坛”在上海市延安饭店举行。来自国内外各高校及研究所的近40位专家学者莅临了本次论坛,并围绕论坛主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就如何解读中西早期经典文本以及如何拓展古典学新视野提出了各自富有价值的见解。本次会议共分为六场,关于中国早期经典与西方早期经典的探讨穿插进行,经过与会学者的共同努力,本次研究论坛完美落幕。现将会议所取得的成果综述如下。

上海大学古典文明研究中心宁镇疆教授首先致词热烈欢迎所有学者的莅临并致以诚挚的感谢,继而对举办本次“古典学新视野研究论坛”的重要意义进行了概述。他说道,不论是中国早期经典还是西方早期经典都是人类文明宝贵的财富,举办本次研究论坛,一方面有利于我们努力修身,完善人格,另一方面也能为进一步推动国内古典学界的学术交流作出贡献。

宁镇疆教授致辞
6月22日上午共有两场,第一场由同济大学张文江教授起头。《周易》作为“五经之首”、“三玄”之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典籍,深入理解中华文明必须理解《周易》。张文江教授认为在传世的经典文献中,中华文明的制高点概括于《周易·系辞下》第二章。此章展示的观象体系和古史序列,建立了中华学术的结构,形成了中华文明的认知基础。张教授为我们详细解读了此章的内容,认为此章中所呈现出的五个主要发明和八个具体的发明已经涵盖了人类生活的各方面,而伏羲、神农是最初的创制,主要和自然有关,黄帝、尧、舜进一步的创制则主要和社会有关。垂衣裳的等级制度,可以认为是政治的开端。由八卦而文字,由简而繁,逐步形成经典,归结为“六艺”和“六经”,标志政治文明体的形成。张教授最后还贯通源流,联系到今天的文明建设,指出若为重新辨认方向,提高文明自觉,必须追溯世界各文明体的源流演变,也需要重新认识中华文明体的源流演变。

张文江教授发言
上海大学文学院杨秀礼老师以《易经•同人》卦为中心,对殷周礼制与《周易》卦爻辞进行了还原性解读。他首先提出了与通常所认为卦爻辞是杂乱无章的组合的不同看法,认为结合当时的礼乐文化会发现有一部分卦爻辞是有逻辑的,并且呈现线性的或者非线形的结构。且《周易》卦爻辞涉及到不少礼制仪节,虽本作揭示《易》道史例之用,却保证了其史料真实性,可作殷周礼制研究的重要史料,同时系统化整理《周易》礼制,对《周易》卦爻辞的整体性解读也有所裨补。随后他疏证了《同人》卦的各爻爻辞,最后杨老师指出,随着考古等新材料的发现,以及学科方法的不断创新,尤其是时代精神的呼唤,《易》礼之学将历久弥新,丰富殷周革命的具体历史细节,可补益当下文化建设;同时也将溢出《易》礼学本身,对《周易》的文学性解读产生新的启发。

杨秀礼老师发言
作为集古希腊口述文学之大成、古希腊最伟大的诗作,荷马史诗显然是本次会议必不可少的主题。重庆大学高研院古典文明研究中心张文涛研究员探讨了《奥德赛》中“宙斯的正义”这一主题。他首先指出荷马的两部史诗共同合成荷马思想,不能偏废。对《奥德赛》主题的讨论即是对整个荷马史诗基本主题的呈现,且“宙斯的正义”这一主题不仅存在于荷马史诗,在荷马以降如赫西俄德以及古希腊悲剧中也反复出现,这说明“神义论”主题实际上涉及到早期的古希腊对整个包含着天、地、人、神系统在内的宇宙秩序的基本表达。他认为“正义”一词首先不是道德性的含义,更宽泛的是秩序上的含义。但在《奥德赛》中,更加突显的仍是“正义”的德性含义,这类似于古典时期哲人笔下的“正义”。奥德赛中的正义问题呈现在两部分之中,其中有三个节点,其一是奥德修斯回家为何会受到阻碍,这也显然是理解荷马写作本部史诗用意的关键;其二是奥德修斯对从人变为神的拒绝;第三个节点是未完成的开放性结尾,即奥德修斯在卷十一中下到冥府预知了他具有神秘性的结局。这三个节点都跟正义的问题是相关的,张老师重点阐述了奥德修斯受阻的原因,认为奥德修斯受阻主要是因为“神义论”,神是正义的,人受苦是因为人自己做得不对,如宙斯将阿伽门农被妻子杀掉的责任从神自身上撇开。奥德修斯之所以十年没能回到家园,主要是因为他得罪了波塞冬,“智慧”恰恰是奥德修斯受苦的原因。所以,如果沿着这个解释线索,我们会发现,奥德修斯的遭遇大概已经接近后来悲剧诗人索福克勒斯要探究的求知导致受苦那个著名主题了。
 张文涛研究员发言
张文涛研究员发言
浙江工商大学陈郑双老师对《伊利亚特》第一卷的内容进行了释义,他从特洛伊战争的起因入手,详细探讨了战争的真正起因可能并不只是为了美女海伦,夺取海伦只是一个勉强的借口,希腊与特洛亚两方都对此心知肚明,希腊借此远征劫掠,特洛亚则可借希腊之入侵而集聚力量。阿伽门农只有在远征特洛亚的大军中才掌握了作为希腊盟军领袖的实权。陈老师认为,出征外邦的远征大军构成了一个更为真实、更有力量的政治共同体。随后,陈老师将焦点放在了阿伽门农与阿基琉斯的冲突之上,人们往往将正义首先理解为公平,然而他们两人对于公平的理解却又不尽相同,表述各异。阿基琉斯将话题引向公义,而阿伽门农则将其引向传统意见。同一件事可做不同的表述,阿基琉斯可称自己因遭受不义而撤离战场;阿伽门农则可将阿基琉斯描述为以公义的借口趁机逃跑。阿基琉斯不愿接受阿伽门农不义的统治,阿伽门农则认为任何对他权威的挑战,都是不义的行为。是否能以正义的方式推翻现有君主的统治,这似乎是一个政治哲学层面的难题,古今中外对此聚讼不已。阿基琉斯此时尚只是拒绝服从,就已被称为叛离,如若他做出主动攻击的姿态,无论结果如何,他将面临如何在言辞中自辩的问题。阿基琉斯咒骂阿伽门农,此时他似乎也不再谈论公正。涅斯托尔让双方停止争吵,从争吵的结局我们可以看出,阿基琉斯在追求公正的争论中一败涂地,阿伽门农则展现了他作为王者的政治手段。

陈郑双老师发言
来自加拿大的Ehud BenZvi教授以Classical texts in the so-called West: Opening a Conversation为题作了讲述,上海大学历史系黄薇老师翻译并评议。他先定义了何为西方经典,即在整个上千年的社会变迁里面,政治、经济、文化甚至宗教等会发生巨大的变革之外的那些不变的核心文本。这些核心文本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圣经文本,一类是希腊罗马文本。尽管这些核心文本会在不同的时代被加以不同的利用,但他们被运用的场景是不一样的。Ehud教授将讲述重心放在圣经文本上,圣经文本在一些方面承担着希罗文本所不能替代的作用,主要有两点,一是圣经文本在神学上具有可靠性,圣经文本揭示的是真理,即使得不同的阅读群体认可文本所认同的真理。Ehud教授随即举了诺亚方舟的例子,诺亚方舟等同于基督教教会,人们只有在基督教会内部才能生存。接下来,Ehud教授提出了四种解读圣经文本的方式,解释、探讨关键词意义以符合读者的认知、添加对于文本的历史背景的解释、把文本中的某一解释放在一个更大的叙事框架下然后提供意义以及找到一个合适的文本去解释当下的现实,即圣经文本可以变成解释当下的资源。

Ehud BenZvi教授发言

茶歇过后,学者们开始了第二场讨论。诠释《论语》的传统由来已久,但采取何种途径则众说纷纭。复旦大学历史系林志鹏教授以《论语》“子罕言”、“子绝四”二章为例,通过相关异说的梳理,揭示了经典诠释的多种途径。林教授开门见山地指出,寻求“内证”是传统经学家的金科玉律,但研究中国早期经典,尤其是先秦的诸子文献,此一原则不能无条件地接受。限于时间关系,他重点以“子罕言”为例进行了阐述。他首先列举了关于“子罕言”的三种断读和解释意见,随后逻辑严密地从“量化”、“义理”、“语法”几个方面进行了疏证,同时按“与”、“仁”、“言”的顺序一一行进,结合前人的说法一一进行了阐释。最后,他介绍了“子绝四”章的新解,他认为站在文献学的立场,通过异文对勘可以尽量地恢复文本原貌,即使所获只是一种可能性,但不能轻言放弃此一语文学的考证方法。他将此章的异文线索引出,并尝试提出了新的解释,以此提供诠释经典的不同思路。

林志鹏教授发言
除了不胜枚举的传世文献,当今的出土文献也呈井喷式增长。江西师范大学王刚教授则以新近披露的海昏简资料为基础,对海昏《论语》文本及相关问题从五个方面做了初步的研讨。在篇章结构问题上,他认为海昏本《论语》有篇题、无篇序,应该反映了抄定古书时,对传统习惯的保留,属于篇题完善化之前的规范本。在分章样式上,每章文字另行书写,分简抄定,应该是古书早期形态的孑遗,反映了由章而篇,由篇而书的情形。在容字及相关形制问题上,通过海昏简及相关出土材料,他认为汉代《论语》文献主要向两种规制和容字量靠近,而两种不同的形制集中于海昏《论语》之下,说明偏于《齐论》的海昏本应存有内、外篇。在书写形制上,它们通过简长和容字的不同来加以区分。在异文问题上,通过文句的错讹,可以说明西汉武宣时代不仅鲁《论》有误,原本不误的齐《论》至东汉后也有了缺失。而在古今字的选择上,比之汉初以来文本新旧杂陈的过渡性,海昏本作为西汉时代的善本,显得更为古雅,保留古字而未改。

王刚教授发言
老子的著作、思想已成为世界历史文化遗产的宝贵财富。同样基于出土文献讨论,上海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宁镇疆教授以郭店简《成之闻之》篇为基础申说了《老子》思想的礼学背景。他先是结合2015年发表的《周代礼学:<老子>思想最基础的知识背景》一文再次提出了与学界根深蒂固的《老子》反礼之思维定势相悖的观点,随后以《成之闻之》篇加以佐证。宁教授将该篇共分为六个部分,一一进行了详细地绎读与疏证,并频频引《礼记》相关内容与之相参,他还特意指出《老子》思想以礼学为背景最大的障碍就是其书38章的“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云云者,宁老师除了借以上内容对此加以反驳外,还认为就38章上下文语义背景看,“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句与前文逻辑上明显存在矛盾。此句“礼者……”显然是全称判断,应该包括一切“礼”,这就与前文所谓“上礼”存在龃龉:既然一切“礼”都有问题,怎么可能还有“上礼”?所以,他认为此句绝非老子所能道,当非故书之旧。由此得出结论,郭店简《成之闻之》篇六句可以说都体现了礼让原则,礼学实是《老子》学说基本的知识背景,亦决定了其思想的一些基本倾向,故其书只可能产生于礼学尚有浓厚影响的春秋时代。

宁镇疆教授发言
中国人民大学古典文明研究中心博士生顾枝鹰对古罗马思想家西塞罗的《图斯库路姆论辩集》这一题名进行了发微,他认为这部《论辩集》有着与西塞罗的其他著作不同的奇特标题。他从“图斯库路姆”和“论辩”两个关键词出发,分别疏证了西塞罗为何要以此为他最厚的作品取名。最后,他得出结论,图斯库路姆小镇在罗马城墙之外而依旧与罗马政治密切相关。类似地,西塞罗的这番教育也出于政治而依旧指向政治。《图斯库路姆论辩集》不仅在行文上与西塞罗其他哲学作品之间有不可敉平的根本差异,而且其书名本身已然暗示,西塞罗以反驳性哲学论辩为文教来应对罗马政治变局以及由武教导致的政制巨变。

顾枝鹰博士发言
北京社会科学院王双洪副研究员立足于《论基督君主的教育》来探究伊拉斯谟的政治伦理和教育理想。她认为《论基督君主的教育》一书是伊拉斯谟政治伦理和教育思想的集中体现,这部著作体现了他成熟且丰富的思想,表达了他对基督教世界最大的期望——和平、和谐,拥有真正的信仰、教育和繁荣,同样的思想可能以不同形式散见于其他著作中,但所有关于政治哲学的思想无不涵盖于此书中。这本书承续着自古希腊以来的一种传统——许多重要的哲学著作中,政治与教育的理论会同时出现,不是探讨统治者如何做贤君,就是谈论老百姓如何做臣民。现如今,我们已很少讨论关于君主或者统治者的教育,我们只是作为受教育者存在。因此《论基督君主的教育》中政治伦理和教育思想至今仍大有可资借鉴之处。王老师的讲述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对《论基督君主的教育》第一章的绎读,第二部分是将伊拉斯谟的《论基督君主的教育》和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进行比较。进而王老师提出,伊拉斯谟对于君主教育的思考对于我们当今的精英教育显然有所启示,几个世纪前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的政治伦理和教育思想在提示我们思考道与术、德性与技术、权能在教育中的位置和作用。我们能够承认,未实现的理想在精神领域不失为一种强大的力量,它昭示并代表了一种需要,这种需要在高处引领着人类精神朝向一条向上的路。

王双洪副研究员发言

6月22日下午的讨论以受柏拉图对话启蒙的学者发端。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江涛老师就《理想国》中“苏格拉底为什么返回洞穴?”这一问题探讨了柏拉图式政治哲学的视野转换,他主要关注《理想国》中的“洞喻”。他先根据情节将洞喻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514a-515c)描述了囚徒在洞穴中的生存处境。第二阶段(515c-515e)描述了囚徒解放的过程。第三阶段(515e-516e)描述了囚徒走出洞穴,获得了真正的解放。第四阶段(516e-517a)描述了囚徒返回洞穴的过程。王老师指出并区别了学界如何理解比喻的本体存在的两种解释,即“统治论”和“教育论”。统治论的解释存在一定的问题,一是情节上的,即如果返回洞穴是为了统治,那么这个人不应该回到自己的位置上,他应该站在矮墙后面;另一个困难由罗森提出,即洞穴中没有共同生活,也就没有城邦,这样一来洞穴与城邦就没有很好地对应。由此引出了另一个解释,即教育论。王老师接着论述道,教育论表面上直接反对统治论,但它并未反对统治论中的政治哲学倾向,因为教育论的要害在于不仅将囚徒理解为城邦的公民,而且也理解为这些公民的灵魂,而对灵魂的理解也是政治哲学的,即把灵魂理解为具有政治秩序的灵魂统一体。但教育的困难在于如何理解教育转向的问题,根据卷七哲人教育的内容,哲人促使青年从变化事物转向不变事物的教育(特指数学教育)。然而,在“教育论”中,数学事物属于可知世界,因而位于洞外,但是使囚徒转向的教育却发生在洞内。统治论与教育论共享这两个前提,一是走出东西的哲人必然看见了太阳,二是整个哲学教育是不依赖logos或不依赖言辞的教育过程。但我们发现苏格拉底的哲学活动与这两个哲学前提都是不一样的。一,苏格拉底一直坚称自己是无知的,不认为自己占有真正的智慧;第二,苏格拉底哲学活动非常依赖logos与言辞,这与洞喻中的哲人形象有着非常大的距离。这个距离在苏格拉底本人那里表现为沉到意见的世界中探寻真理,这样可以避免走出与洞穴带来的,也就是进入可知世界会忽略可见世界事物的危险。

王江涛老师发言
广东社科院哲学与宗教研究所万昊老师以“智术师教诲中的死亡与谎言”为主题对柏拉图《欧蒂德谟》(282d4-286b6)进行了详细地绎读。《欧蒂德谟》中以苏格拉底的叙述呈现了总共五场对话,万老师强调,五是一个奇数,奇数意味着必然会出现一个孤立而没有对应的中间对话,即决不能忽略的第三场对话。第三场对话中,苏格拉底接过克忒斯珀斯的话头,分别对狄奥尼索多洛斯与欧蒂德谟兄弟轮番发问,最终承认自己由于愚笨而犯了错误,败下阵来。在这一轮问答中,尽管欧蒂德谟兄弟天花乱坠的驳斥在苏格拉底的追问下有些乱了阵脚,苏格拉底始终坚持这对智术师兄弟是在刻意掩藏最高的东西,不愿展示惊人的智慧。万老师对通常所认为《欧蒂德谟》有两个重要的主题——对常人的教育和智术师与苏格拉底的关系在这篇中表现出类朋友的关系存疑,并通过文本分析的方法求证这个结论是否正确。万老师通过“苏格拉底的期待”、“爱智慧与死亡”、“通过哲学道路的中断”、“智术师的困境”、“苏格拉底的引导”和“以死亡为始终的哲学”六个部分对《欧蒂德谟》中的第三场对话进行了文本细读。通过细读,他认为在智术师的表层理解里“爱智慧”与“死亡”是划等号的,这不是谎言,由此可以推导出苏格拉底与智术师的关系暧昧的原因,在这篇对话中是因为智术师既拥有最高也拥有最低的哲学,但这种哲学如何被呈现是需要继续被探讨的。

万昊老师发言
上海大学文学院肖有志副教授详细地翻译并疏证了《斐德若》中柏拉图的苏格拉底的前赋,即苏格拉底的第一篇爱欲讲辞。肖老师指出,柏拉图的对话不仅包含言辞,也包含行动。这篇爱欲讲辞在形式上不是为了发现什么,而是教导人。并且,有其内在的行动,也就是劝导,劝导小男孩应该讨爱欲者还是没有爱欲者欢心。肖老师将这篇讲辞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是序歌,第二部分下定义,第三部分出现中断,第四部分讨论爱欲者的好坏,讨论爱欲是什么要跟讨论爱欲者的好坏连结在一块;随后肖老师各自讲述了四部分的具体内容。最后,他强调苏格拉底的两篇爱欲讲辞实际上是一篇,一篇说爱欲是坏的,一篇说爱欲是好的,对爱欲的理解包含着辩证法,甚且爱欲与辩证法直接关联。

肖有志副教授发言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娄林老师的文章《今人与居,古人与稽”——<儒行>引论》来源于他的一个疑惑,即孔子很少谈“儒”,但后世用“儒”来指孔子传授的学问本身。这篇文章有两个前提,一个是比较现代化的,现在的学者讲究学术价值中立,那么当我们在分析《儒行》或传统的儒家学说的时候,采用客观分析的角度,这会导致理论过强而实践过弱,导致理论构建越来越复杂,但很少有愿意实践的人。第二个前提是《儒行》会强调儒者之行,但一定有诗书礼乐易春秋的研习才有“儒行”,而非某种政治姿态。娄老师随即例举了宋儒及道学家对本篇的争议。娄林老师文章的第一节论述了强调《儒行》很好地回答研习并践行六经的人如何称许自己。第二节处理的问题是《儒行》文本的语境。第三部分重点讲到《儒行》一篇两次最受重视的历史时期。自宋太宗开始,进士及第以后,皆由皇帝钦赐《礼记·儒行》,这一制度几乎延续了整个北宋时期——除了王安石变法期间的反复,确立了《儒行》篇独一无二的历史地位。整个北宋朝,《儒行》篇的地位非常高。第二个时期是晚清以后,从章太炎先生始,陈柱、唐文治、蒙文通他们都会谈到《儒行》砥砺人心的作用,鼓舞起儒者在读书时呈现出的外在的行止。正如章太炎所说:“周、孔之道,不外修己治人,其要归于《六经》。”《六经》的呈现需要外在的政治形态。

娄林老师发言
上海大学历史系黄薇老师则论述了贺清泰对《传道书》“智慧”概念的塑造,贺清泰的《圣经》译本是2014年才出版,因此对于学界而言是一本非常新的研究资料。贺清泰的《圣经》汉译一方面隐含着天主教传统对圣经文本的理解,与此同时,他还需要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下寻找相匹配的概念与之对应,这显示出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与接受。本篇论文中关注《古新圣经》中《智德之经:训道篇》 中“智慧”概念的汉译,尝试观察中西传统就此概念进行对话的线索。

黄薇老师发言

茶歇过后,学者们将视野从《圣经》移至继承了荷马之志的古希腊悲剧。重庆大学高研院古典文明研究中心罗晓颖副研究员对欧里庇得斯悲剧《希波吕托斯》进行了深入且细致的分析。罗老师从神之争、人的不同“自然”以及欧里庇得斯作为诗人之罪三个方面出发,对神义的瓦解这一重要问题进行了细致的探讨。《希波吕托斯》的开篇和结尾分别是两位女神出场,女神是这部悲剧作品的起点和情节推动力。爱神阿佛洛狄忒与狩猎神阿尔忒弥斯之间的较量从不停止,但是无辜的人成为她们较量的牺牲品。菲德拉身上的支配因素是血气,她在爱上希波吕托斯以后变得毫无节制。但是,爱名誉与尊崇礼法产生了极大冲突,最终她只能通过自杀维护名誉。希波吕托斯是一种非常特殊类型的人,他对女人、权力、婚姻等都毫无兴趣,是一个缺乏爱欲的人。而欧里庇得斯的罪是作为悲剧诗人的罪,他在此剧中的一重罪是渲染好人受苦,另一重罪是在神的事情上撒谎。因此,通过这个悲情故事,欧里庇得斯并没有为陷于爱欲困境的人提供真正的出路,反而在对“好人总是不幸”和“神是恶事根源”的渲染中,使得城邦传统的神之正义秩序濒于崩溃。这样的诗人或许真的不是城邦合格的诗人。

罗晓颖副研究员发言
扬州大学文学院胡镓老师处理的问题是为什么阿里斯托芬喜欢批评欧里庇得斯。他认为一般学界或阅读者会给出三个理由,第一是欧里庇得斯背弃了古希腊悲剧传统;第二个理由是欧里庇得斯渎神;第三个是欧里庇得斯的政治倾向与阿里斯托芬有很大差异,但胡老师对以上三种看法都不敢苟同。他认为阿里斯托芬嘲笑这位悲剧诗人的理由,与其在《云》一剧中嘲笑苏格拉底的动机相似,属于喜剧诗人对悲剧诗人与哲人在智识方面发起的竞赛。他接着阐述了自己何以得出此等结论的原因,他将这部剧作分为三个部分,并重点阐述了前两个部分。阿里斯托芬的核心观点可概括如下:他以呈现阿伽通错误的摹仿论和摹仿认识来呈现悲剧诗人对真知的无知。他借助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阿里斯托芬本人对阿伽通这位新锐悲剧诗人的戏仿,阿里斯托芬在舞台上呈现出来的可笑以及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对阿伽通的批评,来呈现阿伽通对“摹仿”的无知。第二个问题是通过呈现欧里庇得斯的错误,来呈现老派诗人的对真实认识的缺陷,他们的错误主要体现在对真实的认识不够完整。胡老师猜测这是阿里斯托芬要和悲剧诗人与苏格拉底这样的哲人斗智。如果这个猜测是合理的,那么这篇文章就有助于我们理解阿里斯托芬的另一部剧作——《云》。我们认为阿里斯托芬批评苏格拉底败坏青年,因为他引入了新神和新的哲学。但如果阿里斯托芬对苏格拉底的批评在于他认为苏格拉底对真实的认识存在缺陷,那么我们对《云》的认识是不是就会有些改观呢?

胡镓老师发言
浙江社科院陈明珠副研究员将关注重点放在亚里士多德对悲剧人物的论述。就《诗术》中对悲剧人物最明显的界定来看,陈明珠老师注意到亚里士多德《诗术》第2章中称悲剧摹仿对象是“高尚的行动者”,充满积极正面的道德德性意味;而第13章对于“悲剧人物”的经典介定则称悲剧人物“声名显赫,气运亨通,却并无卓异美德”,几乎完全消解了悲剧人物身上的德性光辉。为何出现如此明显的前后矛盾?她从“高尚与声名”、“德性与机运”、“突转与过错”、“公允之人与悲剧人物”几个方面来细致追踪《诗术》论述行程,联系亚里士多德哲学大全集,诸如《修辞术》、《尼克马各伦理学》、《政治学》及《形而上学》中的相关论述,理解隐藏在亚里士多德对悲剧人物这些看似矛盾论述中的深刻内涵。经过一番细致的论述,陈老师认为,亚里士多德的所有论述是环环相扣的,这种论证,某种意义上完美“摹仿”了思维的认识过程,摹仿了我们“逻各斯”运动中的过错、突转和恍悟。我们甚至可以说,在伦理生活、道德德性方面,人们推理认识的过程往往是悲剧性的,我们总是在犯错中学习,在受苦中成长。

陈明珠副研究员发言
来自德国Justus-Liebig-Universität Gießen的Michael Reinhard Heß教授做了关于伊斯兰教的殉道者的报告,上海大学历史系陈浩老师进行翻译并加以点评。Michael Reinhard Heß教授首先提出“殉道者”其实是一个比较矛盾的概念,因为“殉道”一词的起源是法庭的见证者,但是这个见证者必须要死掉,所以殉道者只能出现在虚构的语境中。他接着从最早的《吉尔伽美什》的殉道者概念追溯到古典时期再到伊斯兰教,另一方面,他又从语义学的角度追溯了阿拉伯语中“殉道者”跟犹太教国际语言的概念之间的联系,这种方法对我们中国学者显然是一种参照。于是,他发现这一概念从古典到今天是有很深的延续性的,可以找到一条十分清晰的脉络。从见证者到殉道概念的转变,Michael Reinhard Heß教授认为最关键的节点是基督教,之所以有“殉道者”的概念是因为基督教的发明。

Michael Reinhard Heß教授发言
上海大学历史系赵争老师以基于出土文献的讨论为中心,重新思考了汉代《诗经》流传及《诗》学家派问题。三家《诗》、四家《诗》的概念已经成为一个不证自明的先天合法性的概念,当出土文献多了之后,在研究时首先会提到一个诗学家派。在这里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判断标准问题,二是方法问题,譬如用字,诗本义和诗本事,即三家《诗》《诗经》异文及诗本事与《诗》学家派的对应关系并不确定,作为判定标准的相关《诗经》文本及传习者的《诗》学家派划分方案也不确定,因此根据异文及诗本事无法推断相关材料的《诗》学家派。汉代《诗经》流传及《诗》学家派呈现出一种官方与民间、统一与分化并行的双轨制状态,四家《诗》概念框架并不能涵盖汉代《诗经》流传及《诗》学家派的整体生态,有必要重新思考四家《诗》概念框架的适用边界问题。

赵争老师发言
同济大学中文系徐渊教授颇具新意地证明了“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古曲的定名,并兼论了春秋战国新声的兴起及其地域特征。一般认为《文选》所录宋玉《对楚王问》一文中“下里巴人”、“阳阿薤露”、“阳春白雪”指的是《下里》《巴人》《阳阿》《薤露》《阳春》《白雪》六首古曲的曲名。根据新旧出土数据,可以论定《下里巴人》《阳阿薤露》《阳春白雪》实为三首古曲的曲名。由于汉魏人在征引这些曲名时的特殊习惯,使得后世的学者误将《对楚王问》中所引的曲名当作六首古曲。厘清古曲曲名对于重新认识战国时代的地方新声起着重要的作用,由此可以窥见春秋战国时代对于以《诗经》为代表的传统雅乐的全面革新。

徐渊教授发言

6月23日上午论坛继续进行,本次论坛第五场由上海大学历史系把梦阳老师开场。他探讨了古代正史的列传中经常出现的一种“乞代”、“义释”的故事类型。在面临盗贼围困之际,传主主动乞求盗贼让自己替同伴赴死,进而感化盗贼将其释放。这类记载最早见于汉晋时代。一般而言,传主所维护的同伴往往是其亲属或长吏,因此这也成为正史中表现孝义事迹的一种经典范式。但与其他常见的超自然、反理性的模式化书写不同,由于古代频繁发生的大规模饥荒与贼乱,这为“乞代”“义释”在事实层面的成立提供了逻辑合理性;此外,其所体现的孝悌或忠义的道德准则,亦使得“乞代”“义释”具有被不断模仿与再现的可能。把老师认为,史书“模式化书写”之成因,除了外部的观念因素之外,亦可通过“模式”本身加以探讨。

把梦阳老师发言
湖南大学文学院吴明波老师则将关注点聚焦于罗马史。吴老师从对罗马的开端思考与对罗马从强大到衰落原因的思考这两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帝国衰落是一个历久弥新的问题。在罗马共和末期到帝制早期,有很多知识人都探讨罗马共和的衰落的缘由,而这些探讨都会把问题上溯到罗马早期的历史,回到城邦的开端。吴明波老师通过分析西塞罗、撒路斯特、李维和维吉尔差不多同时代的四位作家笔下的早期罗马历史,探讨“开端”与罗马历史的叙述模式之间的关系。西塞罗、撒路斯特、维吉尔与李维都处于罗马历史的重要时刻,他们都看到罗马共和国的衰落,除了西塞罗外,其他三人都见证了罗马帝制的开始。这样对罗马历史的重要叙述和思考就有了借古鉴今的意味。他们都或多或少美化了罗马早期的历史,借以呈现罗马衰落的道德化解释。吴老师分别从建城与罗马的历史生成,王政与政体更迭以及尚武与道德化的历史三个角度展开,认识罗马历史叙述中的“兴一衰”模式,政体更迭模式以及道德化历史解释模式。从这些不同的叙述和解释模式中,我们可以看到作家们在城邦与个人灵魂之间建立对应和关联,在历史叙述中有其独特的哲学思考。

吴明波老师发言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刘梁剑教授探讨了“身家国天下”意象的内在结构、利弊得失及现当代转型,同时通过“身家国天下”意象体察隐喻和意象思维的一般特点和中西之异。“身家国天下”意象隐含内-外图式、本-末图式、涟漪图式。内-外结构突显了中心对于外围的结构性优势,与之相应便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外围对于中心的内在建构意义,忽视外围自身的独特性,及其有别于中心的独特性。本-末图式、涟漪图式分别将植物生长与活水的经验用隐喻的方式投射到由身、家、国、天下所构成的社会生活之域,构成了中国思想的一个特色。在当下中国的语境中,“身家国天下”意象的缺陷以及由此意象所引导社会政治实践层面的缺陷不容忽视。异者别之、弱者强之,“身家国天下”意象的当代转化亟待实现。在方法论的层面,刘老师尝试在意象考察的层面进行哲学语法考察。

刘梁剑教授发言
复旦大学历史系邓秉元教授首先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以“经典时代”称先秦时期的诸子与经典诞生的时代,那么这个时代是怎么出现的?第一层从历史学的维度讲,经典时代脱胎于更早的古典时代。另一层面他称之为古典世界,它的观念形态看起来来自经学之前的东西,但它与经学的形成是交织在一起的,巫术与神话传统表达的观念形态甚至延伸到很晚。他认为应该用经典时代形成的思维看待我们的文化传统。因此,他主要借助了山水的观念说明这个问题。比如《周易》中的八卦观念是重要的支柱,从逻辑上讲山水观念要早于天地的观念。“天”的观念来自后来五行中的“火”。他对此做了一些考察。其中第一部分是对古典世界的定位,巫文化对早期文化的作用。第二部分是山水的观念,比如通过山我们可以与神灵沟通,山是神灵所居。水的观念在有形的天地之先,同时水的样态是混沌的,它比有形天地起着更为本源的作用。这个混沌、不可测的力量一方面是生命之源,另一方面也是毁灭性的,因此水与死亡也有关系。水中隐含着生命的裂变,裂变之后形成了文明。最后邓老师总结说山和水的冲突是本源性的,这也与后世经典时代的反思有着密切的关联。

邓秉元教授发言

论坛第六场,北京大学哲学系郑开教授从语文学到哲学的分析进路论述了《逍遥游》中的“卮言”,他认为《逍遥游》中的语词、修饰色彩、篇章结构都扑朔迷离,需要进一步探讨。从哲学研究上看,分析哲学语言区分于日常语言,使文本更加清晰;并将语文学的规律与思想史的规律——特别是哲学——结合起来。譬如“逍遥”这一语词,从“逍”与“遥”的概念入手,这种方法其实是不确切的,此“逍遥”与“消摇”并未探究其深层次的含义。鲲鹏寓言是不是“卮言”呢?這是一个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鲲鹏”语词的滋生和衍化遵循一定的语文规律。“逍遥”、“窈窕”、“昆仑”、“混沌”都是叠韵语词,“鲲鹏”亦如此。《庄子》中的“卮言”既具有鲜明的语文特色,又具有深邃的哲学意味,耐人寻味却难以索解。实际上,惟有诉诸从语文学到哲学的分析进路与方法,才能更好地揭明“卮言”的意义,因为这种文体形式或者修辞特点出深刻的思想动机。《逍遥游》尤其能够反映“卮言”那种“有意味的形式”之特质,其本质是不言之言,即为旨在打破日常语文形式、突破日常思维局限的哲学语言。

郑开教授发言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李锐研究员以“寡过与年化”为主题,由《庄子》论述了《论语·宪问》中的蘧伯玉和孔子。李锐研究员首先提出,古典文献的训诂中,有两种方法,以本经证本经,以子证经,《论语》在秦汉的时候不属于经,而属于传,后来成为经典。《论语》中很多对话失去了背景,有很多解释人云言殊。李锐研究员通过《庄子•寓言》来讨论《论语》中的一处对话。他提及《论衡·问孔》篇云:蘧伯玉使人于孔子,孔子曰:“夫子何为乎?”对曰:“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使者出,孔子曰:“使乎!使乎!”非之也。黄侃认为,孔子是赞赏使者,但黄晖认为“非之也”以及“孔子非之也?且实孔子何以非使者,非其代人谦之乎?”表明孔子对使者的回答并不满意。蘧伯玉和孔子是有很多交集的,关于二者之间的关系,根据《史记》和《庄子》记载,蘧伯玉比孔子年长,当孔子到魏国时,蘧伯玉已经相当老寿,不大可能治政,孔子则是五六十岁。而“欲寡其过而未能”,此一回答未必有什么问题。所以孔子若有所非,应当是围绕“欲寡其过而未能”。然而,蘧伯玉未必有什么过。其实,问题在于“化”与“过”是常见的通假字,其实蘧伯玉是否真的在寡其化,是未知的,孔子也不知道。因此,如果将“过”读为“化”,结合《庄子》,那么《论语·宪问》章中有关的问题或许就能得到更深的理解,而并非求之过深。《庄子》虽多寓言,但是有很多内容还是应该认真看待的,至少可以推进有关研究。譬如我们可以继续追问的是,孔子自谓“六十而耳顺”,庄子却说他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这二者之间可能存在着一些关系。

李锐研究员发言
中山大学中文系刘志荣教授立足“圣贤‘出处’之道”从主题和篇章结构两方面对《论语·微子第十八》进行了详细地析义。他开篇引证朱子《论语集注》和南朝梁皇侃《论语义疏》对本篇的评论,他认为“皇疏略显消极,亦未能通括全篇,朱子语则较为圆通。”他解释道,“出”为出来做事;“处”为退居全身。他认为《微子》篇言“出处”,所记述的多为事迹,然而所记之事多不离道,道则不离事。尽管孔子所处之时代已经与我们相距甚远,但君子之“进退出处”,也应该有章法可循,通过学习古圣先贤的行事,无形之中为我们树立了法则。刘教授接着说到,“进退之处”之道是古学,这在出土文献郭店简中也可找到例证,如《穷达以时》中近乎结论的句子“穷达以时,德行一也。”然而刘教授认为《论语》此篇所记有其特殊之处,《微子》灵活通变,有合于易理,胜于后人所言。限于时间关系,他围绕圣贤出处之道这一主题大致概述了对本篇共11章的义疏。在篇章结构方面,他列举了两种看法,即或以为有其次序安排,或以为乃杂记各事,并以典籍加以例证。刘教授同意前者看法,认为本章不经意之中自有安排,以结构言,最近于音乐的结构,可比拟于交响乐。

刘志荣教授发言
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姜振帅副研究员解说了《托拉》书卷的祭司文本中的社会空间。他想强调的是,空间的建构不可避免地带有社会文化的印记,他从三个部分进行了讲述。首先是对上帝空间的理解。一方面与耶路撒冷圣殿的失去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当时的波斯帝国时期的宗教文化的影响有着直接的关系。第二个是人的空间,首先是政治空间,因此在表达中,在先祖叙事中,他们的先祖不是在以色列而是在两河流域。其次是作为人文空间的“会幕”,上帝的荣光可以跟随具有流动性的会幕,也就是说以色列人在哪儿,会幕就在哪儿;会幕在哪儿,上帝就在哪儿。最后就是自然空间,因为犹太人要弱化锡安山,强调旷野。通过对《托拉》书卷的祭司文本里所描写与建构的多种空间的讨论可以看出,由于当时犹太民族的流放、故土的失去、耶路撒冷圣殿的被毁、国家与王权不复存在等,祭司文本对于同犹太民族相关的空间概念认知中注入了新的要素,也在与宗教礼制相关的空间表达中赋予了新的社会意义。祭司文本对空间要素的重新解释一方面反映出了犹太民族在流放及后流放时期处于的历史情形,另一方面也对犹太群体在流放时期身份的建构、在动荡时代的延续、以及早期犹太教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姜振帅副研究员发言
作为本次研究论坛的发起人之一,肖有志老师在论坛最后做了总结发言。他说此次论坛文学、历史、宗教和哲学等各学科的优秀学者一同专注于早期经典及其相关问题的解读,彼此进行较有效的沟通,因为早期经典显然早于后世的学科分类;但其中可能也隐含着种种分歧,而如果我们拓展语文学与哲学互相成就的进路,或许讨论就能更上层楼;并往前推进至柏拉图《斐德若》中所包含的热爱言辞与热爱智慧这一生命热情本身。

肖有志老师发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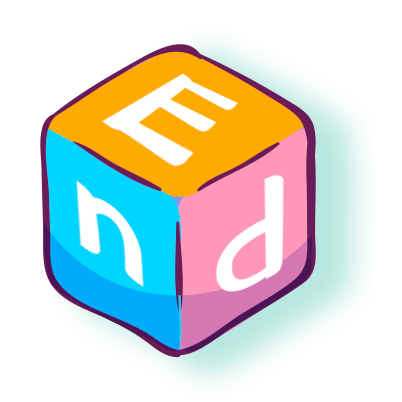
(文稿整理:张霄、陈驰、王思妍、曾茜、许锦娥、曹翠云)
(摄影:胡萍萍)
(编辑:Agall)

●顾枝鹰 | 《拉丁语语法新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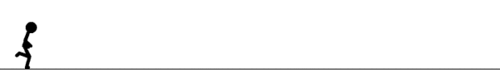

欢迎识别二维码关注“古典学研究”微信公众号
插图来自网络,与文章作者无关。
如有涉及版权问题,敬请相关人士联系本公众号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