娄林 | 亚里士多德论政制维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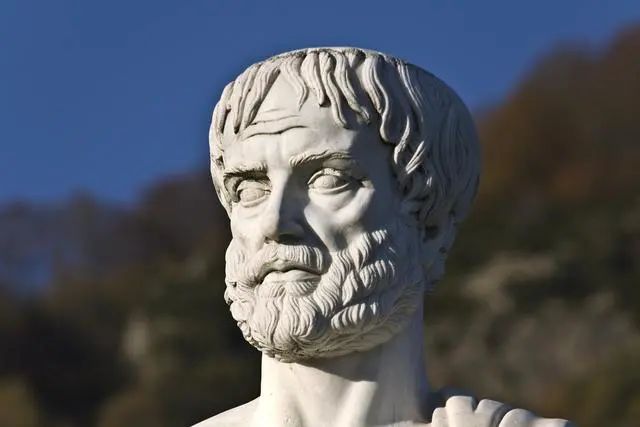
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
哲学生活与政治生活哪一种是更值得过的生活?亚里士多德持有的观点似乎游移不定。(cf. Gurtler,2003:801—802;819)《尼各马可伦理学》(以下简称《伦理学》)第十卷(第7—8章,1177a10—1179a35)明确宣称,[1]哲学的沉思生活最值得人去追求,而合乎其他德性的行为作为人的“现实活动”,只是第二位的。但是,《政治学》第七卷(第2—3章,1324a5—1325b30)却又认为,实践生活(也就是政治生活),才是最好的生活方式。二者看起来有其难解的冲突,但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与《伦理学》之间有一个根本的关联,二者都基于一个前提,即人的善是“符合德性的活动”,这一论断重复出现在《伦理学》第一卷(1094b7—10,1098a17—18)和第十卷(1177a12—14),也出现在《政治学》第七卷(1325b14)等处。这首先提醒我们注意,亚里士多德《政治学》最关键的前提与今天常见的政治科学研究不同,它更是一种关注人的“善”的实现活动的哲学探究。
在《政治学》第七卷,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一个“思想比喻”。倘若我们周围出现一个各种德性都优秀于他人的人——这个人似乎就是最智慧的哲人。人们就应该服从这个人,因为他最具有德性。但这个人还要具备实践他的德性的能力。(1325b10—15)这个思想比喻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对哲学生活和政治生活之间比较的一个中和的答案,这个人类似于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假设的“哲人王”,他既实现了哲学之善,也实现了政治之善。因此,从纯粹理论上来说,哲学生活和政治生活能够得到一种可能的统一。那么,城邦的政治生活要实现其善,就需要智慧或者哲学作为引导。比如,在《政治学》第三卷第12章,亚里士多德在探讨关于“平等”的正义观时,明确要求哲学上的考察。(1282b17—18;20)而就《政治学》而言,这种智慧首先就体现在对城邦的规定:城邦作为人的联合体,虽然是自然的产物,但它的存在目的是为了善的实现(1252a1—5;1252b30),而善的实现又必须基于每个城邦各自不同的政制。
霍布斯《利维坦》中有一章标题为“论国家衰弱或解体的因素”,开篇即明确说道,“国家根据其建立的性质说来,原来是打算与人类、自然法或使自然法具有生命力的正义之道共久长的。”(霍布斯,1985:249)亚里士多德也认为,为了便于我们的讨论,我们可以从理论上假定,各种政制在创建之初,都有其符合正义的原则,我们可以称之为善的开端。(1301a26—28)但是,政制总会由于各种原因而陷入内讧或者衰败之中,这就带来一个棘手的问题,现实中的政制本来就不完美,还面临着不断衰败的危险,在这样的情形下,城邦如何有可能实现城邦和人的善呢?这正是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五卷“政制维持”部分讨论的主要内容。
一
与政治维持有着密切关系的另一个主题是政制衰败,因为政制维持就要尽量避免或者延缓衰败。自西方古典政治哲学在雅典发端开始,政制衰败便是哲人们的重要关注之一,影响最大的当然是柏拉图的《理想国》,这篇对话用了两卷(第八、九卷)来谈论政制衰败。柏拉图曾经给出一个抽象的原因:

一个如此构建的城邦难以变动。然而,因为一切生成之物,有诞生就有衰亡,如此构建的东西同样无法永存;它必然瓦解。(546a)[2]

我们尽力解释一下荣誉政制如何从贵族政制演变而来。或者,以下这一规律是不是很简单,整个政制总是从统治阶层的内部开始发生变化——每当他们中出现内讧(στάσις);如果他们团结一心,政制就不会变动(κινηθῆναι),哪怕构成统治阶层的人数很少?(545d)

政制一旦形成,就必然处于运动之中。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第五卷开篇,即以城邦的统治者为例,说明他们是城邦政制的源头。(1013a13—15)这可以视为《形而上学》第一卷中著名的“四因说”中运动因的现实形态之一。对政治生活而言,这种运动和反向的维持(可视为四因中的第四因“善”)就构成了一种永恒的运动。
在《法律篇》第七卷793,柏拉图换了一个比喻来形成城邦政制未能得到良好维持的情状,他笔下的雅典客人把城邦比喻为房屋,而城邦礼法则是支撑房屋的柱子,一旦柱子发生问题,城邦必然面临倾垣断壁的危险。什么是真正的支撑柱呢?并不是我们今天理解的法律,而是所谓“未成文法”(ἄγραφα νόμιμα):

在柏拉图的笔下,城邦政制在现实中的维系是关系到城邦整体生活的根本前提——房屋的比喻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这里与亚里士多德有两处非常紧要的关联:
其一,柏拉图使用的“保护”(σωτηρία)一词,就是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第五卷所谈的城邦政制维持时所用的维持和保护:“对怎样保持(σωτηρίαι)一般政制或某一政制的稳定的各种政策,我们也必须有所建议,并给各个城邦分别指出维护(σῴζοιτο)其所行政制的最好方法。”(1301a25)第一个保持还是名词形式,第二次的维护是名词σωτηρία的动词原形σώζω的变位。作为柏拉图的学生,并且在《政治学》第五卷明确批评柏拉图的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文本当然很熟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政治学》中对政制维持的充分说明,某种程度上很可能是对柏拉图政制衰败的极好补充,二者对观,对于理解古典政治哲学中的政制思考或有裨益。
其二,对于维持城邦政制而言,最为重要的事情是维护城邦政制建立时和建立之前就一直习传的习俗与风尚,当然也要遵守城邦法律。这一点也为亚里士多德所继承。首先是对法律的遵从:“我们也可以说,一般政制所建立的各种法制,其本旨就在谋求一个城邦的长治久安;大家拥护这些法制,一个政制可得维持于不坠。”(1309b15)再则,维持政制的各种方法里,最重要的是“依照政制的宗旨对城邦民进行教育,不幸在今天,所有人都忽视了这一点。最有益的法律,而且得到了其所统治的全体城邦民的称赞,如果在政制范围内未能形成风尚并通过城邦民教育而深入人心,这样的法律必然是无用的。”(1310a10—15)从思想旨趣来说,亚里士多德同样讲究城邦礼法或者“未成文法”的风尚习俗的重要。
就这两点而言,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好学生。《政治学》也是从这里出发,延伸柏拉图的政制思考;但其关注略有不同:亚里士多德对政制维持倾注了更多笔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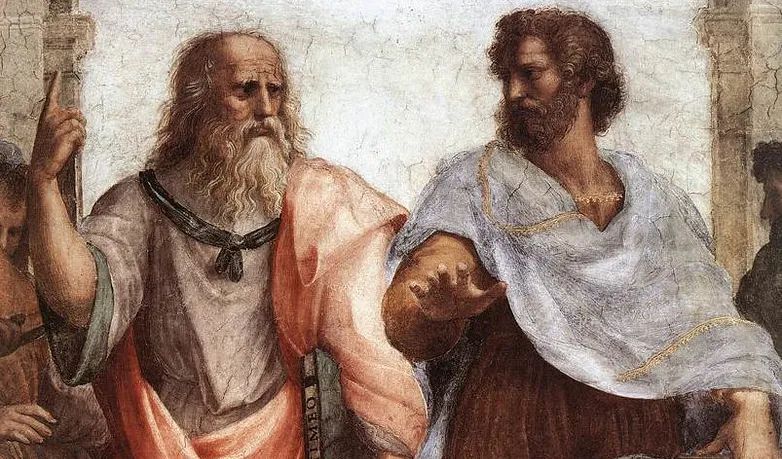
二
《政治学》一书主题看起来颇为混杂。由于主题的相对不集中,有人认为《政治学》只是一些主题的汇聚,作为一个文本本身并不能成为一个整体。著名古典学者耶格在划分《政治学》通行八卷的内在结构时认为,《政治学》混含了亚里士多德深受柏拉图影响时期的写作内容和摆脱其影响的内容,卷二、三、七、八属于前者,而卷四、五和六则属于后者。耶格的说法过于实证,过于依托某种理论假设,这种假说对于我们理解亚里士多德的写作意图来说,并无太多裨益。(cf. Barker,1946:xxxii-xxxiv)
R. 克劳特(Richard Kraut)意识到这一点之后,把耶格的看法内化为《政治学》自身的情节与论证主题的推进,而不是所谓亚里士多德本人的“哲学发展史”,认为《政治学》具有一种从差到好到最好的政治框架。(cf. Kraut,2002:181—187)具体来说,第一卷是政治生活的开端,探讨了政治生活必需的一些问题,但是不是对政治生活自身的探讨;第二卷则是对另一种不完美的政治生活形态,错误理念之下的政治生活的探讨;从第三卷开始,亚里士多德则进一步推进,分析了关于城邦公民与政制的普遍相关问题,来探究理想形态和不完美形态的政制,这一直持续到第六卷;而第七和第八卷则是理想城邦的形态,克劳特认为:“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第七卷和第八卷中的任务是细致展现最佳的可能城邦”(Kraut,2002:192)[4]。
克劳特的结构框架一方面梳理了《政治学》的肌体,但同时引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层次,即最佳政制的可能,也就是说,亚里士多德的政制考察最终是以城邦之善为其目的。就此而言,第七和八卷未必就是理想城邦巨细无遗的安排,毕竟在第四卷亚里士多德已经说过什么是最佳政制(1293b),但是克劳特的说法提醒我们,在理解《政治学》的总体意蕴时,一个根本的参照点恰恰是最佳政制——这一点与柏拉图如出一辙。更明确点明这一点的是施特劳斯。施特劳斯在《政治哲学的危机》这篇讲演中认为,我们摆脱现代危机的最好方法是返回古典政治哲学,尤其是返回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参见施特劳斯,2016:346)因为我们可以借助《政治学》回到根本的问题:

衡量《政治学》的内容和框架都必须基于最佳政制这个问题的指引。回到政制维持的主题,以最佳政制为指引并不意味着,现实城邦一定要发展为最佳城邦,而在于如何让某种现实政制变得更好。这正是《政治学》中一以贯之的基本看法:城邦之存在,是为了实现某种善,而不是仅仅是城邦的生存。甚至,“仅仅是为了生活,人们就会聚在一起,构建并维持政治联合体……大多数人为生活所沉重牵累,也仍然愿意忍受诸多艰辛,这也暗示了,生活自身之中就含有某种健康的幸福和一种自然的甜蜜。”(1278b23—30)只要是一种共同体的生活,城邦就必然蕴含某种善的因素,这才是政制维持最根本的原因所在。
因此,政制维持不是一种马基雅维利式的单纯的自我保存式的维持,而是为了让这座现实城邦从自身秉有的某种善的因素朝向更大更完整的善。而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分析,在以这种善提振城邦政制之前,我们应该探究城邦衰败的一般原因与具体原因。因为只有克服了这些原因,一个城邦才能够得到维持,或者更好地维持。

《政治学》第五卷首先给出了一个重要的一般原因:“一旦人们在一种政制中没有未能像预期那样享有其分内的权力,他们就会联合起来发难……这些情形可以说是城邦动乱的始因(ἀρχαὶ)。”(1301a38—b5)我们需要注意,亚里士多德不是说真实的平等与否,而是一种预期,或者说是感受到不公正,这并不一定意味着真正的不公正,而是说对于城邦中某些人而言,这一政制令人不满——其实,亚里士多德已经暗示,对于城邦政制维持来说,首要的关注必须是城邦中多数人对这种政制的接受。这种不满的根源其实在于这种政制丧失了教育或者引导自己城邦民的能力,这才是一切动乱之源。具体来说,变化方式有两种:“内乱的矛头直指现行政体,其目的在于以另一种政体取代现存政体……或者,内乱并不指向现存政体,而是意图维持现行政体,比如寡头制或君主制,叛乱者把这些体制纳入自己的控制之中。”(1301b)(cf. Skultety,2009:348—351)
这是从政制言之,如果从发动内乱的城邦中具体的城邦民来说,则首要原因依旧是不平等的感觉:“人们为了财务和名誉彼此相争,然而并不见得就是因为他们自身,而往往是因为看到别人公正或不公正地比他们占有更多。”在各种原因中,“暴虐和贪婪能起什么作用,以及以什么方式起作用,几乎是不言而喻的。”(1302b5)“某一部分不成比例的增长也是导致政体更迭的原因之一。……那些对现行政体心怀不忠的人一旦做官掌权,政制就会随之更移”。(1302b35)“动乱可能起于琐碎的事因,但绝不会仅仅围绕这些琐细之事。”(1303b17)总而言之,细小的导火线没有被亚里士多德视为真正的原因,他重复了之前关于首要原因的判断,但这些对政制的不满以对财富和名誉的追求呈现出来,而这种追求又根源于追求者自身的欲望——“贪婪”。这就导致一个基本的问题:一种政制如何处理人的欲望,这正是柏拉图《理想国》的要义之一。[5]
这就是说,一般而言,政制之衰败是由于城邦民与城邦之间的断裂。《政治学》第三卷为《政治学》开启了一个开端:第一卷以对城邦的定义开始;第三卷以对政制和城邦民的规定开始。城邦是一种人为的“组合之物”,它的组成部分或者质料就是城邦民。城邦民与城邦之间的关系即是政制衰败的一个关键切入点。亚里士多德等于给出了两种一般原因(ἀρχαὶ):首先是政制自身无力于以政制所追求的善来引导城邦民;其次,城邦政制再也无力节制城邦民的欲望。
亚里士多德随后概述了政制动荡的具体原因:“让我们来看看每一种政体”的更迭——第五至第七章,他分别考察了民主政制(第五章)、寡头政制(第六章)、贵族政制(第七章)。在谈论政制维持之前,亚里士多德着力分析内乱的成因及其表现,这种安排的意味不难理解:如果城邦政制难以维系,则是内乱不止;同时,城邦的内乱又必然导致政制难以维系。
所以,在到第八章(1307b25)之后,亚里士多德转入第二大部分的内容,篇幅长于前一个部分,“接着我们要从共同的方面,或就个别情况单独考察每一种政制的维持(σωτηρία)。”
随后,针对前面所列举的的内乱而给出维持政制的良方,列出多种可能的方案,既有某种共通性的药方,比如禁止违法之举动(1307a30),比如,每一种政制“都不能让某个人的势力得以异乎寻常地膨胀”(1308b13);“各种政制所制定的有利于自身的一切法律,无一不是为了维持或保全现行政体”(1309b15),也根据不同政制各加论述。和前面对应,亚里士多德还是只谈到民主制、寡头制和贵族制的维持。而最后,亚里士多德给出一个任何一种政制想要维持都必须持守的一般做法:

前文已经说过,这里完全继承了柏拉图《法律篇》中的教诲,也将之前关于法律的种种药方给出一个最重要的说明。其要害在于两点关联:其一是政制与法律之间的关联。这是隐含的前提,即城邦制定的法律一定要与政制一致,各种细致的法律规定很可能陷入法律细节而无视政制的整体特征;其二是法律与风尚习俗的关系。柏拉图称之为成文法与未成文法之间的关系,亚里士多德更加明确地指出这种风尚之形成完全有赖于教育;这首先意味着,对一种政制来说,教育——依照其政制宗旨而对城邦民进行教育——是其维持政制最为有效的方式,明乎此,我们能够明白,为什么《政治学》第八卷,也就是全书以教育作为最后的落脚点:“大家应该都同意,少年的教育是立法者最应关心的事业……城邦如果忽视教育,其政制必将损坏”(1377a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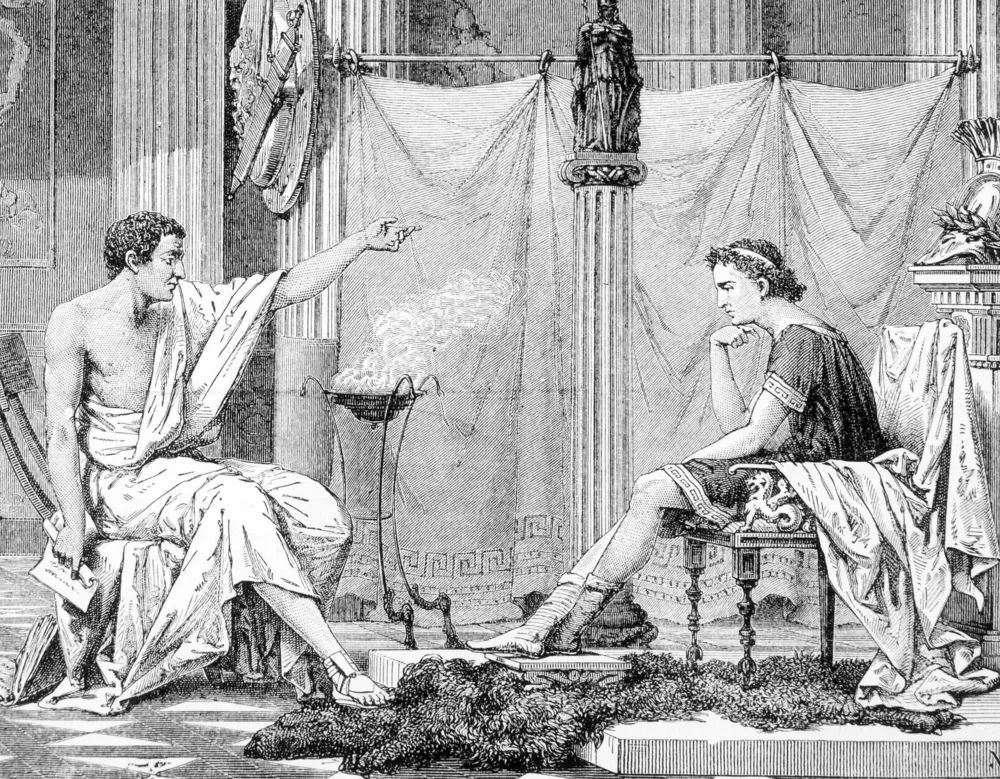
三
但是,奇怪的地方在于,《政治学》第五卷亚里士多德考察了各种政体以及总体概说,却在这些分析之后,又另起炉灶,重新谈论君主制和僭主制的毁灭原因及其维持。似乎君主制和僭主制不在他所分析的“诸种政制”之间一般,这从逻辑上讲似乎难以圆通。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对君主制尤其是僭主制的维持,却占了整个第五卷最大的篇幅。
亚里士多德倒也给出了解释,第八章一开始就说,虽然前面适用于各种政制的讨论虽然也适用于君主制和僭主制,但是,“君主政制具有贵族制的性质,而僭主制则为寡头制和民主制度两种极端形式的复合”。(1310b1—5)亚里士多德指明的是,君主制和贵族制一样,是最佳政制的某种形式,而作为最佳政制的反面,恰恰就是僭主制。(参见柏拉图《理想国》,445d;《政治学》1310b30—35)这就是说,亚里士多德认为最佳政制和最糟糕的政制作为政制之两极,值得我们特别地注意。如果说君主制的维持是为了维持最佳的善,那么,僭主制的维持就让我们难以理解,这种最糟糕的政制有什么值得维持之处呢?我们更加习惯孟德斯鸠式的解决方案,即去除理掉最糟糕的政制。亚里士多德竟然要维持僭主制,这令我们非常惊讶。
亚里士多德开始花费了大量笔墨于僭主制度的维持,似乎他有意要让这种最糟糕的政制得到维持。(cf. Jordović,2011:40)乍看之下,亚里士多德几乎成了一个古代的马基雅维利。不过,亚里士多德区分了两种类型的僭主制,第一种是“卑劣的”僭主制(1313b32),僭主制维持的种种手段有剪除城邦中的杰出之人、禁止集会之内,最后他总结为三点:“在城邦民中制造不信任的气氛;使城邦民们无力举事;使城邦民心志狭窄。”(1314a25—30)如果仅止于此,亚里士多德当然就是马基雅维利了,但是他还花了更长的篇幅分析了另外一种维持的方法,也就说,第一种方法在他看来,终将难以维系,因为根据后面所举例证来说,采用这种方法的僭主政无一得以维持,也就是说,亚里士多德认为,无论采取何种方式,这种“卑劣的僭主制”都不可能得以维持。
能够得以维持的僭主制,其典型如西基翁的阿萨格拉:“这一僭主家族所以能够如此久长,是由于他们善自节制,治民温和,施政大体谨守法度。”(1314aa32)这几乎与之前君主制维持的缘由相同。因此,亚里士多德说,“使僭主制转变成君主制应该是保全僭主制的方法了”。(1314a32)这样,“僭主若更具有君主性质自然能够保全僭主制度。”(1314b35)僭主必须节制,“像君主一样行事”(1314a39);“即使在其他各种德性方面无一能引起他人注意,至少在行伍方面应有几分天资。”(1314b18)“必须最大程度内保持节制。”(1314b34)“他应当修缮和美化他的城邦,就仿佛不是一位僭主,而是一位监护人。”(1314b36—40)“虔敬诸神” 。(1315a1)最后,亚里士多德总结:

一言以蔽之,一位僭主能够如此行事,如此统治,早已成为一个好的君主。既然成为一个好的君主,这样由僭主制转变而来的君主制当然就能够维持,而且分有了某种最佳政制的可能,实现了僭主个体的善和城邦的善。
亚里士多德的教诲看似明朗,但并不总容易把握,我们只能试图理解一些细微之处。他和孟德斯鸠完全不同,并不认为最差的政治制度就是必须灭之而后快,关键点在于,即便是所谓最差的政治制度,如果能够以美德进行教化与改变,还是有转变的可能,那么,我们自然可以推导,即便是最好的政治制度,如果没有美德作为支撑,也很容易走向衰败和灭亡。因此,在论述政制维持的主题下,亚里士多德花费笔最多于僭主制,并不一定是由于针对雅典极端民主制的现实原因(cf. Jordović,2011),而更应该有其审慎的思考在焉:
首先,僭主制虽然是最糟糕的政制,但尚可以美德加以转变——这既有历史上的实例,也有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说明为证,那么其他类型的政制所最应该采取的维持方式大约也与此雷同;其次,很可能糟糕的政制是人间政治现实的常态,而面对这样的现实,政治哲人如何面对这样的政治生活并传达自己的教诲,提振糟糕的政制的品性,这就是一种审慎的朝向善的方式——而美德及其教育正是其中关键之一。这就触及到一个极为明显的古代政治哲学的形式:即劝谕或道德教诲,比如色诺芬《论僭政》著名的结尾,西蒙尼德斯劝诫僭主希耶罗:“如果你在善举上超过朋友们,敌人们就无力抵抗你”。(色诺芬,2016:38)
那么,亚里士多德念念在兹的善是什么?《形而上学》中,亚里士多德认为,“万物之中,善是最高的本原”。(1075b1)城邦之为城邦,是由于最高最全面的善。这并不意味着任何一种政治体就是善的,而是说,只有以这种和目的论的善为目的,城邦才是自然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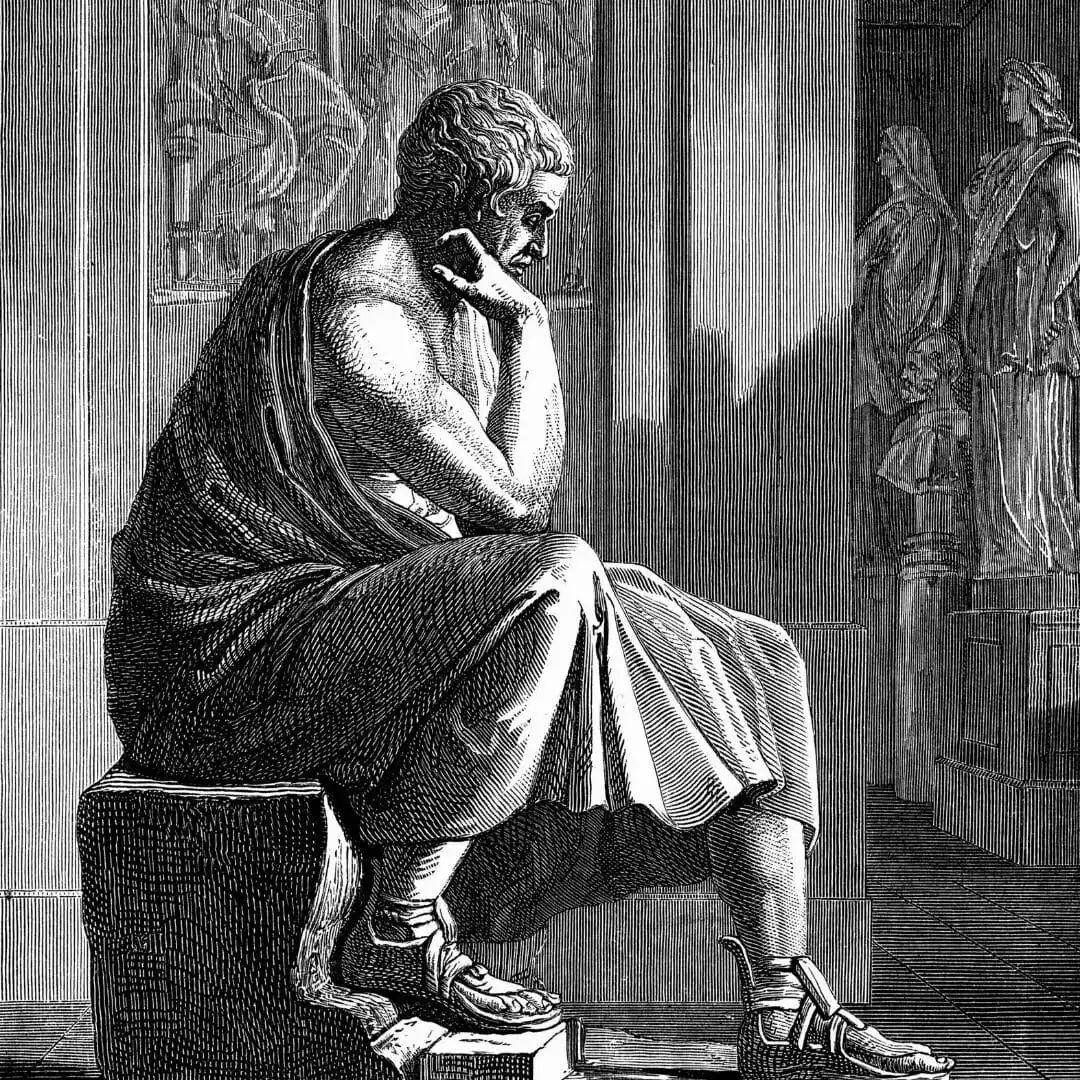
我们最后回到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继承作为结语。《理想国》中构建理想城邦的第四卷里,苏格拉底告诉格劳孔,这座城邦理所当然应该具有“智慧、勇气、节制和正义”四种传统美德,而在细致的考察过程中:

注 释
参考文献

延伸阅读
作者简介


● 娄林 | 李尔王的意图和莎士比亚的意图:莎士比亚的《李尔王》初探
● 贺晴川 | 从家庭到城邦的政治教育——亚里士多德的“人是政治动物”之谜
(编辑:陈若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