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与解释”书系推介 | 马基雅维利集(刘训练主编)

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1469–1527)
出版说明
在西方思想文化史上,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1469-1527)居于一种非常奇特的地位:一方面,他被公认为西方现代政治学的奠基人,甚或被称为现代第一人;但另一方面,他在何种意义上是“奠基人”、“第一人”却又聚讼纷纭,见仁见智。

马基雅维利生活的时代是西方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关键时期,也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由盛而衰的转捩点,而在这个“需要巨人并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作为文艺复兴运动在政治思想领域最杰出的代表,马基雅维利在政治、军事、外交、史学和喜剧等领域都留下了丰富的著述和大量的信件。这些文字表明,他具有强烈的时代意识、浓郁的爱国情怀、深厚的古典学修养、敏锐的政治-心理分析能力和卓越的写作技巧,无愧于“治国术”大师和“最高写作艺术当之无愧的继承人”的称誉。就此而言,他的著作仍然值得我们今天认真对待和不断反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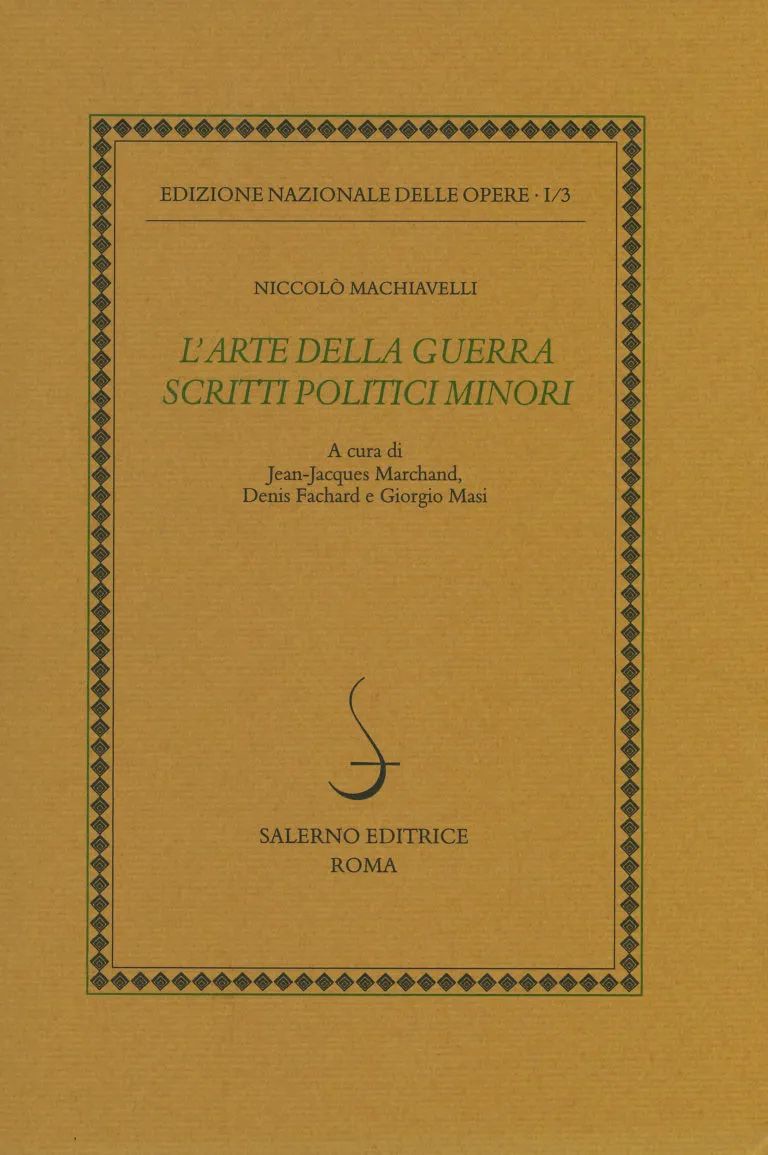
值其主要著作问世500周年之际,西方学界各类传记、诠释著作更是层出不穷、蔚为大观;在此背景之下,我们适时推出“马基雅维利集”。“马基雅维利集”分为两大系列:一是“马基雅维利全集”,以中文版《马基雅维利全集》为基础,参照罗马萨勒诺出版社陆续刊行的意大利“国家版”全集(Edizione Nazionale delle Opere di Niccolò Machiavelli)酌情替换、校订,并适当增加注解、疏义,重新推出《马基雅维利全集》的修订增补版,俾使中文读者有可靠的“原典”研读;二是“解读马基雅维利”,迻译西学中诠释马基雅维利的第一流著作,以便中文读者免除从浩如烟海的二手文献中爬罗剔抉之苦。
书 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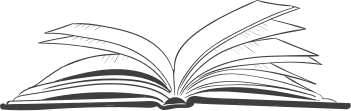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马基雅维利集
刘训练 ◉ 主编

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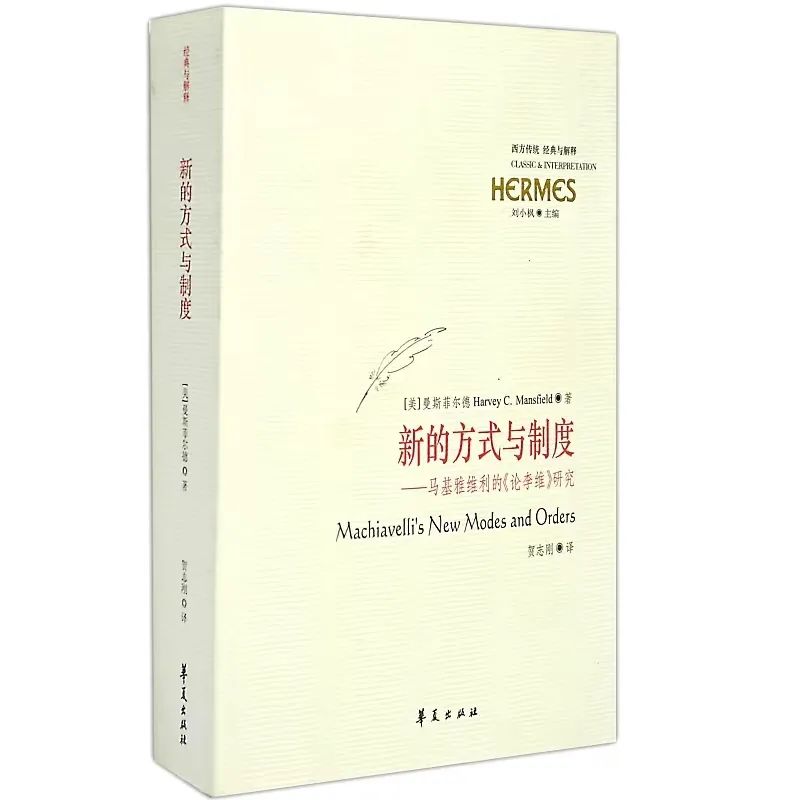
新的方式与制度
——马基雅维利的《论李维》研究
618页,49.00元,2009年3月
华夏出版社
内容简介
《论李维》是自成一体的一部著述,至于《论李维》整体上有什么样的安排以及马基雅维利如何利用李维,作者运用了施特劳斯的发现结果,因而认为没有必要重复他的观点。因为作者的阐释工作主要在于揭示马基雅维利认为应该谨慎地藏匿的东西,所以作者经常会让读者揭开某一个故事的要点或者发现隐蔽要点的东西。作者所做的研究成就的是一部“本质上”属于评述类的著述。本书是对马基雅维利的名著《论李维》的评述。曼斯菲尔德深入原著,紧跟马基雅维利,对他表示的观点和引述的事例几乎逐点逐条地展开讨论和评述,梳理和凸显马基雅维利思想的主要概念,试图揭示马基雅维利的意图以及思想体系。
目 录
* 上下滑动查阅更多内容
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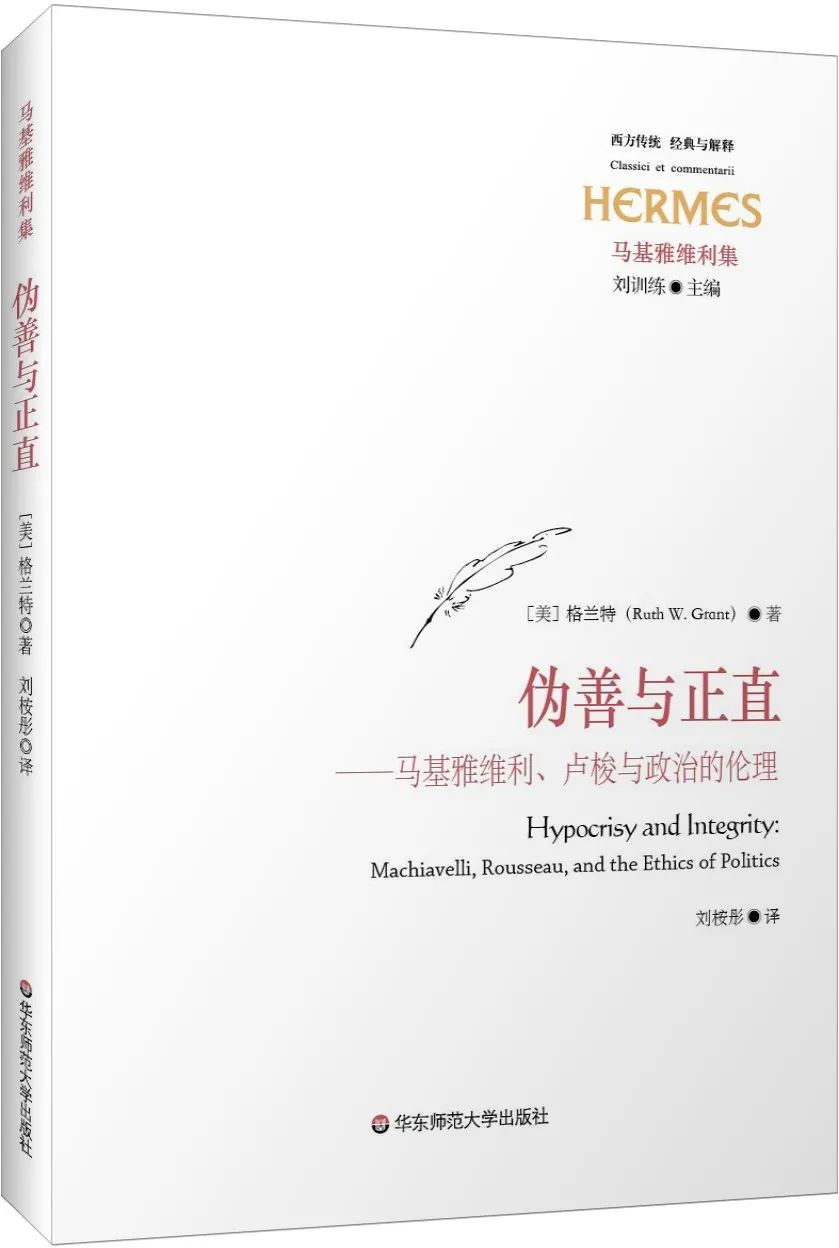
伪善与正直
——马基雅维利、卢梭与政治的伦理
[美]露丝·格兰特 著 刘桉彤 译
257页,58.00元,2017年10月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聚焦于伪善与正直的伦理政治问题,探究它们是什么、具有什么形式、为什么会如此呈现出来,以及用不同的方式辨别它们的特征会有什么不同的政治后果。基于对马基雅维利与卢梭作品的细致分析,作者格兰特指出,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依赖是政治的内在属性,因此,并不彻底独立的个人便无法通过彻底的诚实而在社会生活中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即使最大程度地运用理性,也无法弥补这一内在问题,伪善因而不可避免地成为政治生活的必然要素。面对伪善的必然性,作者指出,必须从伪善中甄别出合理的与破坏性的。
目 录
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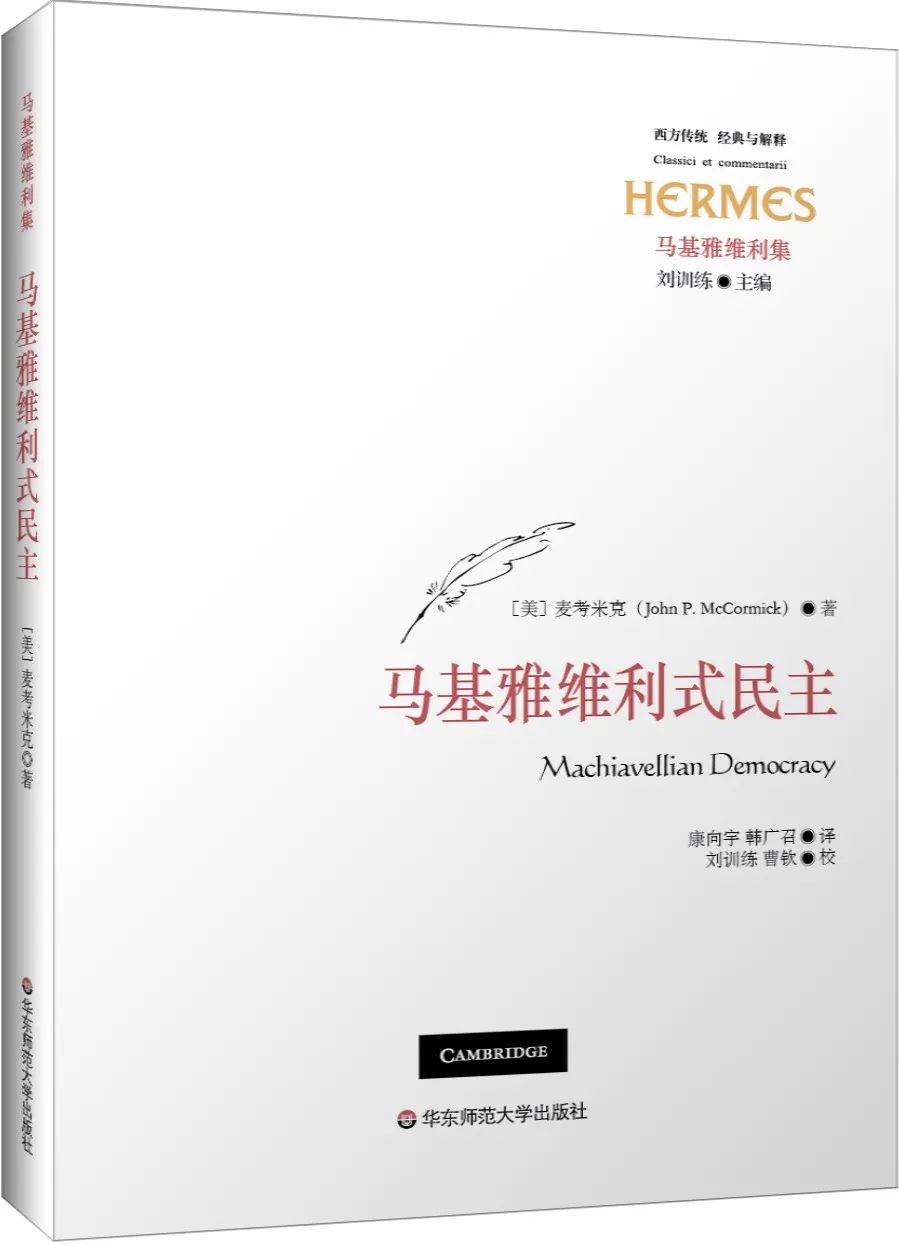
马基雅维利式民主
内容简介
西方当代民主中,即使选举式民主,也不能保证公众选出的公职人员会回应选民的政治意愿和政治期待,甚至给政治和经济精英以可趁之机,以损害公共利益来充实他们自己的财富。在本书中,麦考米克通过考察马基雅维利作品中(主要是《君主论》《李维史论》与《佛罗伦萨史》)之前一度被人忽视的民主特质,发掘出古代、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共和国中平民抑富督官的制度,并设想了如何在今天复兴这些制度。本书不但从根本上重新评价了西方政治教坛中核心人物之一的马基雅维利,而且明确介入了有关制度设计和民主改革的当代论争。
目 录
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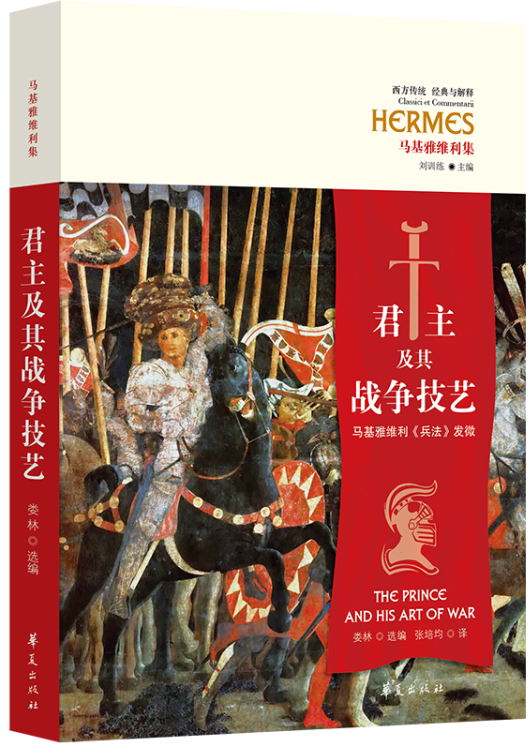
君主及其战争技艺
——马基雅维利《兵法》发微
娄林 选编 张培均 译
内容简介
目 录
编者说明 娄林 1
《兵法》引论 曼斯菲尔德 13
重审马基雅维利的《兵法》 克里斯 51
《兵法》中修辞术的军事“德性” 维特霍夫 77
马基雅维利与战士的修辞术 雷蒙迪 94
敌对行动中的政治:马基雅维利的《兵法》 斯帕克曼 115
君主及其战争技艺:马基雅维利的军事平民主义 温特 135
马基雅维利的军事方案及其《兵法》 霍恩奎斯特 164
奠基者 皮特金185
《兵法》的新秩序:重塑古代事物 林奇 224
书 摘
一部非马基雅维利特色的马基雅维利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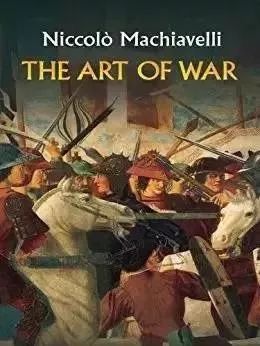
确实,《兵法》卷六列举了33条一位首领可能觉得必需的诡计,卷七补充了被围城者可能遭遇的来自其包围者的一系列计谋,但《兵法》中“马基雅维利式的”部分相对温和,没有显露马基雅维利只要愿意就可以释放的毒液(venom)。而且在战争的背景下,这些邪恶可以谅解,因而也有其限度。在战争环境中,好人被迫去做和平时期无法设想的坏事。马基雅维利并未企图将源自战场的邪恶做法延伸到和平时期的政治中——如他在其他作品中所为。这些邪恶做法看起来始终是那些必须战斗者的肮脏的必需,而他没有把这些做法推荐给所有追逐功名者作为武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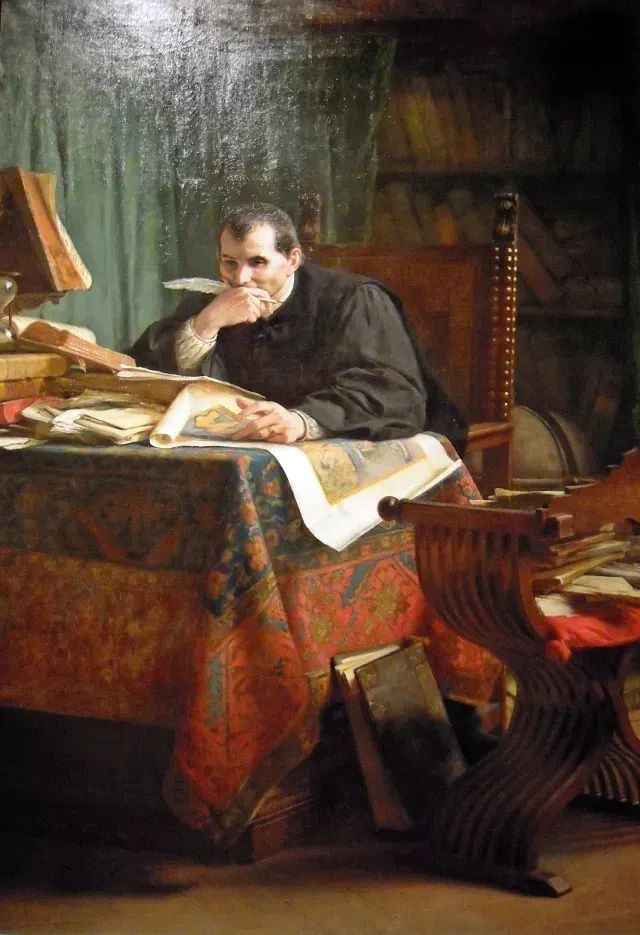
在《兵法》的献词中,马基雅维利声称,他写作是为了反对当今时代那种强有力的观点:平民生活与军事生活互不相同。但这意味着应该使军事生活更接近平民生活,应该用公民军队(citizen armies)取代专业的雇佣军,而不是使市民生活更接近军事生活,从而促使政治家认为自己的专技是战争技艺。尽管马基雅维利赞美其中一位对话者科西莫,赞美他教给人很多对军事生活和平民生活都有用的事情(《兵法》卷一,页329),但这部作品给大多数读者留下的主要印象,则是军事权威当从属于平民权威。献词先表明军事生活与平民生活并非如此互不相同,之后,马基雅维利将军事比作一座庄严宏伟的王宫的屋顶,赋予其防卫功能。在这一关于保卫的描述中,《君主论》和《李维史论》中非常显著的获取(acquisition)的可能性(或者说必要性[necessity]),被悄然略过,在《兵法》的其他地方也几乎再未出现。
马基雅维利也没有用对斯福尔扎的事业的生动描述来款待我们,后者是《君主论》中以擅长兵法获得成功的典范。这样的描述见于《佛罗伦萨史》卷五。相反,我们领受了主要对话者法布里齐奥(Fabrizio Colonna)的智慧,这位雇佣军首领刚为阿拉贡王斐迪南(“天主教国王”)完成一项任务(《兵法》卷一,页329)。斯福尔扎在考虑如何欺骗雇佣他的米兰市民并成为他们的君主,而法布里齐奥似乎并不赞同他此时肯定会有的那些想法(《兵法》卷一,页3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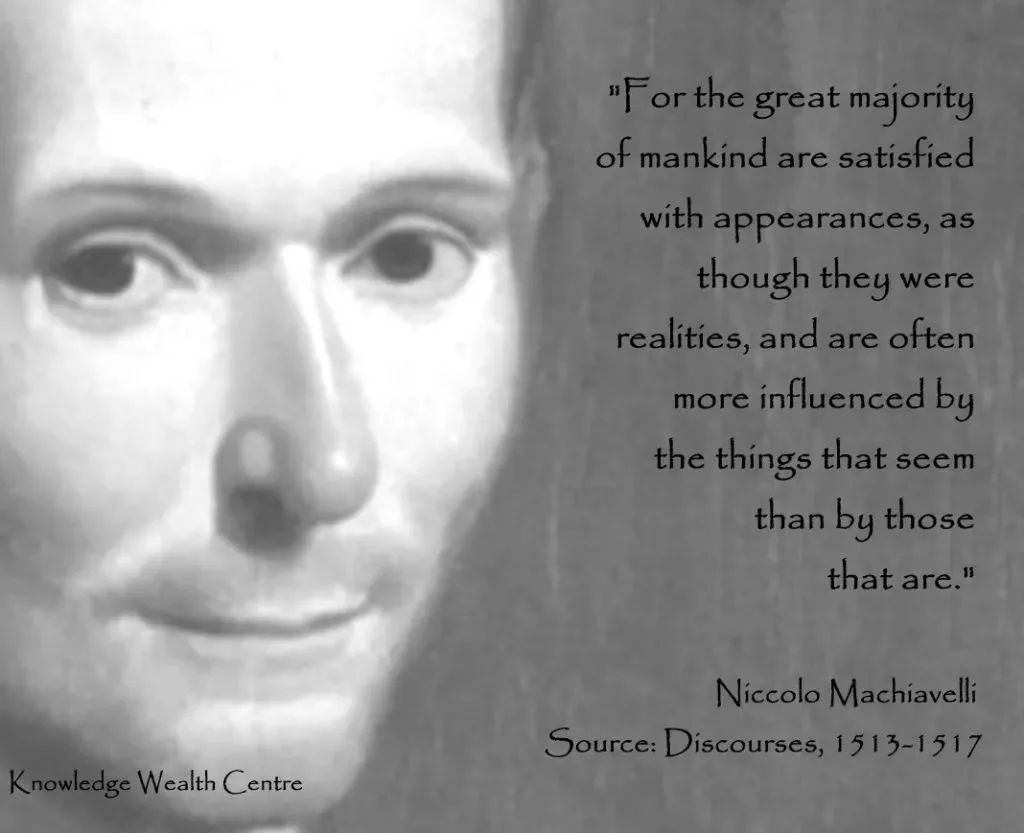
“绝大多数人都满足于表象,仿佛那就是现实。影响他们的往往是事物表面所是,而非实际所是。”
法布里齐奥似乎谴责那种行为,他本人对于以兵法为职业持有道德上的怀疑。他随时职业雇佣军首领,却强烈反对使用雇佣军,并不断推荐“我的罗马人”——共和时期的罗马人——的军事方法。他的名字使我们想起法布里奇乌斯(Fabricius),一位以道德正直著称的罗马共和国将领,《兵法》一开始就引他为例(《兵法》卷一,页332)。马基雅维利在《李维史论》中也有两处提到那个“法布里齐奥”,因他为自己树立了一个“有德可表罕见其匹的榜样”(《李维史论》卷二,第1章),而且他让敌方将领知道他的一个熟人要毒死他(《李维史论》卷三,第20章)。马基雅维利评论说,法布里奇乌斯这一“气度宽宏”的行为使他能够将皮洛士(Pyrrhus)赶出意大利,而当时,罗马军队早已不堪大用。
为何会有这样的差异——这部作品谦和,而其他作品却展示出诡计多端的邪恶?我们并不确切知道马基雅维利写书的时间,但看来他在写作《兵法》之前的1513至1525年间写成了《君主论》和《李维史论》,而《佛罗伦萨史》则成书于《兵法》之后。这一时间表不允许我们推断他在思想上有了某种变化,因为无论如何,对此没有任何文本以外的证据。我在上文已提到,《兵法》是马基雅维利生前出版的唯一一部重要的散文作品。显然,可以假定马基雅维利对于挑战自己祖国的道德和宗教不得不更加小心——如果在他生前必须承受这么做的后果的话。他简单地找到了绕过这一难题的方法,即在死后才出版另外那三部作品。那么,为什么他还要以这种方式写作《兵法》,使其能在他生前出版?对这同一问题更大胆的问法是:这部明显有所节制的作品,如何共同承担起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和《李维史论》中宣称的雄心勃勃的事业(impresa),即为了人类的利益而引入一种新的政治、道德和宗教秩序?这是研究《兵法》时需要解决的入门问题。
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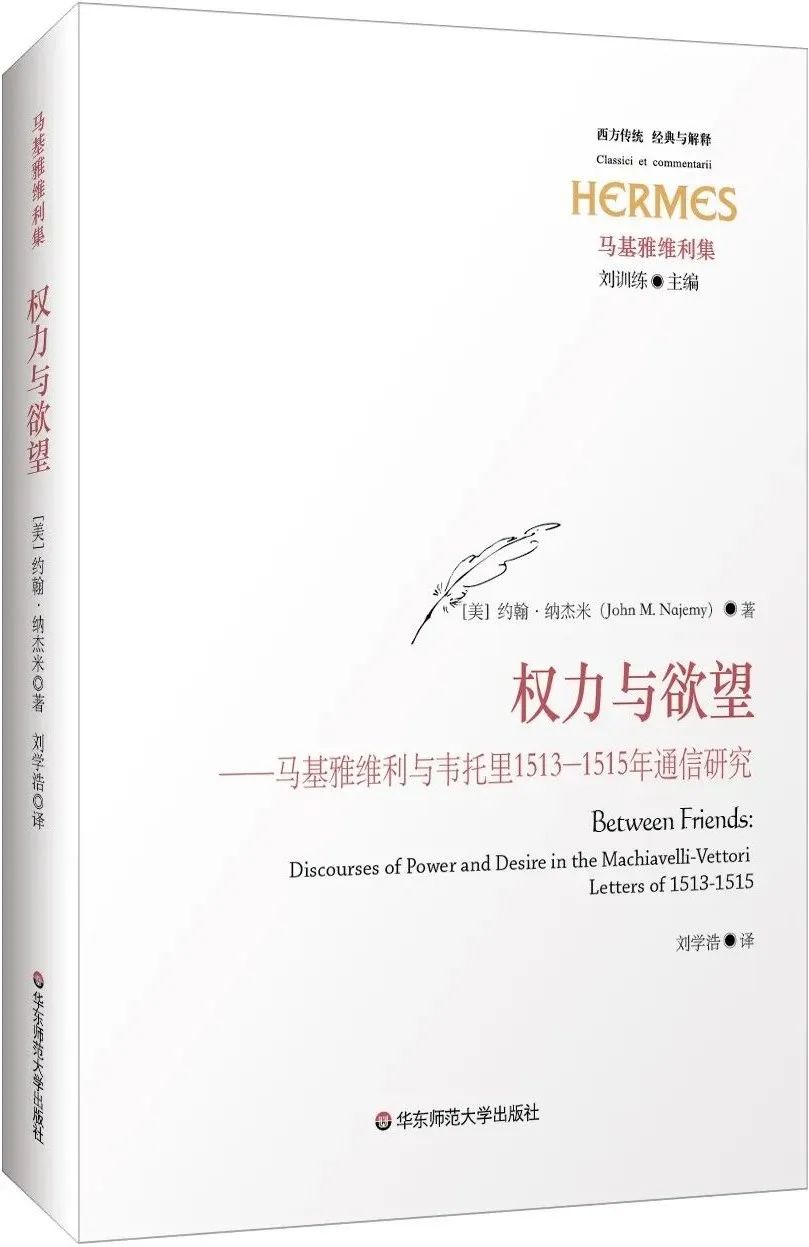
内容简介
谁都知道马基雅维利,但只有专精于意大利文艺复兴史和文学的专家们听说过韦托里,甚至其中很多人也只认为他不过是马基雅维利的一位朋友,他们之间有书信往来并留存。因而,对很多人而言,这两位之间的通信具有一种非常明显的不平衡关系,以至于人们更多地关注马基雅维利而忽视韦托里。
本书作者纳杰米以马基雅维利和韦托里1513—1515年间的书信作为研究对象,既对其进行了详细解读,也尝试着将这一段著名的书信体对话放到马基雅维利转变成为一位作家和政治理论家的背景之中。马基雅维利与韦托里两人关于政治论述的不同基本预设之间的冲突对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写作产生了决定性影响,那些潜藏在看似闲笔之中的文学和历史典故在这场纸上交锋中发挥了独特的暗示和推动作用。
目 录
前言
书 摘
第六章 盖塔与“古人”
(1513年12月10日信)
“但我们只能听天由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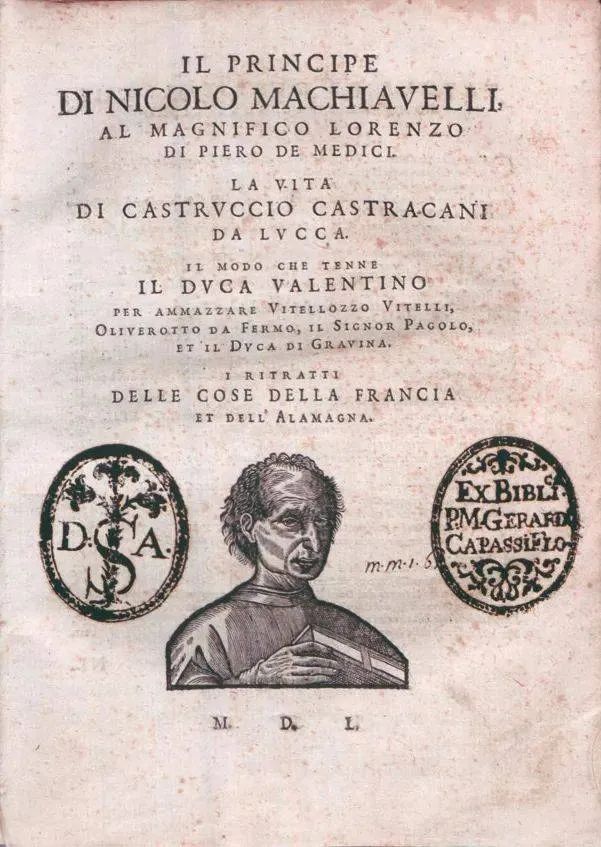


下午,韦托里会在花园中散步,或者在乡间骑马。夜晚用来阅读:“我搞到一批历史书,尤其是罗马人的史书”。他不嫌麻烦地提到了至少11位历史学家,有罗马人也有别的,包括:李维(这是马基雅维利和韦托里通信中第一次提到李维)、萨卢斯特、普鲁塔克、塔西佗、苏埃托尼乌斯,以及其他“写到罗马历代帝王”的人。“我用这些史书来打发时间;我在思索,曾让世界发抖的罗马,这个可怜的城市,忍受过多少皇帝的暴政啊,所以若它[罗马]还容忍了像最近这样的两位教宗,那也毫不奇怪”,他这里指的是亚历山大六世和尤利乌斯二世。大约每四天他会给在佛罗伦萨的十人委员会写一封信,还是像他在教廷的谈话一样,他表示这些报告只包含一些“无聊的、不重要的新闻,您想必能理解,我没什么可写的”。他在傍晚吃饭,和朱利亚诺·布兰卡奇与焦万·巴蒂斯塔·纳西讲故事。韦托里在自己罗马日常生活描述的结尾处,像开头一样同时提到宗教与女人。每逢圣日,他就去参加弥撒,不像您,有时就不去了。如果您问我,我有没有狎妓,我会告诉您,我刚来的时候,就像我以前跟您说的,确实有几个相好;但后来,我被罗马夏日的空气吓坏了,所以戒掉了。不过,我有一个熟识的相好,她经常自己前来这里。她相当漂亮,与她交谈十分愉快。这个[新]地方虽说僻静,但我也有一位女邻居,您绝对不会认为她没有魅力;尽管她出身于贵族家庭,但她可从来闲不住(fa qualche faccend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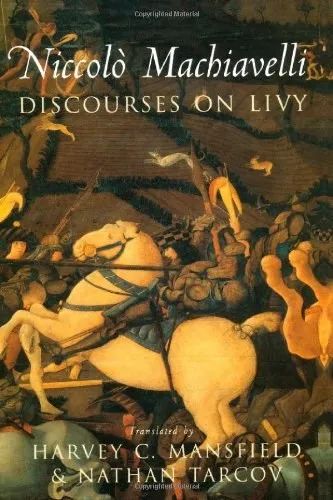
他对这位邻居的这一评价到底是什么意思并不明确,但这里可能是在指他人与她发生性关系很容易,无论她是不是个妓女。
这一发生在教廷中漫无目的谈话的图景,从属于韦托里更高一层的对比:一方面是公共舞台上政治的严肃与拘谨,另一方面则是单纯却愉悦的私人生活。如果在教廷中的谈话实际上并不存在,如果他写给十人委员会的信只不过是讲述一些“无聊的、不重要的新闻”,那么,丰富其生活、填补其空虚的就是与朋友们——无论男女——的谈话。即便是韦托里对罗马历史的阅读,也印证了他关于政治之粗鄙的看法。韦托里对“这可怜的罗马”的皇帝们的总体性指控仅仅是一个巧合吗?还是他可能已经了解到《君主论》中最长的一章(第十九章)恰恰是在致力于区分这些皇帝们的优点与错误?关于韦托里对亚历山大和尤利乌斯两位罗马不得不“忍受”的教宗的蔑视,我们或许也可以提出同样的问题,因为马基雅维利(在第十一章中)赞扬他们采取了大胆且前所未有的行动“壮大教会的势力”。当然,还有关于归还银质餐具以便摆脱向教宗讨好处的要求、摆脱居间调和照应他们的义务的言论:“不过我就是说了,对他们也没什么帮助;所以我决定不去管这个闲事了,省得惹恼或麻烦任何人,也免得自己被他们惹恼或麻烦。”(韦托里把用服务或者好处换取礼物说成是他不想继续下去的肮脏的“闲事”[faccenda],同样这个词在下一段结尾处也用在了邻居太太的身上,这当然使得这一用法多了某种色彩。)

这是在警告马基雅维利,不要再让自己向利奥或者在罗马的其他美第奇家族成员说情了,也不要带着期望向自己寄送任何东西,以为韦托里会更有意愿代表他去接触美第奇家族,或者他们会更有意愿倾听。就算马基雅维利在他的“牌库”(carte)中写入这样一个情节(scenario),它也不会出现在韦托里的牌库里。但是,我们怎么可能不将韦托里的警告与《君主论》的献辞——无论它写于什么时候——的第一段联系起来呢?马基雅维利在其中说道,不像那些习惯于向君主进献如骏马良驹、名剑奇甲、金缕衣、宝石以及其他装饰品等奇珍异宝以获取一位君主恩宠的人,他认为要获取恩宠,在“我所有的东西里面”没有什么比自己“通过对现代事务的长期经验和对古代事务的持续研读而获得的关于伟大人物之行动的知识(cognizione)”更为宝贵了。马基雅维利将这种知识说成是他所有“东西”的一部分,就是在回应韦托里的警告:他有比银质餐具更好的东西,它们是如此珍贵以致他可以直接进献给君主,不需要经过中间人。当然,事情的结局并不是那样,但这里的关键在于,即使是《君主论》献辞的第一句话也受到了他与韦托里之间依旧紧张的对话的影响。



关注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