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宁顿的《现代的起源》
编 者 按
本文刊于《经典与解释(30):笛卡尔的精灵》(刘小枫、陈少明主编,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年5月),伍弗里撰,马涛红译。
当别人在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和洛克的著作中考量现代政治思想的哲学根源时,肯宁顿却更关注培根和笛卡尔著作中现代自然科学的哲学根源。这本书收集了他零散的考量成果,总共有十四篇,其中四篇讨论培根,七篇讨论笛卡尔,后续三篇分别讨论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和洛克。这些文章的写作跨越了近四十年时间,其中六篇在此是第一次发表。按照此书现有顺序通读这些文章,读者会发现肯宁顿在不断地回到同一个根本主题上去。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是在自我重复:

他的重申游走于不同的语境中,有时还针对着不同的读者对象,而且,不管是在何种情况下,他似乎都是从起点处进行着思考,即如第一次思考一般。

这本书在几个方面都不无裨益。首先,对所讨论的几位哲人著作中的某些关键文段,它进行了极富洞见的解读。在此只列举三例:
(1)前面几篇文章描述了培根如何使沉思或理论转向为了人类的利益而征服自然的实践;通过这样做,他如何用一种关于受自然规律支配的简单物(simple natures)的形而上学取代了把世界理解为自然类(natural kinds)的传统观念,个体的人又如何因此蜕变成了物理属性的瞬态聚合。

(2)接下来的文章描述了自《方法谈》时期起,笛卡尔如何把自己的数学物理学和征服自然这个培根式的目标联系在一起。肯宁顿进一步论证说,对笛卡尔而言,根本的二元对立不是心灵与身体这两个彼此割裂的实体,而是新的机械物理学与关于自然的非科学教导,这个二元论内在的目的论贯穿并决定了笛卡尔的整个哲学体系。当然,这并没有使人的性质不再充满问题。笛卡尔使确定性从属于实用性,即研究物质自然的科学从属于人为了自身利益而征服自然的工程,从而以实用而非理论的方式解决了这一问题。
(3)至于培根如何戮力论证普遍的科学启蒙这个人道主义目标与提升帝国势力的一致性,如何论证只要借助于帝国势力即可实现此目标,肯宁顿同样做了描述,而且,他还解释了为什么笛卡尔没有提出明确的政治学说。

此外,这本书具有典范作用还在于,它为我们指明了应该如何解读这些哲人。评论家们开始逐渐接受这样一个观点:笛卡尔的写作主要是针对强者(strong minds)或者说哲人,但又并不会引起非哲人的反对。比如在《沉思录》当中,笛卡尔至少表达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目的:证明上帝存在及灵魂不死;为科学奠定牢固的基础。由此,为了正确地解读此作,读者必须将奠基的部分与和护教的部分切分开来。这实属不易。幸运的是,我们有肯宁顿论述笛卡尔的文章作为引导。同样有助益的是他论解斯宾诺莎《伦理学》的文章,他在文中向我们表明,如何结合“综合的”(synthetic)背景来解读第二部分命题十二之后的“分析的”(analytic)离题内容。然而,最令我惊讶的是他此前没有发表的论莱布尼茨的“自然系统”的讲义,该讲义表明,这位哲人同样也是个“古典”作家。
最后,这本文集的益处还在于它所引出的问题。有的问题明确,而有的则不明确。明确的问题是:在新的自然科学的前提下,应该如何理解人的性质?读者应该怎样糅合洛克《政府论下篇》(Second Treatise)中的自然权利说与更具哲学性的《人类理解论》(Essay)中的追求幸福的学说?不明确的问题是:
(1)我们是否应该把伽利略也包括在现代自然哲学的开创者之列?他关于局部运动(local motion)的新科学不仅关注运动体的症候(symptomata),而且具有实践的倾向,因而类似于培根或笛卡尔的学说。
(2)关于人,是否笛卡尔从未试图从理论上去解决数学机械学和自然学说之间的矛盾?为了弄明白这一点,我们就得研究他的《灵魂的欲情》,肯宁顿在这里只粗略提及了这本书。
(3)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始终忠于我们对事物的前哲学观:它既不是法则性的(nomological),也不和征服自然相承接。然而,新的自然哲学根本上是法则性的并和征服自然相承接:它彻底地抛弃了我们对事物的前哲学观。如果其中一种观点是对的,那么究竟是哪一种呢?今天的粒子物理学家或新本质主义者——克里普克(Kripke)、普特南(Putnam)、威金斯(Wiggins)和埃里斯(Ellis)——是否已找到一条使两者结合或对立的道路?肯宁顿引出了这些问题,回答它们就成了我们的任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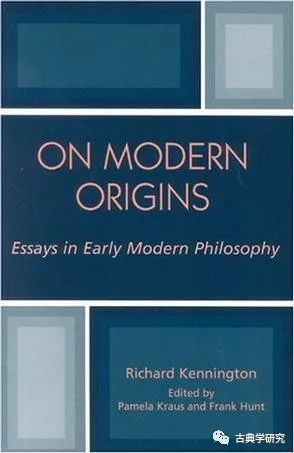
On Modern Origins
延伸阅读

● 雷思温 | 现代人的双重起点:笛卡尔的普遍怀疑与霍布斯的自然状态
● 吴增定 |人是不是自然世界的例外:从斯宾诺莎对霍布斯自然权利学
(编辑:乐铮涛)
关注我们

插图来自网络,与文章作者无关。
如有涉及版权问题,敬请联系本公众号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