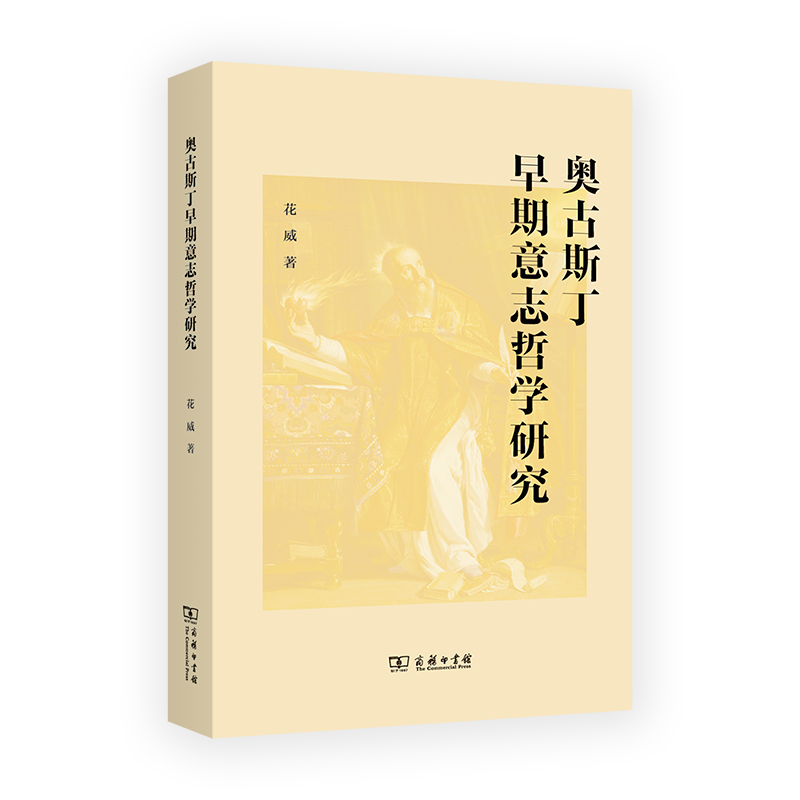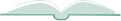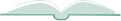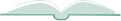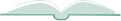奥古斯丁早期意志哲学研究
花威 著
396页,2022年10月
商务印书馆
对于奥古斯丁早期意志哲学的演进,国际学界大致有两种解释路径,即以彼得·布朗为代表的革命论和以卡罗尔·哈里森为代表的连续论。通过细致爬梳奥古斯丁的早期著作,本书试图提出变革论的解释路径,并为奥古斯丁的自我评断进行辩护。
通过检审“意志”概念的发源史,论述其与神义论的关系,本书认为,在4世纪90年代中期密集注释《罗马书》的过程中,奥古斯丁逐步深化自己的意志哲学,使之与“恩典”概念经历复杂的关系摇摆,但最终承认“上帝的恩典占了上风”。
与此同时,不同于使徒保罗“刚强的良心”,奥古斯丁在其意志哲学的演进中实际肇始了一种“受折磨的良心”,由之深刻塑造了后世西方的道德心理学。
Saint Augustine in His Cell by Sandro Botticelli
花威这本书的雏形是 2012 年在北京大学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意志与恩典:奥古斯丁早期意志学说研究》。我是花威的博士指导教师,他现在请我写序,自然不好推辞。动笔之前,先看了看当时为花威博士学位论文写的评语,我写道:
奥古斯丁是西方极难写作具有理论意义的论文的重要思想家,他的哲学和神学理论对基督教思想与西方人的世俗观念都有重要影响。国内外关于奥古斯丁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越来越细化、专业化,写作难度大。只有在广泛吸收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才能写出有理论意义的论文。花威的博士学位论文选择“意志与恩典”这一核心问题,并以奥古斯丁早期思想为研究重点,全面梳理、分析和整合了其早期关键文本,思考和回答了国际学术界提出的几个具有代表性的难题。论文的材料翔实可靠,结构合理,论证充分,注释和写作规范。论文反映了作者具有宽广的学术视野,具有优良的外文水平和古典语言功底,哲学和宗教学方面的知识扎实,对基督教思想有专业性、学术性的理解和把握。希望花威今后能够进一步深入思考和研究西方哲学中理性与信仰的关系问题,把对早期奥古斯丁思想的研究拓展到希腊哲学和中世纪哲学的更多领域。
十年过去了,花威完成了他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并提交了《奥古斯丁早期意志学说研究》的结项成果。我发现虽然上述评语没有过时,他的新成果保持了全面梳理、分析和整合关键文本,回答了学术界具有代表性的难题的风格,但是他并没有按照我“把对早期奥古斯丁思想的研究拓展到希腊哲学和中世纪哲学的更多领域”的期待从事学术研究,而是立足于早期奥古斯丁思想,继续深掘深耕。我并不失望,而是感到欣慰。
大凡学术之道,无非有两条:一是由浅入深,二是化繁为约。一般来说,初学者走第一条路,学成者走第二条路;一般来说,博士学位论文写得好的学生已经完成了初学者的严格训练,毕业后可以走第二条路。读了花威十年后的新成果,我觉得,这个“一般来说”或许不适用于研究像奥古斯丁这样的课题。奥古斯丁对西方神学研究,犹如柏拉图( Plato)对西方哲学研究,不是一篇博士学位论文就能达到学成者的深度,因此需要经久不息地深入,才能有所成就与创新。
学术界的现状验证了我的这一想法。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奥古斯丁研究都在蓬勃发展,研究的焦点仍然集中在花威的博士学位论文涉及的“意志与恩典”这个核心问题上。花威全面梳理了最近的研究成果,总结出奥古斯丁在此问题上前后期的思想究竟是革命还是连续的两种解释思路。
为了找到合理的解释,花威拓展了对早期奥古斯丁思想的研究,把《致辛普里西安》等中后期文本纳入解释重点。他采用历史批判的方法,对奥古斯丁文本做了“意志”概念的发源史、意志与恩典在早期思想中的具体展开过程阐释,最后得到关于其意志哲学的整体意义。通过文本分析和理论论证,作者提出变革论的新解释,既肯定后期对早期思想的理论继承,又强调后期在保罗《罗马书》的视野中,提出完全成熟的原罪、内在恩典和预定等学说,使自己的早期思想得到终极的表达。
虽然花威的新书名为《奥古斯丁早期意志哲学研究》,但无论从问题域还是从解释的文本看,该书都超出了早期奥古斯丁研究的范围,“早期”的限制词是不必要的。或许,花威博士认为,奥古斯丁的早期文本《论自由决断》富有哲理,而反摩尼教的文本侧重于教会内的神学争论,因此把“意志哲学”归于早期奥古斯丁哲学范畴。但我认为,奥古斯丁主义本来就是哲学和神学一体的基督教学术,没有必要在早期和晚期中区别哲学和神学。不过,我的这点建议,无碍于对该书内容的理解。
是为序。
对于《致辛普里西安》1 中的思想转变,奥古斯丁在晚期回顾说:“我实际上在努力维护人类的意志的自由决断,但上帝的恩典占了上风。”(《回顾篇》2.1.3)这一评判显然是符合实情的。在《致辛普里西安》1.1 中,除了提出“原罪”概念,奥古斯丁对《罗马书》第 7章的注释几乎没有任何突破,完全延续了《罗马书章句》和《八十三个问题》66 的成果、局限甚至内在矛盾。而到了《致辛普里西安》1.2 中,在否定了预知信仰与预知事工的模糊界限之后,他才重新反思对《罗马书》第 9 章的注释,根本性地改造了《罗马书章句》和《八十三个问题》68 中的处理,承认“罪的团块”中的意志的绝对无力,不能先行开启信仰而之后才得到恩典,反而是恩典必须在先,是信仰的实际开端。 Adam&Eve by Peter Paul Rubens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上帝的恩典“占了上风”,其作用范围在不断扩大,而意志的作用范围在逐渐缩小,但它不是取代了人类的意志,使意志无所事事或全然被动。信仰的开端仍然是意志的转向,不是被强迫的,反而是在恩典的作用下主动完成的,是具体承载这一开端的主体。在《致辛普里西安》1.2 中,上帝的恩典是先在的,也是外在的,表现为合宜的呼召,而意志正因为呼召的合宜性而必然加以回应,从而完成信仰的转向,既符合上帝的预知和预定,又保持了自身的自主性。
正如布朗所评论的,由于认定意志的绝对无力和恩典的白白赐予,奥古斯丁就把人类的所有善行都归给了上帝,即恩典不是上帝赐给某些人的特殊恩宠,使他们有能力办大事,反而是上帝赐给所有信徒的普遍恩宠,任何日常的善行都是这一恩典的结果,实现了恩典的“民主化”和“去精英化”。不过,基于道德上的罪性和理智上的局限,预定和赐予恩典对于人类是不可知的,这使得恩典同时被“神秘化”,拉开了人类与上帝之间的距离,既认可了人类意志的自主性,又高扬了上帝的仁慈和权能,使得人类不能夸口自己的任何功德,更不能论断别人是否被上帝所拣选或摒弃,集体或民族的救赎完全被个体的救赎所取代。然而,在奥古斯丁前后期思想的演进中,《致辛普里西安》1.1 和1.2 所包含的内在冲突还要历经很长时间才得到消除,其间的重要概念也历经了不断的调整和阐发,最终才形成成熟的原罪学说和恩典学说。首先,即使在完成《致辛普里西安》1.2 之后,奥古斯丁也还没有清楚认识到其与 1.1 所形成的激烈冲突。正如上文所论,与初解《罗马书》相似,《致辛普里西安》1.1 仍然把《罗马书》第 7 章划归为“在律法之下”的阶段,明确肯定了人类“在恩典之前”可以“意志为善”(《罗马书》7:18),从而潜在地承认了意志仍然有能力先行开启信仰,就与《致辛普里西安》1.2的再解释相互矛盾。直到与佩拉纠派论战时,奥古斯丁才意识到这一矛盾,从而把第7章划归为“在恩典之下”的阶段,使之作为原罪和重复的罪仍然不断搅扰信众甚或圣徒的经文依据,理顺了人生诸阶段的前后演进,但却吊诡地契合了《罗马书章句》中对“在恩典之下”这一阶段的理解。其次,在《致辛普里西安》1.2论证人类的有罪境况时,奥古斯丁并没有引入1.1提出的“原罪”概念。即使这一概念包含了从亚当的初罪所继承的灵魂的缺陷,奥古斯丁此时也并不认为,这种罪已经表现在婴儿上,或婴儿受苦和夭亡在于其自己所继承的原罪,甚至以扫在母腹中就有罪(《论自由决断》3.23.66-68)。应该说,初罪和“罪的团块”学说仍然是奥古斯丁早期罪论的核心内容,他还没有使用这一概念来论证整个人类的罪性,特别是婴儿洗礼的绝对必要,如同在《论罪的惩罚和赦免与婴儿的洗礼》中,从而赋予其更为深刻的神学内涵。
Saints Augustine and Monica, by Ary Scheffer 最后,相对于作为合宜的呼召的外在恩典,直到与佩拉纠派论战时,奥古斯丁才开始论证上帝的恩典如何具体作用于人类的意志,就在《论圣灵与仪文》中发展出内在恩典说,承认恩典是内在地促生了意志的转向,而意志自身仍然是自由的,《论恩典与自由决断》就展示了他在这一论题上精微而小心的论证。
不过,《八十三个问题》68.5 和《致辛普里西安》1.2.12中两次引用过《腓立比书》2:13,这已经为内在恩典说找到了经文基础。这一学说的成熟就论证出,佩拉纠派的所谓意志“自由”实际上完全不再有能力去意愿善和行善,人类只能盼望恩典会在“不可知”中降临己身。而在思想史上,奥古斯丁的“恩典”不仅使他与古典的德性理想彻底决裂,而其战胜了佩拉纠派的“自由”甚至被视为西欧古典世界终结的标记。对于《致辛普里西安》在奥古斯丁思想演进中的地位,研究者们给予了毫不吝啬的赞许。波塔利耶认为,因其“准确性、丰富性和清晰性”,《致辛普里西安》是打开奥古斯丁思想的“真正钥匙”(true key),并给基督教教义提供了理性解释。巴布科克论述说,《致辛普里西安》关注了上帝的白白恩典如何与上帝的公义和人类的自由相融合,而这是奥古斯丁对西方基督教的开创性影响。承继了布朗和弗雷德里克森以降的传统看法,韦策尔则认为,《致辛普里西安》1.2开启了奥古斯丁思想的“真正革命”(a veritable revolution),可以被看作驳斥佩拉纠派的先遣书。尽管得到了上述诸多赞许,但《致辛普里西安》究竟蕴含着怎样的思想转变,如何评价这一转变在奥古斯丁早期思想中的地位,学界仍然有着不同的声音。显然,以上分析表明,其中的转变主要是,在信仰的开端中,从人类的意志先于上帝的恩典转变到上帝的恩典先于人类的意志,信仰的起点是恩典,而信仰的载体是意志。除此之外,奥古斯丁在罪论和信仰动力要素上基本延续了初解《罗马书》的思想成果,甚至在四个阶段学说和解释《罗马书》第7章上仍然存留着少许缺陷。对于这一思想转变,以布朗、弗雷德里克森和韦策尔为代表的传统解释认为,《致辛普里西安》表征着奥古斯丁的思想革命,并从此进入以《忏悔录》为代表的思想成熟时期。卡罗尔·哈里森对此描述说:
我所指的就是所谓的“4世纪90年代的革命”(revolution of the 390s),这一说法已经成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奥古斯丁研究的基本特征,极具典型和特色,以致当前学界几乎无法回避,甚至在最为短小的文章中也是如此。现在普遍认为,要理解奥古斯丁,我们就必须认可,他在4世纪90年代早期的思想革命是他阅读和反思保罗作品的结果,其中最特别的是《罗马书》和《加拉太书》。
与传统评价相反,卡罗尔·哈里森认为,奥古斯丁的思想革命并不发生在 396 年的《致辛普里西安》中,而只发生在386年的信仰皈依中,其成熟期的诸多神学特征都从此而开始,之后虽有变化,但在根本上是连续的,并不存在着所谓的“革命”。在其2006年出版的《奥古斯丁早期神学再思:为连续性论证》一书中,哈里森细致梳理了奥古斯丁思想的诸多主题,包括上升、无中生有、堕落、意志和恩典,展示了它们在早期著作中的展开过程,令人信服地阐释了其中的多条连续线索,包括《论自由决断》的内在统一、恩典的绝对必要和《致辛普里西安》对早期思想的承继。
然而,对于《致辛普里西安》1.2,哈里森却坚称,其中调换意志与恩典在信仰开端中的前后位置只是“变化”(change),而这一变化是“自然进化”(natural evolution),根本不是新的学说,反而恰恰回到了之前对恩典的绝对必要的肯定,校正了4世纪90年代早期的错误,“更为清晰地”(with full clarity)理解了先前的信仰。由此,既不存在着布朗所说的“失落的未来”,从乐观主义转到悲观主义;《致辛普里西安》也不表征着存在前后两个截然不同的奥古斯丁,反而只是以新的术语“重新肯定”(reconfirmation)了之前的思想。
Saint Augustine,by Philippe de Champaigne
至于《致辛普里西安》1.2中的思想转变究竟是革命还是连续,基于本书的论证,我们尝试走出一条中间道路,提出变革论(reformation)的解释,既肯定其中对早期思想的理论继承,又强调所蕴含的深刻的理论变革。相较于意志先于恩典,恩典先于意志的调整绝对不是早期思想内部的微调,更不是仅仅回到了早先对恩典之必要的强调。因为在早先著作中,奥古斯丁还根本没有论及恩典在信仰开端中如何具体作用于意志,恩典的必要并不表明恩典在先。对于连续论的解释,罗奇就批评说,哈里森对《致辛普里西安》1.2的研究尚欠清晰,贬低(downplay)了转变的根本性;奥古斯丁的确采纳了新的救赎学说,这与他先前的看法是“截然相反的”(diametrically opposed),他自己甚至都不得不承认其重要性。的确如此,在后来与佩拉纠派的论战中,奥古斯丁就把《致辛普里西安》看作自己成熟思想的宣言,甚至频繁引用《哥林多前书》4:7和《腓立比书》2:12-13,表征自己在《致辛普里西安》之后的思想连续性,并引用西普里安的话表明自己的成熟思想符合教父传统(《论圣徒的预定》3.7、4.8;《论保守的恩赐》17、45;《回顾篇》2.1)。基于意志的自由决断最终顺服于恩典的绝对全能,我们就有理由认定,《致辛普里西安》仍然可以是奥古斯丁早期思想的逻辑终点,是向成熟思想转变的关键节点,是“成熟的开端”。只有等到与佩拉纠派的论战,奥古斯丁才消除在四个阶段学说中的错误,把《罗马书》第7章划归到“在恩典之下”的阶段,提出完全成熟的原罪、内在恩典和单重预定等学说,使自己的早期思想得到“最为终极的表达”(most extreme expression)。对于这一思想历程的深远影响,正如弗雷德里克森所高度评价的:如果西方哲学可以被看成是对柏拉图的注脚,那么西方基督教思想则大部分可以被看成是对奥古斯丁的保罗(Augustine's Paul)的长篇回应。
以上节选自《奥古斯丁早期意志哲学研究》第345—351页,注释略

花威,北京大学哲学博士,现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古希腊罗马哲学、中世纪哲学、奥古斯丁思想和基督教思想史,在《哲学与文化》《道风:基督教文化评论》和《汉语基督教学术论评》等期刊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30余篇,译有《奥古斯丁〈罗马书释义〉》等。(书讯来源:商务印书馆南京分馆)
(编辑:王俊岚)
插图来自网络,与文章作者无关。
如有涉及版权问题,敬请联系本公众号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