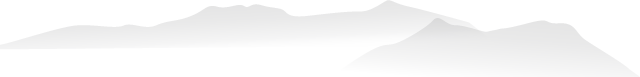古典学研究
王丁 | 怀念王太庆先生

▲ 王太庆先生
我上初中接触了声光化电,可是最感兴趣的是希腊故事,再就是文天祥的《正气歌》、史可法的《复多尔衮书》。念法文我偏喜欢看圣女贞德的抗英事迹,《马赛曲》也能背。进了高中,工厂实习成绩平平,假日却爱上四马路,到书店里站着看书,从尼采的《苏鲁支语录》看起,直看到杜兰的《哲学的故事》。看得似懂非懂,还想再读些别的;也正因为自己知道有许多东西不懂,想求助于别人写的文章,进一步把它弄懂,但是没有成功,因为我不懂的地方别人也很少说。我自己意识到中国人到哪里去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个哲学问题,但是我听来的那点哲学还远不够用。(《王太庆自述》,方克立、王其水主编《二十世纪中国哲学》第二卷《人物志》,华夏出版社,1995年,67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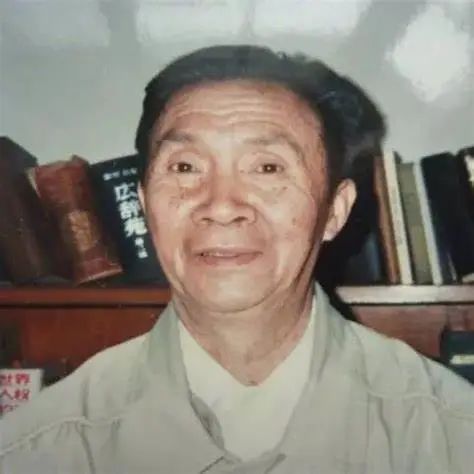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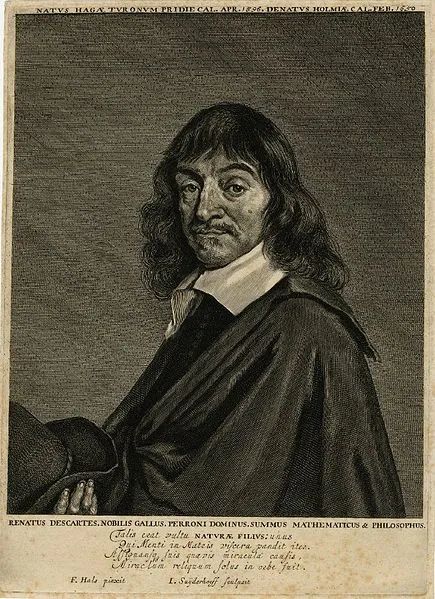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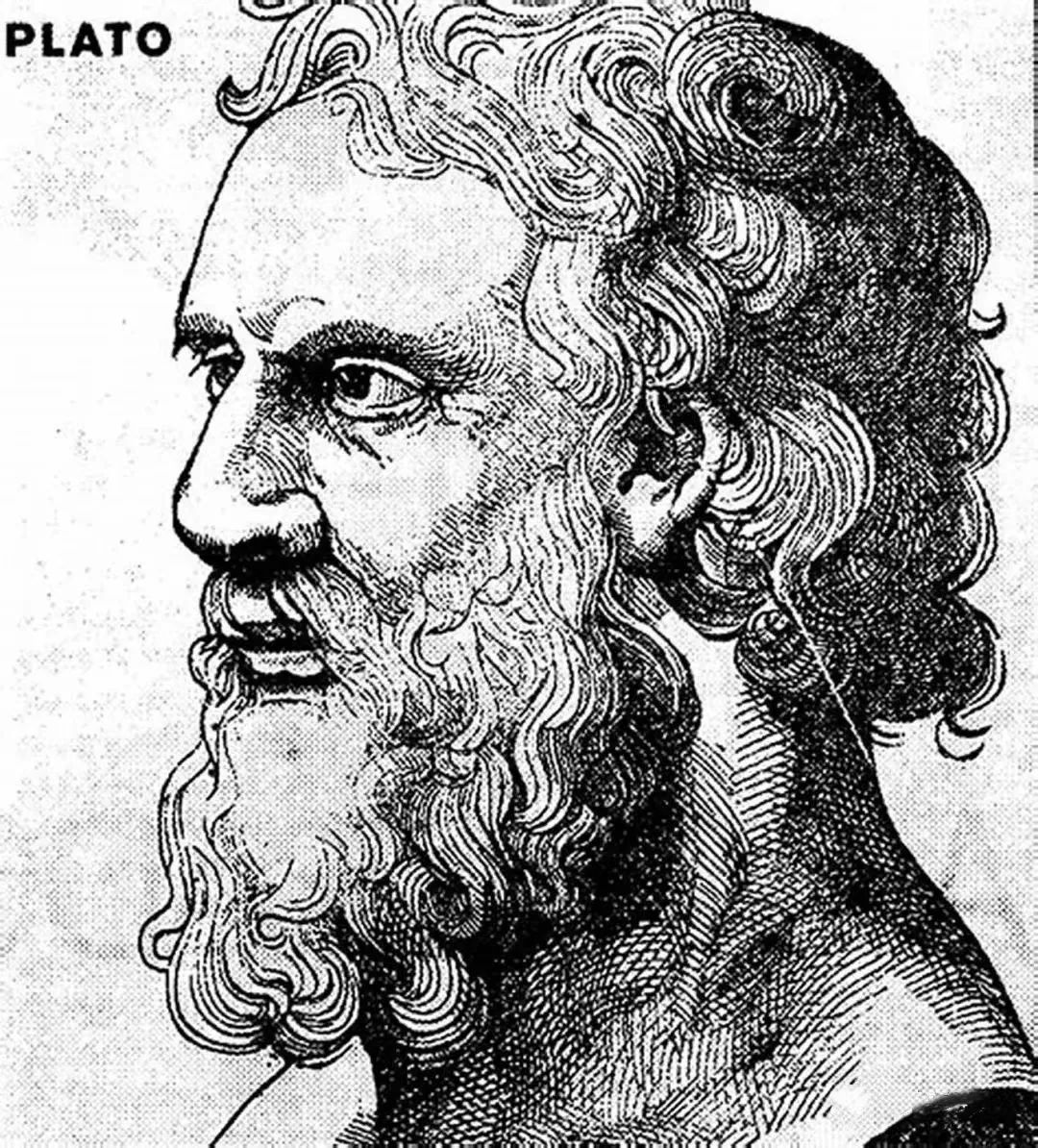
不用白话文,哲学翻译就只能依稀仿佛,精确不起来,不能满足科学的要求,至多做到严复那样的达旨。改用白话文,其实不只是不用文言文,而且包含着改造白话文。原来的口语长期以来不用于文字,用起来虚弱得很,粗率得很,语词不够,语法模糊,而且汉语方言众多,缺乏规范。这个改造汉语普通话的过程在解放前进行了三十来年,解放后又进行了三十来年,到今天才有这个样子,但还不是大功告成,而是仍须不断努力。
在过去的封建时代,一个王朝只有在行将灭亡的时期才出现语文程度低落的现象。
(注:本文作者王丁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延伸阅读


(编辑:许越)
关注我们

插图来自网络,与文章作者无关。
如有涉及版权问题,敬请联系本公众号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