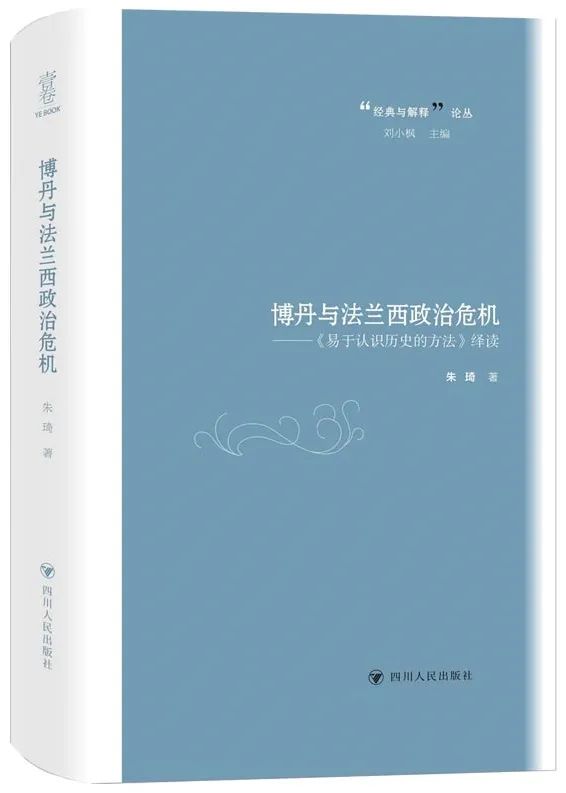中世纪晚期是西欧各王权国家的民族意识开始觉醒的时代。随着罗马教廷大一统的威权和能力下降,各国都希望能够摆脱教宗及其教阶制的控制,建立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只需诉诸于政治常识便知,以民族为基础的王权国家要能立住脚站得稳,领土完整、经济自主和思想独立是必要条件。尤其是思想因素,不仅需要有相对统一的国家精神,而且要有克服分裂的精神因素。法兰西在15世纪时的国土面貌并非如我们现在所见。那时王室控制的领域非常有限,大概南至纳尔榜,东至里昂,北至布卢瓦,西至拉罗歇尔。西边的波尔多尚不在王室控制范围,勃艮第也不断造次。经济方面,无法从贵族那里获得足够的钱财支撑自己的政治措施一直是王室展不开手脚的大问题。1461年,瓦卢瓦王朝的第六位国王路易十一即位。这位抱负伟大的君王一掌权即以雷霆手段对付不顺从的封建领主,企图兼并各方土地。为了挫败反对他的贵族同盟,路易十一采取了一切可以采取的手段,包括武力。他先后收回了阿朗松公爵领地、阿曼雅克伯爵领地、勃艮第公爵领地、皮卡尔迪、普罗旺斯伯爵领地等,为之后其子查理八世收归布列塔尼奠定了基础。布列塔尼于并入王室后,现代法兰西版图开始成型,逐渐形成统一的王权国家,法兰西君主的实权也与日俱增。从路易十一开始,法兰西王室“不再因征税而召开三级会议”, 从某种意义上讲,王室收入有一定的保障因而相对更加独立于各大领主。虽然接下去的两任君主查理八世与路易十二因征战意大利耗费了不少财力,但好在国王的威权得以持续增长。再加上路易十二改革司法体系、为国民减税,百姓生活得到改善,对国王更加爱戴。王位传至弗朗索瓦一世时,法兰西已经朝着绝对君主国高歌猛进。王室基本上解决了领土与经济问题。但国家真正独立的第三个要素,即达成相对的思想统一,并非易事。恰在此时,西欧大地又出现了新局面:宗教改革开始在各国蔓延。以宗教信仰为名,各国境内的宗教分裂势力、政治分裂势力与统治者的权力斗争越演越烈另一方面,罗马天主教廷也一直不肯放弃对各国政务的管制,斗争变得越发错综复杂。16世纪五、六十年代,法兰西境内主要有三大派势力:以吉斯家族为代表的较为极端天主教势力,其后有以西班牙为主导的天主教神圣联盟撑腰,对王室决策有重要影响;以孔代家族、南部纳瓦拉王国和海军上将科里尼为代表的新教势力,聚集了很多贵族和第三等级人物,是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手握着国家诸多实业资产,王室不敢小觑;天主教信徒中以掌玺大臣洛斯皮塔尔和巴黎高等法院为代表的政治家派希望调和双方,尽力保住国家的统一,大多数时候得到王室的支持。很明显,在前两派势力的撕扯下,国家面临分裂危机,第三派为了聚合国家在其间努力周旋。事实上,任何一个国家在任何时候其内部都不可能是铁板一块,总有新生力量或异己要素产生,它可以成为促使国家改善的源头,也可以成为分裂势力的肇端。这一点,马克思唯物辩证法里的矛盾定律早已分析得非常清楚。既然异己要素并非偶发事件,国家统治者和政治家们需要考虑的便是如何建立能够容纳、吸纳或化解这些力量的长效机制,避免威胁到国家的安宁和统一。历史告诉我们,就算是曾经统一西欧的天主教拉丁帝国,内部各种小教派的滋生与摩擦也从未停止过;只是中世纪时期强大的教阶体系一直能吸纳或镇压它们,避免它对体制造成太大危害。显然,16世纪的法兰西在新教萌芽初期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没有在分裂势力刚刚抬头时预见到其可能造成的后续危害。到博丹时代,分裂问题成为法兰西的首要政治危机。作为政治家、法学家的博丹,思考的正是祖国面临的这场分裂危机:法兰西需要什么样的理论支撑和政治策略,才能度过危机?才能成长为真正独立的民族国家?博丹诉诸于王权,即希望代表不同利益的三方能在王权的统领下妥协和解。让王权高于教权和贵族权力的依据是什么?博丹告诉我们,是历史。《易于认识历史的方法》(Methodus ad facilem historiarum cognitionem, Method for the easy comprehension of History,下文简称《方法》)便是在这种探索中结出的果实。它并非旨在指导史家写作历史,而是希望教政治家和法学家阅读历史、从历史中寻求资政治国的方法。从而我们可以说,博丹同修昔底德一样,“从政治历史的角度来看待历史”,政治事务是历史写作的首要对象,立法治国是历史研读的首要目的。正如英国史家弗里曼所讲,“历史是过去的政治,政治是现在的历史”。离开政治的史学定会丧失价值与目的,最终陷入细枝末节的虚无。因此,我们可以把博丹对史学的态度视为施特劳斯定义的修息底德式史学,即“政治史学”。本书第一章简单介绍博丹的生平,第二章将通过绎读《方法》第一至四章、梳理西方史学从修息底德至博丹时代的发展,以明晰博丹政治史学的继承与发扬。
博丹诉诸于普遍历史,目的指向政治事务,为帮助法兰西扫除通向独立王国的重重阻碍。从普遍历史中博丹发现,王制是最好的政治,只有王制能够在国家紧急状态下迅速整合国家资源,做出统一反应。法兰西一直行王制,任何国家若是以一种政体形式延存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说明这种政体形式适合这个国家,有利于该国的存在和发展。法兰西正是如此。本书的第三至五章,通过解读《方法》第五、六章,厘清博丹的立法主权理论的来源与内容,阐述他的国家统治理论,了解他离开学院投身政治实务的远大抱负,以及他对祖国的深情厚望。法兰西如何才能成长?只有诉诸于自己的历史和祖制,坚守自己历时千年的王制经验,将宗教分歧问题置于国家统一问题之下,民才能生、国才能盛。本书第六章将结合法兰西在16世纪面临的政治危机,分析博丹的写作目的及其抱负,揭示他对时局的思考及其理论贡献。
▲ 博丹 (Jean Bodin,1530―1596)
作为为政治服务的史学,政治史学在博丹这里获得了发扬。史学与法学在博丹的立法主权中融合,共同为国家主权提供源泉和凭据,从而为国家主权独立和国家发展服务。作为学者的博丹却没有就此停下。他在《方法》第七至九章把自己的国家理论与宇宙论联系起来,构建出个人灵魂秩序——国家秩序——宇宙秩序的宏大体系,其中不仅囊括对宇宙起源、时间、自然法则等经典哲学问题的探讨,还包括对人的灵性问题的思考。由此,博丹将他的政治史学引向了更高的政治哲学,从而对应了他在《方法》开篇时划分的史学的三个分类。本书第七章讨论的便是博丹的这一上升。同时,作为智识人的博丹,对自己的智识人身份与政治人身份也有清晰的认识,并在理论和实践中展示出来。小书以疏解博丹《方法》一书为线索,对照他的其他主要作品,结合博丹身处时代的混乱局面,展现作为16世纪的智识巨匠,博丹如何坚守自身的精神品质,承担起作为国家公民的重任,为国家面临的政治危机寻求应对之道。所谓危机,概身在危局亦不乏机会;所谓变局,则有向前发展的可能,也不得不警惕后退的陷阱。至于变化的轨迹究竟如何,有偶然因素的作用,更是身在其中的人的意志、行为和德性选择的必然结果。博丹看到的法兰西危局,是外有德意志地区各领主、西班牙、英格兰,以及罗马教廷的虎视眈眈,内有各派政治势力打着宗教信仰的名义构成的分裂势力;国家处于内忧外患之中,濒临四分五裂的边缘。博丹看到的契机,是法兰西王权仍在,传统习俗和礼法对人的约束力仍在起作用,不少国家政治人在为着拯救和重振法兰西荣耀竭尽所能,国家的传统资源还没被消失殆尽。若国家中政治人有智识人的学问和智慧,智识人有政治人的克制和审慎,做好充分准备,待天命垂青,出现集智识、胆魄与德性于一身的统治者,国家战胜外敌繁荣兴盛便指日可待。因此,他将主权理论献予王者,历史教育分享同好,这是作为政治人与智识人的博丹面对国家危机时的自律与他的思考成果。这是每个政治人、智识人、政治人曁智识人在面临国家政治危机或变局时应该做好的职分。西方文明从康斯坦丁大帝发展至今,可以说与基督教的发展和裂变密不可分。不理解基督教,就无法透彻理解西方中古以来的文明,更无法理解宗教改革之后的现代西方文明。基督教历史上经历过两次大分裂。11世纪中叶的第一次大分裂区分出东正教和罗马天主教;第二次大分裂便发生在博丹所处的16世纪,从路德发起新教改革之后引发的天主教内部的大分裂。
第一次分裂的发生,“在本质上不是教会或宗教的,而是政治竞争的结果”, 当然,其中不乏有东西方语言差异、文化背景差异、政治制度差异等因素的影响,但根本原因在于罗马帝国皇帝的威权不足以压制住东西方教会首领的野心,以维护帝国的统一。第二次分裂即罗马天主教内部的分裂,虽然看似由改革教阶制度内部的腐败引发,但最终造成的分裂则是各民族国家之间政治博弈的结果。而且,在第二次分裂出的路德宗、加尔文宗和英格兰国教的内部,又进一步分化成各式各样更小的教派,造成民族国家内部的分裂,威胁到现代初期刚刚开始成型的现代国家。那么,如何才能压制国家内的分裂势力?
博丹在《易于认识历史的方法》中论及帝国的各种变化时说,国家的天性,即国家在建立之初就具有的特性非常重要,国家“在最初诞生时被调和得越好,就越能够抵制外力,很难从内部颠覆”。随即他提到一系列古老的法兰西国家制度——古奴隶制、宗教制度、封臣制度和封建制度。这似乎是说,法兰西最初建国时,国家天性不错,即各种古制不错,因而国家维存了很久。如果废除这些古制,未来就未可知了。然而这个假设已经成为了现实:近年来对这些制度的攻击甚至废除,“给叛乱——前所未有的叛乱以可乘之机,那些叛乱古人们几乎闻所未闻”!然后,他略过了封臣制度和封建制度,直接详谈奴隶制的废除和宗教改革。博丹说,人们一度担心,奴隶被解放,国家可能受到威胁,古代史实也有相关证据。但是呢,由于我们无法确知奴隶制消亡的具体时间,所以没法确认帝国变迁是否因为这个原因。是不是真的无法确认呢?他马上就提到了诸多西欧历史上鼎鼎有名的伟大君主,包括查理大帝、弗里德里希二世、腓特烈,以及强势的如君主般的教宗亚历山大三世(Alexander III)、乌尔班三世(Urban III)和英诺森三世(Innocent III)等,都颁布过关于奴隶和仆役的法律。但是,解放奴隶的做法“在各基督教帝国中引起了严重骚乱……当奴隶解放被批准,紧跟其后的是极度的贫困,这种贫困很容易颠覆国家。由于极度贫困,会滋生抢劫、盗窃、杀戮和公共乞丐贸易”。(页260)
▲ 《独立宣言》1823年原件摹本
用我们现在的眼光去看待奴隶制度,当然要批评它剥夺了奴隶的人权,奴隶也是人,理应得到尊重。然而,博丹告诉我们,现实情况是,这些奴隶被解放后,陷入极度的贫苦之中,人都快饿死了!用法学术语来讲,这相当于在赋予他们所谓自由权的同时,拿走了他们的生命权。让奴隶们自由到一无所有地饿死,这是仁慈吗?毕竟,当代自诩为最讲人权的国家也在其《独立宣言》里把生命权置于自由权之前。博丹显然明白他这样讲奴隶制会给自己招致何种非议,所以毫不客气地指出,“是基督徒害怕他们的奴隶信徒可能落入异教徒的权势中,所以才不停地解放奴隶”。原来所谓的其它原因都是次要的,最主要的还是政治原因——不能让原属自己的人落入敌人手中后反戈相向。就算没有反戈的原因,大量无人约束、无家可归、一无所有、吃不饱饭的人在国家内游荡,也会给原本稳定安宁的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和恐慌,使国家面临被颠覆的危险。所以,博丹说没法确认帝国变迁是不是因为解除奴隶制的原因,也许并不是不能确认,而更像是隐晦地提出,在没有准备好接受并干预改变原有制度可能带来的骚乱前,国家在没有准备好应对变局的策略前,维持原来的稳定状态也许是最好的选择。毕竟,亚里士多德早在2000多年前就指出,最坏的统治也好过没有统治。接下去博丹谈到了宗教分裂。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很多人正是以宗教为借口侵略伟大的帝国”!他说查理五世曾在日耳曼试过此法。查理五世做了什么?哈布斯堡王朝的的首位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尼德兰君主、德意志国王,16世纪欧洲最伟大的君主之一,声名甚至高过英王亨利八世、法王弗朗索瓦一世的伟大君主,做了什么?博丹没说自然是因为在他那个时代,这是个常识问题,他写作此书时,查理五世才刚刚离世(1558年)。但我们必须追问这个问题,才能更明白宗教如何在各国内部成为分裂力量。
▲ 查理五世(Charles V,1500―1558)
1516年,年仅16岁的查理五世便从其祖父手中结果了西班牙的统治权,3年后成为德意志国王,4年后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在西欧复杂的政治环境中杀伐疆场。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于1517年发表,迅速在德意志境内掀起新教改革的浪潮。如前文提到,这一时期西欧政治环境,已陷入罗马天主教教宗、新教改革头目、神圣罗马帝国与各民族国家的国王争权夺利、勾搭背叛的浑水之中。路德提出的“王权高于神权”显然深得查理五世之心,这位伟大的君主既想要摆脱罗马教宗对德意志政务的干涉,又不得不维持自己在西班牙天主教联盟首领的地位。于是我们看到,查理五世先在1521年的沃姆斯帝国议会中与教宗联手,反对宗教改革,指责路德为异端,然而却并没按照处置异教徒的规矩立刻处死他,而是等到三周之后才公布《沃姆斯敕令》。而且,查理五世居然完完整整地倾听了路德对教宗的控诉,还让他毫发无损地离开,这是镇压新教吗?路德离开后仍然专注于以文为器与教廷为敌。放过路德,显然不是所谓迫于众多平信徒的压力,而是因为新教在德意志掀起的狂潮,对于查理五世与教宗之间的权力角逐有重大利好。新教“君权至上”的主张是可以利用来削弱教宗的力量,何必一竿子捅死呢。如果能利用这股力量,强化自己的皇帝威权,聚集各选侯帝,何乐而不为?然而,查理五世没能预见到的是,分裂的种子一旦埋下,自会生根发芽。1551年,德意志帝国境内的新教诸侯势力坐大,竟然与天主教诸侯结盟联手反对皇帝,最后以签订《奥格斯堡和约》大获全胜,年迈的查理五世那时再也无力回天。博丹说查理五世曾在日耳曼试过此法,指的或许就是这一段历史:试过,但并未一直成功。伟大的君主都明白,只要宗教在世俗王国中落地,就决不仅仅是精神性的信仰问题。政治家们当然也明白这个道理,否则不会控诉宗教对帝国的侵略。而且,法兰西这时恰处在宗教战争的风暴之中,国家面临被分裂的危险。显然,纯粹的信仰问题没法掀起如此巨大的浪潮。那到底是什么因素呢?▲ 沃格林(Eric Voegelin,1901—1985)
20世纪的政治哲学家沃格林告诉我们,宗教改革的实质,就是一场反对体制的运动。在西方文明的动力机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运动与体制之间的张力,然而人们一直太过关注纯制度层面,忘记了二者的互动性。针对体制的社会运动是从宗教中的小教派兴起开始,从“7世纪叙利亚的保罗派运动(the Paulician movement),到保罗派向巴尔干半岛的传播,到其支脉鲍戈米勒派(the Bogomil sect),再到保罗派与鲍戈米勒派向上意大利(upper Italy)的移民,一直到清洁派(the Cathars)于11世纪在法兰西南部的出现”,这个运动的传播线索,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勾勒得很清楚。属灵的信仰问题本不是政治问题,基督教的教阶体制却给这个原本非政治的精神元素加上了政治性实体,进而成为了主流体制,且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秩序。同样,与这个主流信仰不同的其它属灵元素有了教派的依托,要在主流体制中获得存在感争取权益之时,非政治问题就转化为政治问题,成为反政治力量。如果在一个共同体中,这种人这种小教派多到一定程度,“并且发展出一种行事哲学,符合那些以‘身体’生活于社群之中而非以‘灵魂’参与其中的人们(借用柏拉图的表述)的需求,借以表达自己的感受与观念的话,就会出现我们所谓社会规模上的非政治主义现象”。 而如果这些人被组织起来形成了一个群体,并且采取实际的政治行动,反制度的革命时机就成熟了,就会对原有制度秩序构成极大威胁——动荡的内力已经集聚成型,一触即发。所以,沃格林警示到,“一项制度必须时刻投身于稳固自身的运动,解决那些如若任其发展将会危机自身价值与意义的问题”。▲ 《九十五条论纲》,原名《关于赎罪券效能的辩论》
可以说,罗马天主教从成为罗马帝国国教开始,就成为了体制的重要构成实体。中世纪前期和中期,作为体制的教会和罗马帝国足够强大,能成功应对各种反体制的势力和运动,不管是采取吸纳各小教派、还是直接镇压异端的手段。从1300到1500这段时间,教会的吸纳能力日趋下降,但总体上还能够镇压各种反天主教体制的运动。而从1500年开始,反体制运动逐渐强悍,甚至逐渐形成了各自的理论体系,或者沃格林所说的行事哲学(路德教义、加尔文教义)和另一套与基督教教会敌对的体制(加尔文在日内瓦建立的归正宗国,以及欧洲各国名称各异的新教教派,例如法兰西的胡格诺派、英格兰的圣公会)。对于原有的体制来说,这显然是无法共存的敌人。很多人会认为,新教不过是希望能废除天主教所谓的“繁文缛节”,去除那些教礼以及中间的教士阶层而已。博丹说,除了犹太人,所有的祭祀礼仪都差不多(页261)。言下之意,祭祀礼仪的内涵是将人们以某种一致的行为方式具体规范起来,它代表的是具有神性的统一性,所谓“因信称义”,所谓无需各种仪式,其实质是废除统一性和秩序,只留下空洞的自由和自欺欺人的虔诚。“礼”,仪式,从来都和“法”密不可分,尤其在国家政治领域。《旧约》中有礼仪律,各国都有其习俗法规定习礼。我国旧制中设有“礼部”,专管国家的重要典礼仪式(如祭天地、祭祖先)并负责给各种仪式制定规则和做出解释,很多时候还主管国家的人才选拔(科举考试)和接待外国来宾,相当于现代国家行政机构里的外交部、教育部以及国家各种司法机构的综合。重要国家祭礼往往是政权寻求并展示其合法性抑或宣扬意识形态的手段,而对民俗习礼的规定和解释则是构建统一意识形态和稳定政治秩序的重要措施。因此,新教所宣扬的废除各种天主教旧礼,其实质是废除了教会构建的制度和秩序。从形式上仍然统一的罗马帝国来看,新教运动与后来政教分离、各民族国家走上世俗化的过程,实质上都是分裂主义——分裂统一的拉丁帝国。
▲ 加尔文(Jean Calvin,1509―1564)
我们不妨再换个角度,从博丹的祖国法兰西的角度出发来理解他的说法。法兰西王国从13世纪开始一直致力于摆脱天主教会和教宗的控制,争取王权在国家事务里的最高决断权。事实上,作为一个王制有古老传统历史悠久的西欧强国,法兰西不仅从未被教会完全控制,而且很多时候通过控制教会控制着大部分西欧。王室成员和权贵多是天主教信徒,这也是首都巴黎长期以来一直是法国天主教大本营的原因之一。因此,当新教在法兰西传播,加尔文宗渐成气候甚至很多贵族包括王室血亲都转投新教时,它就成为了分裂国家统一的政治力量,加尔文本人对其分裂性质毫不避讳:毫无疑问,加尔文提供了法国加尔文主义者造反(不管我们视这个“造反”为防御性的还是侵略性的)所需要的神学上的推动力量,而且他继续组织、支持法国的胡格诺派(即加尔文主义者)的暴动,直到1563年生命将尽之时,他还因认为休战协定背叛了自己而深感遗憾。我们无法理解,作为一个法兰西人,加尔文为何乐于见到祖国陷入分裂和动荡之中。当然,他离开法兰西奔向日内瓦建立归正宗国、成为最高统治者这一事实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丝解惑方向。或许我们更能感同身受的是博丹为了祖国避免被分裂的忧心和努力,毕竟我们自己的祖国也曾多次面临分裂的危险,而且时至今日这种威胁也仍然存在。外部与内部的分裂势力,时刻对我们虎视眈眈。博丹在详述宗教这段的第一句话就大声疾呼:“宗教的多样性已经给国家和统一带来诸多困扰……生出了无穷无尽的政体变化”(页222)。政体变化就是国家质变,就是旧国之覆灭,其根源就在于宗教的多样性分裂了国家。
博丹讲述帝国变化时聚焦在导致国家灭亡的内部力量上,在旧制废除和宗教改革上,不能不说是刻意为之,以呼吁有识之士认识到法兰西正面临的政治危机。▲ 《易于认识历史的方法》
(法)博丹著,朱琦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同样,博丹在《方法》第六章末强调君主教育过程中应该引起重视的两个要素时,其中之一就是需要教育君主信奉真正的宗教。君主需要明白,他统治的目的是侍奉上帝。什么是真正的宗教?博丹本人的宗教信仰一直是个迷,没有研究者能给出确定答案。只一点可以肯定,博丹不是无神论者,他曾明确地讲,城邦中唯一不能宽容的就是无神论者,因为他们是社会动荡的危险分子。诸多研究者认为,博丹的宗教观表达在其晚期作品《七贤聚谈》中,而《七贤聚谈》中揭示的是,每一种宗教都是各自的历史环境所致,仅代表部分真理,因而各种宗教不仅可以讨论、彼此宽容,甚至可以统一于国家秩序。然而,沃格林可能看得更深:博丹确实想要它们都服从国家;但博丹的国家不是一个与教会相分离的政治世俗主义的国家;而是一个皈信上帝的宇宙等级制的类似物;类似地,《法义》的城邦也不是一个政治世俗主义的宪政政府,而是再次展现宇宙秩序的“严肃戏剧”。如此,我们能更好地理解博丹“自然地理——气候特征——民族天性——国家法理”理论链的内涵,即一切都是上帝所安排的自然秩序所致;也可以更好地理解博丹为何为阐述令人费解甚至牵强附会的数秘论——数字是上帝秩序的表达方式;同时能更深入地理解博丹所呈现的国家法理秩序。君主信奉“真正的宗教”,才有可能窥探到上帝所安排的完美宇宙等级秩序,哪怕只是一瞥,便会心存敬畏。敬畏之心是君主美德的源泉,“能够意识到上帝是他所有行为的裁决者和观察者,他也就不会做什么恶毒之事,甚至不会思考任何卑鄙之事。他的国民会对他又爱又怕,会以他为榜样,规塑自己的生活和习俗”(页340)。毕竟,作为掌握最高权力的君主,若是自己不能约束自己,又有哪个职官、哪条实定法律、哪个权威能约束他呢?君主对自己的约束只能因敬畏上帝而来。
也就是说,博丹认为君主需要信奉的“真正的宗教”,可能并非哲学意义上的“真正”的宗教,而更可能是政治秩序意义上的“真正”的宗教。哲学的研究对象是真理,彻底的真理。而任何一种历史宗教都仅代表部分的真理,硬要去追问哪一种历史宗教是真正的宗教,就是追问哪一种宗教是真正的真理,是企图哲学地处理宗教,既没有必要也无法获得解答。政治哲学的宗旨是政治地处理哲学,以此为指导,政治地处理城邦政治事务也包括政治地处理代表部分真理的某种宗教,提倡宗教宽容便是政治的处理方式。不哲学地处理宗教,意味着不去刨根问底地追寻某一种历史宗教的真与假。所以,作为政治家的博丹也许并不是刻意隐瞒自己的宗教倾向,而是认为对于一个把国家政治事务作为第一关注的人,一个目的始终指向公共福祉的人,没有必要表明或讨论自己的宗教信仰。在博丹眼中,《摩西五经》、《旧约》、《新约》都是历史书,是为法学家提供历史记录、立法和治国参考的历史书。另一个例子,“勤政王”亨利四世为了进驻巴黎统一全国,在巴黎城下就地改宗,是一种政治地处理方式;同样,博丹从不太看好亨利四世到相信他是可以重振法兰西的明君,也是一种政治的处理方式。在政治生活中,信奉“真正的宗教”是从内心敬仰且维护上帝所安排的宇宙自然等级秩序,对于君主来说,就是维持国家的安定、国民的幸福生活,让每一个阶层都各得其所。博丹对宗教多样性的担忧,正是意识到它会引发的国家分裂危机,所以出声示警。宗教信仰本是个人精神世界的问题,但是进入公共领域,与国家政治生活相互纠葛,其多样性就为社会的不稳定埋下了复辟。对于作为政治人的博丹来说,什么是真宗教的问题在国家统一问题之下;当然,作为哲学家的博丹,真宗教的涵意及其重要性,那就另当别论了。然而,宗教分裂带来的精神分裂不仅在西欧各民族国家内部危害了统一与秩序,威胁到各国王权,而且最终导致了绝对君主制在整个西欧大地的覆灭。朱琦,法学博士,美国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访问学者(2017),四川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从事西方古典政治哲学方面的研究和教学工作。著有《古希腊的教化》《博丹与法兰西政治危机》,译有《易于认识历史的方法》。
《博丹与法兰西政治危机》
▲ 点击图片 购买图书

《易于认识历史的方法》
▲ 点击图片 购买图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