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与解释·华夏 | 《亚里士多德论政体》(崔嵬、程志敏 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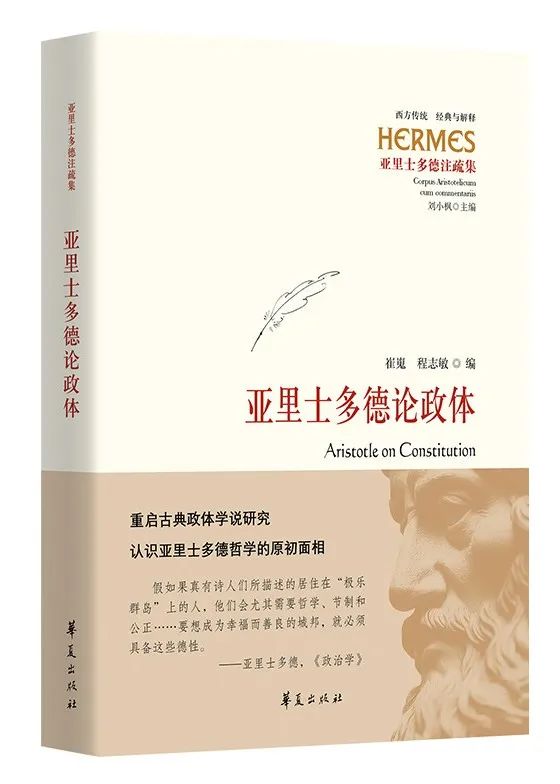
内容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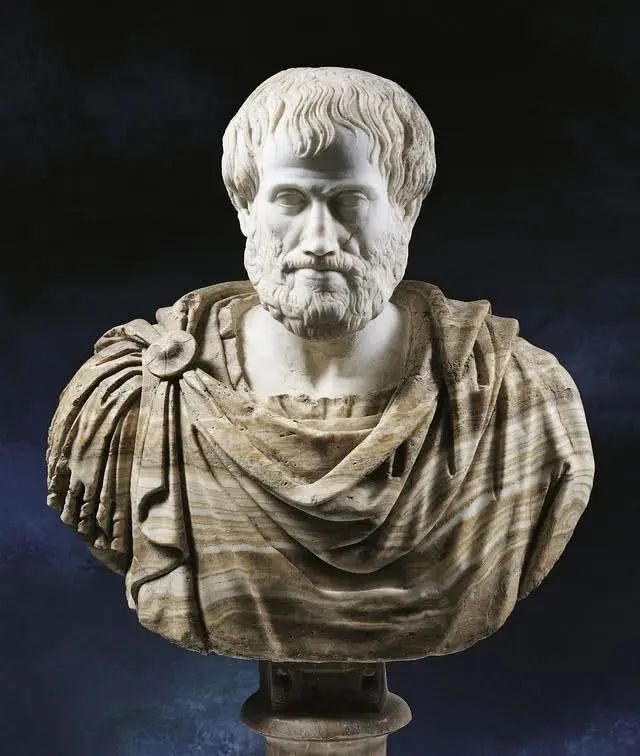
目 录
编者前言
亚里士多德对《王制》的批评
霍布斯论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亚里士多德论理想政体
亚里士多德论较优与稍逊、正确与错误的政体
亚里士多德对寡头制和民主制的分析
亚里士多德与民主制
内文试读
亚里士多德驳柏拉图
政体的目标
整个城邦愈一致便愈好,但是,一个城邦一旦完全达到了这种程度的整齐划一便不再是一个城邦了,这是很显然的。因为城邦的本性就是多样化,若以倾向于整齐划一为度,那么家庭将变得比城邦更加一致,而个人又要变得比家庭更加一致,因为作为“一”来说,家庭比城邦为甚,个人比家庭为甚。所以,即使我们能够达到这种一致性也不应当这样去做,因为这正是使城邦毁灭的原因。(《政治学》2.2.1261a16-22;亦参《王制》4.422d1-423b6,5.462a9-b2)

▲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辩论中
整个城邦政体的幸福
再次,他剥夺了武士的幸福,并说立法者应当为整个城邦谋幸福。但是,如果整个城邦的大多数,或所有人,或某些人没有享受到幸福,整个城邦就不可能有幸福可言。在这方面幸福与数目中的偶数原则不同,偶数只能存在于总数中,在总数的各部分中就不存在了。幸福并不是这样。如果武士们无幸福可言,那谁又会幸福呢?当然工匠或其他庶民也不会。有关苏格拉底所倡导的政体的种种疑难我们就举出这些例子,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同样重大的疑难问题我们就不多说了。(《政治学》2.5.1264b15-24)
令人敬佩的人,请你别认为我们必须把眼睛描绘得如此漂亮,以致它们不再像眼睛,其他部分也如此,相反,请你仔细观察我们是否加上了与各个部分相称的颜料,美化了整体。(《王制》卷4,420d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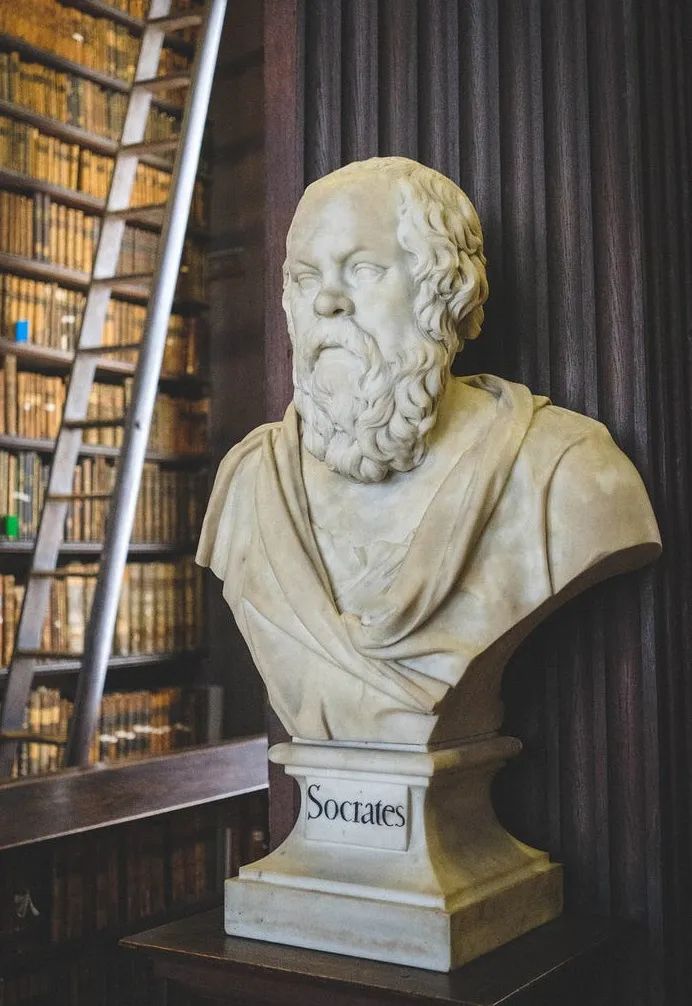
▲ 苏格拉底
哲人王
那些对每一存在的事物缺乏认识的人和瞎子难道有什么区别,他们在自己的灵魂中并没有清晰可见的模式,不能像画家那样看到最真实的物体,一贯能在那里得到参考,并且能以最大的精确度观察它,正因这样,他们不能在这里确立关于什么是美、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高尚的标准,如果它们必须得到确立,即使确立了,他们也不能看守好它们。(6.484c7-d3)
你们每一个人必须轮流下去和其余的那些人住到一起,必须使自己习惯于观察那些朦胧不清的东西。因为,一经习惯,你们就会远远比那里的人们看得更清楚,并且会知道那里的各种图像是什么、代表什么,因为你们看到过优秀的东西、正义的东西和美好的东西的真正面目。(7.520c)
苏格拉底认为理想城邦自身可能存在于这种形式的领域之中:
太空中也许屹立着一个典范,它为某个想看到它、看到它后又想让自己定居于此的人而存在。(9.592b)

亚里士多德可能对此无动于衷。按亚里士多德关于善的形式的哲学知识,即使果真如此,也不会在任何领域产生什么专门知识:
所有的科学都在追求某种善,并对其不足之处加以充实,而把善自身摆在一边。由于它的帮助是如此微不足道,也就无怪技术家们对它全然无知,而不去寻求善自身了。谁也说不清,知道了这个善自身,对一位织工,对一个木匠的技术有什么帮助;或者一旦树立了善的理念,一位将军将如何成为更好的将军,一个医生如何成为更好的医生。(《尼各马可伦理学》1.6.1096b31-1097a11)
编者简介
程志敏,哲学博士,洪堡学者,海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古典政治哲学、法哲学和古希腊政治思想等。迄今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著作20余部(包括专著、译著和编著),主要有《宫墙之门——柏拉图政治哲学发凡》《荷马史诗导读》《历史中的修辞》等。主编“古希腊礼法研究”“阿尔法拉比集”等丛书数种。
崔嵬,哲学博士,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领域为古希腊政治哲学、比较古典学,著述多种。
▼
延伸阅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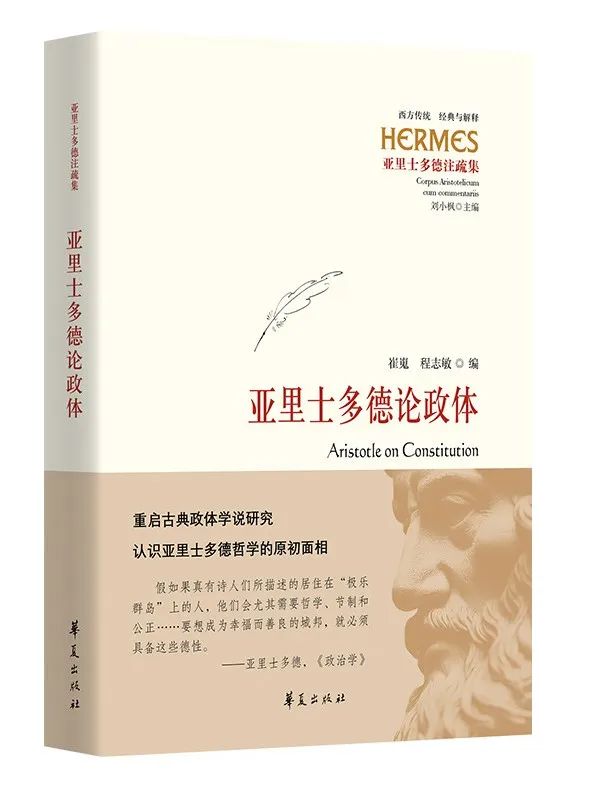

(编辑:刘若辰)
关注我们

插图来自网络,与文章作者无关。
如有涉及版权问题,敬请联系本公众号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