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马史诗的道德本质
编 者 按
本文试图对阿德金斯(A. W. H. Adkins)就荷马史诗中的人物语言及行为所蕴含的道德本质所提出的观点,尤其是对他在《功绩与责任:古希腊价值研究》一书前五章阐述的观点,做出适当评价。虽然阿德金斯对荷马史诗的处理,在许多方面都遭到了严厉批评;但是,关于荷马史诗的道德系统,至今尚未出现其它足以取而代之的论述。因此,过了二十多年,阿德金斯的《功绩与责任》仍然是所有对该问题进行严肃研究的学者必须熟悉的参考资料。
本文力图阐释构成阿德金斯立场的某些重要论述,并考察它们如何继续产生实际的效果。我认为,这项努力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自1960年以来,阿德金斯事实上始终如一地全面坚守自己的立场。他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他在《功绩与责任》中所持的观点做了详尽的阐释和补充;对于那些批评者,阿德金斯似乎没有做出任何明显的让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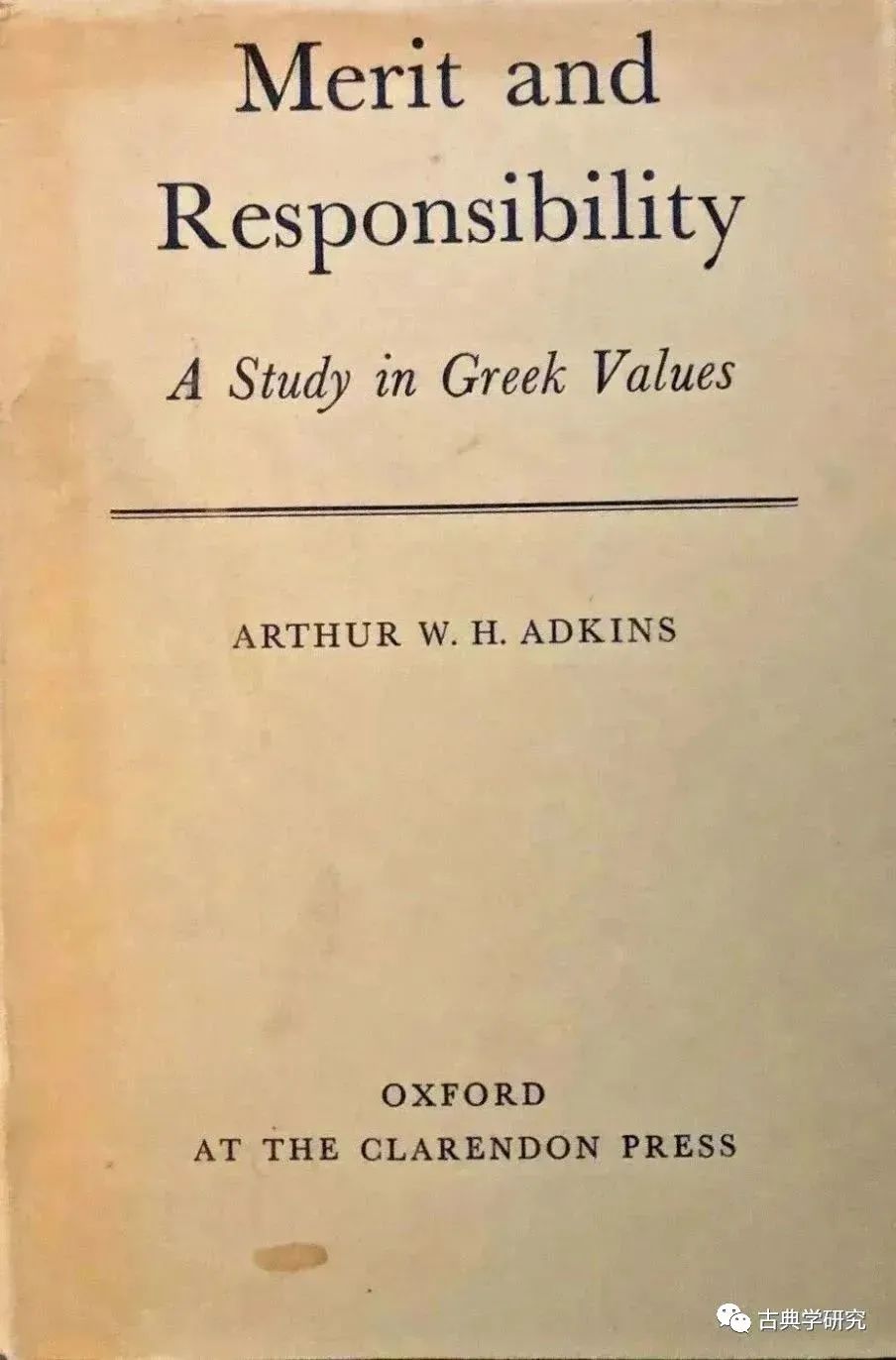
▲ 《功绩与责任:古希腊价值研究》
Oxford: Clarendon Press,1960
本文的主要篇幅都将围绕隆恩(A. A. Long)针对阿德金斯的著作撰写的那篇重要评论展开。隆恩的评论刊登于1970年的《希腊研究》。在所有的相关评论中,这篇评论文章对阿德金斯的观点分析得最全面、最透彻,并且提出了许多至关重要的观点,尽管在我看来,这些观点在某些关键方面还没有切中要害。以下我将首先概述多兹(E. R. Dodds)在其经典著作《希腊人与非理性》中对荷马史诗的道德观的论述——显然,多兹为阿德金斯的阐释提供了依据,并引入了一些基本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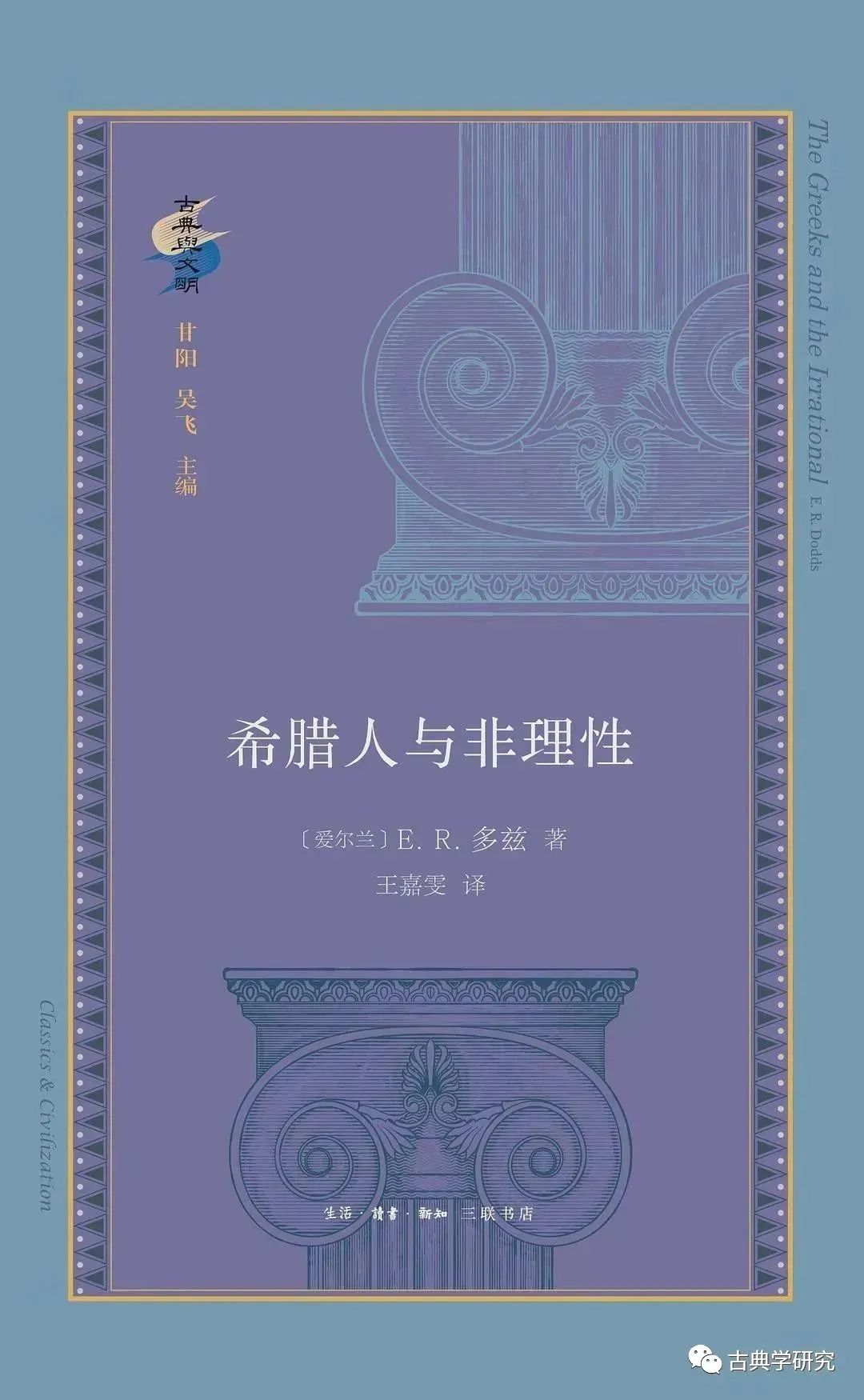
▲ 《希腊人与非理性》,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2
接着,我将全面描述阿德金斯的一些基本观点——这些观点主要引自《功绩与责任》一书。为此,本文将同时引述隆恩那篇评论文,以及阿德金斯紧随其后在同一杂志上就有关问题发表的反驳文章。然后,我试图对他们之间的问题作出裁定,并提出一些更深入的观点——其中既有别人的,也有我自己的,视具体情形而论。最终结果将证实,阿德金斯的整个阐释的核心部分是可取的,同时也将暗示:其余部分中有的尚需进一步证明,有的则有必要完全摒弃。
我们知道,多兹在其论著中把荷马时代的社会,亦即“荷马史诗中描绘的那个社会”,概括为一种“耻感文化”(shame-culture):
荷马史诗中的凡人崇尚的至善,不是对良知的安宁而是对荣誉(tīmē)的渴望,即赢得公众的敬重:“我为什么要征战?”阿基琉斯曾经这样质问道,“如果骁勇善战的勇士得到的荣誉,还不如那些糟糕的战士多。”荷马史诗中的凡人知道:最强大的道德力量不是敬畏神明,而是公众意见的向背。赫克托尔在命运攸关的危急关头说道:羞耻:(aidōs):αἰδέομαι Τρῶας。随后凛然赴死。(《希腊人与非理性》,页17-18)

古希腊社会晚期的某个时候,出现了一种现象——良知的“内在化” (internalizing)。直至世俗的律令开始认识到动机的重要性之后很久,这种现象才逐渐普遍化。从神秘的巫术领域至道德领域,“纯洁”(purity)这一概念的演变,同样也是古希腊社会后期才开始的。直到公元五世纪末,我们才见到这样明确无误地表达:仅仅双手干净还不够——心灵也必须干净。(《希腊人与非理性》,页37)
于是,我们在此看到的就是这样一种社会形态:这个社会总是把最高荣誉赐予那些能够成功地表现出一个战士必须具备的种种素质的男人……这些男人必须拿出勇气去保护依靠他们的人,无论战争期间还是和平时期,他们都必须成功,因为一旦他们失败,就会遭受最严厉的斥责。(《功绩与责任》,页34)
由此可见,成功至关重要——重要的是结果而非意图,所以仅有良好的意图根本不够:“……意图远不及结果重要。荷马史诗里的勇士不能仅凭自己的主张行动,因为他的自我只具有他人赋予的那种价值。”(《功绩与责任》,页49)勇士如果战败,他会感到羞耻(aidōs),并遭受耻辱(elencheie)。人们会因此谴责他。故此可以说,荷马时代的文化既是一种“耻感文化”,也是一种“结果文化”(results-culture)。(在《希腊人与非理性》一书中,多兹没有将“结果文化”与“耻感文化”加以区分,但也许他隐晦地使用了这两个概念[或参阅《希腊人与非理性》,页37])
如今尽人皆知的是,荷马史诗中有两种“卓越”(excellences)类型,即“竞争的” (competitive)卓越与“合作的”(cooperative)卓越或“安宁的”(quiet)卓越之间的差异。根据这种分类,阿德金斯发展了自己的看法。由于社会需要积极有效地预防敌对世界的出现,这势必导致前者即“竞争的”卓越,比起后者即“合作的”卓越,地位更优越;因为“就当时的情况而言,社会群体的安全感很大程度上不是维系于合作的卓越”(《功绩与责任》,页36),而是显著地仰仗于“竞争的卓越”。

虽然,“过错行为不会得到其受害者的推崇,‘安宁’的品质作为正义的表现,也不会像战斗技能和勇气那样,会得到整个社会的高度赞赏——其中原因显而易见:社会更需要战斗技能和勇气,而不是安宁的品质”(《功绩与责任》,页55)。
故此,即使在《奥德赛》中,众神支持正义行为之说也是值得商榷。要是我没有理解错的话,阿德金斯指出,神明倾向于维护道德关系这一观点,总体适用于《奥德赛》的后半部分;但这并不代表诸神的倾向一贯如此(《功绩与责任》,页65)。
他坚持认为,如果两部史诗体现的都是公正最终获胜,
这种胜利也不是源于公正本身。阿基琉斯(Achilles)之所以得到神助,得到宙斯的特别关照,仅仅因为母亲忒提斯(Thetis)的缘故;奥德修斯一直有雅典娜相助,也不过由于雅典娜是他的守护女神——至于个中原委,连荷马也没有言明。(《功绩与责任》,页62)
退一步讲,即便从某种意义上,神明确实在维护某些情形下的道德行为,那么无论如何,他们这种道德裁断显然不具效力,因为根据我们的平常经验,那些不义者往往总能躲过任何惩罚。由此,阿德金斯得出如下结论:“这种想要将更安宁的品质与美德挂上钩的企图,注定达不到目的。”(《功绩与责任》,页70)不管是在《奥德赛》还是在《伊利亚特》中,诸神都与凡人无异,两者主要关心的,始终都是他们渴望的荣誉。


▲ 阿基琉斯之怒, Giovanni Battista Tiepolo 绘
为此,我们首先要考虑这样一个价值体系,它的基础是荣誉和耻辱这两个概念,它主要关心的是个人的地位和力量。
阿德金斯认为,在史诗中,家族的不安全是驱使勇士采取行动的原动力这个说法,表现得并不明朗。毕竟,史诗再三强调了希腊人离家已长达十年之久这一事实,而且,有些时候他们还有可能遭遇灭顶之灾。因此,维护某某的利益只是硬币的一面,硬币的另一面则是:勇士们也需要采取积极行动,以维护和增加自己的荣誉。这就假定性地解释了希腊军队大批驻扎特洛伊的原因:那些死去的人,奥德修斯不无嘲讽地说,也是“为了阿特柔斯之子”。由于担心遭遇死亡的厄运,特洛亚一方的潘达罗斯(Pandarus)抱怨说,他率领自己的部族到特洛亚作战,只为了“讨神样的赫克托尔的欢心”,于己则毫无裨益(《伊利亚特》卷5行211)。
阿德金斯的观点遭到严厉抨击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他关于“竞争的”卓越与“合作的”卓越或“安宁的”卓越的划分。葛瑞德(J. L. Greed)指出,作为“竞争的”卓越的对立面,“合作的”和“安宁的”卓越暗示了完全不同的东西。
“安宁的品质”这种表达暗含了人们在和平时期的素质,与战争时期人的攻击性素质相对照;另一方面,“合作的”和“竞争的”两者之间的对照,这暗示的是,只顾追求自身利益和将集体利益置于自身利益之上两种人的区分。然后,葛瑞德继续写道,与“安宁的”素质相去甚远的军事力量和勇气,属于或者可能属于非同寻常的“合作”素质——两者“都可以既依赖于合作的自愿,又依赖于战斗的能力”。然而,被视为“安宁的”品质节制(sōphrosunē)则不必是“合作的”;“正义”是“合作的”,却可能又并非是“安宁的”;因为它虽然帮助某人的朋友,但同时也意味着伤害某人的敌人。
最后,葛瑞德得出如下结论:毫无疑问,阿德金斯区分“竞争的”卓越与“合作的”卓越的关键所在,正是“合作的”和“竞争的”品质之间的相互冲突——也就是,按葛瑞德自己的话说,一方面的利己卓越与另一方面的利他卓越之间的相互冲突。

但是很清楚,如果这的确就是阿德金斯划分上述两类“卓越”的基点,那么,倘若没有重要的限制条件作为支撑,他就不能得出竞争卓越最终胜过合作卓越的结论;因为竞争卓越自身含有有极为强大的利他因素,它既要捍卫某人自身的财产、地位以及亲属的利益,同时又要保护诸如朋友、外乡人、乞丐和求助者等其他人的利益——这些人以某种方式附属于他的利益群体,但其利益并不直接被认同为其自身的利益。
由此可见,“竞争的”和“合作的”(“安宁的”)卓越之间的差异,不能简单地被视为“利己的”和“利他的”卓越之间的差异。隆恩看到了这两种划分之间的差异:“竞争的”卓越必定依赖结果作判断,而“合作的”卓越依据的则是“与之不同的评判标准,譬如公平”。
如果像通常那样,勇敢和高尚分别被用于描述和评价战争时期与和平时期一个勇士的成功,那么,大多数平常可能被称为“合作的”行为,虽然可能不必是“安宁的”——正如阿德金斯的界定,也可以被证明属于“竞争的”这一范畴。友好地对待宾客、供奉神明、帮助战争中的同伴、举行饮宴——也许这些都是荷马史诗中的凡人们“为了共同目标而团结合作”的最明显的例证(《荷马史诗的道德与价值》,页123)。
这并不意味着,偶尔的“公正处理”在荷马史诗中就不受重视。其实在某些具体情形里,“公正处理”也得到了高度称赞,以至于也要求勇士们善于那样做。按照更荷马式的表达,不仅一些合作事业涉及到价值取向,而且个体的技能表现和勇士自身的地位也涉及到价值取向。(同上)
隆恩举例示之:《伊利亚特》第17卷中,格劳科斯(Glaucus)因赫克托尔没有救下萨尔佩冬(Sarpedon)的尸体而责备赫克托尔;《伊利亚特》第5卷中,萨尔佩冬也因类似问题责备赫克托尔;《伊利亚特》第13卷中,高傲的德伊福波斯(Deiphobus)凭借与埃涅阿斯(Aeneas)的亲戚关系,恳求他帮忙助阵。赫克托尔和埃涅阿斯分别在不同的情形下被激发而采取的行动,隆恩认为,虽然被看作是为了荣誉,然而本质上却都是合作性的行为:“一个人自身的地位和处境要求某些类型的合作行为。”隆恩将这部分情形总结如下:
就荷马史诗而言,阿德金斯关于竞争的和合作的价值的区分,其实不是两种判断的绝对划分,而是那些称赞成功、贬低失败的强大词汇,和评价一种不同类别的结果而非意图的相对弱小的词汇之间的区分。由此可见,这种区分多么虚弱无力。然而,在这两种情形下,一种行为是被裁定为成功还是失败,则可能要考虑到人际关系的或合作性的行为。(《荷马史诗的道德与价值》,页126)
另一方面,阿德金斯认为,也存在需要考虑意图的情形:在这类情形里,人们不关心“集体的安全”。“竞争的行为和合作的行为之间的差异,不在于要求某人在可能的情状下应当有所行动(如果这种行动在当时环境下对他是最强有力的要求),而是在于,自愿接受此人为其不可能行动所提出的理由。”倘若我对阿德金斯这种回答的阐释恰如其分的话,那么,换句话说,作为“竞争的”卓越的对立面,“合作的”卓越在严格的意义上,就应该“包括与集体之外的那些人的合作。”

▲ 阿基琉斯与阿伽门农, Gottlieb Schick 绘
总的说来,不管是更大还是更小的集体内部的忠诚的观念,在《伊利亚特》中都具有某种重要作用。这一点,琼斯在其对该史诗之情节所作的广为称道的分析里阐述得很清楚。这部史诗里有一处关键情节:阿伽门农侮辱了阿基琉斯,阿基琉斯对此耿耿于怀,不甘心就此屈服,更不愿用友谊和忠诚消弭这样的侮辱。然而,大家都希望阿基琉斯能平息愤怒,至少当阿伽门农提供与之相当的(实际上更多的)补偿时,阿基琉斯也应该“同情”(pitying)其他希腊人,与余下的这些人并肩作战。
当得知帕特罗克洛斯(Patroclus)已死,阿基琉斯再也没有继续活下去的愿望,除非去找杀人者复仇。他的这一反应,常常被认为是野蛮人的行径。赫克托尔不是在私人争斗中,而是在战场上杀死了帕特罗克洛斯。帕特罗克洛斯之死使阿基琉斯深感内疚,此时,他突然萌发了一种想要平息这种内疚的强烈冲动。他认为自己毫无用处,因为他没能救助帕特罗克洛斯,没能救助他的任何一个死于神样的赫克托尔剑下的朋友——这里,阿基琉斯至少承认他同情那些阿开奥斯人(Achaeans)。但是,尽管在战场上他威猛无比,所向披靡,而今却只能徒然坐在战船前,成为大地的负担。然而,驱策他去杀死赫克托尔的唯一理由,倒不是这种情绪。因为,如果向杀人者复了仇,帕特罗克洛斯就会得到伟大的荣誉……阿基琉斯[也]提到这种荣耀,现在赢得它的时机已到;但是这一荣耀只是附带。阿基琉斯最终牺牲性命却不为此,而是出于他对帕特罗克洛斯之死的自责和懊悔。在荷马的世界里,对朋友的忠诚,一如对集体的忠诚,并非毫无意义;我想,对朋友的忠诚可以被视为一种合作的品质。(《宙斯的正义》,页21-22)
由此出现的大致图景,已不是两套义务之间的简单区分——即强大且压倒一切的那一面与弱小而通常处于从属地位的另一面之间的区分,而是这位勇士受到的一连串复杂而纷繁的压力,他有时很难在其中做出选择。勇士总是处于各种社会关系构成的巢窠中心,而这些社会关系向他提出的要求很可能相互冲突。阿德金斯认为,这些关系之间大致存在某种可以称之为“啄食顺序”(pecking-order)的规则。

▲ 阿基琉斯与帕特罗克洛斯(古希腊陶画)
有人认为,勇士面临的选择好像是既定的。这种看法不对,我认为,这种看法对荷马,尤其是对作为《伊利亚特》之作者的荷马,简直就是一种损害,因为围绕这些选择所引发的紧张冲突,恰恰是作为整体的《伊利亚特》这部史诗的核心情节。
我想,上述分析的结论必然是:阿德金斯关于“竞争的”卓越与“合作的”卓越的区分,最终并不可行。但与此同时,他也留下一些值得我们深思的东西。正如我们一开始就看到的,这种划分的根据是:荷马时代的社会本质上属于一种“耻感文化”这一论断。荷马时代的勇士主要关注的是自己的“能力、力量或权力”,这种关注将他们置于同别人的竞争关系之中,即使在他与别人合作时亦是如此。再则,勇士行动的主要动机也仅限于维护诸如狭义上的荣誉、财产和家庭之类的一己之利——就此而言,他们的行动更具竞争性。合作行为或许能为他们提供一条增加荣誉的途径,这种荣誉的物质表现形式就是财富;一旦这样的功能不再发挥作用,勇士们就很容易退却。
另一方面,阿德金斯指出,“社会”是否赞同那样的勇士行为则是另外一回事。这里的问题有赖于我们怎样理解“社会”这一概念。如果从家族的角度理解——阿德金斯似乎也这么理解;那么,“社会”确实赞同勇士行为(按阿德金斯的分析,勇士顺应社会要求而行动)。但是广义的社会,作为相似个体之总和的社会,其实际态度则要复杂得多。既然每一个人都倾向于采取同样的行为方式以捍卫自身利益,这样的行为便会构成规范。然而事情并未到此为止。
荷马的道德观也认定如下事实:个体若要维护自己的荣誉,就不可避免地会经常严重地影响到其他人的利益,比方说,会威胁到他人在共同体中的荣誉份额)。这种冲突可能以暴力方式得到解决,但是在正常的仲裁程序里,毫无疑问也存在某些可行的、相对和平的手段,这就为个体之间的正义观留下了广阔的空间。但是按照阿德金斯的逻辑,我们通常也相信,勇士在采取行动时,除了考虑他自己的权利和利益,也会考虑他人的权利和利益;然而,这样的信念在荷马史诗描述的那些伟大人物的实际行为中,很少得到体现。下面,我希望自己能对这一情况作出具体的解释。
在这一部分里,我将首先提到欧文(Terence Irwin)在其所著《柏拉图的道德理论》(Plato’s Moral Theory)中的隐晦批评。阿德金斯倾向于认为,用以描述一位英雄的概念agathos(好的)绝对暗含着如下意思:这位英雄具备时时与这一概念相关的全部素质。所以,他在《功绩与责任》的第31页写道:agathos,aretē以及与之相关的其它词语,“作为称赞勇士的最有力的用语,暗示了任何一个受到如此赞誉的人拥有的所有素质,在任何时候都受到希腊社会的高度推崇”。可这种看法显然不对。阿伽门农侮辱阿基琉斯实属不明智之举,然而事实表明,鉴于阿伽门农的统帅地位和军事力量,对此荷马也竭力再三强调,他的行为依然是好的,帕里斯(Paris)的行为也是好的,尽管他认识到了,作为战士自己身上存在着弱点;涅斯托尔(Nestor)是一位了不起的顾问,但在徒手战斗中却不占优势。
这也正是我们期望的情形。如果所有的好行为(agathoi)都如出一辙,《伊利亚特》就不会有任何特色,也就谈不上有跌宕的情节。
在第1卷里,如阿德金斯所言,阿基琉斯不可能屈从于阿伽门农,因为,一旦他屈从,就可能被看作(阿德金斯告诉我们,此处“看作”一词“在耻感文化里就相当于‘是’”)怯懦和无能。
但当史诗情节发展到第九卷时,情形就彻底变了:阿伽门农提供给阿基琉斯丰厚的补偿,此时,即使阿基琉斯做出让步——或用不太感情化的方式表述,即使他与阿伽门农“达成和解”,那也不会比第15卷里波塞冬屈从于宙斯的行为更耻辱:阿基琉斯可以将自己的战斗才能置于阿伽门农指挥之下,从而较为含蓄地承认阿伽门农的权威;毕竟,与阿基琉斯相比,阿伽门农的地位确实更优越——正如阿伽门农自己所言(《伊利亚特》第9卷第160-161行),他“更有国王的仪容”,而且更年长,尽管奥德修斯在规劝阿基琉斯时以外交辞令淡薄了这一点。
纵使阿基琉斯凭着自己是骁勇的战士和天神的后裔,拥有显赫的地位,但阿伽门农仍然比他更强大、“更优越”或“更好”(至少涅斯托尔这么认为[《伊利亚特》卷1行280-281]),“因为他统治着为数众多的人”。同样,由于比波塞冬年长,宙斯也比波塞冬更优越,这一点波塞冬最终也还是承认了。
确切地说,《伊利亚特》自第9卷起,重在叙述阿基琉斯,一位疯狂地关心自身荣誉,最终又因这种过分关心而感受到重重压力的勇士。
如果说德高者心地慈和,那么,就阿基琉斯证明自己绝不屈服的程度而言,他已经不再真诚(esthlos)、善良(agathos),尽管他还不能被绝对地剥去善的(agathos)这一称谓,因为他满足了美德的其它标准。诗人在《奥德赛》中设置了类似于此的求婚人的情节:从某一方面看来,这些求婚人都是好人(agathoi);然而在其他方面,他们又绝不是好人。

▲ 阿基琉斯的凯旋,Franz Matsch绘
隆恩从截然不同的角度审视这些问题。他极力声称,一般而言,agathos(好的)(或aristos)一词既具有描述力量又具有评价力量;描述力量主要指向社会地位。他认为,这就是该词被用来指称那些求婚人的用法。同样,在《伊利亚特》第1卷中,涅斯托尔对阿伽门农说:“你虽然显贵,也不要去夺取他的少妇。”此外,在第24卷里,阿波罗认为,神明们应该谴责阿基琉斯凌辱赫克托尔尸首的行为,“尽管他是好人”。
隆恩认为,后两例暗示了:就算地位卓越,勇士能够采取的行为也该有限度;agathos(好的)一词在这样的语境里不太具有道德方面的意义和内容。阿德金斯却认为,这些例子只在声明勇士的主张。就此而言,隆恩对他的批评可能非常中肯。此外,这些例子也暗含了阿伽门农和阿基琉斯的行为过分这一判断(隆恩语);在任何一个例子里,与阿德金斯一样,我都看不到有什么理由认为,这种判断无效因而也不具有力量。阿伽门农和阿基琉斯都不可能被感动,这是事实;但暗示的是他们应该被感动。我们不必走得隆恩那么远,从主要是描述的意义上去解读这些语境或求婚人语境中的agathos这一概念。涅斯托尔和阿波罗言及的行为,肯定属于正常情形中的行为。在那样的情形里,你还有绝对的权利做你想做之事——因为你就是你;但在这些情形里则不行。

▲ 阿基琉斯将布里塞伊斯让给阿伽门农(庞贝壁画)
在《伊利亚特》描述的一般战斗里,有许多这样的例子:勇士以一种我们所鄙弃的方式惩罚仇敌。比如奥伊琉斯(Oileus)之子埃阿斯,他割下英布里奥斯(Imbrius)的头颅,把它像圆球似地抛过人群,任它在尘埃里滚来滚去。然而,这一极不寻常的残忍片断诗人似乎没有注意到。赫克托尔不能被这样对待,因为他拥有自己的荣誉,即使这样的荣誉还不能与阿基琉斯相比。赫克托尔是给阿基琉斯个人造成巨大伤害的仇敌,因此我们不能指望阿基琉斯本人会认识到,他对待赫克托尔的尸首采取的行为有多么残忍;作出那种判断是天神的事情。
上述例子暗示了如下观点:勇士不应当在任何情形下都绝对地主张自己的权利。我们也许有理由这样来推断:如果他一定坚持这样做,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他对美德的主张。所以,按我的理解,以下情节都是对上述观点很明显的暗示:阿波罗指出,如果阿基琉斯继续恣意侮辱赫克托尔的尸体,这并不高尚(οὐ κάλλιον)(《伊利亚特》卷24行52);阿伽门农当意识到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时没有让步,或仅仅是很晚才做出让步;而阿基琉斯也是在史诗结束时的第24卷才最终克制了自己的愤怒。
“遵从限制”(observance of limits)是否应该真正成为agathos(好)的“部分含义”(part of the meaning)——我不想这样说;也许对这个问题,我们难以进行有价值的讨论。
我认为,我们必须容许存在如下可能性:在特定的语境里,美德的内涵本身就是一个很值得争议的问题(阿德金斯既然容许这种可能性存在于后史诗时代,为什么就不许它存在于史诗时代呢?)。
而争议的问题之一,正是我们一直在讨论的这种语境,亦即:一个人认为他应该做的,往往背离了别人希望他做的。正因如此,有人指责阿德金斯,说他的阐释依据了一种过于僵化的“词汇分析法”。这种指责不无道理。他采用的那种分析法是一种凭借词典来界定概念的作法;而且,这种界定严格地限制了概念的意义覆盖面。正是通过这种方法,阿德金斯假定,荷马史诗中使用的agathos一词对应一种固定不变的含义。换句话说,这就要求删除那些似乎扩展或修改了这一假定的基本含义的诗句,使说话人相信可以“按自己的意愿随意改变荷马的价值术语的标准用法”(《功绩与责任》,页38)。
然而,要是语言使用者自己都对其持争议态度,我们又如何断定,哪些可以被视作“基本的”含义,哪些又不可以呢?通常,道德语言也许无力用阿德金斯建议的那种方式来予以限定(然而这并不是说,我们仍然不能认同一种某些说话人惯于依循的核心内涵;总体而言,阿德金斯还是恰当地确定了荷马史诗中agathos(善)和aretē(美德)两个概念的核心内涵)。
隆恩在其评论文章的最后,就是按照这条思路反驳阿德金斯,并大体上取得了成功。阿德金斯认为,不同于其它术语——比如aischros(可耻的)——aeikēs和 aidōs(羞耻)都“同时包含了合作的和竞争的卓越”(《功绩与责任》,页43)。然而,隆恩却在aeikēs 与aischos 和aischros 之间建立起紧密联系,并且令人信服地证明:这些术语(包括其它价值术语)也可以用来谴责那些竞争中的失败和超出人们接受范围的英雄行为。

▲ 奥德修斯射杀求婚者,Thomas Degeorge 绘
隆恩作为论据引用的另一个例子出自《奥德赛》卷1行228-229:雅典娜评价求婚人的行为是,“任何正派人遇见他们,眼见这种种恶行,定都会满腔气愤”。阿德金斯认为地处感到耻辱(aischea)的应该是特勒马科斯,而不是那些求婚人。他说:“是特勒马科斯,而不是求婚人,应该感到羞耻,因为他的处境是可耻的(aischron)。”(《功绩与责任》,页42)
但正如隆恩所言,这种解释缺乏相应的依据,因为它超出了适合阿德金斯关于aischos和aischros这两个概念发挥作用之途径的总体观点,即它们专用于指称勇士的失败。持阿德金斯这一观点的人甚少。求婚人这一情节的整个语境实际上暗示了:是求婚人而不是特勒马科斯该遭受谴责。这种看法对于阿德金斯的重要论证,简直就是致命的一击。因为阿德金斯的论证必然要求,荷马本人确实认识到了,个人的行为要受到某些限制;用阿德金斯自己的话来说,如果出现了需要打破这些限制的情形,就存在谴责打破被限制的这些行为的有效手段。
在《奥德赛》中,求婚人消耗奥德修斯家财的行为,遭到诸神和凡人的一致谴责。但必须承认,这些谴责求婚人的凡人(奥德修斯、特勒马科斯、佩涅洛佩和欧迈奥斯)都是当事人;可我们有雅典娜的权威做支撑,任何有判断力的观察者也都会赞同对奥德修斯等人的谴责。我们也许同样认为,神明只是表面上谴责求婚人;尽管阿德金斯指出,神对人的道德裁判是新近出现的理解荷马史诗的一种途径,但他对此没有提供任何依据。
无论如何,我都不愿意支持那种将《奥德赛》简单地归为所谓“正义之诗”的观点;因为,荷马并非是赫西俄德式的道德劝谕者。借助诸多暗示,也许荷马确实是在推崇某些价值,但那不是他的主旨。《奥德赛》中也没有简单的道德倾向。

在《伊利亚特》中,阿基琉斯无疑完全有理由对阿伽门农的侮辱心存怨恨。这些关键情形,无不暗示了勇士通常也应尊重他人的要求;尽管这种观点的适用范围有清楚的限定——就盗窃和偷羊行为也可以被视为完全正当的敛财途径而言。

延伸阅读

● “尽管我们很忧伤,还是把忧伤藏在心中吧” | 阿基琉斯传说中的血气、正义和制怒
(编辑:李舒萌)
关注我们

插图来自网络,与文章作者无关。
如有涉及版权问题,敬请联系本公众号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