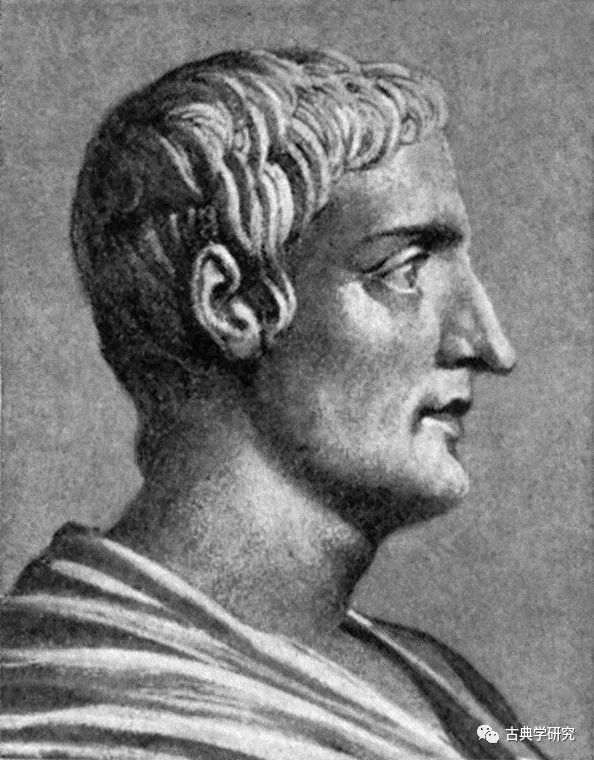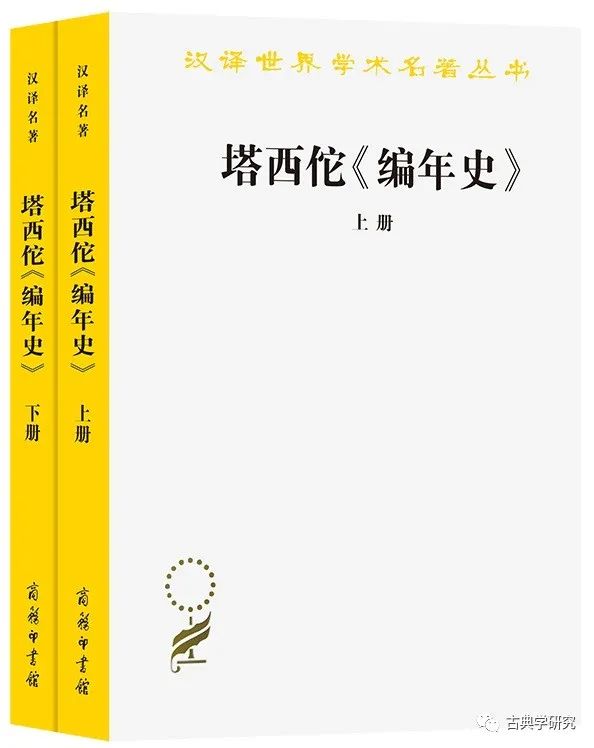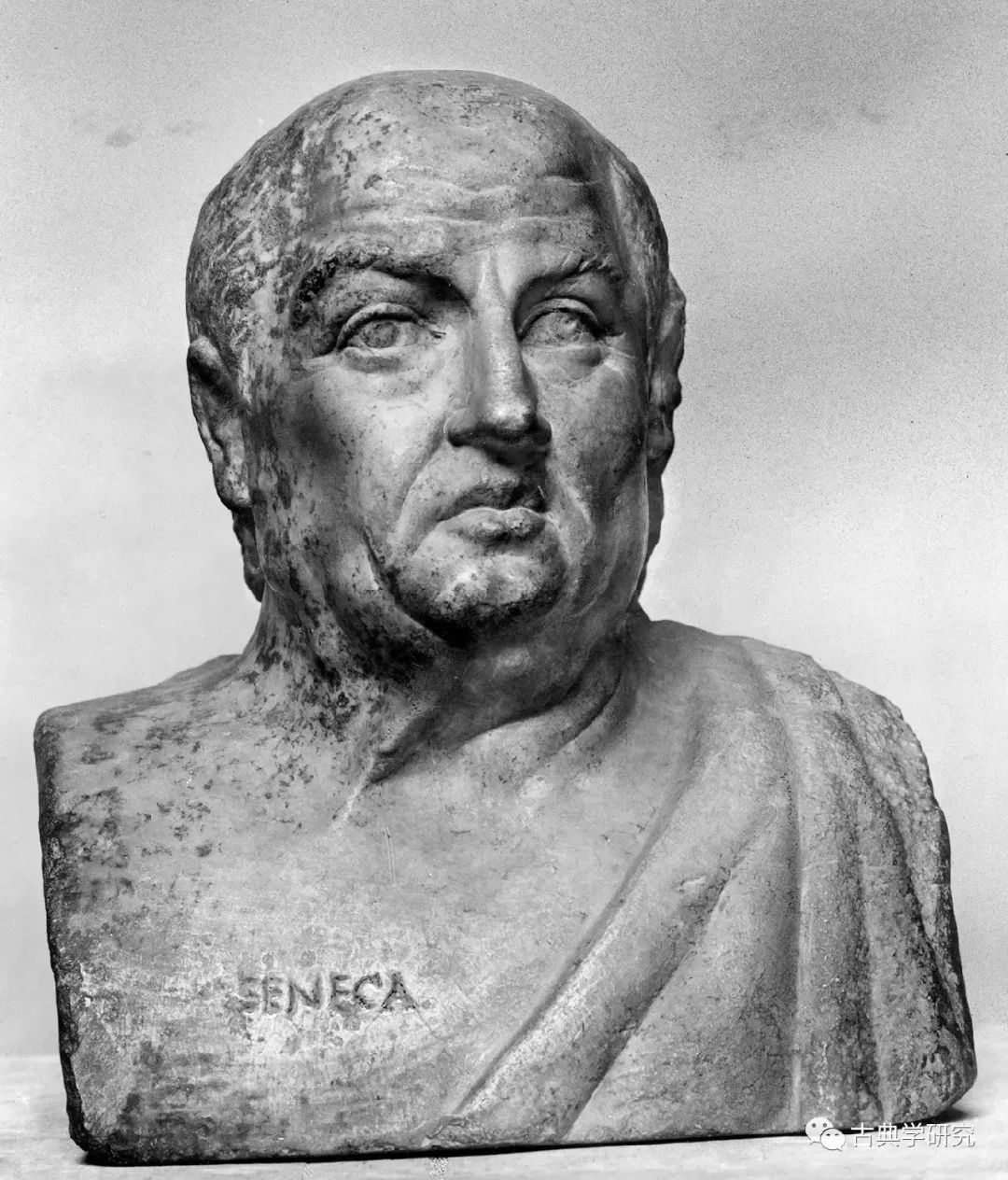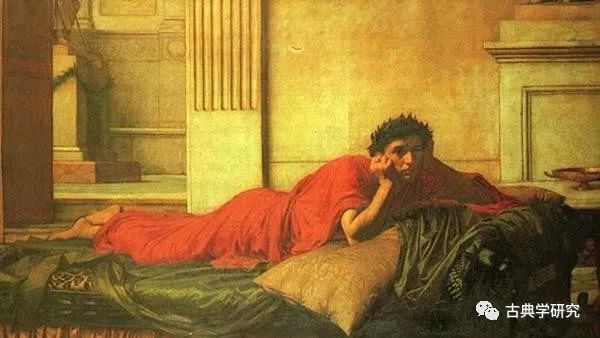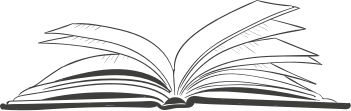1872年,刚入职的大学青年教师尼采,在公众面前扮老并打趣道:让他(泛指如今教古典文学的青年教师)感到快慰的是,他的学生中没有一个人能像我们老一代人一样读他的柏拉图、他的塔西佗。(《论我们教育机构的未来》报告三)本着“和而不同”的学人精神,笔者不理会尼采的辛辣嘲讽,却相当好奇两个问题:首先,为何“我们老一代人”让塔西佗紧跟在光辉的柏拉图身边?其次,怎样才叫像“我们老一代人”一样读塔西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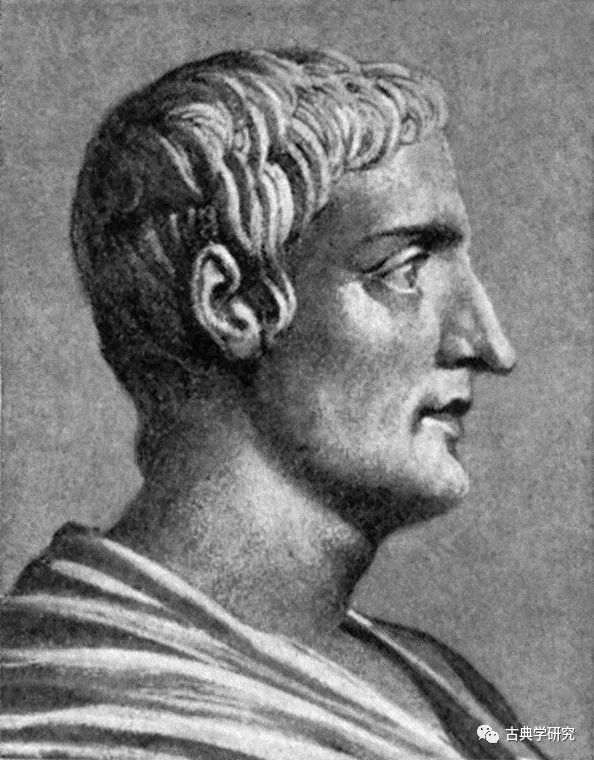
塔西佗生于约56年(东汉光武帝中元元年),逝于约120年(东汉安帝永宁元年),是罗马帝国前期重臣,曾任年度执政官和封疆大吏。诚然,塔西佗生得不算早,没有赶上西方空前绝后的大一统盛世,即罗马开国皇帝奥古斯都在位的三十年(前27-14年),但塔西佗生得也不算晚,熬过“后奥古斯都时代”数场政治风波后,老来赶上罗马“五贤帝”中兴(96-180年),得以寿终正寝,留下五部文史名作,均有力透纸背的中译。他的两部长篇史著《编年史》《历史》连贯地记述了奥古斯都驾崩至五贤帝之前的帝国史,尽管有些篇章今已亡佚。关于塔西佗与柏拉图的关系,塔西佗自己便有两番言论值得玩味(均见《编年史》)。首先,塔西佗称柏拉图(或他笔下的苏格拉底)为“第一有智慧的人”。其次,塔西佗说:
在我们之前的时代,事情确乎不是样样比我们的好;我们自己的时代也产生了不少品德和技艺上的典范可供后人模仿。不论如何,就此而言,但愿我们和古人的种种竞赛,出于正直而永续下去!
在拉丁文原文中,这里的“古人”亦指“更伟大的人”。结合两番言论,可以说塔西佗致力于与柏拉图进行正直而永续的竞赛。用中国古话讲,君子无所争,其争也君子。事实上,塔西佗有此心并不令人意外,毕竟柏拉图素来令西方后世见贤思齐。关键在于,塔西佗是否有这个分量?塔西佗身为帝国大臣,在波谲云诡中历五朝而守分善终,其实际政治经验已经胜过柏拉图。但论思想之高超,则柏拉图远胜塔西佗,此亦不争之事实。况且,一个是史学家,一个是哲学家,在何种意义上形成君子之争?其实,上面引用的塔西佗原话回答了我们的疑问——在不算太好也不算太坏的帝制时代,通过一个个鲜活的历史形象,塔西佗关注“既持重又智慧”这种特定美德如何付诸实践。“既持重又智慧”源自柏拉图《理想国》中的著名主张:最好不过政治权力和对智慧的爱碰巧结合。塔西佗之所以有分量有同柏拉图进行君子之争,是因为当希腊人担心柏拉图这种主张沦为取乱之道时,塔西佗以罗马人的稳健,令这种主张既有益于帝国现实,亦有助于帝国贤人安身立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