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学人|崔嵬:诗术的涵义——亚里士多德《诗术》第一章例释
编 者 按
本文原载《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感谢崔嵬博士授权“古典学研究”公号网络推送。
2019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推出刘小枫的专著《巫阳招魂——亚里士多德〈诗术〉绎读》,此举势必引来学界的争议,因为他正式把亚里士多德的名著《诗学》改译作了《诗术》[1]。早在10年前,华夏出版社在推出阿拉伯思想家阿威罗伊的《〈论诗术〉中篇义疏》之时,刘小枫为该书写了一篇长达18页的中译本前言,就已经表明他要将“学”字改译作“术”字的立场。这篇文字被作者改掉前言格式发表在《中山大学学报》上,后在2015年又收入《比较古典学发凡》一书之中。十年间,刘小枫发表了数篇解读《诗术》的文章,均取自《巫阳招魂》一书。
不过,这些学术动作,应者寥寥,远不如十年来的其他学术活动招人眼目[2]。究其根源在于,这些文字读来太难。实质上,亚里士多德之书本身并非正式出版之作,而极可能是课堂教学提纲[3]。既是提纲,当然需要有人将之补充完整。《巫阳招魂》便是一例,但这个补充的做法并非首创。在1992年,施特劳斯的弟子戴维斯就出版了《哲学之诗——亚里士多德〈诗学〉解诂》一书解读《诗术》全书[4]。然而,无论是戴维斯之书,还是刘小枫之书,即便是学界专业人士,读来仍然不易。《诗术》本身的艰涩既是进一步前进的门槛,也是学术探究的趣味所在。
既然是内部的讲稿,它所针对的学生当然不是普通学生,至少他们具有较好的学问基础,而该讲稿正是针对这些学生来讲的[5]。略有教学经验的老师都会知晓,某个事物若是对于学生们而言太难领悟,那么最好的办法便是举例来帮助学生们理解。亚里士多德显然懂得这个浅显的教学方法,他在《诗术》一书之中频繁征引各式例证来帮助学生们理解关于“诗术”的问题,而学界也早有人发现了这些例证对于理解该书的重要作用[6]。不过,作为学生若想真正理解这部作品,就不应该放弃书中的任一细节例证,以求全面理解老师的意思。这正是本文意图致力解决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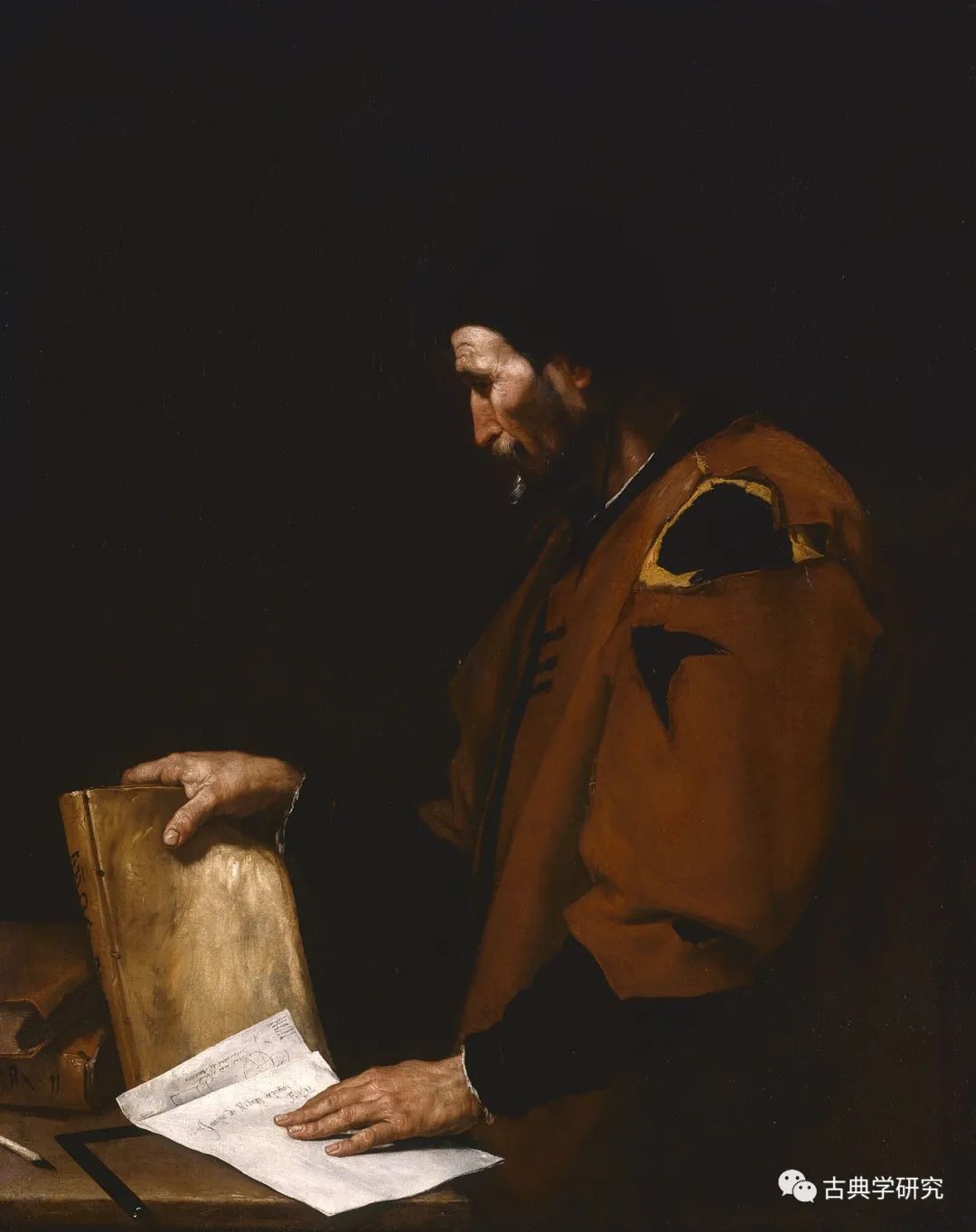
▲ 《亚里士多德》,胡塞佩·德·里贝拉 绘,1637年
一、意涵纷纭的模仿
《诗术》第一章提及的例证有些什么呢?若全部整理则有如下内容:第一组是叙事诗、肃剧、谐剧、酒神颂、双管箫情歌、基塔拉琴合唱诉歌和舞蹈家[7];第二组是索福戎(Sophron)和克塞那耳科斯(Xenarchus)的拟剧、苏格拉底的言辞、荷马、恩培多克勒、卡瑞蒙及《马人》(Centaur)。第一组的例证用以解释何为“模仿”,第二组的例证用于解释何为“诗人”。
模仿是《诗术》的重要概念,也是理解“诗术”的关键。德里达曾言,整个文字解释史均在模仿概念的各式逻辑可能性中盘旋[8]。古典学者哈利维尔(Halliwell)尤其重视论述模仿问题,他在《亚里士多德的〈诗术〉》一书中以专章方式论述了模仿问题[9],又在2002年出版了那本知名的《模仿的美学:古代文本与现代问题》一书[10]。在后一本书中,他归纳了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历史上所形成的两类基本模仿观点,一是认为文学艺术作品模仿了作品之外的物质世界;第二种观点认为艺术作品为自足的异型微宇宙(hetrocosm),它重现了世界,也就复制了我们认知事物的方式。
即便我们有了哈利维尔的对模仿的归纳与总结,但要借此理解亚里士多德的诗术,仍觉困难。或许,我们应该回到古希腊时期的作品之中,还原“模仿”一词的本意,方可知晓亚里士多德使用该词的准确含义。这个方面的研究工作还以哈利维尔为首,另有卢卡斯(D. W. Lucas)的研究颇有助益[11]。在《亚里士多德的〈诗术〉》中,哈里维尔提到了希罗多德、欧里庇得斯、埃斯库洛斯、荷马、阿里斯托芬及毕达哥拉斯的各式文本中,“模仿”一词的使用情况,并将模仿细分作五类:一为形式模仿,以视觉手段重现视觉客体;二为行为仿效;三为戏剧扮演;四为拟声;五为形而上学模仿。前四类简单易懂,唯有第五类略显费解。所谓形而上学模仿即是可感世界与隐秘世界的内在关系,他举毕达哥拉斯的数学为例以作说明:数即是感性世界对至高存在的模仿。哈利维尔费了极大的功夫,意图以模仿的概念带入亚里士多德内在逻辑之中,但效果似乎不太明显;问题仍然存在:亚里士多德《诗术》中的模仿究竟指的是哪一类?抑或可能兼而有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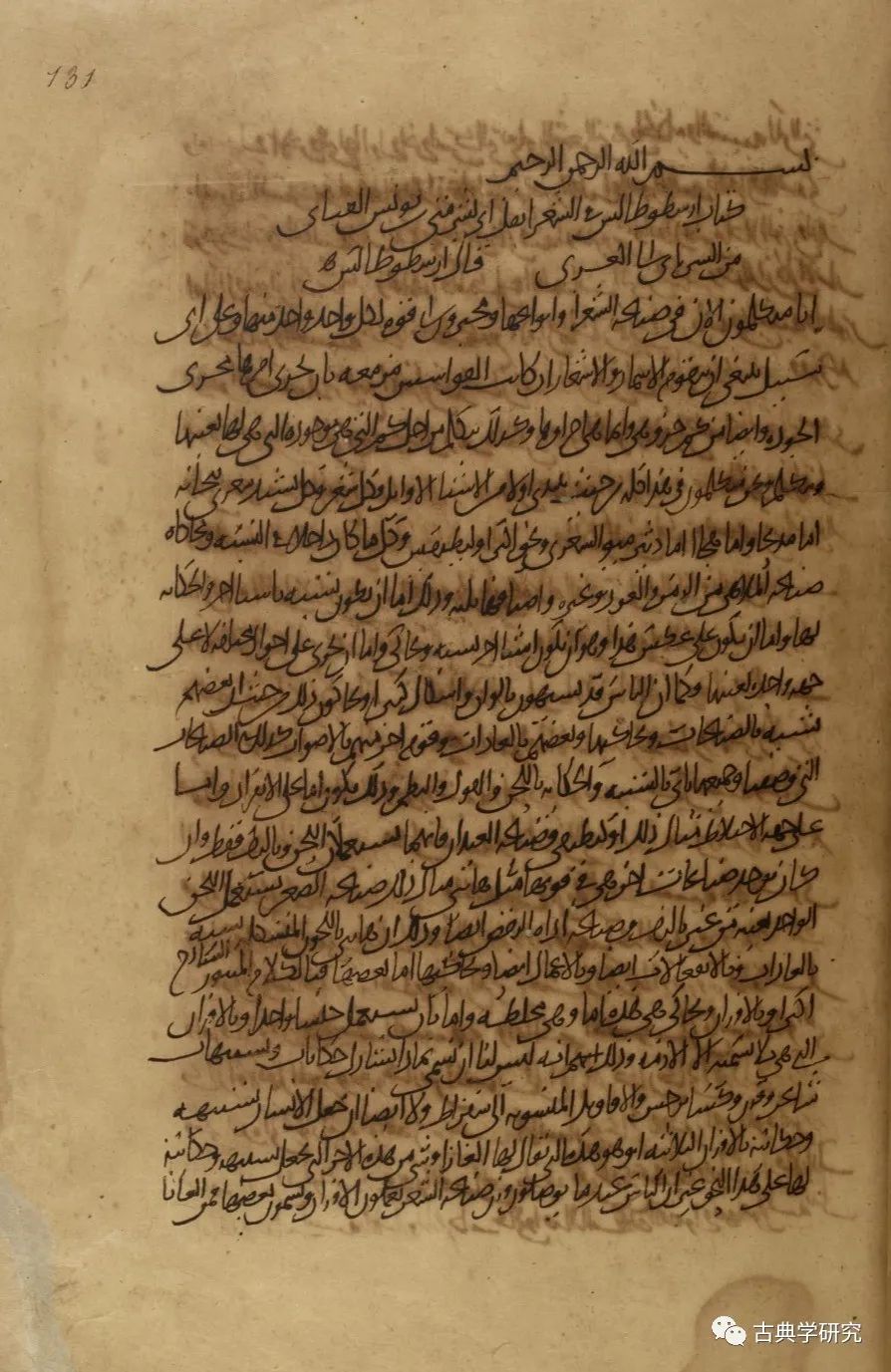
古典学家卢卡斯的工作比哈利维尔更加基础性,他注释了亚里士多德《诗术》全文;国内学者陈中梅所译《诗术》(旧译《诗学》)参考了他的不少注释。他对模仿的分析与哈利维尔大同小异。2006年,犹他大学比较文学助理教授普托尔斯基(Matthen Potolsky)又以《模仿》为题出版了一本文学理论专著,除论述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模仿问题以外,还议及模仿的三种变形及其对现代文学理论的影响[12]。从模仿概念出发进行的现代文学理论式建构始终无法与亚里士多德的文本切合,毕竟无论采用哪种模仿概念,还是采用随语境择机选择模仿的意涵,都无法贯通《诗术》全文。
现代文学理论家不再愿意思考亚里士多德原文的文脉,而是颠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古典论述,以求建立各式新颖的文学理论观念。奥尔巴赫的《摹仿论》堪称此类文章之经典,只是其“摹仿论”同样无助于理解亚里士多德的碎片化写作[13]。不过,该书书名的翻译倒让我们注意到了“摹仿”与“模仿”之间的差异。模仿之义是“学着样子做……”,既指行为,又指成品,而非某种再现;所以,它不同于“摹仿”。摹仿多指物质性的仿制,多用画布、纸张、石头之类实物,而模仿多指照着样子做;若用于诗作中,则与实际的行动有所区别,指虚拟性的行为[14]。学者往往热衷细究《诗术》中的“模仿”究竟是什么意思,它与当时的文化语境究竟有怎样的关系[15]。只是这些解释仍然无法让《诗术》文本变得晓畅易懂。
回到《诗术》首章第一句,我们发现最难理解的并非“模仿”二字,而是他在提及不同文学作品类型之时,采用了不同的表达:
//
叙事诗制作和肃剧制作以及谐剧和酒神颂制作术,还有大部分双管箫情歌术和基塔拉琴合唱诉歌术,所有这些一般来讲都是模仿。[16]
叙事诗、肃剧与酒神均带有“制作”二字,唯有谐剧直接就是模仿。按常识来看,谐剧通过模仿他人的言行引人发笑。在笑声中,我们对“模仿”究竟有怎样的意思会有最直观的体验。我们在模仿中体验到欢乐,是因为我们不仅是理性动物(《尼各马可伦理学》1098a, 1102a-1103a;《政治学》1253a10-15)与政治动物(《政治学》1253a3),我们还是模仿的动物[17]。模仿既描述了人世快乐的源泉,又限定了理性重塑人生的限度——大部分时候,人凭靠模仿而非理性追求快乐的生活。
关于谐剧即模仿的论述,我们可以想到阿里斯托芬的《云》,它模仿青年苏格拉底的哲学研究志趣,既取悦了观众,又反思了哲学研究的弊端,以求实现隐恶扬善的政治哲学目的。阿里斯托芬的笑声抑制了邪恶,而青年苏格拉底之恶在于乐观地相信自然本质的可理解性,进而致力于普遍知识力量的追求,遗忘了人的政治与模仿天性之间的张力[18]。在常人眼中,青年苏格拉底的哲学研究可笑之处,正在于他对于政治生活严肃性的极大漠视。哲学追求在常人眼中,极其可笑,因而具有谐剧的品质。若谐剧即是模仿,而哲学追求又等同于谐剧,那么,哲学追求也就等同于模仿;哲学生活同样是人的模仿行动,而非理性本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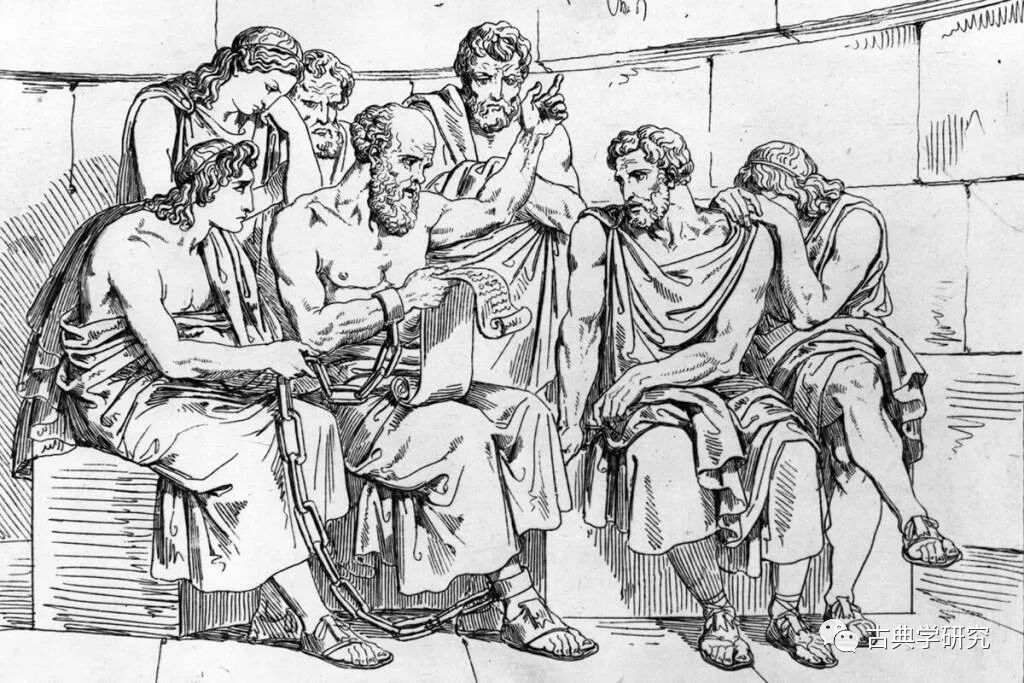
亚里士多德说叙事诗制作、肃剧制作同样是模仿,而非叙事诗或肃剧本身是模仿,这已经挑明亚里士多德所言模仿,绝非论述某种文学再现现实的理论;它要突显的是叙事诗“制作”与肃剧“制作”是模仿;从某种意义上讲,叙事诗制作、肃剧制作等于模仿,而模仿等于谐剧,那么叙事诗制作、肃剧制作这个行为本身就具有谐剧的品质了——叙事诗与肃剧本身的严肃性与它们的“制作”所具有的谐剧性结合在一起。肃剧与叙事诗的“制作”等同于模仿,使得叙事诗、肃剧与谐剧这两类截然不同的文学品质相互交融——柏拉图写作苏格拉底的肃剧作品,这个行为本身却具有谐剧品质。谐剧之笑具有某种出戏的功效,从常识来看,笑声的背后潜台词是:“我比那个笑的对象优越”;肃剧则需要某种入戏,某种认同性沉醉。两种品质截然不同,在柏拉图这位哲人与诗人两重身份之人的身上,两种品质融为一体。
这一点理解起来并不容易,亚里士多德接着说:“酒神颂制作术,还有大部分双管箫情歌术和基塔拉琴合唱诉歌术”是模仿。这几个文学样式与前面不同,均加上了“术”一词;它们的共同点在于需要乐器伴奏,即有音乐。尼采用《肃剧从音乐中诞生》一书的标题来指明肃剧与音乐的关系[19]。音乐利用音符间的历时与共时关系,形成动人的和声效果,直接改变人的现世生存感觉[20]。作曲不过是对这种音乐技术的符号化记录而已。叙事诗制作与肃剧制作,等同于模仿,也就等同于各类音乐之“术”,就是要像音乐般有动人之和声,引人沉醉,改变世人的生存感觉。
哲人要学会的诗术需得像音乐的和声一样,通过言辞的制作引人沉醉,同时这种制作本身亦是模仿,具有谐剧品质,也就有了像哲学一样的追求,即否定尘世间的一切,最终实现对至高智慧的追求。诗术既引得普通人沉醉,又让极少数人体会到尘世生活的可笑,从而实现两类人的和而不同。可是,亚里士多德为什么还说“大部分”而非全部的音乐之“术”呢?原因在于,部分双管箫情歌与基塔拉琴合唱诉歌无情节,难以模仿[21]。肃剧与叙事诗的制作,不仅要引得常人沉醉,还必须诉诸情节,以供常人在故事情节之中沉醉与模仿,以求改变政治生活中人们的行为——现代电影、电视多以这样的情节为根基。叙事诗与肃剧制作的诗术,以情节为基础,实现了政治性沉醉的目标,同时又由于与谐剧的关系,实现了与哲学的互通。
综上所述,亚里士多德谈“模仿”并非后世所述论述的某种文学问题,实质上是指明叙事诗制作与肃剧制作的双重性(它们正是《诗术》后文的重点):一方面像音乐一样,让世人沉醉于肃剧主题的言行之中,从中体会到某种从个人到普遍的生存意义[22];另一方面,要有谐剧的出戏状态,保持哲学的探究与质疑精神。

▲ 公元2世纪的酒神马赛克画
二、从“多”到“一”的上升
有了对模仿的初步理解,我们接下来仔细分析他提到的第二组例证。但在第一组与第二组例证之间,亚里士多德插入了一大段论述:
//
[1447a16]不过,它们彼此之间在三方面有差别,要么赖以模仿的东西不同,要么[模仿]的东西不同,要么[模仿时]方式不同而非同一种方式。[1447a18]正如有些人用颜色和用形姿来制造形象, 模仿许多东西——有些[20]凭靠技艺,有些凭靠习性,另一些人则凭靠声音来模仿;同样,如上面提到的那些技艺,都以节律、言辞、和乐来模仿,不过要么单用,要么混用。[1447a26]由此来讲,仅用和乐和节律的是双管萧术和基塔拉琴术,包括其他任何涉及类似作用的[技艺]如管吹术;舞之术则凭自身用节律,不用和乐——因为舞者通过动姿的节律模仿性情、感受和行为。[23]
若直接解读这段文字的确费解,即便引述古希腊相关文献互相参证,这段文字同样诘屈聱牙,难以卒读。柏拉图在《王制》(旧译《理想国》)中同样提到了模仿的问题。在392c7及此后的文字中,苏格拉底批评了传统诗人关于诸神的讲法所犯下的错误之后,紧接着论述诗人应该怎样讲故事的问题。苏格拉底认为,故事要么用单纯叙事,要么用模仿,或者两者混用。从这句话来看,苏格拉底将单纯的叙事与模仿对立了起来。在后面的行文中,苏格拉底解释说,叙事就是“诗人自己在说”,而模仿则不相同,它是诗人让故事中的人物说话,“诗人隐藏自己”(393c9)[24]。直观地讲,柏拉图的这段文字所言的模仿是“诗人隐藏自己式”的模仿,实质上是戏剧式的扮演,诗人自身退居到幕后。
有了这样的理解,我们再来回到文段本身。各注疏本均以为本段的第一句话分别概述了前三章的主旨[25]。照此说法,第一章的主要就是论述赖以模仿的东西不同;从所引文段的行文来看,文字字面上的确在论述赖以模仿的事物,主要内容似乎包括言辞、声音、形体、色彩之类的事物。然而,若是亚里士多德意图谈论这个简单的问题,何以要把文字写得如此混乱而缺乏条理?或许,亚里士多德这位教授诗术与模仿的老师自己本人也“隐藏了自己”,把真实的目的藏在表面主题之后。唯有发现亚里士多德如何“隐藏自己”的学生,才能跟着他学会“隐藏自己”的诗术。

那么,我们接着来看这些表面上论述赖以模仿的东西的文字背后究竟讲了什么,它与亚里士多德前面所举的例子有怎样的联系。亚里士多德首先说,正如有些人用颜色与形姿来制作形象。卢卡斯认为,颜色和形姿就是画家与雕刻家制作艺术作品赖以模仿的东西[26]。在《论动物的部分》640b30及以下中,亚里士多德称,通过形状与颜色,世人认识个体的人及动物[27]。在《后分析篇》97b35及以下中,他论述在对特殊事物下定义的过程中,我们要借助事物的颜色和形状,此后再上升到普遍[28]。从亚里士多德的论述来看,颜色与形体多指具体、特殊或个别之物。他说模仿就像用颜色与形体来制作形象一样,那么证明模仿所制作出的事物当然亦是具体、特殊或个别之物。
接着,亚里士多德说赖以模仿的三种事物,即技艺、习性和声音。这三类事物似乎完全不应该放在一起,毕竟它们之间的差异太过明显。或有人以为最后一个词“声音”是指乐器的声音,与上下文提到的乐器相关。希腊语φωνή多指人声,在《修辞学》1404a21中,亚里士多德称声音是最适宜模仿的官能。我们不仅可以用声音模仿各式动物及机器的声响以取乐(《论声音》800a25)[29],更为重要的是,声音的模仿最明显地实现了从万事万物的模仿到指向某种明确意义的模仿 (《理想国》397a)。人的声音不仅可以模仿各式具体的事物,诸如动物、自然及机器的声响,而且还可以用具体的声响指向某种意义。模仿在声音的领域内实现了某种上升——从物理现象到意义的呈现。
第一个词“技艺”正是《诗术》一书标题中“术”的同义语。凭靠技艺,凭靠术,则是凭靠某种带有普遍性的基础知识;即便人可凭靠经验完成某种任务,但若要对其加以描述则定需凭靠某种知识[30]。唯有凭靠带有这种知识性的技艺,人能够生产出某种产品——诗正是诗术的产品[31]。居中的习性正是人身上既带有天然性质,亦可接受技术性影响的部分;若无法理解,就可以想象一下方言的养成与普通话的训练的问题,它恰是人的声音所具有的习性与技艺两个方面的体现。
接下来提到的三个事物,即节律、言辞与和乐,它们均有这样的特点,即从混乱杂居的多中走向某种纯粹之一。多种混乱的动静结合转变成某种有规律的动静交替,节律便得以形成;模拟万事万物的声响转变成了有意义的表达,声音便形成了,但还不是言辞。丝弦的振动形成的各式音符,遵循某种音程关系,便形成了历时与共时性的和乐。节律、言辞与和乐均与技艺、习性和声音一样,它们要求某种从“多”到“一”的转变。
从混乱到整一,从物理现象到意义,从粗笨的习性到经由技艺打造而成的诗,三者均是某种上升。亚里士多德用一段含混的文字,横亘在“模仿”概念的正中间,以此隐晦地阐明“诗术”要将“混乱”“无意义的人世”“精笨的习性”引导走向那纯粹之“一”;这个诗术的过程,正是一种上升的过程。亚里士多德将在接下来的文字中同样采用例证的方式隐晦地指明言辞之模仿,即诗的意涵;当然,这种意涵正与模仿所涉例证的上升相关。
三、爱欲之诗
在接下来的一段文字中,亚里士多德首先提到的两个例证是索福戎和塞那耳科斯。叙拉古的索福戎,大约生活于公元前5世纪晚期,以拟剧作家的身份闻名于世。其生平已多不可考,《苏达辞书》(Suda)曾录数语介绍索福戎:叙拉古的索福戎,阿加托克利斯(Agathocles)与达娜西利斯(Damnasyllis)之子,与大名鼎鼎的薛西斯和欧里庇得斯同时。他曾以多里斯方言的散文风格写作男人与女人的拟剧[32]。我们无法确定索福戎的具体生卒年,但或可根据他的儿子塞那耳科斯来推定其生活轨迹。令人遗憾的是,塞那耳科斯同样不可考,且这个父子的关系亦有质疑之声。唯有一点似乎无用质疑,即他们两位所作均为拟剧。

▲ 提洛岛的古希腊剧场遗址
亚里士多德称索福戎、塞那耳科斯的作品与苏格拉底言辞这两种类型没有共同的名称,实质上略有不妥,毕竟索福戎、塞那耳科斯的作品已有共同的名称,即拟剧。若仅为强调拟剧与苏格拉底言辞之不同,则不必提及索福戎、塞那耳科斯之名,仅述拟剧与苏格拉底言辞不同即可。另一方面,现存苏格拉底言辞归属四位思想家名下,分别是柏拉图、色诺芬、阿里斯托芬及亚里士多德本人。据此可知,“苏格拉底言辞”这个说法本身已是一个共同的名称了。不仅如此,苏格拉底言辞与拟剧并非毫无共同之处,据称,柏拉图的枕头下放着的是索福戎的拟剧[33]。足见索福戎的戏剧形式对柏拉图写作的影响巨大。
既然如此,拟剧与苏格拉底言辞的差异何在呢?拟剧篇幅短小,以散文语言和戏剧结构呈现日常生活中的诙谐场景;分作男性剧与女性剧两类,男性剧则是男人为主角,女性剧同理。现存残篇不少内容粗俗,言辞猥琐,多与性、生殖器与排泄物相关,但亦有不少内容涉及日常生活中的对话与观念交流。这些谈话当然会提及古希腊的诸神,只是在拟剧的污浊笑声之中,诸神的神圣性消失殆尽。苏格拉底言辞与此自是不同;在柏拉图的《王制》中,苏格拉底一行人被强行拦下,要求去参加某场会饮,并向苏格拉底许诺奇景异观、美味佳肴;只是在后来彻夜的交谈之中,苏格拉底的言辞让在场的所有人遗忘了这些低级的快乐[34]。
苏格拉底言辞的确与索福戎的拟剧,虽均为对话,但并非同类。亚里士多德称它们并无共同的名称,当然指其品质各不相同。即便用相同的音步模仿,这些内容也没有共同名称。
亚里士多德意在告诉我们模仿并非使用相同的音步,若因其使用音步而称其为诗人,仍没有厘清模仿之意。若结合前文的叙述可知,亚里士多德之模仿有某种从多到一、从混乱到有序的过程,这不正是从拟剧到苏格拉底言辞的过程。苏格拉底言辞要以严肃的形式引人沉醉,实现对混乱日常的牵制与规训,的确与拟剧品质不同,无法用同一个语词对其命名。
据此理解,模仿在亚里士多德这里仅具有政治性?接着,亚里士多德又将荷马与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对举。亚里士多德认为荷马创作了《伊利亚特》《奥德赛》两部严肃的作品和《万事通先生》(Margites)这部谐剧作品,因而是肃剧与谐剧的创始人(《诗术》1448b34)。盲诗人荷马的作品,从行吟诗人的口诵到文本制作影响深远,整一性地塑造了希腊文明的根基[35],甚至还影响了后世的基督教文明[36]。荷马诗作的整一性功能源于它自身所具有的整一性形象[37]。不过,荷马的作品在古希腊的智术师运动之中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智术师们利用自然论说者的研究成果,攻击古旧诗人习传教诲虚妄不可信奉。亚里士多德称与其称恩培多克勒为诗人,不如称其为自然论说者。恩培多克勒生活于公元前5世纪(约前494-434年)的意大利城邦阿克拉加斯(Akragas),曾数次参与该地的政治活动,取得不少成绩,赢得内外声名;恩培多克勒以四因说及爱恨说的理论,进入哲人行列,而其政治成绩取得的声名已使他拥有传奇色彩,生后亦有传记文字视之为非凡之人,虽多不可信[38]。据拉尔修所述,恩培多克勒为毕达哥拉斯的门徒,后因泄露秘传知识被逐出圈子;恩税多克勒运用他研习的自然哲学知识为民众治病,改河道而治瘟疫,用浅显的比喻传播自然研究学识,颠覆了习传诗人的道德教化,赢得民众的崇拜[39]。

亚里士多德认为,恩培多克勒颇具诗人才气,擅长措词,精于比喻及其他诗艺,与荷马同属一派[40]。此处的行文又故意与荷马对举,显然要突显诗艺与带有模仿性质的诗术不同。诗艺多指语言技艺,而模仿则要包含属人的政治行动,赋予众人行动的意义担负,荷马为英雄立传,为诸神著述,首要的功能正在于此。然而,自然哲人的论述传播开来以后,荷马的撰述被斥为虚妄,而那些传播自然学说的人,如恩培多克勒则被视为英雄。从诗艺上讲,恩培多克勒同样为诗人,但究这层模仿的意义上讲,恩培多克勒算不上真正的诗人。
柏拉图《王制》曾记述了苏格拉底对荷马的批评,认为真正的诗人不应该像荷马的作品那样无法承受自然哲人的攻击。[41]荷马对人性诸欲的叙述真实可感,却因对至高诸神的描述无从证实最终有损诗的整一性。自然论述者深研自然规律,以某种技艺服务于现实生活,以为理解了整全,实现了哲学的至高追求,然则他们未曾意识到,正是他们以自然为研究对象,划定了沉思者自身与研究对象的界限;无论他们所研究的自然多么恢宏,他们自身的存在足以明证其研究仍非整全。与荷马的竞赛使得他们遗忘了,荷马对人性的深切把握正是模仿之诗的重大价值。唯有以对人性的模仿之诗进入沉思的哲学之中,才是真正走向整全之路,也是苏格拉底摆脱青年状态,肇端政治哲学重新启航的关键所在。无论是拟剧诗人,还是恩培多克勒的诗作,均无法把握人生的真实情态,唯有荷马所开创的谐剧与肃剧的混合,方能称得上真正的诗术。荷马在《诗术》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42]
接着,亚里士多德提到了他在本章的最后一个例证,即卡瑞蒙(Chaeremon)及其《马人》。从行文上看,卡瑞蒙混用格律,同样称作诗人,似乎意在取消诗与格律之间的关系。但卡瑞蒙的身份特殊,大约生活于公元前380年左右,生平已不可考,其作品文词艳丽,极少以英雄人物、道德楷模为题,但其长于描写物件与场景,利用描写制造快感,满足色欲,尤其善长描写鲜花与女人的美[43]。《马人》(Centaurs)一作早已失传,但马人的形象却流布甚广,它上半身为人,下半身为马,生性野蛮,富有攻击性;他们生活在阿尔卡迪亚(Arcadia)的森林中和希腊北部,介于人类社会与自然社会之间。大树和石头成为他们的武器,由于力大无比,便能轻松击败希腊英雄。喀荣(Chiron)和普弗洛斯(Pholus)在传说中最为有名,为马人代表[44]。

▲ 《喀戎和阿喀琉斯》,约翰·辛格·萨金特 绘,约1922年
虽则《马人》失传,卡瑞蒙之生平不可考,然而从上述描述中可见该组例证与人的爱欲之间的关联。诗之模仿与自然论述的重大不同正在于,前者定然涉及人言行中的爱欲行为。若我们可以结合这些残存的片断大胆猜想,我们会发现“爱欲”在肃剧与谐剧整合体中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柏拉图及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形象身上,我们找到了这种爱欲与肃剧、谐剧结合的典范,苏格拉底自己称其受“大精灵”的召唤,要一生坚持在这种爱欲的驱使之下严肃地渡过诙谐的一生[45]。哲人遗忘掉这种爱欲,自然无法理解“诗术”的内涵,则会带来政治哲学的激变,施特劳斯所关注的“前现代性与现代性对前现代性政治哲学的激进变更”正是理解政治哲学问题的关键[46],同时也是理解重启古典诗术的意义之所在。
所以,亚里士多德借助第一章的例证已经指明了诗术指向的目标,基于人之爱欲,融政治性关怀与哲学性追求为一体;这样的论述实质上指明了柏拉图的写作与荷马诗作之间的关系[47],使得《诗术》在首章就已标明其立场:即《诗术》的最终目的正是在解释柏拉图的哲学之诗的写作手法,也印证了阿尔法拉比关于“两圣相契”的说法[48]。
注 释
作者简介
延伸阅读


● 经典与解释·华夏 | 《亚里士多德论政体》(崔嵬、程志敏 编)
编辑|陈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