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陀罗》中的隐喻
编 者 按
本文作者为洛德(Carnes Lord),曹聪译,选自《古典诗文绎读·西学卷· 现代编》(上册,刘小枫选编,李小均、赵蓉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年)。为方便阅读,本次推送删去全部注释,有兴趣的读者可查看原书。
当代史学研究中一次势头强劲的运动认为,应该把所有传统政治哲学的伟大著作都理解为作者们所处时代政治观念与政治争端的反映。且不说这种研究路向有什么缺陷,它注重研究每个政治哲人面对的政治境况、他们参与的政治活动的深远意义,这点确实能够满足我们的需要。政治哲人的政治活动可以为理解他们艰深的理论问题提供至关重要的线索。这种研究路向还能阐明这些理论著作的写作特征及写作意图。
能支持这一研究主题的相关资料多得超乎想象,甚至年代更久远的作者们也有很多相关资料。不幸的是,这些资料通常不可靠,总是不完整,它们本身就需要阐释。这不足为奇。尤其在前现代不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政治活动需要承担很大风险。政治哲人在其公开写作中谨小慎微地提出政治问题,他们更乐于宣传政治忠诚或讨论政治方案,甚至私人书信中也是这些内容。尤其存在这种可能,政治哲人从事的活动极有可能被解释为颠覆现存权威。不过,关于这类事件的知识并非总是遭到压抑,一些政治哲人或许会出于自己的理由把它记录下来。
在这点上,马基雅维利的个例尤其令人关注。在一流的政治思想家中,没有谁能够如同马基雅维利一般深入地参与到他所处时代的政治当中。马基雅维利长期效力于佛罗伦萨共和国,这让他有着参与同时代意大利——甚至欧洲——最高政治的经历。尽管马基雅维利的政治生涯于1512年随着共和国的垮台和美第奇家族重掌权力戛然而止,他仍旧急切地关注政治动向,与重要人物保持联系,筹划重返政治舞台。在马基雅维利现存未佚的著作中,有很多篇目都能为这次活动提供佐证,包括信件、便笺以及外交公函。很明显,这类资料并未得到更多的重视,人们大多着力于马基雅维利的主要著作《君主论》和《论李维》中的大量迷题。近年来,马基雅维利生平研究倾向于将马基雅维利的个人气质作为解释其理论著作的关键,与此同时,他的政治活动仍旧遭到忽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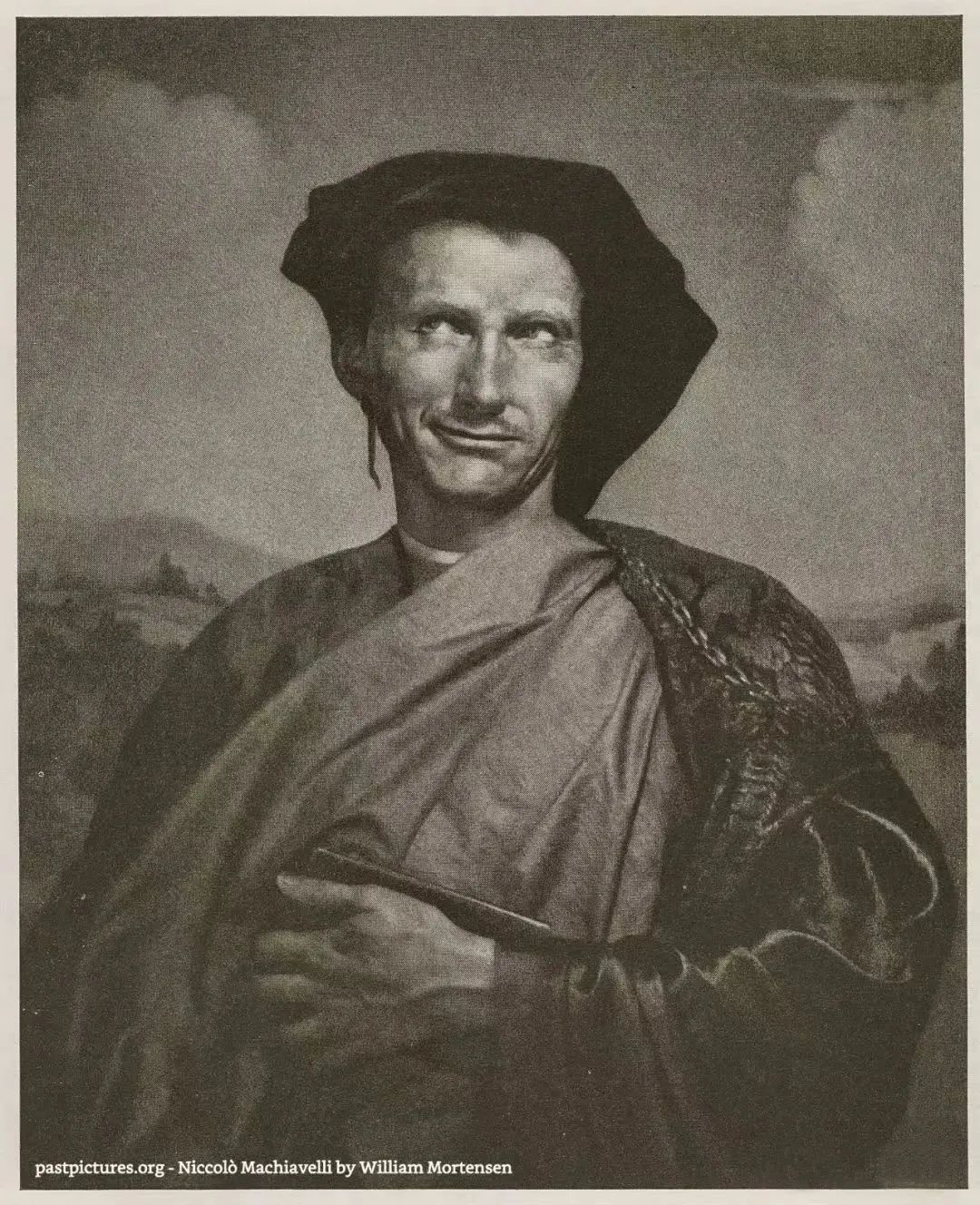
▲ 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1469―1527)
然而,精心研究马基雅维利的通信与随笔或许会让我们获益颇丰,分析他的文学作品或许会促使我们最大限度地理解马基雅维利。接下来,我将试着详细分析马基雅维利的公认最伟大文学著作《曼陀罗》,以此证明我的上述观点。我认为,这出意大利剧院中的经典剧作包含着精心编织的隐喻,这种隐喻为马基雅维利在佛罗伦萨参与的政治活动,以及其政治理念的来源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文献资料。
近些年人们开始关注,马基雅维利的《曼陀罗》中存在一种隐喻,这种隐喻关涉到作者对佛罗伦萨政治的看法及其一般性的政治观点。事实上,为探询这种隐喻做出的努力根本差强人意,然而不可否认,没有充分的借口完全将这些努力完全弃之不顾。马基雅维利这出伟大的喜剧中存在太多的谜题与非喜剧性特征——在和马基雅维利的其他相同体裁作品对比时尤为明显——以至于让人无法满足于传统的解释方法。把《曼陀罗》称作悲剧——正如里道菲(Roberto Ridolfi)以及其他一些人的做法——等于发现问题却不去解决。
《曼陀罗》不是传统喜剧,然而——如同但丁之例充分显示了——文学作品不一定非得采用悲剧形式才能显示出严肃性。马基雅维利的政治视域固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喜剧,也同样不能称作悲剧,因为它认识到人类活动无法逾越的界限,认识到人类强烈的利益冲突无可避免。事实上,难道不正是马基雅维利本人告诫说,完全可以战胜那种由命运或运气替人类安排的局限——命运是个女人,热切莽撞的青年就可以摆弄她吗?马基雅维利的政治见地不是简单的喜剧,倘若通过喜剧能够明白年轻人欢庆胜利的象征意味以及渴望超越年龄、权威和责任的隐喻,那么可以说,他的政治见地和喜剧关系密切。
在今天看来,使用和研究文学作品中的隐喻一点也不新奇。隐喻通常被想当然地视为基督教解经学的产物,故而本质上是一种中世纪现象。然而,传统的寓意写作在古代就已经高度发展,并且在现代持续繁荣,世俗和宗教文本都用过这种写作方式。非宗教地使用隐喻十分平常,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重要诗人,包括马基雅维利同时代的佛罗伦萨人,如兰蒂诺(Landino)和玻阿尔多(Boiardo)等都用过隐喻;但丁和薄伽丘清楚而详尽地讨论过隐喻。
马基雅维利本人就作过一首隐喻诗《蠢驴》(Asino, 1517)——一首摹仿《神曲》的政治讽喻诗,佛罗伦萨当时的头面人物以动物的形象出现。至于喜剧本身,应当更加关注关于这一点的些许传记材料。马基雅维利的亲戚和执行者朱里昂诺·利奇(Giuliano de’Ricci)指出,有一部名为《面具》(Le Maschere)的喜剧手稿,它建立在《云》和阿里斯多芬其他喜剧的基础之上,马基雅维利写作这出喜剧时效力于佛罗伦萨公国,这部喜剧乃是应当时同僚所求而作。利奇拒绝复制这篇手稿,部分原因在于它残缺不全,难以解读,但是还有部分原因在于,作者在这部喜剧中“以隐讳的名号攻击和毁谤许多活跃于1504年的市民”。这一证词似乎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证据来证明,马基雅维利有美德用隐喻写作一部关于当时佛罗伦萨真实政治人物的喜剧。至少可以说,有个显著的巧合是,创作《面具》的那一年——根据马基雅维利精确的年代提示——正是《曼陀罗》中虚构剧情发生的那一年。

“隐喻”一词很容易遭到滥用。有必要区分《曼陀罗》中两个层面或各种隐喻性论辩。我认为,《曼陀罗》确实(既体现在其特定结构,又体现在人物性格的处理方面)影射了佛罗伦萨政治、马基雅维利自己的政治构想和1504年的一些活动。另一方面,我认为《曼陀罗》同样包含可以暂时称作马基雅维利包括“新君主”在内的政治教诲的概述。这两方面理由,在某种程度上相互支持,可以说与中世纪文本“隐喻”与“道德”意义的普遍区分契合。
对于“隐喻”意义而言,其目的可以理解为基本喜剧。《曼陀罗》是一出非常滑稽的喜剧,当马基雅维利的观众轻松地觉察到佛罗伦萨政治的蛛丝马迹时,这出喜剧无疑会更加有趣。尽管现在无法精确分辨出马基雅维利的诸多影射(它们更能契合当时的事件),这出喜剧中的关键性隐喻的要点仍旧组成了一种喜剧虚构,这足以和这出喜剧中任何充斥表面的诙谐妙喻匹敌。与此同时,隐喻并非不带有与生俱来的某种严肃性。正如我将试着论证的那样,隐喻作为一个整体近似于供认了马基雅维利自己的犯罪意识——如果不算犯罪行为的话。
要品味《曼陀罗》的独特品质,简要回顾一下马基雅维利的另一出喜剧《克蕾希娅》(Clizia)不无裨益。正如《克蕾希娅》在很大程度上摹仿了古罗马普劳图斯的喜剧,因此,这出戏剧的体裁在某种意义上是衍生性或模仿性的。马基雅维利强调,《克蕾希娅》的底本是当时佛罗伦萨的一个“事件”(caso),与罗马人普劳图斯依据的雅典事件本质不同;正如马基雅维利在开场诗中提到的,这反映出世界上同样的“事情”总是重演,尽管“人”或人的社会在不同时代各不相同。倘若像马基雅维利在某处所说的那样,“喜剧的结局给私人生活举起了一面镜子”,《克蕾希娅》似乎正是关注私人生活“事件”的典型喜剧,有别于关注社会或政治事务的喜剧。与马基雅维利接受的喜剧标准相近的,看似并非阿里斯托芬,而是非政治的米南德(Menander)及其罗马模仿者。喜剧通常低于政治或远离政治;尤其是,喜剧对古代和现代之间的政治差异保持中立——在马基雅维利看来,这种差异最终来自宗教差异。

▲ 阿里斯托芬与米南德的双头像
对比之下,马基雅维利在《曼陀罗》中并未向古代先贤呼告。《曼陀罗》的开场诗并不包含对喜剧的大体反思(而《克蕾希娅》的开场诗却这么做了),同时它也和任何古代喜剧或喜剧事件无关。《曼陀罗》没有摹仿古典范例,在某种意义上,这似乎和这出喜剧的主题或主要内容有关。开场诗就告知我们,《曼陀罗》将上演“发生在这个国家中的一桩新事(un nuovo caso)。”但这桩“新”事是否并非一桩“新鲜”事?尽管《曼陀罗》中的很多要素都能在意大利旧小说(特别是薄伽丘《十日谈》中的那些故事)中找到来源,这出喜剧情节整体似乎并未因循前例。《曼陀罗》似乎打算上演一桩骨子里新鲜的事件——即便不是一桩彻头彻尾的新鲜事。然而,倘若喜剧中上演的“事件”本质上在任何社会都会重演,都普遍存在——正如我们从《克蕾希娅》的开场歌中得知的那样,《曼陀罗》的情节如何展现一桩“新鲜事”?
答案显而易见:《曼陀罗》是一出非同寻常的喜剧,其展现的事件归根结底根本不属于“私人生活”,而是属于政治领域。马基雅维利正是宣称在政治领域中发现了某些全新的东西——一条新的“道路(via)”,“任何人都未曾走过的道路”,正如他在《论李维》开篇强调的那样(《论李维》卷一,亦参卷二)。《曼陀罗》开场诗和《论李维》卷一之间有着清楚的联系。在《曼陀罗》中,马基雅维利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希望显得智慧与严肃”的人会从事喜剧创作。他给出的解释是:
带着这些虚无的想法,他试图让悲惨的生存变得快意些,因为他无所期待,他无法在其他事业上展示其他美德(virtue),他的劳作没有回报。
然而,马基雅维利不情愿退出政治生活,这预示着更大的不幸,而不仅仅是个人的不幸。每个政治人物能够企求的报偿是,“退到一边讥讽,说出他们看到或听到的恶”。对于这种理由,即“当今时代完全是古代美德的退化;因为,当人们看到每个人都牢骚满腹,在千难万险面前,他们不劳作也不努力,不去追求如风吹散、如雾掩藏的事业”;可对比马基雅维利在《论李维》前言中对“古代美德”和现代衰颓政治所作的比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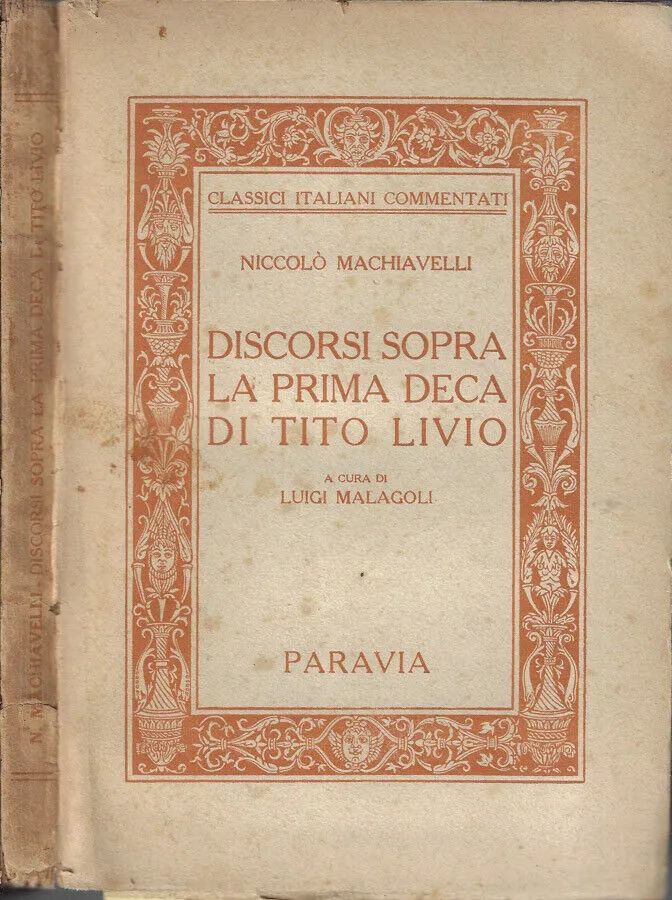
《曼陀罗》尽管回避古典形式,女主人公的名字却让人回想起一个古代故事:正是卢克蕾佳(Lucretia)遭到罗马王强暴引发了早期罗马王权的崩溃和共和国的建立,马基雅维利在《论李维》中高度评价该事件。在马基雅维利的版本中,勾引取代了强暴,尽管卢克蕾佳堪称道德楷模,然而她表现得很情愿甚至热切地为通奸出谋划策。马基雅维利笔下的卢克蕾佳道德突然败坏,这令很多评论者感到困惑不解,因为这似乎有违戏剧的联贯性和真实性。不过,这并不是马基雅维利对待卢克蕾佳的唯一有违常情之处。在这出戏剧的开始阶段,我们得知卢克蕾佳那个富有的丈夫尼洽(Nicia)“让自己完全受制于她”(I.1),而且卢克蕾佳“心思缜密”,尼洽却“愚不可及”。李古僚(Ligurio)把卢克蕾佳描绘得如此了不得——“聪慧、教养优异、配得上掌管一个王国”(I.3)。

▲ 电影《曼陀罗》(1965)里的卢克蕾佳
接下来,提莫窦也同意卢克蕾佳“聪慧善良”,不过,他还认为“女人们说到底都没什么头脑,有谁会说两句别人布道给她的话就了不得了,因为在瞎子的地盘上,有一只眼睛的也算是翘楚了”(III.9)。尽管它出处可疑,在这出戏剧的最后,这种观点竟然被证实所言非虚,当卢克蕾佳的情人卡利马科(Callimaco)告诉她这个成功的计划时,她说道:“我将会把你视为我的主子、保护人和向导;你是我的父亲、我的护卫,我的幸福全指望你了。”(V.4)根据她本人的言辞,似乎这个聪明谨慎得足以统治王国的夫人自己就需要别人掌管。卢克蕾佳的道德堕落并不源于对她丈夫性爱美德的不满——尽管卡利马科认为自己的成功至少与自己和尼洽老爷带给她的不同经历有部分关系——而是源于对他齐家本领的不满。尤其应该注意卢克蕾佳很奇怪地把卡利马科认作“父亲和保护者”,但是没有任何一种解释曾经注意卢克蕾佳表现出热衷家政管理或安全而不是性爱的满足。
卢克蕾佳是谁?或者说,卢克蕾佳是什么?马基雅维利本人在开场诗中就清楚地指出了她的个性。在简要地介绍了卡利马科之后,马基雅维利用下面几句话总结了这出戏剧的情节:
一位年轻聪慧的姑娘,使他深深地陷入情网,出于这个理由她将遭欺瞒,你即将看到欺瞒的方式,愿你和她一样被欺瞒住。
这种奇怪的说法不只是要把卢克蕾佳和观众联起来。在第四幕的结尾,提莫窦告诉观众,卡利马科和卢克蕾佳整晚都会醒着,“因为我知道,如果我是他,你是她,我们也不会睡着”。正如开场诗清楚地表明,马基雅维利假设的观众首先是佛罗伦萨观众。可以说,卢克蕾佳“隐喻着”佛罗伦萨,或者更精确些,等同于佛罗伦萨populo(民众)。
这种解释就可以用来说明卢克蕾佳和尼洽的独特关系。卢克蕾佳受一个“对她言听计从”的男人支配,不过这仍旧无法让卢克蕾佳满意,这使人想到无能为力的皮埃罗·索多里尼(Piero Soderini)治下共和的或民主的佛罗伦萨。尽管卢克蕾佳诚实正直,尼洽不足让她有可能接受别人允诺的更加强有力的统治,以及由此产生皆大欢喜的结果。倘若尼洽是一个完全凭借“财富”统治的君主,卡利马科就是马基雅维利意义上天生的或“有美德”的君主——他野心勃勃,情愿为了“伟大、危险、破坏性或名誉扫地”的事业搭上性命,“野蛮、残酷、无法言表”的行动过程才能满足他的欲望(I.3)。只有这样的君主才有美德满足佛罗伦萨民众最基本的渴求——不是渴求自由,而是渴求安全和有效的统治。
这一论断有个至关重要的前提,即佛罗伦萨人并没有足够的美德管好自己。像卢克蕾佳一样,佛罗伦萨人或许确实“适合统治一个王国”,正如古罗马人确实称职得统治了一个领土甚至超过整个儿意大利的国家。然而,佛罗伦萨人——普通民众——并没有足够的“智慧”或“审慎”来直接统治别人,甚至统治他们自己。尽管马基雅维利在《论李维》中仿佛说,人们永远需要那些受到政治生活回报吸引的有“头脑”者的引导——也就是,由一个有美德的君主或由一个有可能产生有美德君主的阶层引导。
《曼陀罗》本身是否就有一些证据证明卢克蕾佳在审慎或头脑上有所欠缺?我认为,马基雅维利通过卢克蕾佳的宗教观念证明上述欠缺。尼洽证明卢克蕾佳睡前喜欢念祷文(II.6),似乎首先是她的虔敬——她的传统罪恶观念及其衍生物——导致她抗拒卡利马科的计划(III.11)。首先,她相信每日望弥撒可以战胜她可能患有的不育(III.2)。事实上,卢克蕾佳受宗教代理人的“支配”至少和受她丈夫支配一样。那些人物在引诱卢克蕾佳时不仅仅是便利的工具,他们更是卢克蕾佳感情和戒律重要的竞争者,她和他们关系带有性的含蓄之意就暗示了这一点。提莫窦修士暗示,他乐意对观众做出他想让卡利马科对卢克蕾佳做出的事情。
我们同样得知,“那些坏修士中有人(un di que’ fratacchioni)开始打她的主意之后”,卢克蕾佳最终放弃了每日弥撒,这件事轻而易举地改变了她先前的习惯(III.2)。卢克蕾佳遭受这个“可恶的修士”求爱一定会让人回想起佛罗伦萨人和吉洛拉默·萨沃那洛拉(Fra’ Girolamo Savonarola)的政治热恋期。尽管卢克蕾佳——正如佛罗伦萨人一样——最终拒绝了这些诱惑,她的同情心似乎让她容易被这种人的甜言蜜语打动。在这一点,事实上更全面地说,卢克蕾佳不只是佛罗伦萨人的化身,更是平民——普通人的化身。正如马基雅维利在《论李维》中充分地暗示了,民众是每种宗教的来源或支持力量,宗教是贵族统治者或祭司阶层统治民众的关键工具,在现代是祭司阶层和贵族争夺民众忠诚的重要工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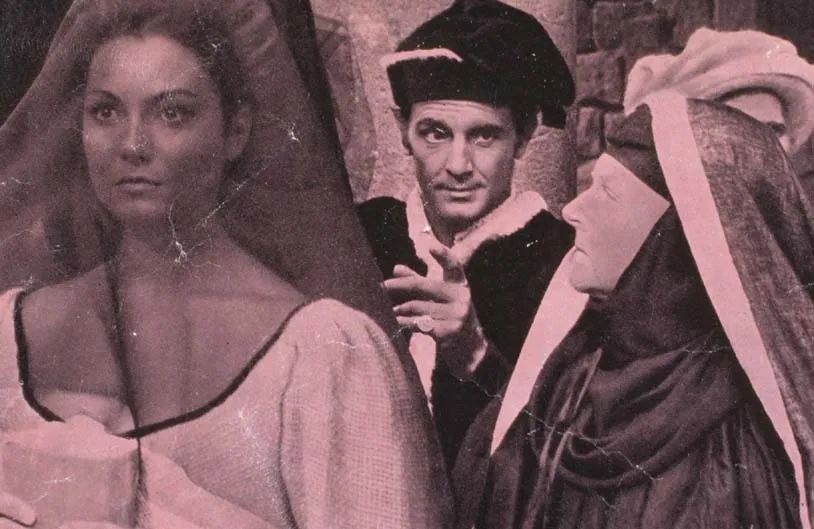
▲ 电影《曼陀罗》(1965)剧照
卢克蕾佳事件并不罕见,马基雅维利在接下来的一幕中就揭示了这一点(III.3)。一个不知姓名的女人要求提莫窦为自己最近去世的丈夫颂亡灵弥撒,这表现了提莫窦修士通常如何听取忏悔。这个妇人尽管承认她的丈夫是个“凶神恶煞”(uno omaccio),她暗示说,肉体的软弱令她无法忘记他,尽管、或者说正是因为他在性方面的做法让她痛苦得时常抱怨。接下来关于土耳其进犯意大利沿岸以及被残忍的敌军“刺穿”的谈话,让读者们毫不怀疑这个妇人的真实喜好。评论土耳其海军给托斯卡纳造成的威胁似乎是在卖弄学问——如同辨别意大利的亚得里亚海岸一样——充其量是个很久以后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然而我们一旦明白,这个无名妇人和她已故丈夫之间的关系就相当于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和其他地方描述的罗马尼亚人和切萨利·博尔贾(Cesare Borgia)之间的关系,这个奇特的细节也就不再奇特。尽管、或者正是由于博尔贾统治的残暴,博尔贾靠摧毁那里“羸弱(impotenti)主人”的统治——一个气量狭小只会毁坏却不会训导臣民的暴君——赢得亚得里亚人民的友谊并且带来“好的统治。”出于这个理由,1503年,当博尔贾政权随教皇亚历山大六世(Pope Alexander VI)死去而倒台后,“罗马尼亚人等了他一个多月”。在马基雅维利看来,比起软弱却专制的主人,以及对政治衰颓负有最大责任的精神主人——他们宣称要把罗马尼亚当作“教会国”统治,罗马尼亚人似乎不只喜欢博尔贾的统治,他们甚至还喜欢土耳其人的统治。
倘若承认卢克蕾佳代表佛罗伦萨人,那么认为尼洽象征着皮埃罗·索多里尼就不难理解了。甚至像里道菲一样坚决反对解释《曼陀罗》象征意味的批评者都得承认,马基雅维利对卢克蕾佳丈夫的写照强烈地暗示着索多里尼(Ridolfi前揭书,页15注6)。1504年,也就是《曼陀罗》剧中的那一年,索多里尼做了两年佛罗伦萨共和国的终身首脑(gonfaloniere a vita)。自从萨沃那洛拉六年前倒台——这段时间正好是尼洽和卢克蕾佳的六年婚龄,索多里尼在共和国政府中一直扮演重要角色(I.1)。和马基雅维利笔下的尼洽一样,索多里尼是一个法学博士,同时也是个富人。同样和尼洽一样,他的婚姻没有子嗣。
马基雅维利为尼洽取的名字,让我们想到了伯罗奔半岛战争时期的一位雅典政治家,他和索多里尼一样,把自己的地位归功于美德或好名声。雅典人尼洽和佛罗伦萨人索多里尼都指挥或导演了灾难性的军事事件,包括围困敌城。尽管尼洽喜剧般地忘却了本邦之外的世界,他吹嘘自己曾到访过比萨,他还提醒李古僚比萨附近一座要塞的正确名称,它最近在佛罗伦萨人旷日持久抗击前属民的战争中被佛罗伦萨人占领了(I.2)。李古僚对尼洽说的话——“像你这样的人,整日沉浸在研究中,懂得那些书本,却不会讨论世事”(II.2)——这似乎反映了马基雅维利在佛罗伦萨政府任职期间对其长官及恩主的真实看法。
在《曼陀罗》的“道德”或更普遍的隐喻中,尼洽占据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没有参与《君主论》和《论李维》关于皮埃罗·索多里尼精确象征的讨论,认为马基雅维利不只是把皮埃罗·索多里尼当作共和政治的例证,更是用他说明现代“教育”——即基督教对现实政治造成的影响,这种看法相对可靠。我认为,尼洽是用来表现现代世袭统治阶层——“继承君主”的。关于这一点,最明显的证据即尼洽和卡利马科的仆人西洛(Siro)的交谈(II.3)。尼洽,先是为流利的拉丁语表演倾倒,由此对卡利马科的医学知识深信不疑,抱怨说“咱们这地界儿,尽是些一无是处的家伙——这里不看重美德”,他还庆幸没有靠自己的学识或美德为生。当西洛鲁莽地问道尼洽收入的时候,尼洽首先否认收入很多,他说:“在咱们这地方,我们这种没有身份的人(chi non ha stato in questa terra, de’nostri pari),狗都不会朝他吠,我们一无是处,只会参加葬礼或婚庆,或是在总督府的长凳上消磨时光。”
接下来,尼洽认为自己实际上相当成功,他暗示刚刚列举的是“那些比我差远了的家伙。”尼洽实际上指的是意大利世袭贵族(“这个地方”)——正如马基雅维利本人在开场诗中暗示的那样,这种高贵的区分只是依据财产和社会地位而非任何政治美德或雄心壮志。更重要的是,除了后者拥有更多财富和名声之外,传统贵族和“有身份”的人们没有任何实际差别。按《君主论》中的术语来说,世袭君主把自己的王位完全归于“运气”而非个人“美德”。显然,从尼洽的言论看来,他把自己最终置于优于“我们这种人”的地位。尼洽尽管极度愚蠢,却特别得益于“运气”(比较I.3),完全符合马基雅维利说的世袭君主:正是由于尼洽这类君主在政治上的无知和轻薄导致意大利近来屡遭外国势力劫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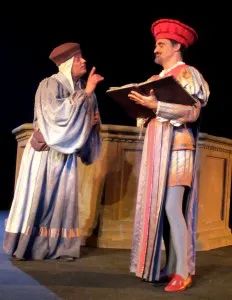
其余角色中最有意思的是李古僚,他也是剧中的实际主角。李古僚是个食客,并且一度成为婚姻掮客,他一度重操旧业为卡利马科征服自己主要恩主的妻子出谋划策。我认为,几乎毋庸置疑,李古僚就是马基雅维利的自画像。李古僚成功地曲意逢迎,讨好尼洽(I.1),这让人想到马基雅维利和索多里尼亲密的个人及政治关系。李古僚从未把自己的忠心献给尼洽——却把它献给了卡利马科——反映马基雅维利对索多里尼政权根本不满意,他希望把佛罗伦萨交到一个新的、天生的君主手中。在直率地谈到最难克服的困难时,李古僚向卡利马科表白了忠心:
不必怀疑我的忠心,因为即便我判断和期望的没有任何好处,你的血性和我相投(ci é che ’l tuo sangue si confa col mio),我盼望你的欲望得到满足(I.3)。
李古僚和卡利马科的亲密关系尤其来自他们天生的才干或美德,还有一种胆量驱使他们挑战稳固的秩序。可以回忆起,马基雅维利在开场诗中把自己描绘成有美德“在其他事业上展示其他美德。”马基雅维利特别强调,尽管他会“扮演一个比他服饰华丽者的仆从”,然而在他看来,整个意大利无人配充当他的恩主。作为君主们的幕僚,他拥有“最卓越的头脑”因为他了解自己,马基雅维利几乎具备一个君主的全部品质,除了拥有一个君主国(参《君主论》第二十二章,《论李维》献词)。
李古僚在《曼陀罗》中筹划的行动,本质上完全是马基雅维利在《论李维》中讨论的阴谋。李古獠的计划是个阴谋(与《论李维》不谋而合),尽管谋划者完全能够一手掌控这一阴谋(《论李维》卷三第6章;参Sumberg前揭书,页321-324)。在很大程度上,这个计划起到的作用归功于李古僚兜售的那种“狡计”——即,他重新招募了一些还没意识到这场阴谋的真正对象及真正罪孽的同盟者。其实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卡利马科都没能意识到为了自己利益而筹划的这场阴谋的真实本质:只是在李古僚的提示下,卡利马科向卢克蕾佳揭示了这场阴谋,并且让她由无心的从犯变成积极、永久的犯罪同谋(IV.2)。
这出戏剧开场时,卡利马科的欲望显得无望实现。卢克蕾佳的品行看起来无懈可击,尼洽的房子建得没有留下任何破绽得以接近她。然而,还有两个理由带来一线希望:尼洽头脑简单,尼洽和妻子都渴望子嗣。卡利马科还提到了第三个理由——卢克蕾佳的母亲索丝特拉塔(Sostrata)抱有一种令人费解的支持态度,我们在下文中很快会谈到她。李古僚得以诓骗尼洽和卢克蕾佳的关键当然在于,他们的婚姻没有子嗣,而且他们渴望补救这个遗憾。这一基本事实在《曼陀罗》的隐喻中象征着什么?
我们已经知道,卢克蕾佳对卡利马科感兴趣,包含着对家庭安全的考虑:卡利马科即将成为她的“守护者”(V.4)。在传统意义上,子女正是要供养、保护父母(参V.6)。佛罗伦萨和皮埃罗·索多里尼联姻中,缺少的子嗣正是士兵——这也是每个意大利人和意大利君主的联姻中缺少的子嗣。尼洽打算追随阿尔卑斯山那边“法兰西国王和显贵们”的榜样(II.6),军事美德现在在那里备受推崇。
在第一个《十年集》(Decennali)中,有一个关于1494年法国入侵的诗体记录(创作于1504年)。马基雅维利记录了自己母邦遭受的灾难,并总结出朴素的良言:“重启玛耳斯(Mars /古罗马战神)神庙吧,前路将平坦而不遥远!”那几十年,意大利(特别是佛罗伦萨)军事力量的薄弱昭然天下。佛罗伦萨对比萨的反抗无能无力,他们惴惴不安地命悬于法国的亲善,他们难敌切萨利·博尔贾这种武装劲旅,所有人都深切地感受到这种灾难。索多里尼本人对佛罗伦萨软弱无力的军事状况感同身受。
关于这一点,我认为可以对参尼洽如何抱怨同胞们缺乏美德。然而,索多里尼和尼洽一样,不去试着改变这种状况,他责怪同伴(佛罗伦萨人)无法胜任,并且假定一切无可挽回。《曼陀罗》中的行动取决于李古僚成功说服尼洽,卢克蕾佳的情况并非他认为的那样无可救药。正是在1504年(再次提醒读者注意,《曼陀罗》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一年),马基雅维利开始努力劝说索多里尼为佛罗伦萨建立国民兵,这难道只是一个巧合?
我认为,要理解《曼陀罗》,必须对照马基雅维利于1504年及接下来的几年参与佛罗伦萨军务这个背景——在某种程度上,《曼陀罗》是这次经历的纪实。《曼陀罗》独特地记录下马基雅维利筹备国民兵扮演的角色,还记录了他那很难不令人吃惊的目的:《曼陀罗》整个情节都在暗示,国民兵是一场阴谋的中心要素,马基雅维利亲自筹备国民兵正是要颠覆佛罗伦萨政府。正如马基雅维利在《论李维》中教诲的那样,有一条真理比一切真理都真实可信——若是人民没有武装,那就是君王的过失(《论李维》卷一第21章,卷三第29章)。很明显在《曼陀罗》中,李古僚认定,真正不育的是尼洽而非卢克蕾佳——正是由于他的不育,除非他本人离场否则“无药可救”(II.2)。马基雅维利知道,索多里尼太好,以至无法对自己的性格或政策进行任何激进的改革。针对佛罗伦萨的病况,马基雅维利的治疗方案与索多里尼政权的含混状况无法兼容。
一旦懂得国民兵在《曼陀罗》隐喻中的重要性,戏剧中其他要素就变得明朗起来。首先,卢克蕾佳的母亲索丝特拉荅是个异乎寻常的角色。索丝特拉荅表现出一种令人惊异的强烈意愿要加盟敌营。卡利马科说她曾是“欢场好手”,如今是个富有的女人(I.1)。李古僚似乎早先已说通了她,因为他告诉尼洽,在对付卢克蕾佳的行动上,索丝特拉荅和他们想法一致(II.6)。索丝特拉荅的主要职责似乎是劝慰卢克蕾佳,让她相信提莫窦的慈善和威信。当提莫窦看到这两个人朝他走来,他说道:“她和她母亲一起来了,那可真是个招人烦的家伙(la quale é bene una bestia),不过倒是个好帮手,能让她按我的意思做”(III.9)。我认为,索丝特拉荅代表着弗朗西斯科·索多里尼(Francesco Soderini),皮埃罗的兄弟,一个野心勃勃的富有教士。1503年,教皇尤利二世(Pope Julius II)任命他为红衣主教(据传闻他出了大笔报偿),1504年,他代表佛罗伦萨出使教廷。
1503年,当马基雅维利到罗马关注新教皇选举时,他更多地了解了索多里尼,似乎和索多里尼建立了亲密的关系。似乎就是这一次,马基雅维利和索多里尼提到了筹备国民军的想法,并得到了后者的支持。在一封1504年五月的信中,红衣主教对马基雅维利写道:
反对筹军的人没有提出实质性的东西,也没人质疑军队是为公众着想而非私利。不要放弃努力!总有一天,你会因它而荣耀。
这一次,马基雅维利似乎早已让首脑和其他有影响力的佛罗伦萨人接受这个计划。当红衣主教的兄弟顺利接受这个计划,而其他人明确反对时——他们担心这支军队会成为皮埃罗个人野心的工具——马基雅维利认为,出于审慎的考虑,应当把这个计划搁置一段时间。在皮埃罗和佛罗伦萨执政团(Signoria)最终下令执行该计划后,弗朗西斯科·索多里尼仍旧坚定地支持马基雅维利的计划。

▲ 电影《曼陀罗》剧照(1965)
倘若索丝特拉荅是佛罗伦萨派往罗马的特使,那么几乎毋庸置疑,提莫窦修士让人想起了尤利教皇。剧中好几处能够支持这个观点。第一处是,提莫窦异乎寻常地关注卡利马科对卢克蕾佳实施的计谋是否得逞(IV.10,V.1)。提莫窦的道德观并非用钱就能收买,不过它很容易变通:他给卢克蕾佳的建议核心在于,罪恶在于意图而非行动,或者说“人们必须注重事情的结果”(III.11)。他确实关心敛聚财富,不过最终他考虑的是其教廷的“名声”——由于疏忽大意、和“我的那些修士”“缺少头脑”而败坏的名声(V.1)。据说尤利异乎寻常地关心政事和军务,毫无忌惮地扩张教会。
至于提莫窦的交易,让人联想起发生在1506年的一个事件。那一年,尤利进攻博洛尼亚(Bologna),请求佛罗伦萨作战时援助一支百人武装——根据古奇阿迪尼(Guicciardini)的说法,这个请求反映出教皇和索多里尼兄弟有某种密约。除了默许佛罗伦萨建立国民军外,我们不知道尤利为践约还做过什么。不过情况可能是这样:尤利提供或允诺某种特殊的办法:《曼陀罗》的情节暗示,确实可能存在这么一个用来打消佛罗伦萨民众道德顾虑的办法。事实上,在某种程度上,反对建立国民军似乎和可以预料的残暴有关,马基雅维利明显把残暴当作招募和训练劲旅必不可少的要素;有证据表明,皮埃罗和弗朗西斯科在为马基雅维利清除道路时遇到了麻烦。
不过,我们是否还记得,让卢克蕾佳受孕的不是李古僚而是卡利马科?谁是马基雅维利的卡利马科——那个取代索多里尼掌管佛罗伦萨的新君主是谁?马基雅维利计划成功后享有荣耀的是谁?
有人猜测,洛伦佐(Lorenzo)是这个君主;除非忘记一切证据都指向1504年(这时洛伦佐只有12岁)这个重要年份,这种假设才能成立。还有一种可能指向唐·米凯莱·科雷利阿(Don Michele Coriglia),他曾为切萨利·博尔贾效力,马基雅维利选择他组织、训练国民军。然而,除了有证据表明唐·米凯莱在残暴方面可以和他的老师匹敌之外,他没有表现出任何君王的品质;事实上,唐·米凯莱的过度为马基雅维利带来了窘状,甚至导致计划的最终失败。更可信的说法似乎是佛罗伦萨贵族伯尔纳多·卢切莱(Bernardo Rucellai),他多年来都是共和国政治的一流人物,是索多里尼政权决不妥协的反对者。
关于这种说法,最有力的证据是,1506年伯尔纳多和儿子乔万尼(Giowanni)迫于某种情势离开佛罗伦萨——据说那时他们参与了反对索多里尼的阴谋。根据古奇阿迪尼的说法,古奇阿迪尼用伯尔纳多的性格和政治生涯解释这个情节,伯尔纳多是索多里尼的敌手,拒绝索多里尼政府的任何职位,据说他还积极和美第奇(伯尔纳多和美第奇私人及政治关系密切)密谋。伯尔纳多是佛罗伦萨的人文主义者,也是知名的政治史家。伯尔纳多的花园奥丽塞拉里园(Orti Oricellari)一度成为有识者的文艺及政治聚会场所,也是索多里尼政权反对者们的活动中心。和马基雅维利的卡利马科一样,伯尔纳多过着一种半闲暇的生活,爱好“读书”、“娱乐”、“做生意”(I.1)。开场诗中提到了卡利马科的姓氏——瓜达涅(Guadagni,即Gains,利润),这或许在暗指卢切莱家族的财富。
最后,《曼陀罗》中似乎还有一个更加明显的对卢切莱家传统的回顾。卢切莱的徽章是一艘由一个女性掌舵、张着风帆的船,象征着命运女神在人类事务中的地位。第四幕一开始,有一段很长的独白,卡利马科坦陈自己备受煎熬,因为计划不知是否成功,在好与坏、希望与恐惧之间“命运和自然保持平衡”:
我是一艘挣扎在两股疾风中的船,越驶近港口就越恐惧……唉呀,我在哪里都不得安宁。
不过卡利马科最终恢复自信,重新坚定自己的决心:
面对机缘吧!躲开恶,要是不想躲开,那就像个男人,扛起它!别让自己像个娘们儿!
卡利马科在短暂的慌乱中考虑到有可能失败,这种可能性令他痛苦挣扎、草草结束这场阴谋,这一点也不奇怪。卢切莱、以及以他为原型的卡利马科秉持的命运观不是马基雅维利的命运观——马基雅维利认为,人可以筑成“堤坝或壕沟”抵御命运的暴风雨,或者说,命运是个女人,脾性相投的男人才能驯服。卡利马科自己重新决断,似乎标志着他抛弃卢切莱的身份,开始只代表马基雅维利的新君主。
《曼陀罗》早先的一处剧情对于理解佛罗伦萨隐喻和马基雅维利意图传播的教诲至关重要。我们发现,早在戏剧的开端李古僚和卡利马科就已经筹划好争取卢克蕾佳的计谋。这个计划需要李古僚说服尼洽带卢克蕾佳去“温泉浴场”——谎称找到为她治疗不孕的方法,实则让卡利马科更方便和她套近乎。正如卡利马科解释道:
那个地方或许能让她换种天性,因为在那种场所人们除了取乐什么也不做。我会自己上那儿去,使尽浑身解数逗乐,我也不会放过任何机会展示慷慨;我要跟她、跟她丈夫混熟(I.1)。

▲ 电影《曼陀罗》剧照(1965)
尽管尼洽找出诸多理由抗拒这个意见,很明显,随着李古僚的坚持,尼洽被说服了。不过李古僚自己有了另一种想法,他对卡利马科说:
你也知道,三教九流都去这些浴场,没准儿还会有人像你一样被我们卢克蕾佳夫人吸引,还更富有、比你还讨人喜欢;那么,要对付潜在的其他麻烦就很危险了——或许这么多竞争者会弄得她更加坚定,或者,即便她温和下来,却投向别人的怀抱,就没你的份儿了(I.3)。
卡利马科表明自己要干下去的决心,即便“这计策野蛮、粗鲁、恶劣得难以形容,”他表示,要么继续那个浴场的计谋,要么“另外开辟一条路(qualche altra via),让我看到希望——即便不是真的,至少也是个假希望——怀抱它,我就可以迸发出思想,从而减轻几分我的苦难”。正是由于这一点,李古僚使得卡利马科同意假扮医生,这样就可以告诉尼洽各种浴场的疗效,而今后他们事业的真实目标不同了:他们将要“进行我想到的另一条计策(pigliare qualche altro partito),它更简捷、更牢靠、比浴场那个点子更容易成功”(I.3)。戏剧一开始夸赞的浴场计谋几乎顷刻间遭到全盘否定,这不能不令人感到困惑。那么,这个计谋代表着什么?
我认为,在佛罗伦萨隐喻的文脉中,浴场应当理解为一次贵族圈子针对佛罗伦萨情势的讨论,时值1494年,那时美第奇家族离开了佛罗伦萨。简单的说,把选择浴场代表着选择governo stretto——效仿威尼斯以及古典混合政权的贵族共和国,佛罗伦萨贵族们支持这种选择。伯尔纳多·卢切莱长期支持在佛罗伦萨建立强有力的贵族政权,效仿威尼斯皮格迪(Pregadi)议会。1502-1506年间,奥丽塞拉里团体的讨论似乎尤其高度关注三个与之相关的主题:古典政治实践、共和统治、以及威尼斯政权的来源。
从卡利马科的角度看来,浴场的问题在于,他们可能会把卢克蕾佳暴露给其他与自己相似的人面前。从卢切莱这样雄心勃勃的贵族的角度看来,以贵族制共和国代替索多里尼的民主制君主国麻烦在于,会把佛罗伦萨民众暴露在其他野心勃勃的贵族面前,尤其是——马基雅维利一定担心流放中的美第奇家族——他们在“华贵”方面超过他,也就是说,他们会利用财富赢得公众的欢心。因此,李古僚给卡利马科的忠告——以及马基雅维利给卢切莱的忠告——正是独自操作。替卢切莱的利益着想,马基雅维利给他的另一条“道路”或“计策”正是《君主论》中给新君主的方法。
当今学术界普遍认为,马基雅维利在《论李维》序言中宣扬的新“道路”归根结底仍旧是条古老的道路——“古典德性”或更文明或古典共和国的道路。与这一观点关系密切的是,《论李维》表面偏爱共和国,它比《君主论》更加贴近马基雅维利的思想。然而这些假设都得不到《曼陀罗》中隐喻的支持。更甚的是,《曼陀罗》暗示出,马基雅维利根本就远离他所处时代的共和主义。不过,这并不是说马基雅维利如同在《君主论》中一样,在《曼陀罗》中充分表达了君主观。我们已经知道,李古僚的目标和卡利马科的目标并非单纯是一致的,尤其是他们共同事业的最终结果不尽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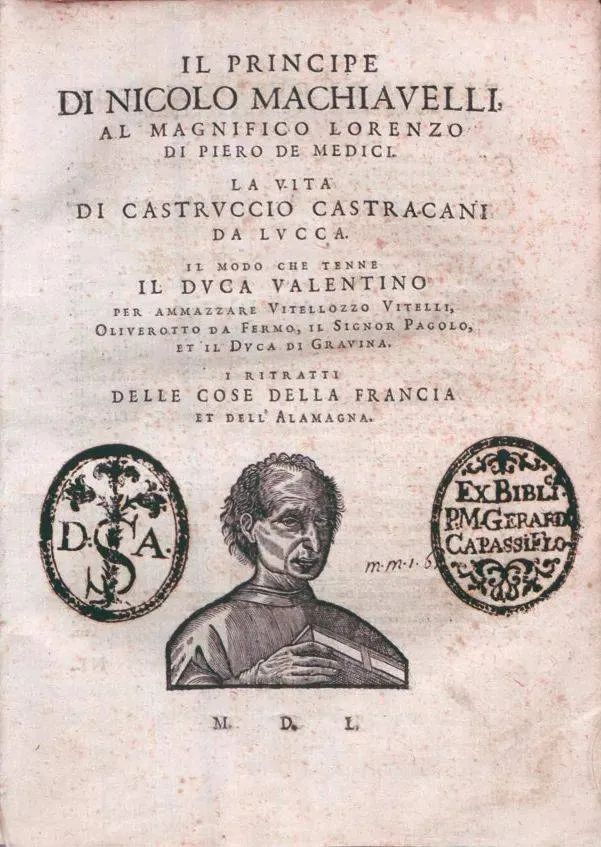
事实上,前面以及讨论过李古僚和卡利马科的谈话暗示出,李古僚为卡利马科谋划的“计策”或许是个虚妄的希望,或者说,李古僚的计划包含的不是暂时而是完全蒙骗卡利马科本人。似乎是这样的,李古僚在戏剧结尾处提议建立的三角家庭关系似乎代表建立一种采用马基雅维利方式的、由新君主执掌的政权。这个政权的本质最终是君主国还是共和国根本无关紧要,关键在于,在君主或政治权威和民众之间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关系模式。
倘若这样解读《曼陀罗》大体没什么偏差,那么就需要小心地掂量一下它的意味。假定马基雅维利的隐喻本质上和史实相符,那么,马基雅维利就唆使、筹划、参与了一场颠覆他本人表面上效力的佛罗伦萨共和国的阴谋。尽管这场阴谋没有在当时的文献中留下任何蛛丝马迹,表面看来难以置信;有人认为马基雅维利不可能做过这样的事情,现在他们有责任为自己的观点举证。这或许还有助于解释或者阐明马基雅维利的个人与政治关系以及他后来的命运,尤其是,1513年他因被怀疑参与反对美第奇家族的阴谋遭到拘禁和拷问。
我们最重要的目的是通过《曼陀罗》解释马基雅维利基本政治思想的发展。毕竟,剧中的隐喻说明,马基雅维利专注于君主统治并非为了应对共和国于1512年倒台后的政治环境而做出的机会主义反应,而是他本人既体会到索多里尼政权的弱点,也否定了索多里尼的贵族共和制反对者。由马基雅维利在《曼陀罗》中设置的精确年代判断,这个重要经历和与之关联的思想确实来自于1504年。
这一分析对于解读马基雅维利全部著述同样重要。倘若承认《曼陀罗》的隐喻是作者精心编造的,就有必要考虑一下这种可能性,这种文学技巧不止出现在《曼陀罗》中,而且出现在马基雅维利的全部著述中。那么,《曼陀罗》中的隐喻满足了一种表现手法的意图——朋友圈子的娱乐,或者为后代留下这个事件的记录。无论如何,最重要的不是手段或意图,而是马基雅维利的示意。它完全打破了这种观点(在当今多数专业解读者看来是不言自明的观点),即认为马基雅维利对读者坦白恳切、直抒胸臆。换句话说,《曼陀罗》确实证明,马基雅维利是个践行隐微写作的作者。
初看上去,认为马基雅维利隐藏了自己的真实思想、或者说,间接在行文中揭示自己的思想似乎是个悖论:毕竟,马基雅维利最伟大的作品很快就因为毫不避讳地阐发非正统异论而臭名昭著。然而,首先,马基雅维利生前没有公开发表《君主论》和《论李维》(尽管它们已经以手稿的形式流传),而那些已经发表或打算发表的主要著作——《曼陀罗》、《战争术》,以及《佛罗伦萨史》——采用了更为常规的形式。其次,完全有这种可能:马基雅维利的肆无忌惮实属有意为之,写作或修辞策略是为了吸引那些不会立即接受马基雅维利全部教诲的读者注意。《曼陀罗》本身就上演给那些对剧中影射人物与事件有着鲜活记忆的观众。沉默和肆无忌惮杂糅在一起,表面上看来不合情理,然而这或许正是马基雅维利修辞术的特征所在。
不过,或许《曼陀罗》最有价值的训诫和马基雅维利采用隐喻作为政治哲学的写作技艺有关。《曼陀罗》无疑是诗体作品,如前文所示,隐喻在他那个时代也绝不罕见。但是,有理由推测,隐喻或寓意类修辞同样出现在马基雅维利的其他散文体作品中。首先当然是《论李维》。中世纪解释者经常把《旧约》的人物和事件对应地解释为《新约》中的人物和事件,同样,马基雅维利有争议地对待古代罗马,不仅是为了构筑一个乌托邦来衬托现代罗马,而是为了隐射或模仿现代罗马,也就是,罗马教廷。思考马基雅维利在《曼陀罗》中隐喻的方法,或许有助于还原马基雅维利伟大的政治著作的某些维度,如今这些方面即便没有全部忽视、也遭到无缘无故地低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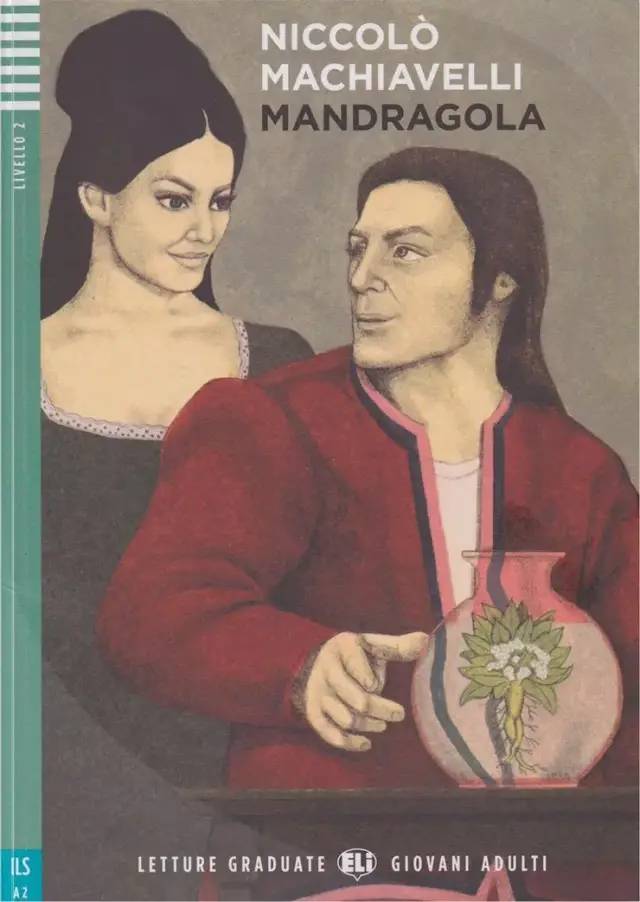

延伸阅读


编辑 | 刘一卫
关注我们

如有涉及版权问题,敬请联系本公众号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