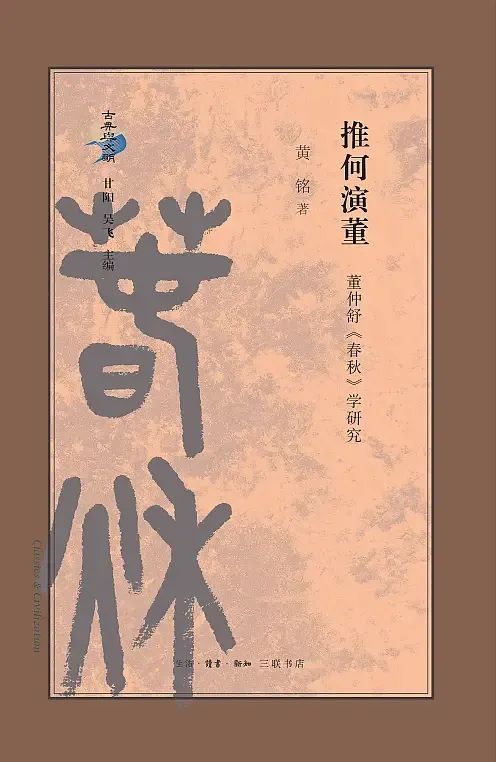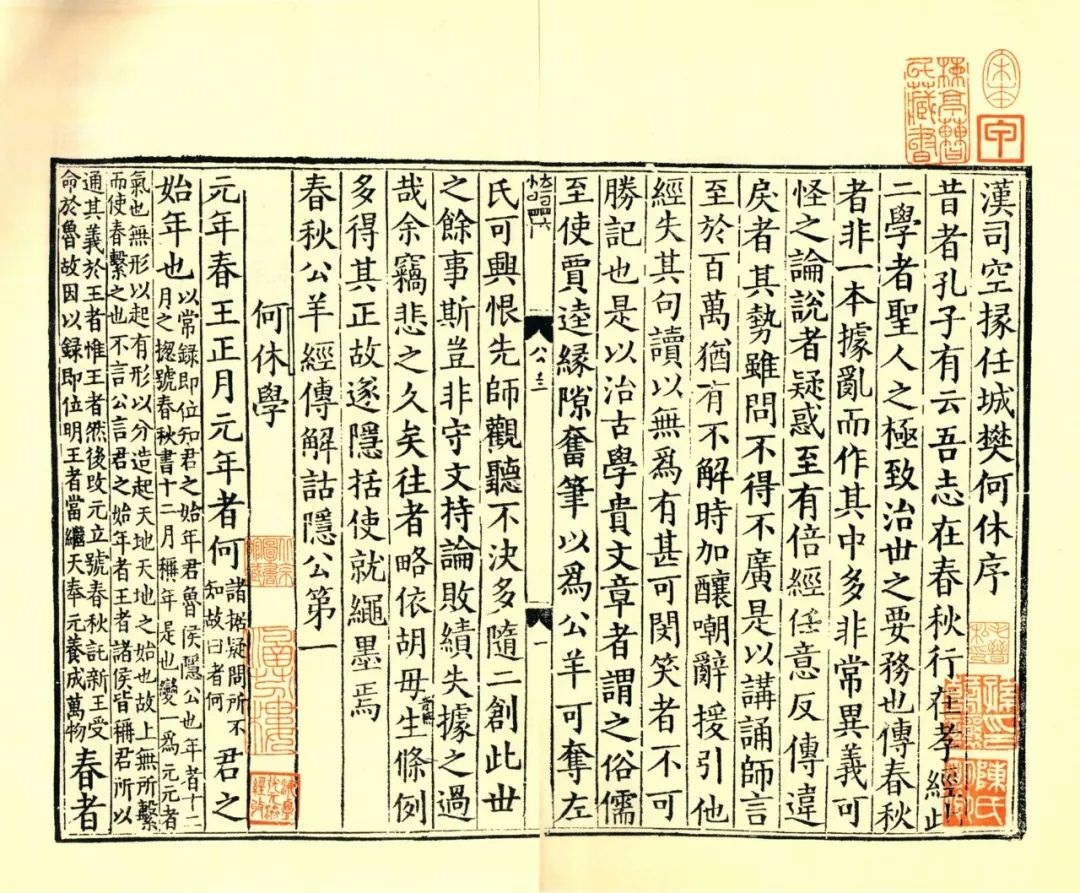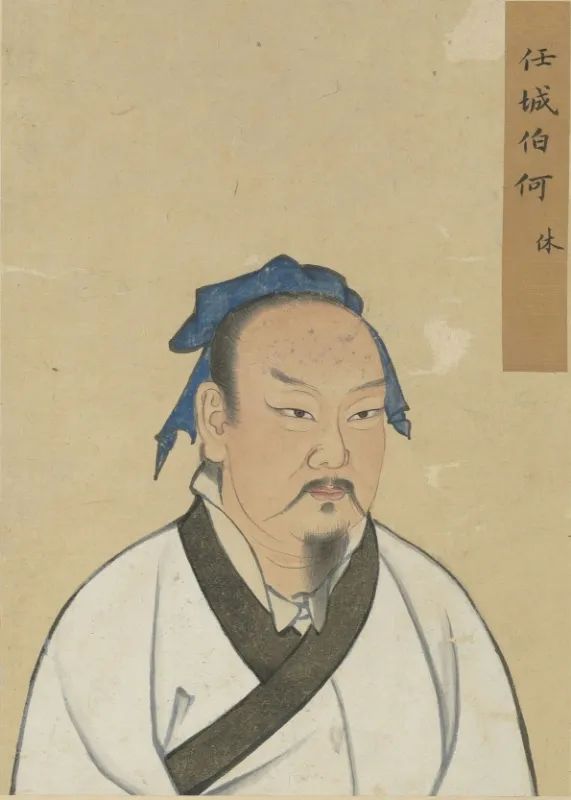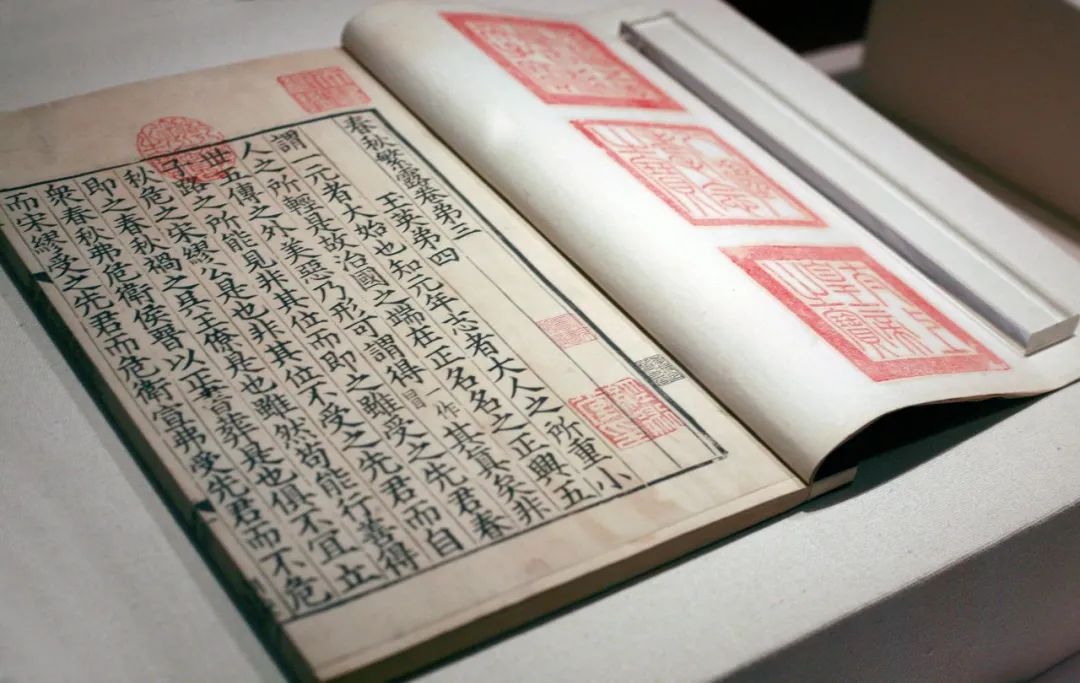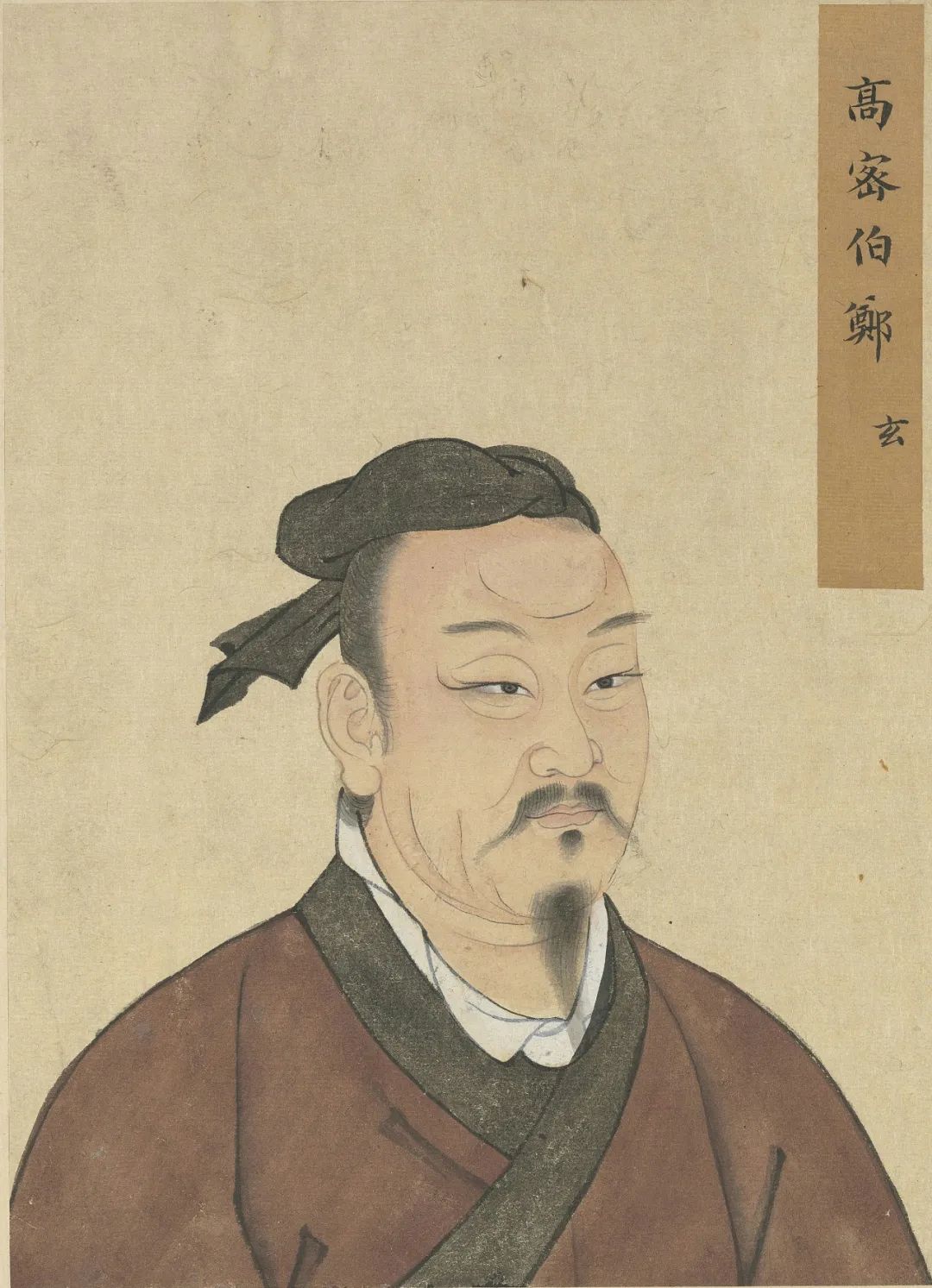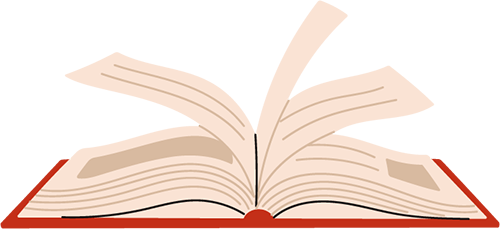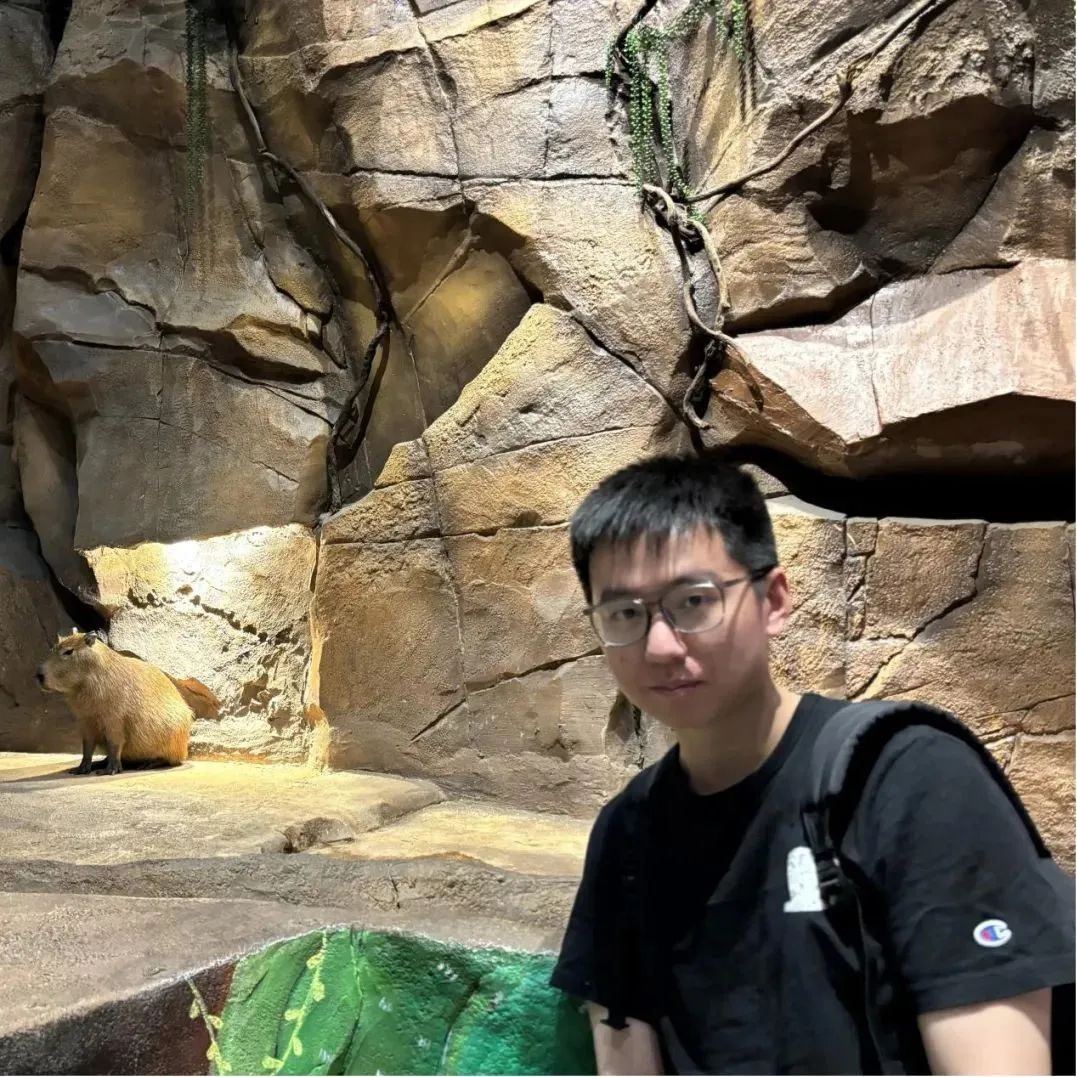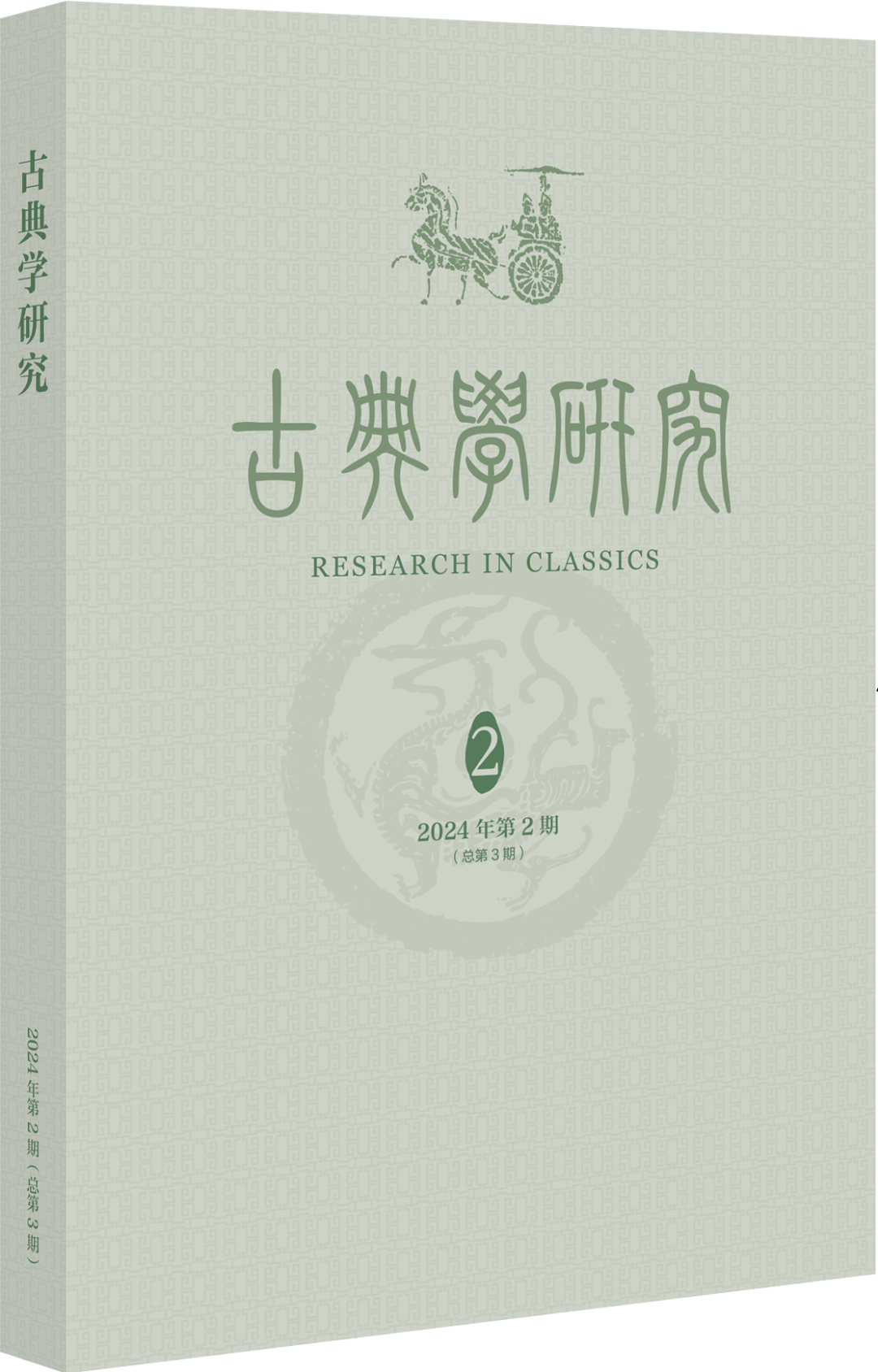本文刊于《古典学研究》2024年第2期(总第3期),注释从略,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原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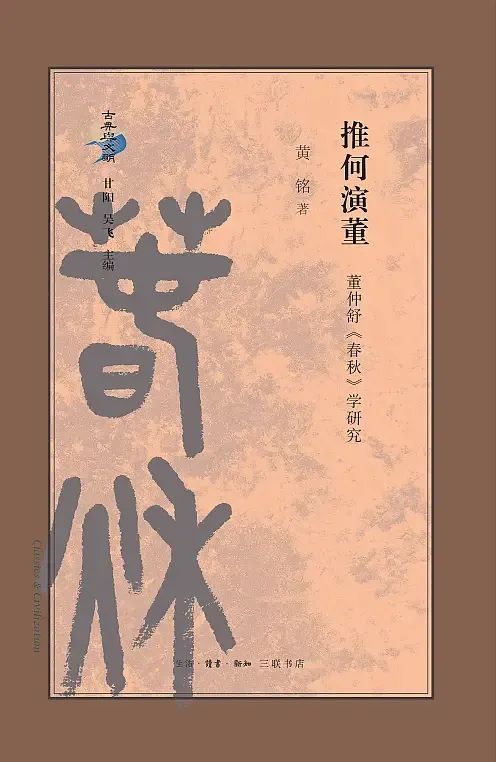
黄铭 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年
今日该如何理解董仲舒?司马迁的《史记·儒林列传》至少给出了最明确的提示:“董仲舒,广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所以,不管从什么角度阐释董仲舒思想,都不应该忽视董仲舒的《春秋》学。这一点也在董仲舒的两种重要著作中得到印证,无论《汉书·董仲舒传》的“贤良对策”还是《春秋繁露》,都包含对《春秋》的大量解释和发挥。董仲舒的《春秋》学是什么,黄铭于2013年在复旦大学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董仲舒春秋学研究》回答了这一问题。十年后论文修改出版,是为《推何演董: 董仲舒〈春秋〉学研究》(以下简称“《推何演董》”)。
尽管《史记》提到董仲舒和《春秋》关系密切,但在前贤的董仲舒研究中,《春秋》学得到关注却是非常晚近的事情。直到清代,方有董天工、凌曙、苏舆为《春秋繁露》作注,庄存与、康有为等在研究中重视董仲舒。康有为的《春秋董氏学》将董仲舒《春秋》学作为维新变法的理论依据,并因此产生了极大争议,如苏舆的《春秋繁露义证》从公羊学内部提出了对董仲舒的不同理解。此后不少现代学术著作也探究了这一议题,《推何演董》对此已有总结。但到底该“以何解董”,仍旧是一个方法上含糊不清的问题。

▲ 董仲舒(前179―前104)
这个问题应分解为两步。第一个问题实质上是如何阅读《公羊传》,其次才是在公羊学的基础上尝试定位董仲舒的《春秋》学。职是之故,东汉经学家何休的《春秋公羊解诂》就显得异常重要。何休的《解诂》是流传至今最早且唯一完整的《公羊传》汉注,而且《解诂》的核心特点是参考运用了西汉公羊学先师胡毋生的条例之学。可以说,正是因为何休《解诂》的存在,后学系统解读《公羊传》才成为可能。唐代的孔颖达曾形容“礼是郑学”,若借此为喻,公羊学亦不妨称为“何学”。这样也就理解了,为什么明明是研究西汉人董仲舒,却不得不从东汉人何休入手。《推何演董》非常鲜明地采取了这一进路,“以何解董”的答案正是“以何解董”,于是“推何演董”跃然成为著作的标题。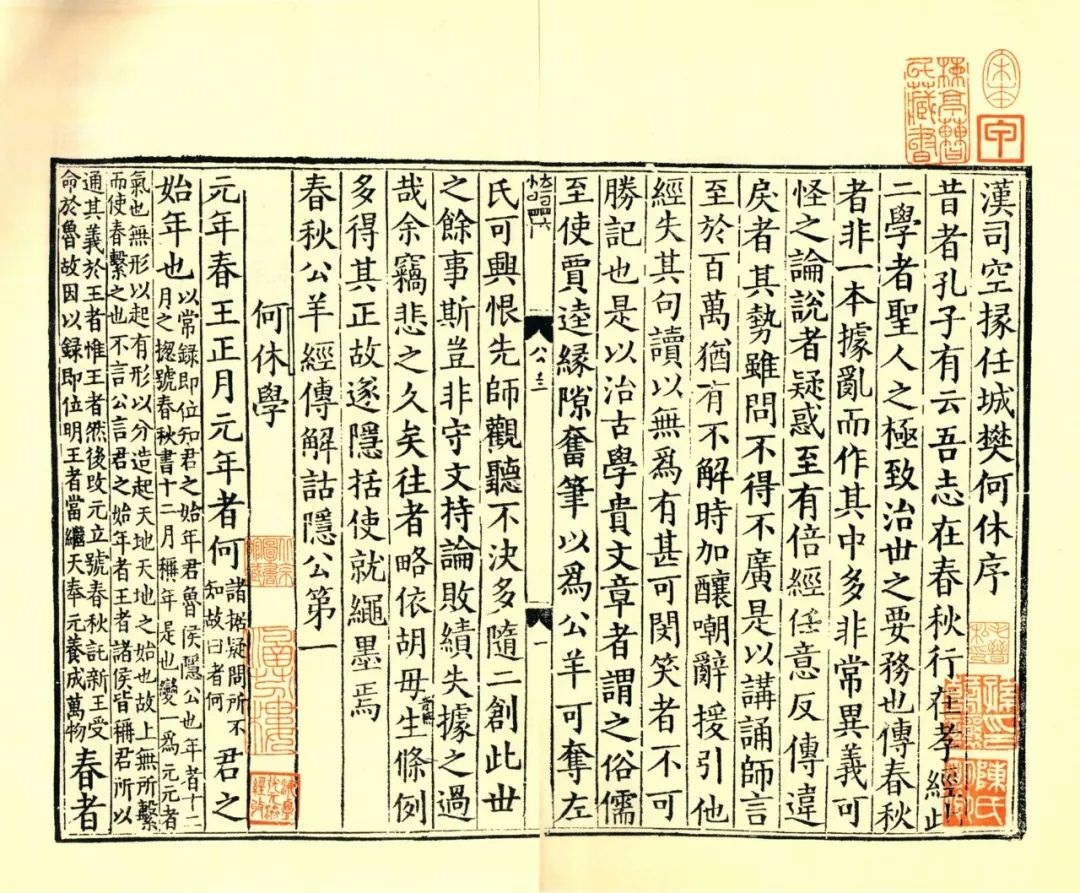
▲ 何休《春秋公羊经传解诂》书影
宋淳熙抚州公使库刻绍熙四年重修本(中华再造善本)
清中叶以降,随着今文经学的复兴,汉代经师的家法、条例受到学人们的重视。庄存与的《春秋正辞》总结了九种“辞”,刘逢禄的《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提炼了三十条“例”,段熙仲的《春秋公羊学讲疏》更加全面,分为“比事”“属辞”“释例”“义”四类,这三部著作成为后学系统解读《公羊传》的典范。段熙仲还特别区分了哪些解释来自《传》文,哪些解释分属董仲舒、何休,初步对比了两位公羊学先师的学问。在今人的研究中,余治平充分总结了董仲舒《春秋》学的“义法辞”。《推何演董》踵武上述前贤的公羊学研究进路,以总结董仲舒的《春秋》学。《推何演董》的梳理包括如下内容:
以“辞”为方法论,“天”为哲学基础,“微言”讨论改制,“大义”讨论让国、经权等问题。
正如《礼记·经解》说“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推何演董》首先界定了“辞”“事”“义”三者的关系,并探讨了“因辞见义”和“因辞起事”的重要性(页31-41)。《春秋》鲁史,以辞记事,传达史实,并没有特别的深意,而且《春秋》又是编年史,诸多史事首尾难以连贯,故董仲舒说“《春秋》无通辞,从变而移”,“《春秋》无达辞”,但孔子笔削,赋予大义,这称为“属辞比事”。比方说,“常辞”表示使用常规的言辞记载史事,但是,倘若同样一件事在记载时没有依照“常辞”,这便能引导读者探索为什么会出现书写上的不同,理解史官的用意。所以孔颖达解释“比事”为“比次褒贬之事”,“比事”即排列史事后对比言辞书写的差异,由此分辨褒贬之别。除了“常辞”,《公羊传》还有“例”,“例”可以理解为书写的法则、范例,《推何演董》认为“常辞”“正例”是同一个意思(页39)。不过,从段熙仲的解释来看,“例”的内涵应该更宽泛一些,因为“例”包含了“常事不书”,表示《春秋》不会事无巨细地记载所有史事,常规事件按照惯例一般都会发生,那么就不需要专门记载说明,这也是一种“例”。通过“属辞比事”和条例,《公羊传》为《春秋》提供了一套解经系统。要理解董仲舒的《春秋》学乃至全部学问,第一步无疑是探索董仲舒会怎样使用这一套系统,而参与编辑这套系统的正是何休。“推何演董”的方法便体现在,读者需要先行理解经传已有的相关内容是什么,何休又会如何解释,那么董仲舒采取什么样的方法、态度就能够对比探究了。《推何演董》最后还总结了董仲舒、何休在解经上的差异(页290-332)。可以说,《推何演董》不仅是一部关于董仲舒的研究,同时完全可以视作《公羊传》本身的导读。“推何演董”的意义不限于梳理董仲舒的《春秋》学,还为今日重新理解中国传统的《春秋》学提供了方法。如所周知,《春秋》的解释本就有《公羊传》《谷梁传》和《左传》三家,三家的解释各不相同,以何者为准,以及该怎样看待这些解释,在传统经学中本就存在大量争议。这不光是如何解释文本的问题,不同时代《春秋》学的背景又很不一样。
关于“微言”“大义”的定义,《推何演董》直接采用了皮锡瑞的说法,“微言”用于“改立法制以致太平”,“大义”用于“诛讨乱贼以戒后世”。曾亦认为,康有为以“孔子改制”为《春秋》“第一微言”。如果说此处对“大义”的定义还算准确,那么将“微言”完全等同于“改制”,恐怕只是皮锡瑞、康有为的一家之言。不过,这并不代表《公羊传》和董仲舒完全不言改制。《推何演董》分析了一个典型案例:《春秋》桓公十一年,“郑忽出奔卫”。此处的“郑忽”实为当时的国君郑昭公。由于其父庄公刚下葬不久,尚未逾年,按照《公羊传》总结的名例,“既葬称子,逾年称公”,本应称郑昭公为“郑子”,以示“嗣君居丧期间,应尽子道,不忍当父之位”(页196)。但是,“《春秋》改制,用三等爵,将周制的伯、子、男合为一等”,称“郑子”不能体现“既葬称子”之意,“只好通过称名来体现丧贬”(页196)。按照董仲舒的理解,《春秋》如此改制的依据是文质论,周代“制爵五等”,尊卑分明,属于“尊尊而多礼文”;《春秋》为了克服周制等级森严的弊端,“制爵三等”,注重人情,属于“亲亲而多质爱”。按吴飞先生的说法,概言之:“质家亲亲,更看重自然亲情;文家尊尊,更看重宗法嫡庶。”条例、“属辞比事”“微言大义”都说明《春秋》不是“断烂朝报”和单纯的客观记录,也不能轻易认为《春秋》只是在历史事件上简单地添加一些褒贬式的价值判断。康有为推崇《春秋》改制,引起了守旧派的激烈反对,但即便像苏舆从公羊学出发反对改制,也不得不承认“制度之可改”这层意思。不论是否承认《春秋》改制,《春秋》至少包含了对秩序与历史演进的阶段性理解。《推何演董》细密地梳理了其中的内容,如改制的三个层面为“受命应天”“救衰补弊”“改制而不变道”,包括与正朔相关的“三正”,与王朝相关的“三统”,与制度相关的“三教”和“文质”,以及改制的合法性问题“王鲁”(页198-233)。《春秋》本是鲁史,而就像《周易》不只是卜筮之书,三《礼》不只是仪式之书,《春秋》也不仅仅是鲁史。但是,鲁史恰恰又是《春秋》最为典型的形式和特征,任何“微言大义”皆由“史”而传达。章学诚直言“六经皆史”“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刘咸炘认为“史”不只是事件和制度,而是体现了“彰往而察来”的“史之原理”,这些都提醒不可小觑“史”本身的意义。此即《推何演董》提到的改制的第三个方面“改制而不变道”,董仲舒称为“王者有改制之名,亡变道之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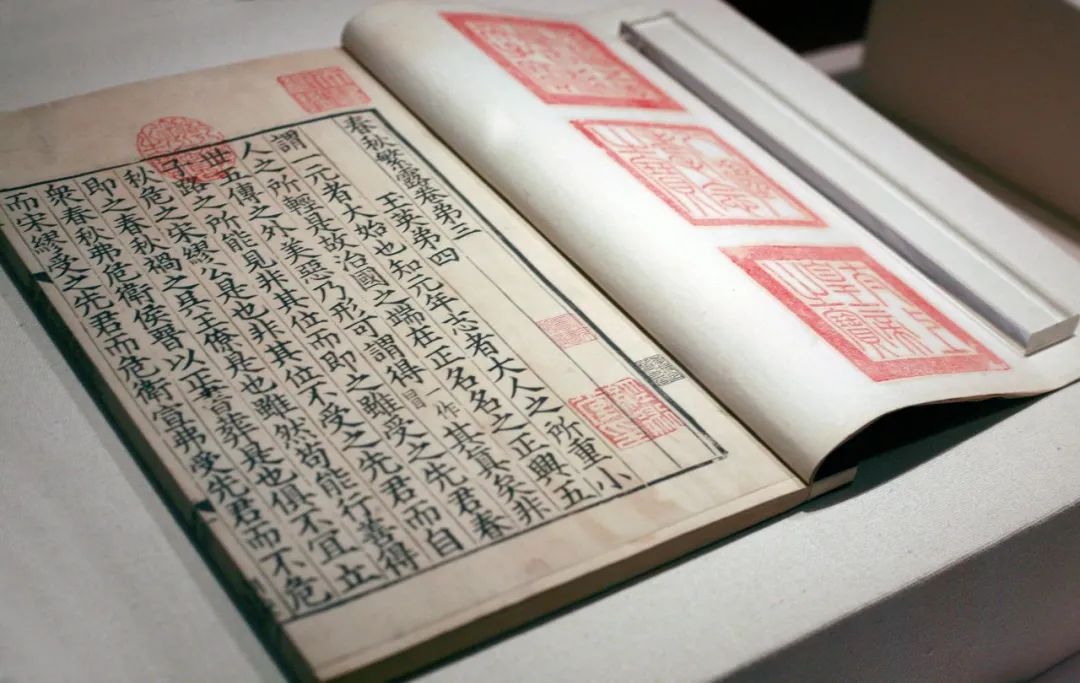
▲ 董仲舒《春秋繁露》书影
宋淳熙抚州公使库刻绍熙四年重修本,中国国家图书馆 藏到底该如何来理解“改制”与不可变之“道”之间的张力,《推何演董》并没有直接阐述这一问题,但对“三正”“文质”“辟秦”“《春秋》决狱”等内容的论述皆与此有关。汉儒对自身的定位和使命的理解来自于对历史的理解(页233-239)。“《春秋》决狱”并非将经书视为具体法律背后的绝对准则,而是在历史演进的“文质”循环中,以“尚质”作为经义法典化的取向,这同样来自董仲舒对历史的理解(页289)。“历史”不是客观事实,而是人面对时间流变的历史感或历史意识。不可变之“道”并不是抽象的、绝对的道德律令,或者历史演进的终点,却始终有赖于人在历史的变动中持续不断地努力把握。《礼记·大传》总结了“亲亲”“尊尊”等“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但这些原则怎样在历史演进中体现,在历史不同阶段各有何侧重,以《春秋》为代表的中国史官、史学传统,太史公所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都是对这些问题的探索。这可能是董仲舒、何休的《春秋》学今后值得关注的面向。
回到开头提出的问题,今日该如何理解董仲舒?董仲舒思想的学术基础是《春秋》学,这当然不可忽略,但《推何演董》更多地是在回答董仲舒如何阅读《公羊传》,还不能说已经完整呈现了董仲舒的《春秋》学体系。从现有研究来看,董仲舒思想常常与“天人合一”“阴阳五行”“独尊儒术”“灾异”“公羊学”等关键词相关。《推何演董》并非没有注意到这些,而关注点依旧是《春秋》学,比如以《春秋》中“大一统”的“灾异”作为“天的政治哲学”(页110)。这虽然揭示了董仲舒“天”哲学的《春秋》学基础,但显然不能说完成了对董仲舒思想体系的整合。以上关键词虽然颇为形象地为董仲舒思想贴上了标签,但也未统合为一个完整的体系,这不仅涉及如何理解董仲舒,也是对《春秋》学本身的追问:《春秋》为什么可以成为董仲舒构建思想体系,参与汉代政治的学术依据?《春秋》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体系?
《推何演董》指出了回到《春秋》学的必要性。“天”哲学与《春秋》“大一统”和“灾异”有关,“独尊儒术”也关联于“大一统”,“阴阳五行”涉及对天道运行变化的理解,这也表现为“史之原理”,总之,这些都可以为董仲舒基于《春秋》建立的历史观所吸收。这让人不禁想问,《春秋》看上去明明只是一部散乱的编年史,凭什么能在中国传统中担当这样的理论重任?董仲舒以《春秋》学为基础,深度参与了汉代礼法制度、经学体系和思想形态的建立,这些内容铸就了汉唐盛世的制度基础,更是对中国古代政教制度有奠基性意义。经学必定与礼法制度相辅相成,礼法制度不得不依靠经传注疏而建立、完善,经传注疏则揭示了礼法制度背后的义理基础。不管是探讨董仲舒如何读《公羊传》,还是从学科专业的角度剖析其思想,也许都还没有完全揭示董仲舒在政教制度上的作用和意义。此外,礼法制度、经学体系和思想形态的建立是一个跨越汉魏六朝的漫长过程,并非一蹴而就。那么,在儒家经典和众多经学家中,《春秋》、公羊学还有董仲舒分别处在什么样的位置?这是《推何演董》遗留的难题。相对来说,如今的研究已经关注到与何休同处东汉的另一位经学大家郑玄,郑玄经学的面目开始清晰起来。比如,郑玄以《周礼》为纲统摄群经,尝试构建统一的经义和礼制,其《丧服》学精义更是受到张锡恭的重视。这进一步带来两个问题。第一,在公羊学内部该如何理解董仲舒与何休的差异?《推何演董》从两者对《春秋》的解释出发,概括为“董、何纯粹师法之异”,董仲舒属于“以义解经”,何休属于“以例解经”(页332)。董、何处在汉代不同的历史阶段,二人的差别是否只是解经之异?第二,在经学内部如何理解何休与郑玄的不同?倘若二者的区别是《春秋》学和礼学的差异,那这种经学内部的差异又意味着什么?这些差异不在于今古文派别或解释路径的差异,而是体现众多学者对文明理想、历史演进、秩序建构、制度设计等问题的不同思考。从这些议题入手,才有可能打破学科专业的限制,真正理解经学在为中国古代政教制度奠基时所发挥的体系性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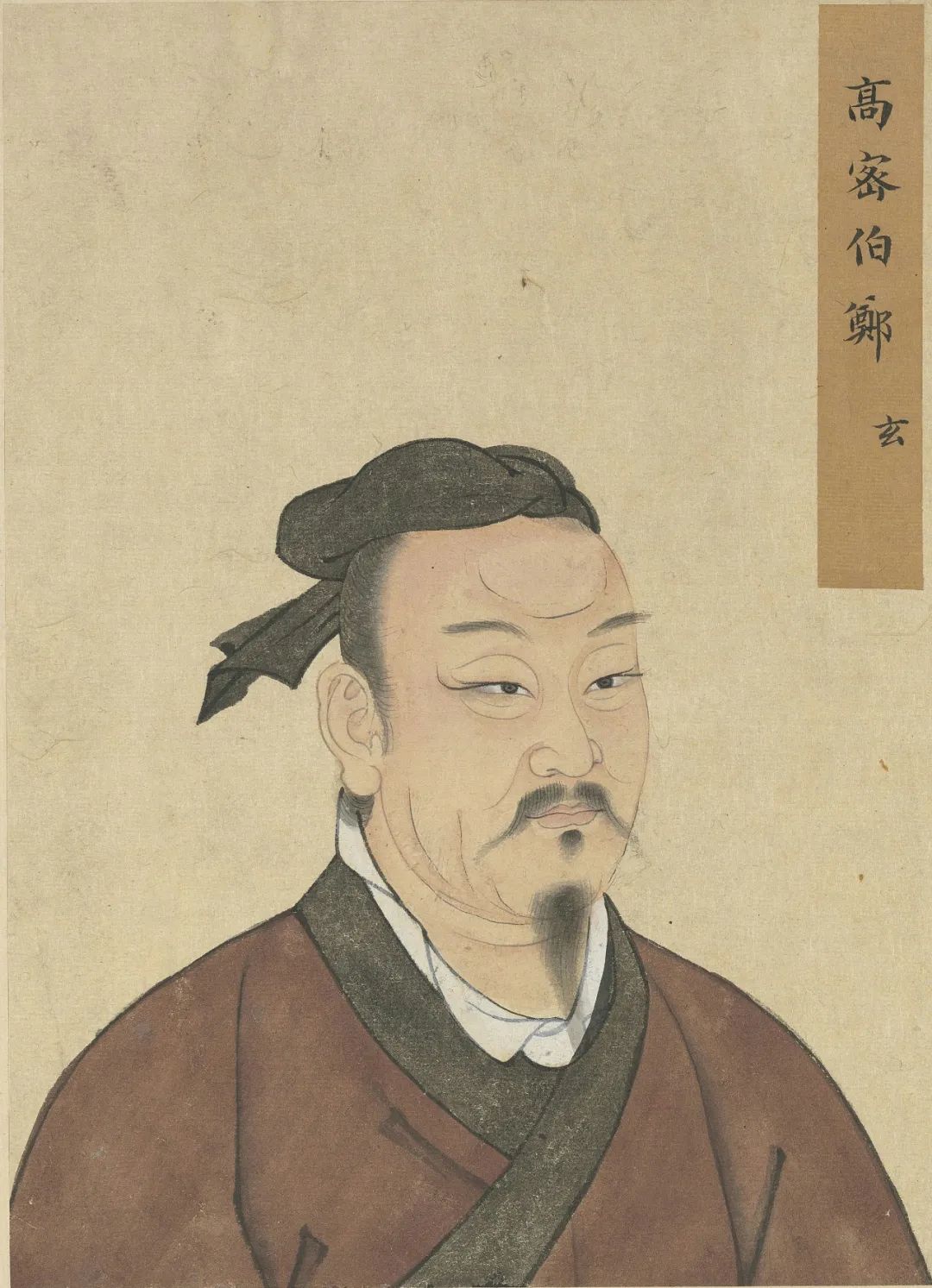
▲ 郑玄(127—200)
此时再来看“属辞比事,《春秋》教也”这句话,重点可能不在于说明《春秋》以辞记事的特点,而是“属辞比事”这样的史官传统何以能成为文明之“教”。在这个意义上,董仲舒的体系应该是以《春秋》学为基础,延续先秦的史官传统,融贯春秋战国时期关于天人关系、阴阳五行的探讨,构建了一套基于《春秋》的历史观,为中国早期建立“大一统”之政教制度提供了体系高度的文明构想。这一构想是什么样的体系,之后获得了怎样的发展,董仲舒、何休的《春秋》学与其他经学的分歧何在等等问题,在未来当还有进一步展开的空间。
雷天籁,华南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特聘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哲学、经学、比较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