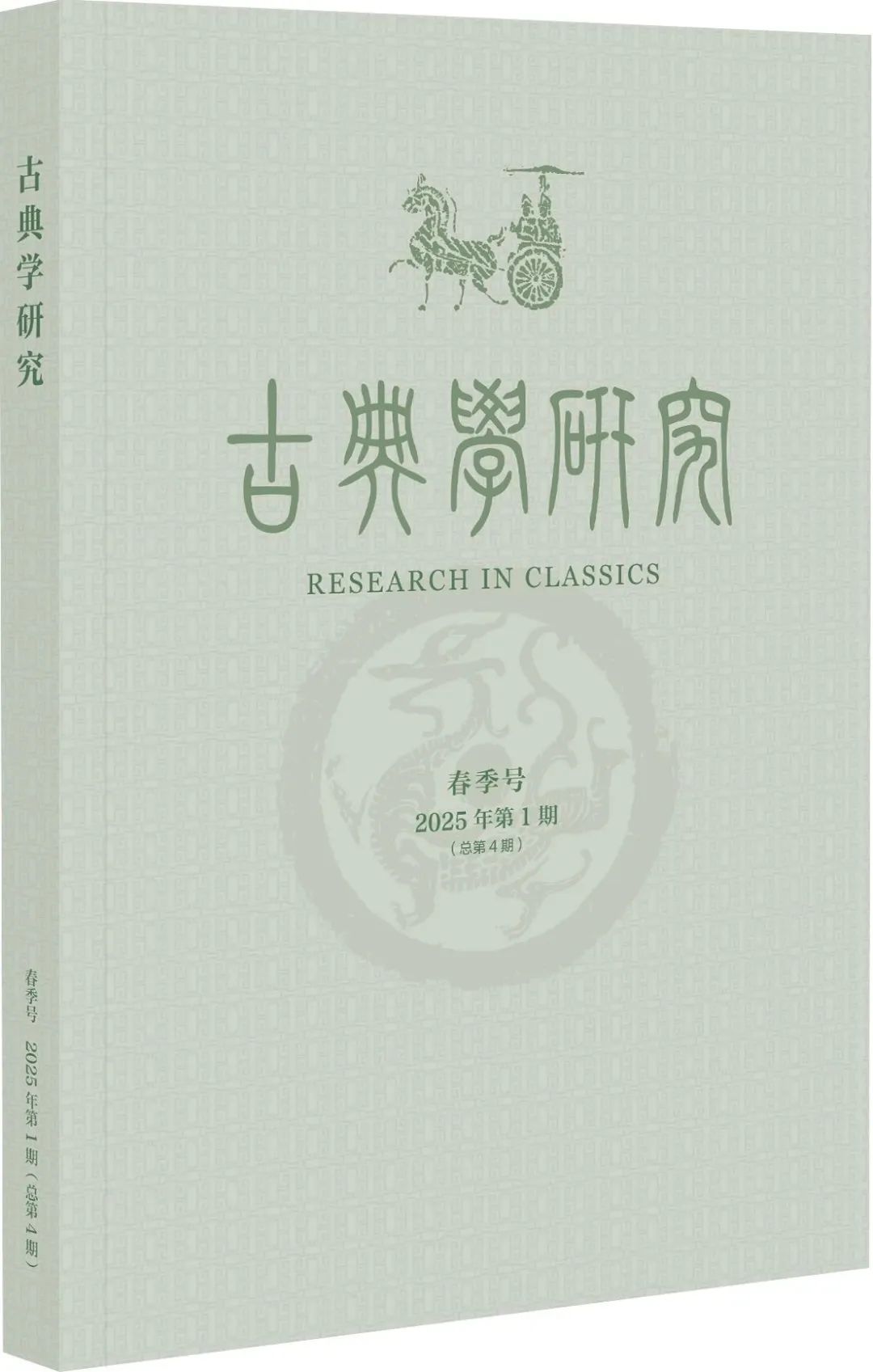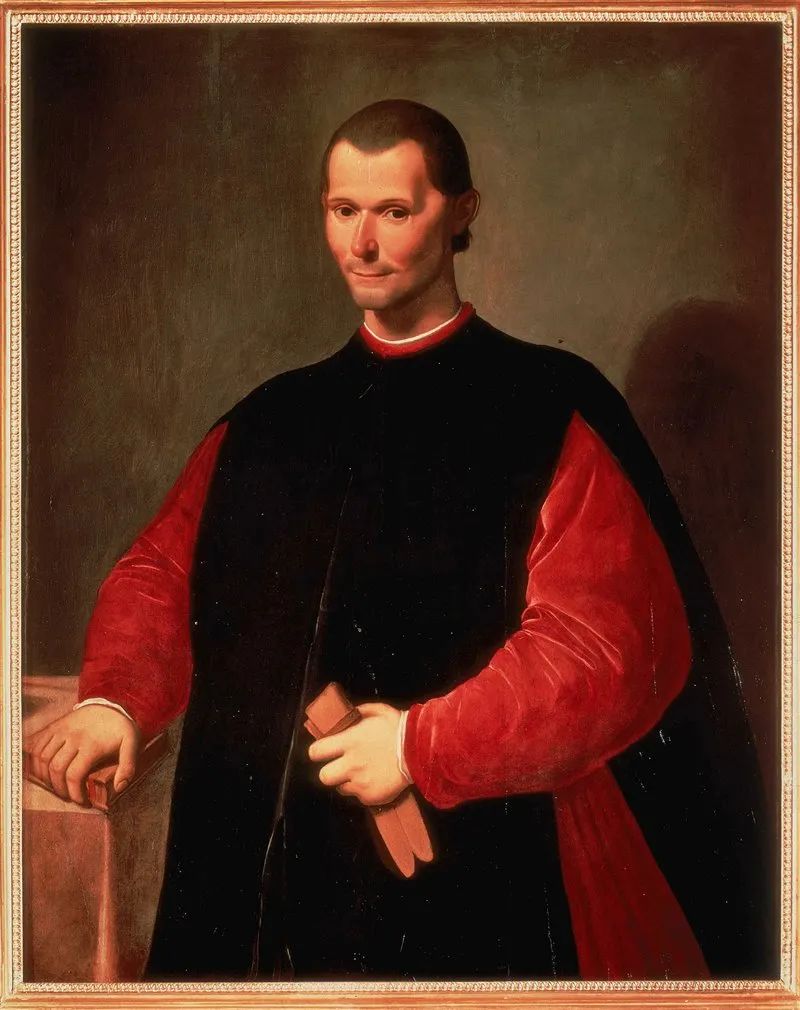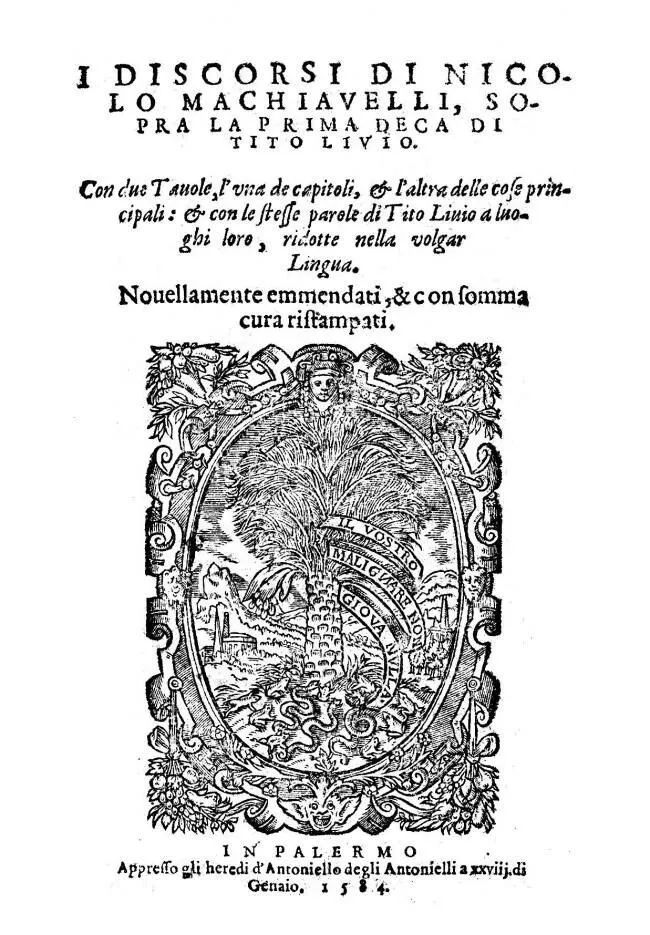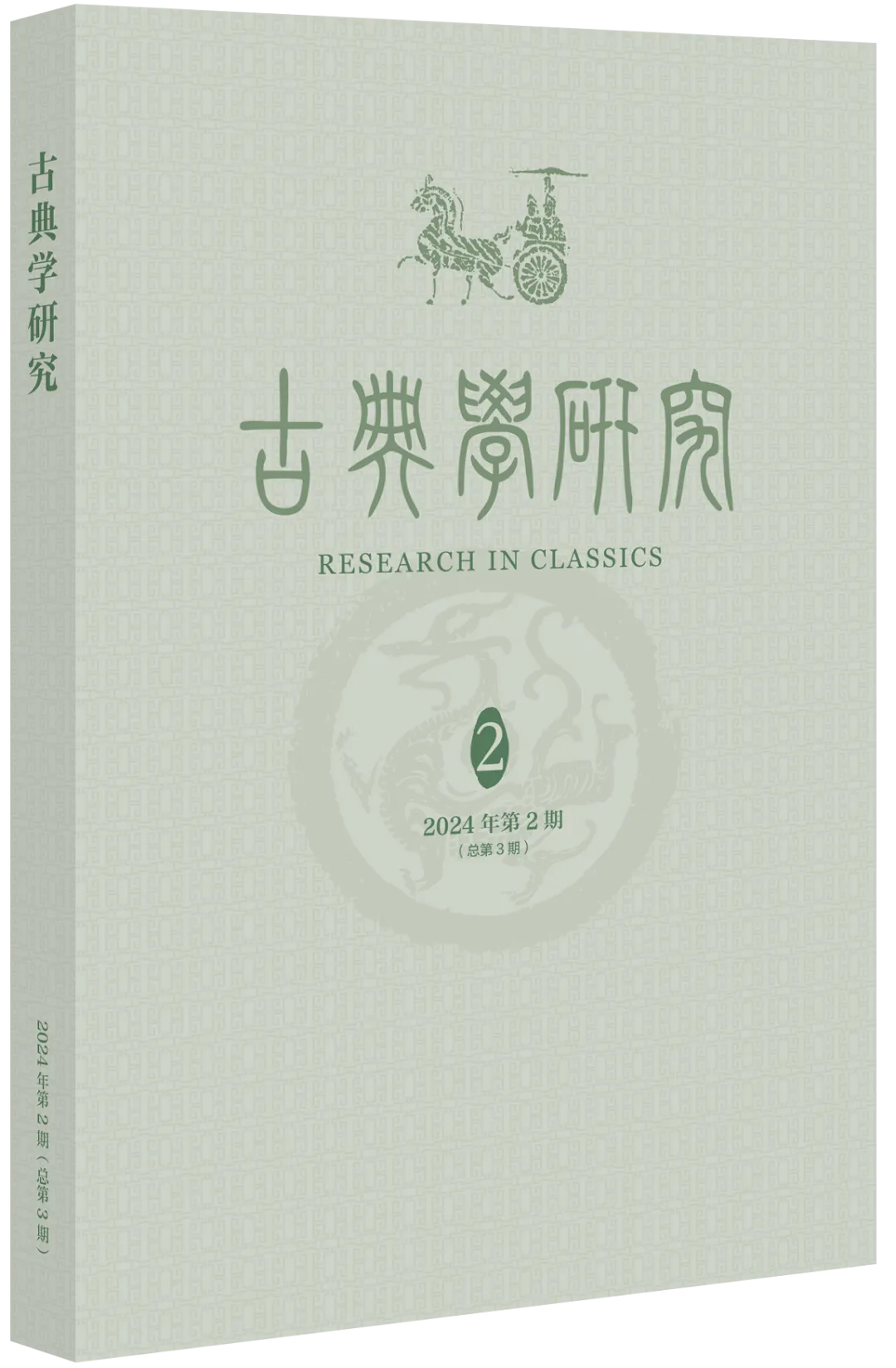本文刊于《古典学研究》2025年第1期(总第4期),注释从略,感兴趣的读者可查阅原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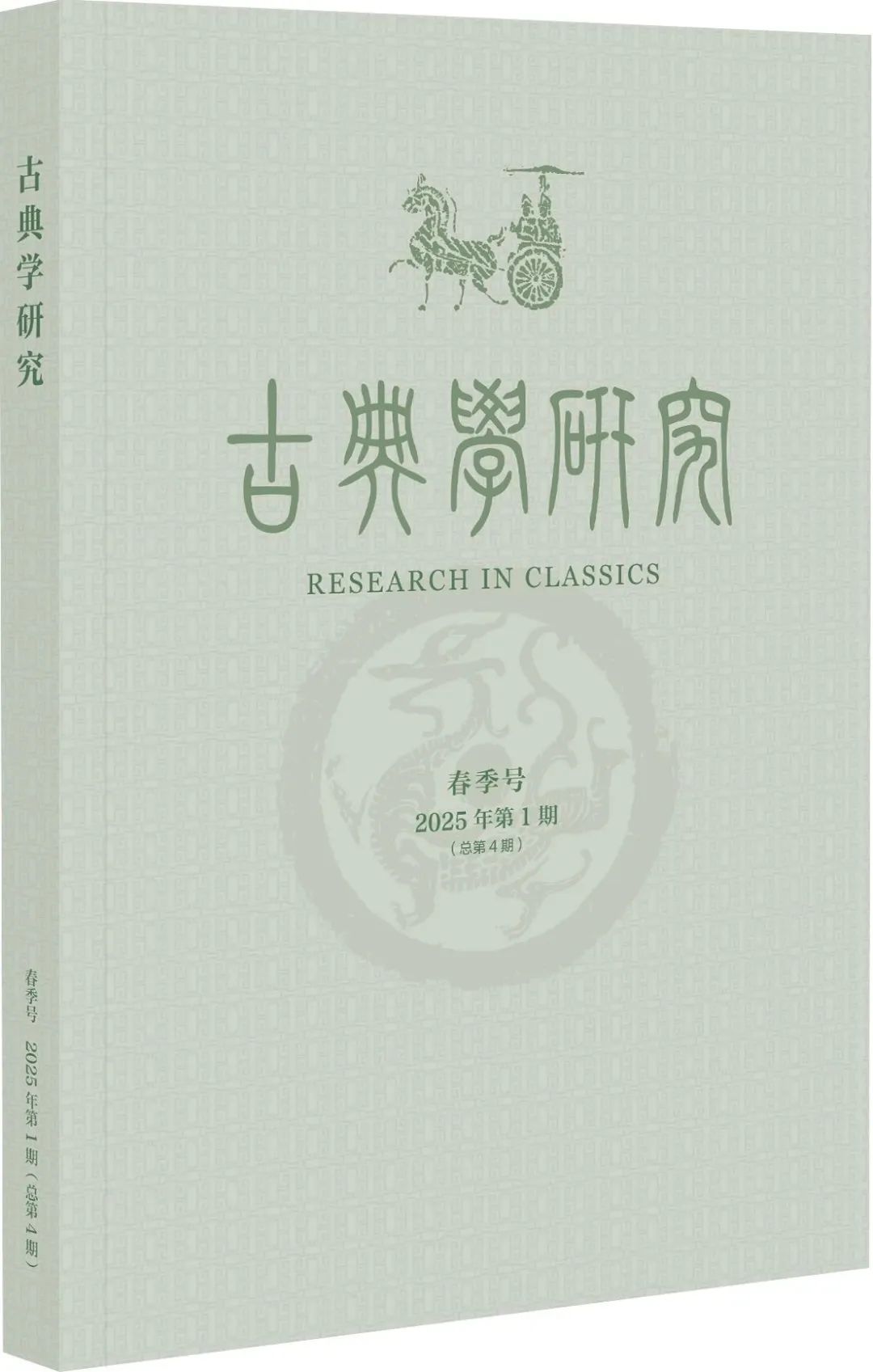
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中的小福丁布拉斯,颇为符合马基雅维利笔下的“新君主”形象。全剧结尾时,他借助由民众组成的军队入主丹麦,成为政治赢家。这一结局表明,《哈姆雷特》是对马基雅维利《君主论》的回应。莎士比亚意识到,在现代政治舞台上,民众逐渐展现其巨大力量,突破道德约束的新君主仍需要在表面上维系道德形象,以获得民众的支持。但是,莎士比亚未必认可马基雅维利对政治道德的贬低。在莎士比亚的现代世界图景中,道德没有彻底在政治面前失去尊严。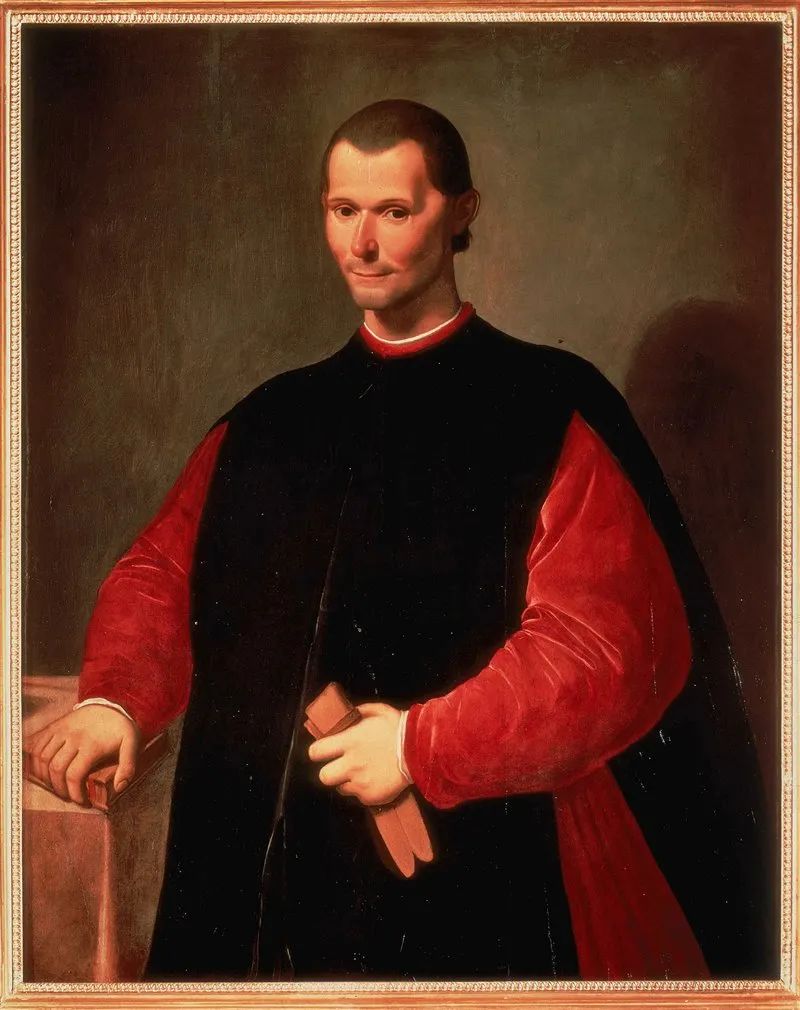
▲ 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1469—1527 )在《哈姆雷特》中,莎士比亚通过剪裁和加工诸多原始底本,重新讲述了哈姆雷特向叔父克劳迪乌斯复仇的故事。全剧情节可分为一明一暗两条线索。哈姆雷特的复仇筹划以及内心挣扎是全剧的明线,主要展现哈姆雷特的内心纠葛,著名的“延宕”问题就在这一层面上展开。但在解析该剧时,也绝不可忽视哈姆雷特的政治身份:他是丹麦的王子和未来的君主。如雷欧提斯所说,哈姆雷特时刻受其身份支配,其决定会影响整个王国的安危(1.3)。剧中的其他主要人物如克劳迪乌斯、小福丁布拉斯等,也都是重要的政治人物。政治动荡和权力变迁,构成整部《哈姆雷特》的暗线。莎士比亚在全剧最后一场揭示了这一暗线的结局:随着丹麦王室凋零,挪威王子小福丁布拉斯率军接管丹麦,使国家易主,而他也实现了其父老福丁布拉斯生前的夙愿,成为丹麦的新君主。小福丁布拉斯的政治功业甚至超过了剧中以善于征伐著称的丹麦先王老哈姆雷特:后者不过占据了挪威部分领土,前者则吞并了整个丹麦,将挪威和丹麦合而为一。
▲ 《哈姆雷特》首页,莎士比亚剧作集第一对开本,1623年
关注这一线索的学者认为,《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亚对马基雅维利的回应。的确,在莎士比亚时代,马基雅维利的小册子《君主论》颇为流行。莎士比亚的早年剧作《亨利六世》(下篇)的剧中人物理查就提到过马基雅维利,而在剧情顺承《亨利六世》的《理查三世》中,这位理查已经被塑造为马基雅维利式的君主。所谓“马基雅维利式的君主”指的是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公开推崇的新君主,他能够创立“新的方式与制度”,并“依靠他人的武力或君主自己的武力”获得领土。新君主的登场往往代表着全新政治秩序的创立,为此他必须扫清旧势力,而这也意味着过去时代的道德、习俗和宗教不再能约束新秩序的创制者。当情势确有需要时,新君主可以运用违背习传道德和宗教的非常手段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马基雅维利笔下的切萨雷·博尔贾(Cesare
Borgia)以雷霆手段处死副将并曝尸广场,让民众在感到“痛快淋漓”的同时又“惊讶恐惧”,就是典型的例子。马基雅维利还教导说,显贵在性情上追求压迫他人且很难讨好,而民众在性情上仅仅追求不被他人压迫,新君主应该联合民众压制显贵(《君主论》第九章)。因此,马基雅维利建议新君主应该尽量不违背民众的道德或宗教信条,即便要做不道德的事,也应该让民众相信自己是既道德又虔诚的统治者。如果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有意回应马基雅维利,那么,他就理应臧否马基雅维利的这两条建议,即新君主应凭靠人民来夺取政权,并且新君主必须为此对习传道德和宗教持表里不一的两面态度。在莎士比亚的这部剧作中,我们不难看到,诡计和阴谋取代了传统的英雄美德,卑劣取代了崇高。用哈姆雷特的话来说,“时代失了序”,人们有理由期待出现一位新君主来整饬秩序。那么,莎士比亚笔下的新君主又是怎样的呢?他会是马基雅维利式的君主吗?
《哈姆雷特》的剧情围绕宫廷展开。除了第四幕第四场外,全剧各场均发生在宫廷之中或附近。剧中主要人物要么是王室成员,要么是朝臣和宫廷侍从,他们无不与丹麦王权有密切关系。在有些莎剧中(如《理查三世》《裘力斯·凯撒》),我们经常能够听到民众的声音。而在《哈姆雷特》中,莎士比亚只吝啬地给民众分配了一两句台词:“不,让我们进来。……好,好。”(4.5.113–114)在第四幕第五场,雷欧提斯得知父亲横死且草草入殓后,从法国潜回丹麦,愤怒地带领民众冲击丹麦宫廷。侍臣报告说,这群“暴徒”(rabble)称雷欧提斯为主上,要推举他做国王,“就像世界还不过刚才开始一般,他们推翻了一切的传统和习惯”(4.5.103–104)。在民众的迅猛攻击下,克劳迪乌斯花费重金请来的瑞士雇佣军不战自溃。在这里,我们第一次在本剧中见识到了民众的力量,以及依靠民众的力量推翻旧传统和重建新秩序的可能。然而,当跟随雷欧提斯的民众怀着满腔义愤希望进入宫殿时,雷欧提斯用只言片语便阻止了人民,而人民也唯唯诺诺遵照领袖的指示,退出了宫殿。
虽然这是民众在剧中唯一的正面出场,但莎士比亚已经用直观而富有冲击力的方式展示了民众蕴含的巨大政治能量。当一位领袖人物将人民组织起来时,其战斗力摧枯拉朽,轻而易举就攻克了有雇佣军守卫的王宫。这印证了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的教诲:雇佣军没有忠义之忱,在你死我活的战斗中会一哄而散(《君主论》第十二章)。与此同时,这一情节也表明,民众自身并不是具有主动性的政治力量。即便对丹麦重臣的死亡和草草埋葬有狐疑和不平,若没有雷欧提斯的动员,民众也不会采取政治行动(4.5.81–84)。民众是被动的,他们必须听从领袖的号召(4.5.113–115)。在这一点上,莎士比亚显得认同马基雅维利的洞察。在马基雅维利笔下,没有首领的民众是无用的,他们无法真正有效地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并影响政局。第四幕第五场表明,雷欧提斯对民众颇有号召力,但剧中多处提示我们,真正获得丹麦民众狂热拥戴的不是雷欧提斯,而是哈姆雷特。当克劳迪乌斯决意借刀杀人铲除哈姆雷特时,他意识到哈姆雷特有着他自己无法比拟的政治资本,即深受民众爱戴(4.3.4)。正是出于对民众的忌惮,克劳迪乌斯非但必须将哈姆雷特置于死地以消除威胁,还得避免自己卷入其中,承受民众的反噬。在劝说雷欧提斯向哈姆雷特复仇时,克劳迪乌斯再次提到哈姆雷特深受丹麦民众爱戴。他解释说,正是由于受制于此,他自己才无法直接出面诛杀哈姆雷特,为波洛涅斯讨回公道(4.7.17–25,尤其4.7.19)。雷欧提斯并未反驳克劳迪乌斯,这意味着他承认,丹麦民众对哈姆雷特的爱戴确实形成了一股重要的政治势力。哈姆雷特本人似乎从未想到这一点,不然的话,他可以利用丹麦民众的力量,轻而易举地复仇和夺权。剧中频繁提到民众对哈姆雷特的爱戴,但哈姆雷特本人从未谈及此事。很难想象哈姆雷特对这人尽皆知的事实一无所知,那么,情形就可能是,他并不觉得民众的爱戴对他而言有多么重要,进而也不会觉得,组织民众起来击垮克劳迪乌斯并替父报仇是一个可取的选项。不难设想,若哈姆雷特愿意发动民众冲击王宫,像后世诸多推翻旧秩序的革命者那样,他甚至会比雷欧提斯更加顺利,也更具合法性。哈姆雷特没有这样做,甚至没有想过可以这样做,原因固然在于,他的复仇观受到基督教道德的约束——他相信让罪人永堕地狱,死后受尽折磨,才是真正惩罚凶手。显然,夺取政治权力并不能实现这一目的。但同样重要的原因是,哈姆雷特从来没有把人民看作一股可以依赖和信靠的政治能量。哈姆雷特从一开始就已认定,复仇是自己个人的事情,他必须亲手杀死罪人。即便在终于开始认真考虑复仇计划后,他也完全没有想过利用民众的爱戴。哈姆雷特对民众显得无所住心,因为我们没有见到他对民众品性的评判。克劳迪乌斯则不同,他似乎对民众的品性有清楚的认识:民众不仅糊里糊涂(4.3.4),而且“他们喜欢一个人,只凭眼睛,不凭理智”(4.3.5)。这里的“眼睛”和“理智”对举,不外乎表明民众没有脑子,看事情全凭感官,没有辨识能力。用哲学表述来讲,民众缺乏透过表象看到实质的能力。这一评判当然预设了克劳迪乌斯认为自己能用理智穿透表象,认识到真相。正是基于这一对民众品性的洞识,克劳迪乌斯针对哈姆雷特设下诡计,用天衣无缝的道德表象来遮掩实质上龌龊的阴谋:为了顾全各方面的关系,这样叫他迅速离国,必须显得是深思熟虑的结果。(4.3.7–9)克劳迪乌斯相信,只要借刀杀人之计“显得”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就能骗过民众。换言之,针对民众对哈姆雷特的爱戴,他必须欺骗和愚弄民众,而民众的品性又恰好容易被欺骗和愚弄。值得注意的是,甚至哈姆雷特唯一的好友霍拉旭,对民众的态度也颇为轻慢,因为他是一位学者或哲人。虽然他屡次出场,但我们几乎可以视他为全剧的旁观者,有如古希腊戏剧中的歌队角色,只有言辞和观察,没有行动。相比于剧中的其他政治人物,他出场更早,退场也更晚。第一幕第一场,霍拉旭谈到了老哈姆雷特死后丹麦国内的紧张气氛,以及挪威方面小福丁布拉斯的蠢蠢欲动:现在要说起那位福丁布拉斯的儿子,他生得一副未经锻炼的烈火也似的性格,在挪威四境召集了一群无赖之徒,供给他们衣食,驱策他们去干冒险的勾当,好叫他们显一显身手。(1.1.94–98)霍拉旭蔑称小福丁布拉斯的追随者为“无赖之徒”(lawless resolutes,直译应为“无法无天的亡命之徒”),与后文克劳迪乌斯蔑称雷欧提斯的追随者为“暴徒”并无二致。无论小福丁布拉斯还是雷欧提斯,他们召集追随者组成队伍,显然并非当时最常见的雇佣军,而应归入马基雅维利所谓“自己的军队”,其兵源只可能是普通民众。或许是出于爱国热忱,霍拉旭颇为蔑视小福丁布拉斯从民众中招募的士兵。然而在第四幕第四场,当小福丁布拉斯和他的军队第一次出现在舞台上时,莎士比亚让我们透过哈姆雷特的眼睛看到,这支军队非但不无法无天,反而军纪严明、士气高昂。应该如何理解霍拉旭的所说与哈姆雷特的所见之间的显著差异呢?如果认为霍拉旭的判断带有偏见,那么就必须承认,民众并非无法无天之徒,由民众组成的军队可以自发形成良好的秩序。如果认为他的判断并无偏颇(从第四幕第五场的混乱情形来看,这种情况似乎更有可能),也仍可推论出,只要民众有了一位得力的领袖,就能克服天性中的各种弊病,形成强有力的组织。这在马基雅维利那里也能得到支持。在《李维史论》中马基雅维利的确说过,民众桀骜不驯或温顺驯服,其实无关紧要。如果民众“没有首领的庇护”,即便性情恶劣也不堪一击。相反,如果民众有了首领,就会成为相当可畏的力量。▲ 马基雅维利《李维史论》,1584年
在《哈姆雷特》描述的政治局势中,虽然民众的声音并不常能被直接听到,与国运相关的决策由君主和朝臣做出,但民众已隐隐然开始逐渐展现出不可小觑的政治力量。君主做决策时,必须考虑民众的感受,否则就有受到冲击的危险。最重要的是,小福丁布拉斯和雷欧提斯的事迹显示,由民众组成的队伍,其战斗力远胜雇佣兵或其他中世纪晚期到近代早期流行的军队形式。可以预见,在小福丁布拉斯治下的丹麦,前者将更彻底地取代后者,而这正是马基雅维利在政治实践和政治教诲中追求的理想。从思想史的维度看,民众在政治舞台上占据越来越大的话语权,乃至统治者需要借助民众的力量和认可才能牢固地掌握政治权柄,标志着现代政治与前现代政治的重大断裂。这样的巨变本不会出现在《哈姆雷特》剧情所处的中世纪盛期,而只可能发生在莎士比亚自己所处的近代早期。在这个意义上,与把哈姆雷特安排在拥有新教路德宗背景的威腾堡大学求学一样,这是本剧中又一处有意设计的时代错置。
本文开篇曾提到马基雅维利对新君主的教诲:新君主应争取获得民众的支持,并借助民众的力量清扫旧政治势力;要实现这一点,新君主有时必须无视道德和宗教的约束,虽然在民众面前,他仍须尽量表现得符合传统道德和宗教信条的规定。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刻画的各位君主,分别在多大程度上符合这一新君主形象呢?在《哈姆雷特》中,共出现了六位君主或君主候选人:丹麦王国的老哈姆雷特、克劳迪乌斯和哈姆雷特,挪威王国的老福丁布拉斯以及现任挪威老王和小福丁布拉斯。不过,实际出场的只有克劳迪乌斯、哈姆雷特和小福丁布拉斯,其他三位要么只有由他人转述的只言片语,要么在剧情开始时就已离世。从代际看,哈姆雷特和小福丁布拉斯属于年轻一代,其他四位则是父辈。在三位没有直接出场的君主中,挪威老王年老体衰,甚至经常无法制衡自己野心勃勃的侄子,他显然与新君主毫无关系。老哈姆雷特和老福丁布拉斯在三十年前曾通过决斗分胜负,他们在这场决斗中既赌上了个人的荣辱和生死,也赌上了丹麦和挪威两国领土的输赢。虽然决斗各有胜负,但这两人无疑属于同一类君主,即传统上以勇武德性著称的君主。老哈姆雷特死后化为鬼魂时全身戎装,就像刚从决斗场上回来一般(1.1.79–94)。在莎士比亚笔下,相比于靠阴谋或策略取胜,决斗显然是更具传统意涵的行为。在《裘力斯·凯撒》中,古典共和派传人布鲁图斯向敌方发起决斗,被干脆拒绝。在《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中,安东尼向更年轻也更狡诈的屋大维提出决斗,同样被一笑置之。在这两部剧作中,提出决斗的布鲁图斯和安东尼与其对手相比,都更老派,也更传统。在后续的战争中,他们都输给了年轻的对手,这表征着传统政治德性的失落,也意味着新秩序取代了传统秩序。在《哈姆雷特》中,从决斗中胜出的老哈姆雷特也可被视为传统勇武精神的代表。他没有死在决斗或战斗中,却在阴谋家手下丧命,这同样表征着传统政治德性的消散。用马基雅维利的话说,两位老王有狮子般的强力,但缺少狐狸般的狡猾。哈姆雷特的脾性与父亲截然不同。父亲刚毅果决,儿子多忧多思;父亲勇武善战,儿子从未上过战场;父亲一生志在为王国开疆拓土,儿子在做决断时却几乎从未考虑过国家的命运。不过,哈姆雷特虽然失去了一大半传统勇武德性,但他颇为执着地追求道德上的完善,多少仍然符合传统君主的理想标准。此外,哈姆雷特身上仍然残留着一些传统勇武德性的孑遗。全剧最后一场,他应允了雷欧提斯的决斗请求,最终死在了决斗中(虽然是死于剑上的毒药)。哈姆雷特之死,以及小福丁布拉斯在他死后为他安排的葬礼,成了全剧的高潮和最崇高的一幕。哈姆雷特虽然在剧中属于新一代,也能够获得民众的爱戴,但他并不懂得如何利用民众来实现政治目的,并且他对道德的追求也妨碍他拥有“狮子”和“狐狸”的能力。

▲ 墓地中的哈姆雷特与霍拉旭
如何在马基雅维利的君主分类中定位克劳迪乌斯,容易引起混淆。一种常见的误读是,基于克劳迪乌斯在政治斗争中不择手段而把他归入新君主一类。确实,克劳迪乌斯与马基雅维利笔下的新君主有相似之处:为了实现政治野心,敢于做极端残忍恶劣之事(弑兄、夺位、娶嫂、暗害侄子)。尤其谋杀兄长一事,容易让人联想到传闻中博尔贾为了成为教宗亚历山大六世唯一的政治继承人而暗杀兄长。但在笔者看来,克劳迪乌斯顶多算半吊子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够不上马基雅维利所谓有能力创立新秩序的“新君主”。首先,如前文所说,马基雅维利心目中的新君主既能在必要时突破道德和宗教的约束,又善于遮掩,以获得民众的爱戴和拥护。克劳迪乌斯做到了前者,但没能做到后者。克劳迪乌斯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始终相当可疑,从来没有获得过民众拥戴。他屡次提到民众对哈姆雷特的狂热爱戴乃是他铲除后者的绊脚石,这也意味着他承认自己无法像哈姆雷特那样获得民众的支持,遑论与之形成联盟。因此,他也无法借助民众的力量来组成“自己的军队”,而不得不依靠不怎么靠得住的雇佣军。其次,马基雅维利谈及新君主时所说的“新”与“旧”,关键在于谁能建立“新的方式与制度”,谁在因循旧的政治模式。固然,新君主有时也得位不正,需要依靠弑亲来获取政治权力,但并非所有以此方式夺权的君主都属于新君主。新君主承担了终结旧时代和开启新时代的使命,而他是否认可民众的力量和有意识地借助民众来夺权,乃是他有别于旧君主的关键区别之一。鉴于克劳迪乌斯鄙视民众且无力发动人民,他注定不可能成为新秩序的创制者。《哈姆雷特》中真正的新君主只有小福丁布拉斯。他十分果断,也足够有野心,志在开疆拓土,且不惜动用与传统战争伦理观念相悖的阴诡手段。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小福丁布拉斯借道丹麦攻打波兰,就是他策划的假道伐虢之计。他最终能控制丹麦,很大程度上也是其处心积虑谋划的结果,而不完全是因为丹麦王室自相残杀。一条证据是:他在前往波兰时,军队相当谨慎(同时也合乎常理)地取道丹麦原野(4.4),而从波兰班师回国时,军队则直扑丹麦王宫(5.2)。即便此时克劳迪乌斯未死,小福丁布拉斯也有绝对的信心,趁丹麦人掉以轻心之机,击破王宫的防卫,控制丹麦王国的中枢。毕竟,由雷欧提斯聚拢起来的“暴民”也能轻松攻入王宫,小福丁布拉斯旗下训练有素的军队与之相比,不知强大多少倍。我们甚至可以大胆猜想,就算丹麦王室没有发生自相残杀的惨剧,他也可能会直接攻打王宫,以实现对丹麦的复仇。他组织民众建立属于自己的军队,又虚与委蛇策划了巧取丹麦的计划,这些都展现了新君主的德性。至于最终由于丹麦王室内乱,他不费一兵一卒就占领了丹麦,则是命运对他的眷顾。这让人想起《君主论》第二十五章的著名论断:命运女神总是眷顾有准备的年轻人。小福丁布拉斯虽然常使用阴诡手段,但他也擅长遮掩,让自己在道德和法理上立于不败之地。小福丁布拉斯在《哈姆雷特》最后五十行才终于出场,而全剧长达四千余行,他的戏份只占整部剧作的百分之一。然而,他在这几十行中的表现,足以充分体现出炽热的扩张野心和权力欲,以及在标榜道德一事上的做戏功夫。来到王宫看到惨烈景象时,他首先的反应是震惊(5.2.348–351),这当然是人之常情。但他很快收敛起情绪,敏锐察觉到这桩惨祸可能让自己从中获得巨大的政治利益。当霍拉旭表示愿意叙述事情原委时,小福丁布拉斯作为现场地位最尊贵者立刻打断了他,然后话锋一转,表示自己也有继承丹麦王位的权利:我在这一个国内本来也有继承王位的权利,现在国中无主,正是我要求这一个权利的机会。(5.2.372–374)小福丁布拉斯所谓的权利,指老福丁布拉斯在决斗中输给老哈姆雷特的那块土地。在当时的情境下,这一说法无疑是在强词夺理。首先,那块土地是在决斗契约中割让的,早已不在小福丁布拉斯所能继承的范围内;其次,即便小福丁布拉斯拥有这块土地的继承权,也不能推出他拥有继承整个丹麦王国的权利。强词夺理背后,反映的是小福丁布拉斯的政治野心,他急不可耐地希望为自己找到一个能够正当夺取丹麦政权的理由。而在此时,霍拉旭甚至还没来得及向他公布哈姆雷特要把丹麦交付给他的政治遗嘱。这意味着,即便没有哈姆雷特的遗嘱为小福丁布拉斯提供正当性,他最终仍会谋夺丹麦王位,并为自己的继位构造法理上的理由。当小福丁布拉斯提到自己准备继承丹麦王位时,霍拉旭秉着哈姆雷特的愿望,希望宣布遗嘱,以定人心。而在这时,小福丁布拉斯再一次打断霍拉旭,并宣布要以军礼来为哈姆雷特出殡:让四个将士把哈姆雷特像一个军人似的抬到台上,因为要是他能够践登王位,一定会成为一个贤明的君主的;为了表示对他的悲悼,我们要用军乐和战地的仪式,向他致敬。把这些尸体一起抬起来。这一种情形在战场上不足为奇,可是在宫廷之内,却是非常的变故。去,叫兵士放起炮来。(5.2.379–387)这是全剧最后的高潮,也是气氛最崇高的段落之一。但读者可能会发现,小福丁布拉斯为哈姆雷特安排的殡仪和做出的评价,都与后者的形象不符。他以军礼让哈姆雷特获得死后哀荣,但哈姆雷特从来都不是一个军人,也从没上过战场。相反,哈姆雷特是长于深宫之中的王子,沉溺在生存还是死亡的哲学沉思中。沉思的哲人与杀敌的军人,两者天差地别。因此,哈姆雷特是否真能当得起如此隆重的军礼,实际上非常可疑。另外,根据小福丁布拉斯的评价,哈姆雷特如果能登上王位,就“一定会成为一个贤明的君主”。这句评价也需要打上问号。从剧中哈姆雷特的表现来看,他几乎不具备任何政治品格,我们也很难想象哈姆雷特式的人物在登基后真能成为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的君主。换言之,小福丁布拉斯此处对哈姆雷特的激赏当属溢美之语,而非公允的判断。事实上,他此前可能从未见过哈姆雷特,遑论根据其实际的才能和秉性做出持中的评价。这是全剧最后的高潮,也是气氛最崇高的段落之一。但读者可能会发现,小福丁布拉斯为哈姆雷特安排的殡仪和做出的评价,都与后者的形象不符。他以军礼让哈姆雷特获得死后哀荣,但哈姆雷特从来都不是一个军人,也从没上过战场。相反,哈姆雷特是长于深宫之中的王子,沉溺在生存还是死亡的哲学沉思中。沉思的哲人与杀敌的军人,两者天差地别。因此,哈姆雷特是否真能当得起如此隆重的军礼,实际上非常可疑。另外,根据小福丁布拉斯的评价,哈姆雷特如果能登上王位,就“一定会成为一个贤明的君主”。这句评价也需要打上问号。从剧中哈姆雷特的表现来看,他几乎不具备任何政治品格,我们也很难想象哈姆雷特式的人物在登基后真能成为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的君主。换言之,小福丁布拉斯此处对哈姆雷特的激赏当属溢美之语,而非公允的判断。事实上,他此前可能从未见过哈姆雷特,遑论根据其实际的才能和秉性做出持中的评价。仔细梳理哈姆雷特与小福丁布拉斯的关系,就会发现两人本应是仇敌。小福丁布拉斯要为死去的父王报仇,如今老哈姆雷特已死,根据父债子偿的逻辑,首当其冲的复仇对象就是哈姆雷特。因此,克劳迪乌斯和雷欧提斯针对哈姆雷特的毒杀计划,不经意间也为小福丁布拉斯扫清了障碍,他也因此得以采取超然的态度来哀悼和赞美刚刚遇害的哈姆雷特。既然仇敌已死,表面上搁置巨大的仇恨和分歧,为死者大唱赞歌致以哀荣,是成熟政治家的惯用操作。在《裘力斯·凯撒》结尾,安东尼和屋大维之于手下败将布鲁图斯是如此;在《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结尾,屋大维之于双双殒命的安东尼和埃及艳后也是如此。无论敌人生前多么可恶,在其死后加以尊崇,都无伤大雅,反而可以展现大度。而在小福丁布拉斯这个案例中,赋予哈姆雷特殡仪和溢美,恐怕还有另一层深意。作为时刻想要向丹麦复仇的对手,他无疑对丹麦国情了如指掌。他应该十分清楚,哈姆雷特在丹麦民众中享有超乎寻常的爱戴和敬仰。因此,如果希望将来坐稳丹麦王位,他就有必要展示对哈姆雷特的崇敬,以获得丹麦民众的好感和支持,哪怕哈姆雷特是杀父仇人之子。全剧结尾处的葬礼,除了展现大度外,恐怕也有小福丁布拉斯试图以此获得丹麦人心的意图。通过全剧结尾处的这一番运作,小福丁布拉斯既掩盖了率军直扑丹麦王宫的真实意图,又占据了道德和法理上的制高点。最重要的是,他用相当低廉的成本继承了丹麦民众对哈姆雷特的爱戴,暂时化解了自己作为敌国王子入主丹麦时可能遭受的巨大民意反扑。与此同时,小福丁布拉斯有野心,也有足够的马基雅维利式的德性(或者说能力)来实现野心。在全剧中,惟有他真正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军队,从而有意识地将民众的支持转化为实际的政治资本。从各个层面看,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刻画的小福丁布拉斯形象,都完美地符合马基雅维利对一位新君主的期待。总之,在这样一个混乱失序、新旧交替的时代,真正重整山河的,并不是对传统道德执念颇深的哈姆雷特,而是小福丁布拉斯这样的新君主。学者们对照《哈姆雷特》及其各种原始底本后发现,小福丁布拉斯这一角色在之前所有的本事中从未出现过。也就是说,这是莎士比亚的原创人物。凭空加入这一几乎完美符合马基雅维利式新君主形象的政治人物,莎士比亚应有其深意。基于《哈姆雷特》的结局,尤其由此展现出的小福丁布拉斯的性情、谋略和成就,我们是否能认为,这意味着莎士比亚至少在这部剧中认同了马基雅维利的教诲?或者说他同意马基雅维利对道德与政治之关系的理解?
▲ 《哈姆雷特》第五幕版画:小福丁布拉入场时的情景
作为现代政治方式的开山祖,马基雅维利认为,在国家的奠基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需要作恶,因而不能完全以传统道德来裁断政治是非。道德失去了前现代意义上相对于政治的优越地位,反而需要听命于政治,甚至被迫成为政治的玩物。与此同时,马基雅维利也强调,政治秩序的稳定无法像前现代的政治哲学家所设想的那样,寄托于自然秩序或宗教秩序,而必须借重于人民。基于这一判断,他建议新君主尽力争取人民的支持,凭此扫清建立新秩序过程中的一切阻碍。这两点即马基雅维利政治哲学中蕴含的古今之变。需要承认,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确实认可了马基雅维利的许多基本判断。在剧中描述的新旧变迁的混乱时代,无论抱有传统勇武德性的老哈姆雷特,还是执着于习传道德的小哈姆雷特,都明显颇为无力。真正有能力重整山河并开创新秩序的,是新君主小福丁布拉斯。这位新君主在道德层面有可疑之处,但他相当精巧地掩饰了自己的野心和阴谋。通过这一安排,莎士比亚认可了马基雅维利的基本判断:在现代世界,能够结束乱局并成为政治秩序担纲者的政治家,应该具有马基雅维利式的新君主品格。▲ 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
但这是否意味着,莎士比亚也认同马基雅维利在他的政治图景中对道德的理解呢?这一问题的答案,就不那么显而易见了,需要分几个层次来回答。首先,如果搁置马基雅维利是不是马基雅维利主义者的争论,只关注莎剧本身,我们可以明确地说,莎士比亚坚决反对马基雅维利主义。在莎士比亚看来,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哪怕取得了暂时的成功,他们在心灵层面和政治层面最终仍会遭受双重的挫败。在心灵层面,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在犯下罪孽后,灵魂陷入挣扎,害怕无法得到宽宥。《哈姆雷特》中克劳迪乌斯的愧疚和祷告就是例证(3.3.36–72)。《麦克白》中的麦克白夫人每晚在梦游中反复洗手,《理查三世》中的理查被噩梦中的幽灵困扰,也是类似的例子。当然,莎士比亚也清楚地意识到,良知对马基雅维利主义者能起到的作用相当有限,克劳迪乌斯、麦克白夫人、理查等人在内心受到愧疚折磨后,并没有幡然悔悟,仍然继续政治阴谋。在政治层面,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们也走向了失败。哪怕克劳迪乌斯没有被哈姆雷特杀死,他也无法抵御小福丁布拉斯的攻击,最终注定会失去权力。莎剧中诸多马基雅维利主义者遭遇的心灵和政治的双重挫败,足以表明莎士比亚对马基雅维利主义的批评,也可视为他对未来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的警示。第二,莎士比亚和马基雅维利都承认,道德至少在明面上不可替代。马基雅维利笔下的新君主意识到,人民仍然重视道德和宗教,因此,新君主为了能与人民形成政治同盟,至少不能公然罔顾道德。《哈姆雷特》中的头号反派人物是背弃道德和人伦的克劳迪乌斯,正派人物则是富有道德感的哈姆雷特,这种安排体现了莎士比亚对道德的认可。第三,在政治和道德的关系上,相比于态度含糊的马基雅维利,莎士比亚更加强调道德的尊严,不认为道德终究会臣服于政治。虽然小福丁布拉斯是政治层面上最终的胜利者,但在几乎所有读者的心目中,整部剧中最崇高的角色无疑仍然是哈姆雷特。哈姆雷特,而非小福丁布拉斯,获得了最多人的爱戴。哪怕是小福丁布拉斯,作为最后的赢家,也需要为哈姆雷特这位掌握道德制高点的人物大唱颂歌。最重要的是,在整部悲剧中,惟有主人公哈姆雷特,其内在反思和外在遭遇,最能让观众和读者感受到灵魂的荡涤,并折服于其道德力量和深邃心灵。显然,相比于小福丁布拉斯,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身上投射了远远更多的同情。更何况,如果哈姆雷特没有被毒杀,面对来势汹汹的小福丁布拉斯,拥有真实道德力量和王位法统的哈姆雷特,显然更能获得丹麦人民的拥戴。在这种情况下,新君主小福丁布拉斯是否仍然能顺利夺取丹麦王国的政权,就未可知了。总之,《哈姆雷特》表明,莎士比亚在许多地方都认可马基雅维利的基本洞察,但两人也有分歧。这两位站在现代世界门槛上的十六世纪思想巨人,都承认在前现代世界向现代世界转型的古今之变中,人民开始逐渐展现其巨大的政治能量。无论新君主多么精于权谋,都必须精心维护自己在明面上的道德形象,以获得人民的支持,从而建立新秩序。在这一大前提下,莎士比亚并不认可马基雅维利主义,同时他也更强调道德在政治面前没有完全失去尊严。违背道德的政治人物会受到良知的折磨,而最受人民爱戴和最有可能获得人民支持的人,仍然是真正具有道德感召力的政治人物。赵宇飞,波士顿学院政治学系政治哲学专业,硕士毕业于芝加哥大学,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主攻方向为十八世纪法国政治思想,同时兼及古典政治哲学、马基雅维利、施特劳斯等相关研究主题。
● 新书推荐 | 《凯撒的精神:莎士比亚罗马剧绎读》(彭磊 著)插图来自网络,与文章作者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