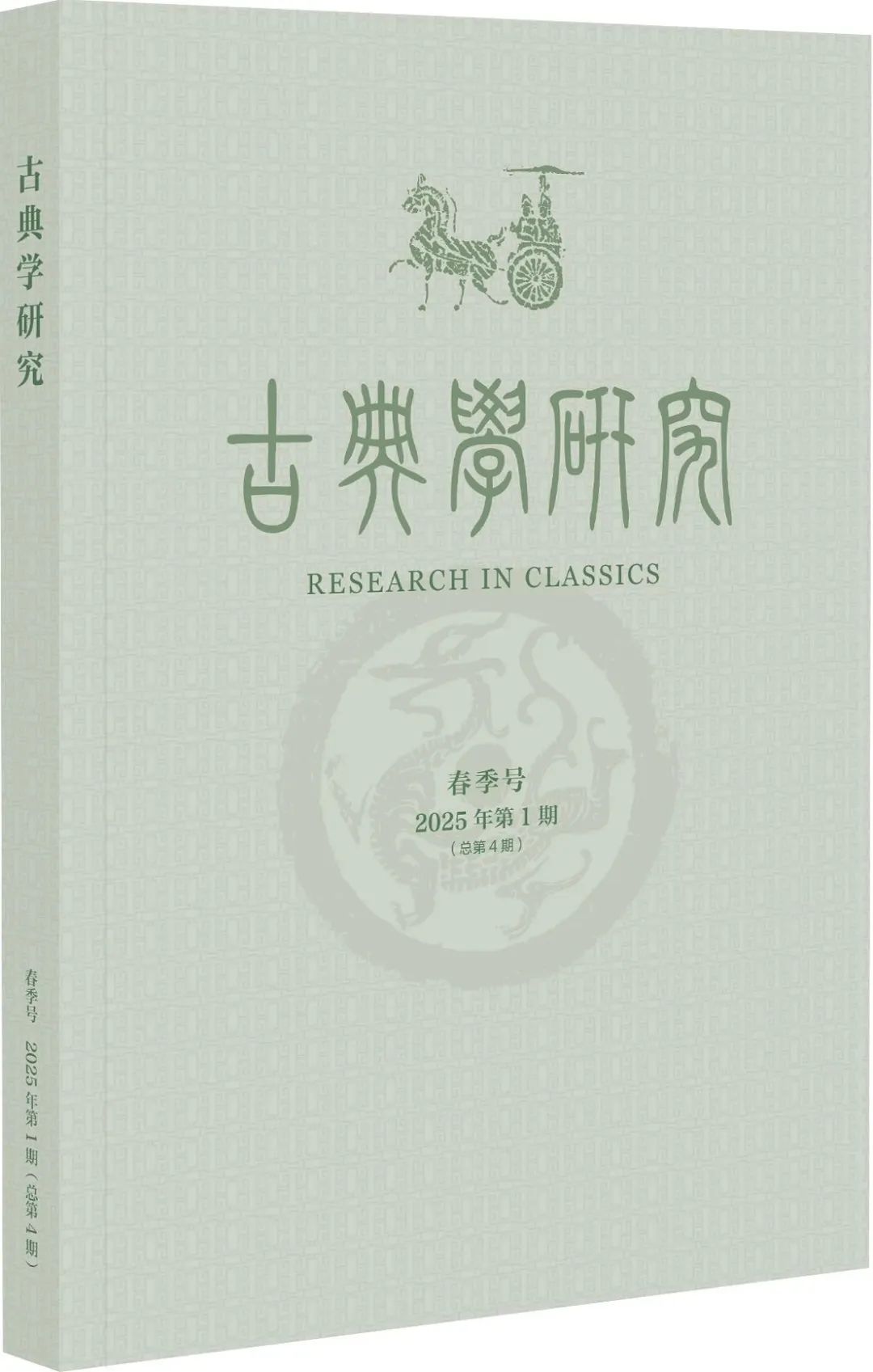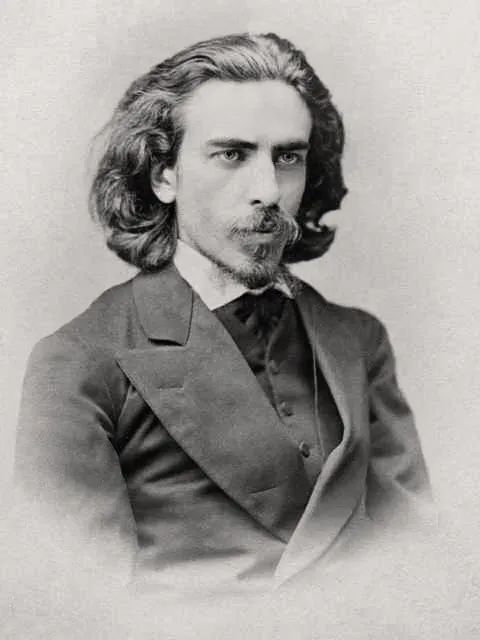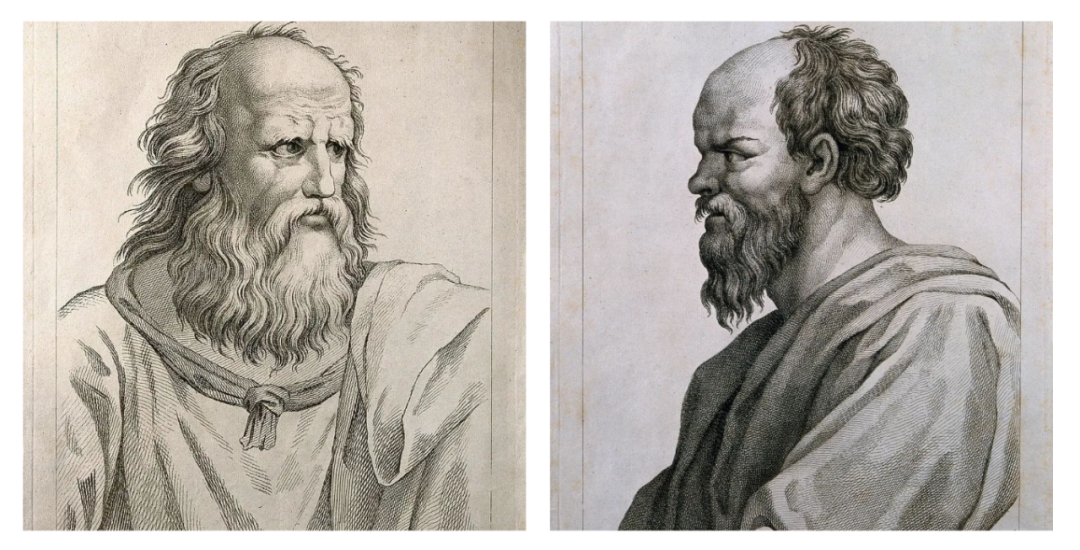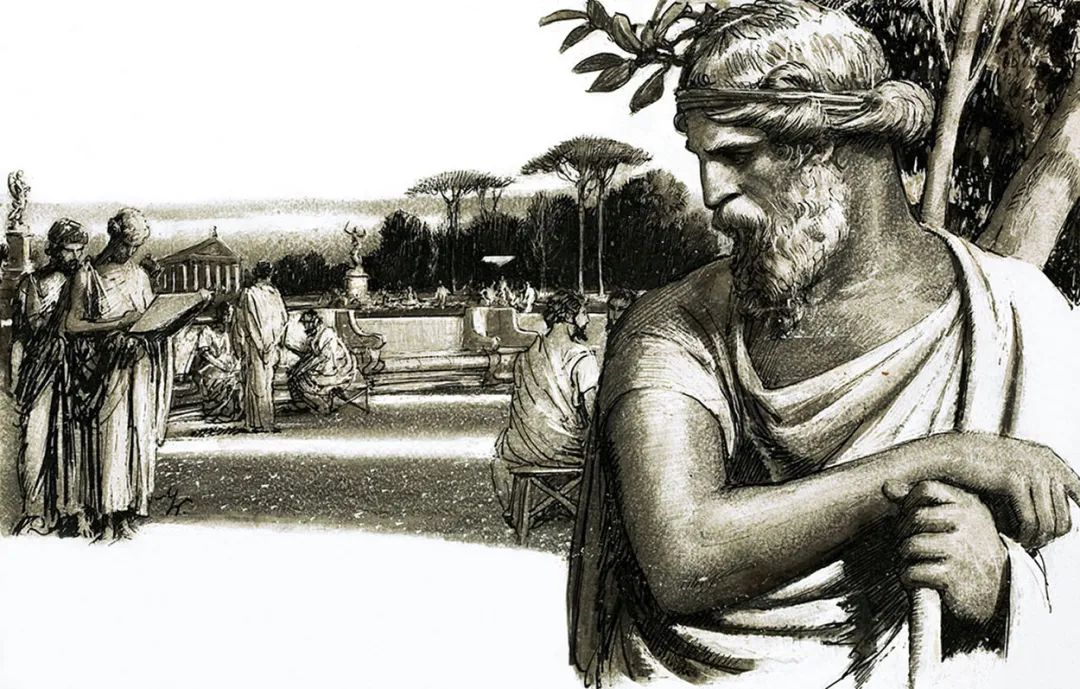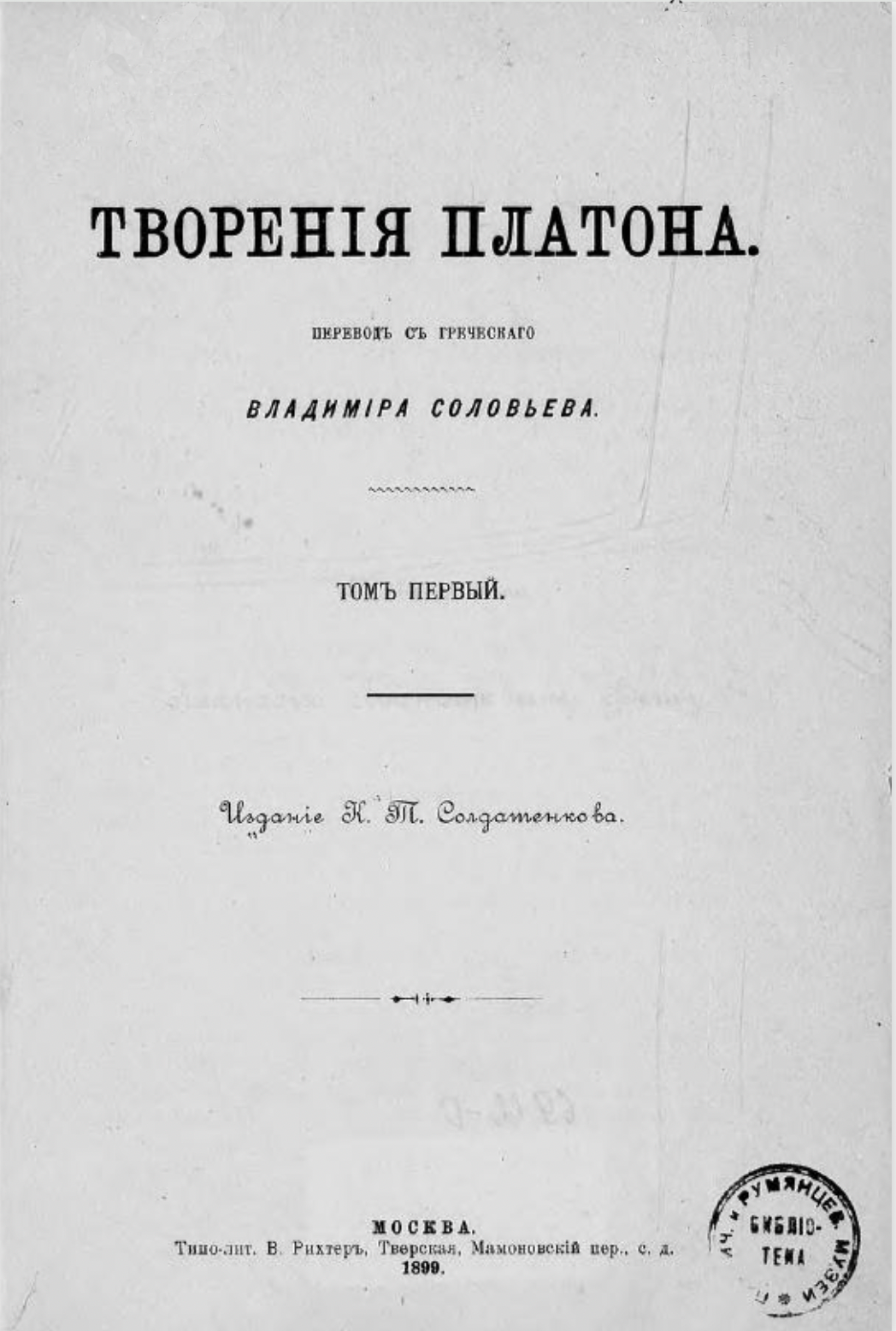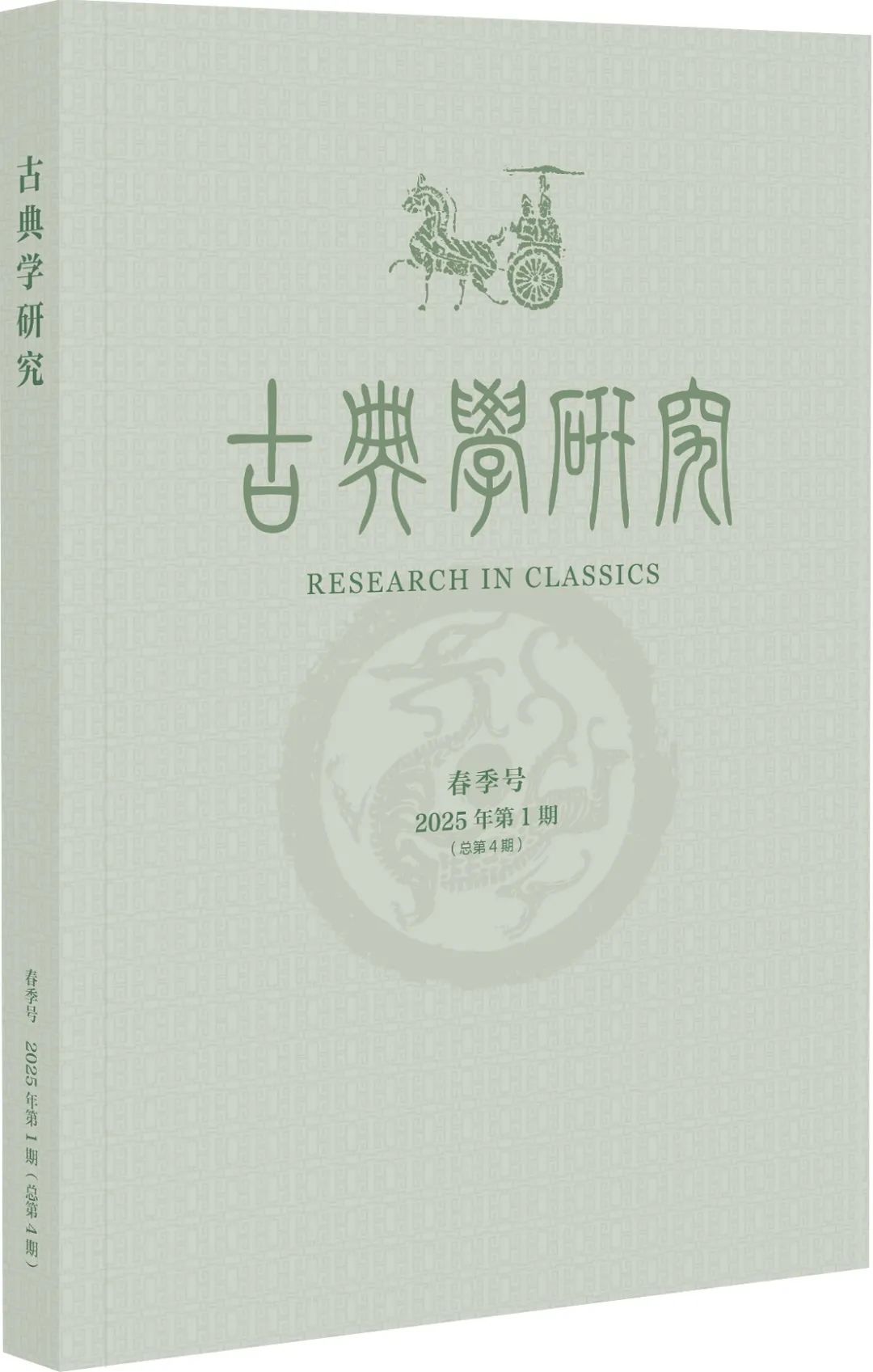本文刊于《古典学研究》2025年第1期(总第4期),注释从略,感兴趣的读者可查阅原刊。
1874年,21岁的索洛维约夫(1853—1900)以《西方哲学的危机:反对实证主义者》一举成名。三年后,索洛维约夫移居圣彼得堡,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的追随者和亲密朋友,尽管他与这位精神导师的立场相反,主张弥合东正教和罗马天主教之间的分裂,以实现教会合一的理想。随着年齿渐长,索洛维约夫日益清楚地认识到,俄罗斯东正教会与皇权政制的关系过于密切,以至不可能完成其使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遇刺(1881)之后,索洛维约夫转向罗马天主教会,甚至要求俄罗斯皇权臣服于罗马教宗,俨然成了与城邦习俗作对的哲人,其激进政治观受到不少俄罗斯学人口诛笔伐。▲ 索洛维约夫(1853—1900)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步入不惑之年后的索洛维约夫意识到,教会合一的理想无法实现,他越来越悲观,于是回到哲学研究,写下《爱的意义》(1892—1894)、《善的辩护》(1897)等著作。随后,索洛维约夫着手翻译柏拉图对话,1899年出版了《柏拉图文集》第一卷。在此前一年(1898),索洛维约夫还发表了小册子《柏拉图的人生戏剧》。1900年7月,索洛维约夫病逝于莫斯科郊外的庄园,年仅47岁。1903年,索洛维约夫的胞弟米哈伊尔与后来担任莫斯科大学校长(1905)的著名哲学家谢尔盖·特鲁别茨科伊公爵(С. Н. Трубецкой,1862—1905)一起,整理出版了索洛维约夫翻译的《柏拉图文集》第二卷(部分译文出自其胞弟)。特鲁别茨科伊在纪念索洛维约夫的文章(1901)中说,“柏拉图第一次为自己提出‘善的辩护’的任务,而这正是索洛维约夫主要著作的主题”。这一评价是否能得到《柏拉图的人生戏剧》的印证呢?
索洛维约夫翻译柏拉图作品,看似起因于他不满德意志哲人施莱尔马赫的柏拉图研究:
施莱尔马赫认为,柏拉图作品的顺序由柏拉图本人及其思想和意图事先确定;所有对话都不过是在实现柏拉图年轻时制定的一个方案,或者说实施一个艺术-哲学-教学的计划,在他的整个哲学活动中,这个计划的细节越来越清晰。
在索洛维约夫看来,施莱尔马赫把柏拉图当作比康德还要固执死板的哲人,而实际上,哪怕康德的哲学观都并非一成不变,柏拉图这样的哲人不可能按照一个固定不变的计划写作。柏拉图作品与其说是在展示某个教学计划,不如说是在展示某个哲人的“人生戏剧”。柏拉图对话的主人公大多是苏格拉底,我们多半会以为,索洛维约夫指的一定是“苏格拉底的人生戏剧”——我们错了,索洛维约夫认为,柏拉图对话的真正主人公是柏拉图本人,而非苏格拉底:柏拉图的写作目的不在于“回忆苏格拉底”,而在于回忆自己的思想变化。因此,索洛维约夫把柏拉图对话称为“柏拉图的人生戏剧”。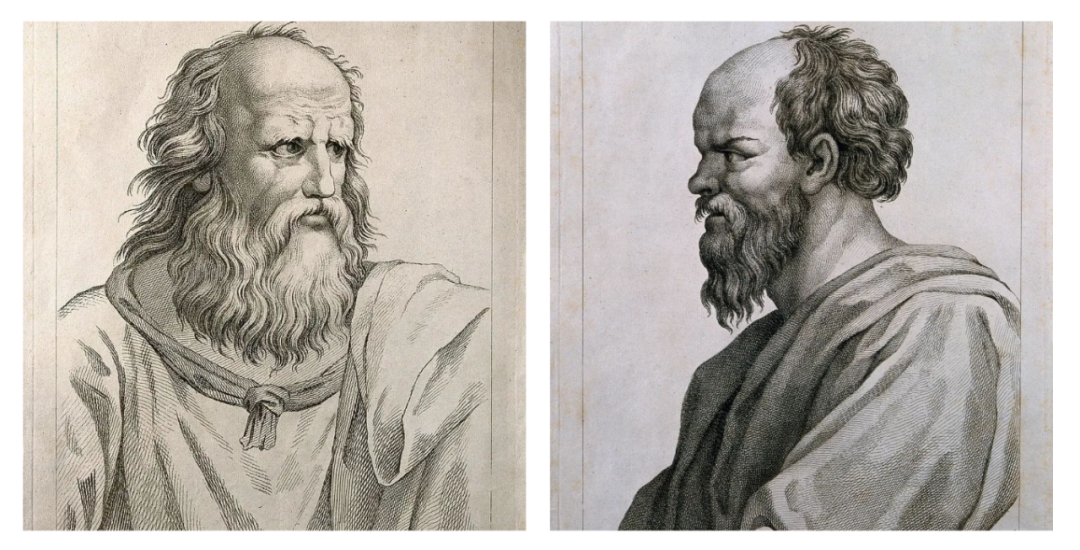
▲ 柏拉图(左)与苏格拉底(右)
《柏拉图的人生戏剧》篇幅不长,索洛维约夫首先简要描述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生平以及从事哲学思考的时代背景。索洛维约夫说,在当时的雅典城邦,有两类相互对立的学人:城邦护卫者与智术师。前者致力于维护城邦的宗教信仰、传统美德以及法律制度,可称为如今所谓的保守派;后者则试图颠覆传统的价值观,也就是今天所谓的激进分子。显然,这两类智识人之间的矛盾无法调和: 那些主张传统信仰和生活法则神圣不可侵犯的人,以及那些像智术师一样偏爱否定的人,两者之间似乎存在某种天然的敌意,他们(智术师)无一例外地否定所有决定性的生活法则,并在原则上拒绝这些法则的可能性,即否认生活和思想的任何基础。(《人生戏剧》,页592)
索洛维约夫显得是有感而发,因为在十九世纪的俄罗斯,保守派与自由派、斯拉夫派与西方派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不过,
在苏格拉底面前,护卫者与智术师之间表面上的敌意消失了,这两个昔日的对手齐心协力,要摆脱这位可憎的最高真理化身——他们因为自己的错误而携起手来。(《人生戏剧》,页592)
护卫者抵制苏格拉底,是因为他们认为后者与城邦的宗教传统相互抵牾,智术师抵制苏格拉底则是因为他们主张相对主义,否认任何真理的存在。而在索洛维约夫看来,城邦护卫者和智术师都误解了苏格拉底,因为:
苏格拉底既没有无条件地、不可妥协地与智术师为敌的理由,也没有无条件地、不可妥协地与祖先传统和法则护卫者为敌的理由。他真诚地、心甘情愿地承认两者中的真理部分。他确实是两者之间的第三个综合的、调和的原则。(《人生戏剧》,页592)
索洛维约夫自己的哲学具有强烈的折衷主义倾向,他把苏格拉底视为折衷主义者,无异于把自己的思想个性赋予了苏格拉底。不过他又暗示,苏格拉底的立场更倾向于智术师。因为在苏格拉底看来,传统习俗已经腐朽,必须革新,智术师对城邦传统的态度虽稍显激进,却并没有错。联想到索洛维约夫自己对待俄罗斯东正教的态度,我们可以说,他对苏格拉底的定位差不多是在说他自己。苏格拉底在雅典被视为智术师,这是历史事实,谐剧诗人阿里斯托芬的《云》就是证明。但索洛维约夫认为,尽管苏格拉底的批判性探究精神十分显著,“民众和像阿里斯托芬这样的坏思想家直接把苏格拉底与智术师混为一谈”,却是错的。索洛维约夫把阿里斯托芬称为“坏思想家”(плохой мыслитель),乃因为在他看来,后者“承认大众信仰和祖先法则的现实权威意义和真实性”(《人生戏剧》,页592)。这足以表明,索洛维约夫自视为苏格拉底式的激进哲人。难道索洛维约夫不担心自己的激进观点暴露,并因自己的宗教-政治思想太过激进而受到官方惩戒?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中期,索洛维约夫的确如此,但起心翻译柏拉图作品之时,他的思想似乎发生了一场转变,因为,《柏拉图的人生戏剧》中最引人注目的观点是:晚年柏拉图背叛了自己早年的精神导师苏格拉底。▲ 柏拉图在学园花园里,约翰·米拉尔·瓦特 绘,1966年
严格来讲,这种观点并不新鲜,《法义》就往往被视为晚年柏拉图背叛苏格拉底的证据。直到今天,仍然有学者持这种观点。但是,索洛维约夫在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提出这种观点,情形就不同了。索洛维约夫认为,柏拉图作品的主要意图无非是极大地高扬哲人的地位,其代表作《王制》(又译《理想国》)中提出的“哲人—王”就是明显的证明。苏格拉底被雅典法庭判处死刑,对柏拉图刺激太大,因此,在柏拉图构拟的“理想国”中,苏格拉底成了城邦的最高统治者。然而,在晚年的《法义》中,柏拉图不但否认了“哲人—王”的观点,还借笔下人物之口宣称,哲人必须遵守自己所属城邦的法律,而城邦则有权监禁甚至处死“不敬神”或不遵守城邦法律的哲人。晚年的柏拉图不但赞成雅典城邦对苏格拉底的判决,甚至还亲自判处自己的老师死刑——索洛维约夫据此对柏拉图提出了严厉的指控:
这是一场多么深刻的肃剧式灾难,一次多么彻底的内在堕落!《苏格拉底的申辩》《高尔吉亚》《斐多》的作者,在持续崇拜被法律杀死的圣徒和义人半个世纪之后,在他的《法义》中竟公然接受并肯定盲目的、奴隶的和虚假的信仰原则,而正是这种原则杀害了他最优秀的精神之父!(《人生戏剧》,页624)
索洛维约夫显得对柏拉图的背叛深感恐惧,难道在写作《柏拉图的人生戏剧》时,他预感到俄罗斯哲学界会出现一位背叛者?
索洛维约夫指控柏拉图背叛其精神导师的说法,出现在《柏拉图的人生戏剧》的最后一章(第30章),他为这一指控提供的证据是否充分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回头去看柏拉图的《王制》。事实上,在《王制》中,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从未表示过自己会做“哲人—王”,也未主张应当由哲人来统治现实中的城邦。相反,苏格拉底在对话中一再表示,不管对他自己来说,还是对其他真正的哲人来说,他们内心都极其不情愿成为统治者:
除非……哲人成为这些城邦的君主,或今日被称为君主和权贵的人们真诚地、恰当地热爱智慧,除非这两个方面结合到一起,一是统治城邦的权力,一是哲学,而许多气质和性格必然被排除在外,因为它们目前只追随这一或那一方面,那么,我的格劳孔,这些城邦的祸患就没有终止,人类的祸患,我认为,也同样如此,在这以前,这个城邦体系并不可能诞生、目睹太阳的光辉,尽管我们对它已进行过理论上的检验。(《王制》5.473c10–e5)
在这一话题的起始处,苏格拉底的确有过让哲人来统治城邦的推论。但苏格拉底最终否认了这种统治的可能性乃至必要性。就可能性而言,城邦不会让沉醉于哲学思辨的哲人来统治,统治者也不会主动把权力交给哲人。就必要性而言,苏格拉底更是坚决否认应当在现实中建立“理想国”。更为根本的理由是,哲人若治理城邦,不可避免会拉低哲人的生活品质。何况,在哲人—王的城邦,民众不仅不可能达到哲人对精神品质的高要求,反而会失去物质满足带来的快乐。
在一个不可能的城邦上花费这么多时间和努力有什么用?——正是为了显示这个城邦的不可能性。这个城邦恰恰不是任何城邦,而是一个为了满足正义的所有需求而被建构出来的城邦。它的不可能性,表明了一个正义政制之实现的不可能性,从而缓和了一个人在看到不够完美的政制时可能经受的道德义愤。
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讨论“哲人—王”的统治,恰恰意在打消哲人应当在现实中取得实际政治权力的主张。因此,索洛维约夫认为柏拉图的“哲人—王”假说极大地提高了哲人的政治地位,并不成立。▲ 苏格拉底教导年轻人
让·西蒙·贝泰勒米 作,1784年,法国兰斯艺术博物馆 藏
《法义》是柏拉图的最后一部作品,苏格拉底在其中没有以明确身份出场。怎样认识《法义》,的确意味着怎样认识柏拉图。对《法义》的不同评价使柏拉图研究者形成两个阵营,要么主张《法义》是柏拉图思想最深邃的著作之一,要么主张《法义》是柏拉图哲学的糟粕。但无论如何,理解柏拉图不可能绕过《法义》。关于柏拉图《法义》的争论,尤其集中在第十卷。柏拉图笔下的雅典异乡人承认,对“不敬神”的哲人,城邦有权审判并监禁,甚至可以判处死刑:
有些人变成这样,是由于缺乏心智,但没有坏脾气或坏性情,法官应依法送到感化所,为期不少于五年。在此期间,其他公民都不得同他们接触,除了夜间议事会成员,后者应接触他们,以训诫并拯救他们的灵魂。当他们监禁期满,如果他们有谁看起来明智,就令其居住在明智者当中,但如果没有,并再次应受到这样的指控,就得处以死刑。(《法义》10.908e–909a)
这段说法难免让人想起苏格拉底的命运。根据《法义》中的这段说法,如果苏格拉底确实“不敬神”,那么他就应该受到城邦惩罚。但从柏拉图的《苏格拉底的申辩》来看,苏格拉底“不敬神”的罪名并不成立。事实上,苏格拉底是极为审慎的哲人,他从来没有表现出任何“不敬神”的行为。索洛维约夫凭靠《法义》中的一段言辞断定柏拉图背叛了苏格拉底,如果不是在阅读《法义》时过于粗心,就会是另有原因。
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是,既然索洛维约夫是十九世纪末期俄罗斯动荡时局中引人注目的政治哲人,那他显然不可能是因为思想浅薄才得出这样的粗糙判断。我们不禁大胆猜想,索洛维约夫是否有可能出于某种特别的原因而故意曲解柏拉图呢?为了澄清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从索洛维约夫身处的时代背景出发,探究他写作《柏拉图的人生戏剧》的真实意图。上文已经提到,《柏拉图的人生戏剧》对城邦护卫者与智术师之争的描述,实际暗指十九世纪俄罗斯的东正教会与激进的虚无主义者之间的政治冲突。索洛维约夫的政治立场则受到维护东正教传统的教士和激进虚无主义者的两面夹击,而他对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这类哲人的描述,不外乎暗指自己所代表的俄罗斯新哲学才是正道。《柏拉图的人生戏剧》一再强调,真正的哲人不同于智术师的地方在于,他们在摧毁传统价值观的同时,也致力于建立一套全新的宗教观。索洛维约夫自己就是这样的哲人:在攻击禁欲主义的教会传统的同时,致力于提倡一种“新宗教意识”。因此,索洛维约夫会觉得,他与苏格拉底在古希腊诸城邦中的处境十分类似:
所有的信仰都必须是黑暗的吗?但在这里,苏格拉底却以其光明的、有见识的信仰,明确驳斥这种假说。显然,他们支持黑暗不是为了信仰的利益,而是为了一些与信仰无关的其他利益。(《人生戏剧》,页594)
在十九世纪的俄国,有“俄罗斯的苏格拉底”之称的其实是阿列克谢·霍米雅科夫(А. С. Хомяков,1804—1860)。此人出生于莫斯科的贵族家庭,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据说是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被称为“俄罗斯的苏格拉底”,主要因为他作为斯拉夫派的创始人喜欢“沙龙式”的辩论。然而,就霍米雅科夫主张废除农奴制和死刑以及实行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而言,称他为“俄罗斯的苏格拉底”明显是张冠李戴。索洛维约夫有理由认为,自己才是“俄罗斯的苏格拉底”,因为他与苏格拉底一样维护传统宗教,只不过其方式是更新传统宗教。因此,索洛维约夫这样描述苏格拉底所受到的“不敬城邦神”的指控:
这种指控的真正含义并不是说苏格拉底不尊崇诸神——事实上,苏格拉底尊崇诸神——但他尊崇它们不是因为城邦承认它们,而只是因为,或者说事实上,在诸神身上存在着或可能存在着某种神圣的东西——他从本质上尊崇诸神,因为它们与无条件者有着内在的联系,而不是因为某种条件。(《人生戏剧》,页598)
同样,索洛维约夫不认为自己“不敬[基督教的]神”,相反,他认为自己是虔敬的基督教徒。他否认的仅仅是教会的上帝形象,并试图以“新宗教意识”的上帝形象取而代之。▲ 叛逆天使的堕落
彼得·勃鲁盖尔 绘,1562年,比利时布鲁塞尔美术皇家博物馆 藏
既然如此,索洛维约夫为什么会认为晚年柏拉图背叛了苏格拉底呢?如果我们想到,索洛维约夫在因病过早离世前发表的《关于战争、进步与世界历史终结的三次对话》(以下简称“《三次对话》”)中不仅否定了自己此前的哲学著作,也与自己的两位精神导师——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决裂,他的所谓柏拉图背叛论也就不难理解了。
《三次对话》的主人公之一是位养尊处优的“公爵”,他大谈“勿以暴力抗恶”。索洛维约夫在对话中不惜笔墨大肆丑化这位“公爵”,称其之所以会相信这种荒谬绝伦的理论,乃因为他生活条件优越,完全脱离现实。谁都不难看出,索洛维约夫这是在抨击托尔斯泰的哲学世界观。陀思妥耶夫斯基批评教会时向来隐晦,索洛维约夫在《三次对话》中对他的批评同样隐晦。在当时的俄罗斯知识界,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索洛维约夫的师生关系是众所周知的事情,索洛维约夫也不可能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公开决裂。因此,索洛维约夫采取了一种自我批判的方式:鉴于自己早年曾追随陀思妥耶夫斯基,他通过否定自己的早年思想间接地否定陀思妥耶夫斯基。然而,在当代俄罗斯哲人伊戈尔·叶夫兰皮耶夫看来: 这比批判托尔斯泰和放弃自己的“错误”要严重得多,因为在这里,整个俄罗斯哲学的发展主线受到了质疑,而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为其奠定了永恒不变的基础。
由此我们可以推测,索洛维约夫写作《柏拉图的人生戏剧》时张扬柏拉图背叛了苏格拉底,无异于把自己视为柏拉图的学生——于是,他要翻译柏拉图的对话作品。
当代俄罗斯哲学史学者亚历山大·阿布拉莫夫这样评价索洛维约夫的柏拉图研究:
索洛维约夫是柏拉图著作的杰出译者,虽然因英年早逝没能完成全部工作,但在他自己的哲学体系中,在他一切统一的形而上学中,他是一个始终如一的柏拉图主义者。
既然索洛维约夫对柏拉图的误解是刻意的,就不能认为索洛维约夫是柏拉图的批评者。的确,索洛维约夫是柏拉图的崇拜者,他甚至将自身的人生戏剧与柏拉图的人生戏剧融为一体,就此而言,他的柏拉图研究带有学术自传性质。 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俄罗斯文艺复兴时期,苏格拉底是争夺“俄罗斯逻各斯”——关于国家哲学性质的争论——的无形参与者;虽然发生了世界观革命,但苏格拉底在苏联和后苏联文化中仍保持着主人公的地位,在整部俄罗斯史中体现了哲学的永恒事业。
柏拉图的哲学思想传入俄罗斯已经有数百年历史,在俄罗斯收获了一大批崇拜者,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俄罗斯古典学流派。在俄罗斯,柏拉图变成了俄罗斯式的,索洛维约夫对柏拉图的解读就是最好的例证。▲ 索洛维约夫译《柏拉图文集》第一卷扉页,1899年

李天昀,1992年生,江苏南京人。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哲学博士,河北北方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青年教师。主要研究俄罗斯古典学、俄罗斯政治史学等等。在《俄罗斯文艺》、《索洛维约夫研究》(俄文)、《俄罗斯基督教人文研究所学报》(俄文)等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30余篇,出版专著《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索洛维约夫哲学世界观中的人类未来》(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