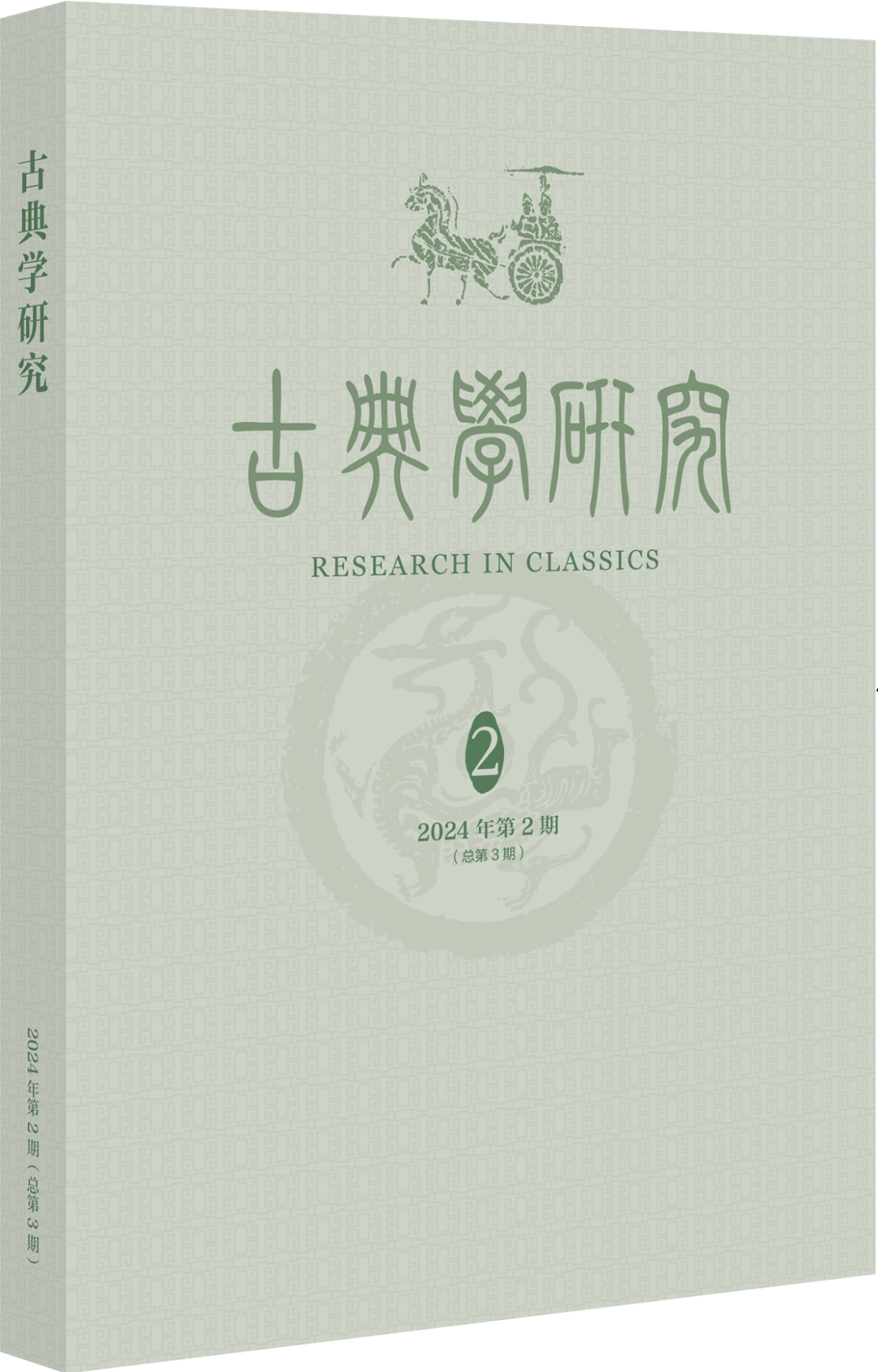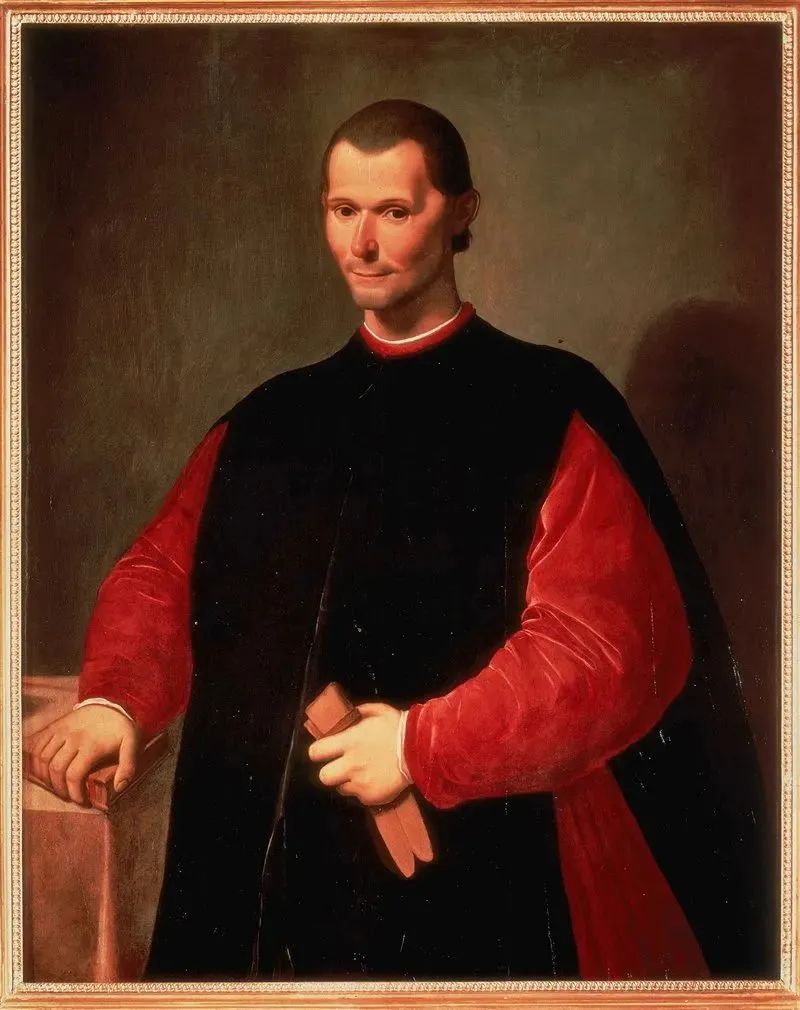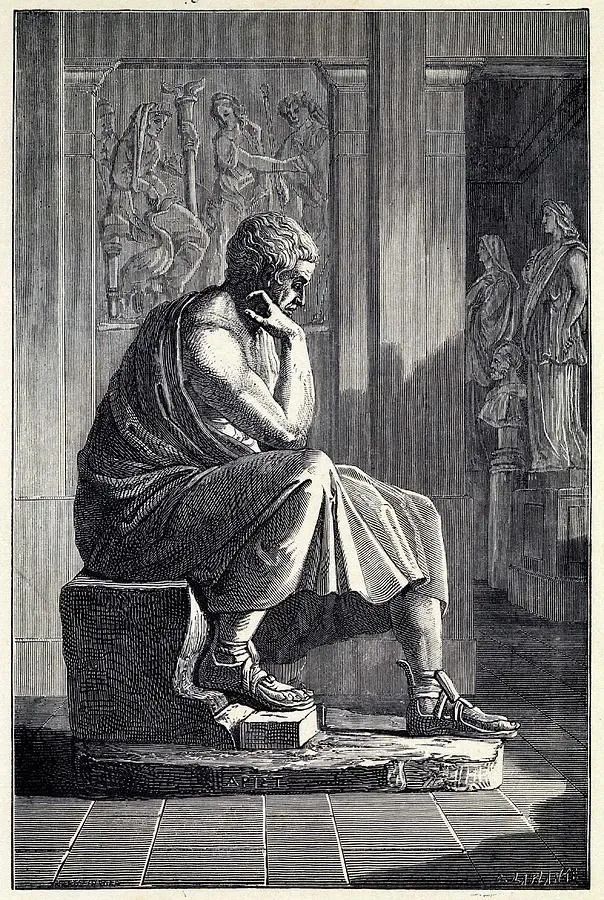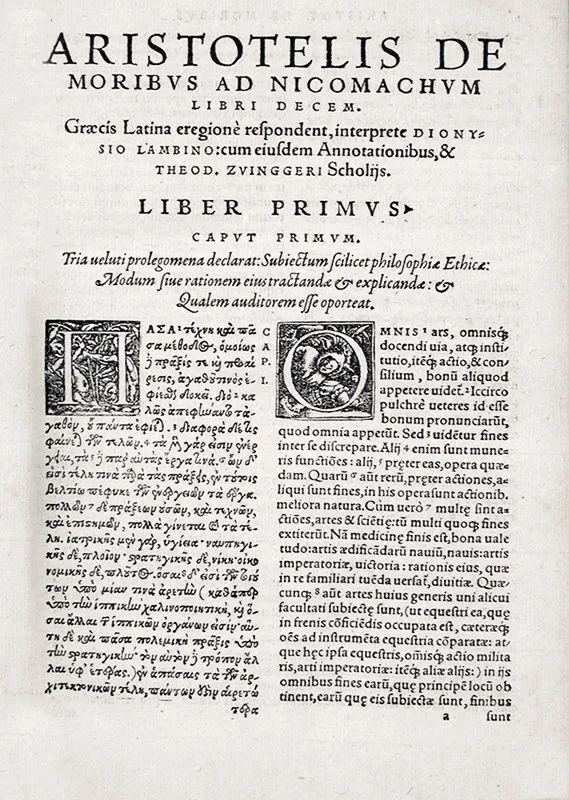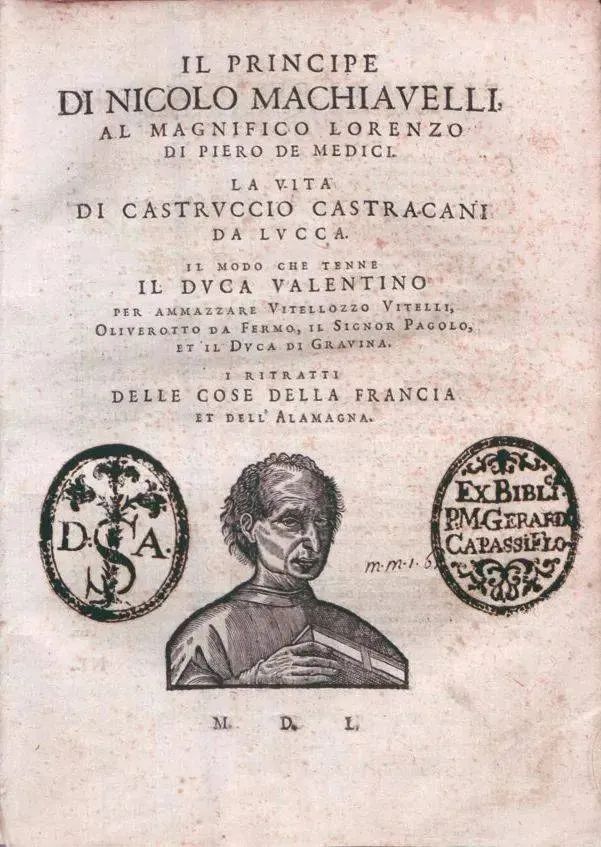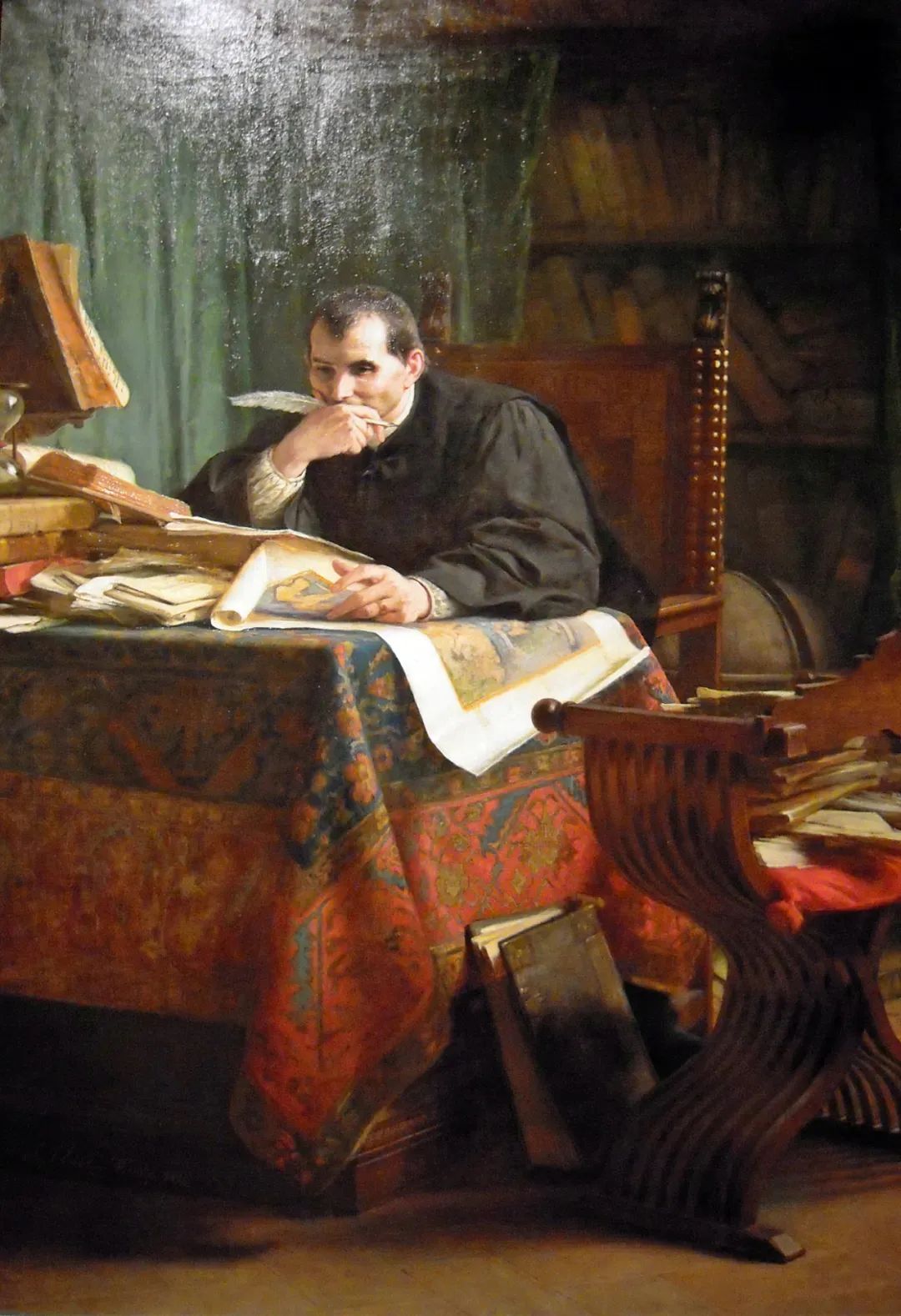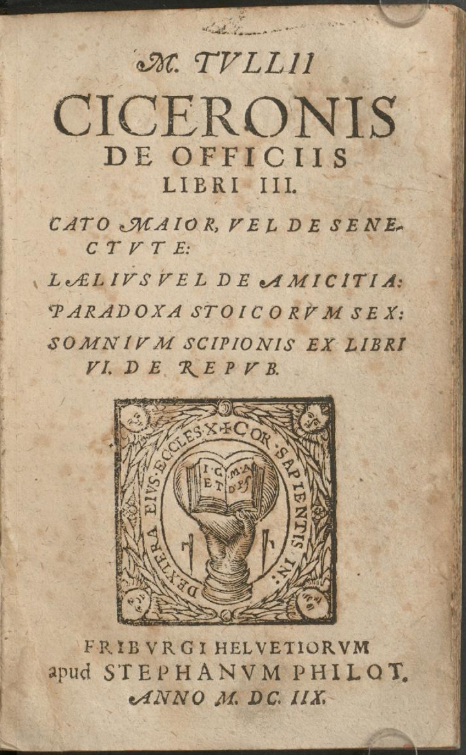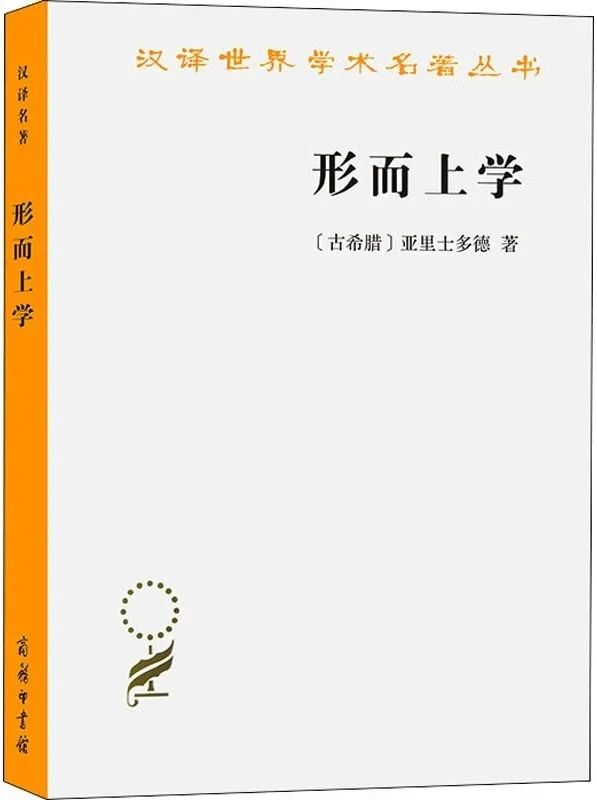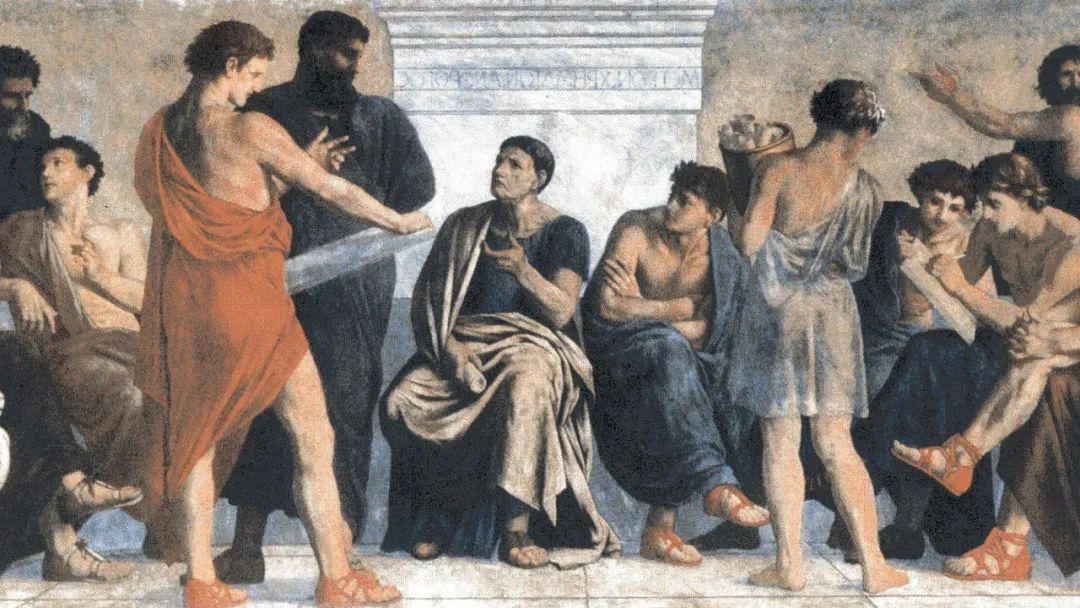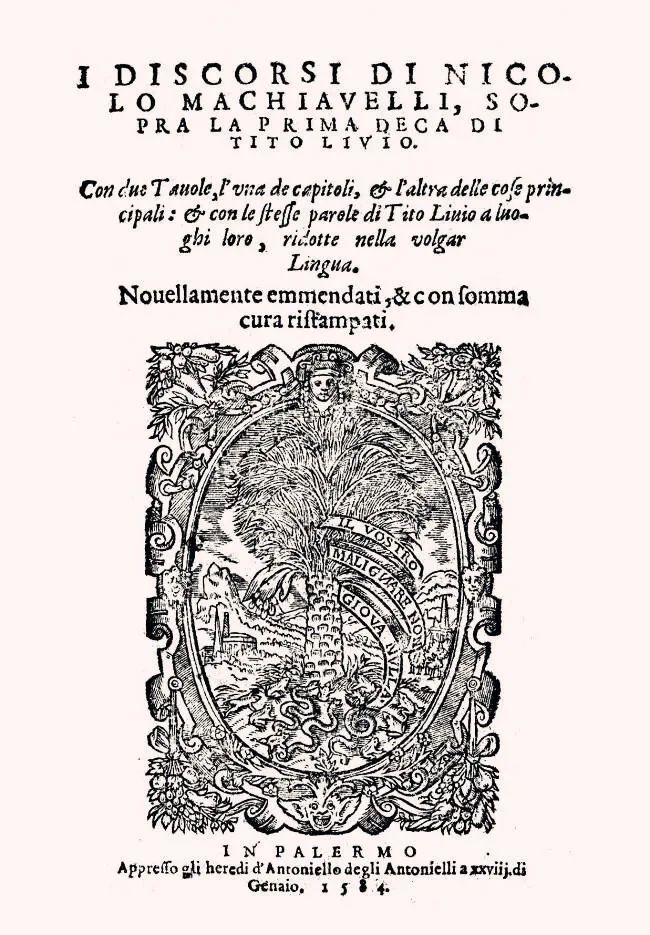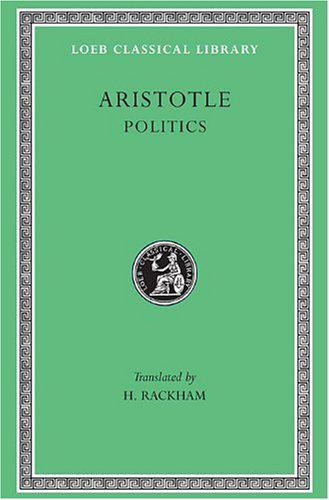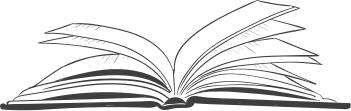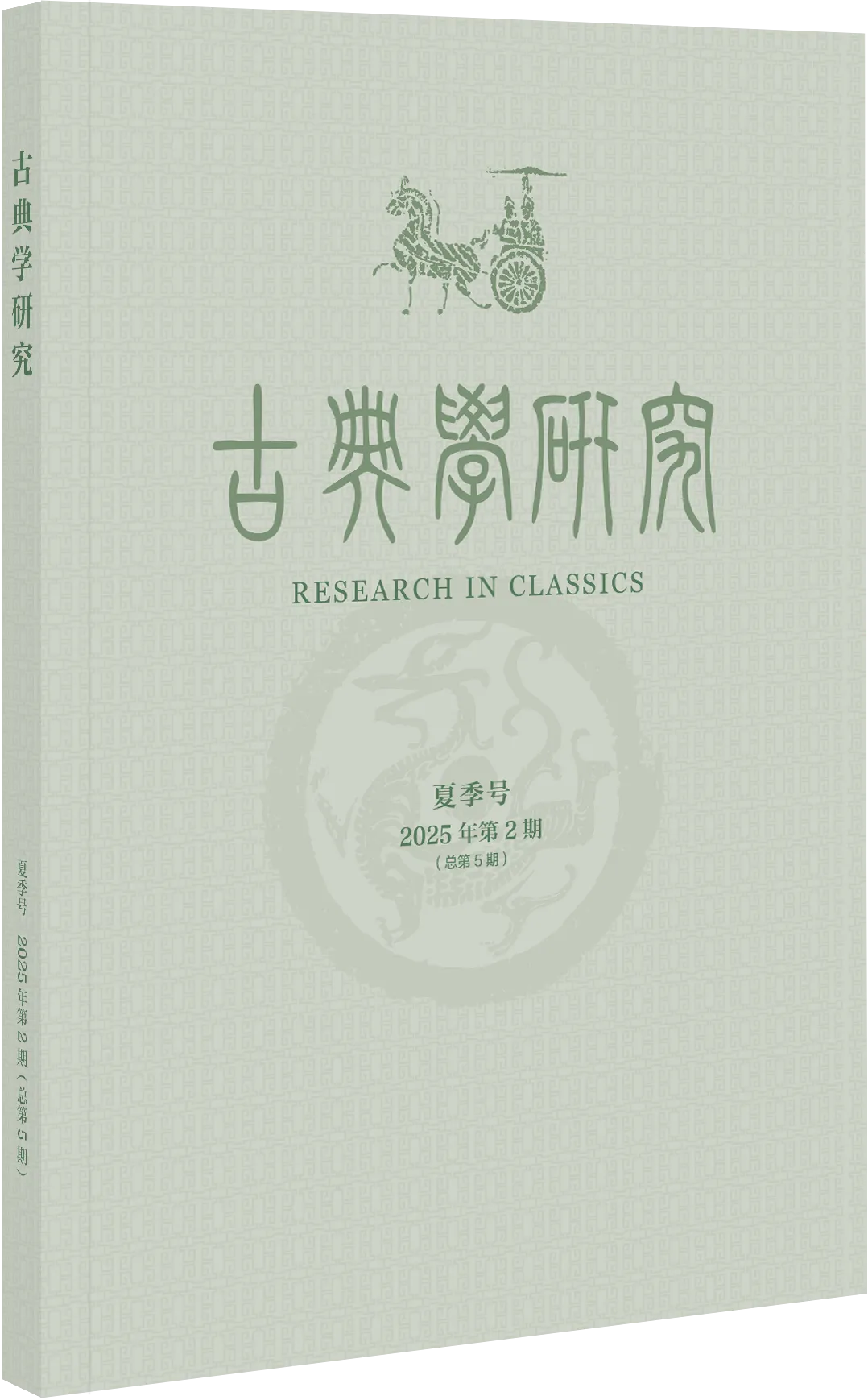本文刊于《古典学研究》2025年第2期,[意大利]大卫·莱维 撰,邓连冲 译。注释从略,感兴趣的读者可查阅原刊。
有教养者——传统上被称作淑女和绅士——的特点是,他们对待道德的态度并非唯利是图(mercenary)。他们相信,做正派的事是因为它是正派的事,而不是因为这样做给他们带来回报,也不在有回报时才这样做。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表达了这一原则:道德德性为其自身而得到践行——或者如他在别处所说的那样,道德德性为了高贵的事物(亦即自身值得选择和称赞的事物)而得到践行。从《君主论》第15章开始,马基雅维利公然挑战这种非唯利是图的态度,背后指涉的正是当时备受推崇的亚里士多德的道德哲学。马基雅维利承认,道德德性会受到普遍称赞,但他强调“实效真理”(effectual truth):如果一个人(尤其一位君主)试图一丝不苟地践行道德德性,他就会被那些不如他一丝不苟[地践行道德德性]的人打败,终将走向毁灭。因此,亚里士多德式的道德教导与君主统治并不相容。在马基雅维利那里,可以把“君主”广义地看作“政治领袖”。因此他的论证意味着,亚里士多德的教导不仅与君主统治不相容,而且与所有一般意义上的统治都不相容,因此也与人类的共同善不相容。与之相反,马基雅维利自己有关道德权变的教导则有利于共同善。▲ 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1469—1527)马基雅维利的论证或许令人震惊,但并非那么不着边际,人们可能还是想知道亚里士多德会如何回应它。然而,学者们极少探究这一特定的问题。本文的论点是,亚里士多德熟知并多少承认这一与马基雅维利的论证非常相近的论证,并的确对其作出过回应。[与马基雅维利相反,]亚里士多德找到了依据,将道德德性呈现为以自身为目的的高贵之物。本文将聚焦于这两位思想家对高贵与善之关系的看法,尤其关注《君主论》第16章与《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四卷第1章对慷慨(liberality)这一德性截然不同的呈现。▲ 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前384—前322年)
在《君主论》第15章开篇,马基雅维利宣布他将与传统的道德教诲分道扬镳。然而,他并未点出其对手的大名,而是含糊地提到“许多人已写过”关于道德问题的文章,他们“曾幻想没人见过或知道其真实模样的共和国与君主国”。或许,亚里士多德在这“许多人”中占据着主导地位,然而这一假定从未得到普遍认同。除了那些直接或间接受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影响的人外,现代学者通常认为,马基雅维利的批评主要针对某些文艺复兴时期和古罗马时期的作者——尤其西塞罗。他们的确有理由认为,《君主论》中的某些论证直接针对西塞罗。然而,在马基雅维利的另一部作品中,有一个段落与《君主论》第15章的表述惊人地相似,同样论及幻想过共和国的作者。只不过,他在那里提及的不是西塞罗,而是“亚里士多德、柏拉图以及许多其他人”。如果马基雅维利的确把亚里士多德(连同柏拉图)看作比西塞罗更重要的对手,这样的表述并不奇怪。在马基雅维利身处的时代和地域,尽管西塞罗无疑影响巨大,但亚里士多德主义仍是“主流的哲学传统”,《尼各马可伦理学》“仍是大学道德教育的教科书,在人文主义圈子和学校中被追捧研读,一再被翻译、付梓和评注”。此外,在马基雅维利成长的十五世纪,“毫无疑问,意大利研究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最活跃的中心”是他的家乡佛罗伦萨。在那里,《尼各马可伦理学》不仅在大学中得到研究,也受到大学外重要人文主义者的关注,宗教团体成员亦参与其中,还有“广泛的公众,他们热衷于阅读拉丁文或意大利本地语言写成的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显然,这些公众中包括马基雅维利的父亲,他购买过一部拉丁文译本和评注。因此,在马基雅维利的阅读视野中,《尼各马可伦理学》不仅是一部重要文献,而且对他来说也随时可以接触到。鉴于这一背景,当我们在《君主论》第15章看到马基雅维利列举的十一对公认的德性与劣性,或许不应仅仅将其当成巧合,而应视为一种暗示。正如但丁与托马斯·阿奎那所指出,十一恰好是《尼各马可伦理学》中道德德性的数目。诚然,亚里士多德把道德德性呈现为介于两种恶之间的中道;而马基雅维利则将每一种德性与单一的劣性对立。例如,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慷慨这一德性是介于吝啬与挥霍之间的中道;而在马基雅维利的列举中,慷慨仅是吝啬的对立面。然而,在随后讨论慷慨的章节中,我们实际上不仅遇到了吝啬,还遇到了挥霍(suntuosità);因此,马基雅维利似乎熟知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马基雅维利论证了,对慷慨与挥霍的亚里士多德式区分在实践中是无效的。因此,在真实情境里,人们要么选择挥霍,要么选择吝啬,无法实现德性的中道。马基雅维利最初成对地(而非三个一组地)列举出德性与劣性,这意味着他并非对亚里士多德缺乏关注,而是有意拒斥他。马基雅维利在此没有提及亚里士多德之名,而是仅仅暗示,这或许是因为,正如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第15章开篇所说的那样,他惧怕自己背负倨傲自大的恶名。另外,对亚里士多德的道德哲学的明确攻讦会冒犯许多读者的成见(他们原本可能会接受马基雅维利的影响),实在是没这个必要。因而,即便马基雅维利对传统道德的批判无疑树立了许多论敌,包括西塞罗、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更不必说《圣经》和基督教教义;但我们有理由相信,他首要的靶子是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 《尼各马可伦理学》希腊语和拉丁语版首页,1566年在《君主论》第15章,马基雅维利论证,尽管每个人都称赞道德德性,但正如今人所言,道德德性不切实际。那些始终践行德性的人(亦即绅士)会败于那些不择手段取胜的人。人们想要获胜,有时需偏离道德德性或善,必须知道如何以及何时变得“不善”。必要性或权变而非高贵性(nobility),应成为行动的指导。善与不善(亦即道德德性与劣性),必须根据实际需要来决定是否“使用”或“弃用”。事实上,严格来讲,唯有那些能让人获得“安全和福祉”的品质才配称作德性——即便它们在传统上被称作劣性。马基雅维利最先列举的德性是慷慨。那么,这一所谓的德性能否促进君主的安全和福祉呢?慷慨不仅是马基雅维利最先列举的德性,也是最具亚里士多德特色的德性。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本人最先探讨的德性是勇敢和节制。尽管马基雅维利对这两种德性的理解不同于亚里士多德(因为它们不再是为其自身而践行),但他仍希望保留它们:某种特定类型的勇敢或大胆显然属于马基雅维利式的德性;对于臣民的财产与妻女,君主被劝诫要保持节制或自制(《君主论》第17章)。至于正义,马基雅维利则小心翼翼地将它排除在德性清单之外。然而,马基雅维利却可以公开批评慷慨这一德性,此举并不会引发过多非议,人们学着抛弃慷慨也显得无关痛痒。我们将看到,人们还未意识到,通过接受马基雅维利的论点,他们抛弃的不仅是慷慨,更是亚里士多德德性论的根基。我们先看看亚里士多德如何论述慷慨(《尼各马可伦理学》4.1)。慷慨是与使用钱财(或物资)相关的道德德性。恰当地使用钱财体现在花费与施予它的方式上。慷慨之人不会轻率或过度地施予他人,他只会正确地施予他人,即在正确时机,将正确数目的钱财施予正确的人。他之所以这么做,是这一行为本身高贵;若他因其他原因这么做,那他就并非慷慨之人(《尼各马可伦理学》4.1.1120a27-29)。因为真正的道德德性为其自身而践行,亦即为了高贵或者说为了美(τὸ καλόν)而践行。如果人们为了名利等其他目的践行慷慨,那么慷慨就不过是一种工具,可以随时被更有效的工具所取代。慷慨之人乐于施予,因为高贵的行动比拥有钱财更令他愉悦。由于他不崇尚钱财,他便不会谋得不义之财。他只会从适当的来源获取钱财,“比如取自自己的财产”,而他这么做是为了施予他人(《尼各马可伦理学》4.1.1120a34-1120b1)。如同其他道德德性,慷慨介于过度与不及这两种劣性之间,是施予得太多的劣性(挥霍)与施予得太少的劣性(吝啬)之间的中道。挥霍意味着自我毁灭,因为挥霍者会迅速耗尽钱财。然而,挥霍这种劣性远没吝啬那么糟糕,因为挥霍仅需加以节制便可成为慷慨,而吝啬通常无可救药。事实上,亚里士多德指出,慷慨并非精确地处于两种劣性的正中间。慷慨倾向于过度,即偏向挥霍一端:“慷慨之人常常在施予上过度。”慷慨偏向挥霍,亚里士多德这一相当不显眼的观察,为马基雅维利提供了一个可以充分利用的切入点。马基雅维利的批评始于《君主论》第16章,他区分出两种慷慨:一种是为了慷慨之名而践行(他或许更喜欢说“使用”)的慷慨;另一种是“合乎德性并且应当如此使用”的慷慨,即不带有任何其他动机的慷慨。当然,后者便是绅士和亚里士多德认可的慷慨。对于这种“合乎德性地使用”的慷慨,马基雅维利提出了异议:“这样做不会被承认,你将不可避免地背负与其相对的恶名。”或许,这一简练的反对意见可作如下理解:施予应得之人是高贵的,这样的人很少;但多数人不会认为自己不应得,因而他们会说你吝啬。这种高贵本身是否足够令人满足,以至于你愿为它背负恶名?换句话说,你果真是为了道德德性本身而践行它的吗?这些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因此,如果一个人希求在人群之中保有慷慨之名”(而这才是人们真正想要的),他“就必须不吝惜任何奢侈的花费”——也就是说,他必须变得挥霍无度。慷慨必然会转变为挥霍,或许可以说,挥霍就是慷慨的“实效真理”。另外,挥霍比吝啬更糟糕,而非更好。因为通过挥霍,君主会很快耗尽其资源。为了获得更多资源,他必须向人民苛以重税,这会让他遭受怨恨,但君主的安全取决于他不被人民所憎恶(《君主论》第9章)。这些由慷慨造成的灾难性后果,足以证明慷慨并不是一种德性,而是一种劣性。▲《书房里的马基雅维利》
斯特法诺·尤西 绘,1894年
倘若君主接受了传统观念,认为慷慨是一种德性,并因此追求拥有这一德性的赞誉,那么他自己便踏上了通向毁灭的道路。但如果他拒斥这种观念,并审慎地行吝啬之事,他的臣民最终会称他的吝啬为节俭,并称他的节俭为慷慨。因为臣民会看到君主拥有足够的资源来管理和保卫他的国家,而无需过度征税。因此,马基雅维利令人难忘地表述道:
他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慷慨的,因为他没有从他们那里征取什么;而他对少数人来说则是吝啬的,因为他们没有从他那里得到施予。
由此,慷慨这一施予的德性被重新界定为不征取的德性。君主并未完全意识到,他已学会如何获取自己梦寐以求之物——不是高贵,而是荣誉和安全。当然,施予并非百害而无一利。一切都取决于为什么要施予,以及从谁那里获取用于施予的钱财。马基雅维利允许想当君主的平民使用慷慨,因为他必须以此赢得朋友和民众的支持,凯撒(Julius Caesar)便是这样做的。普鲁塔克(Plutarch)记述过,凯撒作为一名崭露头角的政治人,曾借用大量钱财供民众大肆消遣;后来他说服克拉苏(Crassus)帮他偿还了债款。另外,征掠外邦的将领也必须对他的士兵慷慨相待,否则士兵不会跟随他;况且他这样做没有任何害处,因为他花费的仅是别人的钱财,而非自己或国民的钱财。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慷慨之人花费的是自己的钱财,以高贵为目标。而在马基雅维利那里,慷慨之人花费的是别人的钱财,以权变为目标。这两种慷慨之人,哪一种更可能获得成功呢?对于普遍的道德德性(尤其慷慨)来说,马基雅维利的论证可以说是这样的:依据传统的理解,应当为了高贵而践行道德德性,但高贵与善(亦即“安全与福祉”)之间存在冲突——我们越清楚地理解这一冲突,高贵所具有的光彩便越发褪去,因此我们必须重新构想道德德性。它们不再是我们头顶令人惊羡的星辰(《尼各马可伦理学》5.1.1129b25-29);毋宁说,它们必须是我们达致世俗目的的现实工具——是否使用这一工具则“视需求而定”(《君主论》第15章)。马基雅维利声称,与前辈们不同,他的出发点是“事物的实效真理”,而非“对事物的幻想”(《君主论》第15章)。这一主张表明,用今天的话来说,亚里士多德等人太过理想化或太过天真。然而,亚里士多德不大可能如此天真,无法察觉到马基雅维利对道德德性提出的那类异议。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忒拉绪马霍斯、格劳孔和阿得曼托斯等人便强有力地表述过类似异议(343c-344c、357a-367e5)。我们可以注意到,忒拉绪马霍斯与马基雅维利持有相似论点(但不必仅把马基雅维利视作现代版的忒拉绪马霍斯):《君主论》第15章讲道,道德审慎之人会毁于那些无视道德的人之手;忒拉绪马霍斯认为,正义者会败于不义者。我们有理由假定,作为柏拉图的学生与《理想国》的读者,亚里士多德充分考虑过忒拉绪马霍斯的论证(参见《政治学》2.1-5)。而且我们将很快看到,对于高贵(或道德德性)与善之关系,亚里士多德并未完全拒斥忒拉绪马霍斯-马基雅维利式观点。所谓“善”,我指的是所有就其自身而言好的事物,或是那些对获取这类事物来说需要或有用的东西。对亚里士多德来说,最重要的善是“灵魂合乎德性的实现活动”,亦即幸福的核心(《尼各马可伦理学》1.7.1098a16-17、1.8.1098b12-16)。但无论如何,充分施展道德德性不仅需要生命和健康,还需要财富(《尼各马可伦理学》1.8.1099a31-1099b7、1.9-10.1100a4-14)。对亚里士多德来说,善还包含快乐,或包含某些类型的快乐(《尼各马可伦理学》7.12-14、10.1-5)。或许可以论证说,高贵与善处于完美的和谐关系之中。在《论义务》(De officiis)中,西塞罗就是这样论证的。他说,高贵(honestum)与有用(对他来说,有用包含所有善好之物)之间永远不存在冲突,因为所有高贵之物都有用,没有任何不高贵的事物是有用的。西塞罗将这种观点归于廊下派,并将其与漫步派(亦即亚里士多德学派)以及其他学派的观点区分开来,他说,这些学派会认为有些高贵之物并不有用,反之亦然。正如他在《论善恶之极》(De finibus)中所言,亚里士多德认为健康、力量、财富、荣耀等诸多其他事物都是好的,但它们不高贵。这或许表明,弃绝这些事物可能是高贵的,但不是好的。西塞罗对亚里士多德立场的理解与《尼各马可伦理学》中的内容相符(亦参《修辞术》3.16.1417a26-27)。在这部作品开篇部分,亚里士多德遵循了一些有声望的意见,认为践行道德德性不仅高贵,还会让真正有德之人感到快乐,从而有助于实现幸福,因为人们通常认为幸福包含快乐。因此,合乎德性的行动“善且高贵”(《尼各马可伦理学》1.8.1099a22)。但随后在探讨勇敢这一德性时,亚里士多德不得不对这一说法作出限定。勇敢地忍受伤痛和死亡很高贵,但这并不纯粹令人快乐。除了身体上的痛苦,勇敢献身的人还将遭受巨大的心理痛苦:他会痛苦地意识到,自己失去生命的同时,也正在“被剥夺最大的善”(《尼各马可伦理学》3.9.1117a32-b16)。在亚里士多德对慷慨的讨论中,我们进一步发现了高贵与善并不简单重合的迹象。慷慨之人需要钱财去变得慷慨,但他不愿花心思赚钱,因为他并不推崇钱财,认为钱财本身并非值得严肃对待之物。因此,除非慷慨之人继承了一笔钱财,否则我们很难理解,为何他有足够多的钱财去施予他人——而他的家族最初又是如何得到这笔钱财的呢?我们也不容易看出,他将如何避免自己逐渐变穷。诚然,慷慨之人不会对其钱财漫不经心,因为他意识到如果自己失去钱财,他将不能变得慷慨。尽管如此,“在很大程度上,慷慨之人会过度施予,以致给自己留的东西太少,因为慷慨之人的典型特征是不会为自己着想”。慷慨依赖于对自身物质需求的某种高贵的遗忘,甚至是对自身物质需求的无知:部分原因在于,他未曾经历过这种需求,继承钱财的人比通过努力获得钱财的人更有可能变得慷慨(《尼各马可伦理学》4.1.1120b2-6、11-13)。既然高贵与善并不重合,人们就可能倾向于把高贵理解成一种自我牺牲或利他的形式。但是,或许除了正义之外,我们不能这样理解《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其他的道德德性(《尼各马可伦理学》5.1.1130a3-4)。考虑一下亚里士多德论述勇敢时的悖谬。尽管他指出战争中的勇敢是这种德性的主要形式——因为战争包含最高贵的危险——但他并没有说,勇敢之人是为了自己的城邦或祖国而战。相反,勇敢之人这样做是“为了高贵,因为这是德性的目的所在”(《尼各马可伦理学》3.6.1115a24-32、3.7.1115b12-13)。如果有人问,为何战争中的危险最为高贵?部分原因无疑是,战争将整个城邦的福祉置于危险之境。但亚里士多德拒绝把勇敢呈现为城邦福祉的附属物,他在此甚至没有提及城邦福祉。亚里士多德确实提到过,不管城邦还是君主,都会赞誉勇敢,但他将这些荣誉与勇敢的高贵性(而非功用性)关联在一起(《尼各马可伦理学》3.6.1115a28-32)。如果勇敢之人战死沙场,他就并非为了他的祖国本身而死,而是为了高贵而死(参见《尼各马可伦理学》9.8.1169a17-26)。慷慨的情形也与此类似。尽管慷慨之人凭借其赠予使他人受益,但他并非为了施惠他人本身而这样做,而是因为施惠他人很高贵(《尼各马可伦理学》4.1.1120a21-25)。与勇敢一样,我们不应把慷慨理解成某种形式的利他主义。因为“对一个人来说,如果他是为了自身而非他者存在,我们就称他为自由人”(《形而上学》1.2.982b25-26)。难怪亚里士多德的道德观会因其“自我沉迷”(self-absorption)而饱受指责。但是,倘若他以其他方式[构想道德],那么就会使更高的德性从属于更低的物质福祉,并且会削弱德性与幸福之间的关联(《尼各马可伦理学》1.7)。如果不能把采取高贵行动主要理解为对他人行善,那么就必须将其视作对自己行善,那些秉有道德德性的人确实作此理解(参见《尼各马可伦理学》9.8.1169a26-29)。但事实上,正如我们所见,高贵与自身的善之间并不简单或始终保持一致。面对这一悖谬,我们必须超越道德维度,以更宽泛的视角审视高贵。宽泛地讲,不能以必需与有用来界定高贵,高贵有别于且高于它们。人们为了高贵本身而选择它,而非为了其他目的这么做;高贵是目的,其他一切事物是达致这一目的的手段。“在与行动有关的诸事项中,一些针对必需和有用之物,另一些针对高贵之物”,人们必须为了后者追求前者。因此,人们必须为了和平追求战争,必须为了闲暇追求忙碌或事务。某些在和平与闲暇中进行的活动——尤其某些理智活动——呈现出是最为高贵的。因为,这些是唯一完全为了自身而追求的活动,从而是唯一真正自由的活动(《形而上学》1.2.982b25-28)。吴寿彭 译,商务印书馆,2022年
自由人(free man)便是宽泛意义上的慷慨之人(liberal man),亦即接受过自由教育(liberally educated)的人。他们首先会被教导高贵地使用闲暇,“因为[对高贵的闲暇的自然渴求]是万物的始点[或本原]”(《政治学》8.2-3.1337b4-35)。高贵地使用闲暇,亦即依据人灵魂中较好的理性部分来使用它。若引导得当,这一部分便能产生最卓越的德性,并提供最纯粹、最自由的快乐——在最理想的情况下,是沉思或哲学中的快乐。哲人的愿望不是通过施予钱财来展现自己对金钱的优越性,而是让钱财服务于最高贵的目的,即致力于沉思真理的生活(《欧德谟伦理学》8.3.1249b16-19)。作为哲人(而非社会成员)时,他并非狭义上的慷慨之人,因为他不需要通过慷慨来实现其目的;类似的说法也适用于他对勇敢和其他道德德性的态度(《尼各马可伦理学》10.8.1178a28-b7)。简言之,在哲学活动层面,高贵与善之间的张力不复存在。《尼各马可伦理学》最后的第十卷教导我们,考虑到道德行动的活动,这些行动显得受到限制且缺乏闲暇。它们经证实其目的是有别于自身的事物(例如,和平与闲暇),并非因其自身而值得选取(《尼各马可伦理学》10.7.1177b4-18)。但从某种方式上看,哲学活动确证了道德本身的高贵性,使我们更加理解这一点。回看第三卷至第五卷所呈现出的道德德性,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与沉思类似,并指涉沉思的高贵性,尽管它们未必是[实现沉思活动的]工具。勇敢与慷慨至少有其高贵之处,部分原因在于它们体现了某种自由。哪怕这种自由只是“摆脱某种束缚的自由”(freedom from),即亦摆脱对必要和有用事物(如生命和财富)的奴隶式依附。也就是说,这些德性至少部分源于这种意识:舒适的自我保全不会是一位严肃之人的最终目标。而这种意识经由深思后,指向第十卷的结论。相比于那些有利的和有益的事物,大度之人更想拥有高贵(或美)而无利可图的事物,因为后者更为自足;最完满的自足将被证明可在沉思中寻得(《尼各马可伦理学》4.3.1125a11-12、10.7.1177a27-b4)。大方的例子尤其引人注目(这一德性与花费大额钱财有关):大方之人“类似知者,因为他能静观(θεωρῆσαι)什么是合适的消费对象,并能以适当的方式大额花费”(《尼各马可伦理学》4.2.1122a34-35)。因为亚里士多德论证过沉思的优越性,因而道德德性作为沉思这一最高事物的类似物,同样可谓保有其高贵性(《尼各马可伦理学》10.7-8)。由此,亚里士多德在哲人与绅士之间建立起了实际的关联。尤其在《尼各马可伦理学》前半部分,亚里士多德为绅士们提供了一幅令人印象深刻的自我画像,描绘了他们的现实样貌或渴望成为的样子。这一画像无论在清晰度、全面性还是可理解性上,都超过其他文本对绅士形象的描述。通过指出道德德性与沉思德性之间的和谐,亚里士多德为绅士的道德信念提供了某种理性支撑。所有这些都使绅士们倾向于敬仰哲学。毫无疑问,他们更可能与哲学为友,因为他们爱慕高贵(美)且无用之物,而不是像大多数人那样,主要爱慕财富与权力,并且将对这些事物漠不关心的哲人视作异类(《尼各马可伦理学》10.8.1179a13-16)。▲ 壁画《亚里士多德学派》
古斯塔夫·阿道夫·斯潘根伯格 绘
当然,哲人与绅士之间有关联,却也意味着这两个群体并不相同,我们已看到这一点。大度之人作为完美的绅士,理应自视甚高。他看不起别人,甚至看不起一切事物,“对他而言,无事重大”。因而他“不会感到惊奇”,但哲学却源于惊奇。另外,由于大度之人傲慢不逊,除非确有大事要做,否则通常便会无所事事。然而,哲人就像普通人那样,总是持续地活跃着。大方之人类似求知者(ἐπιστήμων),也就是说他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求知者。正如我们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中了解到的那样,严格意义上的知识或科学(ἐπιστήμη)是关于不变的普遍性的知识,而非关涉流变的个别之物(《尼各马可伦理学》6.2.1139a5-14、6.6.1140b31-32)。虽然大方之人的宏大视野让我们想到通晓普遍性的求知者,但事实上,大方之人主要思索的还是流变的个别之物,亦即那些与当下进行巨额开支有关的事务。更一般地说,从整个第六卷可清楚看到,虽然君子必定拥有明智,亦即践行道德德性所必需的理智德性;但他并不必定拥有或甚至并不追求智慧,亦即关于最崇高或神圣之物的科学(参见《尼各马可伦理学》6.7.1141a9-b3、6.13.1144b30-1145a11)。然而,绅士与哲人之间的这些显著差别(或许还能说出更多差别)并没有消除我们提到的他们之间的关联。总之,亚里士多德认为,高贵与善在道德层面的张力会导向积极的后果。因为这一张力指向一个更高层面,这种张力在那里或许得以消弭。与之相反,马基雅维利教导我们忘却道德的高贵,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这实则切断了通向更高层面的线索。只有实际的成功(practical success),或那些促成成功的品质才显得重要。必须补充的是,马基雅维利所想的实际的成功,实则是那种最卓绝的成功,亦即君主(尤其建国者)取得的成功,例如摩西、居鲁士、罗慕路斯和忒修斯那种层级的人所达到的(《君主论》第6章)。这些人的目标是荣耀,而非舒适。对亚里士多德来说,荣耀或荣誉作为德性的确证而被追求,因而它从属于德性(《尼各马可伦理学》1.5.1095b26-30)。马基雅维利却认为,德性是获取荣耀的手段,荣耀并不明确指向任何高于自身的事物。政治与战争不再明确从属于和平与闲暇。哲人自己成了建国者,因此也成了政治人:就像摩西与其他人那样,马基雅维利引入了“新的方式与秩序”(《君主论》第6章、《论李维》第一卷前言)。既然哲人是一名政治人,他便也成了一名战士,因为政治技艺与战争技艺异曲同工(《君主论》第14章开篇)。因此,在马基雅维利的体系里,绅士并未被赋予光荣的身份。《君主论》中的绅士卑劣可耻,他们把自己卖给出价最高的切萨雷·博尔贾(Cesare Borgia)。《论李维》中的绅士危害甚多,因为他们表现出一种不平等,这与秩序井然的共和国格格不入。马基雅维利赞许地提到,日耳曼共和国若抓住任何绅士,便会将其处死(《论李维》第一卷第55章)。马基雅维利用君主(包括作为君主的哲人)与人民之间的关联,取代了哲人与绅士之间的关联。这之所以可能,乃因为他的哲学就是(或至少将自己表现得)绝对有用或“有实效”。马基雅维利式的人物追求“荣耀与财富”。亚里士多德式的绅士并非对这些善物无动于衷,但他不会把心思全放在上面。如我们所见,绅士最喜欢拥有钱财的地方在于,钱财为他提供了施予的机会。绅士会理直气壮地要求得到应得的荣耀或荣誉,但他不会对此感到十分欣喜,因为他意识到“对于完善的德性,荣誉不是充分的奖赏”(《尼各马可伦理学》4.3.1124a5-9)。正是这种高贵的矛盾心理(而不仅是天真心理)解释了为何绅士有时会败于小人。例如,由于他的慷慨,他宁愿在商业事务中偶尔受骗,也不愿对钱财过度费心(《尼各马可伦理学》4.1.1121a4-5、5.10.1137b34-1138a2)。如我们所见,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生活能够最彻底地解决这种矛盾心理带来的困难。绅士不崇尚钱财,但他需要钱财来变得慷慨。哲人也不崇尚钱财,但他需要的钱财要少得多:苏格拉底虽一贫如洗,但这并没有使他变得更糟。然而,仅仅指望哲学是不够的。因为不管我们如何自命不凡,我们中的大部分人都不能成为哲人。即便是哲人,不管他的思想多么神圣,他仍是一位不自足的人,因而必须与他人共同生活(《尼各马可伦理学》10.7.1177b26-34、10.8.1178b33-35)。无论绅士还是哲人,良好生活的基础都是闲暇,而闲暇需要城邦这一政治共同体来保障。城邦及其政制可提供一些最初用于自我保存的必需之物,它们理应得到重视。但正如我们在马基雅维利那里所见,对这些必需之物无条件的尊崇会危及道德德性的地位,因为道德德性本身就是崇高的目的。为应付这一难题,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与《政治学》这两部相对独立又有所关联的著作中,亚里士多德以不同方式论述了道德德性。这样做是为了保护为其自身而践行的道德免受政治权变的压力,同时给予权变应有的重视。例如,如我们所见,《尼各马可伦理学》把勇敢呈现为以高贵为目标,而没有提及城邦的需求。即便亚里士多德考察他所谓的政治勇敢或公民勇敢(这种勇敢有别于真正的勇敢)时,他也没有说公民应为了城邦经受危险,而是说出于对荣誉这一高贵之物的关注,公民才做这样的事(《尼各马可伦理学》3.8.1116a15-29)。另一方面,《政治学》把勇敢展现为达成政治目的的必要手段,旨在保障自由,因而也是保障闲暇(《政治学》7.15.1334a16-22)。总体来说,在《政治学》中,公民德性(civic virtue)成为了焦点。亚里士多德明确指出,公民德性的目的超出了自身,旨在维护政治共同体或政制(《政治学》3.4.1276b27-31)。同样的功利原则也被用于界定正义:正义是共同的利益,损害城邦的事不可能正义(《政治学》3.10.1281a17-21、3.12.1282b16-18)。一并考虑《尼各马可伦理学》与《政治学》,我们开始意识到,作为目的本身的道德德性与朝向共同利益的道德德性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因此,从《政治学》的视角看,人们在践行德性时,必定要考虑政治权术,从而受到影响(即便德性是政治的最高目的)。我们很难说清,人们应该对政治权术考虑得多么深远。但毫无疑问,亚里士多德式的统治者不会以危害政制的方式践行慷慨或任何其他德性,因为这并不正义。因而,亚里士多德不会断然拒绝《君主论》第16章中的教导。马基雅维利也许会观察到,人们通常从他那里比从亚里士多德那里更易获得这种教导。他兴许还会抱怨说,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与《政治学》中对德性的两套论述,分裂了人们的忠诚,并剥夺了他们采取必要的极端措施的意愿。或许,亚里士多德会如此回应:他的论述反映了人类境况中不可避免的二重性。一方面,人需要城邦,因此必须服务并保卫它;另一方面,城邦自身还在一定程度上指向高于自我保存的目的,即践行目的在自身之中的道德德性或其他德性,或者说践行高贵的闲暇生活。倘若权变意味着为了获得“荣耀和财富”甚或为了保全政治共同体可不择手段,那么它便不能成为我们唯一的尺度。因为这些目的并非最高目的,因而不必竭尽才智追求它们。这一说法是否为真,或在多大程度上为真,似乎是亚里士多德与马基雅维利之间道德争论的核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