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刊首发|夏尔凡:蒙田的怀疑主义论证及其伦理意涵
编 者 按
本文刊于《古典学研究》2025年第3期(总第6期),注释从略,感兴趣的读者可查阅原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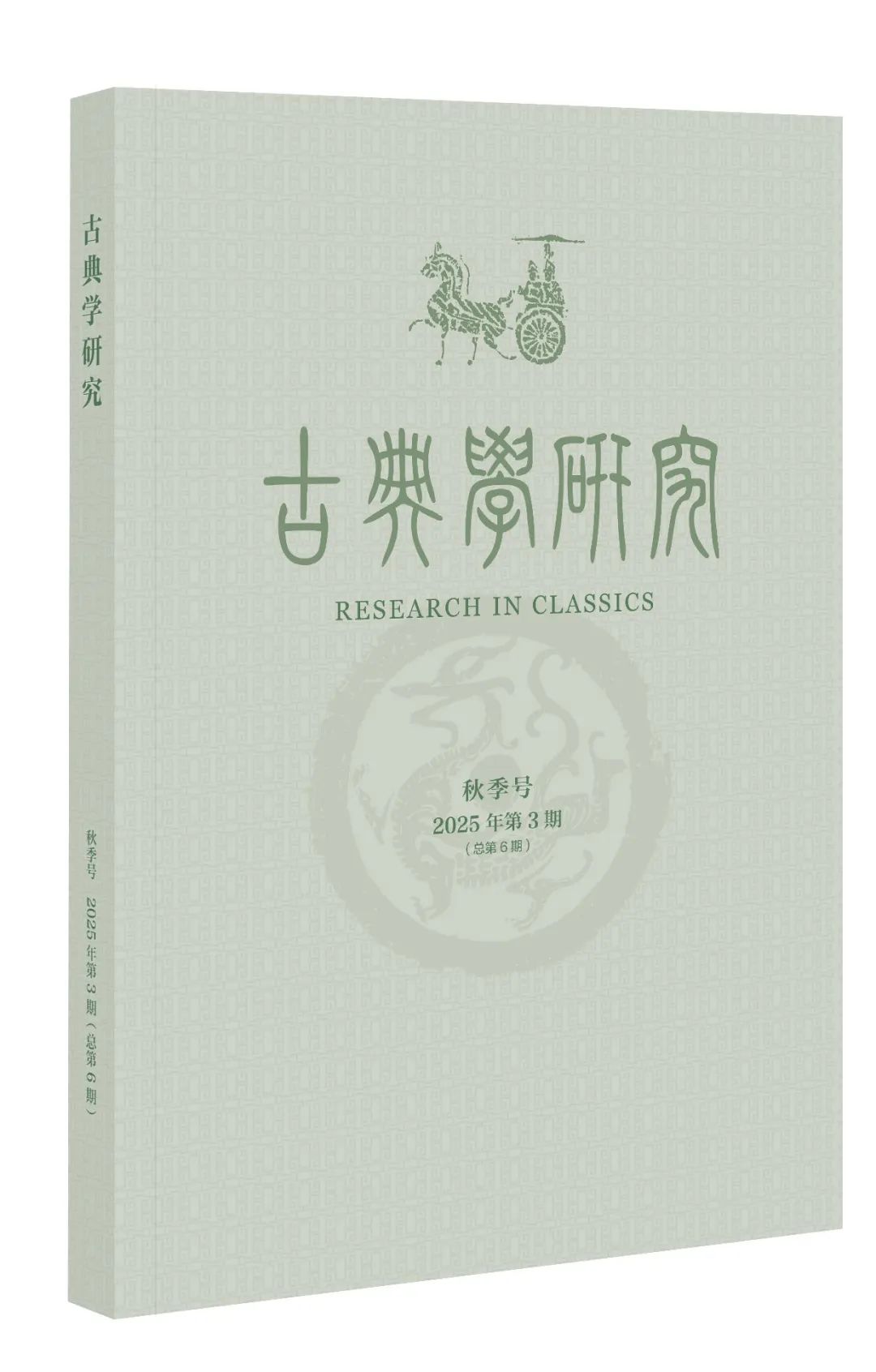
长期以来,蒙田思想的怀疑主义性质是蒙田研究中的焦点。哲学史家往往关注蒙田在怀疑主义史上是否承前(与皮浪主义及学园派的关系)以及如何启后(如笛卡尔),鲜有关注他的怀疑主义与其伦理学之间的关系。而对近百年蒙田研究有奠基之功的皮埃尔·维莱是极少数例外,在他看来,汪洋恣肆的《随笔》一以贯之的根本关切是“人应该如何生活”。

▲ 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1533—1592)
维莱关注《随笔》的形成过程,将怀疑主义视为蒙田在早期的廊下派倾向与成熟的伊壁鸠鲁派立场之间经历的一场阶段性智识“危机”。这一阶段的蒙田在怀疑主义中找到了他天生的“相对主义直觉”的表达。怀疑主义是蒙田的阶段性精神气质,其伦理意涵止于与相对主义的亲和。因此,维莱没有重视蒙田对怀疑主义的具体论证,以及这一论证与蒙田成熟的伦理观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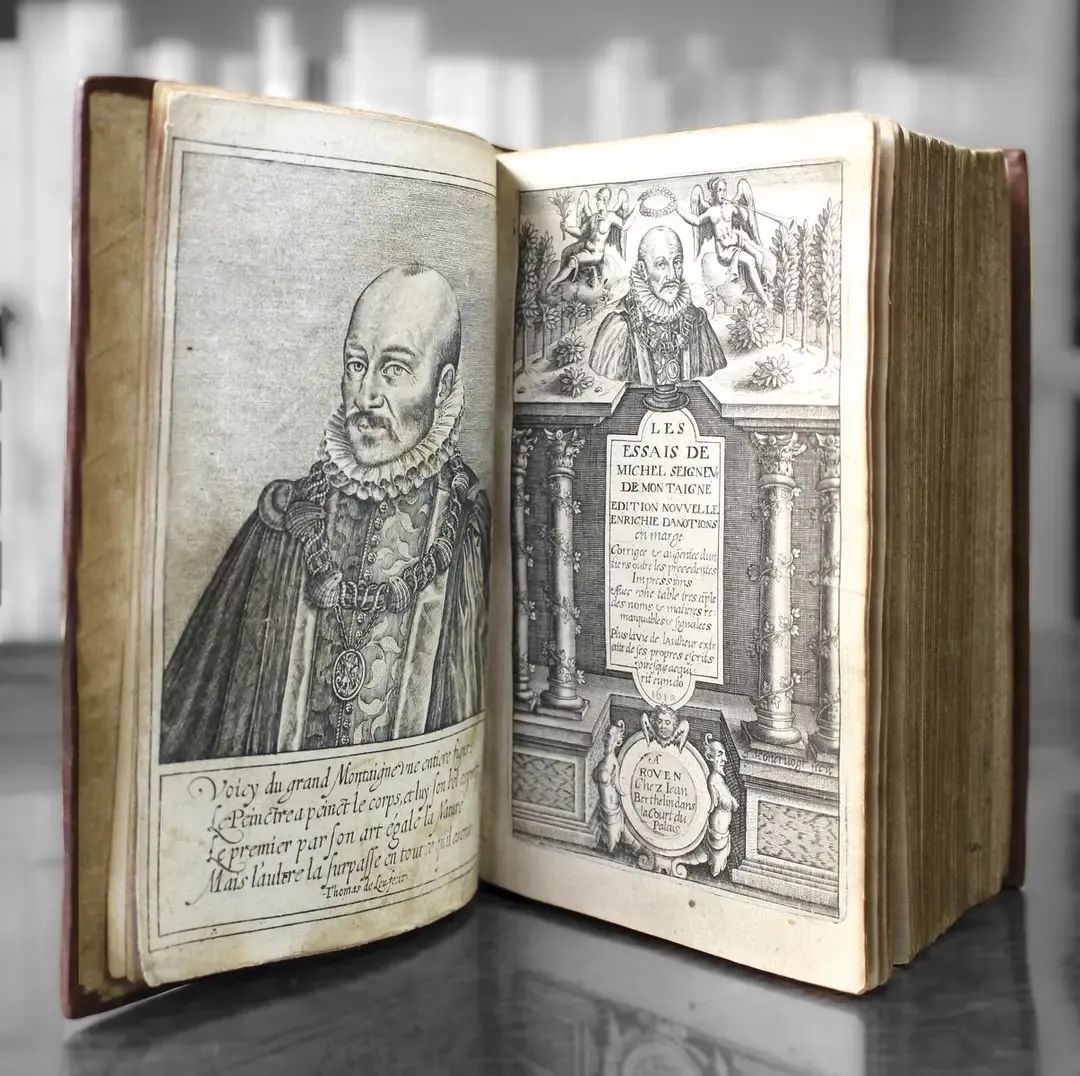
▲ 蒙田《随笔》,1619年
“人应该如何生活”历来与“人应该如何共同生活”的问题紧密关联。蒙田身处政教关系紧张的历史处境,后一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尤为突出。有的政治哲学学者探讨了蒙田怀疑主义的政治意图。杨晓强在《蒙田的申辩》一文中讨论了蒙田如何通过怀疑主义及其相对主义意涵来瓦解宗教战争中各教派的宗教狂热。大卫·谢弗则指出,蒙田将所有哲学与怀疑主义等同起来,又鼓吹怀疑主义与信仰之间的促进关系,意在哄骗宗教权威宽容哲学活动。蒙田的真实意图是用“怀疑主义”的特洛伊木马瓦解启示宗教,营造激进启蒙与自由的政治环境。
这两位学者都敏锐地看出蒙田的怀疑主义具有政治意涵,但都将其怀疑主义过分简化为政治工具。对蒙田怀疑主义的具体论证的忽视,导致他们未能充分理解蒙田这一立场的伦理与政治意涵。因此,只有先澄清蒙田的怀疑主义论证,才能更准确地把握蒙田的怀疑主义所包含的伦理和政治意涵。
《随笔》中篇幅最长的《为雷蒙·塞邦申辩》(以下简称《申辩》),是理解蒙田怀疑主义的基础。塞邦是西班牙神学家,著有《自然神学》,以理性的方式为基督教信仰辩护。蒙田指出,针对塞邦的自然神学有两种批评:“信仰派”的批评是,理性不如虔信更有助于信仰;“理性派”的批评则是,塞邦对基督教的理性辩护太弱,而更强大的理性论证会导向无神论而非神学。蒙田对这两种批评的回应构成了《申辩》的主体,对第一种批评的回应仅约占全篇的二十分之一,其余都是对第二种批评的回应。概言之,第一个回应着重梳理政治与宗教的关系,第二个回应则主要是在批评自然神学和古代哲学,并在此基础上论证蒙田自己的怀疑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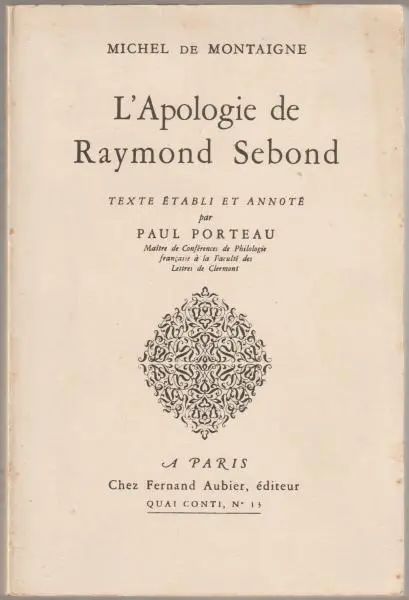
▲ 蒙田《为雷蒙·塞邦申辩》
Aubier出版社,1937年
如果说《申辩》中的第一个回应讨论的政治与宗教的关系问题是当时欧洲失序的主要症状,那么,蒙田在第二个回应中对基督教神学与古代哲学的批评就是对症下药,因为当时欧洲政教秩序的思想基础正是基督教神学与古代哲学的混合。在这个回应中,蒙田诊断出基督教神学和古代哲学的双重基础是虚荣和理性,进而拆解这个双重基础,然后通过综合怀疑主义与伊壁鸠鲁主义,勾勒出一幅新的伦理与政治图景。
一
人之虚荣与理性的缠绕
回应信仰派对塞邦发起的挑战之后,蒙田转向这个神学家遭遇到的第二个挑战,即来自理性派的批评:
有些人说,他的论证软弱无力,无法证明他想说明的道理,因此,他们能轻易地将其驳倒……在他们看来,他们处于有利的地位,可以用纯属人类的武器来自由攻击我们的宗教。(《随笔》[中],页154–155)
在蒙田看来,这个挑战“比第一个更危险和恶毒”,因此他的回应方式也更加严厉:
我用来压倒这种狂热的方法,在我看来最为合适,那就是压制人的骄傲,并踩上一脚:必须使他们感到“人”的虚妄、虚荣和虚无,把他们拙劣的理性武器从他们手中夺过来。(《随笔》[中],页155)
理性派挥动“拙劣的理性武器”来反对塞邦的理性神学,蒙田回应这一挑战的方式是揭示人类理性本身的虚弱。当然,这不仅是对理性派挑战者的回应,也是在批评塞邦的理性神学。
蒙田在回应理性派时清楚表明,他的目标不仅是针对其理性论证的逻辑有效性,也包括这些理性主张背后的人类虚荣——理性基于虚荣。理性派相信人是“这世界至高无上的主人”,而在蒙田看来,这种相信不过是一种幻觉罢了,它实际出自人类对自身理性的信心(《随笔》[中],页157)。正是出于虚荣,人类才声称,在所有动物中,惟独人类具有理性能力。通过理性,人类“发现”自己在自然秩序中享有独特地位,也就是声称自己享有辨认自然秩序内在构造的独特能力,并且辨认出人在自然秩序中享有的独特地位:
人认为自己拥有这种特权,即在这巨大的建筑中,唯有人能看出它的美和构造,因此唯有人能感谢建筑师,并计算世界的损益。(《随笔》[中],页157)
只有理解了蒙田对理性派的这一诊断——人类的理性实际出自人的虚荣,我们才能理解他接下来的回应策略:进入对理性更为实质性的理论批评之前,他先通过赞颂动物来“压制人的骄傲”(《随笔》[中],页1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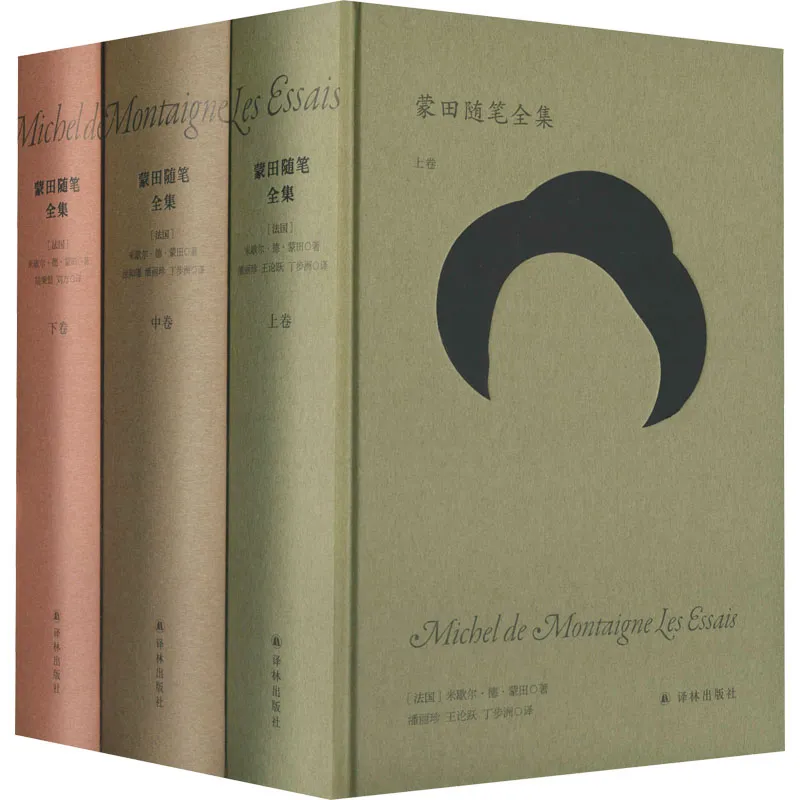
▲ 《蒙田随笔全集》
[法]蒙田 著,潘丽珍 等译,译林出版社,2022年
二
克服人之虚荣的“动物颂”
通过比较动物和人类,蒙田否定人类对自身优越性的各种主张。他首先展示出,所有人类引以为傲的能力——语言、谋划、自由选择、学习乃至宗教虔敬——动物都有(《随笔》[中],页169–182)。相反,动物还可能有人类不具备的“其他许多能力”,只是它们“丝毫也没有对我们显露出来”而已(《随笔》[中],页183)。
在德性方面,动物具备人引以为傲的正义、同情、忠贞、宽宏、自省、仁慈等美德,并且比人做得更好。比如,动物就更节制,因为它们不受人为激情的困扰。动物也比人类更诚信,在它们中间还有“为了互相团结而组成的社会与联盟”(lasocieté et confederation qu’elles dressent entre elles pour se liguer ensemble;《随笔》[中],页196)。
动物中有科学家和工匠:金枪鱼与季节相关的生活习性表明它们具有天文学知识;翠鸟筑巢体现出天才般的技艺。动物甚至还有“想象”和抽象思维的能力(《随笔》[中],页184–201)。即便在“狡诈”方面,动物也不遑多让——蒙田还用“狡诈”(subtilité malitieuse)来强调动物的聪慧(《随笔》[中],页188)。
人类有什么独特之处呢?蒙田用近50页篇幅(以中译本计算)细数了人类的如下特点:脱轨的想象力、人为的肤浅欲望、战争、背叛、傲慢等(《随笔》[中],页156–206)。结束时他这样罗列人类的独特之处:
反复无常,犹豫不决,无法肯定,痛苦,迷信,对将要发生之事(甚至死后之事)的忧虑,野心,贪婪,嫉妒,妒忌,有无度、奇特和无法克制的欲望,战争,谎言,不忠,诽谤和好奇。(《随笔》[中],页206)
“好奇”(curiosité)被视为理性的起点,而在蒙田那里却成了专门批评的对象,这无异于对亚里士多德提出挑战。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好奇是人类的根本欲望之一,它指引人走向最高贵、最愉悦的沉思活动(《形而上学》980a21–983a23)。与此相反,蒙田大谈没有好奇心且安于无知的生活如何幸福:例如,“工匠和农夫”或“巴西土著”就比“瓦罗和亚里士多德”以及“大学校长”(recteurs de l’université)更幸福(《随笔》[中],页207–214)。这意味着,无知比有学识更能促进灵魂和身体的健康。通过这些生动的人物形象,蒙田挑战了沉思作为最高生活的古典理想,转而肯定动物般的生活。这些朴素的幸福生活的新榜样背后,是对人类善的新理解——“至善莫过于灵魂和肉体的宁静”(《随笔》[中],页209)。所谓“宁静”(tranquillité),按蒙田在后文的解释,即“没有痛苦”(《随笔》[中],页216)。
通过讨论“好奇”,蒙田进入了他在《申辩》中要处理的核心问题——知识对于人的意义:
人如果聪明,就会通过事物对人的生活是否有用、是否适合来评估事物的价值(Si l’homme estoit sage, il prendroit le vrayprix de chasque chose, selon qu’elle seroit la plus utile et propre à sa vie)。(《随笔》[中],页208)
知识会使人幸福吗?蒙田的回答是否定的,这让人极易联想到后世的卢梭(1712—1778)对知识的批评:知识对人的幸福无用,对政治共同体有害(《随笔》[中],页214–224)。蒙田甚至认为,“好奇”不仅是“人与生俱来的恶”(un mal naturel etoriginel en l’homme),甚至是人世间一切恶的源泉,因为它带来了所有其他恶(《随笔》[中],页223)。说到底,“好奇”是人类因偏离自然而陷入不幸的起点,人类引以为傲的对知识的好奇对人的生活其实无益。
三
何谓真正的“无知之知”
紧接着对“好奇”的抨击,蒙田进一步抨击人类的理性或者说理性主义的哲学观,以回答两个相关的问题:一,人类自古以来自以为获得的知识是不是真正的知识?二,真正的知识可能吗?
人是否能找到他寻找的东西,这么多世纪的寻找,是否使人获得某种新的力量和确实的真理?(《随笔》[中],页226)
蒙田从苏格拉底的无知之知入手展开讨论:
自古以来最聪慧之人,被问到知道什么时就回答说,他知道自己一无所知(qu’il sçavoit rien)。(《随笔》[中],页227)
这是对苏格拉底无知之知的一种别出心裁的表述。事实上,柏拉图《苏格拉底的申辩》中的苏格拉底是这样表述他的无知之知的:
或许我们两个都不知道任何美和善的东西,但是这个人,他觉得他知道某事,虽然他并不知道……我比这个人更智慧,就在于这个微小之处:我不知道的事情,我不觉得我知道(ὅτι ἃ μὴ οἶδα οὐδὲ οἴομαι εἰδέναι)。(《苏格拉底的申辩》21d)
苏格拉底接下来还说:
最后我来到工匠们这里。我意识到我几乎不知道任何东西……他们知道我不知道的事情,他们因而比我更有智慧。(《苏格拉底的申辩》22c–d)
但紧接着这段说法,苏格拉底批评这些工匠仅仅因为自己知道的东西,就以为自己在其他最重大的事情(τἆλλα τὰ μέγιστα)上也有智慧。显然,苏格拉底承认他对工匠的技艺几乎无知,为的是引出对工匠们自以为知道“最重大的事情”的批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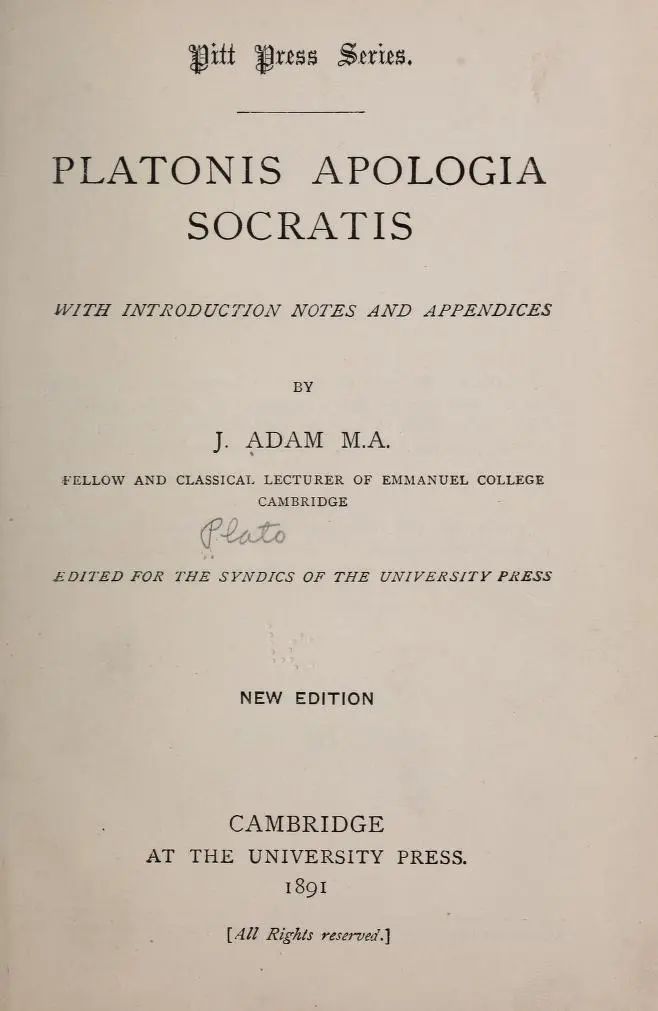
▲ 柏拉图《苏格拉底的申辩》,剑桥大学出版社,1891年
苏格拉底强调,他有别于那些对自己的意见感到自满的人,他并不认为自己知道那些他事实上不知道的事情。具体而言,他“或许”不知道的正是那些“最重大的事情”——什么是“美和善”。《理想国》的洞穴寓言和《会饮》中爱的阶梯表明,要拥有关于“美和善”的知识,需要拥有关于美与善的理念的知识,而这是最困难的知识。苏格拉底承认他或许没有这一最为困难的知识,与蒙田对苏格拉底无知之知的表述显然相去甚远。
蒙田对苏格拉底无知之知的激进表述,预示了他接下来处理基督教神学与古代哲学的整体思路:它们关于“重大知识”的谦逊、对人类理性限度的承认,都内在地指向彻底的怀疑主义。
四
走向彻底的怀疑主义
蒙田的《申辩》接下来的论证分为四步:一,将所有哲学还原为怀疑主义;二,将感官表象与外在世界之间关系的不确定性确立为怀疑主义的基础;三,确立“我感觉”的确定性;四,在此基础上提出与这一怀疑主义相适应的自然愉悦的伦理观。
所有哲学都是怀疑主义
在蒙田看来,对成见的怀疑、对问题的尝试性探索是所有哲学的根本要素,因此,任何哲学教条都站不住脚:
教条主义者……并不是想为我们建立某种确定性,而是要向我们展示,他们追逐真理走得有多远……当蒂迈欧要告诉苏格拉底,他对神祇、世界和人类知道些什么,提出要像人对人的谈话那样来谈这些事,并说如果他的解释和任何一个其他人的解释一样可能,那么这就已足够,因为确切的解释超过了他或者任何有朽之人的理解……亚里士多德常常堆砌许多不同的意见,以便跟他自己的进行比较,并使我们看到他走得有多远,离可能性更近了多少……亚里士多德是教条主义者的君主(le prince des dogmatistes);然而我们从他那里学到:更多的知识导向更进一步的疑惑(que le beaucoup sçavoir apportel’occasion de plus doubter)……这就是披着肯定性之皮的皮浪主义(un Pyrrhonisme soubs une forme resolutive)。(《随笔》[中],页236–237)
这段话无异于说,无论柏拉图式的对话,还是亚里士多德通过考察现有意见的疑难推进思考,都包含了对人类知识限度的承认。问题在于,这种对人类知识限度的承认与皮浪主义是一回事吗?蒙田的推论是:一旦哲人承认自己对人类的知识有限度,他就不得不走向怀疑主义。为了完成这一推论,蒙田就得论证:不完整的、不完全确定的知识即意味着“一无所知”。他通过批判三种追求知识的进路来实现这一目的:首先,理性神学对上帝存在及其属性的论证;其二,柏拉图的灵魂上升的进路;第三,所谓“亚里士多德式”的经验主义进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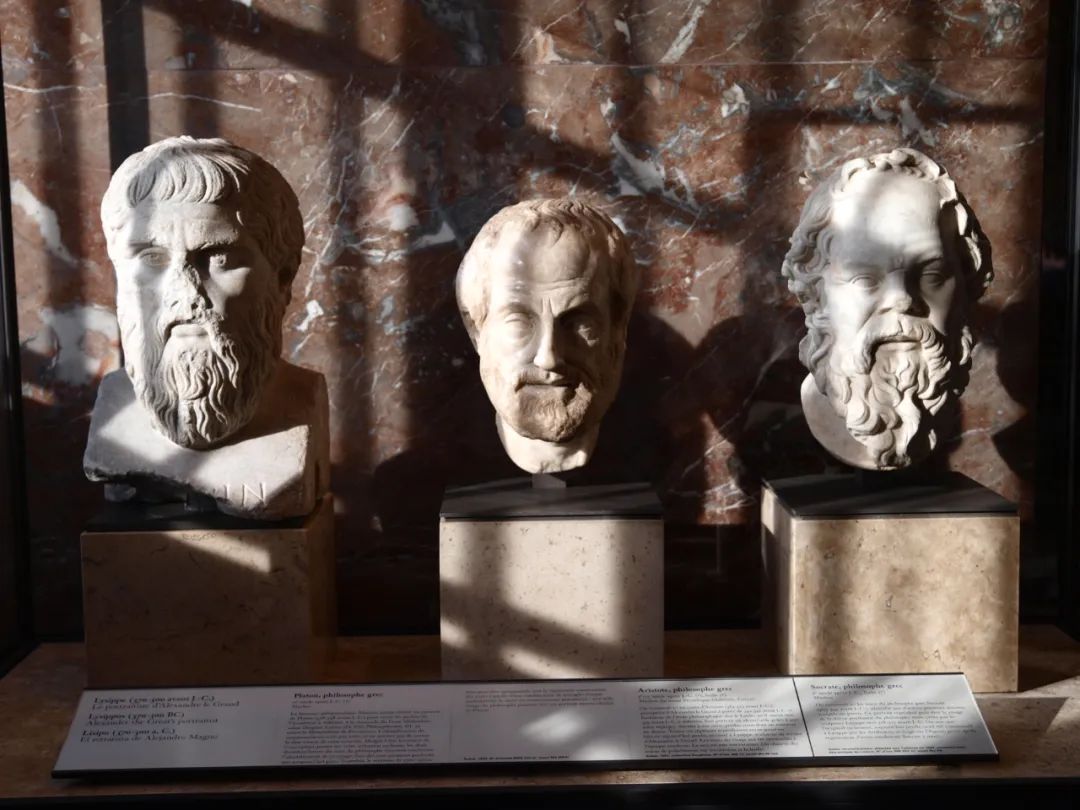
▲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苏格拉底雕像(从左至右),法国卢浮宫 藏
对理性神学的批判
在蒙田看来,基督教神学证明上帝的存在及其属性的关键点是,从人类的不完美推导出一个完美的存在者:
我们无法创造世界:因此就有一个比我们的本性更优越的本性做了这件事。认为我们是宇宙中最完美的存在者,是傲慢愚蠢的看法,因此一定有更好的存在者:上帝。你看到一座富丽堂皇的住所,虽然不知主人是谁,至少不会说是为老鼠所造。我们看到天宫的神圣构造,难道不应该认为它的主人比我们更伟大?……我们有生命、理智、自由,我们敬重善良、慈悲、正义,因此这些品质一定也存在于上帝之中!(《随笔》[中],页271–272)
蒙田言简意赅地总结了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我们可以设想比我们更好的存在者,既然他比我们这些“存在”的人更好,也就一定“存在”)和宇宙论证明(世界的秩序与美指向一个比人更完善的建筑师或主人)。在证明存在这一完美的存在者后,人将所有自己以为“好”的属性一股脑堆到这一存在者身上。实际上,这些关于上帝的论证不过是对人的“神化”,它们的自相矛盾之处不在逻辑层面而在心理层面:这些证明从虚伪地谦逊承认人类不完美出发,最终却从人类的视角来理解“完美”,实质上是将上帝理解成最完美的人,这可谓虚荣的极致。蒙田引用奥古斯丁来批评这些人类中心主义论式的神学论证:
当然,人们想象出的不是上帝,因为他们无法想象出上帝来,他们想象出的是他们自己;他们比较的不是上帝,而是他们自己,即不是跟上帝比较,而是跟他们自己比较。(《随笔》[中],页272–273;原文见奥古斯丁《上帝之城》12.18)
暂且不论奥古斯丁这段话在原语境中服务于什么目的,蒙田的引用非常好地表达了他自己的意思:提出这些上帝证明的神学家如果认识到人类根本的不完美,就应该承认自己的认识无法跨越从“自己”到上帝的鸿沟。换言之,基督教对人类不完美的认识与自然神学在根本上互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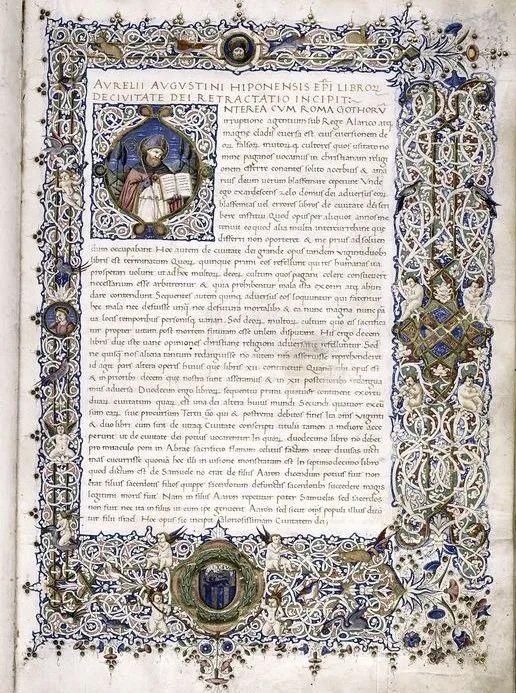
▲ 奥古斯丁《上帝之城》手抄本,1470年
对柏拉图“理念”哲学的批判
蒙田接下来批判柏拉图追求知识的进路:
柏拉图的思想全是关于上天的;他对于神圣事物如此熟稔,以至于他从此被冠以“神圣”之名。他认为在人这么一种可悲的造物中有什么东西可以触及那不可理解的力量,我们是否要相信呢?他[本人]是否相信,我们孱弱的理解力能领悟、我们的感官能承受永恒的至福或痛苦?(《随笔》[中],页253)
显然,蒙田针对的是柏拉图的理念学说。在蒙田看来,这一学说认为人类可以获得最高知识。按照《理想国》和《斐多》中的说法,人可以通过灵魂的上升看见理念,而灵魂的上升要求克服身体的欲望,乃至从身体中挣脱。对此,蒙田假想了一个拟人化的“人类理性”会如何批判柏拉图:在柏拉图的理念世界中,与理念相交往的纯粹灵魂不再是“我”,因为“我”是一个身体和灵魂的混合物;纯粹灵魂获得的神性知识与愉悦,对“我”来说不可想象,“只要其中还有‘我’的某种东西,那其中就没有任何神性的东西”(《随笔》[中],页253)——他稍后补充道,伊壁鸠鲁就很可能会这样批判。紧接着,通过对卢克莱修的一系列引用,蒙田强调人“由身体与灵魂的结合构成”,二者的分离意味着这个人不再存在(《随笔》[中],页255–256)。蒙田甚至跟随卢克莱修一起认为,“灵魂的本质一定是物质性的”(《随笔》[中],页301)。因此,柏拉图所谓“非身体性的灵魂”根本上是自相矛盾的概念。由此可见,蒙田否定柏拉图有关“灵魂上升”的知识的关键点在于强调人的身体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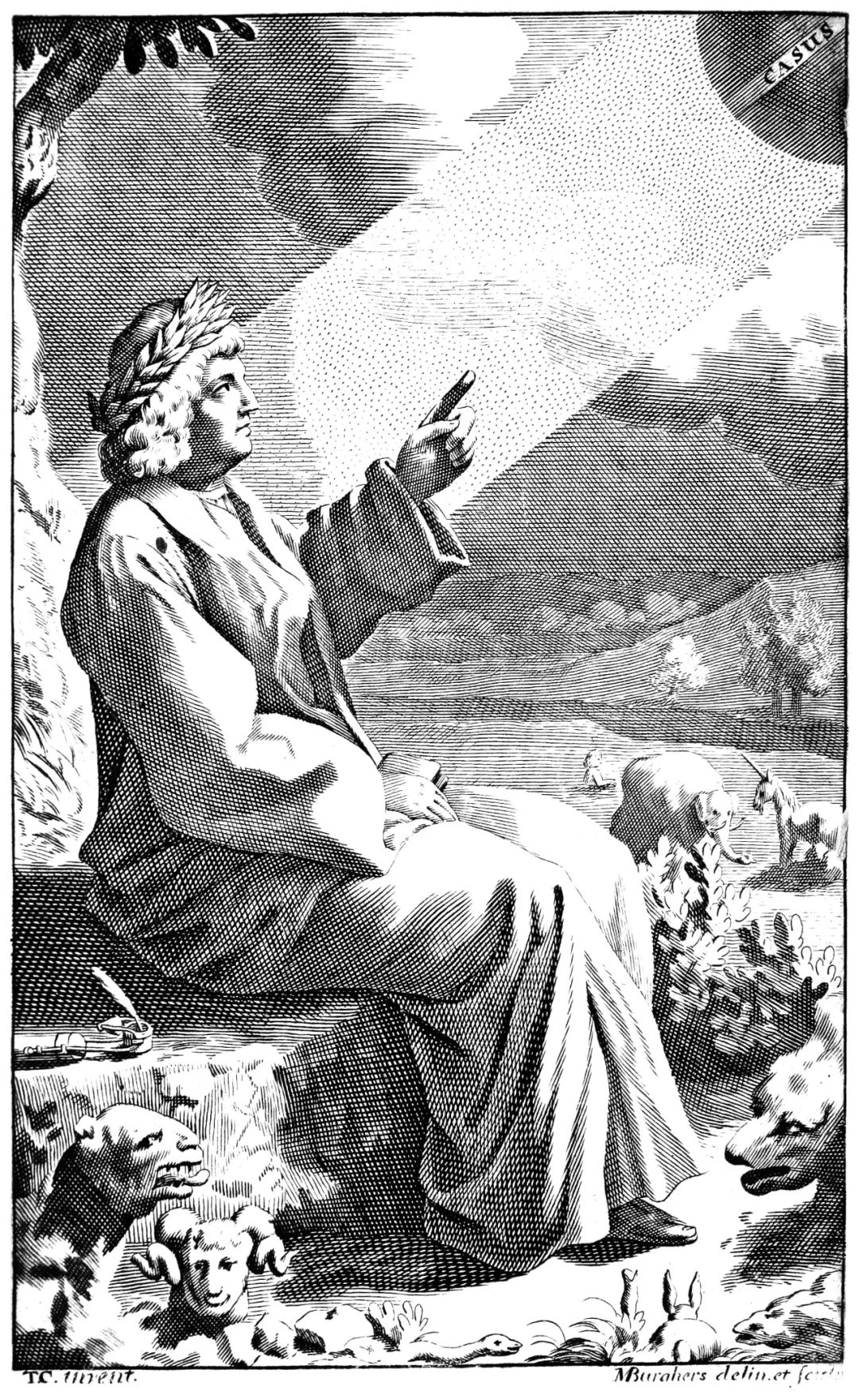
▲ 卢克莱修(Titus Lucretius Carus,前99—前55)
对经验哲学的批判
蒙田对亚里士多德式的经验主义知识进路的批判,以后者最著名的学生忒欧弗剌斯托斯(Theophrastus)为靶子:
忒欧弗剌斯托斯说,人的智慧受感觉支配,因此能在一定程度上判断事物的原因;但如涉及事物的本质或最初的原因,人的智慧就必须知难而退,这是因为它自身有弱点,或因为事情本身的困难。这是一种节制、温和的意见:我们的智慧能认识某些事物,但能力有限,超越这个能力使用智慧,就是轻率的行为。这是折衷之人的意见。
……
当经验显示……这个世纪不知道的事,下一个世纪会弄清楚;科学与艺术不是一次成型的,而是经过无数次雕琢而成形……那我就不放弃探测我力所不能及的东西……我是为后来者提供某种方便,使他们能更顺利地把握这种物质……人可以做到一些,就意味着人类可以做到一切。
但是!如果人像忒欧弗剌斯托斯所说,承认自己不知道事物最初的原因和本质,那他就应该大大方方地放弃其他一切学问。没有基础,他的理智就无所依凭。讨论与探索的唯一目的和终点就是第一原则(n’a autre but et arrest que lesprincipes)。如果他的道路没有这个终点,那么他就被甩入了无限的不确定[无解](irresolution infinie)。(《随笔》[中],页315–317)
蒙田描述了“折衷”的经验主义者“温和”的知识积累图景,但他提醒,这一图景的前提是作为基础的关于第一原则的知识最终是可知的,否则我们永远无法确认所谓的“部分知识”是否真的具有“知识”的地位。没有作为基础的第一原则,来自经验的所谓“部分知识”就不是具有确定性的“知识”。既然折衷的经验主义者承认人类理智的限度,承认第一原则的不可知,他们就应该逻辑自洽地承认,他们根本无法取得任何具有确定性的知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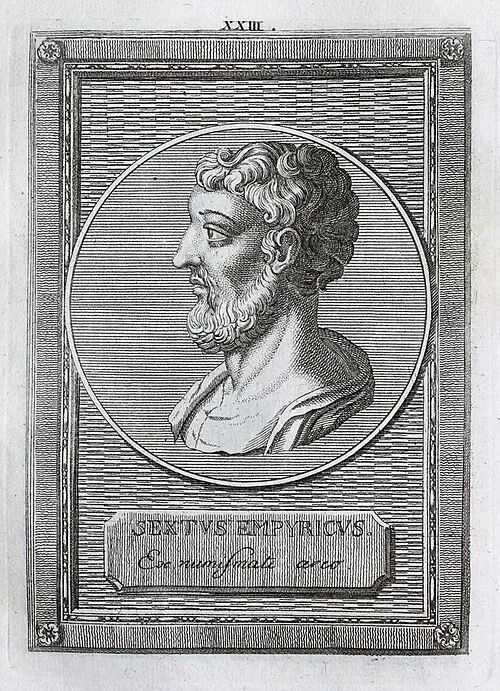
蒙田对经验主义式的知识进步的描述,几乎预示了后来培根(1561—1626)所勾勒的科学进展的图景。然而,作为一个更加融贯和清醒的经验主义者,培根会赞同蒙田对天真的经验主义的批评。培根并不假装“节制”或“折衷”:通过经验对第一原则——用他的话说就是“形式”与“简单自然”——的探寻,处于培根设想的科学研究的核心。他清醒地认识到,经验主义若能成立究竟需要什么。当然,对蒙田来说,培根起心太大,他想要超越“相对于人”(in ordine ad Hominem)的事物,以达到“相对于宇宙”(in ordine ad Vniuersum)的“形式”,进而挣脱“人类心灵的偶像”(humanæ Mentis Idola),最终发现“神圣心灵中的理念”(diuinæ Mentis Ideas)——这样的努力不可能完成。

除了批评天真的经验主义者关于部分真理的主张,蒙田还批评了学园怀疑派的“可能真理”说:判断某事“可能”是真的,这预设了关于什么是“真”的知识——
那一盎司倾斜了天平的可能性,把它放大成100盎司、1000盎司,结果将是天平完全倾向一边,并做出选择,得到完全确定的真理。(《随笔》[中],页318)
换言之,拥有一个可能的真理意味着,存在一个确定的知识来源。然而,学园派之所以提出可能的真理,恰恰是因为他们发现,人类拥有的认识工具(即感官和理性)与其说是确定性知识的来源,不如说是不确定性知识的来源。一旦承认人类官能中固有的不确定性,那就应该认识到,这种不确定性会摧毁任何“可能性”:
如果我们的理智和感觉能力没有基础和支撑,只是随波逐流,随风飘动,那么,让我们的判断被它们的运作所左右就毫无意义,无论它们带给我们什么可能性的表象。(《随笔》[中],页318)
蒙田的思路会让我们想到后来的休谟(1711—1777)在《人性论》(1.4.1)中提出的著名怀疑主义论证:如果人类的官能是不确定性知识的根源,这就促使我们将判断限定为“可能”的判断。如此一来,若对这一可能判断再作判断,由于我们还是离不开自身官能去下这个判断,结果便是我们只能对第一个可能判断形成一个可能判断。于是,我们陷入无限倒退,所判断之事的可能性也随之无限打折扣。不确定性知识的繁衍最终导致彻底的不确定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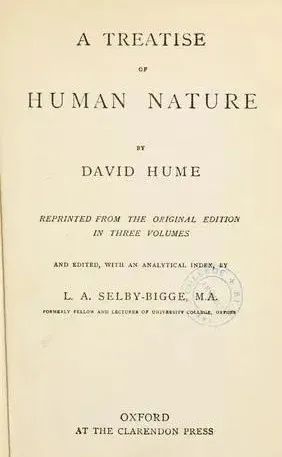
▲ 休谟《人性论》,克拉伦登出版社,1888年
五
基于感官表象不确定性的怀疑主义
对蒙田来说,基督教神学、柏拉图哲学、经验主义都承认人类处境与人类知识的限度,却又都对人类最终可以获得真理抱有乐观的信念。蒙田对这三种理性传统的诊断根本上是心理学诊断:它们既有深刻思考和敏锐洞察带来的谦逊,又不免于“太人性的”虚荣自大。基于这一诊断,蒙田推出自己的怀疑主义哲学观:
事物既非以其形式和本质,亦非以其自身的力量和权威,而暂居(logent)于我们之中……对外部事物的接受取决于我们的看法。(《随笔》[中],页318–319)
“外在对象”如何“暂居于我们之中”?蒙田认为取决于感觉:
被认识的一切事物,无疑是因认识者的官能而被认识……一切知识都是通过我们身体的感觉来完成,感觉是我们的主子……知识始于感觉、可以还原为感觉……这是我们知识的大厦的基础和原则……感觉是人类知识的起点与终点。(《随笔》[中],页354)
“感觉”(les sens)是人类知识的基础,蒙田在这一点上尤其赞同伊壁鸠鲁派——他们“认为任何判断都在于感觉,对事物的认识和愉悦无不如此”(《随笔》[中],页353)。在讨论感官知觉时,蒙田频繁引用卢克莱修集中讨论感觉的《物性论》第四卷。不过,蒙田虽然同意感官是人类知识的唯一基础,却不同意卢克莱修对感官表象真实性的信心。在蒙田看来,感官对外在对象的表象是不确定的、易错的:
人无法逃避的事实是:感觉是他的知识的最高统帅,但它们在各种情况下都是不确定的、可错的。(《随笔》[中],页360)
蒙田复述了经验论者塞克斯都(Sextus Empiricus,约公元二至三世纪)记载的几种关于感官表象具有不确定性的怀疑主义论证:其一,表象受到我们的器官与官能状态的影响;其二,不同认识者对同一事物的感官知觉不同;其三,寻求表象的判断标准会导致无穷后退;其四,感官表象与外在对象自身之间有无法弥合的鸿沟;其五,不同表象之间互相龃龉、矛盾——凡此等等(《随笔》[中],页364–373)。感觉是人类知识的基础,但“我们的感觉不确定,感觉到的事物也不会可靠”(《随笔》[中],页371)。因此,感觉也是“我们的无知最主要的基础和证明”(《随笔》[中],页3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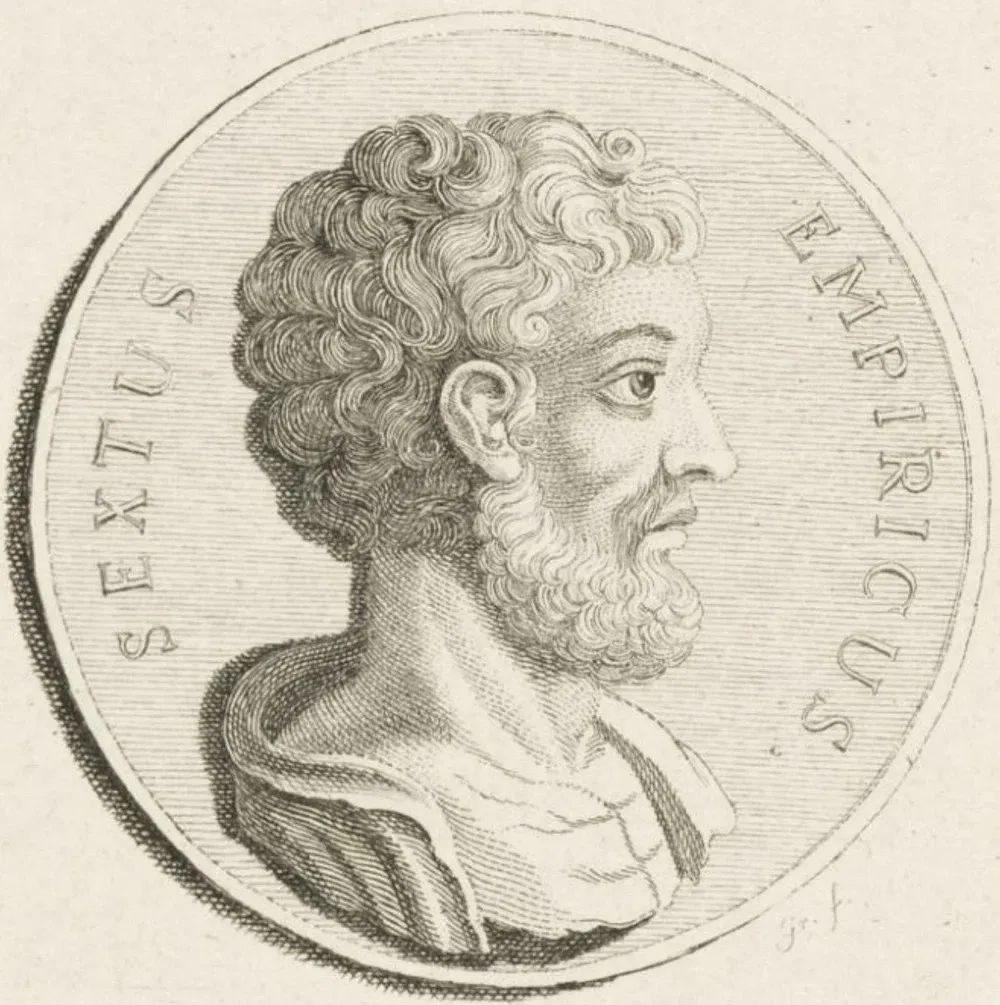
从蒙田的视角看,卢克莱修的学说存在困难。我们如果困在自己的感官之中,又怎么能够判断我们对外在世界的感官表象是真的?蒙田敏锐地捕捉到了卢克莱修自己的怀疑瞬间:卢克莱修一度号召我们必须“大胆地相信感觉”(credere sensibusausis),即使不是为了得到真知,至少也是为了生活。对此,蒙田评论道:
这是绝望的劝告。这可太不哲学了。(《随笔》[中],页359)
蒙田把卢克莱修以感觉为一切知识基础的认识论与塞克斯都关于感官表象可错性的怀疑主义论证揉在了一起,不过,他的怀疑主义立场不同于塞克斯都的皮浪主义。具体而言,塞克斯都既批评感觉表象的真实性,也批评理性论证的有效性,但并没有提出自己的认识论,当然也不主张感觉是一切知识的基础。
与此不同,蒙田追随伊壁鸠鲁传统,相信感觉是唯一的知识来源,并结合古代怀疑论对感官表象的批判,论证了感官知觉对外在世界的表象的不确定性和可错性,由此得出了一种新的针对外在世界的怀疑主义。
六
“我感觉”的确定性与自然愉悦的伦理
因篇幅所限,本文不打算继续讨论蒙田自己的怀疑主义的认识论方面,而是考察他的怀疑主义所带出的伦理学说。毕竟,怀疑主义与伦理生活的关系,在皮浪主义中就已经是一个重要论题。蒙田这样描述皮浪主义者如何生活:
他们要符合自然的倾向以及激情的冲动和约束(Ils se present et accommodent aux inclinations naturelles, à l’impulsion etcontrainte des passions),遵守法律与习俗,以及技艺的传统……是活着的、说着的、思考着的人,享受着自然的愉悦与舒适(jouyssant de tous plaisirs et commoditez naturelles),以正当合适的方式充分地发挥身体和精神的能力。(《随笔》[中],页234)
他有一个身体。他有一个灵魂。他受到感觉的驱使和精神的鼓动。(《随笔》[中],页235)
蒙田对皮浪主义生活方式的描述基本继承了塞克斯都,但突出了跟随自然激情,从而在遵从“法律与习俗”的面向与享受“自然的愉悦与舒适”的面向之间存在张力。最终,主导蒙田怀疑主义伦理的是“自然的愉悦”。
蒙田虽然认为,感官经验与外在世界的对应关系具有不确定性与可错性,但感官经验的发生及其内容是确定的。蒙田的怀疑主义唯一没有否定的知识,就是“我”对于自身的感官经验的知识。由此还能得出,“我”对内在于我的自然激情的知识,是人关于自然唯一可能的知识。因此,蒙田在《随笔》最后一篇《论经验》中说:
我研究我自己超过任何其他对象。这就是我的形而上学,这就是我的物理学。(《随笔》[下],页409)
换言之,自我之中的自然激情是唯一可以通达的存在与自然。对蒙田来说,自然愉悦是自然真正的声音。当然,自然愉悦不等于无限制的享乐:
自然赋予我们的身体各部分——对于感官愉悦及痛苦——以适度与节制(juste et moderé)的天性。(《随笔》[上],页101)
身体的自然愉悦有天然的节制,而灵魂中的想象力与意见使激情变得人为和缺乏约束。因此,我们应该相信感官,这指的不是相信感官能忠实地“再现”外在世界,而是相信自然愉悦是自然生活的向导:“感觉”引导人过“享受着自然的愉悦与舒适”的“正当合适”(en regle et droicture)的生活(《随笔》[中],页234)。
经由怀疑主义,蒙田最终找到了“我感觉”的确定性,这一确定性不是认识世界的起点,却是伦理生活的支点。蒙田的怀疑主义瓦解了古代哲学与自然神学传统中虚荣与理性的同盟,进而将自然激情作为人唯一可以通达的自然、人的伦理生活的向导,这奠定了现代政治的伦理基础。由此可见,蒙田的怀疑主义并非只是阶段性的智识“危机”,而是参与了他的伦理、政治图景的建构,其怀疑主义的伦理与政治意涵也不止于相对主义。
作者简介

夏尔凡,多伦多大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助理教授,研究兴趣是古代与早期现代政治哲学。在History of European Ideas、The European Legacy等期刊上发表多篇论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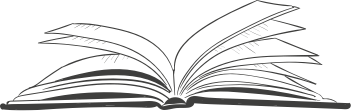

欢迎关注

插图来自网络,与文章作者无关。
如有涉及版权问题,敬请联系本公众号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