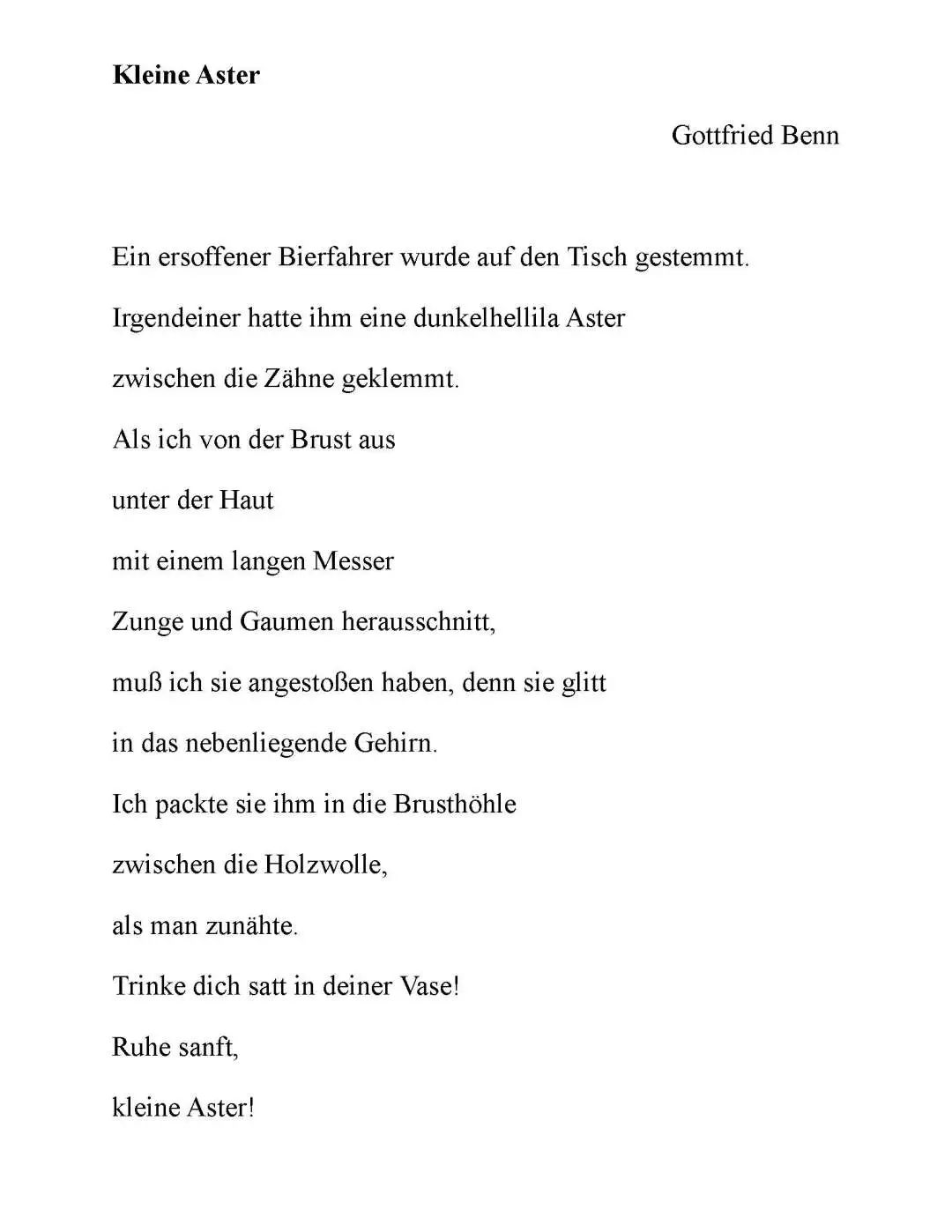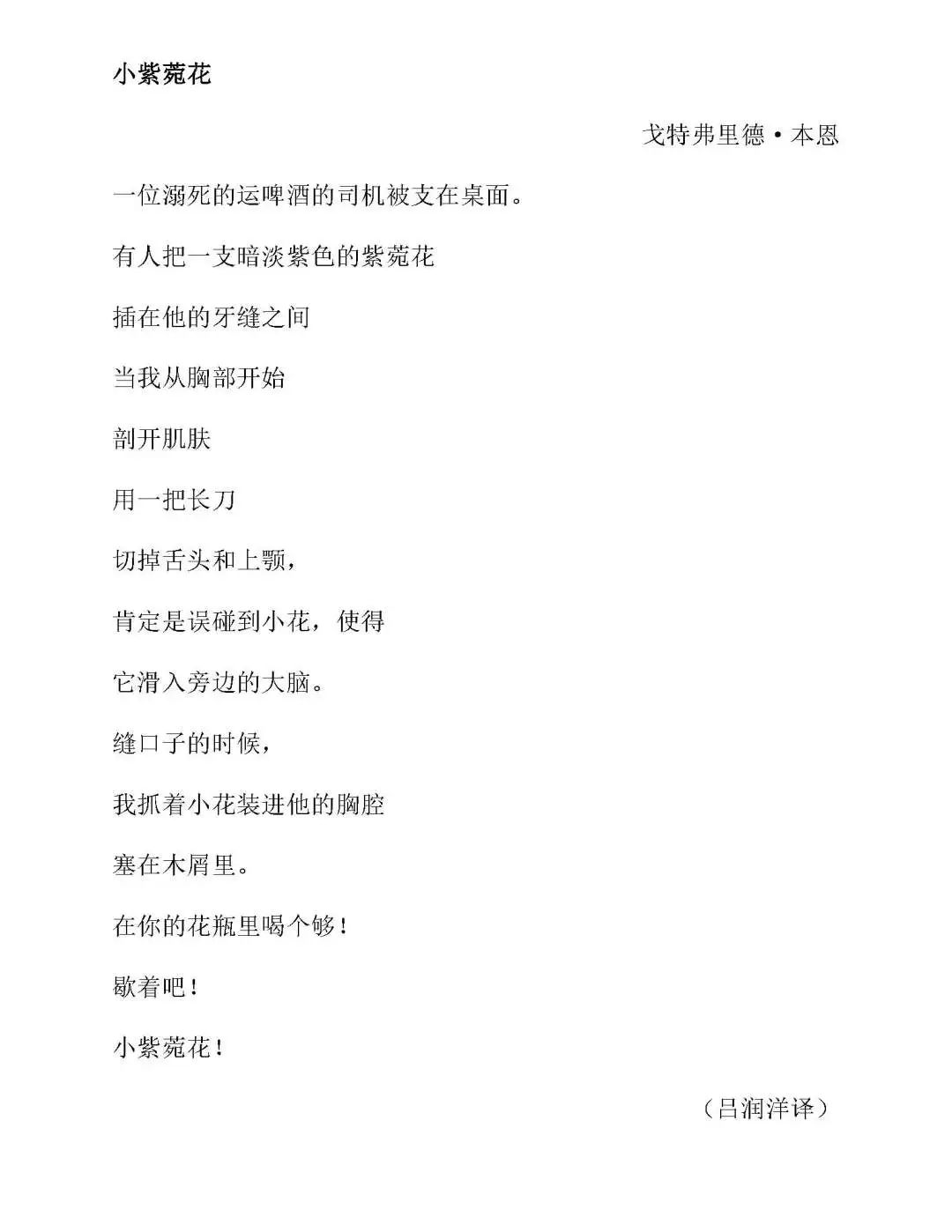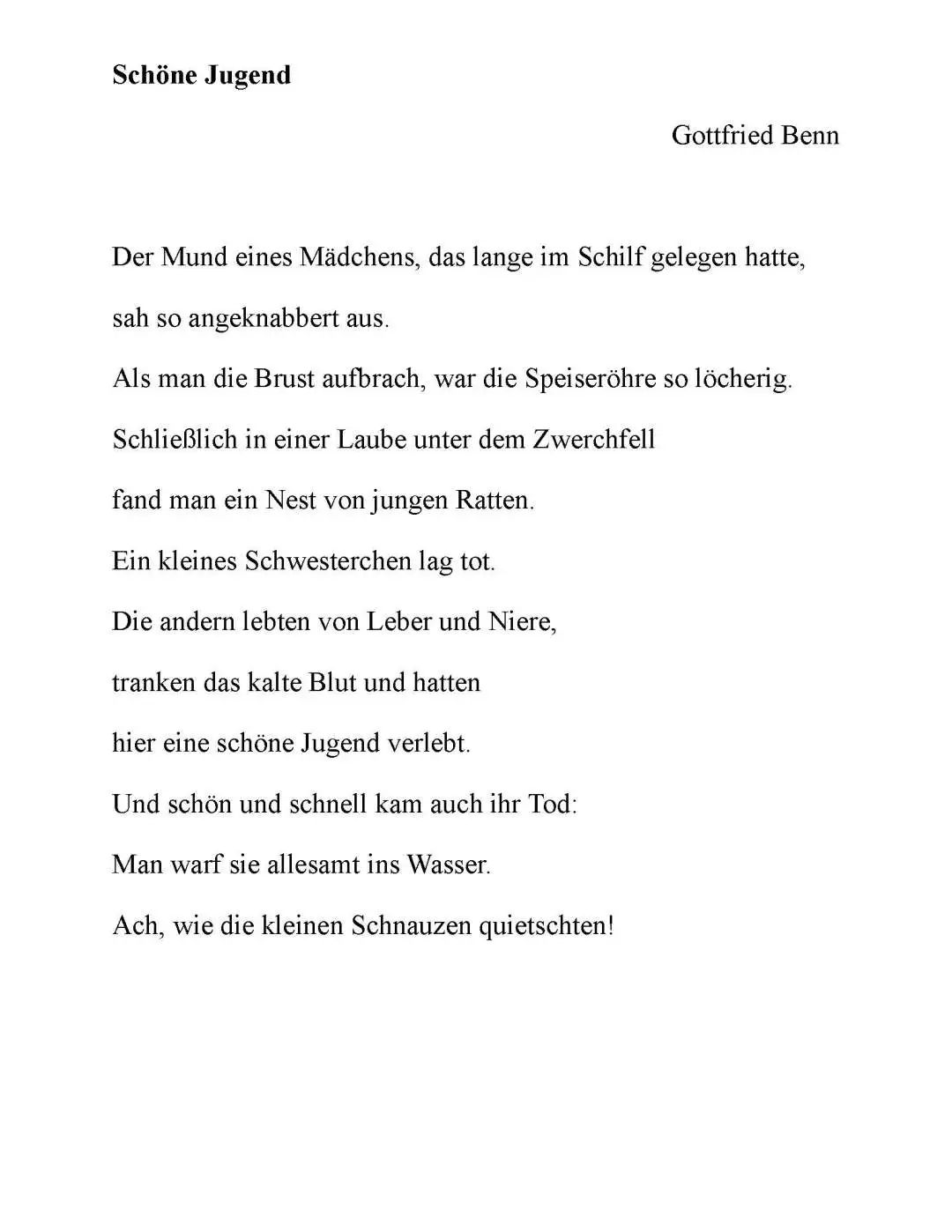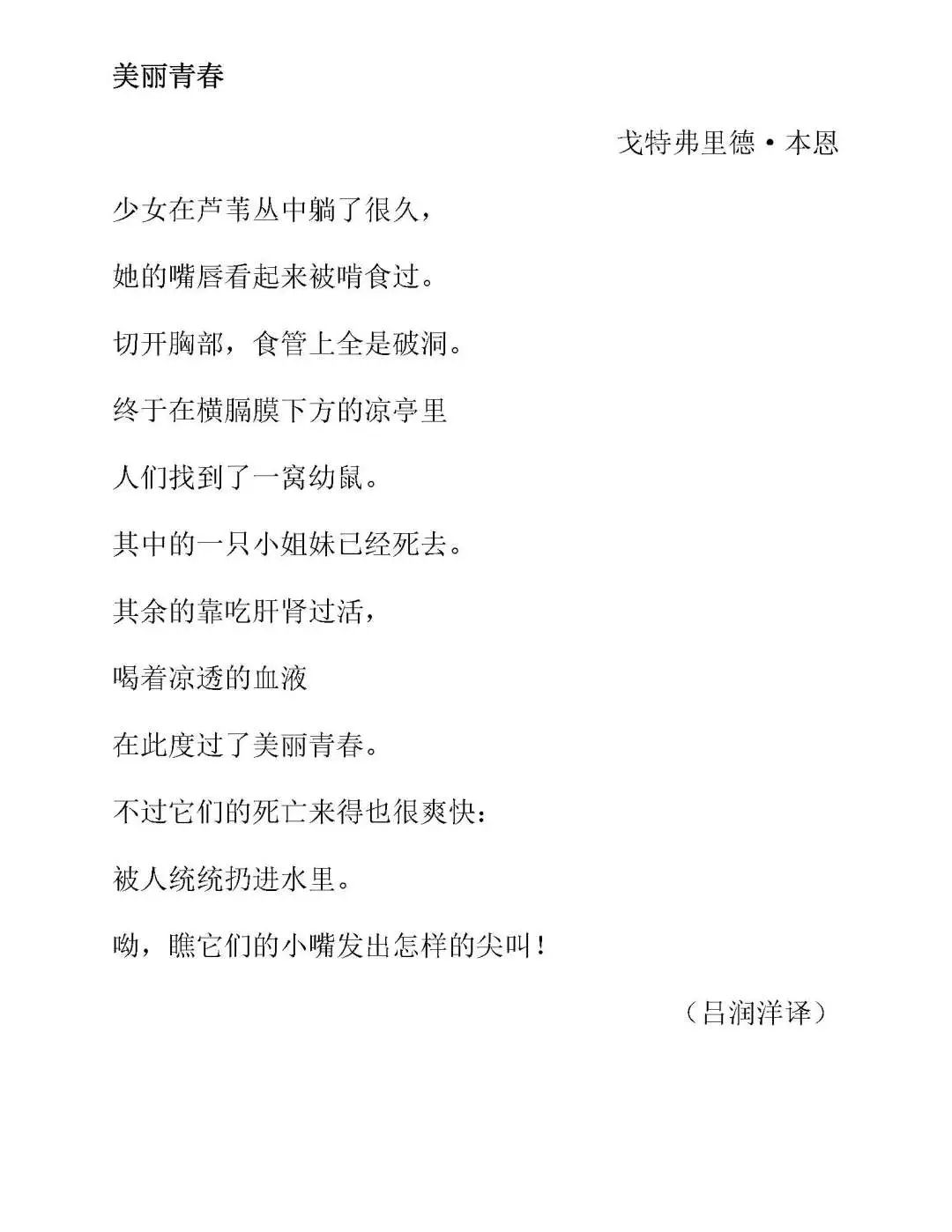诵诗 | 戈特弗里德·本恩诗二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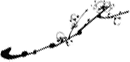
戈特弗里德·本恩(Gottfried Benn,1886-1956)是德国最为著名的表现主义诗人之一。求学初期,他按照父母的意愿学习神学和语文学,1905年,他开始按照自己的爱好转而学习医学。1912年本恩发表了他的第一部诗集,名为《<停尸房>组诗及其他》(Morgue und andere Gedichte)。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与诗集同名的《停尸房》(Morgue 1912)组诗。这组诗和整部诗集的其它诗都有着极为鲜明的烙印,虽然只印刷出版了500册,依然在文坛引发了巨大的轰动。这部诗集的出版者,同时也是对德国表现主义诗歌尤为重要的出版家阿尔弗雷德·理查德·迈耶(Alfred Richard Meyer,1882-1956)评价道:“德国的评论界对待诗歌从来没有过如此夸张的、爆炸性的反应。” 这是因为这组诗恰恰代表着本恩创作早期的鲜明特征——以尸体、疾病和死亡为主要的描写对象,毫不遮掩地展现人类的各种器官和解剖过程,冷峻的叙述语言和充满腐败气息的内容以及对文明和宗教不屑一顾的态度。本文将选取其中的前两首小诗《小紫菀花》(Kleine Aster)和《美丽青春》(Schöne Jugend)进行赏析。

戈特弗里德·本恩
左右滑动查看中德文诗文
左右滑动查看中德文诗文
这两首诗的语言首先是简单的。从诗歌形式上进行分析,本恩的早期诗歌并不像他中后期诗歌一样遵循典雅而严格的格律和押韵形式,而是在形式上自由而松散。《小紫菀花》《美丽青春》秉承自由韵律,诗行数量不定,每一行的音节数都不相同,韵律上也未遵循交替重音原则,且只能找到零星的尾韵。语言更接近散文。同时,除了《小紫菀花》末尾三行的两句命令式之外,两首诗的诗句以平白的陈述句为主,也少因诗行分割而打断的情况,因此散文化的叙述特征并没有受到影响。此外,组诗中虽然有大量人体器官的名称,但并没有在医学框架下运用任何的专业术语,也没有任何难以第一时间理解的外来词,可以说这组诗在语言形式的层面上完全不同于传统的诗歌创作,以直白通俗的语言和冷峻的态度描写解剖操作。
在诗歌的内容和修辞运用上,这两首诗同样极富特色。首先是充满戏谑意味的文字游戏。《小紫菀花》的第一行诗是“一位溺死的啤酒运输司机被支在桌子上。”这里的“溺死”原文用的是ersoffen,词根saufen恰恰是“狂饮”的意思,“支”一词原文是“stemmen”,也有“纵饮”的意思。在后文中,“肯定是误碰到小花”,此处的“碰到”原文使用的是anstossen一词,它同时还有碰杯的意思。诗人刻意地使用有双关义的动词,使得词语的原义和双关义组成了两组对应的意义群。前者指向的是惨白的尸体和冷峻无情的解剖动作,而后者在不言而喻地与“酗酒”相关。除此之外,诗人偏偏要令死者是一位“运啤酒的司机”(Bierfahrer),从事整天与啤酒打交道的职业,同时还有叙述主人公解剖时经过的“舌头”和“上颚”,这些器官对于解剖来说应该是微不足道或者不甚重要的器官,却被着重强调,是因为它们都和饮酒这个动作相关。这些看似无心的词语选择也补充了引人联想的隐含意义。它们让人联想到此时社会上泛滥的酗酒问题,让人猜测死者的死因是否与酗酒有关,一方面补充了死者的丑态,另一方面也以无名的尸体指向全社会的丑态。

小紫菀花
在第二首诗《美丽青春》中也有类似的处理手法。标题中的“美丽青春”、诗中前几行的“女孩”(Mädchen)、“芦苇丛”(Schilf)和“凉亭”(Laube)等词语看起来与“切开胸部”(die Brust aufbrach)、“食管上全是破洞”(die Speiseröhre so löcherig)以及“横膈膜”(Zwerchfell)并不相关,甚至格格不入。这正是诗人想要的意图,前面提到的词语传递出的是安宁、美好、靓丽的氛围,有研究者指出,本恩在这里运用的这些元素恰好是田园诗传统中常见的意象:“‘嘴唇’(Mund)单独来看是供亲吻的,在诗中却是被老鼠‘啃食’(anknabbern)的;‘凉亭’(Laube)不再属于浪漫美好的园林,而在此属于一具尸体;‘巢’(Nest)中住的不是燕子,而是老鼠,‘小姐妹’(Schwesterchen)不再是被美丽的葛蕾卿照料的角色,而是一个让人憎恶的生物。”因此,与第一首诗一样,本恩在诗歌的字里行间创造了指向停尸间之外的一个隐含意义群,只不过不同于第一首诗中对个人和社会病态的指控,此处的意义群则是首先给读者带来一种美好的期待,而紧接着就客观冷静地用解剖的现实和直白恐怖的肉体腐烂场面打破这种期待,以巨大的反差和对比冲击读者的期待视域。
因此,诗歌内容有着巨大的挑衅和讽刺意味,或者说——如果诗人乐在其中的话——是一种戏谑。这源于它对人类社会积累的常识标准的挑战和不屑一顾的姿态,乐于讽刺进而否定传统的资产阶级对美的认识。将具有美丽姿态或引发人们美好联想的意象和污秽、肮脏和纯粹生物意义上原始直白的意象并置,甚至使后者侵入并破坏前者,体现的正是诗人本恩要和美学传统彻底决裂的意图。他要粉碎传统美学系统的标准与范式,在表达中重塑现实,无情地直指事物的本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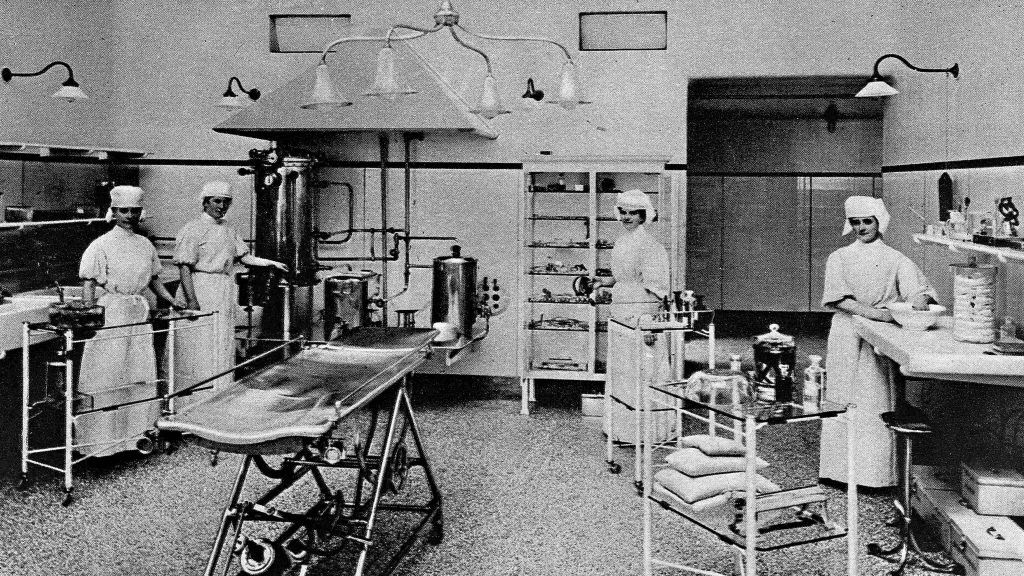
20世纪初的解剖间
被他粉碎的也不止“美”的概念,本恩作为表现主义先驱,反叛的刺刀也刺向了人类尊严和宗教。在《小紫菀花》和《美丽青春》中,人的尸体不再代表着令人叹惋或令人恐惧的死亡,也不代表着生命的消逝,而仅仅是一具容器。第一首诗中的溺亡者尸体成了小紫菀花的“花瓶”,并且要供小花在其中畅饮;而第二首诗中溺死的女孩则成了小老鼠的巢穴。同时,叙述者不再对两具尸体有任何情感反应,一系列反常理、打破期待的现象再次出现:叙述者叹惋的不是死亡的司机,而是小紫菀花;度过美丽青春的并不是美丽的少女,而是寄生在肚子里的老鼠。一直以来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类在诗中却被完全忽视,本恩借此正式戳碎了人类的傲慢——人类并不是高高在上的万物之灵长,而本身就应该和所有的生灵平等,因为一旦去除掉所有的光环,破除掉人类自己创造的意义载体,人类本身也是脆弱的生物,和其它生物一样受制于自然规律,无差别地面对着生老病死,因为人“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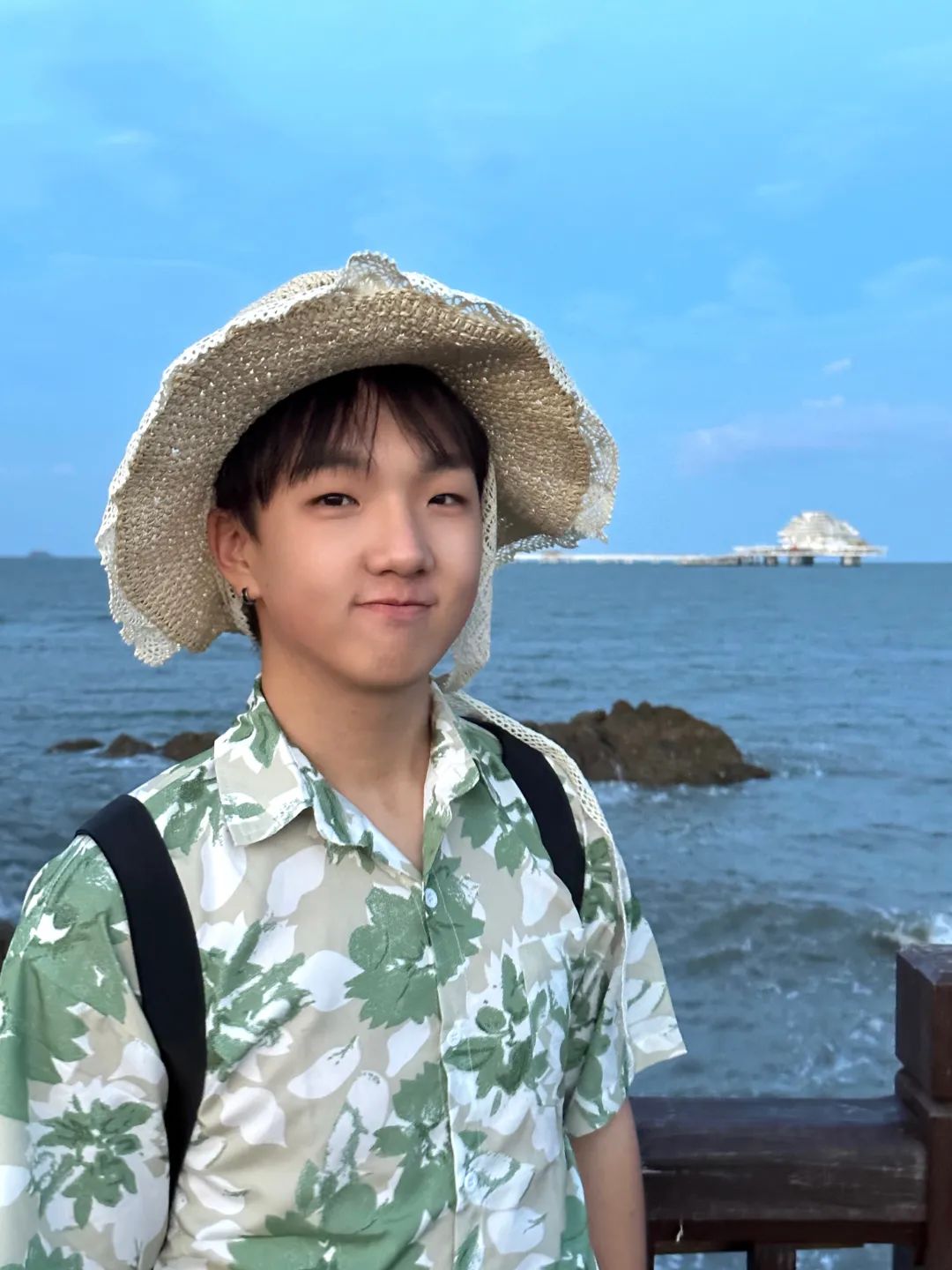
吕润洋,北京大学德语系2022级硕士研究生,研究兴趣为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语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