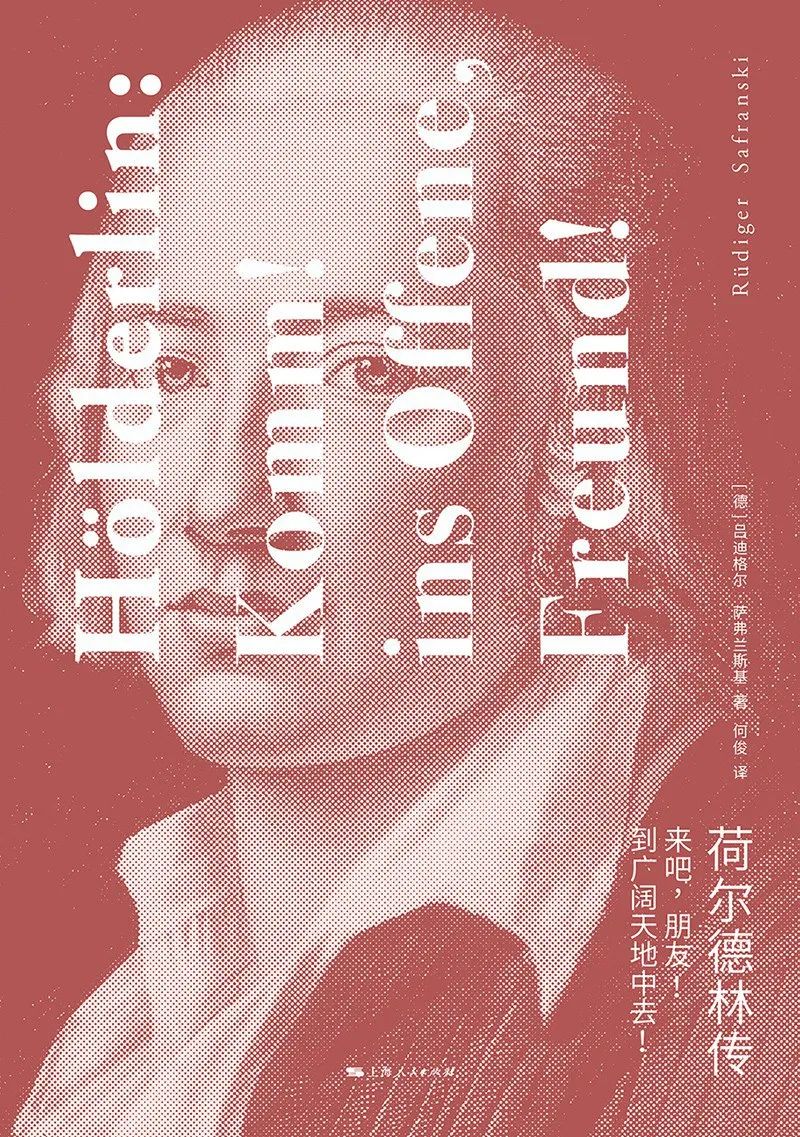新书推荐 | 萨弗兰斯基《荷尔德林传》
《荷尔德林传》
Hölderlin: Komm! ins Offene, Freund!
[德]吕迪格尔·萨福兰斯基(Rüdiger Safranski)
何俊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3年7月
点击封面,前往购书页面
前言........................................1
第一章.....................................1
出身。体面者。荷尔德林自尊自爱。生父和继父亡故,母亲孀居。童年的诸神。跟母亲的关系。科斯特林家族。神童谢林。
第二章....................................15
邓肯多夫。修道院日常生活。致克斯特林的书信。虔敬主义的灵魂考验。一个抗拒“尘世”的灵魂的自我宣言。对自我迷失的畏惧。自由主义的毛尔布隆。初恋史。品达的飞翔和克洛普施托克的伟大。以诗人身份降生。
第三章.....................................33
图宾根神学院。学习的兴趣。荷尔德林研习康德和斯宾诺莎。理智,以及心的根基。爱的宗教。友盟和“神的王国”。黑格尔。谢林。神学院里的革命热情。“勇气守护神”。
第四章.....................................50
创造性想象力的哲学加冕。自我授权。诗人同盟。马格瑙。诺伊弗。施托伊特林。早期颂歌,过于庄严。文学与生活。荷尔德林不是浪漫派诗人。古希腊崇拜狂。席勒的《希腊诸神》与荷尔德林的古希腊。诸神的回归?《许珀里翁》创作的开始。
第五章..................................... 67
神学院时光落幕。政治动荡不安。伦茨。宁愿做家庭教师,而不是牧师。夏洛特·封·卡尔布。荷尔德林在路德维希斯堡拜访席勒。埃莉泽·莱布雷特。告别以及动身前往瓦尔特斯豪森。
第六章...................................... 81
瓦尔特斯豪森。从远方更新友谊。无足轻重的爱情故事。玛丽安娜·基尔姆斯。《许珀里翁》。第一部断片。希腊“狂热”出现,长篇小说兴起。荷尔德林在读者中间寻找成功。《许珀里翁》的前言。乖僻性情和原罪。寻找业已实现的存在。心醉神迷的多个瞬间,但都不长久。
第七章.......................................100
席勒出版《许珀里翁残篇》。与学生相处困难。自慰的问题。与卡尔布一家告别。耶拿。席勒所言“最喜欢的施瓦本人”。与歌德不成功的相遇。费希特的“自我”与荷尔德林对存在的追寻。《判断与存在》。在哲学的影响下修订《许珀里翁》。
第八章........................................121
突然动身离开耶拿。寻找对席勒的亲近,复又逃离。卷入哲学。折磨人的矛盾。自由哲学与青年谢林。哲学或诗歌。《德意志观念论最古老的体系纲领》。一个新神话的创立及美好。
第九章....................................... 138
《致自然》。遭到席勒拒绝。与苏赛特的恋情开始。巴德—德瑞堡的田园风光。色情作家威廉·海因泽担任看护人。《阿尔丁赫罗和蒙福的诸岛》。法国的进军。政治失望以及对德意志文化民族的过度希望。自我断言的梦。被席勒接受的《橡树林》。
第十章.........................................156
《许珀里翁》——终稿版。附加的内容。政治斗争,失望之情。阿拉班达和辛克莱。狄奥提玛和苏赛特。新的自信。对德意志人的斥责演讲。神性。荷尔德林癫狂的顶端。《许珀里翁》——一部关乎诗人诞生的小说。歌德与席勒讨论荷尔德林。贡塔德府上的危机。荷尔德林的离开。
第十一章.......................................178
与辛克莱同赴拉施塔特。朋友们。革命的期望。《恩培多克勒》。在政治和个人前途方面孤注一掷。融合的神话,以及政治。戏剧形式消失,政治契机也是如此。《恩培多克勒》中的自身。杂志计划宣告失败。与苏赛特的秘密通信。了无指望。
第十二章........................................199
荷尔德林保持隐蔽的生活状态。他的创作却洞门大开。在斯图加特的兰道尔一家度过1800 年的那个天赐的夏日。来吧,朋友!到广阔天地中去!思想辽阔的颂歌和哀歌。《乡间行》。《美侬哀诉狄奥提玛》。《爱琴海》。《面饼与葡萄酒》。
第十三章........................................226
寻常的喜乐。《向晚遐思》。豪普特维尔。父国所指者。笃信革命的荷尔德林。《吕纳维尔和约》。时代的转折,与末世相关者。《和平庆典》。从另一首诗中诞生的诗。《犹如在节日里……》与《生命之半》。归乡。对席勒的求助呼告。“他们可能并不需要我。”
第十四章.........................................247
去往波尔多的冬季旅行。当地的魅力。神秘的启程。各种推测。被阿波罗击中。苏赛特之死。抵达斯图加特和尼尔廷根,迷惘,堕落。狂躁。与母亲作对。与辛克莱一起去雷根斯堡。颂歌《拔摩岛》。《思忆》。
第十五章.........................................265
翻山越岭,去穆尔哈特拜访谢林。荷尔德林的《索福克勒斯》翻译。陌生之物变得愈发陌生。迁居霍姆堡。斯图加特数场危险重重的宴会。布兰肯施泰因的告发。辛克莱被捕。叛国罪审判。荷尔德林成为众矢之的。“我不愿成为雅各宾派的一员!”荷尔德林捣毁了钢琴。荷尔德林被转运就医。
第十六章.........................................278
在奥滕里特精神病院。寄居木匠师傅齐默尔家。住在塔楼上可以观景的房间里。仍然还是个美男子。给母亲的信。在钢琴旁唱歌。即席赋诗。癫狂的程度如何?主要材料来源:瓦恩哈根·封·恩泽、威廉·魏布林格和克里斯托夫·施瓦布。当幻想以理智为代价变得更加丰富。荷尔德林的安详辞世。
第十七章..........................................297
浪漫派发现荷尔德林。贝蒂娜和阿希姆·封·阿尼姆。布伦塔诺,格雷斯。忠诚的施瓦本人,青年德意志派。第一批作品版本。青年尼采阅读荷尔德林。黑林拉特和斯特凡·格奥尔格发现了荷尔德林。突破。滥用。海德格尔阅读荷尔德林。1945 年后:充满无穷无尽的阐释可能性!
参考文献.......................................... 322
荷尔德林年表.....................................329
译后记.............................................. 357
写下这个标题时,内心感觉可谓五味杂陈。一方面自然有一丝如释重负,毕竟历时一年半的时间,这本书的翻译总算是划上了一个句号,在此也不由得感叹时光流逝之快。另一方面,这本书是德国顶尖学者萨弗兰斯基为享有世界级声誉的德国大诗人荷尔德林所立的传记,无论是作为研究对象的诗人还是作为同样负有盛名的原作者,都让我觉得翻译这本书大有惶恐不安之感。而这样诚惶诚恐的感受,在一路摸索的翻译过程中一再得到印证。诚然,本书是荷尔德林的传记,但在对这位诗人行云流水般的叙述中,原作者自然免不了援引诗人犹如粲然群星般熠熠生辉的诗篇。都说翻译难、译诗更难,而荷尔德林诗歌的解读已属困难,再迻译成汉语更是殊为不易,再加上萨弗兰斯基的深厚广博的学养和优雅厚重的行文,无疑使得整个翻译过程喜乐参半,常有“拨开云雾、守得月明”的切身感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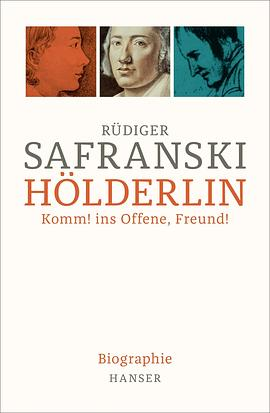
《荷尔德林传》德文版封面
萨弗兰斯基的这本传记出版于2019年,而翌年就是荷尔德林诞辰250周年,这之间的关联自不待言。头顶“天才诗人”“先知诗人”“哲学诗人”“诗人中的诗人”等桂冠的荷尔德林,可以说也称得上“先于时代之人”或曰“死后方生”,即在世时未享盛名,去世后很多年才被重新发现。颇值一提的是,德意志文化的三大源流,即古希腊罗马文化、基督教文化和日耳曼的固有文化,以及代表这三大传统的古典主义、虔敬主义和浪漫主义,都可以在荷尔德林身上找到印记:生于施瓦本地区的他,不可避免地受到当地虔敬主义的熏陶和感染,并遵从母命学了神学专业;但后来的他不惜一再违抗母亲的意愿,不愿做一名侍奉上帝的牧师,而转向做一名以诗艺为志业的诗人,在诗歌创作中一再“言必称希腊”,并参与构建了新神话诗学。他对古希腊文化的遥望与向往不仅体现为在诗歌中对关乎希腊的母题和意象反复吟咏、一唱三叹(有一首颂歌就题为《希腊》),从他笔下汩汩流出的其他文字亦可窥见:比如他在学生时代撰写的有关古希腊艺术的论文,比如诗化小说《许珀里翁》和剧本《恩培多克勒之死》,又如他对索福克勒斯的两部悲剧《俄狄浦斯王》和《安提戈涅》以及品达崇高颂歌的翻译。当然,除了当时涌现的“希腊热”,为诗人的精神生活插上翼翅的还有另外两股力量,其一为以康德等人为代表的哲学思潮的风起云涌,其二是当时发展得如火如荼的法国大革命。就哲学运动而言,荷尔德林不光接受和研读了卢梭、斯宾诺莎、康德和费希特等人的哲学著作,也跟他神学院时期的室友黑格尔和谢林一起参与造就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哲学运动,正因如此,有关荷尔德林的观念论哲学背景以及他与后康德哲学之间的密切关系,早已不是什么新鲜话题。就荷尔德林与法国大革命之间的关系而论,本书中多次提及的法国荷尔德林研究的执牛耳者贝尔托就曾将荷尔德林定义为法国大革命的追随者和雅各宾派,将荷尔德林研究带入了一个左派接受研究的新阶段。事实上,青年时代的荷尔德林非常关注时事政治和革命斗争,投笔从戎也是他的心之所系。正因如此,他才会1798年除夕致弟弟的长信中写道:“当黑暗的王国以暴力入侵,我们还是会把鹅毛管笔扔到桌子下面,以神的名义奔向苦难最为深重而又最需要我们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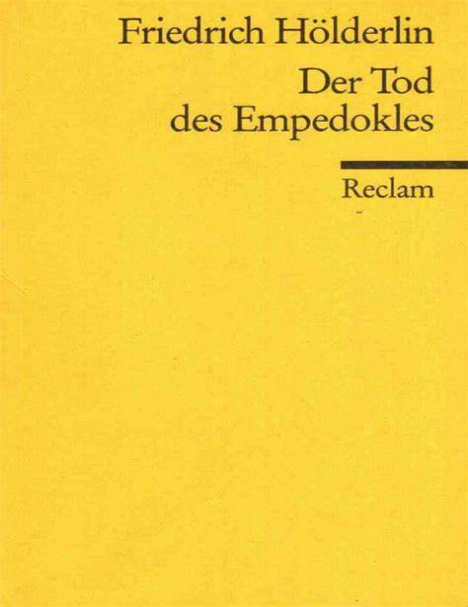

《恩培多克勒之死》德文版和中文版封面
西方精神科学(又称“人文科学”)的奠基者、德国著名学者狄尔泰在《体验与诗》中也曾专辟一章叙述荷尔德林,并用近乎咏叹调的笔触发出由衷的慨叹:“哪里还有另一种由这样柔软的材料,像是由月光编织而成的诗人生活呢?他的生活如此,他的文学创作也是如此。”荷尔德林也俘获了茨威格这位拥趸,后者在《与魔鬼做斗争》中宣扬诗艺对于荷尔德林的重要意义,将它提升为一种指导生命运行的法度:“诗——我重复一下——对荷尔德林来说并不像对其他人那样是生活的一种悦耳动听的配料,是人类精神躯壳上的装饰品,而是具有最高目的和意义的东西,是包容和塑造一切得原则:为此付出自己的一生是惟一有价值的、光荣的献身行为。”茨威格又把荷尔德林与当时德国的诗坛君主歌德进行对比,认为“即使对于歌德,诗艺也不过是生命的一部分,而对于荷尔德林却是生之意义所在,对于歌德来说它不过是一种个人的必需,而对于荷尔德林来说却是一种超个人的、宗教的必需”。茨威格所言并非夸大其词,因为作诗于荷尔德林确实是一种近乎宗教的行为,是一种受神感召的天职。无独有偶的是,荷尔德林就创作过这样一首题名为《诗人的天职》的诗。20世纪初,除了狄尔泰之外,格奥尔格圈也重新发现了荷尔德林。于是,他与陀斯妥耶夫斯基、克尔凯郭尔、尼采同被视为四颗耀眼的明星。当然,更耳熟能详的当是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的推崇备至,这位存在主义与现象学大家甚至借助荷尔德林诗歌这个方向指引或者参照系统,进而构建自己诗思合一的哲学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说,代表“诗性哲学”的海德格尔与代表“哲性诗学”的荷尔德林之间似乎存在一种“相互成全”的关系:海德格尔发现了荷尔德林,荷尔德林也表现了海德格尔。
终其一生,荷尔德林的命运不可谓不多舛。都说“躁狂抑郁多才俊”,天才与疯癫者的交界地带确实令人好奇,只是这位天才诗人差不多有一半的人生都是在癫狂的状态下度过的,而且是寄居他人屋檐之下。本来诗情万丈而且哲思充盈的他,却始终怀才不遇。德国古典文学双子星座的光芒太过耀眼,以至于让他这颗当时还未冉冉升起的新星黯淡无光。而歌德和席勒这两位诗坛巨擘对他的支持和提携也实在有限,对于席勒他尤其表现得过于谨小慎微,拘谨到让席勒本人都对他的敏感表示不适。他申请耶拿大学的一个讲师教职,也以失败告终,于是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从事家庭教师一职谋生。正因如此,在1802年初动身前往波尔多再次从事这一职业之前,他才会在致友人伯伦多夫的信中“哀莫大于心死”地写道:“他们可能并不需要我。”此外,在进入医院治疗之前,他还险些被好友牵连而身陷囹圄。他与一直爱戴的母亲之间的关系也异常复杂:自从被带到医院治疗以后,母子两人就再未谋面,而荷尔德林甚至一度中断了给母亲传书;直到后来在他的房东兼照管人、木匠齐默尔的敦促下,才与母亲恢复了通信往来,然而此时字里行间温情脉脉的推心置腹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近乎机械的问安套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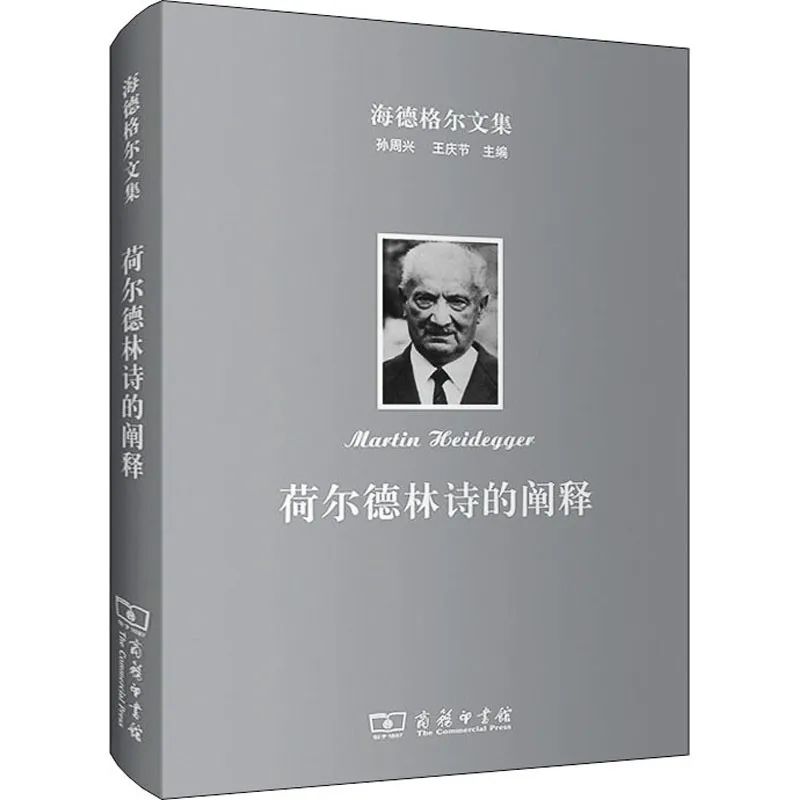
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
年轻时代的荷尔德林本是相貌俊逸的美男子,有过几段风流韵事似乎也在所难免,而某些传闻时至今日也无法查证。但他与担任家庭教师的府上的女主人苏塞德之间刻骨铭心的恋爱经历,才让他切身体会到爱的甜蜜,让他真正感觉到“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她是他植入《许珀里翁》并且得以神化的狄奥提玛,也是歌德《浮士德》中永恒女性的化身。“无奈佳人兮,不在东墙”,毕竟苏塞德已为人妻和人母,他们注定只能相识、相知、相恋,却无法长相厮守。在他俩的不伦之恋暴露以后,荷尔德林除了匆匆不辞而别,别无其他选择。在以后的两年里,两人还保持着秘密的鱼雁传书,甚至还定期幽会。但这样的地下恋情还是让双方惴惴不安,于是荷尔德林做出了搬离到更远的斯图加特的决定,并在这一时期写下了献给苏赛特的长篇告别哀歌《梅侬哀诉狄奥提玛》,这也是德国乃至世界抒情诗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1801年12月上旬,荷尔德林动身前往波尔多,这段徒步征程可算得上险象环生,既有恶劣气候阻挡路程,又有绿林强盗伺机出没,于是他不得不枕着一把上膛的手枪安歇。但荷尔德林在当地只停留了半年,就又踏上了返乡之旅。他矢志不渝的恋人苏赛特在1802年6月22日去世,至于他们是否有过最后一面之缘,学界尚无定论。但《许珀里翁》倒数第二稿的终句,可算是对两人之间恋情的最好诠注:“世间纷杂,如同恋人龃龉。争吵不休,又和好如初。别离的,必又重逢。血液从动脉分流,又重回心脏。这一切的一切,构成了统一、恒久而炽烈的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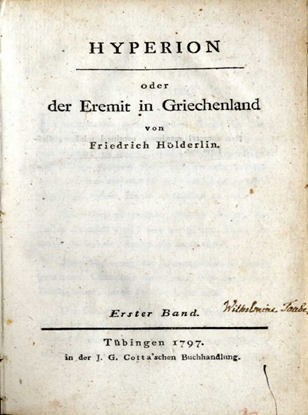
《许珀里翁》首版扉页
除了这段传奇般的恋情,荷尔德林也收获了相当多的友情,以及浓得化不开的知音之情。在图宾根神学院时期,荷尔德林、黑格尔、谢林“三剑客”同住一室,而荷尔德林总是罩着矮小瘦弱的谢林,以防他遭受校园霸凌。日后三人分道扬镳、离多聚少,但荷尔德林在某个夏日一路翻山越岭、长路跋涉,只为了与暌违六载的谢林重逢,莫逆之交何等固若金汤,此处略见一斑。遥想1791年2月,荷尔德林在黑格尔的纪念册上留言,上书歌德诗剧《陶里斯岛上的伊菲格涅》中的一句“喜悦与爱是飞往伟业的翼翅”;黑格尔在1796年夏也赋诗一首《厄琉息斯》,遥赠荷尔德林,这也是他毕生唯一的一首引人重视的诗。荷尔德林精神错乱后,黑格尔也施以援手,帮助他联系出版诗作,这更是两人情谊的见证。要说荷尔德林生前完全默默无闻,那也站不住脚,毕竟早在1805年的法兰克福就出现了荷尔德林的第一批知音,其中心人物有浪漫派成员阿尼姆伉俪、布伦塔诺、格雷斯、京德尔罗德等。至于木匠齐默尔,则可算是荷尔德林的头号拥趸,他去世以后,其女儿接过接力棒,继续承担起照顾荷尔德林的责任,为此甚至终身未嫁。在荷尔德林的下葬仪式举行的当日,风雨如晦,前来送他最后一程的,没有他生前的旧友、故人以及那些学富五车的教授,只有为数众多的知音——好几百名大学生。何其可怜,荷尔德林就像一把绷紧了弦的琴,因为精神疾病的折磨而毁损,又像一只被折断了翼翅的鹰隼,只能浑身痉挛地扑腾着翅膀;但又何其有幸,毕竟他也曾被亲情、爱情、友情和知遇之情包围,也曾被恒久不灭的人性之光照耀。即便是在他幽居塔楼、精神错乱的漫长年头,他还是创作出了“斯卡达内利诗集”(“塔楼之诗”》——这把琴还是奏出了华美而不朽的乐章,这只鹰终能振翅朝着太阳飞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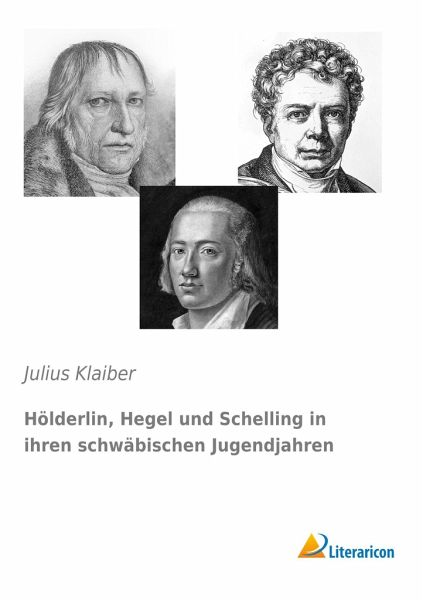
荷尔德林、黑格尔和谢林
自民国时期以来,汉语世界的荷尔德林翻译与研究已经走过了一个多世纪的征程。如何让荷尔德林“说汉语”,向来都不是一桩易事。除了诗人在图像、譬喻、象征、格律、节奏、布局、句法、语序、省略等诗艺层面近乎天马星空的纵横捭阖、游刃有余,诗中充盈的古典学和基督教神学等领域的艰深文化知识也常让人对其诗歌的翻译望而却步。尽管如此,万幸的是仍有“崔颢题诗在上头”。就荷尔德林各类体裁的作品汉译而言,一批翻译界前辈已经提供了可供参阅的译文:这里既有早期前辈学人比如冯至、季羡林、杨业冶等,也有近年来的戴晖、顾正祥、钱春绮、张红艳、先刚、刘皓明、林克、王佐良等。当然,若论如盐融水、不着痕迹般的化用,当属那位写下“血以后是黑暗”的薄 命诗人海子。他极富创造性地汲取了荷尔德林诗歌中的人神关系等养分,成就了自己的不朽诗篇,包括致敬荷尔德林的组诗——《不幸》。海子在与这个世界诀别前夕留下了散文《我热爱的诗人荷尔德林》,约10年后,这篇文章被译成德语,发表于德国荷尔德林研究学会的门户期刊《荷尔德林年鉴》(1998-199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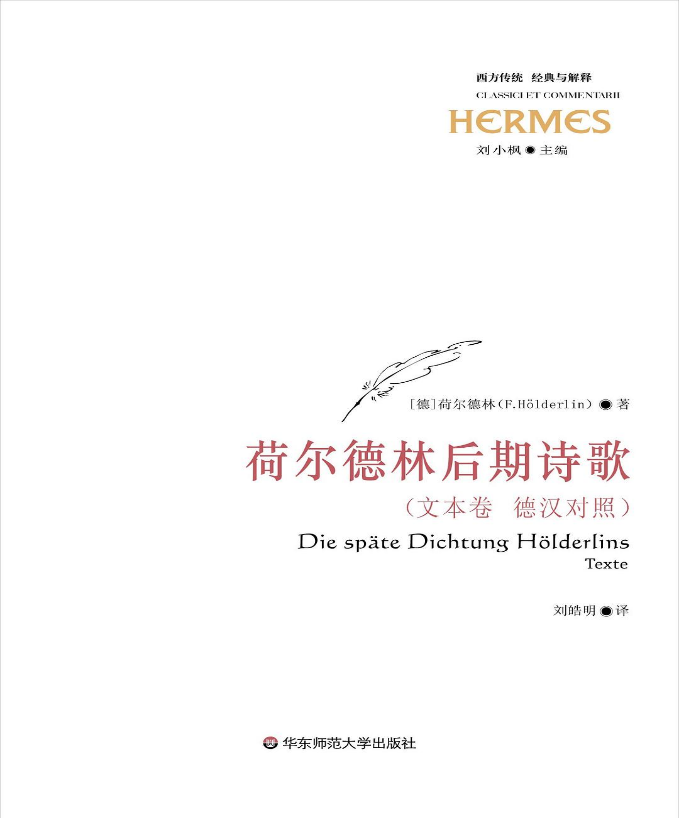
《荷尔德林后期诗歌》
笔者无意在此论资排辈或者臧否现有译文,只想表达对所有先行者的敬意和致谢,但相关的援引和借鉴恕难一一注明。即便是相对不那么好评如潮的译本,在笔者看来,也并非不能从中收获一丝一毫的助益,这也是笔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切身体会。从文学和翻译阐释学的角度来看,既然“(原)作者已死”,每位译者都有自己在进行了“视域融合”之后的不同解读;而且早年间收录于海德格尔作品中的荷尔德林诗歌的汉译,自英语转译者不在少数,所以其汉语翻译或阐释甚或可能大相径庭。姑且不论荷尔德林那些相对小众、在汉语世界尚未传播甚广的诗篇,就是他最为国人所知的那句“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doch dichterisch wohnet / Der Mensch auf dieser Erde),都有不同声音出现。如果采取另一种不同于当下盛行的“诗意”充盈的解读方法,这句诗是否可以堂而皇之地用于房地产商的广告,恐怕要打上一个巨大的问号。另外,各位译者对文风或曰字里行间“气韵”(或许也可以套用本雅明所言的Aura)的偏好也不尽相同,而“直译与意译”“归化与异化”两相争斗的喧嚣早已不绝于耳。至于汉译作品中“汉化”的尺度与原文“陌异度”抑或异域情调的保留问题,也是见仁见智。举例来说,荷尔德林诗歌语序中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经常把主语置于最后,那么这一打上了荷尔德林专属印记的、“彰明较著”(陈维纲译《在柔媚的湛蓝中》一诗所用字眼)的德语句法特征,要以何种程度在汉语中再现呢?考虑到作为非曲折语的汉语和作为曲折语的德语之间巨大的语法结构区别,要想实现这一重构可谓难矣。比如《思忆》一诗中有一句被刘皓明尽量紧贴原文地直译为“远眺着一对儿高贵的橡树与白杨”(Hingeschaut ein edel Paar / Von Eichen und Silberpappeln),对此刘认为可以通过诵读时变换节奏来克服两种语言结构上的差异,即可以把“橡树与白杨”理解为原文中的主语,而非汉语母语者惯性思维中的宾语。但笔者同意程炜的说法,即这一节奏变化恐怕难以奏效。为了尽可能地彰显荷尔德林这一极具个人特色的诗艺特征,笔者只有勉为其难地将原文中不带强调色彩的陈述句译为汉语中的强调句,即“眺望着的,是一对 / 高贵的橡树和白杨”,至于其审美效果如何,还有待诸位读者评价。翻译之难而又因难见巧,此处可以再次窥见。就荷尔德林汉译的文风而言,笔者最赞同的还是已故翻译大家、《里尔克全集》汉译者陈宁的观点。在他看来,荷尔德林所说的汉语,当是一种古风犹存而雅驯典丽的现代汉语。在翻译过程中,笔者借鉴前人翻译成果,在“转益多师是吾师”的基础上尽力朝着这一目标努力,但囿于自身的文化学识、古汉语功底和诗艺水平,恐怕多有力所不逮以及疏漏舛讹之处。
写到这里,感谢之情溢于言表。首先要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尤其是赵伟编辑的邀约和接洽,多年来该出版社一直致力于优秀学术著作的发行,在德语学术文化书籍汉译出版方面贡献颇多。真诚致谢天堂里的陈宁,他发表在豆瓣社区“荷尔德林”小组内的译文抑或原创文章,以及对现有荷尔德林诗文集翻译的评论,都让我受益良多,一并感谢与荷尔德林诗歌主题相关的其他参与者的评论和探讨,限于篇幅无法一一胪列网名。最后还要感谢来自波恩的德国汉学家汉克杰(Heinrich Geiger)博士,没有他不厌其烦地耐心答疑解惑,恐怕译文中的诸多未解之处可能就会不无遗憾地“跳将”过去。另外还需说明的是,萨弗兰斯基迄今推出了多部包括本书在内的德语国家文化名人传记,其风格都可谓通识性、学术性与可读性水乳交融,为此译本中保留了原文的德语注释和参考文献,以备通晓德语者查证;本着方便一般读者非学术性阅读的目的,笔者以毛明超博士翻译的萨福兰斯基《德意志理想主义的诞生——席勒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为标杆,对书中出现的大量专名、尤其是人名做了较为详细的注释。
“不为至大者所拘,而为至小者所含,此乃神性”,这是《许珀里翁》倒数第二稿第一部开篇的引言。按照海德格尔的阐释,天地神人构成“四方—世界”,而处于天和地两极之间的人与神需要一个“中介”,而这个“中介”就是作为半神的诗人。其实,除了诗人,译者又何尝不是一种“中介”,就好比希腊神话中奥林匹斯十二主神之一的赫尔墨斯,其主要的使命是充当众神的使者,向作为大地之子的民众传达众神的旨意。每一位以翻译为志业(而不仅仅是职业)者,都应该立志充当鲁迅所言的盗火的普罗米修斯。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是为序。
何俊
2022年10月5日于诗城成都
荷尔德林在兰道尔的友人圈子里度过了一段创造力勃发的时期。正因为他感觉自己在灵感迸发的瞬间被神性攫取,他就迫切需要当地所能找到的、舒适的、基本的日常。这一日常可能就是他幸福的基础。出于平衡的需要,狄奥尼索斯的闪电会对天父以太提出要求。荷尔德林这一时期诞生的诗歌《我的财富》就发掘了这一关联:对于那更坦荡的男子 / 坚实大地的上空更为光亮。// 因为,它不是像植物那样,扎根自己的土地 / 那必死者的灵魂燃成灰烬……
荷尔德林也创作了一些诗歌,用令人难以忘怀的词句描述了寻常的喜乐,以及对它的向往,比方说这首《向晚遐思》:
茅舍前的阴翳下,静静地坐着
耕者,这知足之人,炉灶内飘出炊烟。
殷勤地为漂泊者响起
宁静村庄里的声声晚钟。
船夫可能也抵达港口,
远方的城镇,宁息了集市上的
忙碌喧声;安静的凉亭内
友朋相聚,杯盘闪亮。
我到底去向何方?终有一殁的人活着
依赖粮饷和职事;在劬劳和休憩的轮换中
万事欢愉;缘何刺痛
永不在我的胸膛沉睡?
向晚的天幕里一个春日绽放;
玫瑰花开无数,宁静地闪光
那一片金色的世界;哦,携我去吧
紫色的云霞!惟愿在那高处
爱和痛在我面前消融为光和风!
然而,仿佛被我愚笨的请求吓倒,魔力
隐遁;夜幕正在降临,
天穹下,我茕然依旧。
来吧,此刻,你温柔的黑甜乡!渴念太多
这颗心;但是青春啊!你终将凋谢,
你这不安歇而又端于幻想者!
俟及暮年,方得平和愉悦。

何俊,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文学博士,现任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系主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兴趣为中德文学关系、翻译史等,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美学散步》德文版”,出版德文专著1部、译著6部,在中外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近50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