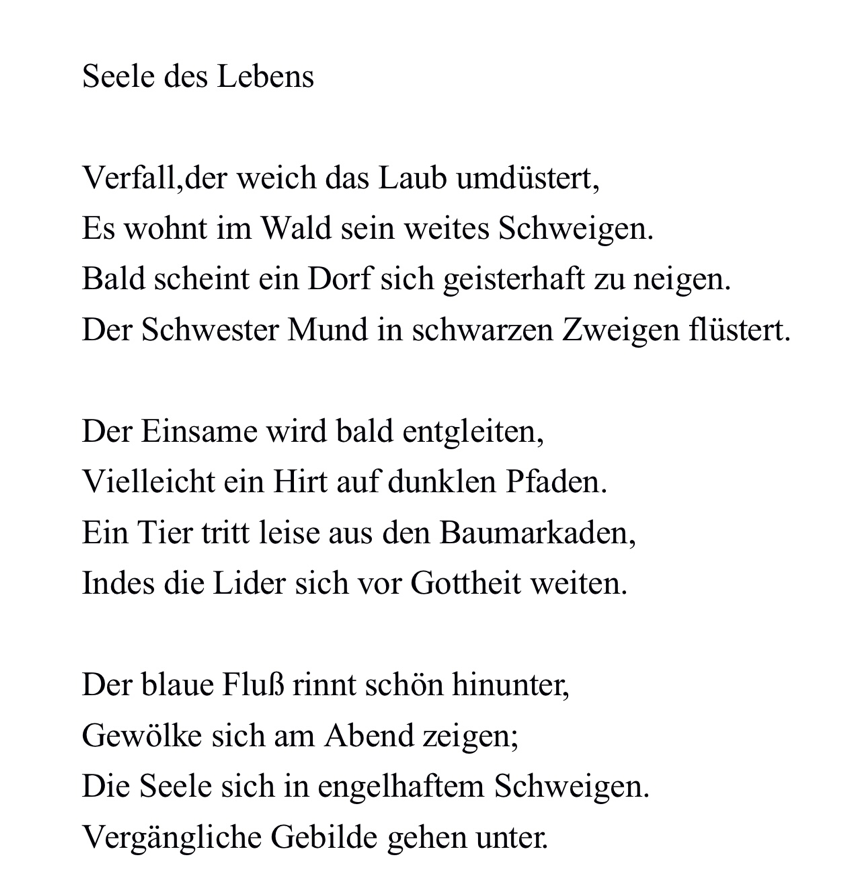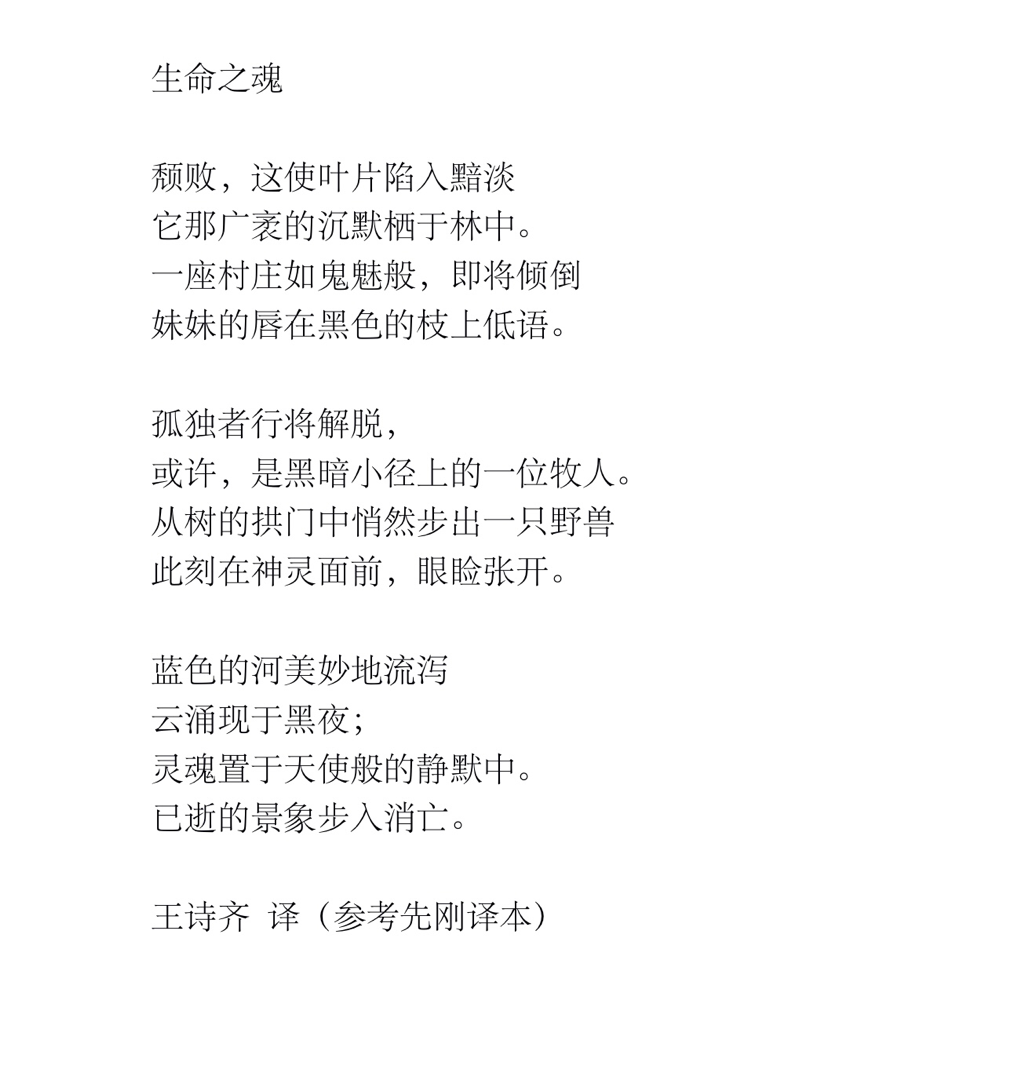诵诗 | 特拉克尔《生命之魂》
特拉克尔(Georg Trakl,1887-1914)是一位才华出众的奥地利表现主义诗人。这位诗人的一生短暂而充满悲剧色彩,他生于萨尔兹堡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对自己的妹妹格蕾特(Grete)一直怀有难言的情愫。围绕着格蕾特产生的爱欲和罪感,在特拉克尔的诗歌中不断交织和变奏。青年时代,特拉克尔在维也纳学习药剂,并接触致幻的精神药品;1912年,他进入军医院工作,并得到了维也纳的《燃烧者》(Der Brenner)主编费克尔(Ludwig von Ficker)的赏识。克拉考尔在该刊上发表作品,进行先锋性的诗歌实验。1914年,一战爆发,作为随军药剂师的克拉考尔精神崩溃,并注射大量可卡因而死亡;这一年,“漫长的十九世纪”也在毁灭性的战火中落下帷幕。

格奥尔格·特拉克尔
左右滑动,查看德语原文和中文译文
《生命之魂》一诗选自特拉克尔1913年出版的《诗作》,诗歌一、三段韵式为包韵,第二段则为对偶韵。全诗的第一个词即是“颓败”(Verfall),这一词语为全诗奠定了基调。它既有叶片凋零之意,又意味着时代的没落;其词干Fall也有神学意义,即堕落。第二句的“沉默”(schweigen)是特拉克尔常用的词语,它代表着可言说之物的无言。广袤的沉默,是在在林地与村野中横向展开的,而村庄的“倾倒”(neigen)这一动词,则具有方向性和动态感,它为画面增加了一条纵向的斜线,同时也是“颓败”的时间的具像化。类似的“水平与垂直”的对称意象,在《夜曲》一诗中也出现过:在北岛的阐释中,《夜曲》的“蓝色水面”与“堕落天使”,分别对应着基督教的水平时间观和希腊的垂直时间观,二者有一种紧张关系。而在《生命之魂》中,空间的沉默和时间的颓败则相互交织,构成死亡的图景。

格蕾特·特拉克尔,婚后姓朗根
诗歌的第二段,由一组更叙事性的画面构成。“孤独者”的解脱,与“黑暗小径上的牧人”有朦胧的关系:夜幕垂下,死亡来临。“牧人”(Hirt)的意象在特拉克尔的《埃利斯》和《安息与沉默》等文本中均出现过,时间在他的手中流逝,并堕入黑夜:“牧人们曾在秃树林中埋葬落日”(Hirten begruben die Sonne im kahlen Wald)。而应当代表死亡的“野兽”(Tier)的意象,也与《给孩子埃利斯》形成了互文关系:“一个黑色的洞穴是我们的沉默,/其中偶尔步出一只温柔的野兽”(Eine schwarze Höhle ist unser Schweigen,/Daraus bisweilen ein sanftes Tier tritt)。死亡被描写为一只野兽,它是“悄然”和“温柔”的。值得注意的是,尾句的“在神灵面前,眼睑张开”,以“眼睑”(die Lider)为主语,是描述这一器官的性状变化的,它未必包含“凝视”(gaze),或许只意味着面对,面对“死亡”和神性的微妙关系。
特拉克尔对“死亡”形象的把握,与基督宗教和德国浪漫主义的影响有关。诺瓦利斯《夜颂》的余音,在他的诗句中隐约地回响。接下来一幅寂寥无人的图景展开:河流泻下,白云涌起。诗歌的第二个色彩意象是“蓝色”(blau),在特拉克尔的诗中,它常与诺瓦利斯的“蓝花”(die blaue Blume)形成微妙的呼应。而“灵魂”(Seele),也即“生命之魂”(Seele des Lebens),则已在静默中安息。这一图景中的“静默”(Schweigen)是“天使般”(engelhaft)的静默,“天使”(Engel)缺席而又在场。在诗歌的尾句,时间的颓败抵达了终点:已经逝去的形象又逝去了一次,它彻底地“消亡”(gehen unter)了。gehen unter也是日与月的沉没;在海德格尔讲授过的《死亡七颂》中,也包含着大量的日沉景象,它也意味着命运和时间的没落(Untergang)。至此,诸形象在孤寂中坠入永夜。
无论是特拉克尔的诗歌还是他的命运,都与“世纪末的维也纳”的历史性“颓废”有着微妙的共振,但这绝不意味着他的写作能被视为病理标本。相反,内在于诗歌中的死亡驱力,在短暂的经验事物与永恒的先验事物之间建立了链接,因为死亡可能正是灵韵的终极形式。欣赏并赞助过特拉克尔的维特根斯坦,其名作《逻辑哲学论》开篇就是这样一句双关语:“世界便是它一切事实的总体”(Die Welt ist alles,Was der Fall ist)。Fall是最初的堕落,也是开端。

王诗齐,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外国语学院2021级硕士研究生,就读于德语语言文学专业,研究重点为中西近现代思想史及比较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