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帆、徐林峰 | “门槛叙事”的镜像隐喻与诗学哲思 ——评彼得·汉德克《痛苦的中国人》
本文原载于《当代外国文学》2020年第4期,感谢二位作者和《当代外国文学》的支持。为方便阅读,本公众号不保留原文注释。


内容提要:诺奖得主彼得·汉德克小说《痛苦的中国人》与地理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几无关联,作为叙事悬念的他者性身份是主人公克服内心痛苦的隐喻。“门槛”作为贯穿整部小说的叙事要素,兼具物象与意象内涵,承载了作者对人类存在和精神境遇的现实关切与诗性哲思,在时空维度勾联古今东西,在自我与他者的交互映射中寻求主体性建构,进而在虚空的诗意世界中完成对异化生存空间的修复与救赎。极具反思性的“门槛叙事”创造出叙事行为的诗学隐喻与审美事件,开掘出新的叙事可能性。
关键词:彼得·汉德克 《痛苦的中国人》 门槛叙事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Peter Handke, 1942-)被誉为“文学天才”、“活着的经典”(Jelinek),他以谜一样的文字“让读者迷惘,使文学评论家失语尴尬,甚至恼怒不堪”(Michaelis 80)。小说《痛苦的中国人》(1983)标题更是灼人眼球,极易将“中国人”臆想为“痛苦”的隐喻,贴上“东方主义”的标签。然而,细读文本,小说与作为叙事悬念的“中国人”这一偶得意象关涉不大,倒是“门槛”作为贯穿整部小说的核心物象和意象,出现逾百次,成为解读小说的密钥。故而《痛苦的中国人》本质上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门槛故事”,“门槛”既是区分和寻找自我与他者、内在与外在、现实与诗性的界限与状态,也是救赎的源泉和信仰所在。这一意蕴丰富的镜像隐喻洞开了小说的诗性哲思和阐释空间,《痛苦的中国人》由此突破德语评论界冠之的“心理故事”(Nenon, Renner 108)或“教育文本”(Oelkers 132),以极具反思性的“门槛叙事”营造“叙事行为的诗学隐喻”(Egyptien 49)和“审美事件”(Haslinger 144),是汉德克对新的叙述可能性的探索(Markolin 113)。

彼得·汉德克
《痛苦的中国人》延续并发展了汉德克秉承的“新主体性”叙事,以“自我观照和自我发现”(程心 106)的叙述手法深度勘察人类存在和精神境遇的写作路向。小说主人公安德烈亚斯·洛泽自称“门槛专家”,在各种房屋、教堂、圣殿、古建筑群遗址中寻找“门槛”的蛛丝马迹,“将门槛位置的确立作为出发点,以它们为界限诠释一个建筑乃至整个村庄的原始布局。”(CS 13-14)门槛是“物象”,也是“意象”,介于历史与现实、沉默与交谈、清醒与梦境之间的意象。在缓慢沉静的漫步观察中,洛泽体认“自我确证”而承受“灵肉撕裂”的“内心痛苦”(Heidegger, “Vom Wesen des Grundes” 127) ——漫无目的的游荡、莫名其妙的凶杀、貌合神离的媾合、锲而不舍的寻觅,喋喋不休的倾诉……在兼有临界性、异质性、矛盾性与混杂性的“阙限”状态中体味虚无的焦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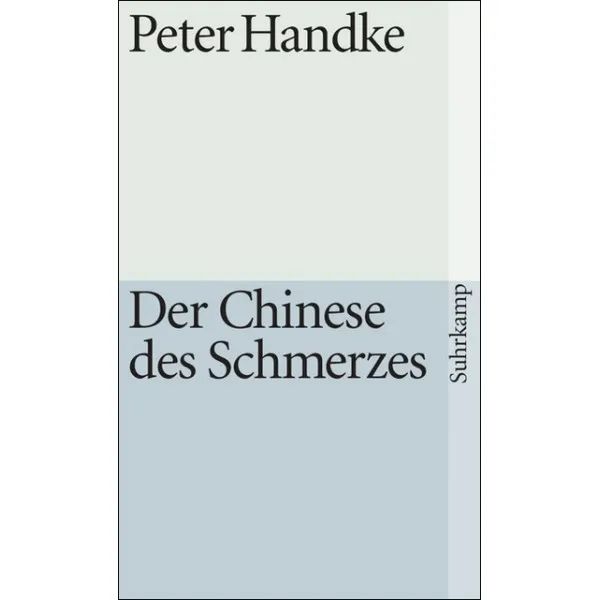
《痛苦的中国人》德文版封面
从词源上讲,“阙限”(liminality)与“门槛”(Schwelle)概念相关,liminality是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从法国人类学家阿诺尔德·范热内普的liminaires(法文,阈限)概念发展而来,liminaires则源于拉丁语limen(阙;门槛)(宋红娟 16)。范热内普指出,“门槛”既具有实体性,即屋内屋外的中间地带,亦指一个境地到另一个境地、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的仪式和人的内心世界的进程(范热内普 10)。门槛之处的人,即阙限主体,其特征是不清晰与不确定,既不在此,也不在彼,而“在社会分类之外、社会结构的断裂之处”(特纳 95),即“阙限阶段”;恰如小说主人公洛泽所处的“门槛地带”——一个尚无任何确定性,却能够连接不同区域的空间——追寻本我和显我、探索精神和实在、勾连历史与现实,它提供了小说叙述的过渡形态和延展方式,文本内外得以诗意的衔接。“门槛不是界线——内在和外在的界线都越来越多了——而是地带……‘门槛就是泉源’,无论相爱的人,还是朋友,都从其中汲取了力量”(CS73),这无疑升华了门槛的意义。
藉此可见,汉德克借“门槛”意象探讨人的存在最为重要的本质问题,正如海德格尔对“门槛”意象的思考源于对存在论差异的反思,此差异的实质是“亲密的区分”(张福海 27),即并非合二为一,也非毫不相干,而是具有“显-隐二重性”(267),在“遮蔽-解蔽(无蔽)”中完成存在的一体化运作 (Heidegger, “Vom Wesen und Begriff der Φάση. ” 301)。“区分”的栖息之处便是“两者之间”(zwischen)——使相异事物保持相互关联,又持续其唯一的和固有的区别性之所在;在充满碎裂性之痛苦、又沉静自足之所在(高宣扬 823)。“在我写的文字里,人们应该感觉到存在、生命与死亡、易逝与不朽。事物越美、越深刻、越真实,它也就越令人痛苦。”(Handke, Aber ich lebe nur von den Zwischenräumen 120) 这种痛苦是“在分离着和聚集着的撕裂中的嵌合者”,而“此种嵌合正是门槛”,它居于“之间”,古今、内外、虚实皆由它贯通(Heidegger, “Die Sprache” 24)。这恰是汉德克借助“门槛叙事”将哲学的形而上的抽象命题在文学范畴内实现“自传性反思”与“审美形象感知”(Renner VIII)相融合。
小说主人公洛泽既是一个观察世界的人,也是“被存在物观看和建构的人”(Heidegger, “Die Zeit des Weltbildes” 90)。洛泽的“自我”是以“他者”形象被区分,是一个“痛苦的中国人”,“很像‘门缝里的那个男人’:他病得很重,还去看望一个好朋友;临别时,病重的男人久久地站在门缝里,强装笑脸,眼睛眯成一条缝嵌在眼窝里,像被嵌在打磨得锃亮的眼镜里一样……”(CS133)显然,“中国人”在此作为“他者”被从“门缝里”凝视观察,正应了中国人的古话:“门缝里看人——把人看扁了”——“他病得很重”,又非常传神地刻画出“看者”固执的、窥伺的、扭曲的投影,这个投影即是掌控话语权的“本地人”刻意丑化洛泽、肆意歪曲“他者”的心迹。
在汉德克笔下,“中国人”洛泽的痛苦通过“门缝”和“眼缝”得以展露,然而,这副“中国人”的面孔对所有当地人而言都很陌生,所谓“痛苦”显然是无中生有地对“他者”的肆意强加和生造。“本地人”囿于“门槛”之内,从“门缝里”凝视“他者”,而“中国人”同样隔着“门缝”在外“强装笑脸”凝视“本地人”,彼此沟通和真实互现几无可能。汉德克在《痛苦的中国人》中以人物身份的“不确定性”对消解中心意义的哲学思考“主体之辩”加以文学演绎。如果说洛泽的当地人身份是显性的,路人对他“中国人”的称呼只是作者玩弄的小把戏,尚不足以制造扑朔迷离的身份迷雾,那么家人、同事对其若即若离,可有可无的态度则直接弱化其作为丈夫、父亲和集体成员的身份,虚化的身份作为一种能指,既隐喻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与沟通乏力,亦还原了人类存在的复杂与多变本质,导致洛泽对存在意义的不确定,他者性身份成为承载痛苦的能指符号。
事实上,汉德克所关注的,并非止于洛泽与外界的不协调经验所形成的他者性,而更多的是反思自身内在的他者。海德格尔认为,“存在论的关系中包含了与他者的共在”(Die Grundprobleme der Phänomenologie 21),汉德克则进一步强调反身他者性,并“以他者视角思考存在与缺席的本质”(Heidegger, “Aus einem Gespräch von der Sprache” 108),自身是他者,他者亦自身。洛泽向喷涂万字符的人扔出石块后,平静地观察着这个濒死之人,直到在他的脸上看到自己的脸(CS57);同样的映射还发生在他年轻时殴打过的低年级男孩、在粮食胡同撞倒的男人身上……打人或行凶时,洛泽是行为主体,而行凶之后,洛泽成为被凝视的客体。根据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他人并非现实的他人,而是自我的一个影像或者投影”(马元龙 75)。主体的自我建构通过镜像的凝视完成,“凝视不仅是一种感知机制, 也是一种最为基本的结构,它成为主体与文化秩序产生联系的方式,而或许更为重要的是,它已成为主体性赖以建构其自身的一种机制。”(Fuery, Mansfield 77-78)对洛泽而言,凝视就是存在本身的问题,自我主体在凝视的过程中发现了他者,并在与他者相互凝视的过程中建构自我,“看”与“被看者”有赖于打开“门缝”互为“敞视”,而彼此“敞视”沟通中“讲述的人就是那道门槛”(CS147)。
小说主人公洛泽既充当第一人称叙述者,同时也是被讲述的对象。他在萨尔茨堡城郊离群索居,沉迷于门槛遗迹的考古,细致入微地观察和描述目光所及的一切,从蕴含生命力的自然物中辨识出“门槛就是我的归属”(CS76)。“门槛”蕴藏在昼夜更替和季节变化中,孕育存在哲思和宗教隐喻,并从诗学层面不断跃出文本,转向新的文本(Markolin 114)。洛泽的意识和经历随着“门槛”意象肆意流转,割裂与疏离所造成的痛感熔铸在意象里萦绕不散,在“客体的任意选择”中瞬间锁定“核心对象”(Bartmann 195)。“洛泽像神秘主义者一样,正在寻找一个原点,首先从中确定某种绝对性的存在,然后获得对其哪怕只有片刻的感知”(Hamm)。洛泽在“排空”与“纯粹”中感知自然,使思想和自然频率一致,观察和讲述得以延续。
作为考古学家,洛泽关注的“是已经丢失的……却又继续存在的空位或空缺”(CS13),虚空无物对他而言至关重要。他每天研读罗马诗人维吉尔的《农事诗》,“所汲取的也并非农耕知识”,而是这首传唱两千余年的诗歌所咏唱的当下体验:“虚空!”它与史诗开头“缪斯的呼唤”(CS6)相呼应,这种“带有诱惑力的召唤”实则是“空白形式”下的“前叙事冲动”(Handke, Aber ich lebe nur von den Zwischenräumen 113)。洛泽以颜色、形状、光亮、声音和动作赋予生命“空白区域”活力,“无限开放”的杜洛克纸牌和夹在打字机中的“空白纸”都是“迎合这种审美想象的符号”(Markolin 118)。然而,这种“诗意的空白”对洛泽来说却是一种奢侈,小说的空灵与无声表面上似乎暗合了虚空主题,实则构成了可怖的“无物之阵”,他们占有各种“符号”权力和命名规则,比如把洛泽归类为“外地人”、“痛苦的中国人”而妄加歧视,并填充、涂抹和篡改历史记忆和文化认知,再现权力的匿名性与弥散性。
于是,洛泽在去玩杜洛克牌局享受“虚空”的途中,杀死了一个涂画纳粹万字符的人。正是这个标记,“造成了我所有的阴郁情绪——所有的苦闷、所有的愤懑,还有强作的笑颜”(CS54)。洛泽通过复仇万字符涂写者,试图抹去勾连集体历史记忆的符码。汉德克在凶杀场景中融入诗性象征意义,杀人行为对洛泽而言是一次“门槛体验”(Baumgart),它制造了裂隙与转折,阻断了对自然风景的客观描述和内在体验,作者因而“无法讲述一个没有冲突的故事”,正如阿多诺所言,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可耻的,如若在没有冲突的语境下讲故事,就是对诗意的亵渎,风景便会“消失”(Handke, Aber ich lebe nur von den Zwischenräumen 24)。因此,仅凭“感知、观察和记忆来创造自我和风景”是不够的,没有冲突,“美丽的沉默”终将沦为“无效的沉默”(20)。作为引发冲突的符号,万字符意味着“视线的扰乱,空间的压缩”(24),它与被洛泽撕下的宣传海报、拔掉的竞选标语牌、抹掉的教堂墙上箴言……具有同等效能,即吸引和分散人的视线,让人偏离自我本真和内心召唤。
在此意义上,谋杀行为在小说中虽然缺乏道德伦理考量,但从叙事审美角度来看,杀人动机却变得可以解释:作为叙述者的洛泽必须将“战争标记”从“(叙述)游戏中彻底清除”,从而“消除阻碍叙事过程及叙述作为维持和平形式的因素”(Markolin 118),复现空无一人的宁静,实现绝对的虚空。洛泽将死者推下山崖,回到山沟,将万字符抹掉,“那块岩石才又充满生气”(CS61)。暴力主题虽显突兀,却在诗性叙事中制造了神秘的陌生化效果,令人联想到海德格尔对特拉克尔诗歌《冬夜》的诠释:“漫游者静静地跨入,痛苦已把门槛化成石头。在澄明光华的照映中,是桌上的面包和美酒。”(“Die Sprache” 15) 在海德格尔看来,“古老的岩石就是痛苦本身,这痛苦趋向大地,关注着终有一死之人。”(“Die Sprache im Gedicht” 37) 而跨入门槛意味着漫游者“已然返乡”(“Heimkunft / An die Verwandten” 13)。洛泽一方面否定“显我”的存在,他的杀人行为和死亡梦境流露出强烈的毁灭欲,以此清空被他者赋予的存在意义;但另一方面他意欲突破自我与世界的隔离,切身体验并发现痛苦的根源。通过对万字符涂写者的复仇,主人公洛泽反抗着对事物的粗暴“标记”和“命名”,他反省自我,持守人类虚空的诗意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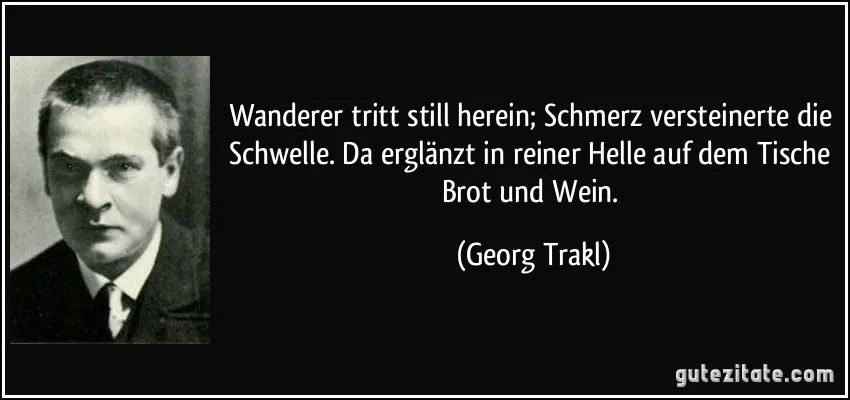
特拉克尔《冬夜》选段
《痛苦的中国人》中密集的风景描写以自然景观的“物象”重现指向自然与文明的交集,即海德格尔所述的作为“生存区域”的空间(Renner 162)。“物”是一种“聚集方式”,物之“物性”在于其“有所容纳的‘空洞’(Nichts)”,也就是说,物的空洞是为了更好地接受和容纳,因而从根本上讲,物就是“无”,这一“无”集“天、地、神、人”于一体,实现“四方合一”或“四重整体”的境界(Heidegger, “Die Sprache” 19)。然而,工具性、对象性和有用性的思维逻辑,导致对“物”的“干扰”甚至“消灭”。洛泽在漫游中观察和遭遇的一切,已成为符号的无差别重复。
洛泽陷入既不能退守自然,亦无法融入文明进程的维谷中,体验身处“门槛地带”的“悬而未决”的状态。他唯有在无声静默中“倾听”——按照《旧约》和《新约》的说法,声音和听觉是世界的基础,甚至将自己的名字“Loser”释为“倾听”者或“偷听”者(CS18),“将世界和事物带入其本质的寂静中的声响”(Heidegger, “Die Sprache” 27),以“空洞的形式”(CS6)实现“我”与物、“我”与他人、“我”与世界的连接,在痛苦之“思”中重获生之可能。他将维吉尔的《农事诗》视为心灵指南,“那些诗句使我觉得时间倒退,或者让时间获得了另外的意义……蕴含了很多大自然的规律,它们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过时”(CS24),“这些物体中的每一个都这样给我打开了通往一个截然不同的故事的大门,因为它们永远脱离了那个历史”(CS25)。在消失的门槛处,洛泽惊喜地发现了刻在粘土上的“Galene”一词,它不仅仅是“闪烁着粼粼波光的、微微起伏的海面”图像,而且成为存在的隐喻,“一种存在模式的典范”(CS15-16)。这印证了汉德克《重复的幻想》中的一句话:“为什么我总是在门槛上寻找文字或图像?门槛本身就是文字和图像”(Phantasien der Wiederholung 78)。门槛是“从贫穷匮乏到丰饶富有的过渡”(CS23),极具解放性和创造性力量,暗含重建世界的可能性。
小说最终以解构和重构的方式演绎升华出一个救赎故事。牌局后返家的洛泽“迷失了方向感”,犹如“行尸走肉”,“生活在诅咒”中(CS104),窒息到连“钟声也沉默了”(CS106)。这种异化状态无疑具有鲜明的本体论和美学隐喻,陷入卢克莱修关于“黑洞即无限本身”的想象(CS107)。诗性叙事贯通了“门槛”和“生死”之间的联系,洛泽作为叙述者在门槛区域或临界点感知虚空,以此审视和疗愈自己与世界之间的陌生、疏离,架起“门槛”内外自由畅通的“心桥”。他拜访母亲,飞往维吉尔在意大利的出生地,前往他孩子的出生地,并能够直面童年、纪念堂里阵亡的士兵和同样阵亡的生父,以及萨拉赫河承载的历史……通过“重新找回那些被抹去的门槛”(CS73),洛泽终于能够向他的儿子——这个门槛故事的见证者诉说痛苦。而在讲述中,洛泽意识到讲述者自身就是那道门槛,这是实现解脱和救赎的“肯綮”。作为贯通内外而同时保持内外之别的“中间者”,“门槛”显得坚实有力,不仅能“重新创造那些失去的东西”,而且这种门槛意识还会“把人们的注意力从一个物体转移到另一个物体,接着再从这个物体转移到下一个上,如此类推,直至地球上重新呈现出一场和平盛宴,……每天再继续循环往复下去。”(CS74)于洛泽而言,“我的故事名叫‘门槛的故事’”(C147),它“是我的寄托”(CS61),“是一种积聚在内部的力量”,并内化为“自然宗教中的一个元素”(CS74),成为救赎的力量和信仰所在。
小说《痛苦的中国人》极为平缓克制地倾诉孤独与伤痛,与卡夫卡对生命孤独和存在的反抗不同,汉德克“对存在的认同构成其叙述的基调和力量”(Pektor)。“痛苦”是“诗性生活”的“基本特征”,是一种“裂缝”(Heidegger, “Die Sprache” 24),使事物从框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既是个体创伤的宣泄,更是对现代人无所适从的危机与主体哲学式微之时代命题的回应。“中国人”虽非小说叙述主体或对象,但作为一种叙事悬念和象征,暗含对话语霸权排他倾向的反讽。作品由门槛意象延展至他者映射、虚空之境和精神救赎等诗学与哲学层面,呈现出撕裂状态的现代人对痛苦的体认与超脱,完成从自省到自赎的历程,追索人类存在的终极意义。

张帆,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中国话语与世界文学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系与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双聘教授。入选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等。从事德语文学研究、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主持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三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等。主持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荣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宝钢优秀教师奖等。

徐林峰,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德语系副教授、博士,德国柏林工业大学访问学者,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话语与世界文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从事德语当代文学研究、中德文学关系研究,在《德国研究》、《中国比较文学》、《当代外国文学》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多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