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军 | 传统的记忆与文化包容 ——奥地利文学中的传统文化意识特征
内容提要:本文以奥地利传统文化对本土文学的影响为出发点,借鉴学术界关于“哈布斯堡神话”的观点,以毕德麦耶尔时期代表作家的主要作品为例,阐述奥地利传统文化意识的基本形态及其在文学中的表现,并以此探讨奥地利文学的文化内涵。文中指出,哈布斯堡王朝的历史对奥地利社会的长期影响渗透在各个时期的文学之中,毕德麦耶尔时期的文学是大奥帝国大一统文化传统的典型体现;20世纪中期以来,这种大一统文化传统演变成为一种和谐意义上的社会伙伴关系,渗透于奥地利当代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自然也成为奥地利当代文学发展的主背景。
关键词:奥地利文学、哈布斯堡王朝、文化传统、文化包容
关于奥地利文学的探讨,学术界几经波澜,至今仍在地域疆界、作家背景、文化历史渊源及归属等问题上存有不少争议。1966年,意大利日耳曼学者克劳迪奥·马格里斯(Claudio Magris)发表了《奥地利文学中的哈布斯堡神话》一书,阐述了哈布斯堡王朝的封建文化对奥地利文学的持续性影响;1990年,奥地利作家罗伯特·梅纳泽在《社会伙伴关系的美学》一书中从政治和经济角度出发,提出了“社会伙伴关系”的概念,并以此概括二战后奥地利文学发展的社会文化特征。虽然这两位学者的研究对象是不同时期的奥地利文学,但是他们在探讨奥地利文学的文化特征方面是具有共性的。表面上看,奥地利是一个小国,探讨其文学的独立特性似乎没有太大的普遍性,况且长期以来评论界关于奥地利文学相对于德国文学的独立性问题的探讨,似乎也没有十分明确的结论。但是,有一个事实是学术界公认的:历史上一直被纳入德国文学史的奥地利文学在整个德语文学中的成就是巨大的,尤其是二战以后,奥地利文学在整个德语文坛的地位日益突出,众多作家脱颖而出,成就卓著,显示出引领潮流之势。这正是奥地利文学几度成为学术界热门话题的原因所在。

《奥地利文学中的哈布斯堡神话》德译本封面
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学的发展都离不开其特定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土壤的孕育,奥地利文学的独特性根植于国家特有的文化传统之中,并且传统的文化意识对其文学的影响是巨大而深刻的。尤其是哈布斯堡王朝长期的封建统治形成了国家大一统文化传统——即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统治下多民族统一的大一统和谐理想,它作为一种固化了的精神财富渗透在现代文明社会的各个领域。19世纪复辟时期的毕德麦耶尔文学作为奥地利文学史上的第一座高峰,非常典型地表现了这种大一统文化背景下的生活情感和文化意识特征,对后世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一、哈布斯堡王朝的传统文化及其基本特征
奥地利文学主要是在哈布斯堡王朝千年文化传统深厚积淀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不过,当哈布斯堡王朝随着奥匈帝国的衰落逐渐走向解体之后,这个千年神话留给后世的只能是深深的记忆了。正是这种对传统的记忆经过历史的洗礼逐渐演变成一种普遍的文化意识,并对文学的发展起着一种精神支配作用。对此,克劳迪奥·马格里斯对一战前奥匈帝国的社会景象作了如下描述:
奥匈帝国于1918年崩溃解体了。然而对知识分子和文人们来说,老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奥地利是一个幸福和谐的时代,是井然有序的、童话般的欧洲心脏。缓慢的生活节奏使人们 [作家们] 并不急于忘记昨天的事件和感受,他们记忆中的大奥帝国是一个“国泰民安的黄金时代”。这个千年帝国的一切似乎都是永恒的,而国家本身则充当了永恒的最高保证人。[…] 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所占的份额,都知道什么允许、什么禁止。一切都有它的标准、尺度和砝码。[…] 在记忆的演变下,奥匈帝国成为“一个古老的国家,由一位老态龙钟的皇帝统治和一群老态龙钟的部长们管理,一个没有奢望、只期求能抵御欧洲各种变革力量来维持生存的国家”。所以,人们并没有把这个时代当作“充满激情的世纪”加以缅怀:那些老人们“步履缓慢、言谈适度,说话的时候还不时地捋一捋那修剪得整齐的灰白胡须”。
马格里斯在此借用了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的回忆录《昨日的世界》中的话,把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奥匈帝国描绘成一个“国泰民安的黄金时代”,用以强调哈布斯堡王朝的历史对奥地利文化传统的重要影响。总体来看,奥地利文化传统主要体现为一种秩序意识,即把宗教、政治与社会体制融为一体的大一统文化秩序,并将其视为一种天定的、合理的、因而不可改变的上帝意志的体现。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优越的霸强意识。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曾经作为欧洲历史上最为强大的国家,在自身的文化发展过程中常常表现出一种优越的霸强意识。例如,西文中最常见的五个元音字母(A,E,I,O,U)在哈布斯堡王朝辉煌时期是这样被解释的:“Austriae Est Imperare Orbi Universo” ,意为“天下皆为奥地利臣民”,或者说,“奥地利是天下臣民的帝国”。
2.严格的宗法等级制度。奥地利在历史上一直是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国家,建立了一系列严格的宗法等级制度,对社会意识形态产生了很大影响。所谓的大一统文化秩序就是由圣父、国父(皇帝)到家父所构成的一整套社会秩序,完全体现了上帝意志,因而在公众意识中是合理的、不可抗拒的。全能的上帝不仅为世界制定了一个周全的规划,而且还为每个人都规定了位置,目的是要创造一个和谐世界,让每个人都获得幸福。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便处于附属地位,应该抛弃自我,信奉神灵,感受上帝的存在,服从上帝的意志,只有这样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从另一方面讲,天主教文化的影响促使人们更加注重情感和精神因素,从而表现出一种细腻的、颇有文化色彩的生活意识,表现在对精神理想的追求,对艺术的重视,通过艺术方式表达对神灵和幸福的向往。
3.顺从、保守、自足的社会意识。大奥帝国强盛的国力和持久的太平盛世保证了奥地利贵族阶层以及中产阶级稳固的社会地位,皇权至上和君权神授的思想深入人心,臣仆对皇权的绝对忠诚,国民谦恭克制、尊崇礼仪的行为方式以及长久以来形成的官僚行政体制等因素,为皇权统治营造了一种父权社会的家长制政治气氛。尤其是自19世纪后期,奥匈帝国皇帝弗兰茨·约瑟夫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根本不像一个威严的统治者,而更像一位温文尔雅、德高望重的长者;此外,中产阶级逐渐成为社会的主体阶层,其社会意识更趋于顺从、保守、自足的状态。
4.中庸节制、闲适快乐的生活态度。帝国统治下的大一统和谐理想孕育出一种普遍的热爱祖国、依恋家乡、美化自然的传统道德意识,不仅表现为一种追求中庸节制、享受闲适快乐的生活态度,而且更为突出地流露出一种美化乡村、讴歌自然的乡土情感。这一点在毕德麦耶尔时期的文学作品中表现得非常典型,并构成了奥地利传统文化中最富有民族和地域色彩的一部分。
以上几点仅能说明奥地利文化意识和传统的基本特征,并不包括其全部。毋庸置疑,在奥地利文化意识和传统形成的过程中,哈布斯堡王朝封建体制的长期影响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如马格里斯所言,哈布斯堡王朝变成了一个神话。这个神话经过长期的社会历史演变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社会生活情感,一种日常习俗,一种既涉及国家政治又关乎个人命运的文化意识。

1899年的奥匈帝国版图

二、毕德麦耶尔时期文学中的生活情感以及传统文化意识
拿破仑战争以后,当维也纳会议翻过哈布斯堡王朝历史的最后一页时,这个千年神话就已经开始了。尤其在以剧作家弗兰茨·格里尔帕策(Franz Grillparzer,1791-1872)为代表的文学作品中,这个用记忆建构起来的文化理想则表现得非常典型。如马格里斯所言:“毕德麦耶尔时期可以看作是哈布斯堡神话产生的时期。杂乱无序的、不太典型的、甚至还有不少缺乏文学性的表现题材汇聚一起,大致构成了格里尔帕策的创作素材和出发点。此后的整个奥地利文学,但凡披上哈布斯堡王朝色彩的文学作品,都可以追溯到这一时期。其中所表现的人文精神和艺术风格都具有这一时期的特征,就像古老的奥匈帝国时期的家庭家具一样。格里尔帕策的哈布斯堡悲剧便产生于这种古老的、昏昏欲睡的气氛之中。”
毕德麦耶尔时期是欧洲列强竭力恢复旧的封建制度的复辟时期,当时奥地利的政治气氛极为森严,强权制度压制了一切民主和自由运动,严格的新闻出版审查制度限制了作家创作和出版自由,广大民众也几乎被剥夺了参与政治活动的权利。在文化观念方面,哈布斯堡王朝统治所形成的文化传统和世界观经历了多次历史变革和政治运动之后构成了一种相对稳定的价值体系——大一统和谐理想,一直到奥匈帝国解体都还保持着原有的风貌。此外,欧洲的巴洛克文化在当时的奥地利也具有极为广泛的影响,因为巴洛克文化中感叹人生苦短和及时行乐的思想恰恰迎合了中产阶级的生活态度。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广大民众始终徘徊于个人与社会、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之中,基本上没有摆脱传统观念的制约。这一时期的日常生活和文学作品都非常清楚地表现出大奥帝国时期最传统、最典型的公众社会意识,例如,市民阶层对政治变革表现出冷漠和反感的态度;主张谦恭克制、顺从天命、躲避现实、追求个人安逸;回归个体价值、讲求内心平和等等。
弗兰茨·格里尔帕策的戏剧作品勾勒出了一幅哈布斯堡王朝的文化图景,也体现了奥地利文化的精神内涵,其影响一直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年代。他的创作主题大都显露出保守、正统的悲剧色彩,其主人公在个人意志与社会法则之间、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冲撞,最后在认识到一种超越个人的整体秩序之后找到了自我价值,在放弃个人意志和欲念之后获得了拯救。如戏剧《萨福》(1818)、《梦感人生》(1831) 中的主人公萨福、鲁斯坦等表现的正是这一主题。古希腊女诗人萨福的形象表现了艺术与生活、理想与现实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主人公为了追求世俗感情而疏离了诗人的神圣使命,从而超出了自己的行为界限,最后坠入绝望的境地: “被神灵选中的人/本不属于凡世之列,/凡人与超人的命运绝不混于同一杯盘! /两个世界你必择其一,/一旦选定别无退路! ”在《梦感人生》中,野心勃勃的年轻主人公鲁斯坦信誓旦旦地要抛开未婚妻出外闯荡,去干一番大事业,然而当他被临行前夜的一场噩梦惊醒后,便发出感慨:“富贵隐藏着祸端,/荣耀是空戏一出; /它的给予皆为泡影,/它的索取贪婪无度! ”显然,戏剧主人公一番感慨式的内心独白表达了当时社会流行的谦恭克制的思想。此外,格里尔帕策的中篇小说《穷乐师》(1848)也是通过对主人公的生活态度和命运结局的描写,表现了奥地利中产阶级乃至平民阶层的传统生活方式:其一是维也纳人乐于享受生活的天性所表现出来的轻松愉快的生活气氛,如作品开始所描写的宗教节日的快乐气氛;其二是穷乐师朴素、内敛,清贫甚至有些悲观的,然而却富有尊严的有节制的生活方式。

弗兰茨·格里尔帕策
更为典型的是,格里尔帕策的历史剧大都取材于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历史人物和故事,表现了大奥帝国的文化风貌,在很大程度上宣扬了一种爱国主义思想。剧作《奥托卡国王的兴与衰》(1823) 把奥地利描绘成一个繁荣富强、充满友爱和平、虔诚而自由的人民安居乐业的幸福家园。这一表现主题对弗兰茨·约瑟夫执政时期市民对皇权充满敬畏、对上级唯命是从、事业上尽职尽责、工作上一丝不苟的官僚机构行政气氛产生了推波助澜的影响。1848年革命之后,梅特涅执政时期所代表的旧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体系逐渐失去了其原有的影响,然而弗兰茨·约瑟夫皇帝统治的开始则标志着哈布斯堡王朝的一个全新时代,三个月前革命时期那种压抑的政治气氛已经演变成为平民对皇权充满敬畏、忠于职守、一丝不苟的行政机构氛围。可以说,格里尔帕策戏剧的主题基本上体现了哈布斯堡神话的兴衰。尽管他的许多作品是在毕德麦耶尔时期创作的,并且也明显表现了大奥帝国文化的题材,但是从思想内容上看,它们对奥地利文化意识的影响一直延续到1848年之后,直至奥匈帝国步入解体。作家在作品中宣扬了所谓帝国大一统的合理法则,并把这种法则视为一种凌驾于个体之上的和谐秩序。奥托卡,这位狂妄自大、意欲称王的波希米亚国王由于不顺从皇权统治则注定走向灭亡,因为不顺从皇权就等于违反了更高的和谐法则。因此,敬畏皇权、顺从和谐秩序便是这部作品所表现的基本思想。这里把皇权描写成神性意志的体现,皇帝既是国家的统治者,也是上帝在尘世的代言人。可见,格里尔帕策把中世纪的国家概念理想化了,即国民要绝对服从皇权统治,任何个人意志都是违反上帝意志的。此外,这部作品也表现了哈布斯堡王朝时期奥地利社会那种轻松愉快的家长制气氛,皇帝被描写成慈祥和蔼的国父形象。
格里尔帕策的另一部政治剧《忠实的臣仆》(1826) 是一部表现主人公忠于职守、不惜献身、充满英雄精神的悲剧作品。主人公班克巴努斯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匈牙利国会议员,虽然他在剧中并没有被刻画成为一位英雄形象,但却浑身充满了英雄主义精神。国王外出前授权予他要保持国家安定和平。于是,他忠于职守,竭尽全力保持国家稳定,免受内讧和动乱之灾。他命令所有机关按部就班,例行公事,就像国王执政时一样。当然,他不能替代国王执政,而只能主持政务、阅读和签署文件,做到尽职尽责。不论外界有何干扰,不论发生多大的事情,甚至他年轻的妻子被人杀害,也没能扰乱他的工作制度,表现出了一种感人的、鞠躬尽瘁的但却难以理喻的忠诚。绝对地守时,绝对地忠诚,行政事务一丝不苟,恪守日常习惯,杜绝一切个人欲望等等,甚至到了迂腐的程度,这种保守、古板、恪守旧制、厌恶变革的生活方式在班克巴努斯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成为奥地利文学中的一个典型形象。这部作品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毕德麦耶尔时期的帝国宰相梅特捏。其忠于职守、绝对服从皇权的做法,是哈布斯堡王朝保守体制下官僚机构作风的生动体现。
阿达尔伯特·施蒂夫特是毕德麦耶尔时期的另一位代表作家,创作了《五彩石》(1853)、《晚夏》(1857)、《维迪克》(1867)等一系列著名的长短篇小说,展示了19世纪奥地利社会现实生活的另一面,即闲适宁静、清新质朴、富有田园色彩、充满家庭气息的乡村生活传统。如果说格里尔帕策从历史和政治的角度表现了奥地利传统文化意识的话,那么施蒂夫特则最大限度地体现了本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从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对奥地利乡村自然景色的感受和描写达到了极为深刻和细腻的程度。一方面,他对自然界生息变化的神秘法则充满了敬畏和崇拜;另一方面,他又把自然的神秘法则延伸到人类精神和道德范畴。自然景色描写与人物描写完美地融合在一起,通过细致生动的心理刻画展示人物的不幸命运:主人公的苦闷和内心冲突常常与静谧的大自然形成鲜明对照,最终主人公以伤感的克制和放弃的方式来化解内心矛盾,求得精神平和。施蒂夫特本人性格内敛孤独,思想正统保守,生活俭朴清苦,一生都处在孤寂和伤感的想象世界中。他严守自己的一套中庸节制的道德说教思想,在作品中歌颂道德,追求和谐,崇尚大自然的“温和法则”,描绘了一个远离社会现实和城市喧嚣的理想世界,反映了当时中产阶级的传统文化意识和社会心理。短篇小说集《五彩石》前言中的一段话颇具代表性 :
人的一生充满正义、质朴、自律、理智、在自己的圈子里干练有为、崇尚美的事物、以快乐平和的态度面对死亡,我认为这一切是伟大的; 情绪的激烈波动、骇人的暴烈脾气、复仇的欲望、那种激进的、试图用行动去摧毁、改变、破坏一切,并常常由于过激而以自身性命为代价的精神,我认为这样并不伟大,反而是渺小的。……我们要看到那种温和法则,人类受它的支配。这就是正义的法则,道德法则,这就是要求人人都受到重视、受到尊敬、不受别人伤害、能够走向自己更高尚的人生道路、能够得到同路人的爱戴和赞赏、作为一种珍贵的价值受人保护并且每个人对大家来说都具有珍贵价值这样一种法则。
施蒂夫特的作品也像格里尔帕策的作品一样,处处反映了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民众谦恭克制的生活意识。他笔下的众多文学形象也都可以从《穷乐师》的主人公形象特征中引申出来:《石灰岩》中的牧师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在偏僻的小山村过着孤独简朴的生活,在普通工作中把握着自己的生活尺度。《晚夏》中的里萨赫男爵、荒岛上的哈格施托尔茨、失望的布里吉塔以及许多放弃了爱情的人物形象等都属于此类。

阿达尔伯特·施蒂夫特
此外,施蒂夫特的创作方式还突出地表现了奥地利文化史上一种普遍的乡土文化意识和传统,因而堪称奥地利乡土文学的鼻祖。自19 世纪初期,欧洲连续不断的社会动荡引发了一系列的政治变革运动,各民族独立意识增强,哈布斯堡王朝开始动摇了。然而,生活上优裕、政治上保守的中产阶级则习惯原来那种宁静闲适的生活方式,对社会动荡持反感态度,希望保持昔日那种富足、中庸、有节制的生活习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施蒂夫特的小说作品更能迎合奥地利社会的大众口味。他笔下的山川、河流、森林、乡村习俗、日常生活情趣等展示出一幅幅宁静和谐的乡村生活画面,不仅把大自然理想化了,而且还描绘了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的理想境界,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显然,他这种创作方式开辟了奥地利文学传统所特有的“乡土文学”体裁。这是一种以田野、森林、教堂和村落为描写背景的叙事文学作品,所表现的理想世界当然也是一个主观想象的脱离现实社会、远离城市喧嚣、和谐美好的世外桃源。因此,此类文学作品在讴歌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大奥帝国的辉煌盛世的同时,也明显流露出一种传统的乡土文化意识。正如施蒂夫特所言: “奥地利是不会衰落的,因为它经受住了艰难和困苦。即使它受到了屈辱,正义的思想也会在它的国土上继续生存并发射出光芒。愿上苍保佑这个美丽的国家和这座优美的城市,让它的国民……有思想、有智慧、行为有节制;让他们不要听从那种既可能导致忧虑、也会唆使人去复仇的狂热激情,让他们像两个不和的朋友那样,不再以恶相向,而是友善相待,并且从团结与和睦中……产生力量。” 不难看出,施蒂夫特在此表露他对本时代欧洲政治动荡形势所持的态度是保守的,但是他所描绘的帝国理想则展现了奥地利文化传统的最高境界。无疑,乡土文学也是最能反映奥地利文化传统的文学种类之一。在这一方面,施蒂夫特的文学成就不仅影响了本时代的社会文化意识,甚至还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三、大一统文化意识在当代文学中的延续和演变
毕德麦耶尔时期的文学是对大奥帝国的大一统文化传统的直接体现。事实上,这种大一统文化传统对后世文学的影响之深远也是显而易见的。关于这一点,马格里斯在其著作中列举了阿图尔·施尼茨勒、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约瑟夫·罗特、斯蒂芬·茨威格、弗兰茨·韦弗尔、罗伯特·穆西尔、海米托·冯·多德勒等一批作家,分析了世纪转折时期维也纳现代派的颓废文学所面临的文化困窘景象,还论述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文学所表现出的对大奥帝国传统文化的依恋倾向。他指出,尽管这些作家的创作题材各不相同,但是他们的作品所表现的精神内涵是相通的,其共同点在于缅怀昔日辉煌的文化传统,把一个昨天的世界追想为理想的精神家园:
从茨威格到韦弗尔、罗特和索克、穆西尔和多德勒,许多作家都直接或 间接地向往奥匈帝国那种文化生活方式的氛围和特征。这里不存在建立在一定标准之上的明确统一的纲领,如共同的创作动机和作品内容,而是存在一种凭借诗人灵感特有的基调和丰富的文学形式表现出来的文化土壤。这些作 家对人类的看法和思想,对具体生命问题的各种反应以及他们丰富细腻的尘 世感受都受制于传统的包袱而无法解脱,尤其不能解脱的是他们生存的双重负担,即生存于动荡不定之中和对历史现实的不满,由此他们逃避现实、沉湎于一个已经从历史上消失了的世界的生存方式和情感世界之中而不能自拔。
需要强调的是,奥地利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国家走向中立,民众趋于保守,但依然存在的哈布斯堡神话并没有停留在茨威格式的惜古之情上面,而是将那种大一统文化传统的残迹逐渐演变成了一种社会合作意识并渗透于民众生活之中,形成了一种新的现代社会文化形态。罗伯特·梅纳泽把这种社会合作意识称为“社会伙伴关系”(Sozialpartnerschaft)。这种“社会伙伴关系”明显承袭了哈布斯堡王朝时期所留下的大一统文化观念,甚至是大一统文化在当代社会的延续和演变。随着战后奥地利社会的发展,这种社会伙伴关系演变成为一种代表政府职能的意识形态,在公众意识领域具有广泛的影响。梅纳泽指出,“伴随着社会伙伴关系,在奥地利确实已经形成了一种涵盖全社会活动范围并能代表国家层面的体制,当然还只是非正式、非官方的性质,正因为如此,政治力量的对峙便脱离了任何官方支配,也不存在民主进程所导致的突变危险了——这样便赋予它高效、和谐、持续的优点。”梅纳泽借用马克斯·韦伯的说法,把这种特有的社会伙伴关系称为“最理性的政治形式”。在他看来,社会伙伴关系的功能在于避免和疏导各种社会冲突,集中和巩固现有的政治权力,避免各种变革力量形成,从而达到社会和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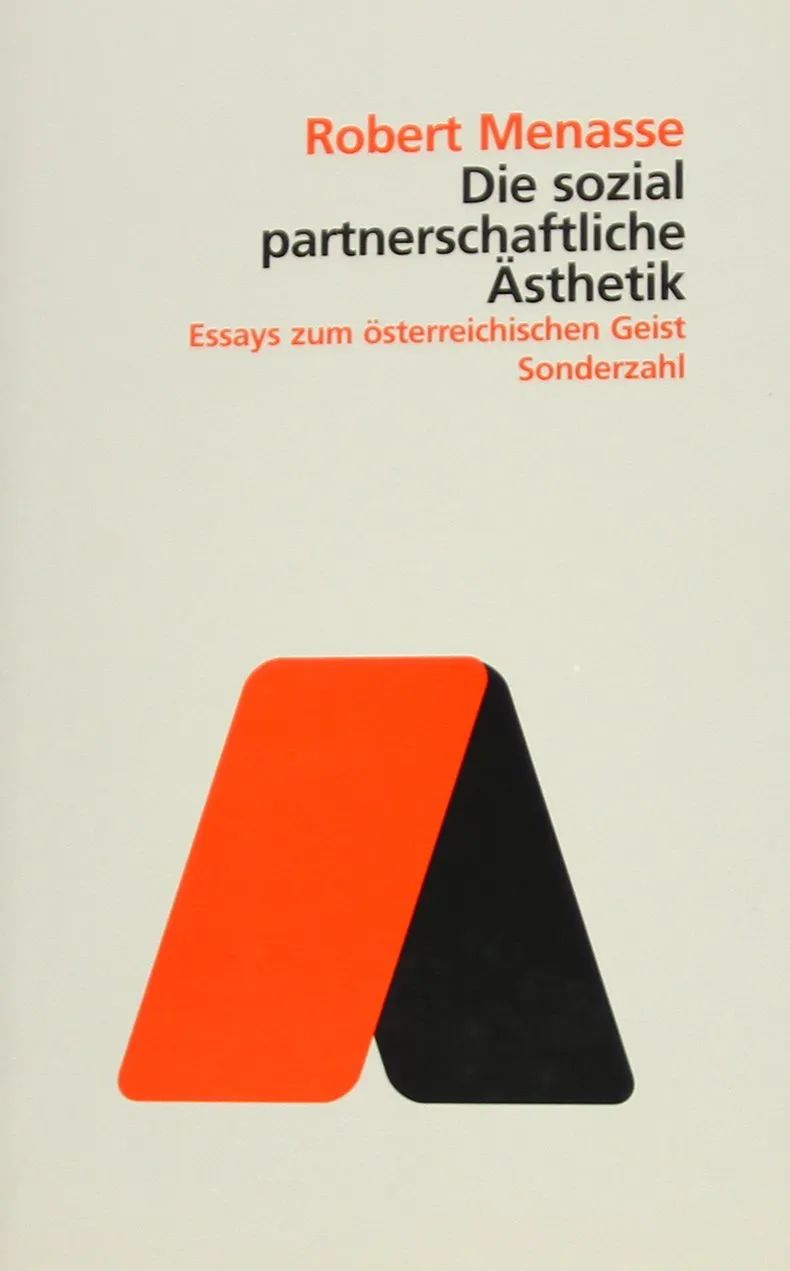
《社会伙伴关系的美学》
不难看出,受到这种社会意识的潜在影响,战后奥地利文学的发展出现了与德国文学明显不同的景象。奥地利当代文学评论家瓦尔特·维斯(Walter Weiss)指出,二战以后,虽然奥地利文坛上作家的创见各自不同,但毕竟出现了一个新老作家协作并存的局面。老一辈作家依旧遵循传统的创作模式,并以修复和颂扬一战前大奥帝国时期的传统文化体系为主要创作题材; 虽然战争已成为历史,但是人们的思想仍然深陷于恐怖的阴影之中。人们不愿意回顾历史,但又不可能忘记历史,因而长久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在这种背景下,人们把精神寄托于19世纪奥匈帝国时期的大一统文化,依恋昔日的太平盛世,以期在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中获得精神慰藉。50年代,以海米托·冯·多德勒、赫伯特·艾森莱希等为代表的老一辈作家以探索 “旧奥地利与新奥地利之间的文学联系”为己任,表现当时的社会心理与传统文化之间的瓜葛。他们的作品多以奥地利特有的社会环境为背景、以大自然为依托、以对昔日辉煌时代的回顾和憧憬为表现主题,将传统文化勾画成一种永恒的民族精神家园,并称其为一笔“伟大的遗产”。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新一代的创新派作家开始对传统的写作方式进行反思和批判。例如,格拉茨“城市公园论坛”(Forum Stadtpark)和“维也纳诗社”(Wiener Gruppe)的一大批实验派作家的反传统创作对整个德语文坛产生了很大影响。他们反传统创作的题材很广,从一开始对乡土文学的反思扩大到对当代社会各个领域的批判,政治、经济、历史、文化、自然、艺术、宗教等领域无所不及,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创作潮流。在他们看来,传统的叙事手法已经变得苍白无力,根本不可能真实反映当代社会的现实。因此,他们力图创新, 以表现真实为主导思想,形成了各种不同的艺术风格。
除了以上几位作家,奥地利文坛还活跃着一大批新老作家,在对传统与现实进行反思的创作过程中也形成了截然不同、甚至相互对立的艺术倾向。这一点恰恰反映了这个国家所特有的 “社会伙伴关系”的文化意识。

四、结语
毕德麦耶尔时期是拿破仑战争之后以帝国宰相梅特涅为首的欧洲列强主张复古的复辟时期,而这一时期的文学恰恰是这种复辟政治文化背景下出现的一个繁荣景象,堪称奥地利文学的经典时期,也最为典型地表现了奥地利的传统文化意识。另外,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正是哈布斯堡王朝走向崩溃的时代,整个奥地利笼罩着浓重的颓废没落气氛; 在这世纪转折时期出现的维也纳现代派文学在整个欧洲文坛独树一帜,但是它所流露的唯美主义倾向也无异于一首时代挽歌。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之后,哈布斯堡神话依然存在于奥地利现代社会意识形态之中,传统的大一统文化在延续和演变过程中衍生出了一种文化共识,即社会伙伴关系,从它构成了奥地利当代文化发展的基本特征。


聂军,西安外国语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多年从事德语文学研究与教学,发表学术论文、专著、编著、译著等多项成果,曾参与并主持国家社科项目;多次被评为年度优秀科研工作者,荣获多项省级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担任国家和省部级人文社科成果鉴定、立项和评奖评审专家;获2016年度“全国优秀社会科学普及专家”荣誉称号。现任陕西省外国文学学会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