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秋月 | 冯塔纳《施泰希林》中的空间诗学与时代思考

本文原载于《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感谢作者王秋月老师和《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的支持。为方便阅读,本公众号不保留原文注释。


内容提要:德国著名现实主义作家冯塔纳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施泰希林》是一部探讨传统与现代、新与旧问题的时代小说。小说通过构思巧妙的空间构建,有意突出保守贵族与开明贵族二者之间形成的反差,并通过对前者的漫画式戏谑勾勒传达作家本人的立场态度,即在时代潮流不可阻挡的前提下,从传统社会一路走来的贵族阶层应该抱持开放、从容的态度面对社会发展与时代变化。与此同时,无论在乡下施泰希林还是在都市柏林,传统与现代、自然与工业都已实现有机地相互交融。传统在可承受的范围内接纳先进,新兴事物只在必要情况下才去代替传统。面对历史发展的正确态度在于新旧事物和谐并存的中庸之道。
关键词:冯塔纳;《施泰希林》;空间诗学;中庸之道


台奥多尔·冯塔纳(Theodor Fontane)是十九世纪德国现实主义文学中的典型代表,其作品“涵盖社会各个阶层,囊括生活的方方面面”。与诗意现实主义风格相对应,冯塔纳认为,作家的使命并不在于“再现日常生活,更不是展露生活中的不幸和阴暗”。在他的作品中,现实世界经过美化和隐晦的处理后,一切问题和矛盾不再尖锐,对现实的批判在幽默或戏谑方式的掩饰下更温和。这就要求读者在阅读他的小说时不仅要关注文本表层看似寻常的人物与情节,更要揭开作家创作时刻意蒙上的朦胧面纱,思考背后的深层涵义和主旨。一方面虚构的世界合情合理,让人容易忽视潜层文本的存在;另一方面文本中存在或多或少的微妙线索,使被抹去的痕迹忽隐忽现,有迹可循。冯塔纳擅长在作品中和读者玩“隐藏与发现”的游戏,巧妙运用文字游戏和语言本身的内在力量,为小说打开多重阐释的空间。

台奥多尔·冯塔纳(1819—1898)
《施泰希林》(Der Stechlin)是冯塔纳一生中最后一部长篇小说,1897—1898年发表于杂志《海陆漫游》(Über Land und Meer),并于作家去世不久出版。对于该部小说,文学批评界褒贬不一。一部分人极端地认为,从这部小说可以看出冯塔纳创作力的明显衰退,而更多的人则认为这是“一部世界级别的德国小说”,因为它是冯塔纳一生心血和写作实践的“集大成者”。作家本人对这部小说主要内容的概述是:“五百页左右的笔墨,叙述的事情不过是一位老人去世了,两位年轻人最终走到一起。”。这里的老人是指主人公杜布斯拉夫·施泰希林(Dubslav Stechlin),两位年轻人结合指杜布斯拉夫的儿子沃尔德玛(Woldemar)和另一贵族家庭的二小姐阿姆嘉德(Armgard)的联姻。小说的题目“施泰希林”不仅是书中主人公的名字,也是其庄园的名字。附近的村庄,村庄旁那个充满神秘色彩的湖泊和围湖而立的树林,都被冠以“施泰希林”这一富有历史感的名字。“施泰希林”这一方水土以及生活其中的人,在冯塔纳的笔下构成一幅宁静祥和、岁月静好的“桃花源”生活图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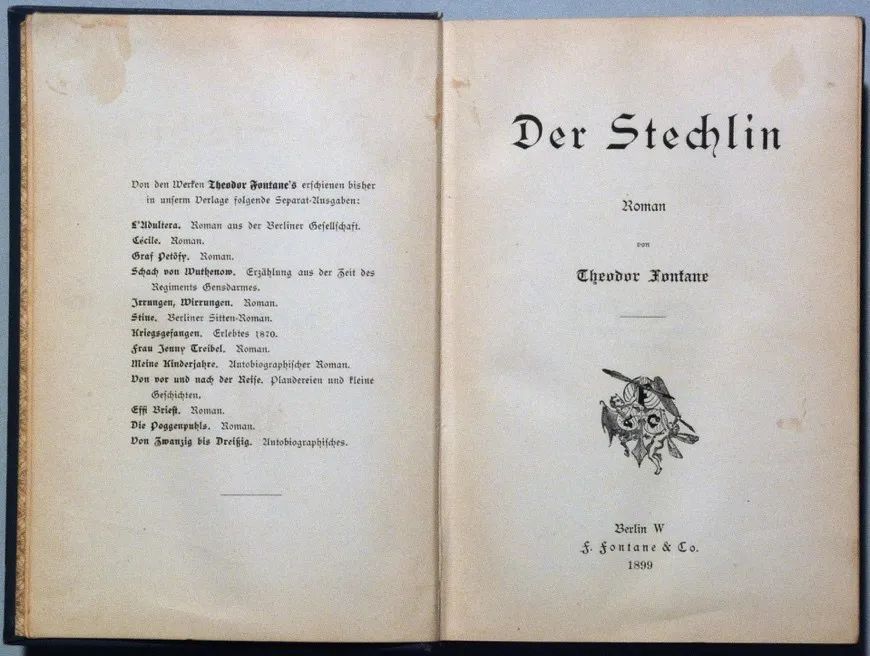
《施泰希林》第一版
《施泰希林》既是一部政治小说,更是一部时代小说。虽然小说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通篇主要以作家擅长的对话形式叙述一个贵族家庭的家长里短和社交往来,然而小说的精髓在于平淡无奇的对话中所展露的时代画卷。小说出版之后,同时代的弗里茨·毛特纳(Fritz Mauthner)于1898年11月在《柏林日报》上对小说大加褒扬,认为这部小说再次证明冯塔纳思想的广度和深度,不仅仅涉及“上帝和世界,俾斯麦和老弗里茨,普鲁士和马克勃兰登堡,社会问题和军队以及男人灵魂和女人心灵……”。
在《施泰希林》的故事背景里,19世纪末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在过往时代享有优待地位和特权的贵族阶层,对于“新时代”和“旧体制”的态度和立场无疑是作家想要探讨的中心话题。之前的研究多从人物思想性格,抑或从历史主义角度联系时代背景,阐发时代的变化与发展,却少有人注意到这位匠心独运的老者其实通过空间构建,将自己对时代的思考悄无声息地隐藏于字里行间。他的主张是:社会的传统上流阶层不要执念过去,而要以开放和淡然的心态面向未来,接受变化。对于新兴阶层来说,则要在可承受的范围内尽量接纳传统事物的存在。二者结合来看,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新事物与旧事物要实现和谐相处,传统敢于面向新的时代,而新兴事物在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过程中也不可操之过急,而是先要学会共存,再共同致力于改变。这一思想与我国春秋时期孔子的中庸之道不谋而合。下文将从内外空间和城乡空间两个维度分析冯塔纳如何借助他的空间诗学传达对时代变化的中庸思想。
《施泰希林》虽无一波三折的故事情节,却依然能将每个人物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原因在于冯塔纳对细节的极致追求。一方面,小说中“描写如此丰富而又细腻的各类宴会场景”堪称冯塔纳诸多作品之最。另一方面,冯塔纳对人物的勾勒精细到语言层面:不同教育程度、身份地位之人各自的语言表达真实而贴切,比如管家恩格尔克(Engelke)简朴且略带方言的话语可以让人感受到他对老爷杜布斯拉夫的忠心与爱护;老妇人布申(Buschen)粗犷的低地德语甚至为现代读者所不解;小女孩阿格内斯(Agnes)自然单纯的表达恰到好处地体现一个孩童的天真烂漫。然而,冯塔纳不仅通过对话语言等,更通过贴合人物的空间环境布局使人物更加饱满,同时凸显小说主旨。由此可见,环境描写在冯塔纳的小说中不只是一种背景式的存在,对于小说的阐释也至关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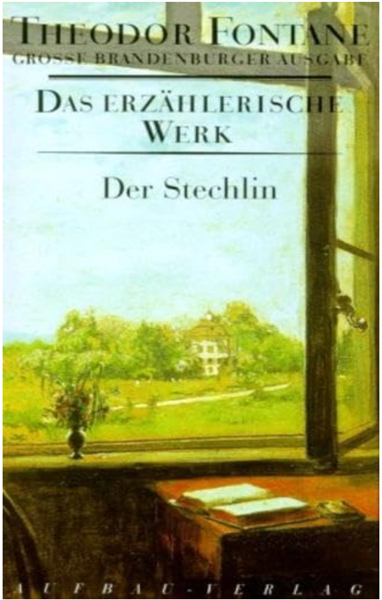
《施泰希林》(大勃兰登堡版本)封面
“冯塔纳一生都是国家政治动态的观察者和评论者”。在小说中无论传统的贵族,还是社会地位不断上升的资产阶级,他们对时代进步的态度主要分为守旧和开明两派,前者以武茨修道院的掌事阿德尔海德(Adelheid)和地道的柏林资产阶级里克欣(Riekchen)为代表,该群体作为传统社会秩序的既得利益者,宁愿固步自封,也不愿走向外面的世界,从心底接纳社会的改变。这一性格特征显著体现于人物生活空间的构建方面。同时,刻画这两位人物所采用的漫画式风格进一步表明作者的态度倾向。
文中沃尔德玛携雷克斯(Rex)、扎克(Czako)两位好友拜访自己的姑姑阿德尔海德时,作家详细描述了其住所的外部环境和内部陈设。在离武茨修道院非常近的地方,道路两边不再是杨树,取而代之的是石墙。石墙相比杨树致密厚实,没有任何缝隙,给人坚不可摧之感。石墙和院门由此构成第一重屏障。进入院中,目之所及无不透露着历史与沧桑之感。庭院风格可以追溯至三十年战争时期(1618—1648),院里几乎全是灌木丛生的碎石堆,“杂乱不堪,一片狼藉”。雷克斯将庭院与罗马的帕拉蒂尼山相联系,证明这里也曾兴盛过,然而一切又如过眼烟云,只留下令人唏嘘的颓迹。这里不仅只是表面呈现衰颓之象,修女们居住的那排房屋也十分“离奇”地嵌在残存的墙体之中,与破败的表征融为一体。更惹人注目的是墙体的窄边一侧山墙,墙体很高,“时刻面临倒塌的威胁,好似准备掩埋一切”。修道院花园的尽头默默竖立着一段倾颓残缺的木质栅栏。其实,“废墟是建筑和文化衰落的一种象征形式”,院中的破败景观无声地诉说着容克贵族在时代潮流冲击下不可避免的衰落之路。

武茨修道院的现实原型
作家不仅对外部景观描画细致,对于室内陈设的描写也不吝笔墨。因此,他的小说被赫尔曼·巴尔(Hermann Bahr)称为“家具诗学”。比如小说中一行人进入房屋之前要穿过“满是柜子包围”的门厅,这相当于第二重“屏障”。之后进入屋内,尽管窗户开着,却被“厚重的窗帘严严实实地遮着,就跟关着窗户没什么差别”。这层窗帘是将阿德尔海德与外部世界隔离的第三道屏障。
阿德尔海德试图避免与外界的一切接触和联系,在自己的世界中怡然而满足。屋内分上下两层,连接上下空间的通道在叙述者看来无法将其视为“楼梯”,只能称为一段狭窄陡峭的“台阶”。上面一层让客人暂时休息洗漱的房间是由原先的熨衣房临时改造而成。盥洗台上摆着袖珍版的洗脸盆和水壶,恰好与门钩上悬挂的六条硕大毛巾形成鲜明的反差。在楼下局促的空间中,继承得来的古旧家具甚至给人一种“荒诞、滑稽”和“过时”之感。桌上铺着厚重的桌布,窗边挂着黄雀鸟笼,钢琴上挂着一幅装饰画《威廉皇帝在利帕山头》。阿德尔海德宁愿让房间整体的搭配布局呈现一种混乱之感,也要时刻标榜普鲁士历史上曾经取得的辉煌。低矮的天花板、令人窒息的房间无不暗示屋主思想的停滞不前,犹如一潭死水,难以溅起火花。阿德尔海德孤高自傲,却住在狭小的两层楼房之中,这一反差与局促之所容纳不合尺寸的大件家具恰好形成隐喻性的对照。不论是作家还是读者,甚至小说中去修道院做客的雷克斯和扎克都能觉察其中的违和,可阿德尔海德浑然不觉,依然像往常一样为这里的一切感到自豪。比较之下,阿德尔海德对新兴事物的排斥和抵触形象跃然纸上。修道院的庭院中有鸡笼、鸭笼,还有菜园、花圃和肥料车,阿德尔海德和其他四位修女在这远僻之地自力更生。她们甘愿退回更原始的生产方式,也不愿面对先进的工业生产模式。
人物周边的空间构建以及人物置身空间的感受在此成为塑造形象的有力途径。与此同时,作家对人物空间的处理方式也是传达文本主旨的重要途径。冯塔纳对于阿德尔海德的住所,包括言行举止的描绘不乏揶揄,说明作家并不赞同以阿德尔海德为代表的守旧派贵族面对社会进步和新兴事物所采取的立场态度,文中直白明了地指出阿德尔海德的缺点:“无趣、狭隘、多疑”。她站在时代发展的对立面,通过对自己的重重封锁,妄图切断与外部的联系。然而,梅露西娜(Melusine)作为作家的传声筒指出:“最重要的是施泰希林湖教会我们的道理:永远不该忘记世间万物存在的联系。封锁自己就等于抱残守缺,而抱残守缺就是死亡”。阿德尔海德管理着修道院,而“修道院”本身就已“讽刺性地强调她的无子,暗示家族脉络的断绝,而非持续”。此外,阿德尔海德对自己的家族抱有强烈的归属感和荣誉感,自视甚高。在她眼中,家乡马克勃兰登堡,尤其是莱因斯贝格(Rheinsberg)地区优于其他地方,她将家族的希望全部寄托在侄子沃尔德玛的婚姻上,建议他“娶个本地姑娘,娶个路德教徒”,期冀以此让施泰希林家族在时代动荡的洪流中继续苟延残喘,但这样的想法得到来自同为贵族的扎克否定。作为年轻一代的贵族,他所看到的现实是:“我们所有人都会走向没落”,贵族时代必将在滚滚向前的时代车轮下成为过往云烟。
另一位守旧派的代表是防雹灾害秘书席克丹茨(Schickedanz)的夫人里克欣。身为裁缝的她在与席克丹茨结婚之后跻身于柏林的资产阶级。1885年冬天,席克丹茨弥留之际给妻子留下一笔财产以及王子河岸(Kronprinzenufer)的一栋房子。对于丈夫的临终之言,里克欣铭记在心。宁愿让房屋空着,她也不愿将房子拱手被富有却品质低下的人糟蹋,只为实现丈夫“只接受高雅正派之人”的遗愿。
叙述者形容她对丈夫临终嘱托的执行程度已近疯狂,这一特点在其室内陈设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18世纪末,随着社会的发展,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分离开来,居住空间成为房主性格和意识形态的符号表达。对里克欣来说,房屋内部空间影响甚至主宰了她的日常,“每天上午的时间属于高大的紫檀木柜”,里面摆的都是将人思绪带回过去的物件:银质奖杯象征着丈夫曾经取得的荣耀,相册更是怀念丈夫、追忆往日瞬间的有效方式。所有物品都是以往岁月点滴的凝结。“每月的第一个周一是大扫除日,风雨无阻。”里克欣一方面日日怀念过去,沉浸于丈夫往日的荣耀之中;另一方面通过每月定期的打扫试图努力挽留过去,保证所有一切不会被历史的尘埃所湮没。她和丈夫拥有相同的守旧观念,席克丹茨一生只开一种玩笑,没有变化,他的迅速离世预示着守旧的思想观念只会停滞不前,没有出路。里克欣作为地道的柏林人,和其他人一样“只会和过去比较,不与外面世界相比,……他们对外部世界没有概念,更不屑于去知晓”。另外,跳出文本,从此处的叙述口吻可以推断,叙述者依然站在一定距离之外对人物进行漫画式描绘,如“圈椅和坐椅被蒙在大花罩子下面”,“自从服丧期结束,里克欣戴的所有便帽上都别上五月花,整体穿着艳丽,使其身材更显轻飘飘的”,无不显露出一种调侃。由此推断,作家并不赞同里克欣执着于过去,沉浸于自我,与外界隔绝的行为。
与保守、古板的阿德尔海德和里克欣相比,同为上流阶层的巴尔比伯爵与杜布斯拉夫则表现出对外面世界更强烈的向往,对于新兴事物也更开放,愿意以平和的心态面对时代的变化与发展。
青年时期的巴尔比伯爵足迹遍及德国、英国与意大利,饱经世故。晚年的他由于腿脚不便倾向于静坐室内,但他不像阿德尔海德那样将自己束缚在封闭的空间,蒙蔽自己的眼界,而是将目光透过阳台的窗户,投向傍晚的天空。虽然他年事已高,行动不便,却利用窗户这一连通内外空间的途径,表达对外界的神往。巴尔比伯爵将人生的最后归宿定于当时的国际都市柏林,即使社交不多,也能在通信四通八达的热闹繁华中与外面的世界保持关联。
巴尔比伯爵一家住在里克欣出租的这栋房子的二楼,房屋立面的左右各有一个敞廊,分属伯爵和两位小姐的房间。虽然这栋房子对于贵族来说略显局促,但伯爵一家却已经对它形成一种依赖。当贝尔希特斯加登斯(Berchtesgadens)男爵夫人建议梅露西娜迁居别处时,遭到梅露西娜的强烈反对,她给出的理由是:“伦内街道是封闭的,闭塞的,目不能及远,没有流动的河流,没有穿梭的交通。但是这里,当我坐在房间,城轨的车厢一个接一个地驶来,从我面前经过,不太近也不太远。我看到,晚霞映红火车头冒出的浓烟,使公园塔楼的金丝装饰熠熠生辉。您住的周边那动物园墙壁又怎可与之相比?”巴尔比伯爵一家定居之处的具体位置和周边环境说明,他们不愿被束缚在闭塞的空间,更想与外界的变化保持联动。
杜布斯拉夫虽然大半生足迹囿于鲁平地区的一角,深居简出,却并没有导致思想的古板僵滞。从未踏出国门的他依靠时代发展与社会进步,做到在相对偏远的乡村地区依然心系世界。他对一切新鲜事物或自由的想法充满兴趣,对相左的观点也同样表示欢迎。沃尔德玛在日记中写道:“我从未见过比我老父亲内心更自由不羁的人,只是他自己不愿承认罢了”。
相比晚年的巴尔比伯爵,杜布斯拉夫则更进一步,将脚步从室内迈向室外。在傍晚时刻,他习惯拄着拐杖,戴上略皱的毡帽,踱步走向湖边,在他常坐的石凳上静心观察透过树木缝隙洒下的夕阳余晖。他坐在那里回忆一生,说明他知道人生已近尾声,贵族的命运也快走到尽头。但与阿德尔海德和里克欣不同的是,冯塔纳通过杜布斯拉夫在空间上的运动倾向,透露出他对外面世界的渴望和面对变化做好的准备。
杜布斯拉夫不仅喜欢在湖边散步,也乐于接待外来的客人。当沃尔德玛带着两位好友回家时,杜布斯拉夫早已站在门前的斜坡上等待他们。沃尔德玛和他的两位青年朋友是新一代贵族的代表,思想更加开明、开放。面对他们,杜布斯拉夫欣于接受年轻一代以及他们所展现的未来发展与时代潮流。他形容自己是“苦恼的孤寡老人”,因为“听不到什么,也看不到什么,所以希望多接触新鲜事物”。阿姆嘉德从意大利的蜜月之旅寄回的信中,字里行间洋溢着欢快与兴奋之情,仿佛平日腼腆内敛的她变成另外一个人。对此,杜布斯拉夫带着些许羡慕地说:“在旅行中……人能增长见识,也会由此发生改变”。这一切都说明杜布斯拉夫希望与外面的世界沟通、联系,从而不断汲取新鲜的精神给养。
巴尔比家族和杜布斯拉夫在小说中以正面形象出现,对他们的描摹没有塑造阿德尔海德和里克欣时的那般漫画笔调,从而间接传达了作家的立场:传统上流阶级以开放之心迎接时代的改变才是明智之道,因循守旧只会走向没落。
《施泰希林》主要围绕两次“选择”展开,一是沃尔德玛对于婚姻对象的选择,他一直在巴尔比家的两位小姐之间徘徊。第二个选择是沃尔德玛对住所的选择。在他和阿姆嘉德结婚以后,定居柏林还是迁居乡下的施泰希林庄园,一直都是萦绕在他脑海、挥之不去的潜在问题。柏林和施泰希林是小说中两处极为重要的地点,在它们之间形成许多对立的特征,如新与旧、现代与传统、世界与家乡、社会与孤立等。沃尔德玛是连接两地的纽带,他的家乡是施泰希林,而他的工作地点在柏林,两地之间通过人物的拜访看望和通信工具(信件、电报)实现信息互通。
为了呼应主旨,作家对两地的空间布局进行了诗学处理。小说开篇和作家先前的其他小说一样,首先展开对地理位置和周边环境的描述。对于冯塔纳研究,学者的共识是:“小说的开端基本交代了所有重要的元素,可被解读为后面情节的一种预示”,尤其是第一段的前几行。《施泰希林》第一段以电影中由远及近的镜头逐步聚焦,从周边环绕的森林慢慢缩近至眼前的施泰希林湖:“这片林区人烟稀少,这里或那里星星点点地散布着几个古老村庄,其他地方则是只有林务所、玻璃熔炉和焦油熔炉的森林。……施泰希林湖被平缓的河岸包围,只有一处地势陡峭,像个码头,周边是老山毛榉树,枝条因自身重量向下垂着,树梢已经触到湖面。这儿或那儿长着一些香蒲和灯心草。不见一条小船游过的痕迹,听不到一丝鸟儿的歌唱,只有偶尔一只苍鹰飞过湖面,留下倒影。这里万籁俱寂。”作家通过一系列形容词突出表现了施泰希林的人迹罕至、古老传统和静谧单调。即使这样的地方,也开始出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痕迹。这一段不仅讲明小说情节所依附的具体地理环境,同时暗含小说主旨——自然与文明、传统与现代可以并行,二者并非排斥关系。

现实中的施泰希林湖
当施泰希林父子带领客人站在观景塔眺望周边景色的时候,除了南面,其他三面都被森林包围。在森林和施泰希林湖之间犹如一道堡垒般的红瓦屋顶建筑是玻璃工厂工人的住所,他们将其戏称为“格洛布索殖民地”,住所后面则是玻璃工厂。此处工厂嵌入森林和湖泊构成的自然环境之中,与周边融为一体。这一方面证明,即使如前面所述此地少有人类活动,原始与传统保存较为完整的地方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工业生产;另一方面,参观玻璃工厂作为压轴项目被杜布斯拉夫安排在游览计划的最后,说明该工厂对当地生活的重要作用和意义。
与施泰希林乡下形成对照的都市柏林则是另外一番景象。沃尔德玛拜访家住柏林的巴尔比伯爵时,先在哈利施桥乘坐环形轨道马车,好似以一名游客的身份穿越于柏林最繁华的地区(波茨坦门和勃兰登堡门)。作家并没有事无巨细地将沃尔德玛的眼前所见一一道出,只是描写了有趣的城市一角:“到了那个令人感到奇特的国会大厦边的河岸,宏伟的山墙上画着一位二十英尺高的咖啡女郎,她头戴小巧的帽子,友好地俯瞰下面来来往往的行人世界,向他们递上一包克奈普麦芽咖啡。”虽然这一处并没有直接描写城市的繁华,读者却足以从描述中感受到柏林的现代化程度。广告的出现说明工业已经实现规模化生产,导致商品供大于求,需要向消费者推销以促进生产过程的循环,生产消费又是带动经济发展的重要一环。冯塔纳仅仅通过一处广告牌便点出柏林的高度商业化和经济繁荣。值得注意的是,城市的繁荣景象以象征着历史的标志性古老建筑为背景,二者的同时存在是社会发展变迁的有力见证。
同时柏林还有国际化的一面。杜布斯拉夫去柏林参加沃尔德玛的婚礼,住在以英国西部港口城市命名的布里斯托尔酒店(Hotel Bristol),此处作家通过下榻酒店的名称变化体现一座城市的国际化发展趋势。杜布斯拉夫说他是属于勃兰登堡大酒店(Hotel de Brandebourg)那个年代的人,一切都向法国看齐,可如今看来却已过时。这次下榻的布里斯托尔酒店从名字上已超越以往的视野,人们不再局限于邻国,而是放眼世界,将目光投向海峡彼岸。
另外,柏林也有工业化的一面。作家借人物出游的方式,即沃尔德玛陪同巴尔比伯爵、两位小姐以及贝尔希特斯加登斯男爵夫妇去艾尔霍伊斯辛郊游,以动态的视角展现那个时代的日常。众人集合之后登上蒸汽船,从船上看到岸边各式房屋应接不暇,城轨桥洞将这一切天然装裱入框,间或还有栽种着锦葵或向日葵的花园从旁掠过。而当城轨桥洞逐渐远去,取而代之的是被草地和白杨包围的道路时,“在河岸码头的地方,停泊着满载沙土的小船,还有驳船,一架挖土机模样的机器正从驳船中挖出大量碎石和沙,倒入紧邻河岸的石灰窖中。这是柏林的混凝土业,是这里的主导产业,也成为岸边的主要风景”。首先,同样是码头一样的地方,施泰希林湖边罕有小船留下的涟漪,这里却停满参与生产作业的小船,二者形成鲜明对比。其次,该段景色描写主要分为前后两部分,以是否沿着河岸行驶为界。前半段主要围绕城轨桥洞和不时出现的花园,后半段描述草地、白杨与混凝土生产。不论前半段还是后半段,都是工业化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交融出现。作家通过这段对柏林环境的描写阐明,即使是如此商业化、国际化、工业化的城市柏林,也兼具自然和传统的一面。
不管是偏远冷僻的施泰希林地区,还是车水马龙的都市柏林,都是自然与工业、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融合,只是融合的方式和程度有所不同。施泰希林地区整体保持了原始的自然面貌,玻璃工厂与焦油熔炉间杂其中。柏林则主要依赖工业生产和商业活动运转,不时出现自然风景和传统要素点缀其间。
对新与旧的探讨是小说《施泰希林》的重要主旨。对于这一问题,冯塔纳并没有直接介入并表态,而是通过环境空间的巧妙构建,即空间诗学间接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态度。人物的居住空间与其性格巧妙对应,他们“对于空间与事件的各自态度体现不同形式的感受、认知和价值观”。塑造人物的语调方式则是作家对人物性格及其思想的间接评判,借此传达小说的时代主旨。对于阿德尔海德和里克欣,冯塔纳都采用一种戏谑的漫画式风格塑造:前者选择束缚自己,主动切断与外界的联系;后者被过去所牵绊,思想禁锢于有限的室内空间。由此可以看出作家对当时上流社会阶层的含蓄劝诫:不可因循守旧,时代发展的年轮无法阻挡,以开明、开放的态度迎接社会发展才是正确的选择,就像巴尔比伯爵和杜布斯拉夫那样,向往外面的世界并敢于走出去。
其次,小说中的施泰希林和柏林形成一组鲜明的对照,看似分别代表自然与工业、传统与现代、旧与新,但这些要素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都互有交融。因此,在19世纪末社会变革不稳的过渡时期,传统的社会阶层抑或地区不能消极抵制进步事物的到来与壮大,而代表社会进步的阶层或地区也应容许传统要素的合理延续。把握时代变化的度,找准中庸之道,或许就是《施泰希林》中的空间诗学针对时代和社会发展问题暗示的出路所在。

王秋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与海德堡大学联合培养文学博士,硕士就读于同济大学与波恩大学,现为安徽大学外语学院德语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近现代德语文学。


